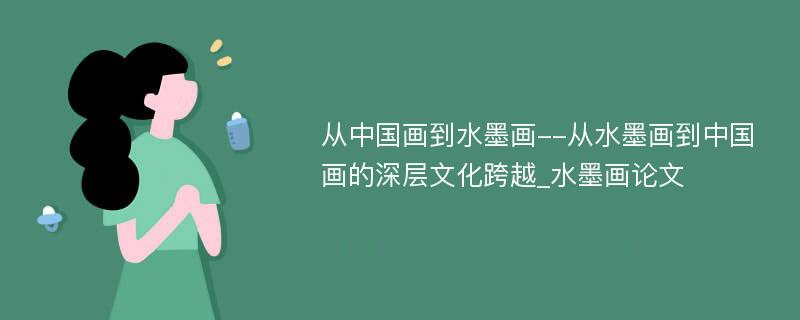
从中国画到水墨画——水墨画对于中国画的深度文化跨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墨画论文,中国画论文,国画论文,深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画是在西洋画传入中国本土后而形成的一个概念。这种用以与西洋画相别的中国画命名本身,就意味着与异质文化的横向比较与参照。因而,“中国画”从其本名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提出了跨文化命题。从中国画到水墨画,既是中国画面向现代的文化探索,也是跨文化发展的一次超越。表面上,水墨画在呈现当代文化审美观念之中,去除了中国画的文化身份,骨子里显现的则是水墨这种媒材所能承载的多种非汉语体系的文化内质。从绘画的媒材属性而言,水墨画已疏离了传统中国画以书法语言作为笔墨语言的价值体系,而更加凸显了造型、图式、图像语言在绘画中的审美作用。从绘画的文化属性而言,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媒材已渐渐失去笔墨语言的文化内涵,而仅仅把宣纸和水墨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媒材特征。
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性转型改变了笔墨的价值系统
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性转型,主要包括两个过程。其一是从20世纪之初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化的过程,它将西画的造型、色彩、透视等再现性的观念与技巧引入中国画,从而加强了中国画表现现实的能力,并在这种表现过程中更深刻地体现了从“出世”向“入世”的文化观念的转换。其二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反写实”这个新传统为目标的现代化过程,它凸显了艺术主体在表现审美对象过程中的自主性,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彰显了媒材在画面上的独立审美功能。这两个过程都促使中国画从传统的以笔墨个性为核心的价值判断转换到以图式个性和笔墨个性相结合的新的价值系统。
中国画在20世纪的这种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20世纪上半叶,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中的中国画,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逐步接受了西洋写实绘画的影响,西画“对景写生”的观察方法和“焦点透视”的表现方法为传统中国画注入鲜活生动的时空变化,并因尊重感受的真实性而开始较多地运用水墨呈现现实的境界。
吴庆云是20世纪初开始注重观察和感性表达的山水画家,在《雨景图》(1903年)中,他不仅第一次在山水画史上表现了乌云,而且在画面上表现了唯一一条视平线(即湖平线),这和倪瓒三段式太湖出现的三个以上的视平线有质的区别,因为只有唯一的视平线,画面才具有深度感。他善于表现烟雨之景,“用水渍纸,不令其干,以施笔墨”,这实际上是因尊重视觉的真实性而减损了传统用笔的力度。30年代,岭南画派高剑父、陈树人的作品充溢了更丰满的现实时空。《渔港雨色》(高剑父,1935年)清晰明确的视平线和占据画幅一半的港滩,本就是特定时空的自然截取,水彩画式的渲染、扫刷疏离了传统山水的假定程式和笔法皴法。《后湖柳色》(陈树人,1934年)似临景写生,保留了鲜活而丰富的现场真实感,雪山映照下的天空不再以白为空,呈现灰蓝色的面,画幅中间的柳树矫健挺拔,绝无传统树法程式,完整清晰的视平线,展示了特定视角下岸、湖、树和雪山的空间关系。倡导写实主义的徐悲鸿在他的《漓江春雨》(1937年)中也表现出感性的真实性,视平线略低于画幅的中轴,笋式山形按渐远渐小的消失方式一字排列在视平线上;霏霏烟雨中,取消了任何用线的地方,只有墨的浓淡、渗化表现出春雨中空气的透视关系。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尊重眼见为实的视觉真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的主流美学思潮,当这种思潮演变为一统的文艺运动时,虚拟时空、超脱现实的传统山水画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了“改造”。李斛的《长江大桥赞》(1954年)再现了在江中建桥的夜景,在空间上以宽阔的江面和辽阔的苍穹为画面的主体,高高的脚手架和长长的灯光倒影构成这幅超宽画面的纵向构成,这种深度空间无疑是某个固定视点的再现,它在时间上对于灯火通明的江上施工场景及江边城市灯火的描绘,都是传统山水中不曾出现也难以用固定皴法去表现的。谢瑞阶的《三门峡地质勘探》(1955年)以写实主义主题性创作模式取代传统山水创作的随意性,广角镜式的超宽画面给视觉带来最大的深度感,长江宽广的河面与汹涌的激流在这纵深的视域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画面山石也具有一种触摸感,皴法不仅表现出山石的坚硬度,而且表现出体面的阴阳向背。
李可染自1954年起开始了直面现实山水的写生实践。这种对景写生的过程,实是他根据现实感受对传统笔墨的整合过程,传统皴法的程式消失了,代之的则是对传统笔墨那些纯粹质感和表现力的体悟。这种笔墨体悟通过他个性的选择,被强化地运用到对山林幽深的质感和逆光光影变幻的感受表达中,他此后的创作实是用积墨语言去放大加强这两个现实感受,并力求提炼、升华到浑厚、苍茫、幽深的精神境界。狂放不羁、充满浪漫激情的傅抱石,在他的《黄河清》(1960年)、《待细把江山图画》(1961年)和《天池林海》(1961年)等作品中表现出一种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来源于他对感受真实性的尊重,他的“思想变了,笔墨就不得不变”表达了现实感受对于笔墨变革的激发作用。的确,他在《黄河清》中表现的土质地貌、在《待细把江山图画》中描绘的扑面而来的裸露山岩以及在《天池林海》中刻画的白山雪松,都因审美客体的变化显现出笔墨、结构和造型的区别。“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石鲁,在画史上首次将秃秃的塬顶、横断的立土、缺乏绿色植被和烟云缭绕的地貌特征不加修饰地表现出来,他创造性地用直、硬、圭角外露的颤笔及墨色交融的语言塑造出横断高原的立土质感。
这些写实性画面所构筑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于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和现实事件以及由它们揭示出来的人改造自然的一种关系,这和传统中国画“以形媚道”体现出来的天人合一、和谐无为的精神恰恰相抵触。现实主义运动之所以能给中国画以深刻的影响,就在于它不仅为中国画时空观念的转换带来一种普遍性,而且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使遁隐、出世、淡逸的传统文人画变为入世、观赏、参与乃至表达现实感受的山水,这种文化定位的改变,才在根本上引发了中国画对视觉图式的关注。
山水的极简化既是对写实性山水的高度提炼和审美修饰,也是山水画价值观从笔墨个性的视点转向图式个性的重要过渡。一方面它相应减少了山水的空间深度,山水自然形态一些影响视觉表达的细节被省略了,另一方面在从写实性时空转换到极简化图式调度的过程中,为适应视觉上的调整而进行了笔墨上的新变,大笔头的墨块、色块和渲染的出现,开始减少了用笔的密度,水性和纸性的材料特征被强化出来,传统意义上的“笔墨”开始化解。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一些画家的实践就开始了图式方面的探索。譬如石鲁的《东方欲晓》(1961年)不仅简洁到只有窑洞的门窗和树这两个形象,而且进行了平面化处理。钱松嵒的《红岩》(1960年)不仅强化夸张了色彩对主题表达、意境烘托的积极作用,而且简洁化构图与黑、白、灰的运用为山水画带来了现代感。石鲁、钱松嵒画面的这种极简化趋势,在上世纪80年代初逐渐演化为山水画的一种普遍样式,这种样式客观地体现了简洁、精练的现代视觉要求为社会普遍接纳的事实。
提倡“横向移植”的周韶华更加偏重中国画视觉冲击力的尝试。他的《黄河魂》(1981年)几乎没有勾皴,代之的则是大笔头的墨块、色墨或色块之间的混融,作品以色与墨、水与墨、水与色的渗化交融留下的水迹渍痕,表现出黄河波涛汹涌澎湃一往无前的气势。周韶华在他的“大河寻源”的组画中揭示了水、墨、色、纸之间材质美感的可塑性,而不单纯是笔性(当然笔性赋予了色墨混融的生命力度和精神意识)。显然,周韶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进行的艺术探索,促进了中国画从笔精墨妙这种微观价值观的解放,图式和材质成为此后中国画价值判断的重要变量。他的《夜探唐古拉》(1993年)实际已表明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画的一条探索方向,即在山水画的简化图式中抽象出构成意味,用点、线、面的构成关系探索自然山水的永恒结构和画家内在的精神空间。
吴冠中的水墨画完全跳出了中国画的笔墨语系,“不表达画面内容的笔墨等于零”,既是他对于中国画笔墨的理解,也是他从水墨画的角度对于中国画的价值颠覆。而他的“风筝不断线”,则形象地表述了在具象中凸现形式构成的水墨画的创作理念。就吴冠中的个案而言,他的水墨画着眼于图式个性的建构,许多作品既可以看作从具象的自然中抽象出形式结构的过渡,又可以看作是由抽象向具象的嬗变。他遭到非议的是非传统规范的线条和墨块,其实他具有运动感的流畅线条和排笔板刷产生的面,是对笔性、纸性泛书法状态的现代阐释。中国画至吴冠中已完全改写为水墨画。①
殖民文化对水墨画跨文化命题的提出
如果说“笔墨等于零”是中国画在20世纪进行“横向移植”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对于传统的渐进消解,水墨画的概念是从传统内部逐渐向外演变的结果,那么港澳台水墨画则完全是从殖民文化的外在文化环境对于传统中国画跨文化表现提出的命题。
20世纪60年代,香港画家吕寿琨首倡水墨画运动,他认为“水墨画,就是使用水墨表现自我的一种绘画”,既是国际现代艺术,亦是中国现代艺术。在媒介材质上,可以有观念上的突破;在思想精神上,可以是“较倾向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也可以是“较倾于西方的”。因此,水墨画没有固定不变的定义,并“必随时间与画家而改变”②。吕寿琨的现代水墨画理念,不仅将传统中国画的“笔墨”还给水墨泛媒材本身,而且赋予了这种载体以多重的文化内涵。吕寿琨的艺术理念,无疑为以后数十年港澳台现代水墨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几乎和吕寿琨同时,刘国松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中国画进行了现代语言转换,他在台湾创立的五月画会,在真正意义上将先锋者的水墨画探索变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水墨画浪潮。按刘国松的理解,“笔墨”之“笔”就是“积点成线”,“笔墨”之“墨”就是色彩。从笔墨到水墨,刘国松将充满老庄道学观的“文言”笔墨解构为“白话”水墨。不仅如此,刘国松还将人类对于月球的探索直接表现在画面中,并从此将视点移至太空,从太空观照球表,以充分展示他通过揭撕纸筋而造成具有神秘感的山水肌理。刘国松对笔墨中国画这种从语言到内在精神的转换,既体现了20世纪中国画家对于表现人类精神与视阈不断扩展的思考,也使水墨文化第一次在西方文化中获得了认同感,水墨由此而成为能够被西方文化与现代审美取向所释读的中国文化象征。
具有跨文化意义的水墨概念,并不仅仅疏离了传统的笔墨语系,提升了个性化的视觉形式在水墨媒材运用上的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全球化语境中融入更多非汉语系的文化观念与审美诉求。作为一种运动,水墨画之所以从香江兴起,是因为传统中国画在英属殖民地领土的香港只能作为一种民间文化而存在。传统中国画在殖民文化中的边缘化,必然导致中国画的去身份意识与中国画传统文化内核的逐渐消解。因而,水墨画跨文化命题,难以在中国内陆这个中国画源远流长的大本营中提出,而只能在排斥中土文化的深度殖民化地区(港澳台)获得新生与发展的土壤。
港澳台与内地水墨画的互动发展
尽管在中国画内部因现代化的转型而逐渐形成水墨画现象并终于以“笔墨等于零”而确立水墨画概念,但有关“笔墨等于零”的讨论仍然成为世纪之交内地守护传统与突破传统的一次文化论战。这表明,在内地中国画是中国绘画的主流形态,水墨画还是处于中国绘画次要地位的非主流样式。
除了中国内地从传统中国画内部逐渐演化出来的水墨画发展,港澳台水墨画概念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内地,并刺激了内地水墨画的演化。刘国松于上世纪80年代在内地首次举办水墨画个展,从而把港台现代水墨的观念带到内地,一时开国内水墨风气之先。他的水墨观念给当时内地美术界以巨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来自于刚刚恢复对于传统笔墨认识的中国画家面对他作品时的失语,中国画家们从笔墨的角度一时还无法对他的作品进行判断和评析。刘国松对于水墨的理解和作品中表现出的宇宙意识,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都显得异常新鲜。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初刘国松的水墨观念还只是对于内地画坛的一次启蒙,那么直到80年代中期,内地水墨画运动才在85新潮美术中获得广泛的回应。其原因是,一方面像潮水一样涌入国门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冲决了传统艺术观念,中国画从来没有像那个时代那样陷入一种生存的危机;另一方面诉求于观念更新的中国画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中也获得了叛逆精神与走向现代的通道。谷文达最早赋予水墨以纯媒介观念,并努力消除文字与书法的传统美术内涵,使水墨获得一种现实的批判力量和当代艺术的形态。而石果、阎秉会、刘子健等人探索偶或性、抽象性与潜意识性的实验水墨,又鲜明地展现了水墨画由媒材革命而展开的更为深入的观念更新,以及水墨画作为一种“开放”的文化使命而具备的审美独立性。
内地水墨画虽受港澳台水墨画的启蒙而勃兴,但形成的条件与文化意义不尽相同。港澳台水墨画的产生是在殖民文化语境下进行文化变种的结果,即水墨画承担着表达多种非汉语文化体系的人文诉求,这种诉求在远离本土文化的殖民地获得了一种自然的媒介还原。而内地水墨画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种文化象征,它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诸流派的冲击下而促成的一种自我变革,它并不必承担非汉语文化体系审美表达的使命,而体现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主体意识的现代自觉。
港澳回归祖国后,港澳英属、葡属文化的主体性悄然发生了一种改变。随着与内地文化艺术交流的日益广泛与深入,一方面港澳台的中华民族传统艺术开始重新获得重视,传统中国画正逐渐改变被边缘化的地位;另一方面内地现代水墨的各种发展态势受到了港澳台艺术家的关注,港澳台艺术家参与内地的水墨展示活动也有增无减,水墨画学术探索的回流现象日益明显。比如,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连续数年举办的水墨中国艺术展,几乎每届都邀请港澳台艺术家的参与;深圳已举办多年的水墨双年展也起到了连接内地与港澳台水墨画资讯与互动的作用。加之一些从内地移居港澳台的水墨艺术家,新身份所代表的仍然是内地水墨画的创作理念。这些无疑都缩小了港澳台与内地水墨画的差距,海峡两岸多地水墨画的互动发展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机制。
新世纪以来,港澳台与内地的水墨画已构成中国绘画一种完整的艺术生态。当下港澳台水墨画既有抽象水墨,也有观念水墨、装置水墨和影像水墨,这种结构几乎与内地水墨画的发展态势相近。但这种相近并不是失去地区性的无差别。相对而言,内地水墨画仍然以坚实强大的中国画为依托和比照,中国画仍然成为水墨画发展的重要资源与路向调校的参照坐标,而港澳台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是港澳台比内地的水墨画更具有开放性的天然条件。作为社会高度发达的移民地区,港澳台多种族文化的聚居与混融造就了这些地区与内地不同的文化类型,时尚、轻快、新颖,无所顾忌、不择手段,依然是港澳台水墨画的审美品格;而内地的水墨画也总是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沉重性,深沉、厚实、恢宏,享受传统中国画的资源支撑与受其制约,也便构成了内地水墨画的审美特征。这种审美类型的区别,无疑来自于内地与港澳台文化主体的差异。③
面对当下与面对国际的共同课题
虽然港澳台和内地水墨画产生的文化条件与历史进程并不相同,但改革开放已获得世界瞩目的内地和港澳台却拥有了面对当下与面对国际的共同课题。
从面对当下而言,水墨画虽从中国画内部蜕变而出,却也更具有这个泛媒介时代的艺术共性。这是一个媒介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混合材料的时代。电子信息的网络化和高速传播,已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复合材料的广泛应用,使建筑、航空和交通获得了迅猛发展,人类由此得到了上天入地的更加自由的伸展。艺术也不断从相互隔离的媒介走向复合重组。不同艺术门类间的边界在模糊和扩大,甚至于从物质媒介走向虚拟媒介。在某种意义上,水墨画便是从中国画传统媒介中走向复合媒介的一种现代性拓展。因而,在所有的现代水墨作品里,都可以看到当代艺术家共同探索的一条鲜明路向。这就是,一方面用宣纸与水墨媒介和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一种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将宣纸与水墨进行现代性的媒介重组:或加入其他媒介其他溶剂,或置入现成品,或从平面走向空间装置等等。总之,水墨画在当下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方的一种重要复合体。“传统”在这个复合体中重获新生,而“现代”则在这个复合体中承续了传统的文脉;“本土”在这个复合体中进入了当下,而“外方”通过这个复合体也传递了具有外方文化特质的东方情韵。
从面对国际而言,水墨画的开放性无疑比以笔墨为价值判断的中国画更能进入全球化视野,这不仅表现在水墨媒材的当代性混融与当代性审美经验的直接表达上,而且表现在不同国度与不同种族都可以通过这种媒材表达他们各自的文化理念与审美个性。也可以说,水墨画是新世纪中国文化进行全球化辐射的重要载体。当然,就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水墨画尚存一些亟待探讨的命题。比如,水墨语言是否存在自身的评价标准?如果有,又如何建构自身的价值体系?即一个成熟的具有历史文脉的绘画种类是可以通过系统的价值判断进行优劣的比较和筛选的,否则,水墨画作为一个绘画种类便难以独立。又如,水墨画的未来是否存在更多的民族的文化身份?也即水墨仅仅作为一种艺术媒材时,能否更快地被其他国度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他化”。除了日本水墨、韩国水墨,我们能否在其他非汉语文化圈获得更多的印证。再如,水墨画作为一种开放的艺术种类,已经从“架上”走向“架下”,水墨多媒体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诉求文化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水墨的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关系?等等。
这些命题,毫无疑问都涉及水墨画在国际上的发展境遇与开拓空间问题。水墨画的国际化与国际影响力,已成为这个世纪一个新的国际文化的生长点;水墨画的深度跨文化研究与推广,也必将成我们更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与文化使命。
①尚辉.从笔墨个性走向图式个性——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程及价值观念的重构[J].文艺研究,2002(2).
②吕寿琨.国画的研究[M].香港,1956年序.
③尚辉.殊途同归——香港与内地水墨画之比较[A].2010港澳视觉艺术论坛文集[C].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标签:水墨画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跨文化论文; 中国画论文; 艺术论文; 美术论文; 山水文化论文; 刘国松论文; 东方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