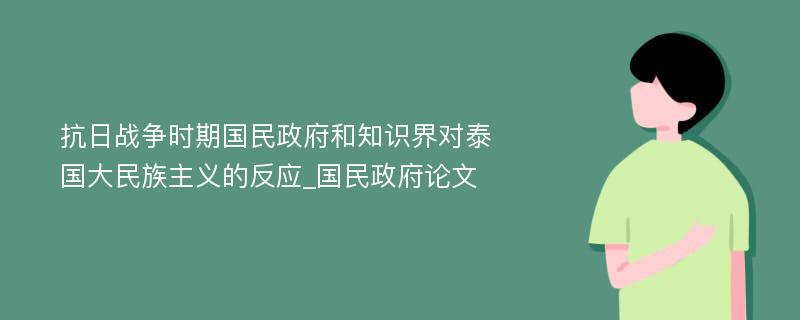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之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泰族论文,知识界论文,国民政府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76年,法国人戴·哈威·圣丹尼斯出版《中国的哀牢民族》,首次提出了哀牢的后裔泰族人建立了南诏(即南诏泰族王国说)的观点。1885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T·D·拉古伯里发表《掸族发源地》,力倡“南诏泰族建立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德、美等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纷纷著书立说,谈论泰族早期历史,逐渐把南诏史移花接木地搬到泰国或泰族古代史。其中以美国传教士杜德(W.C.Dodd)发表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s,Iowa,1923)和伍德(W.A.R.Wood)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London,1926)影响最大。《泰族——中国人的兄长》于1932年译成泰文,在泰国流传很广。《暹罗史》则是第一部用英文写成的泰国史,其古代部分集拉古伯里以来西方学者观点之大成并加以系统化,在英语世界里有着广泛的影响,许多东亚史著作转述的“南诏泰族王国说”往往采用伍德的说法。由于这些学者的影响,到20世纪30年代,“南诏泰族王国说”已获得了广泛的流传和认可。①泰国学术界对此更是全盘接受,几十年来这一观点正式载入泰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泰国人。②
上述这些观点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③但在抗战期间,它却成为暹罗(泰国)当局用以实现其“大泰唯国主义”(大泰族主义)的有力武器。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初期,以銮披汶为首的泰国政府,大力宣扬“大泰唯国主义”,并“以守则的形式发布了全民必须遵守的‘唯国手则12份’命令”,竭力怂恿泰国去“统一”所谓邻国中的“一切泰人”。由于全力推行“大泰唯国主义”成为当时泰国政府的国策,于是“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在泰国国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噪与喧嚣。1939年5月25日,狂热鼓吹“大泰唯国主义”的泰国艺术厅厅长銮威集瓦他干发表广播演说,泰族“在广东约有70万,广西约有800万,贵州约有400万,云南约有600万,四川约有50万,海南约有30万,越南的东京、老挝约有200万,缅甸约有200万”。他还说:“滇、黔、桂、粤至越、缅各地的泰族,闻暹罗亦有泰族而喜,故须唤起泰族,团结合作,领导泰族,进于繁荣。”銮披汶在1939年“六·二四”广播中也称“我泰语在暹境以外者,有二千余万人,大都散布在中国南部滇、川、黔、桂一带”,要收复失地。在其改国号告人民书中更是充满了大泰族主义的胡言乱语。在泰国政府的鼓励下,一批宣扬“大泰唯国主义”的历史剧和歌曲应运而生。这样,通过“宣传机器、文艺演出、各种著作等途径的宣传”,所谓“汉族压迫泰族南迁说”就深深地印入了泰国人的脑海之中。④
泰国当局的大泰族主义言行,对我国有明显的领土要求,严重威胁到我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引起了处在艰难抗战中的重庆国民政府、西南地方政府及中国知识界的警惕,引发了我国政府及知识界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反思,促成了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问题的重视和民族政策的改变。然而长期以来,这个问题仍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愿拟就这一问题做一探讨,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在抗战爆发前,政府对云南究竟有几种民族,各民族的分布情况如何,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怎样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尚未有过深入调查研究。经营开发边疆民族地区的方案无从着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泰国当局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政府的密切关注。国民政府首先密电云南省政府“饬查详情”,以了解傣族的实际情况。国民政府外交部在致云南省政府的密函中说:
案据报告,暹罗自改称泰国后,对我云南之泰(傣)族人极为注意……查本部前曾迭据报告暹罗改称泰国之动机,在以大泰族主义号召,并宣称泰人散居我西南各省者为数达1950万云云,显欲效希特勒大日耳曼民族主义之故,知其中别有用意,自应加切注意。究竟贵省南部是否有所谓泰人杂居?如有,其散步之区域如何,人数若干以及有无特殊活动情形?相应咨请查明,饬查详情,见复为荷。⑤
可见,国民政府对大泰族主义的阴谋是有清楚认识的。而正是大泰族主义的言行促使国民政府开始关注西南民族问题。江应樑指出:“自国民政府有边疆政策以来,勿庸讳言的,其注视的重心,是在西北而不在西南……自抗战以后政府西迁,西南边疆及西南边民的实况,始渐为执政诸公所明瞭,才深觉得这广大区域与复杂的宗族,实在不能不有特殊的治理方策和开发方案,实在应当和蒙古新疆作等量齐观,于是政府治边的范围乃始扩大,把西南的苗夷区域算作了边疆,把西南的苗夷人民认作了边民。”“抗战后政府对西南边区政策的转变,是一个智慧进步之举,承认西南边疆的特殊性,是极为为合理的。”⑥显然,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从过去只重视蒙藏问题,发展到认识西南民族问题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相当棘手和重要的,进而更加重视西南民族问题,是很大的进步。而促使国民政府发生这个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无疑就是对大泰族主义的忧虑和警惕。
云南省政府在接到外交部秘函后,即令云南省民政厅“迅即转饬本省南部各县县长,详确查明呈覆,以凭汇转!”⑦云南省民政厅指出:“暹罗改名泰国(Thailand),其民族名,国籍名用泰Thai,实含有希特勒所倡导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并吞捷克之野心,以谋吸收我西南边区之大部民族……在未改国号以前,(泰国国务总理銮披纹)曾旅行越南考古,详询越方人事登记职官关于泰族在越南及中国西南之人数。其改国号告人民书中云:‘在中国居留之泰族人,与汉族比较疏远,有一部甚至划一特别区域,不受任何方面之统治。’弦外之音,不啻视我车里、镇越等地聚族而居之区域如苏台德区。”当时,云南省民政厅对泰族的认识仅局限于美国传教士杜德《泰族》一书的记载,认为有文字之泰族或佛教徒之泰族,在云南境内者汉摆夷60万人,水摆夷40万人,其他之水摆夷、花腰摆夷、龙家、水家等100万人。但是,对其大概分布及人口比例,云南省民政厅还是大致清楚的:“惟是水摆夷之聚居,以车里为最多,约占该县人口总数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镇越、江城、南峤、佛海、六顺及宁江设治局一带,数亦约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此外,澜沧地方则有水、汉摆夷交处,景谷、景东则亦有汉摆夷在焉。又腾龙边区,则为汉摆夷所聚居。即开广、普思以及石屏、元江亦有摆夷。是知内部各地亦有所谓泰族者存在,不仅西南一部而已。”在云南省民政厅正拟办理的时候,禁烟终查员彭钊函报“澜沧二区被暹罗派人前来运动得紧”等语,再结合暹罗改称及其总理之种种言行,云南省民政厅认为:“本省之泰族问题,前途实堪危惧!倘不急谋补救,则西南半壁,恐将发生重大变故。盖今日之敌国日本,正积极策动暹罗做政治之进攻也。”于是,云南省民政厅发布密令,制定调查表式一份,令云南有傣族的县(局)“于文到一月内详查,将该属境内所有泰族人民详细调查明确,依限汇填具报,以凭核转。事关重要,勿得视同具文,抑或向壁虚造!”⑧《云南省泰族人民调查表》的内容包括:种类(要求填水摆夷、汉摆夷、花腰摆夷、白摆夷、龙家、水家等所谓泰族人民)、人口数目、散布区域、与汉人及其他民族的百分比、有无特殊活动情形(有无外人入该区域活动)及备考等项内容。1940年5月到1941年7月对云南有泰族的砚山等51个县(局)进行调查,通过这次调查,云南省政府掌握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及上层土司的情况。1943年10月,云南省民政厅成立了“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江应樑任主任委员。正如江氏在《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中所言:“日人更嗾使暹罗,改国号曰泰,倡所谓泛泰族主义曰:暹罗人民族为泰族,摆夷亦泰人,其意谓,凡属摆夷,皆应归之泰国,凡摆夷所居土地,皆应为泰国土地,边民不察,多受其惑……而我沿边僰民,则因失于教化,数典忘祖,一遇敌人诱惑,难免资敌所用,此从民族团结言,本境不能不亟求开发也。”⑨
显然,云南省政府对大泰族主义的阴谋是有深刻认识的,对暹罗在我国泰族地区的活动也极为关注和担忧。大泰族主义使云南省政府认识到不仅云南西南部,而且我国西南半壁都已危机四伏,促进了云南省政府对云南及中国西南民族问题的认识,及对云南西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通过汇报,云南省政府的认识及忧虑无疑对国民政府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转变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贵州省政府对大泰族主义言行也是有深刻认识的,它使主政黔省的杨森坚信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关系。杨森说:“民国成立以来,边事日非,可说大半都由于少数民族问题引起,譬如外蒙古的片面宣告独立,新疆、西藏纠纷不已。”⑩正是出于对大泰族主义的警惕,杨森极为重视西南边疆民族问题。他在任贵州省主席时,提醒我国西南边疆有着重大隐患,指出中央政府强弱与边疆民族问题息息相关。他说:
西南方面虽然还没有表面化的问题发生,但是我们已不能不承认隐忧重重,外国势力之侵入早已根深蒂固……东南亚各国中,如泰国即一再宣传他们祖先早年是位在云贵及广西一带,而这一带即为从前的六诏国,诏,是夷语对“王”的称呼。他们这样强调宣传,是否觊觎我国西南边陲,企图重建六诏之国,我们虽不敢必信,然而弦外之音,不无蛛丝马迹可寻,我国中央政府力量强大,边疆问题当然不会发生,只怕万一有日中央自顾不暇,对于边区鞭长莫及,抑或泰国人和夷胞连手,造成西南的内忧外患,那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终有大问题爆发出来的一天。(11)
基于这样的忧虑,杨森强烈谴责国人对西南民族问题的无知与漠视,他说:“在这样重重隐忧之下,国人对于西南民族问题漠视,可谓之麻木,而边地官员处理这个问题稍一不慎,就极可能会出事,基于这样的了解和认识,我在行政会议上开始大声疾呼!‘什么叫做先见?先见就是要在问题未发生前,先去发现问题!因而有以防止问题的发生!’”(12)正因为如此,杨森特别重视贵州境内的民族问题,他在《边铎》月刊发刊词中要求学者“所著之中华民族学史,或人类学,乃至描写民俗,考求骨董诸书,所述宗族之大同小异之风习语言等,不宜强调其异,而应力求其同”,极力宣传“中华国族,同出一源”的理论。(13)在他主政贵州期间,提倡苗汉通婚,创办苗民学校,在省政府下设边胞文化研究会,开设边胞文化讲座,全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以强化贵州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
暹罗改称泰国虽然是在1939年6月,但在此之前就有议论。中国知识界对此也早有警觉,较早对大泰族主义有警惕的是顾颉刚、傅斯年、陈序经等人。
顾颉刚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极感兴趣,早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时就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杂志,致力于边疆、民族和中国古代地理沿革的研究。“七七事变”后,顾颉刚离开北平,由西北而西南,任教于云南大学。日本人的全面入侵,大片国土的沦丧,促使了顾颉刚对边疆、民族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他曾说今日应有的文化运动包括“整理旧的”和“创造新的”两个方面,而“创造新的”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打通边疆与内地之隔阂”,其具体措施为:“一、搜集材料,写成系统的书籍,激发内地人对于边疆之注意。二、联络边疆人才,激起其内向之心。三、以策划贡献政府,并造舆论,以督促政府之实行。”(14)1938年12月,顾颉刚在昆明创办《益世报·边疆周刊》,自言其创刊宗旨是“要使一般人对于自己的边疆得到些认识,要使学者们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要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事业投资,要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要把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要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直到中华民国的全部疆土笼罩在一个政权之下,边疆也成了中原而歇手。”(15)顾颉刚的这一番话表明边疆研究应走出传统的历史沿革地理的研究模式,更多地为边疆建设和抗战建国出谋划策。
1939年1月1日,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发表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的文章,指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是日人伪造、歪曲我国历史以窃取我国领土的凭证,必须废弃。(16)同在昆明的傅斯年看到顾的文章后,给他写信,劝其谨慎讨论民族问题。这封信明确强调对大泰族主义要给予高度警惕,并要求顾颉刚宣扬中华民族是一个,证明夷汉为一家,以杜绝外人觊觎,避免伪满洲国的惨剧在西南地区重演。他在信中说:
有两名词,在此地用之,益必谨慎。其一为“边疆”……其次即所谓“民族”……今来西南,尤感觉此事政治上之重要性……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英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今更收纳华工,广施传教。即迤西佛教,亦自有其立国之邪说。则吾辈正当曰“中华民族是一个”耳。此间情形,颇有隐忧。迤西尤甚。(17)
基于这样的认识,傅斯年在信中提醒顾颉刚要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证明夷汉之为一家,还表示“弟愿吾兄之俯顺卑见,于国家有利也”。顾颉刚读了傅斯年的信后,对其担忧和主张“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随后抱病撰写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1939年2月13日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文章指出: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18)
这篇文章刊出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大讨论。参与讨论的学者大多对顾先生的观点表示赞同,他们根据当时形势,认为顾的观点对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唯有费孝通和翦伯赞表示了不同意见。(19)
在暹罗改名泰国之后,顾颉刚又明确指出大泰族主义的言行实质上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妄图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侵略行径,“这个新的国名,一方面是在表示这个国家,只是泰族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在表示:凡是泰族均应属于这个国家……至于暹罗政客式的学者所大唱的泰族来源说,更是毫无历史上的根据。”他再次重申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某一种族征服某一种族的事实(有的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统一了中国境内的各色各样的百姓)。”(20)
陈序经对泰国的大泰族主义言论也多有揭露。早在1937年他就撰文告诫国人,对暹罗人的野心应抱有警惕。他说:“东亚的独立国家,除了中国和日本外,只有暹罗。现在我们看不起我们的南邻,正与从前我们看不起我们的东邻一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南邻的野心未必减于我们的东邻。”(21)1939年6月,暹罗改国名为泰国,大泰族唯国主义甚嚣尘上之时,陈序经连续写下《暹罗与汰(泰)族》、《暹罗与日本》等文,并在1939年底出版了《暹罗与中国》一书,称銮披汶政府改暹罗为泰国“别有用意”,是大泰民族主义膨胀的反映,对于暹罗奉行亲日政策,日暹狼狈勾结给予了义正辞严的揭露和批评。
对泰国的大泰族主义言行,张廷休也是高度警惕的。其对民族问题的主张在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傅、顾只是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张廷休却主张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而且自古就是同源的。他在《苗夷汉同源论》中指出苗夷并非为外来的异族,而是与中原汉族同出一源。当时持反对意见者也不乏其人,于是张氏在1939年5月又发表《再论夷汉同源》,继续阐发汉苗同源论思想。文章开篇即指出部分学人将苗夷视为汉族以外的民族是根本错误的,要加以纠正。张廷休认为夷汉是一家,是同源的民族。并根据语言、传说、历史、体质各方面的事实来证明。张氏指责学者研究苗夷问题喜欢滥用“民族”二字,如苗傜民族、摆夷民族、特别是云南民族的说法,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现在的云南人无论夷汉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绝没有什么云南民族。如若拿这个新名词去问云南人,他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做云南民族,而且以为你是侮辱他,有意说他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如此滥用‘民族’二字,随便说夷汉是两个民族,中华民族之中又分什么云南民族,这不但忽视了历史,而且在目下对于抗战的影响实在太坏了。”“现在日寇正在勾结暹罗,宣传滇桂为掸族故居而鼓励其收复失地。我们再正叫着云南民族,这是在替敌人做宣传工作了。”(22)
当时,有关中华民族的观点,实际上主要有两派:即张大东归纳的中华民族自古同源论与中华民族起源多元但在发展中已逐渐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23)正如岑家梧所言:“顾、张二氏对于中华民族的分析,顾氏是主张许多不同的种族,经过历史的演进,逐渐混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内的人民,是不同始而同终的;张氏则主张中华民族内的人民,自始就是同源,不过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边疆与内地之间,逐渐隔膜,便形成文化上的差异,可谓是同始而不同终的;二氏的主张虽稍不同,然都是同样的指出中华民族的统一性。”(24)这两种观点都指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都体现了知识界团结民族、争取胜利的拳拳爱国之心,所以两派观点都有人赞同,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原因,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仍然深感忧虑。1941年8月《边政公论》创刊,其发刊词云:“在我边疆广大的区域上,散居着汉满蒙回藏各族的人民,而这各个民族,都是伟大中华民族之一支系,在初本出一源,历史所纪,彰彰可考,中间复经过几千年来的往来接触,使其混合熔铸,成为一个国族。只因历史相沿,畛域未尽泯除,每予敌人以分化挑拨的口实。当此国际风云日趋险恶的今日,应一本民族主义团结国内各民族为一大中华民族的伟大方针,积极研求有效的团结办法,同时更应以学理上事实上的证明,盖坚我国人团结的信念,而打破敌人分化挑拨的企图。”(25)这样,一部分民族学者主张学术研究应为民族团结、争取抗战胜利服务,一部分学者继续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还有部分学者则为了避免承认民族及民族问题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大力宣传和倡导“中华民族同源论”,反对使用“民族”一词、承认民族问题和讨论民族问题。主张学术研究应为民族团结、争取抗战胜利服务的学者,如从事贵州民族研究的吴修勤就提出了要强化贵州少数民族中华民族意识的主张。他说:“敌人的铁蹄,东面到了湘北,南面到了越南,这(指贵州省——引者注)是抗战建国的核心地,它也是一座防敌的重要堡垒。”这里虽有着三百多万的特殊人力,但“他们的每个脑海是纯洁无色体,如果我们不急急替他们染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颜色,那敌人便会替他们染上将薄嵫嵫的‘红日’颜色的,这是多么危险”。泰国总理銮披汶在1939年“六·二四”广播中提出要“收复失地”,而且他“深恐我们不明白,他清清楚楚地加以注解:‘我泰语在暹境以外者,有二千余万人,大都散布在中国南部滇、川、黔、桂一带’”,所以“我们要巩固这座堡垒,必须建设这三百万民众的心理,然后敌人才不能攻破,这是国防大事”。(26)
同样从事贵州民族研究的岑家梧也极力强调“黔省民族研究,首要的为研究苗、仲各族与中原文化之关系”,以揭露大泰族主义阴谋而对国家有利。他说:“自暹罗改国号为泰以来,受敌人之唆使,鼓吹大泰族主义,宣称暹罗泰族之故乡为中国南部,后受汉人压迫而迁入暹。对我国境内之泰语系民族,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所以在贵州民族研究方面,“吾人今后应就苗、仲与中原文化之关系上作深刻的研究。揭发中华民族有不可分割之关系,反以增强民族意识,则敌人之阴谋,不攻自破矣”。(27)谈到西南民族研究,岑氏认为:“几千年来,共同生活在同一的环境中,使各族的利益趋于一致,形成了整个利益共同的集体。我们今后需对各族的历史作深刻的研究,用历史的事实,说明各族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28)岑家梧还撰文驳斥法国学者伯叙吕斯基、马伯乐、德国学者斯密德、瑞士学者戴密微及国内学者马长寿等将仲家归属于泰语系的观点,认为“仲家原为中原汉人,后来因为犯罪流徙或奉调戍边,日久便与土著通婚土著化了”,其与汉人在血统上混合已久,不属于泰语系民族。(29)
继续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学者,如姚薇元说:“中华民族之内涵,实包有汉满蒙回藏苗瑶诸族,此宗族间之相互关系,自远古以至现代,无时不在错综交织之中。”“吾汉满蒙回藏苗瑶诸宗族,经五千年恒长之共同历史,生活于同一政治教化之下,其间虽有政权之变迁,势力之消长,然其民族之关系,则愈接触愈融合,愈交织而愈密致。迄今已由诸宗族销融混化而成一整个的‘中华民族’。”“今诸宗族间仅存些微之生活方面或宗教方面之差异,一如英格兰人与爱尔兰人间之差别,初不失为英吉利民族然。要言之,汉满蒙回藏苗瑶诸宗族经五千年之交融混化,业已铸成一中华民族,此民族之本身具有一种错综密结之‘整个性’,绝非外来暴力所分裂也。”(30)朱谦之也说:“中华民族分开说,有汉、满、蒙、回、藏各族系,合而言之,却同是蒙古利亚种,就中如一般人类学者所认为种族和语系不明的边疆同胞,实际均已早感受中华文化,在血统上混合已久,不能详为分析。在整个系统看来,这些边疆同胞,可以说是中华的原始民族,是带着中华民族的共同色彩,所以近日谈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只是一整个的复合民族,是历史上形成起来的固定的人类集团,虽在各族系里面免不了带多少特殊的色彩,但就整个来说,中华民族只有一个,即是蒙古利亚种,所谓黄种便是。”(31)此文虽是从种族的角度来论述的,但目的仍是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
为了避免承认民族及民族问题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大力宣传和倡导“中华民族同源论”,反对使用“民族”一词、承认民族问题和讨论民族问题的学者,如黄举安认为使用“民族”一词及承认民族问题是授人以柄,因之否认国内民族称号有存在的价值。他说:“事实告诉我们,到了今天,还有人在提倡什么‘苗夷问题’和‘云南民族问题’,滥用了名词,恰好给野心者一个绝好的侵略机会,像泰国也在高唱滇桂是他们的故居谬论,这责任不能不归之于乱喊‘民族’的人们来负担。”黄氏还严厉批评:“在国内无异族的最高原则下,所谓某某民族全是无根之谈,因为中华民族在血统上早就无分彼此了。”而在“全民族正在精诚团结,救亡图存的今日”,使用“民族”一词的人是“不识大体的”,他们“像有意在离间民族感情,侮辱边胞人格”。黄氏还认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虽然有过各种民族名词的记载,可是是否能够当得起民族称号,实在大有讨论余地。”“在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民族名词,何止百数十种,从前的姑且不去管他,既现在一般人称的汉、满、蒙、回、藏、苗、夷等等名词,同样没有存在的价值。”(32)
为了粉碎大泰族主义的侵略言行,团结各民族共同争取抗战胜利,国民政府也在不断调整民族政策:开始承认并尊重少数民族,取消歧视性的少数民族称谓;为减少分化民族的称谓,以出生地称谓取代族属称谓;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将知识界“中华民族同源论”主张付诸实践。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融合而成为整个的国族……在未得胜利以前,吾境内各民族唯有同受日本之压迫,无自由意志之可言,日本口中之民族自决,语其作用,诱惑而已,煽动而已;语其结果,领土之零星分割而已,民众之零星拐骗而已;日本知此广大之领土,与繁庶之民众,非可一口吞灭,故必取而脔切之,脔切越细,吞灭越易,其所以制造傀儡,惟日汲汲,如恐不及者,职由于此。故吾同胞必当深切认识,惟抗战能解除压迫,惟抗战获得胜利,乃能组织自由统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各民族今日致力于抗战,即为他日享有自由之左券也。”(33)一方面,认为各民族已融合成一个国族;另一方面,向国内各民族揭露日本以“民族自决”为诱饵分化我国民族的阴谋,号召各民族为实现彻底解放而共同奋斗。
1939年1月,中央研究院接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公函:“我国边疆民族之名称常因‘猺族’、‘獞族’、‘猡猡’等犬旁名词,引起国人之歧视;请予纠正,以免误会,等情。查所呈不无见地。惟此等民族各有其历史上构成制因素;应如何修改方为妥善,拟请贵院详加研究。”中央研究院把这项任务转交史语所办理。参加“考定我国四方少数民族名称之工作”的芮逸夫,“乃就旧搜,略加考稽,计得西南少数民族使用虫兽偏旁之命名凡50;遂厘定改正原则,编成正字表”。1940年1月18日,中央社会部会同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商讨修正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决议补充二项:(一)以为学术上研究便利起见,拟请中央研究院依据下列原则详订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原则如下:(1)凡属虫兽鸟偏旁之命名,一律去虫鸟偏旁,改为人旁。(2)凡不适用于(1)项原则者,则改用同音假借字,如蜒、蛮等是。(二)少数民族成为其根据生活习惯而加之不良形容词,应概予废止,如“猪屎仡佬族”,“狗头猺”之“猪屎”、“狗头”等形容词。(34)
1940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阳壹字20985号训令,公布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会同教育部及中央研究院拟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规定:“本册所列各民族之命名,其见于此项命名表者即从其规定,并于备考栏内注明,其未见诸此表者,亦本中央改正命名之原意加以改正,以示平等。”(35)故《云南省边民分布册》所载云南少数民族的名称,不再有虫兽鸟及反犬等字样,全部改为“亻”字旁,不再用歧视性的民族名称。并对云南少数民族进行了初步的识别,将原来的150余种识别为85种。
1939年8月,国民政府渝字第四七○号训令全国一律废除各族旧名,而以其生长所在地人呼之,如蒙古人、西藏人或贵州某县人等。训令指出:“我国民族、文化、血统,混合已久,不能强为分析,历史记载,斑斑可考。后因辗转迁移,环境悬殊,交通隔绝,语言风习,遂生歧异。在专制时代,对于边疆同胞,视为附庸化外,实行其割裂封锁之政策。民国以来,国人复受敌方恶意宣传,在心理上已遗留本国内有若干不同民族之错误观念,于是相沿成习,往往仍妄用含有侮辱性质之蛮、番、夷、猺、猓、獞之称谓,加诸边疆同胞,在呼之者固易生藐视之心,而听之者尤易起憎恶之感,是无异于自行分散我整个之民族。殊与总理倡导民族主义之本旨相背谬。国民政府前据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提议,曾通令禁用番蛮等称谓,加诸西藏人民,以矫正陋习,昭示平等。时逾十载,不独种习未除,益以近来国内人士,逐渐注意边疆问题之故,不妥名词之使用,有日趋扩大之势。即以西南边地同胞而论,竟有二百余种不同名称。广西省政府,虽曾将猺猓獞等字样,改为傜倮僮等,以示平等。但不同民族之痕迹,仍未见泯除。若专为历史与科学研究便利起见,固不妨照广西省前例,将含有侮辱之名词,一律予以改订。而普通文告,及著作品宣传等,对于边疆同胞之称谓,似应以地域之区分,如内地人所称某某省县人等,如此则原籍蒙古地方者,可称为蒙古人……其他杂居于各省偏僻地方,文化差异之同胞,似亦不妨照内地分为‘城市人’‘乡村人’之习惯,称为某省某边地,或边县人民,以尽量减少分化民族之称谓。”(36)这种以出生地称谓取代族属称谓的做法,虽然有以示平等的用意在内,但也是国民政府贯彻中华民族是一个,否认国内各民族称谓存在,淡化国人民族概念及各民族族属意识的具体表现。
国民政府将知识界“中华民族同源论”主张逐渐付诸实践。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各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作演讲时说:“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们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说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集许多家族而成宗族,更由宗族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国父孙先生说‘结合四万万人为一个坚固的民族’,所以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其中各单位最确当的名称,实在应称为宗族。”(37)在《中国之命运》初版中,蒋氏又进一步指出:“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也就是说,各宗族之间不是存在血缘关系,就是存在婚姻关系。而在增订版中,蒋介石则直接表述了其国族同源主张:“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他们各依其地理环境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文化。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启族姓的分别。然而五千年来,他们彼此之间,随接触机会之多,与迁徙往复之繁,乃不断相与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38)
综上所述,抗战时期,大泰族主义言行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西南地方政府及中国知识界的高度警惕,引发了政府及知识界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深刻反思。第一,大泰族主义言行引起了重庆国民政府和西南地方政府对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促成了政府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转变。这表现在:其一,大泰族主义使国民政府从过去只重视蒙藏问题,发展到认识到西南民族问题也是存在的,而且也是相当棘手和重要的,进而更加重视西南民族问题。其二,大泰族主义使云南省政府认识到不仅云南西南部,而且我国西南半壁都已危机四伏,促进了云南省政府对云南及中国西南民族问题的认识以及对云南西南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其三,大泰族主义使贵州省主席杨森坚信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关系,促使他特别关注西南边疆民族问题,认为要完成新贵州的建设,必须解决民族问题,强化贵州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意识。第二,大泰族主义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高度警惕和重视,促使知识界普遍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或整体性,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和“中华民族同源论”的主张。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原因,部分民族学者主张学术研究应为民族团结、争取抗战胜利服务,部分学者继续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更多的学者为了避免承认民族及民族问题予敌人以分化的口实,大力宣传和倡导“中华民族同源论”。第三,出于对大泰族主义的忧虑和警惕,国民政府为团结各民族共同争取抗战胜利,将知识界“中华民族同源论”主张付诸实践,对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抗战时期泰国政府一直坚持大泰族主义的侵略行径,但是国民政府及其知识界对大泰族主义言行的揭露、批驳和反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泰国政府的侵略野心,这对于维护多民族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抗战胜利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①参见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马勇:《泰国古代史研究述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②据泰国人素察·奔波里叻回忆:“二十年前,正当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中国一位史学家谈及南诏历史时说,建立南诏国是乌蛮族(现在的彝族)和白蛮族(现在的白族),而不是泰族,我听后只得发愣,因为在小学、中学念书时就从历史教科书里知道南诏原是泰国的疆域,所以这个认识一直深刻的印在我的脑子里。”(素察·奔波里叻:《南诏——是我们泰族的疆域吗》,叶国忠译,《东南亚研究》1980年第4期,第71页)
③为了回应西方学者对历史的无知或有意歪曲,我国学者长期驳斥“泰族建立南诏”论。参见方国瑜:《云南沿革》,《云南史地辑要》(上),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49年11月;林超民:《白族形成问题新探》,林超民主编:《民族学评论》第二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贺圣达:《“南诏泰族王国说”的由来与破产》,《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④陈吕范:《中泰关系若干问题研究课题小结(代序)》,《泰族起源与南诏国研究文集》代序,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⑤《云南省政府秘外字第537号令》(1940年4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13,第2页。
⑥江应樑:《请确定西南边疆政策》,《边政公论》1948年第7卷第1期,第1、3页。
⑦《云南省政府秘外字第537号令》(1940年4月2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13,第2页。
⑧《云南省民政厅叁三字第4444号密令》(1940年5月15日),云南省档案馆藏,1011-13,第7页。
⑨江应樑:《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4年11月,第2-5页。
⑩杨森:《贵州杂忆(续)》,《杨森传记资料》(四),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11)杨森:《贵州杂忆(续)》,《杨森传记资料》(四),第68页。
(12)杨森:《贵州杂忆(续)》,《杨森传记资料》(四),第68页。
(13)杨森:《〈边铎〉月刊发刊词》,《杨主席言论选集》第一辑,贵州省政府秘书处编印,1946年,第353页。
(1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4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422页。
(15)顾颉刚:《益世报·边疆周刊发刊词》,《益世报》,1938年12月19日。
(16)顾颉刚:《“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益世报·星期评论》,1939年1月1日。
(17)傅斯年:《致顾颉刚》,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5页。
(18)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顾颉刚在1939年2月7日的《日记》中记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因写此文(《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告国人。”(《顾颉刚日记》第4卷,第197页)
(19)费孝通写有《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翦伯赞写有《论中华民族与民族主义》,顾颉刚撰有《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关于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参见周文玖等:《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辩的考察》,《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19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九四○年代的中国(下卷)》,2007年8月。
(20)顾颉刚:《暹罗改号与中国之关系》,转引自张凤歧:《云南边务》,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云南史地辑要》(上),昆明: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49年,第28页。
(21)陈序经:《进步的暹罗》,《独立评论》第235号,1937年5月。
(22)张廷休:《再论夷汉同源》,《西南边疆》第六期,1939年5月。
(23)张大东:《中华民族发展史大纲》,重庆:军训部西南游击干训班印,1941年,第21-22页。
(24)岑家梧:《论民族与宗族》,《边政公论》第三卷第四期,1944年4月,第8页。
(25)《边政公论》发刊词,《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一期,1941年8月,第1、3页。
(26)吴修勤:《怎样训练苗夷的干部》,《社会研究》第三十五期,1941年10月,吴泽霖等:《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9页。
(27)岑家梧:《贵州宗族研究述略》,《边政公论》第三卷第二期,1944年2月,第37页。
(28)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1940年),《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31-32页。
(29)参见岑家梧:《由仲家来源斥泰族主义的错误》,《边政公论》第三卷第十二期,1944年12月,第20页。
(30)姚薇元:《中华民族之整个性》,《边疆通讯》第三卷第一期,蒙藏委员会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编印,1945年1月。
(31)朱谦之:《中华民族之世界分布》,《民族文化》复刊创刊号,民族文化月刊出版社,1941年4月。
(32)黄举安:《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蒙藏月报》复刊第十三卷第六期,1941年。
(33)《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资料汇编》第5辑第二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09页。
(34)参见芮逸夫:《西南少数民族虫兽偏旁命名考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论稿》(上),台北:台湾大学人类学系,1989年,第96页。
(35)杨覆中:《云南省边民分布册》,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1946年,第3页。
(36)转引自吴景贤:《抗战以来中国民族之团结》,《蒙藏月报》复刊第十三卷第四期,1941年。
(37)蒋介石:《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九,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216页。
(38)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增订版),上海:正中书局,1944年,第2页。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顾颉刚论文; 边疆论文; 民族问题论文; 1939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泰国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