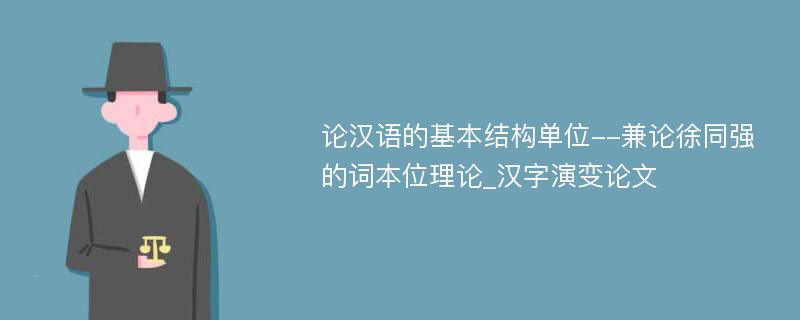
也谈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评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本位论文,也谈论文,理论论文,单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词是语言系统中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词汇学、语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由于汉语的词与字(语素)存在着严重的纠葛,所以提取和确认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就成为长期困扰汉语研究的一大难题。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一书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全新观点[1],为解决这一难题,深化对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认识,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引起了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其字本位理论本文仅就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
1
徐先生经过近20年的研究探索,找到了汉语结构的基点——字,并以此为突破口,阐释汉语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为语言理论研究开拓一条新的途径。他认为,自《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基本上是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的,虽然它开创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时期,但是也给汉语的研究带来了“印欧语的眼光”,导致人们长期以来一直用印欧语的结构原理来观察汉语的结构。徐先生对百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提出印欧语系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始终是语法;而汉语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它的研究重点是语义。并且强调,“字”与“词”尽管只是一字之差,但涉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改造,涉及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和语言结构的差异,是由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而形成的不同的发展道路。
字本位是徐先生的理论核心,也是他认识汉语特点的基础。他呼吁应该以“字”为研究汉语的基础结构。他把“字”定义为: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在徐先生的理论中,“字”不仅是汉语的书写单位,也是一级最重要的语言单位。因为在他看来,汉语中没有与印欧系语言中word相对应的一级单位,所以“字”和“词”不仅仅是一字之差,而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观、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
这一理论能否解决汉语由于基本结构单位不易确定而带来的一系列麻烦,关键在于他的理论及其依据是否完全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他的各种结论的推导过程是否完全合理。我们把徐先生的基本观点及其依据和推导过程大致概括为以下4点:
(1)“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字”不光是写出来的字,也是嘴里说的字,平常人们说“吐字清楚”、“字正腔圆”、“咬字不准”中的“字”指的是字音;而《文心雕龙》“夫人之立言,积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2],陈佩斯、朱时茂小品“只有一个字:不服”,电视主持人杨澜语“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惊心动魄”,这三句话中的“字”则是指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写出来的字仅仅是把这种心理现实性书面化而已。[1]11-12
(2)一种语言的结构本位只能有一个,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不可能一个领域一个“本位”。“字”是汉语结构的本位,在结构关联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是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的交汇点,一切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它对各个层次的关联方式都是以“1为基础的“1=1×1”的层级体系,形成“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基本结构格局。[1]125-127
(3)根据汉语语言编码形、音、义三位一体和书写单位、听觉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的情况推导出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则。字有理据性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顽强的表意性,从汉语中借词的命运可以证明“字”的表意性,即尽可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语法构词规则,对于那些难以意译的外来词就尽可能设法进行汉语化改造,使之意译化,如古代借词“狮”、“佛”、“罗汉”等,现代借词“啤酒”、“卡车”、“卡片”、“酒吧”等。[1]47-52,135-142
(4)根据汉语理据性编码机制和印欧系语言约定性编码机制的不同,推导出两种语言结构的原则差异和语言的两种类型:汉语的突出特点是语义,属于语义型语言;印欧系语言的突出特点是语法结构,属于语法型语言。语法型语言重点研究“主语—谓语”的结构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划分,而语义型语言的研究重点是有理据的字,突出语义、语音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不讲主、谓、宾和名、动、形之类的语法。[1]52-55
2
对上述“字本位”理论的几种基本观点及其依据和推导过程,我们简要分析如下:(1)徐先生说“字”是汉语社团具有心理现实性的结构单位,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的心目中,“字”的确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书写单位,有时也把它看作一个语音单位。正像赵元任先生说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2]248“我说的社会学的词就是‘字’。不光是写出来的字,也是嘴里说的字,如‘你敢说一个“不”字!‘词’,也就是语言学的词,我管它叫句法词,这对一般中国人说来是个不熟悉的名字。比如‘现在’,是个词,但是如果有人要问这个词的意思,他总是说:‘“现在”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3]78-79正因为汉语一个音节就是一个字,所以人们常常把发音叫做“吐字”或“咬字”等。这说明在人们心目中,“字”既是书写单位,又是语音单位。
然而徐先生进一步指出“字”在汉语社团心理中,还是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这正是我们的疑问之一,因为徐先生所举的3个例证不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中第1个《文心雕龙》的例子属于古人的概念,古人认为“积字而生句”,是由于在古代汉语里一个字基本上就是一个结构单位,所以这种说法没有问题;但是古今汉语有了许多变化,今人对于语言的认识也跟古人有所不同,因而古人的概念不等于今人的概念。第2个例子,小品、相声中所说的“只有一个字:不服”,或者与此类似的“一个字:还不错”之类,都不过是一种笑料而已,正由于在人们心目中它不是一个字,才得以成为笑料,所以不足为证。第3个例子,我认为应该属于电视主持人的口误,如果我们用“惊心动魄”以及徐先生所列举的“彷徨”、“朋友”、“绿油油”、“稀里哗啦”等属于一个“字”的双音字、三音字、四音字去询问识字或不识字的说汉语的人,恐怕没有人会回答是一个字的。所以从汉语社团的心理现实来看,大概不会把一个“字”全都看成一个结构单位。一个字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个结构单位,但是反过来说一个结构单位就是一个字,恐怕多数人不会认同。
赵元任先生也注意到汉语社团所谓的社会学的“词”就是“字”,它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中心主题,但是他说“现在”这个语言学的词,一般中国人常常说成“两个字”,并没有说是一个字,这说明赵先生仍然认为语言学的词和社会学的词(字)并不相等。吕叔湘先生也十分重视“字”在汉语中的特殊作用,但同时还特别强调二者的区别。他说:“古代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是‘字’——用一个汉字代表的,有一定意义的单音节,它在现代汉语里,从语言学上看,可能是一个词,也可能只是词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不但在古代,甚至在现代,这个有意义的单音节——‘字’,还是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在说汉语的人的语言生活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远过于像俄语这种语言里的‘词根’。但是无论如何,它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词’,而后者在现代汉语里所起的作用正在渐渐地重要起来。”[4]359在吕先生看来,“字”这个有意义的单音节,在汉语中还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尽管“在古代汉语里,‘字’和‘词’是基本一致的”,但它无论如何都不是语言学里的词。
(2)徐先生说“字”在汉语结构关联中处于核心的位置,是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的交汇点,所以“字”不仅是一个书写单位,而且还是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的一个基本结构单位。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的词本位或词组本位理论,以往以“词”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跟书写的“字”并不一致,所以在提取或确认“词”时,常常遇到不少困难。正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为了更加简便地提取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徐先生提出了以“字”为本位的观点。“字”作为汉语语音和文字上的一个自然单位,可以非常容易地找到它,如果它也能够成为语法结构上的基本单位,提取它当然是再方便不过的事了,但是实际操作时是否如此简单呢?
汉字产生之初,形成了“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基本结构格局,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一个概念,就是语法和词汇中的一个基本结构单位。如果汉语能够长久保持这种格局,那么字本位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上,都是完全可以行得通的。但是随着语言发展,“字”的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因而很难说一个“字”仍然是一个基本结构单位。
我们先看看在一个字之内区别“字”与结构单位的复杂情况。如果一个“字”有几个不同的字形,如“鸡、雞、鷄”;或者一个“字”有几个不同的读音,如“尾”(wěi,yǐ)、“核”(hé,hú)等,那么应当看作几个结构单位呢?一般认为只要概念不变,可以把它仍然看作一个结构单位。如果一个“字”在原来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概念,读音也发生了变化,如“磨”(mó,mò)、“强qiáng,qiǎng,jiàng等;或者一个“字”读音不变,可以表示几个联系不十分紧密或根本没有联系的概念,如“胡”可以表示“古代北方和西方的少数民族”、“为什么”、“随意地”、“胡须”等,那么应当看作几个结构单位呢?照常理,音不同,概念不同,就应当把这种“字”看作几个不同的结构单位。如果一个“字”在原来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许多新的概念,读音也没有发生变化,如“信”,可以表示“诚实”、“相信”、“消息”、“信件”等,那么究竟应当看作几个结构单位呢?如果把上面的几种情况都简单地看作一个结构单位,那么它们已经不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一一对应的基本格局,有的甚至差别很大,一般人恐怕难以接受;如果看作几个结构单位,那么如何区别,区别的标准又应当以形、音、义中的哪一个为主要依据呢?这样一来,“字”作为结构单位也不是可以简单方便地提取了。
其次,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许多概念已经不能用一个汉字表示,而必须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合才能表示。汉语逐步由单音格局向双音为主体的格局转化,以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交际的需要。这一点徐先生已经看到,他说:“根据交际的需要,对原有的编码体系进行适当的改造和调整,不同的语言都会有这种过程。”[1]355“汉语以联绵字的语音结构为桥梁,利用已有的字,根据它们在意义上的联系,加以灵活组配,构成不同类型的复音字,这是汉语理据性编码机制的一次重大调整。它突破了一字一码的限制。”[1]354“为适应交际的需要,用双音字来实现‘一个字义=一个义类×一个义象’的结构就逐渐成为汉语编码方式的主流,而单字编码格局也就由此而退居次要的地位。”[1]359在这种情况下,表示一个概念的不同类型的复音词如“葡萄、蝴蝶、苹果、芒果、白菜、羊肉、村民、人民、国家、洗澡、开会”等,哪些是一个结构单位——“字”,哪些由两个“字”组合而成的“辞”或“块”呢?况且究竟以什么标准把这些复音词区分为“两音字”或“辞”、“块”,恐怕也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究其原因,就在于作为书写单位的“字”和作为音义结合的语言单位的“字”(一般称为“语素”或“词”)早已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了。对此,吕叔湘先生曾经作过精辟的概括:“汉语的语素和汉字,多数是一对一的关系,但是也有别种情况。语音、语义、字形这三样的异同互相搭配,共有八种可能:两同一异的有三种,一同两异的有三种,全同和全异的各一种(表略)。”[5]不知徐先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书中似乎没有明言。
如此看来,作为书写单位的“字”和作为结构单位的“字”只要不相等,提取汉语结构单位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就不能说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3)徐先生根据汉语语言编码形、音、义三位一体和书写单位、听觉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的情况推导出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则,并且说字有理据性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顽强的表意性。我们认为字的顽强的表意性和字有理据性似乎没有必然联系,因而分别讨论。
汉语的字具有顽强的表意性确实属于汉字的一个突出特点,大量的例证都可以证明它。比如联绵词或译音词中的字本来没有表意作用,但在长期使用中也逐渐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成为可以单用的结构单位或可以用来组词的单位。例如连绵词“蝴蝶”、“猩猩”中的“蝶”和“猩”;本来没有什么意义,可是用在“蝶恋花”、“采茶扑蝶”、“蝶泳”、“猩红热”等词语中时,就成了有意义的单位。再如译音词“葡萄牙”、“巴士”、“的士”中的“葡”、“巴”、“的”,本来没有意义,可是用在“中葡双方”、“大巴”、“中巴”、“面的”、“打的”等词语中时,也成了有意义的单位。为什么汉语的“字”会具有这样的特点呢?这大概就是徐先生所说的由汉字本身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编码原则所决定的。在这种大背景下,人们往往会把不表意的汉字也习惯性地当作有意义的单位来使用。
然而我们认为,汉字顽强的表意性并不能用来证明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则,而且推导出这一原则的两个依据之一“书写单位、听觉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的情况”,我们前面已经论证过它与语言实际并不完全相符,这样就可官能对结论的正确性有所影响。
所谓理据性,是指语言单位音义的结合有无理据,即所谓“语言内部形式”的理论,该理论关注词的内部音义之间的理据性联系,试图找出某一概念之所以读某音的原因。徐先生推断汉语编码具有理据性主要依据的是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情况,而早期汉字“象形”、“指事”、“会意”的特点是直接通过形体来表示意义,这些汉字以及后来占主体的“形声字”所表现出来的理据性都属于文字的理据性,即形义结合的理据性,文字形义结合的理据性并不等于语言单位(词)音义结合的理据性。可是徐先生却根据形义结合的理据性假设音义结合的理据性,他说:“由象形、指事、会意到转注,形与实的理据渐次淡化和虚化,而形与义的理据则渐次加强;通过假借的过渡,到形声字的阶段,在形义结合的理据中又清楚地隐含着音义结合的理据,语言的结构特点渐次明朗化。”[1]273“形声字给语言研究提供的最重要的线索就是‘转化’:‘义’可以转化为‘声’,而‘声’也可以转化为‘义’,相互处于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充当声符的形符原来大都是表意字,有音有义,是语言中的一个‘码’,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汉语社团用它来编码,使其转化为‘码’的一个构件,表示字音。这样,‘义’在结构体系中就转化为‘声’,成为语言再编码的基础;‘形’就是在这个‘声’的基础上加上去的,以摹写与这个‘声’的意义有联系的现实现象。这真是‘声由义转,形(义)由声生’,使汉语编码途径得到重大的改进。”[1]271在徐先生看来,形声字是汉字由形义结合的理据向音义结合的理据转化的枢纽。然而把它作为音义结合有理据的重要证据,是建立在形声字的声符既表音又表义的基础上的。他所举的例子是:由表义字“共”转化为“供、恭、拱、拲、栱”等字中的声符,而这些由“共”得声的字,都从两手托物以表供奉的初义引申而来,即声中有义。但是问题在于,是否所有的形声字或者大多数形声字都像以“共”为声的这组字这样,声符既表音又表义,因而具有一定的音义关系呢?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像“共”之类具有音义对应关系的形声字只占形声字中很小的一部分。沈兼士先生曾经把形声字的声符分为两类,一类是和意义无关的,一类是和意义有关的;而和意义有关的一类中,一个声符的意义也不一定都一致[6]。既然如此,那么如何论证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则呢?
再说那些具有理据性的音义关系的编码,其理据并不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有两种不同的理据。一种音义关系是模仿客观事物而形成的象声词,这是纯粹意义上的音义结合的理据,但是这类词数量极其有限,不足以成为理据性原则的主要证据。另一种是滋生词与滋生源词之间的音义联系,即上述“供、恭、拱、拲、栱”和“共”之间的关系,而滋生源词的语音形式gong与所表意义“两手托物以表供奉”之间不一定有什么必然联系,目前讨论汉字理据性编码原则的证据主要是指后一类。严格地说,它只是一组同出一源的“同族词”的滋生理据,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音义结合的理据,因为它是在某个词的音和义已经结合为一体的基础上,词汇发展的理据,新词以这个音义结合体整个地作为依托,不断滋生扩展,而不是仅仅借其音或仅仅借其义。因此我们认为,这两种理据不是一回事,不能用“同族词”滋生的理据作为音义结合的理据。更重要者,无论是前一种象声词那样的音义结合的理据,还是后一种同族词发展的理据,都是所有语言所共有的,因为各种语言都有象声词以及自己的词源学。既然如此,也就不存在理据性编码机制和约定性编码机制的对立。
由此可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应当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完全对立的。正像沈兼士先生所说:“凡义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依,展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作一概而论,作如是观,庶几近于真实欤。”[7]259
(4)徐先生根据理据性编码机制和约定性编码机制的不同,推导出汉语属于语义型语言,印欧系语言属于语法型语言,并且明确指出两种类型的语言研究重点的不同。对于这个推论,我们也存在疑问。
上面说过,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理据性或约定性两种截然不同的编码机制,汉语是否真的属于理据性编码机制,我们尚且不能肯定,因而由此推导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类型是否存在,我们当然难以认同。根据一般原理进行判断,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语义(内容)和语法(形式)两个方面,不可能存在只有语义没有语法或只有语法没有语义的语言,因而就必然产生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两个不同层面的研究。如果说不同的语言对这两个方面各有所侧重,因而语言研究的重点也有所不同,那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徐先生所说的两种不同的语言的研究重点讲得很明确,让人感觉语法型语言似乎没有语义问题,而语义型语言似乎没有语法问题,所以研究汉语这样的语义型语言的语法,分析什么主语、谓语、宾语之类的句法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划分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之类的词类,简直就是无谓的牺牲,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样没有出路。徐先生的结论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我们不能相信汉语的结构单位在组合成句子的时候,只有语义上的搭配关系而没有语法上的搭配规则,只研究它的有理据的“字”,研究语义、语音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都要受一些共同的结构原理支配,所以不管是所谓语义型语言,还是所谓语法型语言,都包含一些共同规律和普遍特征,同时又各自具有一些特殊规律和个别特征。语言研究的任务包括上述两个方面,二者都不可忽视。尽管传统的汉语研究没有系统的语法研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汉语本身的原因,也有其他复杂的原因,但是这绝不等于汉语没有语法,汉语的结构单位之间不存在形式上的结构关系。《马氏文通》参照西方语法并结合汉语实际,建立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尽管它带来了一些“印欧语的眼光”,但毕竟开创了汉语研究的一个新时期。《马氏文通》以来的一百年间,汉语语法研究一方面认真参考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探讨汉语语法自身的特点,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也取得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因此我们不同意把它一概斥为“用印欧语的结构原理来观察汉语的结构”。徐先生的“字本位”理论能否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还有待于实践的验证;况且这一理论目前还只是一个框架,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和一系列具体操作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阐述说明。
3
综上所述,我们对徐先生“字本位”的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存在一些疑问,但同时也认为这一理论给了汉语研究许多有益的启示,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入认识汉语的特点,反思以往的研究工作所走过的弯路。其中最大的启示在于他揭示了汉语中“字”这一级单位的特殊作用,以及语义的特殊地位,为解决汉语基本结构单位的认识分歧,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下面简要谈谈我们对这一问题的两点思考。
(1)尽管“字”在汉语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作用,但是最好不要用它来代表汉语基本结构单位,因为它与作为书写单位的“字”在实际操作中不易区分清楚,况且作为语言的结构单位,“字”和“词”也是有区别的。为了清楚地区别这两套术语,并尊重现行一般理论,我们认为,“字”仍然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的简称,作为汉语的结构单位,仍然采用“语素、词、词组、句子”这一套术语,其中“词”是最小的句法结构单位,“字”绝大多数都是“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但要特别注意汉语的“语素”具有许多不同于印欧系语言的特点。虽然徐先生一再强调“字与语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把字等同于语素,这实在是观念上的一大失误;语素既没有理据,也不是句法的最小结构单位,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无法相互类比。”[1]16-18但是我们仍然觉得,只要充分认识两种语素的不同特点,采用什么术语是次要的,只要不至于引起混乱就行。况且我们也不完全同意字都是有理据的,是汉语句法的最小结构单位的说法。
(2)两种“语素”的主要区别在于:印欧系语言里“词”是现成的,而语素是从词中分析出来的;汉语里“语素”(字)是现成的,词是从句法结构中分析出来的,因而赵元任先生称之为“句法词”。印欧系语言的问题在于如何从词中把语素剥离出来,汉语的问题在于如何鉴别语素是否成词。过去的汉语研究过分强调二者的严格界限,一定要确认是自由语素还是黏着语素,结果越分越分不清楚,就连一些教材里列举的几个基本例子也常常有例外的情况。如朱德熙先生所举的语素有“人、民、履、历、我、们”等,说只有“人、我”可以单独成词,其余则“本身不能形成单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结合起来形成合成词。”[8]但实际上汉语语素能否成词是相当灵活的,其中“民”和“历”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单独成词,例如:
民:军爱民,民拥军/利国利民/让利于民/为民做主/替民伸冤/军转民。
历:历尽千难万苦/历尽艰辛/历时八年。
与此类似还有许多常常被当作不成词语素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单独成词,例如:
令:一个将军一个令/令人头疼/军委令你部原地待命。
视:下周的郊游能否成行视天气情况而定。
伴:亲人伴我渡过难关/红星伴我去战斗。
暂:这项决定暂不执行/领导班子中正职暂缺。
侮:中国人民不可侮。
吕叔湘先生曾对语素能否成词的复杂情况做过精辟的概括,他列举了“楼、院、氧、叶、虎、言、语、云、时”等用例,说明许多语素在一般场合不能单用,但在一定的格式、专科文献、成语、熟语、文章等场合里,却可以单用的事实。可见汉语语素和词的界限很难截然划分清楚,其原因就在于这些语素(字)在古代汉语里都是可以单用的,而现代汉语是由不同历史层次的成分积淀而成的,现代典雅的书面语、正规的专业文献中所含的文言词语自然就多一些。这样就形成了目前的局面:有些语素既可以单独成词,又可以和别的语素组合成词;有些语素只能和别的语素组合成词;有些语素一般不能单用,但在一定场合又可以单独成词。因此,我们认为,任何语素只要能够单用(即在一定的句法结构中独立运用,不是“单说”),就得承认它是词。因为语素在汉语里是现成的,而词是从句法结构中分离出来的,其间没有严格的界限。二者的区别在于:
1)语素是静态的备用单位,词是动态的使用单位,它们是一种实现关系。所有的词都是由语素形成的,语素能否单独实现为词,全看它在句法结构中的作用。
2)一个语素可以形成几个不同的词。语素既然是备用单位,那么它就可能是多义的;词既然是使用单位,那么它在一定的句法结构中只能是单义的,而不可能同时具备几种意义。因此一个字的几个义项只要有联系就属于同一个语素,没有联系就属于不同的语素;一个语素的几个义项有的能单用,有的不能单用,能单用的义项就是一个词,意义不同的语素分别形成不同的词。例如:
锁(1)链子:锁链|锁镣|拉锁|枷锁。(2)加在门、箱等上面,起封闭作用的器具:一把锁|大门上了锁。(3)形状像旧式锁的东西:石锁|长命锁。(4)用锁关住或用链子拴住:把门锁好|锁上箱子|把猴子锁起来。(5)一种缝纫法,多用线斜交或勾连在衣物边沿上:锁扣眼儿|锁边儿。“锁”的5个义项都有联系,因而是一个语素;其中(1)和(3)在现代汉语里不能单用,(2)(4)(5)可以单独用在一定的句法结构中,因而“锁”这个语素可以实现为3个词。这3个义项在具体的语言环境里意义和功能一般不会混淆,所以分属3个不同的词。这就是所谓的“词的同一性原则”。至于词的同一性的确认和义项的概括,则属于另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