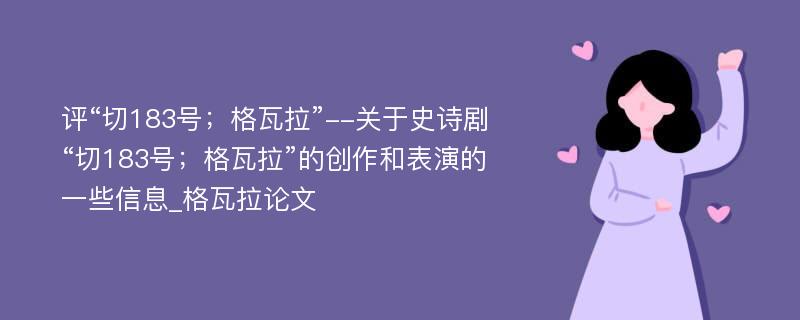
《切#183;格瓦拉》评论——关于史诗剧《切#183;格瓦拉》创作及演出的一些情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瓦拉论文,史诗论文,演出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切·格瓦拉》演出期间,常常散场后有观众和我们在剧场门口,在街灯下,在周围的小饭馆里,在深夜的电话中继续剧中话题的讨论,戏剧小舞台无形中伸展到人间大舞台。格瓦拉这位人类正义事业的使徒和殉道者所具有的永恒现实性,本是我们创作的起点,但《切》剧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却为我们始料所不及。以下就本剧创作的初衷、演出情况、社会反响三个方面做一简要回顾。
一、为什么要创作这部戏
这个问题经常分解为三小问:(1)你们为什么要搞戏?(2)为什么选择格瓦拉?(3)你们有什么“特别”背景没有?
《切》剧属集体创作,这个集体的几个主要成员无一从事专业戏剧创作。沈林的本职是西方戏剧理论研究,张广天从事的是工业化时代民间音乐的研究与实践,我本人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说,我们参与文艺特别是戏剧活动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为知识分子,作为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伟大传统的当代读书人,思考天人古今、关心国计民生是我们生不能辞、死而后已的义务。至于以什么样的形式担当起这种责任,则并不重要。去年杂文,今年戏剧,明年数来宝也说不定。但有一点,只要我们从事艺术,那就肯定是有感而发的艺术、载道的艺术、为人生的艺术;只要我们从事戏剧,那就肯定不是为了戏剧的戏剧、醉生梦死的戏剧、脱离人民的戏剧。
为什么选择切·格瓦拉?直截了当地说,格瓦拉对于我们只是一个载体,当然是最合适的载体。其承载的,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命运的思考和感受。引一段我们在创作之前写的《创作思想大纲》:
我们将要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怎样的格瓦拉呢?通过这位格瓦拉我们将要向观众传达些什么呢?
本世纪以来,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矛盾冲突,将人类带入空前的浩劫,使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对贯穿整个人类以往文明史的生活原则——剥削压迫——发生了深刻的怀疑。民族解放运动一时波澜壮阔,社会主义思想一时深入人心。格瓦拉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时代英雄。他不是那种礼花式的政治明星,而是真正地体现了对旧世界的彻底否定,对正义理想社会不屈不挠的追求。
历史并没有随革命的血与火飞流直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经历一番风雨飘摇之后终于稳住了阵脚。旧世界的新一代统治者痛定思痛,在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以缓和社会矛盾,使人民在花花绿绿的小恩小惠面前忘记或默认了被剥夺的事实。他们还把全世界的财富巧取豪夺到几个资本主义“窗口”国家,然后锣鼓喧天地向全人类举办“资本主义成就展”。八、九十年代保守主义张牙舞爪、新自由主义风行一时。资本主义俨然“长宜子孙”了。与此同时,处在旧社会滔天汪洋包围渗透下的新社会,倒是险象环生,终于一朝倾溃。昔日的革命者不少争先恐后地浪子回头,到各处的忆苦思甜会上哭诉革命的“暴政”,摩挲资本家的红包。为换取剥削社会的良民证,有些人公开放弃了对正义的追求、理想的探索,当众宣布与格瓦拉们的事业一刀两断。如此看来,我们舞台上的格瓦拉就不仅仅要立于五六十年代的风云前了,他还要立于八九十年代的反思前,更要立于对反思的反思、也就是世纪末的回想前。
我们从格瓦拉的一生中选取了几个片断,让它们和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意义的联系。比如第一幕“格拉玛号启航”,我们把格拉玛号从社会主义革命如日中天的五六十年代,放到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陷入低谷的世纪末,重新思考人类追求平等大同的事业究竟能还是不能,该还是不该。又比如第二幕“人间长街”,通过格瓦拉学生时代漫游南美大陆,从中产阶级走向底层人民,从街北走向街南,我们在舞台上就贫富这一最具社会本质意义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再如第三幕“建设新社会”,我们对社会主义这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走出社会丛林的伟大尝试及其艰难历程做了沉痛的回顾。总之,格瓦拉可以说是一面镜子,给现实一个打量自己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条船,装着对过去现在的思考,驶向未来。
关于“特殊背景”问题,曾辗转听到一些议论,说《切·格瓦拉》必定有“来头”。不过某观众曾援引某名流的话:这是几个“无门无宗”的人搞的一出标新立异的戏。我们知道,名流从入门混到掌门,对各家各派的谱系无不烂熟于心,他们的见解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我们这些人的确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百姓,甚至党员也没有一个。做这出戏,根据的是独立思考,进行的是独立表达。比起抛出共产股吃进资本股、整日在外国基金会左近熟悉地形的所谓“自由”精英,我们真要纯粹出不少百分点。“谈艺不入文社,论世不缘政党”之类的佳话暂时也还轮不到他们。
二、关于演出的一些情况
包括加演的三场、(为贫困大学生)义演的一场,《切》剧一共上演了37场,平均上座率达120%,共接待了一万多人次的观众,有时过道都坐满了人,迟到观众站着看的情况并不少见。笔者不得不从家里带去几个折叠凳以备不时之需。演出真正达到了媒体所说的“火爆”程度,票房自是“不俗”。有些城市和大学还邀请我们去他们那儿演出。
关于演出的效果,媒体使用了“震撼人心”之类的描述,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相核对,大体属实。当然“震撼”并不就意味着认同,有观众看了戏“整个找不着东南西北了”,有观众看了戏“对生活开始迷惑”了,又有观众“出了一头冷汗”,还有观众听了某段台词“想落荒而逃”,这些都在证明该剧的效果以及效果的多向性。连看两遍的观众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五六场,最多的一位竟达十二场。这不免使人想到《泰坦尼克号》上演时的情况,并进一步思索争夺青年、争夺心灵的文化战争。难怪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切》剧在搞“精神吸毒”,难怪自由主义作家叹息,“这是人们,尤其是生活在21世纪之初的北京人和中国人的悲哀之所在”。
这次演出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以突出的思想内容和明确的社会功能改变了现有话剧观众的结构。大约前十场,来的还是传统的小剧场观众,即实验、先锋艺术的爱好者。在那之后,就有大学生络绎不绝地到来,约占去了观众总数的40%,印象中以清华、北航的同学最多。再就是不少老同志。天津赶来的一位女观众,用她的话说,是“普通退休职员”,在听了电台播放的实况录音后,十几个朋友在电话上进行了长久热烈的讨论。她在演出后的座谈中作了动情的发言。看着老人拄着双拐走出剧场的样子,我们整个演出集体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一些单位还专门组织党员来看戏。
我们平日听到不少关于艺术“规律”如何、艺术市场怎样的教条,意思不外乎把文艺定作三陪,将观众视为嫖客,让老鸨也似的文化商人捞得脑满肠肥。我们这次演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他们的花花“规律”,证明了文艺绝不是“下半身”的一统江山,正气一样会摇荡人心,高尚一样能赢得市场。我们总算在“历史终结”“告别革命”的水潭里丢了一块石头,给逍遥其中或正宽衣解带的人煞了回风景。
三、社会反响
有媒体在《切》剧演出不久便指出,这不仅仅是“一次戏剧行动,也是一次社会行动”。为人生的艺术理应如此,我们所极力追慕的兴观群怨、文以载道的屈杜传统历来如此。戏剧小舞台如果不能通向世界大舞台,满台的活色生香都只不过行尸走肉。应该说,《切》剧的特点在于它触及了重大现实历史问题,它的意义在于触发了大家对这些问题的思绪。亚子写到:
在这里,切·格瓦拉本人构成了一个伟大论坛,因他的缺席而形成的戏剧空间极大地扩展了该史诗剧的思想容量。紧紧围绕贫富问题、压迫与反抗、历史与人性、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等重大问题,在正反人物之间,艺术化地展开了短兵相接的激辩。
对《切》剧的反应见仁见智,毁誉势同水火。一位从郑州专程赶来的观众,说这是他“二十年来最痛快的一天”;而网上的一篇文字,则说这是“二十年中国话剧的奇耻大辱”。处于中间状态的则游移徘徊,矛盾重重。有位中年女记者对我说:“结尾的时候我也流着泪唱《国际歌》,但一边唱我一边对自己说,不行不行,社会主义就是没救了,中国就是没戏了。”每天演出后我们都和观众座谈,一问一答不免演成不同观点、价值、立场的激烈交锋。例如一次有位老者厉声喝问:“那你们如何看待输出革命!”我们也不禁火起:“那是因为帝国主义在输出反革命!”有时辩论就在观念之间展开。一位中年男观众在历数社会主义累累“罪行”、认定只有美国才真正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时,被一位大学生打断:眼光应该放远点,社会主义毕竟刚刚几十年,一时失败不等于永远失败。一位中年妇女忿忿道:你凭什么不让人把话说完,还有没有民主?!学生身后的老师则说:正因为我们的大学生敢于打断你们的话,我认为中国才有希望!辩论还从剧场扩散开去。有位留美学生约我改日继续探讨。后来我们就前东欧解体后的命运、就民主自由问题、专制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平等、人性等等交换了意见。有位记者告诉我,他到西安去,也听人家议论这出戏,“什么意见都有”。另一位记者最近来电话说,他一篇评论文章竟写了几个星期还是觉得思绪不清,以往写剧评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以下将这些反应分为正、反、中三种,并稍作分析。
持肯定意见的观众几乎都为该剧所宣扬的正气所打动,很多人能够认同格瓦拉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生活原则。几位从事新闻外交工作的老同志在演后座谈中热泪盈眶,说目前社会上自私自利歪风邪气盛行,正需要一声春雷。一位青年观众说,“这个戏反映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它让我看到不平等、压迫永远也无法阻挡正义的声音出现——这是一种启示,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一位大学生说,“我觉得大学生现在处在一种迷茫中,忧患意识慢慢地被掩盖、被埋没了。这部戏重新点燃了它,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路该怎么走。”另一位大学生说,“我们对现实已熟视无睹。这出戏重新触动我去分析、去思考,辨别善恶是非”。一位中年观众说,“谢谢你们告诉我,世界没有变——真善美没有变,正义没有变!”一位母亲说,“在当今赚钱为上、做官为上的时代,我们的理想和信念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部戏直指人心。现在的孩子们是以我为上,我想这部戏也是对年轻人的最好教育。”有位上了年纪的观众说,“在忙着崇拜西方的年代,能有这样的戏,我为现代青年的精神自豪。”一位研究劳工问题的教授说,“我没想到年轻人在考虑这么深刻的事情。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现在是老板文化,而你们却为工人、穷人说了话,我非常高兴。今天我们系的全体教师都来了,明天我们要组织全体学生来”。
有些观众还能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有一次来了十几位老部长,最大的已经87岁了,其中一位代表他们发言:“当今有人在‘告别革命’,而你们却在宣扬革命,坚持革命,有很多新思想、新论断。”有一位观众说,“整个世界弥漫着资产阶级的倾向,但无产阶级总有一天要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早晚要垮台。”有位从事新闻工作的中年同志讲到“父辈们开创的革命”时不胜感慨,声泪俱下。
清华有位博士生在给张广天的长信中反省了自己的经历,讲得朴素真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看不惯很多不公平的事。看不惯当官的欺侮穷人,搞不懂为什么父母拼命干活而收入却远远低于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更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高考报志愿时我报清华,那时我想我一定好好学习,将来回到家乡当个市长,好好治一治这些贪官。上了大学以后,感觉眼界一下子开阔多了,竟有些不知所措……对于国家,劳动人民我却关心的少了,感觉是渐渐地被这个环境同化了,整天想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还经常无缘无故地感伤(无病呻吟),这就是一年以前的状态。去年的5月8日,美国的几颗炸弹炸醒了很多人,也炸醒了我,虽然那时有许多东西还看不清楚,但已经足够使我产生很大的变化。到今年的三月台湾大选,我的政治热情(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词)被激发起来了。《切·格瓦拉》则给了这一切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我告别了过去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第一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回归。
(这封信在网上发表后,点击律非常高)
反对的观点除了在演后座谈会上以及私下交谈中听到,还在网上和报刊上读到不少。这读到的,因为不存在真人对真面的问题,颇有几篇直呼我们为“这些家伙”——切齿之声宛如听到。反对的意见相当成“体系”,而且情与理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仅三年五载的社会化绝达到不了这番境地。例如,觉得格瓦拉是疯子的人,多半也认为“两弹一星”无聊,不过“加强了共产党的暴政”;听见“革命”二字便反感的人少不了要在艺术上对“活报剧”“广场剧”嘲讽一番。他们对《切》剧的“质疑”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1)格瓦拉们的社会理想纯属虚妄;2)格瓦拉们的政治道路通向法西斯;3)资本主义才能拯救人类。总之,是对社会主义全盘否定(而且还要株连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庚子年间的义和团),视由美国领衔新罗马帝国为人间坦途。有位观众的发言很有代表性:
所有的革命者都说要带领人民走向天堂,结果却把他们引进了地狱,包括格瓦拉、马克思等人。文化大革命也犯了很多错误,儿女反对父母,母亲出卖孩子,这是人性的堕落。我觉得改造社会应该用改良的办法而不是革命。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最发达的国家,谁都愿意去美国,不想往穷国家跑。
有位作家在评论文章中以跟美国鏖战了多年的越南为例,进行奚落:
时隔半个世纪,越南人自己戏言,战争时期,我们的口号是,赶走了美国佬,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现在,人们说,美国佬回来了,一切问题就会解决。
其实,持右翼观点的人不乏和我们一样疾恶如仇、居心善良的方正之士。大家如今的针锋相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民族经历的曲折、求索的艰难。记得有回演后座谈会结束了,还有些观众在那里辩论,一位中年女性异常激越:“这么多年轻人跟着激动,我觉得太恐怖了!难道四九年那次抢劫还不够么!”后来他们邀我到附近的小铺继续辩论,大家比较平心静气地谈了几个小时。分歧当然不可能消除,但都同意应对一些似乎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做重新思考。我有时在想,知识分子具有两重性,他们的屁股既分别坐在他们所代言的阶级一边,但两脚也插在同一大堆中西书本里。他们的分野既是立场的,也是认识的。有时辩来辩去辩出一句“穷人活该”或“人渣就配吃药渣”,辩论只好结束,因为接下来的是立场或社会存在了。但也不排除有人昨天读了马克思于是左倾,今天读了哈耶克便右转,来日很可能取中间立场,因为枕边正放着本《正义论》。立场与认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我们演出集体中一个家道颇殷实的演员,初来时觉得这出戏是针对她的,听了台词直脸红。后来通过学习思考比较认同了《切》剧的立场,经常在组里做好人好事。
中间的观点很值得玩味。有个观众说,“《国际歌》响起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可是走出剧场又回到了现实。这个戏在多大程度上,能像台词里说的‘将人心点燃’?”某文学杂志的负责人说,“看你们的戏流泪激动,但回家以后再一琢磨,不对啊,格瓦拉是行不通的。这个社会有脑无心,可你们的戏是有心无脑。”另有一个年轻观众说,“我非常非常愿意停留在这出戏的气氛中,因为人跟人应该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戏总要散场,我还要回家”。一位做网络的青年人在海报上给我写了一番话,“看了这出戏,我很受震撼。我不会改变我的生活,但我对自己的生活一定会重新思考。”还有一位观众说,“我是一个从文革中过来的人,已经50多了。以前看过格瓦拉的日记,当时我的战友中有很多人受了他的影响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不少都牺牲在越南。抚今追昔,思绪万千……没想到你们把格瓦拉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了。这样做,很有意义。但转而一想,又觉得这些问题恐怕永远解决不了,人类只能得到相对的公平。”这些人大都认同正义理想,但他们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新败、资本主义中兴的事实以及各类“历史终结”的叫嚣。
还有些观众希望把格瓦拉对于“正义”价值的一般追求,从他对道路的具体选择中剥离出来,使他成为一个纯粹的大侠:资本主义有罪恶他固然要吊民伐罪,社会主义出了问题他也应一视同仁,断然倒戈。一位在世行工作的观众说“我同意格拉玛号‘前往前南母亲默默流泪的地方,前往战斧导弹满天飞舞的地方’,但为什么不能前往北朝鲜大饥荒的地方,前往红色高棉大屠杀的地方,前往斯大林大清洗的地方?”应该说,这种见解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但它在似乎直面现实的同时,却未能正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南方有位学者对我说,左派具有道德上的优势和经验上的劣势。这话有几分道理。要想追求一种更人道的生活,就不免要背离四千年虎狼之道的“经验”,常常落入无所依傍的尴尬境地。理想的正义与路途的艰难既造成了现实政治的分野,也构成了《切》剧的悲剧底色和孤绝姿态。我们戏中有首歌是这样唱的:“陆地淹没了/你就在海上飞翔/海洋干涸了/你就在天上飞翔/天雷滚动了/你就在火里飞翔/火焰熄灭了/你就在苦难中飞翔过去倒下了/你就在未来飞翔/未来退却了/你就在现在飞翔/现在迟疑了/你就在心中飞翔/心灵败坏了/你就在创造中飞翔”。以人道为终极目的的社会主义探索,是人类在价值上告别动物世界的一次最悲壮的出走,是一段百折前徊历程,是一首悲欣交集的史诗。有位观众讲得非常好:
我是40多岁的人了,一直觉得社会要达到公平和正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一直在这种矛盾中徘徊。这个戏我已经看了五遍,每次看都受到更深的感染,唤回我内心对正义和理想的渴望和追求,让我知道自己以后加倍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结果。
演出结束后我们在《真理的追求》编辑部召开过一次座谈会,在京以及外地甚至海外的学术思想界朋友一共来了几十位,大家进行了十分坦诚热烈的交流。亚子在他的文章末尾期待着这出戏的“理论续篇”。如今社会主义处于低谷,这未尝不是我们文化思想工作者退而结网、检讨过去思索未来的最好季节。这个季节的劳动,将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重新出发,格拉玛号能否再次启航。
标签:格瓦拉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戏剧论文; 正义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