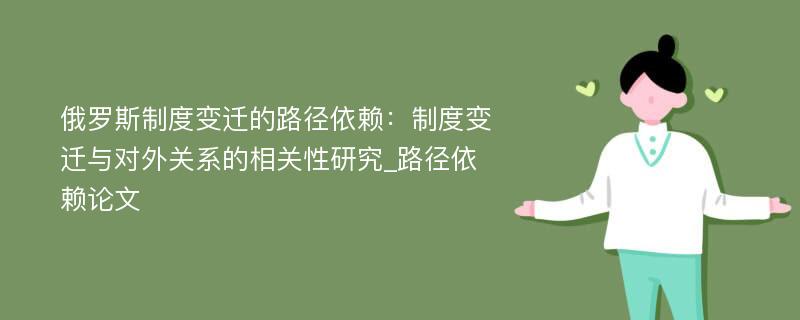
俄罗斯体制转型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相关性视角的一项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相关性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近二十年来,俄罗斯的转型和发展过程展现出极其丰富的内涵。这一问题对于整个转型研究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迄今仍然处于有待发掘和研究的状态。本文试图通过对俄国转型的路径依赖的分析,探讨体制转型与对外政策之间的相关问题。
一、为什么要将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首先,我们需要对本题的几个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在一般意义上,体制转型指的是从传统集中的计划经济与政治高度集中的体制,向法制化的、有更高程度民主的、同时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现代管理体制转变。这一过程就是转型。
转型至少涉及两个英文词汇,即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其中,前者较为常用,强调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类似于在机场换乘飞机,需要有签票、改道、换机等一系列的过程。在转型过程中,指的则是对于另一种发展模式的选择。而后者则更具有整体性、革命性的涵义,也包含有强调突变的可能性。①就体制转型这一概念来说,尽管我们在中文的理解上是指从传统体制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市场化、民主化和法制化体制变换的过程,但是从英文和俄文表达上会找到不同程度的、不同色彩的表达,这说明体制转型的理解还可以有多种表达。显然,不同形式的转型过程有着不一样的外部环境相伴随,也有着不同的对外政策与战略取向。
与转型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制度范式”(system paradigm)。这一概念是由雅·科尔奈(Janos Kornai)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并认为“制度范式”强调的是不分学科地把整个转型过程看成为一个整体;强调整体研究眼光之下的社会运行的基本体制特征;强调与静态的研究不同,注重的是动态的体制转换过程;强调比较的方式是转型研究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科尔奈特别强调转型发生的历史条件、阶段性变化、外部环境以及各个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科尔奈甚至认为,近三十年来所发生的转型,是15-16世纪整个世界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社会以来所没有过的宏大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样一种转型研究的观念则进一步关联到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这个问题。因为,外部环境和外向拓展问题直接成了内生于“制度范式”的一个部分。②
对于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研究,在学术界已经有了较长时间的讨论,但是也存在着很多盲区和空白点。
关于国内制度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学科形成伊始,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其发展经历了复杂的过程。比如,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等早期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作品都非常强调国内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反而到了新现实主义时期,特别是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将国际关系理论结构化,把国际关系主体的思想内容抽象化以后,每一个在国际结构中活动的主体被视为单一的、同质的存在,然后强调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结构关系的变化。这样就将内部的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这个重要问题抽象掉了。③
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二战以后的政治理论研究(包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多年来主要局限于国内政治的研究,并不把国际政治问题纳入视野;而国际关系理论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抽象化了”国内问题。这样一种状况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和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处于相互游离的状态。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五十年的分离:思想史与国际关系”一文中对此也作了很好的梳理。④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全球化趋势有所发展的背景之下,新自由主义理论兴起,对于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国际政治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都提出了很多类似的问题。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首先提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在70年代末,基欧汉提出外交政策的实质就是为了塑造一个能够跟国际环境匹配的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安排。基欧汉所编撰的专著《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中,苏珊·秀克(Susan Shirk)的文章就是从这样的视角提出,当年中国加入WTO就包含着进一步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战略目的。⑤
到了1988年,普特南(Robert Putnam)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双层博弈》(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普特南在文中提出,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不光是开展对外活动,他同时还要回过头来面向国内,对国内的整个利益集团以及各个层次的政治、经济关系作梳理和整合。“双层博弈理论”提出以后,这个话题就开始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⑥
在这样一个语境下讨论俄罗斯问题,我们会发现,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的俄国,还曾经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她在20世纪前期和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两次变革都引发了巨大的世界性反响。为什么这些撼动全局的现象都发生在俄国身上?而且,无论是当年的十月革命还是今天的转型过程,都表现出了内部制度变化与对外政策的密切关联。因此,至少可以认为,将内部过程和外部取向相互脱离的研究方式,在面对俄罗斯问题这样一个宏大进程的时候,是不甚适宜的。
在当代这样一个世界环境下谈论这个问题,还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结构。G20等国际新形态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经济、包括政治体系未来的前景,即新兴国家参与世界治理已经是不可改变、也不可阻挡的趋势。那么,正在发生重大影响的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内部进程将会如何作用于整个世界进程,而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又将如何作用于上述国家内部的进一步转型?这些国家究竟是将会以内部制度转变的惯性更多地延展于这个世界,还是更多地领受外部影响而认同于现行的国际体制。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俄罗斯,而且事关中国。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国内制度与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对于我们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发展的方向和趋势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关于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相关的理论要素和相互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国际环境如何影响国内的制度变革
第一,开放性的国际环境对体制变迁产生引导作用。
回顾近三、四十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开放的国际环境,或者在一个区域合作的环境,甚至全球层面上的合作环境,能够使得不同体制的国家相互借鉴各自的优点和长处,而不一定是产生互相之间的恶意竞争。所以,即使在今天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并没有出现上个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那种程度的各国恶意竞争、多米诺骨牌式地竞相推动保护主义政策的状况。在今天的国际市场上,虽然有一些针对新兴国家的举动,但并没有出现全局意义上的保护主义态势。这种情况的出现证明,即使碰到了严重的波折,世界各国仍然认可开放的国际环境。这对于各国国内体制的发展和进步是有很多益处的。
第二,开放环境对当地传统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带来新的挑战。
这一点对新兴国家的影响尤为明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问题是研究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相关性的核心问题。面对开放的国际环境,传统文化应该如何适应,思想意识形态又应该如何调整和构建,这是一个必须正视和认真加以研究的问题。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与苏联80年代的改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盖达尔(Yegor Gaidar)在讲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曾提及,戈尔巴乔夫认识到苏联体制必须加以改革,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比较清楚。但当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台以后,他至少需要三年时间来学习怎样制定改革政策。非常可惜的是,他没有运用好这个机会,尽管80年代中期的情况其实还没有那么恶劣。⑦当时指导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他唯一的著作《改革与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开放的国际环境,过于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任何超级大国都是无出路的。但同样,任何放弃对于本土价值的思考和坚守,同样会带来灾难。而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这本书中几乎没有一个词提到苏联的本土传统、本土价值。他讲全人类,讲改革,讲开放。⑧这些都没有错。但正是对于本土文化和自身思想意识形态构建的忽视,最终带来了整个意识形态的偏颇。也就是说,在改革的起步阶段,他的整个认知水平和制度安排为以后的改革设下了前提,而这种前置性的偏颇是很难调整的。
第三,外部环境的压力导致了内部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也带来了体制变迁的巨大压力。
根据基欧汉的研究,开放条件下世界经济中的价格、汇率、关税等机制与杠杆,是能够对于国内制度变迁起到引导作用的。⑨一般来说,几乎所有转型国家,特别是在经济开放后,都出现了国内产业二元化的趋势。一部分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另一部分企业面向国内市场。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往往成为盈利和高收入企业,具有比较好的福利条件。而面向国内市场的部分企业在经营情况和待遇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反差。不仅如此,在开放条件下,我们可以看到参与国际活动的主体大量出现,不再局限于国家、公司,甚至个人、旅游者都成了国际交往活动的主体。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使得原有的体制管理和体制适应均面临很大的压力。因此,是倾向于精英式的利益分配格局,还是倾向于平民主义式的利益分配格局,这样一类事关体制安排的选择,马上就会成为国内政治博弈的焦点。
(二)内部制度变迁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
从体制变迁造成的影响来看,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将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
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和产品在很大程度依赖国际市场,那么它的对外政策的开放性几乎很难逆转。这个问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制度安排,也有地理原因。例如,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讲到帝国的时候就说过,如果我不得不生活在帝国,我最好生活在帝国的沿海地区。⑩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如果她的整个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它需要海外市场,它的内部资源需要输出,随之整个文化也需要更多的交流,而与其匹配的对外政策就理应是更加开放、而不是封闭的。特别是其沿海地区的开放程度往往比较高。而且,对外依存也并不局限于沿海地区。例如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尽管身处内陆,但对于海外市场仍然有很大的需求,特别是这些能源型产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迄今为止,当其产业结构表现出对于外部市场的依赖的时候,其对外关系的开放和多样化取向,从长时期来看乃是一个趋势。
今年四月初,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Alexei Kudrin)在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的学术年会上直截了当地提出,今年俄罗斯不再有新的贷款发放,其基本原因是目前俄罗斯的资金依然短缺,而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能够改变以能源依赖为主的经济模式;除此之外,除了外资企业还能维持,几乎所有的国内企业都运转不良。这说明,长期的能源依赖型经济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因此,库德林甚至强调,俄罗斯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政治也需要改革。(11)由此可见,俄罗斯虽然大部分地区地处内陆,但是它的资源依赖型经济模式使得它的对外依存度太高。而既然对外部世界存在着高度的依存性,那么,指望它与西方保持长期抗衡状态,是不能持久的。
第二,制度变迁效应的“外溢”。
制度变迁具有发散性,会迅速超越一国的界限,向外扩展。有两个很明显的例子: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后建立了新的政治制度,然后随着拿破仑战争的扩展,整个19世纪的前期,中欧、东欧的民族国家纷纷出现。实质上,这是利用武力推进制度变迁的扩展。这一做法为以后制度变迁采取强烈手段的外推开了一个头。另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第三波浪潮”。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著作中曾谈到,在到新自由主义思想扩张的背景下,在世界各地所出现的制度变迁过程呈现出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了像雪崩一样的政治变化。(12)我们所说的从80年代初开始的整个制度转型和改革过程,并不局限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我一直认为,所谓制度转型最早出现在70年代中期的南部欧洲,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出现,然后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拉美直接受其影响,同时东亚在80年代也出现了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13)
第三,传统价值对于对外政策的塑造。
体制的核心部分是它的价值,而它的价值当中的传统因素始终有着重大的影响。犹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相混合的价值观对于外交始终保持着巨大的影响,也如中国传统当中天人合一式的和谐中庸的世界观也强烈地塑造着当今中国外交,像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也是文明古老的国家,它的传统价值对于它的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不仅是它内部政治经济体制变迁过程的激进性,而且还包括整个对外政策的趋向,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其中既有传统弥赛亚精神作用下与生俱来的救世情怀,还有作为欧亚大国的多方位外交在长期积累之下形成的灵活多变、善于适应形势、并且很会交替运用软硬两手的外交经验与风格。这也是我们在分析时需要注意的内容。
(三)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相关性借以发生的载体
通过哪些载体可以在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之间建立有效联系,也是转型研究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否则研究无法深入推进。
关于制度从外部输入的问题。就整个国际关系史而言,制度的外部输入曾经有过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从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从宗教改革到民族国家系统建立之初,人们看到,随着文艺复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过程几乎席卷所有欧洲国家。第二个高潮,是前文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那样一个民族国家纷纷诞生的过程。第三个高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主导的民主制度的输出,一直延续到今天。另外一方面是以前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思想的输出。制度输出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不仅牵涉到国际法、政治理论,而且牵涉到现代伦理学研究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到现在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里面包括着:是否需要从外部输入体制因素,以及用怎样的方式从外部输入体制因素等问题。多年以来对于苏联晚期扩张性外交的批评,新世纪以来人们耳熟能详的对新保守主义鼓吹的“民主推广理论”的批判,都是这一范畴的问题。制度输入的问题至少涉及一系列的载体,诸如武装力量的使用、意识形态的扩张、包括一直被称为是公正的国际法程序被“片面”运用等等。人们发现,看似“价值中立”的这些规范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运用”的。
除此之外,在载体方面还有很多因素值得介绍,比如货币因素。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就曾经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说,金融、货币不仅是国家主权和文明的象征,而且货币本身就是沟通国际社会的重要渠道。因为货币至少表现出两个功能:一个是储蓄,一个是交换。货币体系中的利率,原来在一国条件下它主要起作用于内部的金融管理和储蓄。而在开放条件下,利率也成了影响资金流动的重要手段。至于货币的交换功能,特别是通过汇率跟外部世界进行能量的交换,在当今世界的国际纷争中特别显眼。(14)所以像货币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比较强调的是国家的主权体现,而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对外交换的重要工具。转型时代俄罗斯的利率政策曾经起到过戏剧性的作用,当年硬是靠超高的利率把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给压了下来;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多年相对稳定的汇率不仅表明俄罗斯宏观经济的趋稳,而且卢布的坚挺也预示着在今后的国际金融秩序构建中,俄罗斯将是不可忽视的一方。
在制度变迁和对外政策的相关性问题的讨论中,还有一个社会载体问题也值得讨论。比如,“中产阶级”这一范畴。一般情况下,我们把中产阶级看成是推动国家开放、进步和稳定的重要力量。比如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欧洲经济复苏和60、70年代欧洲缓和局面的出现,显然跟欧洲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作用有关。因为从本质上说,当年欧洲中产阶级需要的是稳定和相对平和的国际环境。但是,对于转型国家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大学教授、法律工作者、医生等等人群,一般来说,他们都比较趋向于开放和追求和平外交政策。但是我们也经常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出于维护本土价值和利益以及维护传统文化的需要,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也会表现出对于外来影响和外来因素的激进情绪,比如,对于移民的态度。所以,我认为,中产阶级在整个制度变迁和对外开放当中,它的角色与功能还是一个动态的现象,因时因地而异。
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在具体的转型研究中进一步把握,并且结合具体国家的转型过程出现的实际情况,加以研究和把握。
三、俄罗斯体制变迁与对外政策相关性问题上的路径依赖
下面我们将视角转向俄罗斯这一案例。从俄罗斯转型的经历来具体分析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国家的发展的。
转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这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一旦人们作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程序化的、惯性的力量会使起始的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现在,这已经是制度经济学中的惯用概念。这一概念不但标明改革的路径,而且也指一种状态。即当你选定了最初的方向,改革的最初安排就会使你以后的改革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产生递进的效果。就像电脑程序一样,可以按照某种路径进入,也必须按照特定的程序退出。当然,社会改革无法像电脑程序一样,在启动以后,是很难有退出的机会的。
路径依赖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它隐含着另一个概念——“选择”。路径依赖与选择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般来说,我们比较强调其初始安排将规定今后总体的发展,但并不是说在每一个环节的发展和转折的过程中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正如科斯(Ronald H.Coase)等制度经济学家所说,选择是始终存在的。路径依赖不等于说转型主体在转型的过程中毫无主动能力或者主动运作的空间。路径依赖的存在,不等于说开头出现了错误,就会一直将死路走到底,其中也可能存在着进行调整的空间。
那么,在确认内部转型和对外政策之间存在相关性的前提之下,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路径依赖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呢?
研究俄罗斯转型过程的路径依赖问题,可以围绕以下四个问题展开:
(一)自由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进路线
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俄国进入改革阶段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逻辑,即俄国的改革从传统体制走向改革开放,走向自由主义;但是它走向自由主义以后,并没有出现民主制度稳固化的阶段,也没有出现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甚至也没有出现国家管理的稳定状态。我们看到的是政治权力在各个集团的精英之间不断地转换,或者在政治跟商业集团之间转换,看到的是动荡和不稳定。到了90年代后半期,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由自由主义起步的改革,它导致的结果却是平民主义的上升。平民主义在俄语当中还有另外一个词叫作“民众主义”,整个决策听从民众的意见。
这样的逻辑并不只是在俄国出现。实际上这个过程,即从传统主义走向自由主义,然后走向的并不是自由主义的稳固,而是相反出现了平民主义。这在拉丁美洲也出现过,甚至在其他地方也能发现这样的逻辑。
平民主义不等于保守,但是平民主义的确与对对外政策有很重要影响的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是贯通的。平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族主义,表达出来的是民族主义的思考方式。从这个角度讲,俄国改革路径的发展过程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也不仅仅是在俄国出现,也是今天许多国家社会转型过程当中的发展路径。弗拉基米尔·马乌(Vladimir Mau)就在自己的论著中将俄国改革同法国大革命作过比较。他发现了一个相同的逻辑:当年法国革命从“雅各宾党”到“吉伦特党”,最后一直到具有保守倾向的拿破仑执政,是通过政治形式的保守化来实现对改革成果的保护的。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革命的成果是通过保守化的资产阶级宪法——拿破仑的资产阶级宪法才得以保存下来的。(15)
我们看到俄罗斯的改革过程,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Boris Yeltsin),最后再到普京(Vladimir Putin),也展现出了非常类似的过程。改革大幅度地突进,但是大幅度推进之后并没有得到自由主义的稳固、民主体制的稳固,相反在形式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保守化。这样一个过程不断地被重复,要经过一个很长阶段的过渡,才能够使自由主义的诉求逐渐地转化为民主政体的构建。这一现象是不是体制变迁的一般逻辑呢?如是,这样的逻辑会产生怎样的国际影响?显然这又与以下重复出现的逻辑相互联系。
(二)与西方关系的周期性逻辑
非常值得人们关注的是,最近二十多年,亦即冷战结束前后的这二十多年来,为什么每一次俄罗斯与西方调整关系的结果总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在这里,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独立以来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政治发展逻辑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即几乎每一任政治领导人在其执政开始阶段总是以倾向于西方的政治选择作为开端,但是,在其执政之末,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与西方关系的崩坏或疏离。
戈尔巴乔夫改革显然是一个20年来俄罗斯接近西方的开端。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的求助不成,反被抛弃,以及苏联的最终解体。这是第一个轮回。叶利钦开始执政时以内政与外交向西方“一边倒”为起点,但是激进政策所引起的是政局不稳、民怨沸腾,乃至于最终发生俄罗斯与西方交恶的科索沃战争。这是第二个轮回。普京2000年当选总统时,明显地以回归欧洲为起点,包括在2001年“9·11”事件中给了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帮助。但是到了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处于相当低落的状态,卸任总统后不久,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便发生了“五日战争”(16)。这是第三个轮回。梅德维杰夫(Dmitri Medvedev)接任以来,显然是又一次以“重启”与美国的关系为起点,但是,待他刚刚访问美国归来,却又传来美国抓捕俄罗斯间谍的消息。
与上述历史现象有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二十多年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这一逻辑与国家内部结构有何关系呢?
与上述逻辑相伴始终的是俄罗斯内部政治的演变进程:也即几乎每一任俄罗斯政治领袖在其执政之初,都是以相对宽松的施政风格登上政治舞台,而到末了,总归是多多少少地走向了权力的相对集中。戈尔巴乔夫以民主化改革为开端,但是几年以后,便走向了由一人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总统职务的局面。叶利钦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但是到他执政的晚年,却出现了“家族政治”的局面。普京总统执政初年表现的宽容和励精图治,使得俄罗斯得以重归大国的行列。但是八年执政的后期,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对于其国内政治“集权化”的尖锐批评。梅德维杰夫总统就任以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背离这种惯性,尚难断定。
换言之,上述连续四个轮回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由好转坏,往往是与俄罗斯内部政治结构“先民主、后集权”的反复重现相对应的。再进一步说,只要俄罗斯内部政治中这一现象重复出现,尽管实际情况并不像西方媒体渲染的那么可怕,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就始终是一个难以稳定实现的目标。
虽然,本轮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出现了不少新的背景,比如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使得双方都无力再回到“新冷战”这样一种对抗态势;又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又使得作为半个西方国家的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有了一层新的接近。俄罗斯与美国《削减战略核武器协定》的确立,就是这种改善的一个鲜明例证。但是,由于上述历史逻辑的存在,俄罗斯与西方的接近,多少将受到限制。
(三)纵向的“第二次转型”与横向的“第四波改革”
俄罗斯转型研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范畴——“Second transition”(第二次转型)。这也是受到一位美国同行启发后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所谓第二次转型,在俄罗斯,大体上是在新世纪之后出现的。按照他的说法,这个过程不仅在俄罗斯出现,甚至在中国也有某种迹象。第二次转型的出现,是为了对80年代以来第一次转型过程当中出现的制度陷阱进行弥补,进行修缮,进行调整。这是一个对于转型进程的大体中性的评价。这个概念可以用来作为观察某些现象的出发点。(17)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一定要用保守、改革这些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而是可以使用功能性的说法,来描述转型的过程。整个90年代,俄罗斯遇到了太多的困难:社会秩序的紊乱、经济发展的滞后、外交的消沉。如果不是普京上台以后进行的调整,现在的情况可能会更糟。尽管西方对于普京有很多的批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这一过程。有人认为,俄国第二次转型的起点是在2003年,标志性的事件是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同时,俄国和法国、德国一起,反对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也是在这一年,中国也出现了一场有关“国进民退”的大辩论,来自香港的学者郎咸平对于国有企业中严重的资产流失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当然,2003年作为一个时间概念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中国的过程同俄国不一样,表现得比较谨慎,注意各方面的平衡。总之,不管是中国的还是俄国的“第二次转型”,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意义上的退却。相反,这是对于前一次转型进程的合乎理性的休整和修正,这样的一个看似停顿和进行调整的阶段,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有可能孕育着未来更大规模和更加深刻改革的到来。
在对转型进程的阶段性进行纵向比较的同时,学界还对各个转型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英国著名学者阿齐·布朗(Archie Brown)并不认同亨廷顿在其《第三波》中提出的俄罗斯转型不过是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国际进程的一部分的观点。在他看来,俄罗斯的转型自有其独具的特点,是独具特色的所谓“第四波”的一部分。阿齐·布朗认为:“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非社会主义制度的威权主义国家,比如南欧、拉美、东亚等等。而有着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经历的前苏联地区表现不一样,至少在接受西方影响这一点上,俄罗斯几乎是一个独立的过程,而没有受到多少外部的影响。(18)
(四)未来国际制度构建中的制度因素
俄罗斯内部制度变迁产生了怎样的国际影响呢?至少在西方,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判断,迄今依然是受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影响。这是俄罗斯转型的路径依赖中的第四个不可忽略的外部制约。
关于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学术界并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认识。目前总的来说,有三种观点:第一是著名的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观点。在他看来,现在出现了一场新的冷战。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这样推行“威权体制”的国家,重新走到了一起。虽然还是在搞市场经济,但是政治上的立场则依旧如故,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挑战。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否搞市场经济,因为,目前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已经一分为二:一部分就像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另外一部份是欧、美为主导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19)到了“五日战争”爆发,在奥运会开幕式之后没几天,罗伯特·卡根发表文章认为,奥运会的开幕式与格鲁吉亚战争的爆发,就证明了中国跟俄罗斯这两个威权国家重新走到了一起,成为整个未来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思路。
第二个观点的美国自由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是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他在谈到未来体制的时候认为,中国和俄国这些新兴国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美国一国独大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接受或者用暴力推翻西方的制度。关键原因是国际体制和新兴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有了根本的改观。现有的国际体制不仅具有包容性,而且善于吸收新兴国家融入自己的体制。因此在他看来,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是非常乐观的。(20)
一个是悲观的,一个是乐观的,存在两种判断。这两种观点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目前以西方为主导的体制是非常完备的,俄罗斯和中国加入其中也可以获益,完全可以好好地进来享用,因此,也大可不必进行对抗与挑战。
但我想提的第三点,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互动来共同构建新的体制。美国新闻周刊的主编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是印度裔的美国人,他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也时有尖锐批评,但是他承认民主具有多样性。(21)关于民主是否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概念,普京表达的民主观点与西方不一样,与中国也不一样。中国坚持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普京则强调俄罗斯不会去搞具有俄国特色的民主,但民主原则在俄国要根据具体的历史、时间和地点加以执行。在目前的国际事务中,体制转型与国际秩序的构建显然已经发生了密切的关联。西方舆论中不可避免地已经将体制变迁因素作为国际体制构建的一个部分加以考虑。作为新兴国家,一方面完全不应按照简单化了的西方逻辑,不合情理地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是另一方面,尽一切可能发扬民主精神,新兴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合法性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证。在多样性前提下推进民主建设,这种理念将直接影响到未来国际秩序的建构。
从这一点上说,中俄之所以接近,中俄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合作的水平,我觉得除了战略利益的互补,以及历史背景的相似和地理上的接近之外,两国之所以可以比较方便地沟通,体制因素其实很重要。我认为,体制因素还是对中俄接近起了推动作用。因为当我们同样是转型国家,当我们同样背负着传统体制的包袱,当我们同时处在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碰到的是同样的困难,我们有同样的关切,我们同样受到了外部的批评。(22)这种政治文化,这种感受,我觉得使得我们两个国家的接近有了一种可能性。
四、结论与启示
对于体制变迁与对外政策的相关性研究来说,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俄国转型过程中呈现的经验和教训都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启示。
首先,俄国无论是推进改革还是推进对外政策的调整,从表面上看,一般都是危机反应。似乎只有危机才是推动俄国转型的基本动力,似乎不处于重大的危机之下,传统体制好像找不到动力让它发生变化。但是,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具有一定内在逻辑依据的转型进程,即上世纪80年代以后,俄罗斯转型实际上是依傍着一定的路径而依次发生变化的。从大的过程来看,首先以民主政治为转型的切入口;难以突破之后,转向自由主义的激进经济改革。而实际上,每一轮政治领导人物的上台,总是伴随着新一轮内部政治经济改革的启动。同时,每一轮改革启动总是辅之以与西方关系的调整。但是,从自由主义的路径切入之后,我们发现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向着平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翻转,民主政治重新返归权力集中,包括与西方关系由密渐疏的离异。而且,这每一种趋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如果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那种从自由主义—平民主义—民族主义的路径依赖转向,也就不会发生80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到普京,到梅德韦杰夫(与普京)几个时期一次又一次的从民主到权力相对集中(这是一个中性概念)的变化。相应的,也难以发生几乎每一个领导人执政时期外交上都反复出现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先是相互接近、到末了又重新交恶的循环形态。至于“第二次转型”与“第四波改革”这样一些范畴的出现,则清晰地描述了俄罗斯转型的独特与艰难。而未来国际秩序构建中、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体制担忧”,也表明存在着一个俄罗斯未来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关系的有限空间。这一空间的限制,与上述来自俄罗斯社会基层与上层政治现象的重合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惯性,一起构成了其转型的路径依赖的标尺。简言之,俄罗斯转型未必没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其演进的路径则远为曲折和偏离出发点,其转型的目标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有可能部分达致。
其次,即使俄罗斯转型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艰难空间中运行,但是,其对外政策基本上仍然呈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这一点和中国的外交传统正好相反。中国一般比较强调邓小平所说的“守拙”,而俄国基本上是以攻为守。即使在当代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俄国仍然奋发有为,而且显然颇有所得。这一点无论在与西方的交手中,还是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态势中,都有显示。这说明,即使经济危机使俄罗斯经济遭逢挑战,但是,其外交方面好像非但没有受到很大影响,反而愈加不折不挠。问题的实质是,除了俄国人的对外事务基本倾向一向就是以攻为守之外,还在于俄国政治精英对于转型进程中非常有限的机遇与政治资源的充分运用,以及对于转型的路径依赖的深刻洞察。这使得俄罗斯无论从内部还是从外部都在渐渐地摆脱苏联解体以来的困境。比如,梅普政治的出现。就像《围城》这部寓意小说中所言的“究竟是谁领着谁走?”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对于梅普两位,还是对于西方与俄罗斯这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值得推敲、而且是大有深意的问题。
再次,俄国无论内部转型还是对外政策都具有东西方兼顾的广阔视野,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注意。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经说过:俄国与一般帝国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他帝国垮台了,但它存活了下来。可以说,它是20世纪最后一个被终结的帝国。它特别善于利用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空间的优势。它经历过很多失败,但它仍然能够不断恢复,重新成长起来。马克思说过,俄国是一个具有非常长远的目光、善于确定目标、并且孜孜不倦地加以追求的大国。(23)因此,俄罗斯现象远没有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讲,对于体制转型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其中最困难的,是无论在思考内部体制转型、还是思考对外政策的时候,我们总需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这个取舍有时从体制的角度权衡,有时从外交利害关系的角度进行考虑。比如,我们多年来一直囿于对于“先进性”和“多样性”这两者之间孰轻孰重的考量。前者要求我们追随先进的发展与规范标准,而后者则遵从多样性文明共存这样的价值取向。我认为,在目前还难以确定是将“先进性”标准置于首位、还是将“多样性”置于首位的情况下,要紧的还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沟通”,以取得平衡。不能只顾追求“多样性”目标,忘记了若干普适标准需要顾及,也不能够只顾追求“先进性”而忘却自身发展的特性。
第二个问题是选择性与规律性。我们的确发现,有一些现象即使还谈不上规律性,却也是重复出现的。比如,类似于从自由主义出发,但却走向平民主义,然后又转向民族主义的路径转换;比如,不断循环出现的放权与集权,以及与之相应的先扬后抑的与西方关系的几个周期,包括在参与国际秩序构建的过程中被强烈要求接受既存体制,等等。总之,在这些路径演进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自己的选择性?选择性又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得以实现?选择性与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规律之间是怎样的状态?人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但是,俄国转型的丰富实践给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参照。
最后一个问题是继承性与断裂性。这是我们在思考俄国这个国家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我们在研究俄国问题的时候常常会这样思考:因为历史上的俄国曾经如此,所以今后的俄国也会遵循旧辙。这种思路本身也许没有错。但是,正如卡尔·波普所说,历史是不会重复的。(24)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对于俄国来说,它过去制度变迁的历史是不是能够证明将来,还是一个相当不确定的问题。对于俄国这个国家来说,经常可以发现它对于传统的接受态度,在很多情况下既是具有断裂性,又是充满创新性的。正如当年大家虽然看到了苏联经济正在走下坡路,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测到苏联的解体。同样,当人们都在预言俄罗斯依然困顿之时,不能忽视,一个未来的欧亚大国正在重新迅速兴起。
总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用历史来证明未来,这仍然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本文探讨的俄罗斯转型的路径问题,只是希望提供一种分析的视角,为进一步的思考给出参照。
注释:
①2009年冬天,美国前总统俄罗斯事务顾问托比·盖蒂(Toby Gati)和她丈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俄罗斯与欧亚问题资深副教授查尔斯·盖蒂(Charles Gati)来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访问座谈时,后者曾谈及关于“转型”的这两个词(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的不同含义。
②[匈]雅诺什·科尔奈:“制度范式”,《比较》,2002年第1期,第1-24页。
③参见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1990年版)中有关意识形态和国际关系相互关系的论述,以及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有关国际系统中活动主体的抽象化的论述。
④David Armitage,"The fifty years’ rift: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2004,Vol.1,No.1,pp.97-109.本文是经由本机构周保巍博士推荐后读到,特此感谢。
⑤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Edited by Robert O.Keohane and Helen.M.Miln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p.186-208.
⑥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Vol.42,No.3,pp.427-460.
⑦[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51-152页。
⑧[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第三章“我们怎样看待世界”,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69-204页。
⑨[美]罗伯特·基欧汉等:《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姜鹏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2页。
⑩[美]阿·塞尔·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问题的影响》,见“学报版引言”,范祥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64页。
(11)Выступления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P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Министрафинансов P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 А.Л.Кудрин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м заседани《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ки:рынки,фирмы и структурные сдвиги》,6 апреля2010 г.10.00-13.30,ул.Воронцово Поле,5 А,Культурный центр ГУ-ВШЭ.
(12)[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1页。
(13)参见冯绍雷、相兰欣主编:《转型时代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总序。
(14)[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3-121页。
(15)Ирина Стародубровская,Владимир Мау.Великие революции.От Кромвелядо Путина.М.:Вгриус,2004.
(16)我认为“五日战争”时,在俄罗斯起实际决策作用的还是普京。
(17)关于“第二次转型”的概念,笔者第一次听到是从与卡耐基基金会学者裴敏新的谈话中,时间大约在2004年。
(18)Archie Brown,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World: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Oxford Press,2007,p.218.转引自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封帅的一篇文章:“观念、体制与领袖——阿奇·布朗眼中的俄罗斯转型”(未刊稿)。
(19)Robert Kagan,"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Policy Review(a publication of the Hoover Institution),July/August,2007.
(20)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Feb,2008.
(21)2009年9月14日扎卡利亚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倡导的雅罗斯拉夫“现代国家与全球安全”国际研讨会上的大会发言。
(22)冯绍雷:“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与三个‘十年’的俄国问题研究——基于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比较的一项观察”,《俄罗斯研究》,2008年第4期,第9-11页。另可参见ShaoleiFeng,"China-US-Russia Trilateral Relations under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onfiguration in Transition",Sino-American Relations Challenges Ahead,Edited by Yufan Yao,Ashgate,2010.
(23)卡尔·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卷,第320页。
(24)转引自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The Long and the Short of Global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n Evolutionary Approach",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1999 Summer,pp.109-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