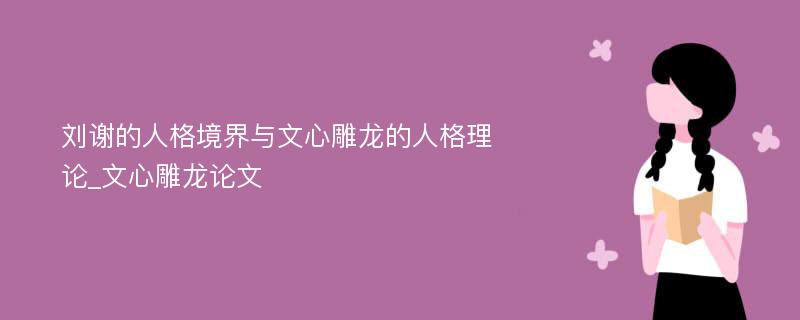
刘勰的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格论文,文心雕龙论文,境界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勰的一生,除了作《文心雕龙》而干之于沈约,还有两件事颇值得注意:一是早年依沙门僧佑和晚年燔发变服,二是天监年间出仕,官至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可见刘勰生活于佛的世界、文的世界与仕的世界。刘勰的人格理想是“学以达政”,“崇佛”与“研文”不过是“达政”之手段。然而,志大才高却势窘人微的刘勰,最终并未显达于仕途,而是以佛徒之身辞世,以文人之名永生。生存环境与理想人格的反差,酿成刘勰的耿介愤懑之气,并最终形成以“傲岸泉石”为个性特征,以“彩云若锦”为美学品格,以对生存方式之自由选择为高峰状态的人格境界。刘勰的人格境界,在《文心雕龙》中呈现为“道”、“智”、“性”三位一体的作家人格论。“原道心”、“研神理”中所包蕴的自然之道,与“怀宝挺秀”、“智周宇宙”所张扬的智术才藻,共同铸成作家人格的内质与外观:而作家个性的“其异如面”和作品风格的“风清骨峻”,又赋予作家人格以独特的美学魅力与永恒的艺术生命。
一、刘勰的三个世界
刘勰于齐武帝永明依沙门僧佑时,大约二十岁刚过。身为男子,当婚娶之年而入佛寺,刘勰为何作出如此选择?王元化认为,刘勰之依沙门僧佑,“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是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①a]刘氏世系中,最早显露头角的刘穆之,实以寒人身份起家,“少时家贫……好往妻兄家乞食”[②a],因此《宋书》关于穆之为“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记载是不可靠的,故在《南史》中被删去。张少康先生亦主张刘勰出身庶族,并认为舍人之依僧佑,“主要原因是想借助僧佑的关系,利用僧佑的地位,结交上层名流、权贵,为自己的仁途寻找出路。”[③a]
刘勰依沙门僧佑的原因是多重的。“南朝四百八十寺”,钟山上定林名列前茅,这里高僧辈出,饶有资财,又富于藏书。刘勰于家贫势微之时入居定林,既能解决温饱问题,又能找到一个读书的好去处。正如杨明照所描绘的:“舍人依居僧佑后,必‘纵意渔猎’,为后来‘弥纶群言’之巨著‘积学储宝’。于继续攻读经史群籍外,研阅释典,谅亦焚膏继晷,不遗余力。”[④a]刘勰在定林寺,可谓同时进入“佛的世界”与“文的世界”。作为僧佑的助手,刘勰佐僧佑整理经藏,编制目录,并代僧佑撰写各种序记;而作为以“弥纶群言”为己任的文论家,在定林寺的十年,又是深析文心、精雕文龙的十年。“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定林寺无车马之喧而有桑门之静,正是“论文叙笔”的好去处。
刘勰一生两次入寺。第一次虽长达十年,桑门却并未成为舍人志之所系,而只是“他希图走入仕途的终南捷径”[⑤a]。“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文心雕龙·程器》,下引《文心雕龙》,只注篇名),刘勰在等待时机,也许有一天,某位高僧会将他荐引给显贵,或者某位策踵山门的名流会为他打开仕宦之门……然而,至少在梁武帝天监初年之前,这种“机会”并没有到来。终齐一世,刘勰未获一官。如此才大志高之士,历十年苦寒而不见用,刘勰不能没有牢骚:《文心雕龙》“耿介于程器”,便坦露出一位不宦之才士的愤慨与悲凉。天监十八年,舍人受敕重返定林。是年,他已经出仕近廿年了。第一次入定林,居十年之久而未变服;此次入寺,不到两年便“燔发以自誓”(《梁书》本传),毅然皈依佛门。是彻底熄灭了功名之念,亦或终于寻到了心灵之归?刘勰从“佛的世界”出发,在历经“文的世界”之孤寂与“仕的世界”之喧嚣之后,又回到了“佛的世界”。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在依沙门僧佑时撰成。正如他身居桑门其志并不在佛,舍人潜心论文其志亦不在文。诚然,《序志》篇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之自白,但那正好表明刘勰之“心”还未寻到他理想中的载体或归依,表明他“文的世界”还未通向“仕的世界”。以文达政较之由佛而仕,似乎要容易一些、快捷一些。但对于命途多舛的刘勰,佛与仕,亦或文与仕之间,何来坦途?“无路”之路,全靠刘勰自己去走。然而,这是怎样辛酸而卑微的“走法”:“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梁书·刘勰传》)
寄居佛门而笃信儒学的刘勰,舍“注经”而取“论文”,诚然是对学术上“自成一家”之法的优选,更是顺应南朝“以文史取仕”之时风。齐萧遥光:“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为伎艺,欲求官耳。”[①b]陈姚察亦曰:“两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②b]马融郑玄的时代以注经求官,刘勰的时代则是以文史取官。
梁天监初,刘勰从奉朝请起家,开始踏上仕途。刘勰之祖灵真既未登仕,父尚所官亦不过越骑校尉,家贫以至于不能婚娶,更无余荫可资凭藉。那么,刘勰靠什么厕身仕途?细考舍人生平,多半与“佛”和“文”相关。刘勰于齐末撰成《文心雕龙》,负书求誉沈约,沈约大重之,恰如左思赋成三都,倚玄晏先生之序而名噪洛阳。舍人“未几入梁,即起家奉朝请。隐侯盖与有力焉。”[③b]正是靠了沈约的荐引之力,刘勰的“文的世界”方能通向“仕的世界”。
刘勰入仕后的第一个官职,是任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萧宏乃梁武帝异母弟,为崇佛之王侯,对僧佑“崇其戒范,尽师资之礼”[④b]。萧宏在僧佑处出入时认识了刘勰,因赏其才而任之为掌文翰的记室。靠了名寺与高僧,刘勰的“佛的世界”亦通向了“仕的世界”。刘勰仕宦二十年间,有一次较大的升迁:由位列九品的通事舍人,迁位列六品的步兵校尉。升迁之由,似与政绩无涉,却是因了一则与佛事相关的奏章:“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梁书·刘勰传》)。刘勰以佛心之笃而“对扬王庭,昭明心曲”(《章表》),使崇佛之梁武帝有“启乃心,沃朕心”(《奏启》)之悦,故“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梁书·刘勰传》)。刘勰之任记室与后来之迁步兵校尉,与其说是得事佛之利,不如说是因事佛而得萧氏兄弟之赏识。大凡寒士欲仕,必依附权贵。刘勰之前,有左思之附玄晏、鲍照之附临川。观刘勰一生,先后依附三人:僧佑、沈约和昭明太子。刘勰的“佛的世界”与“文的世界”,最终均能通向“仕的世界”,此三人当是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刘勰的人格境界
刘勰的“三个世界”,也可以说是刘勰三种不同的生存行为或生存方式。刘勰在他的“三个世界”中,先后(或同时)扮演三种不同的角色。《文心雕龙·议对》感叹“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而刘自己却既“工文”,又“练治”。刘勰“工文”自不待言;刘勰之“练治”亦有史可稽:《梁书》本传称勰“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而刘勰之事佛,表现更为不凡:不仅是“博通经论”、“长于佛理”(同上),而且献身于佛门,以信徒身份辞世。刘勰在“三个世界”中所扮演的三种角色都是成功的,无论是作为“文士”、“官宦”亦或“佛徒”,刘勰的人格形象都是不错的。
刘勰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梦”,一个是“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一个是“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序志》)。后者是刘勰自觉追求的人格理想,前者则是刘勰所期望达到的人格境界。二者与刘勰的人格外观一道,共同构成刘勰真实的自我,构成刘勰完整的人格形象。梦随仲尼而南行的刘勰,终其一生以孔儒人格范型为准的。刘勰人格理想的核心是孔儒的“树德建言”。《程器》篇:“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而这所谓“政事”,又是文武兼备:“岂以好文而不练武”、“习武而不好文”(同上)?故“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同上)。刘勰的“文的世界”与“佛的世界”,最终均通向了“仕的世界”,从根本上说,是对自己所认定的孔儒人格理想的身体力行,是人格的自我塑造。
研究刘勰的学者,一般不太注意刘勰的第一个梦,或者只是将第一个梦视为第二个梦的组成部分。我以为,第一个梦之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昭示了刘勰所追求的人格境界,而这一“境界”与第二个梦所揭示的刘勰的“人格理想”是有差异的。因此,刘勰的第一个梦有着独特的人格内涵。
刘勰所“原”之“道”并非纯儒,其间不乏老庄“自然之道”的意味。《原道》篇将“日月叠璧”、“山川焕绮”、“云霞雕色”、“草木贲华”等自然界的美,称之为“道之文”,也就是自然之道的感性显现,这正是抓住了美的本质与要义。这种体现了自然之道的合规律之真的感性之美,是刘勰梦寐以求的。
刘勰在他的“三个世界”中,追求的是一种现实的“名逾金石之坚”(《序志》)的成功感。刘勰“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同上)的儒家人格理想,与他学文达政、由佛而仕的人格形象是表里如一的。然而,刘勰在梦中“攀而采之”的“若锦”之“彩云”,则是一种超越了或消解了功利内涵的感性的美,因而也是超越了孔儒人格范型的具有美学意味的人格境界。
衡之以儒家人格准则,最能体现刘勰之成功感的,并非《文心雕龙》,亦非《灭惑论》,而应首推“太末令”、“通事舍人”、“步兵校尉”之类的官职与政绩。刘勰之“崇佛”与“论文”,都是为了仕途上的成功。因而,现实生活中的刘勰,不可能进入“彩云若锦”的唯美境界,他只有在自己精心营构的“文心”之梦中,才可能攀采到若锦之彩云。
刘勰的文学观,有着“尚质”与“尚丽”的矛盾。以“征圣”、“宗经”为本的刘勰,视“文绣鞶帨,离本弥甚”“为“异端”(《序志》);而《文心雕龙》却辟专篇讨论“声律”、“章句”、“丽辞”、“练字”等形式美问题。更有甚者,《文心雕龙》本身,“炳烁联华”、“玉润双流”(《丽辞》),实为骈俪之范本。以在《文心雕龙》写作实践中对俪辞骈句之美的追求,消解其文学思想中对孔儒“尚质”文论之恪守,昭示出刘勰唯美之人格境界对其孔儒人格理想的超越。
刘勰“攀云采锦”的人格境界,与他“树德建言”的人格理想一样,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基于他严肃认真的生活态度,基于人格主体对此岸世界的愤懑与不平。《序志》篇有一段文字,概括性地表述刘勰作《文心雕龙》时的心态与情感,其中有“耿介于《程器》”一语。《程器》篇颇为集中表达了刘勰的人格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刘勰自塑其人格,何以为准的?——“学文而达政”,“好文而练武”,“纬军国”,“任栋梁”。然而,在定林寺静待十载而不见用的刘勰,深知寒士入仕之难:“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史传》篇亦云:“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以叹息者也。”刘勰之前,先有左思“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之愤懑,后有鲍照“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之悲叹。而刘勰的“耿介”与“叹息”,实为两晋寒士忧怨之嗣响。
未仕之前的刘勰,集“才大志高”与“势窘人微”于一身。“树德建言”的人格理想,与“涓流寸折”的生存环境,构成强烈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成为刘勰人格生成与流变的内在动力,亦催生出刘勰人格构成中的耿介之气。“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好辩”,是他作为文士的生存方式或手段,通过“好辩”,他既可以将“文的世界”导向“仕的世界”,亦可以在“文的世界”中营构“攀云采锦”的人格境界。
为了打通由“文的世界”进入“仕的世界”的通道,刘勰甚至负书干誉、状若货鬻,于“涓流寸折”之现实中,表现出一位寒士的窘困与卑微。但是,当刘勰以一己之文心精雕文龙,并置身于一个纯粹的“文的世界”时,他有着足够的 自信与自尊,显示出一位文学理论家独特的人格魅力。
个体人格的生命,在于人格主体的独立与尊严。《序志》篇末之“赞”有“傲岸泉石”语,似可视为刘勰人格独立与尊严的诗性写照。鲍照《代挽歌》:“傲岸平生中,不为物所裁。”亦有“傲岸”一词。而“傲岸”者,乃不随波逐流,不媚世谀俗,有老庄道家“逍遥浮世”之韵,有魏晋名士“越名任心”之风。刘勰的“傲岸泉石”,与体现自然之道的“彩云若锦”,一实一虚,一刚一柔,共同铸成刘勰的人格境界。
“傲岸泉石”又是一位文士对文章之事的自信与自负。刘勰有感于时文之“去圣久远,文体解散”,有感于近代论文者之“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故决定“搦笔和墨,乃始论文”,立一家之言,建千载之功。刘勰曾自评《文心雕龙》:“按辔文雅之场,而环络藻绘之府,亦几乎备矣。”(均见《序志》)纪昀评曰:“此处自负不浅”。岂止是“自负”!是一位文论家对自己的思想与才华,对自己文论著作之体系与价值的充分自信。不难想见,在第一次入寺的十年孤寂中,这种对于“文”的自信,是怎样支撑刘勰消弥桑门之苦寒与不遇之焦虑。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审视,刘勰的“傲岸泉石”,甚至足以超越“佛界”之虚幻与“仕途”之庸烦,使得人格主体最终进入美的境界。
然而,考察刘勰的一生,不少时候是既不“傲岸”亦远离“泉石”的。他将“纬军国”、“任栋梁”视为人生之目的,终其一生,都在为这一目的而奋斗。或许,他太看重自己的目的了,为此,他甚至不惜牺牲人格的尊严(如负书干沈约)与真诚(如《时序》篇谀美南齐宗室)。然而,被刘勰视为目的的东西,最终并未成为目的。在写完《文心雕龙》之后,他有过近二十年的仕宦生涯,但他最终并不是以官宦的身份甚至也不是以文士的身份辞别人世的。如果说,刘勰年轻时的入寺,多半是出于生计与名利的考虑,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到了晚年,刘勰的燔发变服,则是一种自觉的选择,没有任何外在的力量,亦无任何世俗与功利的诱惑。
龙学界认为刘勰晚年弃官出家是一个谜。其实,由“傲岸泉石”到“皈依佛门”,实在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个体人格自觉而自然的演变。刘勰是在一种完全自觉因而也是完全自由的情况下作出如此选择的。在已逝去的时光中,他曾依附过高僧显贵王室帝胄;而临近生命终点的此时此刻,他不再依附亦不再属于任何人或任何观念。他只属于他自己。他是完全独立的。
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与最后的魅力,是自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只属于我自己。刘勰之归,归到一个自由的因而也是最高的人格境界。
三、《文心雕龙》的人格理论
刘勰的人格境界,其现实基础是才高势窘之反差以及由此而酿成的愤懑耿介之气,其美学品质是“彩云若锦”,其个性特征是“傲岸泉石”。而这一人格境界在《文心雕龙》中的具体显现,便是他的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作家人格论。
刘勰的作家人格论由三个关键词构成:道、智、性。刘勰所“原”之“道”,既是一个哲学范畴,同时也有人格心理学内涵。“道”之根本性质,是指由天地人“三才”所构成的宇宙本体;而“三才”之中,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乃“性灵所钟”,是“有心之器”(均见《原道》)。刘勰的这一思想,来源于上古心理学“人贵论”之传统。《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礼记·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天地间,人为贵。人之可贵,是因其“有心”,有“性灵”,是“最灵”、“最圣”者也。人之“心”、“性”、“灵”、“圣”通过其人格形象显现于外。天地人“三才”之中,惟人有格;故人之贵,亦贵在有人格。
《原道》篇指出:天地人之“道”,各有其“文”。日月、山川、草木、林泉、龙凤、虎豹……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千姿百态,五彩缤纷,以它们的“形”与“象”,以它们的“妙”与“奇”,既体现出天地之“道”(自然规律),亦传达出“道”之“文”(合规律之自然美)。刘勰梦寐以求“彩云若锦”的人格境界,表现出他对自然之道,对体“道”之“文”的推崇与执著。
“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为“三才”之一,为“天地之心”,当然也有体道之文。那么,人如何通过“文”来体“道”?“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均《原道》),“道心”乃人文之心,“神理”乃圣人之理。作家作文,以二者为最高目标;而作家之文所体现出的人格形象,又以二者为超验形态。
“三才”之中,亦惟人有智。《序志》篇曰:“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人之于“三才”中出类拔萃,是因其“智术”;人之超越时空而臻永恒,是因其能倚“智术”而“制作”。人凭着自己的智术与制作,“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同上)人生天地间,聚日月山川之灵气,钟草木泉岩之神秀,既能以一己之心感万物而动,又能以超常之智状万物之貌传万物之神体万物之道,最终以一种独具魅力的人格形象与天地万物共存。
作家的“制作”,将“为文之用心”物化为文学作品,其本质是一种审美创造,所谓“一朝综文,千年凝锦”(《才略》)。天地之文体“道”,在宇宙造化、时空凝聚中完成,并呈现为自然之美;人心之文体“道”则在以智力活动为特征的审美创造中完成,最终呈现为人文之美。倘若没有“智术”(创作才能),“制作”(创作过程)无法进行,作家人格无从外显,体“道”亦成了一句空话。
若将《文心雕龙》之《原道》与《序志》这一头一尾打通,则不难看出刘勰人格理论中“道”与“智”之关系。人,作为“三才”之一,与天地共存,并共同体现着自然之道;人通过“原道心”、“研神理”,通过“心生言立”、“言立文明”而传达出来的人文之道,便构成作家人格的形而上内质。人又是“天地之心”,是“三才”之中最有灵性者。“智术之子,博雅之人”(《杂文》),以特有的人文之创造,于天地之间塑造着自身独特的形象,从而构成作家人格的外观,所谓“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诸子》)。在刘勰的人格理论体系中,“道”与“智”内外统一地共同铸成人文创造者——作家的人格形象。
人通过他特有的“智”来体悟“道”,从而使自己区别于天地万物;而人在“制作”体道之文,在驱遣其才力进行审美创造之时,则表现出不同的“性”,这种体现在具体制作过程与具体文本之中的个性,赋予作家人格以独特的艺术生命和审美特质,并最终使得作家从整体的人之中独立出来,从而形成艺术心理学意义上的作家人格。
在审美创造过程中,作家人格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先天的才、气,与后天的学、习,二者合称为“性”。不同的作家,其先天禀赋因人而异,后天努力亦不相同,因此形成“其异如面”的“性”之特征。这些不同的气质个性又形成不同的“体”(作品风格),《体性》篇一口气举出十二种类型,诸如“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用孔儒人格标准来衡量,司马相如之“傲诞”与阮籍之“倜傥”都是颇值得非议的。儒家伦理道德,对作家之“性”有严格的规范与要求。正是因为在文学批评中用孔儒人格的德性标准苛求作家,才会出现《程器》篇所列举的曹丕、韦诞“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的现象。一般认为,《程器》篇是指责作家“性”之瑕累而主张德才兼备。细绎全篇,似乎并非完全如此。《程器》一开篇,便对“历诋群才”感慨万千,叹一声“吁可悲矣!”刘勰的悲哀中饱含着同情(亦不排除“自怜”),甚至激愤。当然,以儒学为人格理想的刘勰,并不否认文人的德行之瑕累,故《程器》篇列举了十多位作家德性人品方面的毛病。但他紧接着说:“文既有之,武亦宜然”,而且后者的焕行劣质在数量与程度上都超过前者。刘勰进一步指出文士中亦不乏人品高洁者,在列举数例后,他反诘:“岂曰文士,必其玷欤?”
似可将《程器》篇视为对“历诋群才”的反驳,它表现出刘勰作家人格理论的宽容特征。刘勰还从更深的层次挖掘“历诋群才”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心理根源,其矛头直指“江河腾跃”“涓流寸折”的门阀制度。可见刘勰的人格理论与他自身的人格境界一样,都是建立在对生存状态之批判的心理基础上的。
《程器》篇为文人之“性”苦心开脱,《才略》篇则为文人之“才”大唱倾歌。若将这两篇对照起来读,便会发现:在《程器》篇中被罗列了“文士之瑕累”的人(如司马相如、马融、王粲、潘岳、扬雄等),在《才略》篇中却一一得到了桂冠或颂词(分别是“辞宗”、“鸿儒”、“溢才”、“敏给”、“诡丽”等)。而在作家的人格构成中,真正与“溢才”、“敏给”相统一的,是作家独特的气质个性,也就是“体性”之“性”。如果说,“才难然乎”是人整体区别于天地万物的标志;那么,“性各异禀”则是个体的人相互区别的标志。个体人格最可宝贵的价值是他的独特性、不可重复性与不可摹仿性。
刘勰论“性”,视“风清骨峻,篇体光华”为作家人格与之高标。这种以“风骨”为特征的人格,实则是“耿介”之峻骨、“傲岸”之清风与“若锦”之光华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显现。于此,我们看到刘勰人格境界与《文心雕龙》人格理论的完美而谐和的统一。
注释:
①a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页。
②a 《南史·刘穆之传》。
③a 张少康:《刘勰为什么要“依沙门僧佑”?》,载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④a⑤a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92、2页。
①b 《南史·齐宗室始安王遥光传》。
②b 《梁书·江淹任昉传论》。
③b 《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第393页。
④b 《高僧传·僧佑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