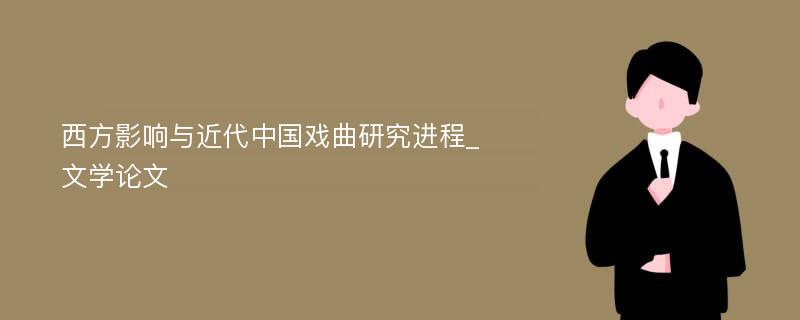
西方影响与现代中国戏曲研究之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中国戏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王国维发挥清人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点,在《宋元戏曲考》开篇写下一句名言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实,一代又何尝没有一代之学术?“西学”从近代开始“东 渐”,到了天地翻覆的20世纪,在中国逐步成为现代世界组成部分的历史过程之中,中国的 学术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冲击,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而现代中国的戏 曲研究之兴起和发展,就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展现了上述历史性的变化和转型。
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中,戏曲没有一席之地。经、史、子、 集的学术分类既反映了传统的价值观念,也长期主导了中国文人学者们的思维模式。尽管在 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戏曲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娱乐形式,深远地影响了各类中国人的审美,并 向占当时人口大多数的文盲和半文盲传播历史和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但是戏曲不但不为士林 所关注,反而被贬为小道末流,不见于官方的文献记载。例如,关汉卿、汤显祖是现代戏曲 研究中必提的巨擘,然而,关汉卿的生平于史无征,《明史》虽然为汤显祖列传,但是却只 字不提他的戏曲活动。
明清两朝,随着戏曲、小说的长足发展,确有一些文人士子开始关注戏曲、小说,但是戏 曲、小说在当时远没有获得和诗文平起平坐的地位。有人认为:“文学四位一体的观念在明 代隆庆、万历最后确立”,(注:饶龙隼:《中国文学四位一体的确立》,《中国诗学》第六辑(1999年12月)。)
然而,纂修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虽卷帙浩繁,却连 一部戏曲作品也不收录;《四库》的子部虽有“小说家类”,却既不录宋元话本,也不收明 清小说。显然,《四库全书》中的“小说”并不等同于现代文类意义上的“小说”。
与中国不同,戏剧(准确地说应该是悲剧)在西方一直占有极高的地位。在古希腊,演剧是 盛大的庆典活动。西方文艺理论的鼻祖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里着重讨论悲剧问题,给予 悲剧极高的评价。他的思想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的文艺理论。西方的叙事文学也有着久远的历 史传统,等到了近代,随着长篇小说这一文类在西欧崛起,小说在西方现代意义的“文学” 观念中也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所以,当欧洲人按照他们的文学观念来观察、阐释中国文学时,就必然会作出一些不同 于中国传统观念的价值判断。例如,一百年前,英国人翟理斯(Giles)的《中国文学史》设 专门章节讨论戏曲和小说。这部书的元明清部分把戏曲、小说放到了和诗歌同等的地位。(注:Giles,Herbert A.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1 .P.256-424.)
翟理斯自称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注:Giles,Herbert A.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1 .P.V。)
不过另有材料说明,19世纪80年代俄国汉学 家的《世界文学史》中已经包括了中国文学史,而该书关于中国文学史的部分1880年在圣彼 得堡 曾用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其中亦论及戏曲、小说。(注:前苏联李福清著,田大畏译:《中国古典文学在苏联(小说、戏曲)》(北京:书目文献出 版社,1987年,)第1—3页,第111页。)
此外,日本人笹川种郎1903年出版的 《支那文学史》也破除成见,研讨戏曲、小说。(注:戴燕:《怎样写中国文学史——本世纪初文学史学的一个回顾》,《文学遗产》1997年 第1期。)
不过,也有人说该书出版于1898年。(注:金启华:〈四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上,中华书局,1 995年版,第65—66页。)
应该说,戏曲、小说在中国真正受到人们的重视,是由于外来的冲击而引起的。鸦片战争 之后,原本封闭的中国被大炮轰开,西方的各种思想观念源源不断地输入;甲午战败之后, 中国人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威胁,积极努力地向西方学习,包括通过向已经 “维新”了的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一个颇有趣味的例子是,当初王国维是拜日本人为师 学习英文的。)(注:袁光英、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23页。)
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下,小说、戏曲开始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1902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颇能说明问题。这篇文章论述小说的社会功用 ,把小说看作改良政治和国民的最有力的工具。梁文中所说的“小说”实际上是“俗文学” 的代名词,包括戏曲在内。例如,为了论述“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除了《 水 浒传》和《红楼梦》之外,他还列举了《西厢记》和《桃花扇》加以佐证。(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近代文论选》,(台北)木铎出版社1988年版 ,第158—159页。)
梁启超这种把 戏曲和小说混在一起论述的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文类观念模糊;同时,梁启超关于西方小 说之社会功用的描述,在今天看来也并不准确。不过,梁文的本意并非是仅仅谈论文学,而 他把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曲强调到了可以重塑国民人格、振兴国家的重要地位,这 就无疑是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反动了。一叶知秋,由此也可以窥见当时中国社会思潮、价值判 断的变化了。
二
若要讨论现代中国关于戏曲的学术研究,自然不能不从王国维开始。虽然在王国维之前, 从元代的夏庭芝、钟嗣成,到清代的焦循、姚燮,也有一些文人曾经写过有关戏曲的论著, 但是他们的著述还属于旧的“曲学”范畴。旧曲学算不上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不仅是因为 在旧时代文人士大夫的心目中,曲只不过是诗词的附庸,所谓“词为诗余”、“曲为词余” ;更因为旧曲学或论述曲律、技巧,或记载本事、掌故,大都以杂记或实录的形式写成,如 果以现代的学术标准审视之,难免会感到它们偏于简单、零碎,甚至真伪错杂、互相矛盾, 更谈不上有什么历史的逻辑了。
王国维更新观念,把前人视为“小道末流”的戏曲,当作一门学问,花费气力来认认真真 地 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 尝为此学故也。”(注: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见于《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 3页。)
1908年,他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戏曲研究著作《曲录》,是年32岁。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又写成了一系列的戏曲研究著作,最后,于1912年末到1913年初在日 本期间,完成了《宋元戏曲考》。(注:袁光英、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87-
)王国维运用新的方法,为戏曲研究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 系。古人论曲多用“戏文”、“杂剧”、“南戏”、“传奇”等名词指称各个具体样式;而 当时“戏曲”一词,多指演唱的剧曲,不同于现代人所说的戏曲。(注:详见拙文〈关于南戏和传奇历史断限问题的再认识〉,华玮、王瑗玲主编《明清戏曲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版,第301—302页。)
王国维为“戏曲”一 词重新定义,“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注:王国维:《戏曲考原》,同⑨,第163页。)
从王国维的这一表述可以清楚地看出, 他已经是把戏曲当做歌舞剧,而不再仅仅是“曲”来看待,他的定义已经涉及了戏曲的综合 性和戏剧性等本质特征。在此基础之上,他把“戏曲”当做一个“类概念”(generic conce pt)来运用,在《宋元戏曲考》中以“戏曲”为全书命名,统领该书所论述的各个分类,如 金院本、元杂剧和南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方法已经不再是旧曲学中那种直觉、感性的方 式了。王国维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学者,现在“戏曲”一词已经成为概括中国古今所有土生 土长的戏剧样式的特定概念。
研究者的观念和方法决定了其学术研究的面貌。王国维以新的眼光审视原本混沌一片的历 史材料,从中探寻出戏曲起源、综合、形成、发展的历史线索,为如何阐释戏曲的历史发展 找到了一种历史的逻辑。虽然他只写到元代戏曲为止,但是他的戏曲历史发展的逻辑,已经 在学理上为戏曲通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的戏曲学说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当然,随着新 材料的发现,他的一些具体的结论也已被后人修正。例如,现在一般认为,最早真正的(即 成熟的)戏曲样式是宋南戏而不是元杂剧。(注:详见拙著《东西方戏剧纵横》,(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0页。)
但是,后人对王国维的这种修正,其本身也 还是依循王国维当初设定的标准来行事的,即,以有无剧本来衡量某一戏曲样式是否已经成 为“真正之戏剧”。即使是有少数学者(如,任半塘)不同意王国维的这一衡量标准,试图在 比宋元更早的历史时期找到成熟的戏曲样式,他们也还是依据王国维的“以歌舞演故事”定 义来讨论、判别,何种歌舞表演应为最早成熟的戏曲样式。换言之,他们并没有能够从根本 上摆脱王国维当初设定的历史逻辑。
王国维的戏曲论著材料翔实,考证精审,大不同于前人那种带有很大随意性的曲学论著。 于是,有些学者便认为王国维之所以能够在戏曲研究上取得不同于前人的突破性成果,主要 是 因为他得益于乾嘉朴学的学术传统。例如,钱南扬认为,王国维是“以乾嘉学者治经史之法 治曲”。(注:钱南扬:《前言》,《戏文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宁宗一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王国维继承了清代乾嘉以来‘朴学’大师的治学 方法,在戏曲史方面作了精深的研究,结束了我国戏曲自来无史的局面。”(注:宁宗一:《评〈中国戏曲通史〉》,《戏曲研究》第11辑,第142页。)
其实,这些 学者都只说对了一半,准确地说只说对了一小半。固然,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中不乏爬罗考据 ,有类似乾嘉朴学之处。但是,应该说,他在戏曲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首先是得益于观 念以及方法上的更新。王国维早年热衷于学习西方哲学(包括逻辑学)、文学,一个为人们所 熟知的事实是,他深受叔本华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的《红楼梦评论》和《宋元戏曲考》中 显而易见。而且,张舜徽认为,王国维在以甲骨、金文证古史之前,对于乾嘉朴学做学问的 途径与方法是“很存隔阂的”。(注:张舜徽:《王国维与罗振玉在学术研究上的关系》,《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一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1—412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35岁的王国维随罗振玉避居日本 ,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也开始转向,他立志从事古史的研究,受罗振玉启导开始钻 研乾嘉学者的著作。(注:袁光英、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5-76页。)
还是陈寅恪说得中肯。他曾经把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概括为三点,其第三点是:“……取外 来 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 元戏曲考》等是也。”(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6年版,第2页。)
除了本文前面所分析的部分之外,阅读《宋元戏曲考》,还可以 或明或暗地看到另一些“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互参证”的地方。例如:从“进化” 的观点来看待中国文学和中国戏曲的发展;从“巫”,即从原始宗教与原始歌舞的关系入手 探讨戏剧的起源;用悲剧、喜剧的概念来划分戏曲作品;按照叔本华的“意志说”来阐释悲 剧。此外,在《宋元戏曲考》的“余论”部分,王国维还专门论述了中国戏曲和外国艺术的 交流,例如,作为戏曲的重要成分的乐曲和古代西域音乐之关系,中国戏曲的西文译本。以 上这一切说明,处于中国历史大转变之中的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上,已经开始有了一种他的 前辈所无法具备的世界性的眼光。王国维早年有一段话说得非常之好:“异日发明光大我国 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注: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科大学章程书后》,同上,四,第1823页。)
而王国维本人正是这样一位 学术上的“通人”。
如果把王国维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研究戏曲的代表性人物吴梅进行对照,就可以更为明显 地看出王国维是一位深受“外来之观念”影响的学者了。和王国维一样,吴梅非常重视戏曲 研究,而且比王国维更加酷爱戏曲艺术。他系统深入地钻研艰深的曲律,使得这门学问得以 流传至今。然而,阅读吴梅的戏曲论著,不难发现,他的研究基本上遵循了传统曲学的路数 。较之前人的曲学研究,他虽有系统、深化之处,但缺乏带根本性的更新。这里,笔者将王 、吴进行对照,只是试图更加清晰地凸显本文的论题,绝无褒王贬吴之意。吴梅是中国将戏 曲搬进大学讲堂的第一人,他曾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讲授戏曲 ,培养出了任半塘(二北)、钱南扬、卢冀野、王季思等一批戏曲研究的大家,对于推动现代 中国的戏曲研究发展而言,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三
自王国维为现代的戏曲研究奠基,几代学者孜孜不息地努力,终于建立起中国戏曲历史和 理论研究的体系。几十年来,戏曲研究者的阵容大致可以划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学( 主要是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也包括戏剧学院的戏文系)教师,其中成果卓著者除了上述的 任半塘、钱南扬、王季思外,还有赵景深、徐朔方等人,以及他们的一些弟子;第二部分则 是自50年代以来先后建立的中央和各省市戏曲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而其中又以张庚为首的 “前海学派”影响最大。(注: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建院,梅兰芳任院长。1953年,张庚由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调 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为该院的实际领导人。“文革”之中,中国戏曲研究院不复 存在。“文革”之后,张庚任新成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而原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大部 分成员则组成了该研究院下属的戏曲研究所。由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坐落在北京前海西街的原 恭王府内,戏曲理论界便戏称以张庚为首的研究群体为“前海学派”。)
本文无法逐一评说每一位重要的戏曲研究者,却不能不讨论“前海学派”。张庚原本从事 话剧工作,是当时戏剧界一位学者气质颇重的领导人。他本人喜爱做学问,曾着力研究话剧 艺术的理论和历史;50年代奉命带领一批新文艺工作者参加戏曲改革运动,由此和戏曲结下 了不解之缘。张庚等人,以及他们的一些学生,在改造戏曲的过程中,也逐渐地被戏曲所 改造:从一开始并不怎么喜欢(有些人甚至是反感)戏曲,到渐渐地被戏曲的魅力所吸引,最 后变得热爱戏曲,并且为研究戏曲付出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前海学派”的治学方法和学 术贡献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戏曲通史》(注:该书编写于60年代初,并于1963年付排,但是因为政治原因,一直未能问世;“文革 ”以后,经过修订,该书上、中、下三册于1980年至1981年先后正式出版。详见张庚、郭汉 城主编:《编写说明》,《中国戏曲通史》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版,第1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1983年)、 《中国戏曲通论》(1989年)等著作之中。
张庚等人以前曾经从事过话剧或新歌剧的艺术实践活动,曾经直接学习过西方的戏剧、音 乐理论。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审美意识不同于王国维、吴梅等老一辈戏曲研究者,也不同 于大学文科里那些研究戏曲的同龄人。因此,他们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独特的面貌。
首先,“前海学派”非常关注戏曲艺术的本体,他们把戏曲看作是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 ,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样式。王国维虽然比他的前人看重戏曲,但是他重视戏曲文学,轻视 舞台演出。王国维“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注:青木正儿:《原序》,《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吉庐(古鲁)译,上,台湾商务印 书馆1936年版,第1页。)
他治戏曲,止于元代。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向他表示,打算把戏曲研究推进到明清两代,王国维“冷然曰,‘明以后 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注:青木正儿:《原序》,《中国近世戏曲史》,王吉庐(古鲁)译,上,台湾商务印 书馆1936年版,第1页。)王国维所说的“死”和“活”,可 能 是指元杂剧语言自然,是适合演出的“场上之曲”,而明清传奇文辞典雅,是不利于搬演的 “案头之曲”。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他所说的活文学并未能存活下来,元杂剧早已消 亡,是一种已经死去了的戏剧;而他所说的死文学也并未死去,明清传奇中的一些折子戏在 昆曲舞台上一直流传至今,是戏曲研究者不可忽视的宝贵的活戏剧。其中奥妙在于:昆曲是 一种既和传奇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又不等同于传奇的演剧艺术,历代的艺人是这一艺术最主 要的载体,是他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逐渐地改造了许多原本属于“场上之曲”的 本子,使之传唱不歇。(注:参见拙文“The Closet Drama and Performers’Revisions in Traditional China.”C hinese Culture,Taipei,33.2(1992).P.84-86.)
由此也可以看出,研究戏曲,如果不考虑演出和演员的因素,仅 就剧本来发议论,那就难免不得出片面的结论。
当然,把戏曲看作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重视研究它的演剧艺术,这并不是从张庚等人 才开始的。1936年,周贻白出版《中国戏剧史略》、《中国剧场史》,已经开始探讨戏曲的 舞台演出;然而,“前海学派”则是以前人所未有的规模和力量,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戏曲的 演剧艺术。在《中国戏曲通史》之前,戏曲史著作往往侧重于探讨戏曲作家和作品。《中国 戏曲通史》明确指出:“一部戏曲史,既是戏曲文学的发展史,也是戏曲舞台艺术的发展史 。”(注:张庚、郭汉城主编:《编写说明》,《中国戏曲通史》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第303页。)
为此,该书设独立的章节讨论戏曲的音乐、表演和舞台美术。《中国大百科全书戏 曲曲艺》中的“戏曲”部分,除了“中国戏曲史”、“戏曲文学”分支外,还有“戏曲声腔 剧种”、“戏曲音乐”、“戏曲表导演”、“戏曲舞台美术”和“戏曲剧场”等分支,其篇 幅大大超过了戏曲史和戏曲文学的部分。《中国戏曲通论》全书十一章,仅一章讨论戏曲文 学,其它大部分则分门别类地讨论戏曲的音乐、表演、舞美、导演、观众等各个方面。
这种研究方式,依照文学、音乐、表演、导演、舞美等各个门类,来解析戏曲,实际上是 西方的艺术分类理论在戏曲研究中的一种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有助于人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 ,细致地、深入地理解戏曲,但它也多少存在着与研究对象不尽吻合、不尽贴切的问题。因 为,在传统戏曲(其主体是以京剧为代表的一批产生于清代的地方戏)里,最有光彩的是演员 的表演,相对于表演这一主导性的、支配性的因素,其它的(如,文学、舞美)只是一些辅助 性的、被支配性的因素。而师徒之间“口传心授”传统剧目的方式,则更是极大地抑制了导 演 艺术的发展。所以,如果要想在中国古代的戏曲里探索“导演的历史传统”,实在是有点勉 为其难。实际上,即使是在西方戏剧的研究中,关于导演和导演艺术的探讨也是较晚的事情 。至于有人(当然,并非“前海学派”)从过去文人的诗文、批注中找材料,再对其进行现代 阐释,把汤显祖称为中国“导演学的拓荒人”,探讨冯梦龙等人的“导演艺术”,总是显得 缺乏说服力。(注:详见高宇:《我国导演学的拓荒人汤显祖》,《戏剧艺术》1979年第1期,《古典戏曲 的导演脚本》,《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第3期。)
当然,自20世纪50年代起,文学、音乐、导演、舞美等各方面的人才被调 入戏曲界,戏曲逐渐形成了专业化分工的艺术生产方式。在由这种新的艺术生产方式创作出 来的戏曲中,编剧、导演、音乐和舞美的功能大大加强。此时,再讨论戏曲的导演艺术则 是完全说得通的了。然而,必须看到,这种新的艺术生产方式本身就是西方戏剧文化影响下 的产物。(注:详见拙文《二十世纪世界戏剧中的中国戏曲》,《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 年2月号。
“前海学派”高度重视戏曲的演剧艺术,所以他们自然也就重视研究地方戏。王国维看不 起元代以后的戏曲,吴梅把戏曲研究扩展到了清代,但是他也只研究传奇和杂剧,并不染指 地方戏。而中国戏曲演剧艺术的精髓极大地体现在中国清代以来兴起的各种地方戏,包括从 皮簧戏里脱颖而出、后来成为国剧的京剧里;可以这么说,中国戏曲对世界戏剧的贡献,主 要不在于它的戏剧文学,而在于它的演剧艺术。(注:详见拙文《二十世纪世界戏剧中的中国戏曲》,《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 年2月号。
)就戏曲研究的一些个体而言,他们完全 有理由因自己知识结构和研究兴趣而忽视地方戏,但是,作为戏曲研究的群体,“前海学派 ”则必须重视地方戏。加上,如前所述,“前海学派”因戏曲改革和戏曲结缘,他们一开始 接触和了解的就是活的戏曲,是存活在舞台上的以京剧为代表的一批产生于清代的地方戏。 是他们组织人力进行采风、调查(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田野调查”),系统地了解分析昆山、 弋阳、梆子、皮簧等各大声腔以及与其相关的众多剧种的来龙去脉,第一次清晰地勾勒 出众多地方戏剧种的历史发展轨迹。
“前海学派”受到西方的影响,这还表现在他们在研究中时常有意或无意地以话剧作为戏 曲的参照物。中国话剧是在西方戏剧文化影响下产生的艺术形式,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几乎是写实戏剧的代名词。和这种写实戏剧进行对照,戏曲艺术的一系列特征便显得格外 地鲜明突出。由于这种对照,戏曲理论研究中曾经出现过一些很热门、也很有趣的论题。例 如;因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而引起了关于戏曲表演中“体验”与“表现”的 讨论。又如,本不应该成为戏曲研究重要课题的自由的(或超脱的)舞台时间和空间问题,一 度成了一些戏曲理论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其实,古往今来,世界戏剧在大多数情况之 下并没有像写实戏剧那样,采用一种固定的舞台时空,东方戏剧则更是如此。只有在和写实 戏 剧固定的舞台时空进行对照时,戏曲自由的舞台时空才成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也只有在 反对戏曲盲目摹仿写实戏剧时,关于戏曲舞台自由时空的讨论才会有意义,并且显得格外地 重要。(注:详见拙文《二十世纪世界戏剧中的中国戏曲》,《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 年2月号。
四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的学术里,戏曲毫无地位可言;到了王国维的时代,戏曲研究成为 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到了“前海学派”的时代,戏曲研究已经成了 一门独立于文学研究之外的艺术学科,当然它和文学研究仍然有着交叉重叠的部分。
在上述历史进程之中,戏曲研究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 只是其中的一些影响在今天看来其“西方”的特色已经不再那么明显。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已 经全方位地渗透进了中国现代学术之中,从名词术语的译用,到理论体系的移用,这一切互 相作用、互为表里,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中有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君不见“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之类,已经是非常“中国化”、非常普遍的表述方式?因而,身处于这种 新的学术传统之中的人们,往往难以自觉该传统在其生成过程之中所受到的西方的影响。如 今,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学者是按照经、史、子、集的学术传统训练出来的了。尽管一些学 者并不一定公开标明自己在研究中运用了西方的理论,但是其研究成果却往往明确地向人们 昭示,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西方观念和方法的影响。
本文试图通过剖析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和“前海学派”,来观照西方影响在戏曲研究中的一 些具体表现,而不是要对这一历史现象作出什么价值判断,更不是说现代中国的戏曲研究就 是西方学术的照搬和移植。自然,戏曲研究中西方的影响,远不止以上所论及的,还可以举 出一些更为显性的例子,比如,悲剧和喜剧理论移用的历史,80年代以来注重宗教戏剧的倾 向,目前出现的引用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理论的苗头,等等。因为这些研究中的西方影响显 而易见、几乎不证自明,也因为它们在现代中国戏曲研究的历程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这里 就不再作详细论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