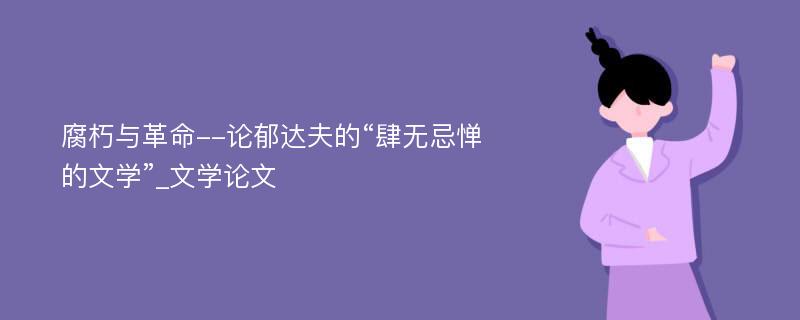
颓废与革命——试论郁达夫“不端方的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端方论文,试论论文,颓废论文,达夫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0)09-0118-04
颓废,是郁达夫的主要精神特征,毋庸多言。至于造成颓废的原因,也已有多篇论文探讨。目前需要深究的是:为什么郁达夫一以贯之地坚持表现“颓废”?而“颓废”作为一种美学因素,在中国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一、“这一个不革命的”郁达夫
20世纪30年代,苏雪林为郁达夫勾勒了这样一副画像:“郁氏自宣告写作态度转变后,每以革命的文学家自居。然而他的革命情绪也令人莫名其妙。尽管向读者介绍自己荒淫颓废的生活,却常鼓励读者去提刀杀贼鼓励读者去赴汤蹈火为人类争光明。这好像一个脸青似鬼,骨瘦如柴的烟客,一面懒洋洋躺在铺上抽鸦片,一面却眯着眼哑着声喊道:‘革命!革命!你们大家努力呀!都上前呀!’”。[1](p390)
郁达夫果真如苏雪林形容的这般不堪吗?的确,郁达夫偏爱描摹以“色欲”为主题的颓废生活:除了性苦闷外,还好写鸦片、酒精、麻雀牌、燕子窠、偷窃、诈骗以及其他堕落行径;还好表现病态心理,孤独、零余、敏感、愤世嫉俗等;还钟情于描写疾病和死亡……因为他的大部分小说都以“自叙传”的方式写出,让人以为都是他本人生活的写照——从精神到肉体的彻底“颓废”;他的小说也基本上笼罩在这种通过大量爱欲、疾病、死亡以及堕落行为的描写所营造出的那一种感伤颓废的氛围当中。诚然,郁达夫有颓废的成分(一种情绪性的精神形态),但同时另一面,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无比真诚的郁达夫,对劳苦大众充满怜悯、对人类充满热爱的郁达夫。早于1923年,他就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中指出“我们正和革命前的俄国青年一样,是刚在受难的时候。但这时候我们非要一直的走往前去不可”,还大声疾呼“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团结起来实现理想。[2](p240)《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则召唤青年对一切恶势力进行叛逆和反抗,持久地争取自由。1927年,他发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艺》论述“革命的最终理想,在使全人类得享到幸福”,而“真正彻底的革命,若不由无产阶级者——就是劳动者和农民——来作中心人物,是不会成功的。”[3](p251)他在《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中说明对于劳动文艺的主张。在《诉诸日本劳动阶级文艺界》中则说:“中国的国民革命若不成功,世界革命是不会成功的。革命文艺的战士,不应该有国境的观念。目下日本的革命文艺家,应该唤醒日本的军人和资本家的迷梦……”[4]1937年全面抗战后他在新马更是写下大量政论,《敌我之间》等文章体现出强烈的爱国心……这些都展现了另一个郁达夫,一个正直的、具有极强烈道德责任感的郁达夫——“革命”的郁达夫,与那个“颓废”的郁达夫正是同一人。抛开这些政论性文章,即使是他的描写“颓废”的小说,也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小说里面对现实的反抗,对社会的批判,态度都很明确。郁达夫对革命的看法也别具一格,他不盲从于任何党派,只相信正义和真理,希望有权有产阶级绝迹,多数者(the mass)摆脱被奴役状态获得解放,成为自我的主人。“革命的最终理想,在使全人类得享到幸福,在使无论那一个人,能享受他或她的本来的生存权,在打破一切私人的压迫和解放全民众的束缚。”[3](p253)在这一“革命”的最高原则下,他同情左翼,反对国民党政府,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革命在他是一种反抗,反抗专制、反抗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这种革命观也渗透进他的“革命文学”观念中:“所以当古典文学发达到极点,弄到了处处械梏,常常碰壁的时候,突然起来的浪漫文学,在当时就是革命文学。其后又因浪漫文学的放肆太过,弄成千篇一律。内容空虚的时候,起来补她的缺的写实文学,又可称之为十九世纪的革命文学。”[5](p269)他也是这样看待西方世纪末颓废文学的,“其他各国的颓废派的作家,差不多可以说都是虚无主义者。……无聊的政治社会,钳制个性发展的目下的政府法律和道德,为他们攻击最烈的目标,……梅特林的戏剧和洛罢哈(Rodenbach)的小说及诗,表面上虽则没有攻击社会制度的调子,然而仔细研究起来,那一篇不是对现实表示不满的?那一句不是对已成社会表示反抗的!”[2](p240)他认为颓废文学也是有着革命性的。这样看郁达夫的颓废,则是表达他的革命情绪的一种形式。他选择这样一种非常态的存在方式,来表现某种个人性。所以,在他身上,颓废与革命是一体的。正如锦明于1927年指出的:“今日公开的性的讨论,那神圣的光,是《沉沦》启导的;今日青年在革命上所发生的巨大的反抗性,可以说是从《沉沦》中那苦闷到了极端的反应所生成的。”[6](p334)可惜那年代很少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
苏雪林的说法,虽有绝对的女性主义立场,但自有其观念:颓废决计与革命挂不上钩。另一个激进派华汉,断言“达夫的全部作品,可以说赤裸的反映了这一没落的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达夫是这一没落的士绅阶级底最彻底最大胆的代言人。”[7](p362)因了郁达夫写了颓废堕落,就成了没落阶级的代言人。无论是右翼倾向的苏雪林,还是很左翼的华汉,不约而同地都标明颓废与革命无干。后者如华汉,更认为革命应该是一股前进的动力,革命者大义凛然,主张正义,有一种道德优势。以此道德标准来要求文学,革命文学应该要么反映底层人们的悲惨生活,以达到控诉的目的,要么描写英勇的群众、人民,以颂扬革命的主力。郁达夫的颓废,又怎么与革命沾得上边?这类看法又很具有代表性。对此,郁达夫自嘲道:“我——这一个不革命的——郁达夫,……我只认识一位不革命的老人鲁迅。”[8](p422)而实际上无论鲁迅还是郁达夫,都是中国革命的前锋。只不过,鲁迅选择了启蒙主义,郁达夫选择了颓废美学,来表达他们的革命。
二、“不端方的文学”
“文学革命”以来,胡适主张开拓平民题材,周作人提出“平民文学”、“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血与泪的文学……这些主张都要求表现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命运,带着一种历史的正义、人道主义的精神。就是说,新文学初期,因为预设的社会改造目标,所以强调文学表现社会底层平民的题材。这样,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是限制性的,由于中国式现代性的需要而产生道德限制,“现在的创作家,人生观在水平线以上的,撰著的作品可以说有一个一致的普遍的倾向,就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反抗,最多见的是写出家庭的惨状,社会的悲剧和兵乱的灾难,而表示反抗的意思。这确是现时非常急需和重要的。”[9]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直有一种冲动、破坏力,一种反现代性的蛮力,郁达夫的颓废则代表了这股破坏力。他对颓废文学某些方面的兴趣,与“五四”时期的主调如此的不一致。郁达夫自己作了辩白:“游荡文学,在中国旧日的小说界里,很占势力。不过新小说里,描写这一种烟花世界的生活的,却是很少。劳动者可以被我们描写,家庭间的关系可以被我们描写,那么为什么独有这一个烟花世界,我们不应当描写呢?”[10](p111)不无道理。从内容上看,郁达夫的表现个人颓废,对新文学初期的题材褊狭是一种补充。更重要的是,郁达夫描写了人的生存层面的某种真实,他的真切表现人性心理,则提供了一种自我观照的方式,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空间,使之有了向纵深处发展的可能。从美学上看,他的“颓废”,在更深层次上,意味着一种新的审美道德对压抑性理性律令的反抗。
无论他的真切还是他的反抗,都引起青年人的共鸣。当时《沉沦》销行二万余册,并且很快有“后起之秀”如倪贻德、王以仁、叶鼎洛等模仿他的路数。对于这一无法否认的现象,文坛必然需要有所解释。《沉沦》诸作发表后,毁誉参半。周作人最先出来以“《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它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至于所谓猥亵部分,未必损伤文学的价值”的解释平息了一些争议,奠定了郁达夫在文坛上的地位。[11](p304)但是大量维持风化的批评家,并非都来自封建伪士阵营,除了华汉、苏雪林外,茅盾、徐志摩、梁实秋、王独清等也都非议过郁达夫。茅盾就在答复读者信中表明,他厌恶作者所作的自己个性的“自画像”,也不欣赏他“心灵与肉体矛盾”的描写。[12](p304)梁实秋则点名道姓:“譬如郁达夫先生一类的文人,报酬并不太薄,终日花天酒地,过的是中级的颓废生活,而提起笔来,辄拈酸叫苦,一似遭了社会最不公的待遇,不得已才沦落似的。”[13](p11)王独清痛骂:“郁达夫底自甘堕落,谁也不能替他辩护”,“我们决不像鲁迅,在所谓左翼作家底会议上说他底颓废是可以原谅的”。[14]他们最不见容的是郁达夫的颓废及所谓的“灵与肉矛盾”的描写。相较起来,创造社太阳社同人似乎更能接受郁达夫。除了郭沫若、成仿吾撰文为郁达夫小说进行辩护外,钱杏邨还以“时代病:性的苦闷——社会苦闷——经济苦闷”论来阐释郁的小说。他们试图把郁的小说纳入正途,纳入“革命文学”的正统,确立它们存在的合法性。不得不这么做的原因,在于郁达夫原属于他们的阵营,且郁达夫在任何公开状里都表明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尽管本质上可能是无政府主义),他又是极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人如果不解释清楚,很容易被右翼攻击,污蔑革命同志都是郁达夫这样的堕落分子,沉湎于色情文学。国民党就主要以“普罗文学”、“色情文学”的名目查禁郁的作品。即使对于郁达夫,前后期创造社成员态度也还不一,尤其在郁宣称与创造社脱离关系以后。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1928年写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在贬斥了叶圣陶、鲁迅后提到:“郁达夫的悲哀,令一般青年切实地同感的原因,因为他所表现的愁苦与贫穷是他的所要申诉的,——他们都是《沉沦》中的主人公。但是,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15]冯乃超评价前辈郁达夫时含含糊糊,连郁本人都察觉出他“褒有所不甘,贬有所顾忌”,“而最后是很巧妙地说出来的这一个似褒却贬的评断”。[16](p416)这种暧昧的态度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郁达夫遇害。郭沫若在1946年的悼念文中评价道:“(《沉沦》)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17](p88)总算是为郁达夫的小说定了性,定下了“反封建”的调子。但是这种解释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充分、不完全的。
这些阐释都不足以表现出郁达夫的意义和路向,相反,把他狭隘化了。郁达夫也算是革命派,但与创造社的朋友们步调并不一致。他一直以来都是在叛逆的轨道上滑落,因为“天才的作品,都是离经叛道的,甚至有非理性的地方,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究是不能理解的。”[18](p21)周作人说他是“不端方的文学”。“不端方”,就不是正轨,而有叛逆之意,可以说是颇正确地理解了他。
颓废是一个美学范畴,革命是改变世界的手段,郁达夫以颓废表现他的“革命”,使得本不相容的颓废美学与革命意识内在地纠缠在一起。事实上,二者都是深刻的现代性体验,与民族国家有关。
三、情爱描写与国家寓言
民族国家在中国现代成为压倒一切的最高价值。在这一历史语境下,《沉沦》里的一声“祖国啊!如今你就是我的情人。”就不是肉麻之笔了,而是发自内心的呼喊。这个“祖国”,不是传统的家族之国、封建诸侯之国、一王专制之国,而是受日本、欧美富强国家刺激下产生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这种国家观念,恰恰是现代性的产物。当时的留日学生们大都有这种明确的国家意识。郁达夫最奇特之处,在于把“祖国”这一称谓与颓废的意象联系在一起。《沉沦》描写一个留学生性的压抑,他因为几名日本客人“抢去”了他所意属的妓女,于是怨怒:“罢了罢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再也不爱女人了。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
一般祖国都和母亲、女神等伟大形象联系在一起,郁达夫却偏作“侍女(妓女)——情人——祖国”这样的意象关联。这表明郁达夫看重的是这一意象所代表的身体的实在性一面。成仿吾指出:《沉沦》于描写肉的要求之外,丝毫没有提及灵的要求,主人公是以全部的热诚肯定他的肉的要求的,引起他的恐怖与后悔的,只是因为不自然的满足与变态的欢娱,而不是肉的要求本身。[19](p310)确实,郁达夫是肯定爱欲之情和性的本能的,“种种的情欲中间,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是爱欲之情。诸本能之中,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是性的本能。”[20](p202)在郁达夫看来,性爱有它自在的目的,同时就是生命本身的目的——快乐。他实际上肯定的是爱欲,而不是性,类似于希腊“Eros”的原义“爱欲是创生的原动力,是最根本的生命原则,是本体性的东西”,[21](p16)也似弗洛伊德的“爱欲作为人的生命本能,是人的本质”,[22](p16-19)或者马尔库塞的“爱欲作为生命本能,则蕴含更多的内容,既包括性欲,也包括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生物欲望”。[23](p4)小说中屡屡写到性的沉迷,并不是展示性活动的充沛和满足,而只是说明爱欲本能被压抑后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郁达夫显然是肯定人的爱欲、人的肉身性的存在的,他常在作品中直接吁求和表现个人的自然需求。诸如“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之类赤裸裸的道白,毫不顾忌地表达出个人的情爱本能、物质生活改善等的追求,与“五四”以来个人解放的精神取向很不一致。
现代民族国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空壳,而是由其主体支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是“国民”、“个人”。“五四”以来的个人解放主要在精神重塑的一面,陈独秀的“启民智”,鲁迅的“立人”,郭沫若宇宙精神的“巨人主义”……都重在涵养人之神思、拯救国民灵魂、铸造人的主体精神。他们迫切想要确立的现代性主体是一个理性的主体、知性的国民、伦理的超人。然而,郁达夫反其道,他看重肉身性的存在,肯定感性和欲望,人的非理知的一面。他的身体关注,对肉体欲望的高度体察,是对“五四”以来重精神的个人主体的一个重要补充。精神和肉身,实在是现代性主体不可分的二面。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也正取决于它能否为身体这一最根本的价值空间提供其“自我实现”的“场所”。中国现代历史的最大问题,恰在于不能为身体这一最根本的实体提供栖居之所。所以,郁达夫说:“国际地位不平等的反应,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在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24](p93)在他这里,身体之爱等于民族之爱,男女之爱等于国家之爱。他总是把二者联系起来,将爱欲本能化为民族意识,将情爱描写作为国家寓言。所以《沉沦》里设计这样的情节:主人公留连日本酒馆,因妓女问他一句“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他就感到羞愤难当,呼唤着“中国啊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并且,他的国家之爱,绝不是什么正义凛然、神圣崇高类的爱国情思,而是伤感、哀怨、愤懑甚至是绝望的情绪,就像是恋爱中的男女彼此常有的感觉,一种对可望而不可即的情爱对象的感觉。郁达夫把自己的现代国家的观念的确立,通过个人的情爱体验非常细腻地表达出来。在他的现代性体验里,国家话语失去了它的超越性价值,个人与国家处在同一层面之上。他不认为国家有绝对的优先权,也恐惧国家把个体吞没,不满于“国家因为要达到这兵富民强的目的,就不惜牺牲个人,或牺牲一群人,来做它的手段,所以在国家之前,个人就不能主张他的权利。”[25](p57)他甚至强调个人的至高无上,“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有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家族等哪里会有”。[26](p194)但郁达夫也不是全然以个人为本位,中国的现实,特别是留日时期“支那人”身份的屈辱,使他深刻认识到:没有国家依托,个人的肉体将无栖身之所,灵魂也将无所皈依。因此他描写的个人在绝望中仍然呼喊祖国的强大。《沉沦》的主人公性心理受挫,可他自杀前仍在呼喊“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郁达夫看到:性压抑是强势文化对民族生命力压抑、阉割的表征,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民族生命的压抑。在这超压抑性的社会,人的爱欲本能处于被压抑状态,人的本性遭受严重摧残,急需摧枯拉朽的革命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保障自由的爱欲;同时,革命解放的人的生命本能,也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内驱力。在这一点上,郁达夫所见的中国社会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命题所形容的资本主义社会,状况是略微不同的。马尔库塞认为,在社会经济状况不好的情况下,为了造就文明,一定限度地压抑爱欲是必要的,以便本能转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但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劳动的异化成为爱欲被压抑的主要表现,单调乏味的异化劳动对人的本性的压抑和摧残变本加厉。那么,这种额外压抑就是不必要的,多余的了。这时候,压抑性文明的成就已经创造了废除压抑的物质前提,人类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没有任何压抑的自由社会。[24](p2-25-158)郁达夫所讲的恰恰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贫困和弱小,使它缺乏保障爱欲本能的物质基础,革命就是要建构这个基础,革命是要解放爱欲本能。并且,对于不断高涨革命中的一种倾向——力图使一切爱欲化的生命本能投入到非爱欲的、有利于革命的工作中——这样一种新的压抑机制,郁达夫显然也是不赞同的。因此,他看到沿着“五四”以来对理性主体的强调走下去可能会产生的压抑,提出“爱欲之情”和“性的本能”以补充。他的表现方式,类于马尔库塞的“非压抑性升华”,“是解放和扩展性本能的结果”,“鼓动生命本能充溢完满的自由实现”;而不同于弗洛伊德,其“压抑性升华”“强迫生命本能萎顿、缩小,以适应社会需要”。[21](p18)
郁达夫开掘了个人主体性的感性肉身的一面,使“五四”个性解放得到了另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表达。他的感性生命,使“五四”以来的理性主体血肉丰盈,鲜活起来。“五四”以后的无数青年被这样一个活生生的清瘦、忧郁的青年形象所打动,尽管这一形象并不纯净、高大而完美。“在作品上那种神经质的人格混合美恶,糅杂爱憎,不完全处,缺憾处,乃反面正是给人十分尊敬处”,[29](p363)“他的小说里的主人翁可以说是现代的青年的一个代表,同时又是一个自有他生命的个性极强的青年,我们谁都认识他。”[30](p318)郁达夫向现代文学历史贡献的这个感性个体,不能说不是对现代性主体的一个健全构成的补充。而这正是郁达夫之选择“颓废”所表达出的现代性体验。他开启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关涉了生命的个体体验、身体性、爱欲、压抑与升华以及颓废美学的问题,最终则指涉了主体性建构以及民族国家主题。”[31](p6)
郁达夫小说中存在着的这种“颓废”,与“革命”相关联的颓废,是他在个人的生命体验中得到的,可堪称“现代性”的另一面。在他的颓废与革命中,反抗和进步是其旨归,反抗对肉身的压制,主张身体的栖居之地,彰显生命与人性的尊严。这使得他的作品无论在他的时代还是今天,都自有其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