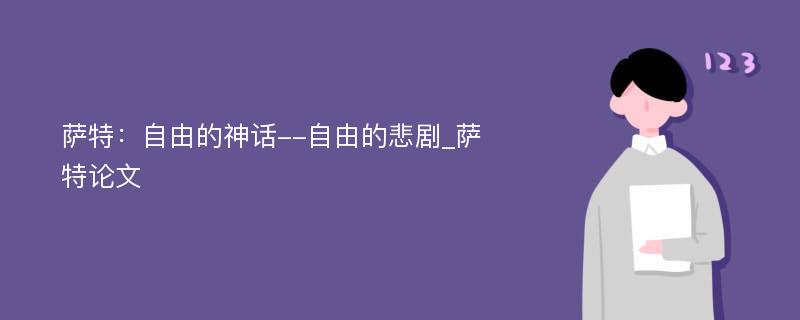
萨特:自由的神话到自由的悲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自由论文,悲剧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对萨特的自由观一直存在着两种误解:一种来自正统的理论家们,他们认定萨特鼓吹不负责任的绝对自由,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另一种来自激进的青年们,他们视萨特为精神导师,奉其自由观为人生指南。其实,萨特的“自由”既不象后者所想象的那般宽广和美妙,又不象前者所臆断的那般放任和恶劣。它并不意味着行动上的任性随欲、无法无天,而是意味着意志上的无条件自主选择。它要受到处境的各种限制。它总是与责任形影相随,而责任常常重大得使人陷入焦虑中。萨特自由观的要旨是鼓励人们尽职尽责地充分发挥实践主体性。
关键词 萨特 自由 选择 处境 责任 焦虑
萨特的自由观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对西方青年的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青年的人生观发生了广泛作用,而自本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它问世以来,一直是理论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数十年来,对它一直存在着两种误解。一种误解来自某些正统的理论家,他们认为萨特宣扬绝对自由意在怂恿人们随心所欲、无法无天,从而断定他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另一种误解来自许多激进的青年人,他们认为萨特的自由观是他们反传统,反政府、反社会的有力的理论武器,是消除社会疾病、造就理想人生的灵丹妙药,从而把他视为精神导师。其实,萨特的“自由”既不象前者所臆断的那般放任和恶劣,也不象后者所想象的那般宽广和美妙。它经历了一个由宽广到逼仄、由美妙到严峻的渐次收缩过程。
一、自由的前提:不容有决定论
人性论上有各种各样的决定论,如神定论、命定论、道德决定论、普遍人性决定论等。但因承海德格尔“生存先于本质”之说的萨特认为,既然人是首先生存然后其本质才生成的,那么一切决定论都是虚妄的。
首先,神定论和命定论是虚妄的,因为上帝是没有的。文艺复兴以来先进思想家们为之明争暗取,直至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才得以确立的无神论在生长于信教家庭的萨特那里得到了坚持,甚至如他自己所说得到了彻底的贯彻(见《词语》)。在他大量的理论著作和文学作品中都包含着无神论思想,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自称是无神论存在主义者(见《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在这一著名的学术演讲中,他多次提到上帝是不存在的,因而先定的人性是没有的。没有先天的人性,因为没有上帝来设定它。①否定上帝的存在是萨特给人的自由的第一张通行证。
其次,道德决定论和普遍人性决定论也是虚妄的,因为并没有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和人性模式。萨特认为,人是自己造就自己的,他成为怎样的人,取决于他做什么和如何做,这是存在主义的基本原理。②他强调,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生存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他是投身于未来的有意识的自我筹划,他在不断地造就自己。③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行动、由自己的行动造就自身的,因此,将任何先验的强制的道德规范套到人的行为上都是不合适的,将任何先定的抽象的人性模式套到人的心灵上都是行不通的。人不是某个普遍概念的实例,无法用一个现成的人性模式去说明其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抽象的形式化的道德规范不能约束或指导人的具体的情境化的行为。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家们深信不疑并精心论证的道德律令的普适性或普效性被萨特决然击碎了。否定普遍的道德规范的存在是萨特给人的自由的第二张通行证。
康德坚信不要把他人当作手段或不要损人利己是一条普遍有效的道德律令,而萨特则认为它并非普遍有效,人们可以遵循它,也可以不,二者可能都是正当的,因为都出于自由。他举例说,在英国作家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塔丽芙为了不破坏另一女子的幸福放弃了她的爱情;而在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小说《帕尔姆修道院》中,撒塞维瑞娜则因认定情感创造人生价值,而选择牺牲别人以实现她自己的幸福;这是两种严重对立的道德,但在萨特看来,它们是同等的,因为它们设置的目的是一样的,这就是自由。黑格尔认定国家利益高于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后二者当然应服从前者。萨特则不承认这种脱离情境的当然性,因此不愿意断定当国家利益与团体利益或个人利益冲突时应选择什么和放弃什么。他自例云,二战时期,一位法国青年前来请教他:他(指青年)是留守家中尽孝侍母还是应征入伍精忠报国呢?他(指萨特)拒绝提出选择性建议,只是说:你是自由的,你去选择吧!去发明吧!任何普遍道德都不能指点你必得做什么,世上没有指示。⑤萨特的道德相对主义通过上述二例得到了充分的表露,他的这种倾向在现代伦理思潮中是有代表性的。
如果说否定神定论或命定论扫除了妨碍自由的先天的或天国的障碍,那么否定道德决定论和普遍人性决定论则扫除了妨碍自由的后天的或人世的障碍。在取得了两张通行证之后,萨特的“自由”阔步走进了理论殿堂,似乎对周围的世界不屑一顾。人是自由的!人注定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人不是自在存在,而是自为存在,自为总是在对自在进行否定,进行超越,用萨特的术语说,进行“虚无化”。自为对其存在进行虚无化的永恒可能性就是自由。人的生存先于其本质,并且是其本质的条件,这就意味着:人是自由的,人注定是自由的,他没有停止其自由的自由。⑥
为了替自由开辟道路,萨特清除了一切决定论。在他的人生哲学里,决定论是没有的,更确切地说,是不容有的。如果确实是生存先于本质,那么人就永远不可能参照一种给定的或凝固的人性加以解释;换言之,没有什么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⑦
在为自由除障辟路时,萨特以无神论否定了人性观上的神定论或命定论,这还只是在重复前人的做法,以道德相对主义否定人性观上的道德决定论或普遍人性决定论,这才表现出萨特的理论个性。不过,这种过激做法招来了一些不无道理的非议。
尼采以空前的理论勇气摧毁了传统的基督教道德体系,世界战争和社会变异又给传统价值观念以重创,这些给萨特的道德怀疑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和事实的依据。但是,他借助于这支撑和这依据跳得太远了。要否定神,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神的名义下的一切。神律(基督教道德律令)大多是假托神的名义的人律。上帝死了,但是以上帝的名义制定的许多道德律令依然可以活着。认为上帝死了人就可以不受约束了,如同一个孩子认为严厉的父亲不在家了他自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一样,是天真可哂的。任何名义下的道德规范都是一定范围内民众意志的约定,个体意志不能把它当皮球踢来踢去。
不要损人利己,个体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这些是公认的道德律令,认为克己利人和损人利己半斤八两彼此彼此,因为两者所悬的目标都是自由,这未免太唯我主义了。认为尽孝侍母和尽忠卫国孰轻孰重难以定夺,因为任取其一都违背不要把他人作为手段之道德律令,这未免太无政府主义了。高场人的自由,高场人的主体性,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自由总是基于必然和应然的自由,主体性总是面对客体性和规定性的主体性。如果让自由泛滥到汨没道德,让主体性膨胀到排斥世界,自由就会溃散,主体性就会崩裂。
二、自由的含义:自主选择
萨特如此慷慨地赠与人的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人是一种其生存先于其本质的存在者,没有什么东西先天地规定他的本质,他是自我造就的。他将如何,取决于他如何自我筹划或设计;他实际上如何,取决于他如何行动或作为。行动或作为,自我筹划或设计,这一切都基于自为的自主选择,而它们正是自由的表现。因此,自由就是选择,就是自我选择,就是选择的自主性,或选择的内在独立性。自由、选择、虚无化、时间化只不过是同一种东西;对于人的实在来说,存在就是自我选择,而自由是人的存在,即他的存在之虚无,因此自由就是人的自我选择;自由只可能存在于自我选择活动中;不论我们的存在是什么样的,它都是选择,我们选择为“伟大的”和“高贵的”或“低下的”和“受辱的”,都取决于我们,即都是自主的或内在独立的。⑧可见,萨特的自由还是一种心理自由,主要表现为意向自由。
由于人注定是自由的,而自由意味着选择,因此人不能不选择,即便决定不选择,这还是一种选择。人有选择的自由,没有不选择的自由,他必须进行选择,因此萨特认为选择是无条件的。⑨
萨特试图将他对自由的理解跟一些古典哲学家(如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的理解区别开来,尤其是跟常识的理解区别开来。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与常识理解的自由是不同的。后者意指获得满足、达到目的的能力,而前者意指选择目的的自主,至于目的达到与否对它来说是无关紧要的。⑩萨特以狱中俘虏为例说明他的自由概念与常识的自由概念的区别。说俘虏是自由的,并非意指他有随时越狱的自由,而是意指他有随时企图越狱的自由,前者是常识的自由观念,后者是萨特的自由观念;前者注重的是能力和获得,后者注重的是愿望和选择。萨特提醒人们注意获得的自由与选择的自由之间的本质区别,不要以能力的不自由否定愿望的自由。(11)这进一步表明萨特理解的自由是心理自由,而主要是意向自由。
自由作为自主选择,既不意味着任性随意、无法无天,也不意味着尽心遂意、自得其乐。自由的选择不一定是愉快的选择,在许多情况下选择是在屈从或不安中进行的。自由选择,这丝毫不意味着我在站起来或坐下去、进来或离去、逃避或面对危险上是自由的,如果人们把自由理解成一种任性随意的、无法无天的,无根无据的和不可理解的纯粹偶然性,这就大错特错了;诚然,我的每一个行动,即便是最微细的行动,是完全自由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能是任意的。(12)对全部目的的选择,尽管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并不必然甚至并不经常在快乐中进行,不应把我们在其中自我选择的必然性跟权力意志混淆起来,选择可能在屈从或不安中被执行,它可能是一种逃避,它可能在自欺中实现自己。(13)这里的“屈从”、“不安”,并非意味着选择的自由或自主受到了严重限制,而是意味着选择并不总是趋向肯定和积极。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积极选择,更不意味着最佳选择。有些人选择做伟人、英雄、好人,也有些人选择做凡人、懦夫、歹徒。每一价值系列的各个档次都有人选择,并且所有选择都是自主的。
把自由理解成自主选择,等于将它局限在心理世界,这种退让为萨特免去了许多诘难。人是完全自主地为自己进行选择的,因此人是自身造就自己的。这是萨特的一个重要观念,他正是根据它来断定人是自由的,但这个观念应予分析。人自身造就自己,就整个人类而言,这是完全事实;但就个人而言,这就是不完全事实了。实事求是地说,没有一个人完全是由自身造就的,有极少数人主要是由自身造就的,大多数人部分是由自身造就的,有一部分人完全不是由自身造就的。
人生之初,或用存在主义者的行话说,人被抛入世界之初,他确实是白布一块。生活使这块白布变成了图画。作画者中有本人,也有相关的他人,甚至全人类都参与了创作。在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中,底色不是本人涂上的,底稿也不是本人勾勒的,因为人在生命之初是没有决断意识和选择能力的。当人发展到能独立地进行选择即能行使自己的自由时,他也不可能完全自主地描画自己,因为虽然画笔握在他手中,但是并非每一笔都出自他的意愿和构思,可能有许多笔是在外力的强制下不由自主地和未假思索地涂抹上去的。
自为的每一行动都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但并非每一选择都是自主的,因而并非每一行动都是自由的。萨特不可以认识不到这一点,但是他依然宣称人的选择是完全自主的,人的行动都出自其绝对自由。这种无视现实的论断只有在想象中才找得到依据。俘虏不能选择不受监禁,但他可能想象不受监禁,他的行动是不自由的,但他的意愿是自由的:萨特最终只能用俘虏的这种想象的自由来论证其绝对自由说。确实,人的想象的自由是不受限制的和无法剥夺的(除非使他丧失想象力成为植物人),但是这种自由只对精神创造活动有意义,而对实际行动是毫无助益的。
三、自由的界限:处境
作为行动哲学家,萨特不会让其自由停留在空想中享受它的绝对性和无限性,他把它拽出了想象的殿堂,推进了现实的天地。在这里,自由遇到了它的界限:处境。
人总是在一定处境中存在的,自由总是一定处境中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只有理论意义,处境中的自由才有实际意义。在萨特看来,自由与处境的关系是相反相成的。一方面,处境只有通过自由才显现,才具有意义;另一方面,自由只有在处境中才闪光,才展开活动。这种关系被称作“悖论”。关于自由的悖论:只有在处境中[活动]的自由,也只有通过自由[显现]的处境。(14)
萨特所说的处境比日常语言中的处境要宽泛一些。后者指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他在其中的遭遇。前者包括五个方面:一个人的场所,他的身体,他的过去,他的立场(已由他人的指示决定),他对他人的基本关系。(15)萨特分论了其中三个方面(场所、过去、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论分为“我的周围”和“我的邻居”二部分。分论中还论及死亡,它不是一开始就被萨特包容在处境中。
无疑,在处境中,人的自由将遭遇到许多障碍,有来自自身的,有来自他人的,还有来自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的。但是,在萨特看来,这种种障碍不是对自由的否证和取消,而是对自由的确证和显明。因为任何障碍只有在与自由照面之后才成为障碍。自由总是在每种冲着它的障碍之先存在;因为障碍是自由自身为自己设置的,其敌对系数取决于自由提出的目标的价值。(16)在自由选择某一目的作为追求对象之前,针对这一目的的障碍就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是无意义的。萨特以岩石为例来说明他的这一观念。横在山路上的岩石,只对以登山为其目的的人来说才成为障碍;而对于城里的律师来说,它是不成其为障碍的,它是根本未显现的;而对于山下的漫步者来说,它也不成为障碍,它的意义不是有利于攀登与否,而是美或丑。
由于障碍是自由自身为自己设置的,因此自由在处境中所受限制可以说是自找。这样,萨特就可以宣称他把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自由是自己限制自己的。(17)萨特的这个观念有二层含义:一是我自己的自由限制我的自由;二是他人的自由限制我的自由。这里只取其前一层含义。
人的自由只能是一定处境中的自由,这是萨特从观念世界进入现实世界时的一个切实想法。不过,萨特并不因此而放弃其绝对自由说。他认为,即便自由在处境中遭遇到障碍,它也不会丧失其完全自主性,因为障碍是自由自设的。这种说法即使不是违背事实的,也是片面偏颇的。全面的事实是:一方面,障碍是自由自设的,自由设定了多高的目标,就对自己设置了多大的障碍;另一方面,自由又是受障碍规定的,自由根据障碍的大小来调整目标的高低。后一方面是第一位的,因为人在世以来是先遇障碍后有自由。一般的障碍给自由以自知之明,自由再凭自知之明去设置具体的障碍:自由与障碍的事实关系就是这样。
一般的障碍虽然不是针对某一个体的自由的,但是它对每一个体的选择 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不能说它对于那一个体来说是未曾显现的和没有意义的。乞丐不会真正选择做亿万富豪,奴隶不会真正选择做总统(幻想不是真正的选择),因为一般的障碍使他们知趣地收敛了他们的自由。萨特的障碍只有在自由的光照下才显现共意义之论断当分解为:个别的障碍只有在与之相对的个体的自由的光照下才显现其意义;一般的障碍既可以在个体的自由的光照下也可以在一般的自由的光照下显现其意义。在一般的自由的光照下显现其意义的一般障碍对于个体的自由同样是有意义的,这一点被萨特忽略了。
自由与处境的关系类似鸟与笼的关系。在萨特把自由置入处境中后,自由便不能再自由地飞翔了。萨特不想让他的“自由”难过,他拍拍笼中的鸟,安慰道:别伤心,宝贝,你要换个角度想一想:不要老想着笼子囚禁了你,而要想到,正是笼子使你有了一个自我实现的场所。萨特当然知道:笼子只是玩鸟的而不是飞鸟的“自我实现”场所。但出于某种理论上或信念上的需要,他不愿捅破这层遮陋的墙纸。
四、自由的要求:责任
即便是处境中的有限的自由,自为也不能随心所欲、不负责任地享受。权利与义务是孪生兄弟,自由与责任之间也有着类似的关系。萨特鼓励人们抛开一切既定规范,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但他并不主张滥用自由。尽管人们在进行自主选择时,不必依赖任何外在的既定规范,萨特甚至认为没有任何道德命令值得依赖,但是意志却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听从内在呼声,它向自由宣谕的是自为本身对人类价值的处境性的理解。当一个人进行选择时,他不仅是在为自己选择,萨特认为,他也是在为他人选择,为其处境中的所有人选择,甚至为全人类选择;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他总是要选择自己感到满意而他人也能接受的东西,在造就自己时,他既要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又要考虑怎样适应处境乃至整个时代和全部人类。(18)
萨特的逻辑似乎如此:人之所以要对其选择负全部责任,是因为它不仅是为他自己做出的,而且是为所有人做出的。萨特所要求的道德选择的普适性与康德所要求的道德律令的普适性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后者是前者的依据和前提),尽管这位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明确否定过那位理性主义哲学大师的道德先验主义和形式主义。
由于人注定是自由的,因此他肩负着整个世界的重量,即他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且要对整个世界负责。这种责任之重大,重大得难以承受,然而人又必须承受它,因为它是人固有的自由的逻辑要求。抱怨是荒唐的,因为一切都经由你自己选择,生活中并没有偶然事故,最恼人的麻烦、最严重的威胁都是在你自己的筹划中显现的。不论处于怎样的境地,人都应当满怀豪情地担当起处境对自由的敌对系数。(19)一些看似外在地强加给自为的事情,其实还是自为自己选择的。萨特以被迫参战为例详析了这一点。一个被迫参战的人深究起来还是自愿地选择了参战,或是为了家庭的荣耀,或是因对舆论的畏忌,否则他完全可以拒绝参战,或自杀,或脱逃。正因为人自己选择了战争,所以他应对战争负责,在此意义上,萨特转述并认可了一位法国作家的话:“战争中没有无辜的牺牲者”,他还加上一句:“人们有人们应得的战争”。总之,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自由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美妙,萨特的“自由”更是如此。享有一份自由就应负有一份责任。自由是责任的必要前提,责任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在道德和法律领域,丧失或没有意志自由的人(如精神病人、婴幼儿)对其行为不必负责。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出自自由意志,他就必须对其行为负起道德的或法律的责任。萨特强调人应对其出自自主选择的行为负责,这表明他的伦理学说与传统的伦理学说立于一共同的基石——责任上,尽管这基石上面的外在建构是迥异的。
当萨特说人是自由的时,青年人欢呼雀跃,老年人不以为然;当他说自由意味着责任时,青年人神情沮丧,老年人颔首称是;当他说人的责任重大时,青年人咂嘴吐舌,老年人亦惶恐不安了。强调责任是必要的,但夸大责任则大可不必。并非每一个人要因其每一个自由行动而对整个时代和全部人类负责。其实,每个人只要负起他应负的那一部分责任,就算对世界尽了责任。萨特似乎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了叱咤风云的伟人,把每一个行动都视为了惊天动地的壮举。凡人小事,虽有责任,但并不重大得关涉整个世界,并不沉重得难以承受。夸大责任只会导致不负责任。
五、自由的后果:焦虑
人被抛入世界之后,孤立无助,没有什么神谕圣旨指导他应当如何作为,没有什么金科玉律规定他应当怎样做人,一切都靠他自身决定,一切都由他自己选择;这样,他就必须对他的决定、他的选择、他的行为、他的为人负全部的责任,而且不仅仅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他人负责,甚至对全世界负责;因此,责任是重大的,重大得难以承受,人因之陷入一种焦虑之中,一种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中,一种冥思苦想不得其法的焦虑之中。一种不敢轻举妄动而又不得不动的焦虑之中,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天地悠悠而斯人伶仃的焦虑之中,存在主义者爽快地宣称人就是焦虑,那句话意思是这样的:人,自我行动并领会到他不仅是他选择做的人而且是一个同时为全人类选择自己的主法者的人,不可能摆脱其整个深沉的责任感。(20)
萨特通过责任在“人就是自由”和“人就是焦虑”之间划上了符号。自由意味着责任,而责任意味着焦虑,人不能摆脱自由,因此也不能摆脱焦虑。逃避焦虑恰恰是意识到焦虑的一种方式,因为要逃避某种东西,就必须先知道它是什么。这样,萨特就可以宣布,焦虑不仅不可摆脱,甚至不可逃避。(21)不过,焦虑虽不可避开,但还是可以掩盖的。萨特自己也承认,许多人和人在大多数时间里之所以不显得焦虑,是因为他们在自欺中掩饰和逃避焦虑(22),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自欺中逃避焦虑(23)。
为了不陷入悲观主义,萨特强调,焦虑不会导致无为主义,不会导致无所作为。那与导致无为主义,导致无所作为的焦虑无关,它关涉的是一种平平常常的、所有曾拥有过责任的心灵都了解的焦虑。(24)他以军官下达作战命令为例。将十个、十四个还是二十个人投入战斗,这完全取决于一个军官的选择,而此事又关系到若干人的生命,因此他在做决定时免不了某种焦虑,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他下达作战命令。萨特相信,所有首领都体味过这种焦虑。
萨特沿用海德格尔的“生存先于本质”之论断开始其自由论,又化用海德格尔的“人就是烦恼”之论断结束其自由论。“人就是烦恼”与“人就是焦虑”意指无异。
由于责任被夸大,因此焦虑也被滥施。许多人不显得焦虑,并非因为他们掩饰它,而是因为他们所负的责任不足以产生它。人在大多数时候不感到焦虑,并非因为他总是在逃避它,而是因为他只在极少数时候担负重大的责任。无关紧要的日常选择是不会导致焦虑的。不关涉到自己或他人的重要利益(如生命、健康、前途、幸福等)的普通选择是不会导致焦虑的。谁会为了早餐喝咖啡还是喝茶而忧心忡忡呢?谁会为了坐火车不是坐汽车去旅游而顾虑重重呢?
即便事关许多人的生命或前途,有些人在做决定时也丝毫不感到焦虑。为了个人的野心或阴谋,为了某种狂热的信念或偏执的妄想,有些政治首领或军事首领毫不犹豫地大笔一挥,把成千上万年轻的生命(其中甚至可能有他们的子女亲友)送往生死场、送上不归路。我们倒也希望每一位领导人常怀必要的焦虑,如萨特信以为真的那样,这样,许多无谓的牺牲将可以避免,世界将会在清亮的鸽哨中而不是在轰鸣的炮声中迎来每一个黎明。但是,严酷的政治现实彻底粉碎了这种希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幻想。
由上可见,萨特的“自由”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般宽广和美妙。他在一步一步地收缩自由,大体可分为四步:第一步,自由不是指行动自由,而是指心理自由,表现为自由选择;第二步,即便是自主选择之心理自由,也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处境限制的;第三步,这种受处境限制的选择自由不是可以随便享受了,而是必须承担相应责任;第四步,与自由选择相应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以致承责人深陷焦虑中。这种四步收缩法将自由的神话变成了自由的悲剧。
自由观是萨特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之可以见出后者的若干主要特点。例如:第一,相对的主体主义。萨特充分肯定人的实践主体性,即选择自主或意向自由,但又承认这种主体性、这种自主或自由受客体世界、受处境的限制。第二,温和的相对主义。萨特不承认有什么普适的道德律令能够指导人的具体的选择活动,但又坚持每一选择应对相关的他人甚至全人类负责,而这意味着选择必须基于被普遍认可的标准。第三,清醒的乐观主义。萨特相信人总会选择那些对大家都有益的善的东西,但又并不排除有些人可能迫于处境的压力而选择于人甚至于己都无益的恶的东西。在机械决定论和主观唯心论之间、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之间、盲目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寻求一种适中的立场,是萨特自由观的从而是其人生哲学的总特点。
萨特的自由观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表述上和观念上的误失,但是这无损于它的良好意图。他实在并不鼓励唯我主义和无法无天,而是真诚地希望每个人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实践主体性、完全地行使自己的自主选择权,同时又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成为一个有益于世界和人类的人。他把只应寄托于少数人的希望推及所有人,这是一种失误。不过,这是一个大哲学家的失误。
收稿日期:1995-02-20
注释:
①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P.22.Les Editions Natel,Panis,1970.
②-⑤Voir,Idem,P22;P.23;P.87-88.P.39-47.
⑥Voir,L,etre Et Le Neant,P.515,Librairie Gallimard,Paris,1955.
⑦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P36-37.
⑧-(12)Voir,Leetre Et Le Neant,P,543,516,558,552;P,561,558;P,563;P,564;P,530.
(13)-(14)Idem,P550;P569.
(15)-(17)Voir,Idem,P570;P,569;P.608.
(18)Voir,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P.24-26.
(19)(21)(23)Voir,Letre Et Le Neant,P.639;P.81-82;P.642.
(20)(22)(24)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P.27-28;P.28;P.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