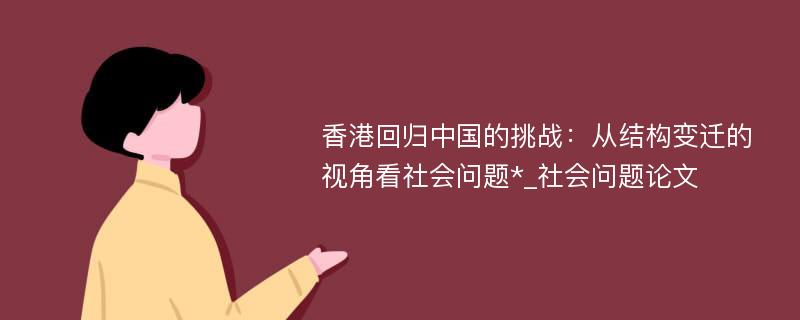
香港回归的挑战:从结构转变看社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问题论文,香港回归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社会问题的角度,研究以往香港人口、阶级和文化结构,提出几个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人口结构方面,有人口老化及新移民剧增可能引致的文化、制度滞差和个人适应问题;而于阶级结构,则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富裕中的贫穷并未消除;在文化结构中,保守内向的功利家庭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亦开始转变,而市民参与公众事务的意念及信心有退却趋势。
前言
1997年,香港面对一连串体制改革,加上香港经济正值转型当中,社会不免受到冲击。如何维持未来香港的自由法治和安定繁荣,是各阶层人士关心的课题。过去几年,由于政制改革的迫切性及争议性,已引起公众相当关注。相反,许多随着社会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却由于在政治议程以外而被忽略。本文尝试探讨香港三种社会“结构”的发展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它们包括:人口结构、阶级结构及文化结构,〔1〕以期未雨绸缪,建设一个更好的香港。
一、人口结构的发展
港府于1996年7月发表的《全港发展策略检讨报告》中, 估计2006年人口将由1995年的610多万人增至730万人,到2011年将增至750 万至810万之间,比1991年所作的估计多出百多万。香港出生率持续下降, 每年移民外地数以万计;而造成人口剧增的原因主要是死亡率下降,平均寿命延长,以及每日百计的新移民和回流人士。人口增长除对一般居住、医疗、交通服务构成负担外,人口老化及新移民带来的问题亦必须正视。
1.人口老化
香港65岁或以上的人士在过去十多年内所占的比例一直递增,现时估计占人口10.4%,到2001年占11.6%,而到2006年则占12.1%。换句话说,到2001年,65岁及以上的老人估计达70.5万,若以60岁以上计算则达100万,即每六七个人中便有一位老人。到2001年, 老人增长速度达15.6%,比起全港人口增长快了近五倍。事实上,香港早于1981年已达到联合国人口老化标准。但估计人口老化率将逐步放缓,其中一个原因受到新移民影响。由于移民中儿童及年轻妇女占相当大比例,抗衡了人口老化的趋势。据政府聘请的惠悦顾问公司就老年金研究报告显示,在2036年香港人口老化高峰时期,如没有外来移民因素,65岁及以上的老人数目与15至64岁的人口数目比例(抚养比率)将是470对1000之比。加入移民因素后,下降至310对1000之比(刘进图,1994)。在此情况下,未来的老人问题主要集中在土生土长的香港家庭当中。
由于医疗服务的改善,老人的寿命持续增长。据1987年统计处人口推算,香港男性的寿命由1971年的67.8岁,增至1991年的74.9岁。估计到2011年,可达77.7岁。而女性寿命则由1971年的75.3岁,增至1991年的80.5岁,到2011年则达83岁。随着寿命的延长及退休年龄的限制,老年人口“抚养比率”持续上升,1984 年为105,1994年已至131(HongKong Social and Economic Trends,1995:2)。1990年统计显示,老人中领取公援的人口比例为全港领取公援人口比例的五倍。特别是70岁及以上的老人,其贫困程度较全港情况更达11倍。换言之,老人成为各类人士中最贫苦的一群(莫泰基,1993)。
此外,户口统计亦发现1986年有76845位单身老人,占21 万单身住户中的35.8%。预计到2001年,39.5万单身住户中将有14万以上为单身老人。即从1986到2001年这十五年间,单身老人增长达83.9%,而全港老人人口则从1986年的64.03万增至2001年的98.64万,增长只有54.1%年,故单身老人的增长比整体老人人口增长更快。最保守估计,到2001年,单身老人将占全体老人人口的15.6%。但由于离婚和分居率不断上升,估计到时会有更多独居老人。如何照顾与日俱增的独居老人渐渐成为社会问题。
特别是年轻夫妇及其子女相继迁入新市镇,基于交通原因,难以照顾留在旧市镇中的老人,问题相继而至。据中文大学香港社会指标研究报告(1987:57)显示:年老被访者的生活圈子狭小而孤立、缺乏分担困难的知己朋友、少与亲戚交往、绝少参加社团组织和活动,遇到生活困难,大多只能依亲属援助。
从社会学角度看,老人问题的出现是基于医疗科技的急速发展使人类寿命延长,但社会上的文化、制度未能及时与之配合而造成“文化滞差”(Cultural lag)。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以前一个人退休后十年八年,很快便要面对死亡。今天拜医疗发展所赐,一个人如果55岁退休,还可享受25到30年余生,但亦可能意味要面对一连串经济、社交和情感问题。
香港大部分雇员均无退休收入保障,以往是依赖“家庭照顾”来解决问题。当老人寿命不长而子女众多时,孝道不难彰显。但未来老人长寿而只得子女一二,养老便成为问题。有关设立全面退休保障已经谈得不少,这方面的“滞差”实在严重,必须尽早补救。现时政府决定强制私人机构设立公积金制度,但对于将近退休的人士却是无能为力的。
不过既然市民健康得以改善,以往对“老人”的界定及退休年龄的规定,是否亦应因时而变?用社会学的“标签理论”来说,一个“老人”的称号会令一些本来活力充沛的长者的“自我观念”转变,为符合社会的期望而表现退缩、依赖。年长的人体力可能不及年轻人,但适量的工作对心身亦有益处,社会应提供更多机会给有能力的年长人士工作。事实上今天有许多人在退休年龄之后仍继续工作,对此,与其心感歉意不如更新观念,在每个机构中设计一些合乎他们的工作。对于不宜工作的长者,则需助其安享晚年。
谈到更新观念,往日对老人的感情、社交及性需要的理解可能亦已不合时宜。由于寿命的延长,老人如离婚或丧偶,将要面对漫长的孤清岁月。有寻觅“第二春”者,时遭讥为“临老入花丛”或“为老不尊”。正如中大社会指标调查显示,老人大都孤立及缺乏朋友关怀,如何重建老人的社交生活,包括与异性的交往,应该受到关注。
当然,最重要莫过于家人对老人的照顾和关怀。可惜在香港,许多人根本不懂照顾老人。我们的传统累积了许多照顾婴孩的智慧,坊间亦有各式各样育婴书籍或婴儿用品出售,但对于今天老人的心理、疾病,人们所知甚少,在处理老人临终期间,甚至手足无措。照顾老人在许多家庭来说是一个头痛问题,社康服务以至普及护老知识,对一个老龄化社会非常重要。
2.新移民
人口结构发展的另一课题是新移民的涌入。香港是一个主要由中国内地移民聚居而成的城市。战后,移民涌入香港历久不衰。由于中国在1949年政权转移,移民开始在港落地生根,融入社会,而他们的子女亦成为土生土长的新一代,推动了香港的经济起飞。但在七八十年代后来自内地的移民,由于在经济及文化上与香港人差距甚大,被视之为“新移民”。他们在融入香港社会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亦为香港带来不少问题。
据香港政府的统计数字,香港在过去十多年约吸纳了百多万新移民。由1995年7月1日起,单程来港定居的中国新移民配额,每日增至150名,每年由内地来港定居的新移民将达55000人。这个数字超过香港每年的自然人口增长近一万。〔2〕根据1992至1994年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来港定居的新移民中,内地妻室占41%、与内地配偶的婚生子女占44%。
此外,即将在港实施的《基本法》二十四条规定,香港永久居民在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在1997年后将可成为香港居民。香港政府透露,这些中国籍子女约有八至十万人。但如包括港人与“二奶”(指在合法妻室以外之配偶——作者注)所生的子女,数目可能更多,他们对香港的教育、住房、社会服务以至康乐设施将形成重大压力。
其实新移民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如何适应新生活,融入新社会。所谓社会适应,除受本身的年龄、教育水平、性别等基本个人特征所影响外,亦深受当地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所影响。社会学的“社会解体理论”(Social Disorganization Perspective),特别关注移民在新社会里所经历的文化冲击及引起的社会问题。学者发觉移民在面对许多新事物时,会感到毫无指引,茫然无措。有时却发现对同一问题,社会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令他们无所适从。这种情况令移民感到精神困扰,难于适应新社会的生活。有学者相信部分移民中的酗酒、吸毒、精神病,以至犯罪亦可能与此有关。
对来自中国内地农村的新移民(特别是港人在广东的配偶及所生子女)来说,他们更要经历双重的“解体”:从中国内地到香港和从农村到城市的冲击。他们以往生活的环境非常简单,社区的价值比较一致,邻居是相熟社群,生活的安排受到国家政策和所属社区相当的约束,当要和政府打交道时往往透过所属单位或委托熟人办理。他们移民后才真正体验香港是如何多元复杂,是非标准不一。他们可能举目无亲,更不习惯邻居关门闭户,互不往来;发觉生活上许多问题自己安排,譬如说孩子的上学、经济援助、住房的申请等,再没有单位的安排,亦难以找到政府内的亲友来解决。如果没有亲友提点或者社团的协助,自然惶恐焦虑。
在经济方面,许多新移民均要经历社会阶层“向下流动”所带来的生活问题和心理创伤。据林洁珍、廖柏伟的研究(1993)显示,自1981年取消“抵垒”政策以后,男性新移民之素质无论在教育水平及工作经验等均有所上升。但移民与土生港人之教育及经验回报差距却逐渐扩大,以致从1986至1991年,新移民相对土生港人收入下跌。男性移民之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土生香港市民下跌,是由于80年代经济转型,扩张中的服务业提供了大部分的就业机会,移民加入服务业导致他们在国内积累之人力资本大部份报废。
新移民子女教育亦是一个问题。据教育署资料指出,港府于1993年批准增加中国合法移民配额,由每日75人增至105人时,在每日额外增加30个配额中,有15名留给21岁以下的子女,故每年将有额外的五千多名儿童获准在港居留,其中有60%至70%为适龄入学儿童。当中约2/3为6至11岁,须接受小学教育,余下1/3为12至18岁的儿童,须接受中学教育。当时教育署估计需兴建多所中、小学以应付需要。去年移民名额再度增加,教育需求将进一步提高。
其实不少学校对收录新移民学生态度消极,一方面是学校怕影响教学,另外本地家长对他们的歧视亦令学校感到压力。新移民儿童在语言、学习以致生活习惯上均需时间和毅力去克服困难,才能适应香港竞争剧烈的教育制度。
新移民家庭面对的问题实在太多,非这篇概论社会发展的文章所能处理。可惜政府一直忽视,直到近两年才投入资源筹办儿童适应课程和印制一些供移民用的社会概览手册。既然香港每年人口增长中,新移民比本地自然增长人口更多,他们对未来香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协助他们面对社会解体的挑战,不单只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更加深新移民和土生港人的相互误解与冲突。
二、阶级结构
香港常被视为梦想者的天堂,就像电视广告说:“在香港总会挨出头来。”根据吕大乐和黄伟邦的研究(1993),这种有关社会流动的乐观论述是在70年代中、80年代初才逐渐形成。主要原因是这段期间社会经历重大的阶级结构的转变,其中由“结构性流动”(structuralmobility)造成的“代间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不可忽视。所谓结构性流动是指在两代之间出现了职业结构的变化,造成流动的机会,下一代从事其他行业而脱离父辈原来阶级。
据香港中文大学1988年香港社会指标研究显示,有51.7%被访者估量自己仍停留在原出身阶层,但有37.1%的人自觉本身较父母阶层为高,只有11.2%的人认为自己较父母阶层为低。吕大乐和黄伟邦在1989年进行较详细的社会流动研究发现,有55.2%被访者经历了代间流动,当中12.6%是属于结构性流动。譬如被访者的父亲只有11.2%是属于管理阶层的“服务阶级”,但被访者中却有22.6%置身这个阶级,反映经济发展造成职业结构的转变,令更多人流入这些新增空位。
不过,深入的分析发现,不同阶层出身的人士,其向上流动的机会并不相同。出身“服务阶级”的人士,不少是可抗拒下向流动,继续留在原来的位置。同样,一般体力劳动工人阶级的流出率偏低,亦显示阶级背景对参与社会流动的竞争影响,令他们较难向上流动。如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分析(loglinear analysis),可发现香港阶级结构存在着一条介乎体力与非体力劳动阶级位置的界线,限制了工人阶级上向流动至服务阶级的机会,而一些白领阶级、小雇主和低层主管的中间阶级流出率反而较高(Thomas W.P.Wong & T.L.Lui,1992:63-79)。可见,香港其实并非真如广告所宣传的那般流动开放、人人有平等机会往上爬升。
以往二十多年来阶级结构发展显示,当中、上阶级生活得到大幅改善的时候,社会最低层市民不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5》数据显示,24个最高水平地区中,香港所得分配最不平均。香港收入分配出现长期恶化趋势,香港历年的十等家庭收入比例显示,最低收入的10 %(一等)的家庭所占全港收入的比例, 由1971年的2.3%下降至1981年的1.4%,1986年稍微反弹,1991年却又滑落至1.3%;而同期最高收入的10%家庭占全港总收入比率由1971 年的34.6%升至1991年的37.3%。在1991年,最高收入的20%家庭的收入已超过全港收入的一半,是24个地区中分配最不平均的(曾澍基, 1992;1996)。此外,据统计处资料显示, 1981年基尼系数〔3 〕为0.451,1991年增至0.476,显示收入差距趋向恶化。可以肯定的说, 低层市民在以往二十年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比例”,一直在减少。〔4〕
分配不平均并不代表下层市民生活一定“贫穷”,这完全是定义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从“公共援助金”个案数字了解香港贫穷的情况。由1981年至1990年,当香港经济正在急速发展的同时, 公援个案由45752激增至66675宗,增幅达45.7%,相对同期人口增幅的11 %多出了四倍多。接受公援人士多数是老弱孤残,单是老年人士、一般病患者和单亲人士已占八成以上,反而因低收入及失业而领公援的只占极少数(1991年只占4%。参见莫泰基,1992:9)。 但近年随着工业进一步转型及经济不景气,更多低收入市民无法维持生计。据乐施会“劳工与贫穷”行动纲领所载,1990/91年度低收入及失业的公援个案共2672个,但1995 年首季这类个案已增加至6520个,五年间增长224%, 可见问题的严重性。
即使在公援线以上,仍有不少家庭生活还相当困难。1991年最低收入的20%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每月港币$3460,可知日子并不好过。乐施会1995年发表有关低收入住户的研究,以每户收入在$3999或以下作标准,估计低收入住户的数目达23万户,占全港住户之14.9%,跟周永新在十多年前发表的贫穷研究估计相近(1981年占全港住户之13.9%)。这些低收入家庭来自渔农业工作者、经济转型而遣散的雇员、单亲家庭、新移民、单身老人和长期病患者。
香港阶级结构从来不是完全流动开放,但过去二十年的确有很多人随着经济起飞而经历了结构性向上流动。大家虽知道不同“家底”上升机会不一,但低层人士一直希望以勤力补救,而不渴求绝对的公平。问题是这种结构性向上流动的趋势未必可以持续,当爬升机会减少,对更公平分配(以达至公平竞争环境)的诉求,便会提上日程。透过改善低下层市民生活处境,增加社会流动,对整体社会的发展都有好处。相反,现时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不单有碍社会流动,甚至会导致社会冲突。
三、文化结构
香港多年来如何保持政治稳定?这问题一直吸引着许多社会科学家。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系刘兆佳教授在1982 年发表的SocietyandPolitics in Hong Kong一书中对此提出一个系统分析。 首先在社会结构方面,刘兆佳认为香港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群组成,而彼此间却缺乏(中间社团) 有力联系,
形成一个“低度组合的社会政治系统”(Minimally-Integrated Social Political System)。 这种接近“一盘散沙”的状态令政治动员困难重重。与这种社会结构相配合,是家庭内成员的文化及行为模式, 他称之为 “功利式的家庭主义”(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在这种文化结构下, 香港人以家为重,对公共事务审时度势,敬而远之。
这种文化心态形成的背景,可追溯至60年代的早期工业化社会。那时家庭资本的形成,主要在汇集家庭各成员的资源,可以说是中国家庭形态在对香港都市工业环境的一种适应。首先是所谓“难民心态”。在1945至1950年间大量的内地移民涌入香港,他们当中许多是为了追求财富而来,除了显著的经济动机外,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嫌恶感,对他人及香港社会亦只有极有限的承担,功利考虑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调。其二是由于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完善,造成家庭成员必须相互依赖,并以种种方法增加家庭的资源。其三是在殖民地政权下,中国人被剥夺或削弱政治参与权利,因此家庭群便成为那些在政治上有疏离感的中国人唯一可以认同并退居的社会群体(Lau,1982;1985)。
功利式家庭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把家庭利益置于社会及其组成之个人及整体的利益之上。而在众多家庭利益中,物质利益至为重要。家庭成员间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性十分重要,核心成员且会用功利标准来罗致外围成员进入“家庭群”,以增加家庭资源,因此家庭的范围亦可随之而扩大。成员不单在情感上对家庭有所认同,亦应理解到自己对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家庭成员外出工作非单为工作上的满足感,而强调金钱上的获得,故对工作上的严苛管理并不积极抗拒。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成员是家庭获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家庭利益不再是着重于成员间的感情,而在经济利益,成员间以互惠互利构建出家庭关系。
在这种文化结构下,香港华人的社会参与程度很低,只是被动地向现存体制作出适应。至于试图改造社会秩序,特别是可能会破坏社会之安定,则多招不满。在香港华人眼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政治及社会的安定,使家庭群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内活动。个人及家庭如遭失败,则常会援引一些非社会性及非政治性的因素来自我开脱,其中最常解释是个人与家庭勤奋不足或时运不济,反映出香港华人普遍弥漫着一种社会及政治的无能感和疏离感。
功利家庭主义这一文化结构不利于政治上的动员,因为香港人主要是从功利的态度对待香港政府。此外,家庭群的自助精神亦将许多社会问题在家庭群中处理,而无需上升到政治层次。当这样的文化形态结合所谓“不干预政策”,而社会精英又一心想保持现有地位而采取对政府合作的姿态,结果带来社会稳定。
近年刘兆佳(及关信基)的观点已有所修定,他们认为功利家庭主义和对政府的需求已有根本性的改变,以往香港人政治上的恭顺,不容忍那些含有与政府对抗意味的非正规政治手段等观念正慢慢冲淡。自助精神不再,家庭结构变弱,故社会风气亦由功利家庭主义变为利己个人主义(egoistical individualism)。但对以功利和物质为主导的香港人,利己个人主义在本质上仍和功利家庭主义一样(Lau & Kuan,1988:51-58)。
随着过去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及更多的研究,这种论述开始受到质疑。如吕大乐和黄伟邦在其阶级流动的研究中发现,不同阶层的市民可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和对社会现实不同的理解。即使在同一阶层,其信念亦可能矛盾重重(Wong,1996),而非像刘和关所形容的铁板一块。
譬如说香港社会的流动开放,往往被视为政治稳定的要素。吕和黄调查发现市民的确相信这种“香港梦”原则上存在,但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向上爬升,其实并不乐观。他们亦相信家庭背景左右着梦想的实现。可见一种所谓共同信念或者社会意识形态不一定是十分协调整合,在抽象与具体、核心与边沿信念间可以存在差距、矛盾(Wong & Lui,1992)。从葛兰西学派(Gramscian)的角度看, 这些矛盾差距正为文化变迁埋下伏线。换句话说,如果这种差异、矛盾能够有系统地呈现人前,可能会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冲击作用。
不同的阶层对处理生活上不同层面的问题取向不一。虽然“自助”及“社会网络”是各阶层都会采用的方法,中上阶层自然较有能力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相反,当涉及一些社区性问题,低下层市民更愿意以集体行动的方式诉诸公众(Wong & Lui,1992)。因此, “功利式家庭主义”所描述的内向形态,在某阶层处理某类问题时未必呈现。有些学者特别指出,随着以往香港工业化及金融中心的发展,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中专业及管理工作的“新中产阶级”,表现出一种新的文化外貌。张炳良(1988)认为新中产阶级的动向对香港的政治发展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张氏形容香港的中产阶级为年轻、有干劲、学识高、大部分有专业的知识和工作。一般都推崇民主、自由、公平和平等的原则;同情低下阶层的境遇,也是政治改革的先锋;若中产和基层民众结合,可发挥较大力量。
不过,基于新中产阶级成员来自不同背景,他们是否有如此整合的文化,值得商榷。此外,新中产阶级基本上是透过学历制度及经济领域等自由竞争场所得到晋升,对政治一贯是较为冷漠。新中产阶级能够追求经济上的利益而不需要对资本家等既得利益者作出敌意的行动,而工人阶级亦鲜有行动威胁到新中产阶级的利益。可以说,香港的新中产阶级可以获取及保留利益但又无需在政治上有太多的要求(Lui,1994)。
但无论如何,香港的文化结构已默默地产生变化。199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市民基本上欢迎香港政制民主化,对民主制度有殷切的期望。有82.7%市民认为民主会带来更多自由;80.1%认为民主会令香港政府更顺应民意;76.2%认为会带来更多福利;75.5%认为政府会因此而更受市民爱戴(Lau,1996:163)。可见, 张炳良所言之新中产阶级文化形态已相当扩散。这种对民主、自由以至社会福利的诉求,显示香港的文化结构已慢慢脱离功利家庭主义的轨迹。
不幸的是,市民的“政治能力感”并没有随着他们的民主信念而提升。中英之间、本地商人及民主派间,甚至不同的社会团体对政制的争论,令市民不禁厌烦。争论中涉及之问题的复杂性令市民望而却步。调查发现有近七成市民同意“政治和政府是很复杂,一般人实际上很难知道发生什么事”(箫新煌、尹宝珊,1996)。
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普及、资讯流通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功利家庭主义为核心的文化结构已产生变化。但市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以及对集体行动的日趋接受,并无转化为一股参与公共事务的洪流。这主要是由于政府以至各社团、领袖未能就错纵复杂的过渡问题寻求出路,令市民困于云里雾里,失却自信,亦失却对他人的信任。这种无力、疏离、犬儒(cynicism)心态在香港那种玩世不恭、“无厘头”的大众文化中表露无遗。问题是这种文化心态的发展会否令市民退却回80年代前那种内向的功利家庭主义?如果是这样,回归后的各种制度如何能找到文化的支柱,实践“港人治港”的精神?
四、结语
本文从社会问题的角度,整理以往对香港人口、阶级和文化结构的研究,提出几个问题来共同思考、寻求出路。在人口结构发展方面,本文指出人口老化及新移民剧增可能引致的文化、制度滞差和个人适应问题。在阶级结构发展方面,本文提出在“香港梦”以外,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富裕中的贫穷并未消除。在文化结构方面,保守内向的功利家庭主义,多年来虽为香港普遍市民的行为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亦开始转变。可惜是香港政治发展波折重重,令市民参与公众事务的信心及意欲在幼苗阶段已饱受风霜,甚至有退却的趋势,实在值得忧虑。
既然问题就在前面,我们应该及时面对。只希望市民在要求政府有更大承担之余,民间社会亦应发挥更大的互助精神;在批评、冲击有问题的制度的同时,亦要能以智慧和忍耐寻求出路。如何缔造一个关怀的社会,重建市民的信心,是回归路上的挑战。
*本文初稿发表于1996年10月9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之“香港的远象”学术会议。此文之完成有赖中文大学社会系借调谢庆生同学为研究助理。
注释:
〔1〕所谓社会结构,是指人口按社会划分的位置而分布, 从而影响人们的角色和与他人的交往。至于文化结构,是指文化规范或一套阐释现实及引导行动的理念架构。
〔2〕以1995年计,香港出生婴儿七万多,死亡人数三万多, 自然人口增长四万多。见周永新1996文章。
〔3〕此系数由0至1。0代表绝对平均,1代表绝对不平均。
〔4〕从统计数字看, 最少在一至五等家庭(最低至中等收入的50%家庭)从1971至1991年所占总体收入百分比一直下降。
标签:社会问题论文; 香港移民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移民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