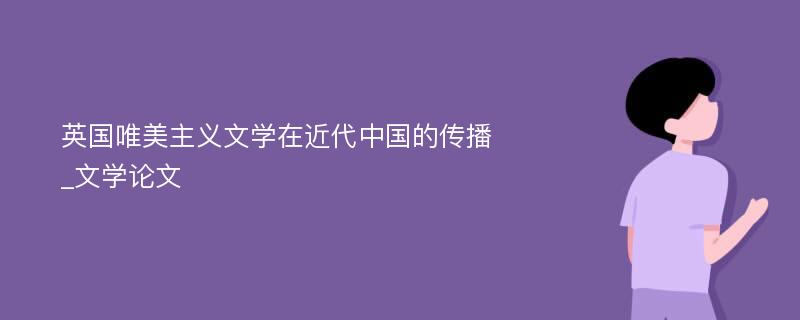
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中国论文,唯美论文,主义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先拉斐尔派到史文朋和佩特
虽然到20世纪初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已盛极而衰,但毕竟余波仍在,加上现代中国作家中留学英美者最多,他们较为熟悉的也大多是刚刚过去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而唯美主义又恰是这一时期英国文学的主潮,所以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对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介绍也就颇为全面,其影响也相当明显。
这里先从先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又译为“拉斐尔前派”)说起。先拉斐尔派是英国唯美主义的先声。1928年之前中国文学界对先拉斐尔派的介绍甚少,只在1925年10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6卷第10号上刊印过D.G.罗瑟蒂(罗塞蒂)的画《李丽斯贵妇》,1926年1 月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一周年增刊》上有徐志摩译罗瑟蒂的诗《图下的老江》(John of Tours)。到了1928年, 情况有了明显改变。这一年是先拉斐尔派核心人物罗瑟蒂的百年诞辰纪念,值此之际,对罗瑟蒂及先拉斐尔派的介绍呈一时之盛。先是在这年5 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9卷第5号上刊登了罗瑟蒂的自画像、 诗作及赵景深的纪念文章《诗人罗赛蒂百年纪念》。接着在6月出版的《新月》第1 卷第4号上刊印了罗瑟蒂的绘画名作《比阿特丽克斯》及中国画家刘海粟所作的两幅罗刹蒂(即罗瑟蒂)画像,还有闻一多的文章《先拉飞主义》。闻一多在文章中对以罗瑟蒂为核心的先拉斐尔派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评论。同年5月间, 吴宓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也发表了一系列纪念和介绍文章,它们稍后转载于同年9月出版的《学衡》第65期。其中,《英国大诗人兼画家罗色蒂诞生百年纪念》一文,较详细地介绍了罗瑟蒂及先拉斐尔派;素痴译的24首《幸福女郎诗》是对罗瑟蒂诗作的最集中的译介,但译者用的是七古体,不易见出原作的精神。最热心的介绍者是邵洵美和他的小圈子。1928年7 月邵洵美主持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2 期为“罗瑟蒂专号”, 其中有邵洵美的《D.G. Rossetti(1828—1882)》一文、朱维基译罗瑟蒂的小说《手与灵魂》、张嘉铸的《〈胚胎〉与罗瑟蒂》一文(《胚胎》,The Germ,是先拉斐尔兄弟会的刊物,又译为《萌芽》)等。此外,1930年10月出版的《真美善》第6卷第6号载有王家棫译罗瑟蒂的诗《当我死了》;1931年1 月出版的《学衡》第73期上还介绍过罗瑟蒂的绘画。
史文朋(斯温伯恩)的诗歌创作在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因而颇受一些中国作家和翻译家的重视。邵洵美就把史文朋奉为自己的“两个偶像”之一〔1〕。他不仅在1927年5月出版的《狮吼》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史文朋》一文,而且还写过一首《怀史文平To Swinburne》的诗〔2〕,表达其对史文朋的尚友之情。 这使史文朋的好友T.J.Wise感动地致函邵洵美说:“假使史文朋仍然活着,他一定要快乐得不得了,知道中国有像你这样一个好友。”〔3 〕朱维基和芳信在他们合作的一部唯美主义译文集《水仙》〔4 〕中介绍了史文朋的诗作。此外,徐志摩和梅川等人也译过史文朋的诗作。对史文朋的介绍在30年代仍在持续, 如1931 年周骄子曾把载于前一年纽约BookMan杂志9月号上的“Swinburne:Thaumaturgist”一文译出,题为《奇人史文朋》,发表在1931年9月出版的《新月》第3卷第7期上。 该文洋洋万言,颇有精彩见解,无疑有助于加深人们对史文朋诗歌艺术独特造诣的理解。
沃尔特·佩特是为唯美主义提供系统理论的重要批评家,自然更受重视。一般以为郭沫若发表在1923年11月4 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26号上的《瓦特裴特的批评论》是第一篇介绍佩特的文章〔5〕, 其实在前一年6月,子贻(可能是胡子贻,本名胡哲谋,子贻或许是其字, 待考)就已译出了佩特的《文艺复兴研究集序》,刊登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1号(1922年6月10日出版)。此着, 胡子贻又写出了《读华尔脱配德的名著两种》,分载于《文学旬刊》第91期(1923年10月8 日出版)和第99期(1923年12月3日出版)。此后, 张定璜又译出了佩特的《文艺复兴时代研究》(即上述《文艺复兴研究》)的著名结尾,这个结尾被视为唯美主义的“传道书”,刊登在1926年8月10 日出版的《沉钟》半月刊第1期上。周全平的《文艺批评浅说》〔6〕也介绍了“佩特底快乐主义批评”。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对佩特的介绍有所深化,并扩展到佩特的创作与哲学思想。在北方,青年学者萧石君发表了《裴德的哲学思想与英国世纪末文学》,刊登在《华北日报》副刊第315 号(1930年11月24日)和316号(1930年11月25日)上。在南方文坛上, 邵洵美、朱维基等对佩特热情颇高。朱维基译出了佩特的小说《家之子》,先在邵洵美主编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9期(1928年11 月出版)上发表片断,1929年5月又由邵洵美主持的金层书店出版;同年1月,朱维基又在《金屋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由他翻译的佩特的《文体论》,据该刊本期的“金屋谈话”透露,其时朱维基正在翻译佩特的小说代表作《享乐主义者梅榴丝》(Marius the Epicurean)。此外,邵洵美在1931年5月20日曾致函中华书局主持人舒新城, 推荐芳信翻译的佩特名著《文艺复兴》(全名为《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7〕。可惜,这两部书稿后来都未见出版, 但南方作家对佩特的兴趣由此可见一斑。另外,(汪)铭竹也译出了佩特的《音乐是可以了解的吗》一文,发表在1930年11月南京出版的《文艺月刊》第1 卷第4号上。
二、持续的“王尔德热”
当然,最受中国现代文坛注目的英国唯美主义作家还是王尔德。最初的介绍可能是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 8〕,其中收有周作人译的王尔德童话《安乐王子》。1915和1916两年里都有人译介王尔德的剧作。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新文学界明显加强了对王尔德的介绍。1917年2月,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热情地呼唤“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出现。从此在中国新文坛上出现了一股竞相介绍王尔德的热潮。王尔德的剧作是这一时期介绍的重点,重要的剧作几乎都被翻译过来,而且有的不止一个译本。风俗喜剧Lady Windermere's Fan 最初由神州天浪生译为《扇》,载《民铎》杂志第1卷第4号(1918年5月出版,未载完), 紧接着沈性仁又译为《遗扇记》,连载于《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差不多与此同时,潘家洵又译为《扇误》,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 月)上;到1923年,洪深又据王尔德原著改译(其实是改编)为《少奶奶的扇子》,连载于1924年《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至第5号,并将它搬演于舞台,风行一时。据朱光潜说,洪深改编本的上演比原作在英国的演出还成功〔9〕。洪深的改编本后来又被收入《剧本汇刊第一集》, 由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1926年,潘家洵又对其1919年的译本《扇误》进行了修订,并改用原名《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由朴社出版。此后以《少奶奶的扇子》为名的译本至少还有三种:张由纪译本,1936年5月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杨逸声译本,1937年6月由上海大通图书社出版;石中译本,1941年7月由长春广益书店出版。 作为王尔德代表作之一的独幕剧《莎乐美》更是备受瞩目,中译本也屡见不鲜,并曾被搬上中国舞台〔10〕。一般以为《莎乐美》最早的中译本是田汉所译的《沙乐美》,它最发表在1921年3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第2卷第9 期上,1923年1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至1930年3月已印行了5次。 其实,早在1920年3月27日至4月1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 就连载了陆思安和裘配岳的译本《萨洛姆》。此后又有徐培仁的译本《莎乐美》,1927年由光华书局出版。1937年1月和3月,上海启明书局又接连推出了汪宏声的译本《莎乐美》和沈佩秋所译同名小说《莎乐美》。1946年6月上海星群出版公司还出版了胡双歌的译本《莎乐美》。 王尔德的其他剧作也不乏中译本。 早在1915 年, 薛琪瑛就把王尔德的AnIdeal Husband一剧译为《意中人》,连载于《青年杂志》第1卷第2 号、第3号、第4号、第6号和第2卷第2号(从1915年10月15日至1916 年10月1日)。该剧后来又有徐培仁译本《一个理想的丈夫》〔11 〕和林超真译本《理想良人》〔12〕。 王尔德的著名喜剧The Importance ofBeing Earnest,由王靖和孔襄我合译为《同名异娶》,1921 年由泰东书局出版;A Woman of No Importance一剧也有耿式之译本《一个不重要的妇人》,连载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5、第6、第8及第12 号(从1921年5月10日至1921年12月10日)。 连不太知名的The Tragedy ofFlorence一剧,也早就有了陈嘏的译本《弗罗连斯》〔13〕。
王尔德的小说代表作《道连·格雷的画像》是译介的又一个热点。郁达夫率先译出了该书的序言,以《淮尔特著杜莲格来序文》为题,发表于1922年3月15日出版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到20年代后期, 王尔德的这部小说成了竞相翻译的抢手货。先是1927年10月赵家璧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10号上发表了《陶林格莱之肖像》的述评(其实是撮述故事梗概,同期还有徐调孚的《莎乐美》述评)。紧接着在次年即1928年,至少有两个人同时翻译这部小说:杜衡的译本《道连格雷的画像》于9月间由金屋书店出版; 而张望(可能是章克标的笔名)的译文《葛都良的肖像画》则从该年1月出版的《一般》杂志第4卷第1 号起开始发表,不过在连载三期后,得知杜衡的译本出版在即,不得不宣告停载。尽管发生了这样的“撞车事件”,1936年6 月中华书局仍然出版了凌璧如的译本《朵连格莱的画像》。此外,曾虚白也编译了王尔德的短篇小说集《鬼》,由真美善书店于1928年4月出版。
王尔德的童话、诗作和散文、文论等也时有中译文发表。最初为王尔德赢得文名的是他的童话,而在中国文坛上王尔德最早也是以童话闻名。自周作人1909年译介了王尔德的童话名篇《安乐王子》后,译介者就接连不断,译文散见各处,而且不乏重译,结集的译本有穆木天的《王尔德童话》和由宝龙的《王尔德童话集》。前者收童话五篇,1922年2月由泰东书局出版;后者收童话七篇,1932年11月由世界书局出版。 对王尔德童话的评论与研究,有周作人的《王尔德童话》〔14〕和赵景深的《童话家王尔德》〔15〕二文,对王尔德在童话上的成就作了相当中肯的分析。王尔德的诗作与散文则有刘复译《王尔德散文诗五首》,载1921年1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1号,张近真译王尔德诗《行善的人》,载1921年11月13日《晨报副刊》。次年7月2日至7 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也有数首王尔德诗的译文(美子女士、张近芬女士译)。王尔德的散文《青年的座右铭》由张闻天译出,载1922年8月29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8 年曾虚白又译了一组王尔德的散文诗,载《真美善》第1卷第7号(1928年2月1日出版)和第9 号(1928年3月1日出版)。稍后,徐葆冰也翻译了王尔德的散文诗《行善者》和《门徒》,发表于1928年12月15日出版的《大江月刊》第3期。 王尔德的最后一部诗作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1898)有沈译民的译本《莱顿监狱的诗》,同张闻天、汪馥泉所译王尔德的散文集《狱中记》(最初连载于1922年4月20、23、24、25、27、28、30日和5月4、 7、8、9、11、12、14日《民国日报·觉悟》上,原名De Profundis, 直译为《从深处》或《自深渊》等)合在一起,1922年12月以《狱中记》为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巴金也曾编译过王尔德的童话与散文诗合集《快乐的王子集》〔16〕。王尔德的文论,除郁达夫所译《杜莲格来序文》之外,还有朱维基所译《谎言的颓败》(The Decay of Lying),收入《水仙》一书中;王尔德著名的The Critic as Artist一文则由林语堂分五次节译发表:《论静思与空谈》(载1928年3月26 出版的《语丝》第4卷第13期)、《论创造与批评》(载1928年4月30日出版的《语丝》第4卷第18期)、《印象主义的批评》(载1929年10月1日出版的《北新》第3卷第18期)、《批评家的要德》(载1929年11月16 日出版的《北新》第3卷第22期)和《批评的功用》(载1929年12月1日出版的《北新》第3卷第23期)。 即使是王尔德表现其乌托邦社会—艺术理想的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1891)一文, 也未被热心者遗漏,震瀛的译本《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1928年由受匡书局出版部出版。
关于王尔德生平和创作的评价文字也为数不少,较为重要的有:沈泽民的《王尔德评传》,载1921年5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2 卷第5号;张闻天和汪馥泉的《王尔德介绍》,连载于1922年4月3、4、 6、7、8、10、11、13、14、16、17、18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该文后来又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狱中记》一书,文字略有修订,并删去了引言与末尾一小节,另写了第十三段。这两篇文章对王尔德其人其文的品评颇为翔实得体,基本上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学界对王尔德的认识水平。20年代中期以后,评介文字仍不断出现,如梁实秋的《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收入《文学的纪律》,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茅盾的《王尔德的〈莎乐美〉》(收入《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一书,中国文化服务社,1935年4月出版)、 朱湘的《谈〈莎乐美〉》(收入《中书集》,生活书店1937年5月出版)、 胡洛的《〈莎乐美〉研究》(收入《胡洛遗作》,上海黎明书局1937年出版)、袁昌英的《关于〈莎乐美〉》(收入《行年四十》,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等等。如果加上各种译本的导言及有关西方近代文学思潮的诸多论著中对王尔德的介绍,数量就更为可观了。此外,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一些西方及日本的文人学者对王尔德的评论也被介绍到中国,如安德烈·莫洛亚的《从罗斯金到王尔德》(郭有守译,载1929年5 月出版的《金屋月刊》第1卷第5期)、本间久雄的《王尔德入狱记》(士骥译,载1930年1月6日出版的《语丝》第5卷第43期), 罗伯特·林德的《王尔德》(梁遇春译,载1933年3月5日出版的《青年界》第3卷第1期)和A.纪德的《王尔德》(徐懋庸译,载1935年4月16日出版的《译文》第2卷第2 期)等。
三、《黄面志》—《萨伏依》作家群及其他
在王尔德之后最引人注目的英国唯美—颓废派文人和艺术家是比亚兹莱、西蒙斯、道生和乔治·摩尔四人。尤其是比亚兹莱和西蒙斯曾先后编辑著名的《黄面志》(The Yellow
Book )和《萨伏依》(TheSavoy),他们以这两个刊物为阵地,呼朋引类,此唱彼和, 把“世纪末”的英国文坛搅闹得有声有色,以至于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文坛被称为“紫红色十年”(“mauve decade”)〔17〕。时隔二十多年后,《黄面志》—《萨伏依》文人集团的名声传到了中国,其魅惑力仍然不减当年。1923年9月,郁达夫在《创造周报》第20号和21 号上率先发表了《The Yellow Book及其他》一文, 满怀同情地向中国新文坛介绍了《黄面志》作家群,由此为《黄面志》在中国赢得了不少热情的爱好者。同《黄面志》相比,《萨伏依》在中国的名气要小得多,但也并非完全寂寞无闻。在邵洵美主持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7期(1928年10 月1日出版)上,有洛文(邵洵美)所译《Savoy杂志的编辑者言》,在同期的编后记“我们的话”中也不忘介绍说:“ Savoy 杂志为 ArthurSymons 所主干, 第一期于一八九六年正月出版, ……撰稿者均为前Yellow Book中作文者。”
诚如郁达夫所说,“使《黄面志》的声价一时高贵的,第一要推天才画家Aubrey Beardsley(通译比亚兹莱——引者)的奇妙的插画”〔18〕。西方文学史家也公认比亚兹莱是围绕在《黄面志》周围的颓废文人们的真正领袖,并认为他那线条纤细曲折、明暗对比强烈的绘画是病态、反常的唯美主义运动趋于堕落之极端的典型表现〔19〕。但也许是由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艺正处在破旧立新的大变革时期,比亚兹莱的违反常规的绘画以及诗文反倒备受中国新文艺工作者的青睐,介绍者、模仿者接踵而至。如果说郁达夫是最早介绍比亚兹莱其人的人,那么在“中国最早介绍比亚斯莱作品的人,该是田汉先生。他编辑《南国周刊》时,版头和里面的插画,用的都是比亚兹莱的作品,而且他所采用的译名很富于诗意,译成‘瑟亚词侣’。后来他又翻译了王尔德的《莎乐美》,里面采用了比亚兹莱那一辑著名的插画,连封面画和目录的饰画都是根据原书的”〔20〕。在这以后,1927年光华书局出版的徐培仁译本《莎乐美》也附有比亚兹莱的12幅插图。1929年4月, 鲁迅也选编了《比亚兹莱画选》,收装饰画12幅,列为《艺苑朝花》第4辑, 以朝花社名义出版。在“小引”中,鲁迅赞扬比亚兹莱“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21〕。同时,鲁迅也批评说,“有时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的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22〕。1929年6月, 浩文(邵洵美)鉴于比亚兹莱的绘画“早经许多人介绍过了,但他的文章与诗也被人尊为别创一格的伟大著作”〔23〕,于是编译了《瑟亚词侣诗画集》,由金屋书店出版,但其中仍以绘画居多。可以说,在20年代后期的中国新文艺界掀起了一股介绍比亚兹莱的热潮。直至1946年,上海星群出版公司出版的胡双歌译本《莎乐美》仍同样附有比亚兹莱的插画。若就对中国新文艺界的影响而论,比亚兹莱为《莎乐美》所作的插图几乎不亚于王尔德的原作。不过,中国新文艺界对比亚兹莱绘画的兴趣中不无猎奇和低级趣味的成份,而比亚兹莱的绘画艺术也确有可诟病之处,如其中颓废、病态和色情的成份就恰好投合了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因而也就难免被人滥用。据叶灵凤回忆,“使得比亚斯莱的作品,在当时给一般人印象甚深的,倒是靠了另一部畅销书,那便是张竞生先生所编辑的《性史》第一集,因为他选用了比亚斯莱所作的《莎乐美》插画第一幅《月亮里的女人》作这书的封面”〔24〕。其实,叶灵凤本人与张竞生相比,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20年代中后期的叶灵凤曾因模仿比亚兹莱的插画而赢得了“中国的比亚兹莱”的名声,对此晚年的叶灵凤供认不讳:“我当时给《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所画的封面和版头装饰画,便全部是比亚兹莱风的”〔25〕。在这些画中就不无颓废情调以至于色情的低级趣味。对此,鲁迅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批评,并称叶灵凤是“新的流氓画家”〔26〕。虽然鲁迅本人也是比亚兹莱绘画的爱好者,他曾坦言,“‘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27〕,但鲁迅在赞赏比亚兹莱过人的天才和非凡的艺术时,也对其缺点有严正的批评。而鲁迅之所以编选《比亚兹莱画选》,恰是有感于当时文艺界对比亚兹莱的介绍和模仿过于偏向其不健康的一面,这一点在他的《〈比亚兹莱画选〉小引》中交代得明明白白:
他的作品,因为翻印了《Salomé》的插画, 还因为我们本国时行艺术家的摘取,似乎连风韵也颇为一般所熟识了。但他的装饰画,却未经诚实地介绍过。现在就选印这十二幅,略供爱好比亚兹莱者看看他未经撕剥的遗容……〔28〕
这清楚地表明了鲁迅不同流俗的着眼点。无论如何,比亚兹莱的绘画对不止一位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过显著影响,确属不容讳言的事实。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就是一例。据冯至晚年回忆,他的为许多人喜爱的抒情诗《蛇》就是在比亚兹莱的或其模仿者的一幅同名画的影响下获得灵感而创作的〔29〕。这幅画还影响过邵洵美和章克标的创作,邵洵美也有一首题名为《蛇》的诗,章克标则有长篇小说《银蛇》(第一部)。
像比亚兹莱一样,道生也颇受一些中国作家的喜爱和同情。诚如西方学者所说,道生“悲剧性的短暂一生完全和‘世纪末’的唯美主义相始终”〔30〕。而一些中国作家之所以对道生的作品特别感兴趣,很可能首先是出于对道生悲惨一生的同情。至少最早介绍道生的郁达夫是如此。郁达夫曾坦率地声明:“Ernest Dowson的诗文, 是我近年来在无聊的时候,在孤冷忧郁的时候的最好伴侣。我记得曾经在一篇小说里,把他的性格约略描写过。大约是因为我的描写还没有力量,所以到了今日,仍不见有人称道他的清词丽句。但我对他的同情和景仰,反而因世人对他的冷淡,倒是日见增高了。”〔31〕正是出于这种同情和不平,郁达夫在《The Yellow Book及其他》一文中对道生的介绍最为详尽, 并附带译出了道生的两首诗《无限的悲哀》和《现在呀我不如西奈拉治下的时候了》。
这虽然不是道生作品的最早中译文(郁达夫的《TheYellow Book及其他》发表于1923年9月,而在同年7月30 日《创造日》第8期上就有郭沫若所译道生的诗《无限的悲哀》,8月11日《创造日》第19期上也有成仿吾所译道生的诗《无望的希望》),但应该承认,中国的新文艺界之真正知有道生其人其作, 还是始于郁达夫在《TheYellow Book及其他》一文中的介绍。此后, 对道生作品的译介逐渐多起来。1924年6月21日《晨报副刊》之一“文学旬刊”第39号上, 有王统照的《珰生E.Dowson 诗选译》, 译介了道生的一首名为Beata Solitudo的抒情诗,认真的郁达夫随后写了《读了珰生的译诗而论及于翻译》〔32〕一文,对王统照的译文有所订正。1925年10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6卷第10号上,有傅东华所译道生的歌剧剧本(其实是诗剧)《参情梦》。到20年代后期,对道生作品的译介明显增多。朱维基、芳信合译的道生诗《致疯狂院中的一人》,朱维基所译道生的歌剧剧本(诗剧)《一瞬间的吟游歌人》,均收入光华书局1928年出版的《水仙》一书;1928年11至12月出版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10、11期连载了朱维基译道生的小说《勃丽旦尼的苹果花》,朱维基译的道生的另一篇小说《骄傲的眼睛》发表在1928年《现代小说》第1卷第5期上;杨子戒译的道生《空排遣》一诗载1929年6月1日出版的《戏剧与文艺》第1卷第2期;梅安娜译道生诗《春风里》载1932 年1月1日出版的《新时代》第1卷第6期; 佩欣译道生诗《四月的恋》和《悲秋》载1932年12月15日出版的《小说月刊》第1卷第3期。集中编译的则有夏莱蒂所译道生诗集《装饰集》,收诗31首,1927年由光华书局出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维基所译的《道生小说集》,收小说8篇, 可说是填补空白的译作,1928年2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当然, 道生主要的创作成就还是在诗歌上。在这方面集大成的译介工作是由戴望舒和杜衡合作完成的。据施蛰存回忆:“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望舒、杜衡,都隐迹在我松江家里的小楼上。日久闲居无事,就以译书为消遣。……当时,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上介绍了英国诗人欧奈思特·道生的诗歌,恰巧商务印书馆西书部新到了《近代丛书》本的《道生诗集》,望舒就去买了一本,正值傅东华译出了道生的诗剧《参情梦》,这个译本,不能使人满意,望舒就倡议与杜衡合译。不到三个月,他们把道生的全部诗歌及诗剧都译出了。这部译稿题名《道生诗歌全集》,由杜衡抄写,当时竟无法出版,一直保存在望舒箧中。”〔33〕尽管如此,这却是道生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史上的重要一笔。虽然这部《道生诗歌全集》未能及时出版,但它至少对翻译者本的创作产生过影响,“初期的戴望舒,从翻译英国颓废派诗人道生和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开始,他的创作也有些道生和雨果的味道”,〔34〕这是戴望舒的生平好友施蛰存所见,应无庸议。不过,在戴望舒早期诗作中这两种味道也许并非等量,只要读读《雨巷》等早期诗作,就不难感受到颓废派诗人道生的影响要比浪漫派诗人雨果的影响更大更深些。
西蒙斯首先是作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而受到中国新文学界推重的,尤其是他的名作《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一书,成了当时中国作家和学者介绍欧洲近代文学的权威参考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些吸取过“世纪末”果汁的年轻作家对西蒙斯赞叹备至。如沉钟社的陈炜谟就钦佩地说:“英国有一位批评家,名字叫作Arthur Symons, 我以为这人的态度很可爱。他的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即《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引者)一书,是我常放在案头翻读的读物,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35〕另一位年轻学者萧石君也把西蒙斯推为“更能继承裴德(即沃尔特·佩特——引者)的衣钵者”〔36〕,并选译过西蒙斯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即使当时的文坛先进鲁迅、周作人和徐志摩等也对西蒙斯颇为推重。例如鲁迅在《〈比亚兹莱画选〉小引》中就曾“摘取Arthur Symons 和 Holbrook Jackson 的话”〔37〕,来说明比亚兹莱的特色;而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时,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西蒙斯来认识英国及欧洲其他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的,1923年回国后,他也把西蒙斯当作自己所喜爱的批评家推荐给国内的文学青年〔38〕。至于一些唯美—颓废情调较为浓重的作家如邵洵美等,更是把西蒙斯奉为批评的权威。邵洵美曾翻译过西蒙斯的《高谛蔼》一文,而邵氏在自己的批评文字中也常常西蒙斯长、西蒙斯短地拉扯个没完。应该说,正是这种崇敬心情,
使邵洵美在复活了《狮吼》半月刊之后,
不忘组织对“Arthur Symons 所主干”的Savoy杂志的介绍,并亲自翻译了《Savoy杂志的编辑者言》(署名“浩文”,出处见前)。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的文学刊物上,也经常可以看到对西蒙斯的译介。如西蒙斯的诗《你为什么温柔》由方纪生译出,载1928年10月16日出版的《北新》第2 卷第23号,他的另一首诗《回忆》由章石承译出,载1933年1月1日出版的《新时代》第3卷第5、6期合刊上。 西蒙斯的文论和文学史论著尤其成了竞相译介的热点,如《事实之于文学》一文由石民译出,载1929 年1月1日出版的《北新》第3卷第1期,《论散文与诗》也由石民译出, 载1931年12月31日出版的《文艺月刊》第2卷第11、12号合刊; 《魏尔伦》一篇由萧石君译出,载1930年8月15日出版的《文艺月刊》创刊号, 《两位法国象征诗人》和《法国文学上的两个怪杰》由曹葆华译出,分别刊载于《文学季刊》第2卷第2期及第3期(1935年6月及9月出版)。
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接受过各种艺术流派的多种影响,并且复杂的民族情结也影响过他的文学活动,但不论怎么说,他对唯美—颓废主义曾经颇为热衷,确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而这一点恰好是一些中国作家对摩尔感兴趣的地方。这种兴趣自然不应夸大。事实上,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中摩尔几乎是个无人问津的作家,但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他却颇受某些中国作家的青睐,尤其是邵洵美主持下的“狮吼社”同仁对摩尔颇为热心。邵洵美是摩尔的崇拜者,并与之有通信联系。据邵洵美在1928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透露, 当时刚刚病愈的摩尔“一出院便寄给我一册最近由Traveller's Library出版的The Confessions of AYoung Man增订本。我去谢他的信,大概已收到了”〔39〕。 两个月后, 徐志摩在从欧洲寄给邵洵美的一封信中报告说:“我已见到GeorgeMoore,他叫我代他问候你。此老真可爱……”〔40 〕虽然摩尔对邵洵美可能只是客气的敷衍,但邵洵美对摩尔确是真心实意的崇拜〔41〕。正是怀着这种崇拜之情,邵洵美在先后主持《狮吼》和《金星月刊》两个刊物期间,始终注意推动对摩尔的介绍。在1928年8月16 日出版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4期上,邵洵美发表了《纯粹的诗》一文, 详细介绍了摩尔的纯诗理论,并对英国学者R.D.詹姆斯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不准确说法作了纠正。稍后,邵洵美又连续译介了摩尔的几部作品:描写一位有夫之妇私情的短篇小说《信》(Letters),载1928年11 月出版的《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9期; 从摩尔的《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忆》(Memories of My Dead Life)一书中选择的几个片断,载1929 年1月出版的《金屋月刊》第1期。不久,在1929年5月,邵洵美又在金屋书店推出了全书的中译本;小说《和尚情史》〔42〕的译文载1929年2 月出版的《金屋月刊》第2 期; 甚至连摩尔翻译的一部古代传奇Daphnisand Chloe(今译为《达弗尼与克洛埃》, 叙述两个牧羊的少男少女性爱意识的觉醒),也被邵洵美重译为《童男与处女》,发表在1929 年4月出版的《金屋月刊》第4期上。此后,在1930年6月出版的《金屋月刊》第1卷第9、10期合刊号上,邵洵美还发表了《George Moore》一文。其他人如曾虚白、费鉴照、招勉之也对摩尔有所介绍,如《真美善》第5卷第6号(1930年4月16 日出版)上就有曾虚白译介的乔治摩阿(即乔治·摩尔)“名著”《三十岁妇人的迷媚》。但他们都不如邵洵美那么专心致志。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坛知有乔治·摩尔其人其作,主要是靠邵洵美努力。反过来看,乔治·摩尔对邵洵美的创作也确实产生过影响。例如邵洵美的创作以“颓加荡”(邵氏对Decadence 的庸俗化译名)的官能刺激为特色,而这显然与乔治·摩尔的影响有关。难怪郁达夫在读了邵洵美发表于《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5 期上的小说《搬家》之后,曾欣然致函邵洵美,称他的这篇小说“大有George Moore的风味,是近来少见的飘逸的文章”〔43〕。
四、两本系统介绍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专著
综上所述,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对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介绍是相当广泛和持久的,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只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发生过一段短暂的“王尔德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英国唯美主义文学的介绍,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几年间达到了前所未见的广度和深度,其标志是出现了两部系统介绍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发展史的著作。一部是滕固的《唯美派的文学》,1927年7 月由光华书局出版发行。滕固20年代初在日本留学时因读沃尔特·佩特的论著而对英国唯美主义文学产生了兴趣;20年代后期由于邵洵美的推动,加上当时一些文学青年对唯美—颓废派文学的兴趣,不期而然地重新唤起了滕固“夙昔的爱好”。《唯美派的文学》就是由作者应某高校青年朋友要求所作的讲演稿汇集而成。这是现代中国文坛上出现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专史,更准确地说是一部英国唯美主义运动史。但滕固并没有完全局限于“世纪末”的英国文学,而是把视野扩展到18世纪末叶的诗人画家布莱克和19世纪前叶的天才诗人济慈。滕固同时也敏锐地看到,英国“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并不完全是英国本土的产物,而是“直接与大陆尤其法国象征主义(Symbolism)相结合”的结晶, 因而他认为英国的“唯美运动,远之是完成浪漫派的精神;近之是承应大陆象征派的呼响”〔44〕。
继滕固的《唯美派的文学》之后,萧石君又在1930年撰写了专著《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部分章节曾在一些刊物上先行发表,全书则由中华书局于1934年9月出版发行。除最后一章论爱尔兰文艺复兴外, 全书主要讨论“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实际上就是英国的唯美主义文学运动。同滕固的《唯美派的文学》相比,萧石君的这部专著又有明显的进展。如对裴德(佩特)哲学思想的探讨,就深刻触及到了英国“世纪末”唯美主义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其悲剧性的人生观或生命观。同时,萧石君对“狄卡丹”(Decadence )的起源及其风格特征也有详实准确的阐述。尽管这本名为《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的著作着重叙述的是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历史,但萧石君并不是就英国而论英国文学。他在书的开头就明确交代说:“往日编者读世纪末英国文学,知道它受法国文学的影响极大。年来读法国象征派的作品,心中更多印证,遂着手编译本书。”〔45〕因此,萧石君在这部著作中特别注意揭示“世纪末英法文坛的关系”,从而在更具国际性的文学视野中对英国唯美主义文学作出了正本清源的叙说。这种深度和广度都是以往的介绍所无法比拟的。
注释:
〔1〕邵洵美《两个偶象》,载《金屋月刊》第1卷第5期(1929 年5月出版)。
〔2〕载“狮吼社同人丛著第一辑”《屠苏》,光华书局,1926 年。
〔3〕《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9期(1928年11月16日出版)上“金屋谈话”之(六)“史文朋的好友”。
〔4〕光华书局,1928年。
〔5〕稍前,郭沫若在1923年10月28日出版的《创造周报》第25 号上发表的《批评——欣赏——检查》一文中,就摘译了裴特(佩特)的《文艺复兴论》(全名《文艺复兴:艺术与诗的研究》)序言中论“审美的批评”一段,作为“对于批评家的真正的要求”。
〔6〕商务印书馆,1927年。
〔7〕《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第123页, 中华书局, 1992年。
〔8〕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1909年。
〔9〕孟实(朱光潜)《旅英杂谈》,载《一般》第1卷第2 号(1926年10月5日出版)。
〔10〕南国社曾在1929年7月演出《莎乐美》。据田汉回忆, “特别的是为着《莎乐美》,我们在短时间与贫乏的经济状态中所费的气力颇多”,见《我们自己的批判》,《田汉文集》第14卷第339—34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
〔11〕金屋书店,1928年10月。
〔12〕神州国光社,1932年6月。
〔13〕连载于《青年杂志》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和第3 号(1916年11月1日)。此外,在1918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2号上有刘半农译“英人”P.L.Wilde著独幕悲剧《天明》(Dawn); 阿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将这个P.L.Wilde与Oscar Wilde当作同一个人。其实P.L.Wilde(1887—1953)是美国人, 以写作独幕剧著称,著有《黎明及其他独幕剧》(Dawn and Other One-Act Plays of Today,1915)。
〔14〕载《晨报副刊》1922年4月2日。
〔15〕连载于《晨报副刊》1922年7月15日和16日。
〔16〕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
〔17〕〔19〕〔30〕参阅塞缪尔.C.丘和理查德.D.奥尔蒂克《英国文学史》第4卷第1482、1482、1483页, 劳特利奇和基根·保罗出版社,1967年第2版。
〔18〕《The Yellow Book及其他》,载《创造周报》第20 号(1923年9月23日出版)。
〔20〕叶灵风《比亚斯莱的画》,《读书随笔》第二集第296页,三联书店,1988年。按,叶灵凤的这段回忆可能有误,田汉翻译出版《沙乐美》在前,主编《南国周刊》则是后来的事。
〔21〕〔22〕〔28〕〔37〕《集外集拾遗·〈比亚兹莱画选〉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第338、338、339—340、34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3〕《我们的话》,载《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11期(1928 年12月1日出版)。
〔24〕〔25〕《比亚斯莱的画》,《读书随笔》第二集第297、296页,三联书店,1988年。
〔26〕《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7〕《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9〕冯至《外来的养分》,《立斜阳集》第187-188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
〔31〕《The Yellow Book及其他》,《创造周报》第20号。按, 这里郁达夫所说的描写道生性格的小说即其处女作《银灰色的死》,最初发表于1921年7月7日至9月13日《时事新报·学灯》。 在这篇小说的末尾,郁达夫特意用行路告示的方式点明, 死去的主人公“衣袋中有Ern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一册”。郁达夫还在篇末用英文写下了一段附记,其中特别申明:“One word however,must be mentioned here that he owes much obligation to R.L.Stevenson's A Lodging for the Night and the life of Ernest Dowson for the plan of this unambitious story”,意为:“有一点必须说明, 作者的这篇不足道的小说之构思,从史蒂文森的《宿夜》和道生的生平取材不少。”
〔32〕载《晨报副刊》1924年6月29日。
〔33〕施蛰存《〈戴望舒译诗集〉序》,《文艺百话》第224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按,由戴望舒和杜衡合译的这部《道生诗歌全集》也有部分曾在当时刊物上发表,如署名戴望舒、杜衡译的《道生诗抄》载于1929年11月15日出版的《新文艺》第1卷第3号,“全集”则在戴望舒死后由施蛰存保存,居然无损无厄,如今已全部编入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戴望舒诗全编》中。
〔34〕施蛰存《〈戴望舒诗全编〉引言》,《文艺百话》第232 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35〕有熊(陈炜谟)《谈文学批评》(续), 载《华北日报》1929年6月24日副刊第98号。
〔36〕萧石君《裴德的哲学思想与英国世纪末文学》,载《华北日报》1930年11月24日副刊第315号。
〔38〕参阅徐志摩《近代英文文学》第六讲,《徐志摩全集补编》第3卷(散文集),上海书店1994年据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版重印本。
〔39〕邵洵美《纯粹的诗》,载《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4 期(1928年8月16日出版)。
〔40〕见《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9期(1928年11月1日出版)上“金屋谈话”之(七)“徐志摩来信”。
〔41〕参阅邵洵美《贼窟与圣庙之间的信徒》,《火与肉》第51—52页,金屋书店,1928年。
〔42〕此书原名不详。按,乔治·摩尔曾改写过著名的传奇故事《爱洛绮斯和阿贝拉》(Heloise and Abelard,1921), 但《和尚情史》的男女主人公却叫Crede和Dinoll。——录以待考
〔43〕郁达夫信见《狮吼》半月刊复活号第7期(1928年10月1日出版)上的“狮吼信箱”。
〔44〕《唯美派的文学·小引》,光华书局,1927年。
〔45〕《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序言》,中华书局,1934年。
标签:文学论文; 唯美主义论文; 翻译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翻译理论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王尔德论文; 莎乐美论文; 水仙论文; 比亚兹莱论文; 邵洵美论文; 语丝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