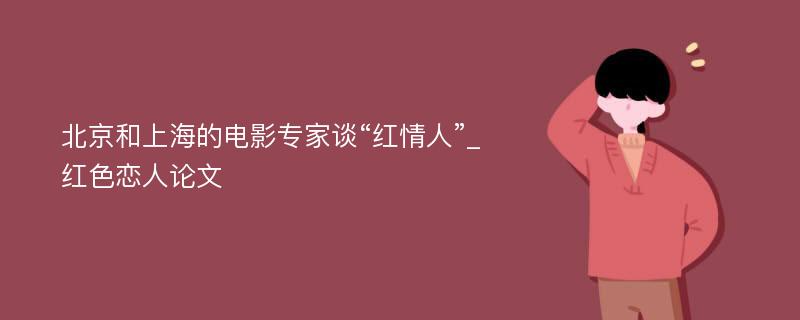
京沪两地电影专家纵谈《红色恋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地论文,京沪论文,恋人论文,红色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文斌(《中国电影报》总编辑):每次看紫禁城的新作心里都很激动,这次是第二次看《红色恋人》仍很受感动。在这里我们来研究它很有意义。
叶缨(该片导演):在《红樱桃》的采访中,认识了许多老前辈及一些革命烈士后代,我们了解了许多革命者故事。由于是家里人讲,所以跟我们以前了解的角度不一样,包括一些个人情感上东西,很感人。当时就很想拍一部反映革命者浪漫情怀的影片。96年初,我们开始创作,一开始剧本中没有外国人,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去交待地下党的工作,再就是成本问题,我们要考虑到市场,投资这么大,只在国内发行是不行的,所以后来想到用英语和引入一个外国人来,结果这一个改变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我们的真实是根据一个外国人的回忆来表现的,这样就把最具有表现性的东西留在了银幕上,再把一些具体的交待省略了。这个剧本准备了两年多,拍摄了50多天。
彭加瑾(《文艺报》副主编、著名评论家):紫禁城在成立很短的时间内,不断出奇出新,出了不少佳作。这种探索、创新精神很可贵。《红色恋人》从视觉上来说有很多可取的宝贵的地方。新的视点和表现方式都很好,角度也很好,是一个陌生者来理解我们的革命。在声音上比一般的国产片都要好,包括音响语言的使用,也很大胆,在需要强调的地方音响也给了很大的冲击。
阎晓明(广电总局总编室副主任):看完之后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部片子比较成功的把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对历史题裁的影片有一种新的拍法。一代年轻人在看历史时候会加一些自己的想法,时代的体验。我们以前有些作品塑造的人物有些概念化、脸谱化,带有时代的烙印。这部影片从外国医生的角度来讲这个共产党人,他看的更多的是人格魅力,意志的魅力,而对共产党人政治上追求未必能理解,对今天的观众来说,这里没有直接表现靳的工作的,表现更多的是其丰富的内心世界,如果把共产党人都写成不食人间烟火,这在艺术上站不住的。这部片子最大的成功是人物的成功。
于敏(电影理论家、剧作家):我想艺术品本身是很难比较的,叶导走的路很正,这是当前电影界很难追求的。没有哗众取宠的东西,影片很动人,情绪很饱满。看片过程中我内心很激动。通过人物关系来讲故事,表达人的感情与思想活动,从真实角度来讲许多东西值得推敲,但是我在看片的时候,就忽略了这些,而被影片的人物所打动,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是永远探讨不完的,艺术魅力使我不去追求真实细节。总的来说影片很好,希望能够叫好、叫座。
张卫(影评家):该片不论是故事情节、画面的颜色还是机位都十分欧化,叶导探索信仰,超脱了政治高度。中国文化是入世的文化,但今天我们把许多东西变得很粗俗。因此,青年缺乏了对理想的追求。这部浪漫的片子,确实让我们感动,我们今天的人也应该追求一种信仰。
梁光弟(全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很激动,用一句话概括这部影片就是融入历史情感的浪漫,是表现人的情感世界、人的魅力的。秋秋对靳的感情,有男女的感情,也有与理想信念结合起来的感情,这个给我的印象比靳更深。通过人性的东西来表现人物的信仰。讲一个好故事吸引人,正路与新路结合很好。
罗艺军(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我们的社会经历很多,为什么我们电影这么平淡?这部影片,在视听语言,导演的构思,镜头的衔接方面,总的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有些镜头确实给人诗意的感觉(比如靳被处决一场)。但总的来看我们的电影与国外电影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如果我们的电影要占领我们自己的市场,这些基本的功力,制作水准方面还是要进一步提高。不足的方面,是老上海“老”得不那么地道,革命者当时的生活,精神状态上某些东西把握得还不十分准确。
王人殷(《电影艺术》主编):这是一部令人感动的,富有艺术魅力融入个人情感的影片。可以说是从一个现代青年,甚至可以说叶缨自己的视点去看历史和先辈,这一点非常独特,影片风格是诗意的,同时又是很粗俗和大众化的。故事本身具有传奇色彩。其实,爱情的三角关系在以往的经典影片中非常常见,但在本片中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和突破。
章柏青(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影视研究所所长):八十年代末至今,电影市场出现滑坡,电影产量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电影导演逐渐探索着打破艺术片与商业片之间的一堵墙,有些导演在这个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比如张艺谋,他的有些影片我们已经很难说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我想这些探索可能能够改变“电影危机”,能够起到雅俗共赏的作用,叶大鹰导演就是在此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导演,这部影片的情节与感情心理方面的描绘结合得相当好,真正达到了既有相当的艺术质量,又能吸引观众的初衷。
邹建文(《中国电影报》编辑部主任):本片调动各种手段来表现导演心中的“红色情结”。九十年代的革命影片该如何去面对青年,面对观众,这部电影起了一个很好的开头。而且我也希望叶大鹰导演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更为风格化,更为成熟,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自己的风格。
李文斌:走正路,走新路是新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应把握的宗旨。
梅朵(著名电影评论家):看完这部影片非常激动,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影片表现了人类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美。可以让人在精神世界里得到提高。整部影片没有让人感到是在重复过去的一种手法来叙述故事,而是用一种全新的艺术手法来释意一个革命者的故事,有一种新的艺术生命在里面。第二是导演在表现手法上处理的很新。在整个处理方式上,在叙述方式上都很新。节奏感觉很跳跃,有一种动感的美。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感人的影片。
顾晓鸣(电影评论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现在我们终于看到了新一代的艺术家,在一个全新的角度上把历史重新拆开,重新组合。在他们的作品里洋溢着历史的激情,用他们的眼光认识并重新理清历史的关系。他们深入历史,表现的是一种他们对历史的感受和心情,最后结果是看完他们的作品之后我们把眼泪掉在影片上。距离了这么多年的历史,我们感觉到了那些历史人物,包括“靳”,包括“秋秋”都被升华了,崇高了。中国的电影终于让我们看到了一部有诗味的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这部电影的出现预示着中国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表现会出现一个新的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所表现的革命女性。
张瑞芳(著名表演艺术家):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有一种期待,期待我们的影坛上能够很好地表现我们过去这代人的革命情操。历史实在是太美了,但也太复杂了,有些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戏,我需要有很大的耐力才能看得下去,要想有一种突破的东西,真是很难找到。这部影片富于激情,有极强的浪漫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凝聚了的,升华了的浪漫,影片洋溢着的激情,比真的更感动人。我以前听说过这部影片,在没来看片之前,我还担心像我们老的这一代人可能不会接受,但我现在看过之后,我倒有些担心年轻人能不能理解和接受。因为这的确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看完能让人思索的主旋律影片。
吴贻弓(上海广电局艺术总监,著名导演):“看了《红色恋人》以后非常非常的高兴。首先,觉得叶大鹰导演有一种跨跃式的成长。影片从构图,从音乐,从视听,从所有的技术手段,为主题内容进行了非常得体的处理。从中我感到了导演的成熟与成长。第二,非常佩服紫禁城公司,他们用一种新的思路,用很短的时间给我们电影界以很大的启示。就剧本创作来讲,几十年来中国电影有了一种非常凝固的思维定式,这种思维定式制约了我们的发展,而谁又不肯承认,以此为创作几十年,到最后是观众不承认你了,不看电影了,这种固定的思维定式使我们电影难以发展。去年十二月份,我看到了一篇文章。电影界已经开始注重这个问题了。首先是编剧怎么从固定的模式中走出来,重新演绎我们的革命历史生活,中国电影如何从一种非常浅薄近视的功利主义中跳出来。制片人、导演要从拖住中国电影的这种方式中冲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讲,在我们目前的电影状况下出现了像《红色恋人》这样的影片对革命者的塑造,对革命历程的叙述,对革命者和叛徒关系的演绎达到了一种令人震撼的高度。在中国电影第三次高潮之前,我觉得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不是我们过去习惯的那种思维方式。而我们过去习惯的方式现在已经不能得到观众了。它的出现预示着一种生机,一种美好,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意义。可能大家认为我现在说的是言过其实,但是我们可以等待几年以后回头看,时间和历史将证实一点。我虽对影片导演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我还是感到了不满足,为什么这个医生是个美国人而不是一个中国人,而这个中国人最后也是一个革命者呢?影片还可以再深一点儿,再开放一点儿。
徐生民(《电影时报》主编):这部影片已经被关注很久了,张国荣演革命者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点,我看完以后感觉张国荣演的这个革命者非常有个人魅力、有个性、有风采。风采和魅力的这种结合使这部影片的人物立住了,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感。《红色恋人》在艺术表现上也是颇具新意的一部影片。影片本身完全风格化,电影理想主义的色彩已经接近于诗化,具备了非常强烈的故事色彩,它的张力很大。但并没有写实,而是用大量的回忆把情绪托得特别饱满,不是在叙述精彩的故事。要说遗憾呢,就是‘靳’和‘秋秋’间的关系,在同志阶段到爱人阶段的这种变化和转移,我觉得少了一点儿,好象缺乏过程,还可以深一点。
方全林(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我看这部影片很受感动,艺术就是要写人、写独特的人。这种独特的人是为理想而战的人。影片中表达的这种纯真的情感,崇高的精神是人类共有的,所以影片的这种精神被大家所接受,这种美好的情感被大家所接受。大鹰把这种东西表现出来,老前辈、年轻人都接受了。艺术要独特,创新是艺术独有的品格,创新是民族艺术的灵魂。这部影片确实使我们感到了这些。我们要认真研讨一下上海电影界的问题。我听说这部影片,叶大鹰原来找过上海,但我们不够热情,人家本想与上海合作的,结果走了。而紫禁城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紫禁城是独特的,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教训也是深刻的。我们要认真的好好想一想,我们平时总认为我们的本子少,好的题材少,而好的题材送上门来我们又放掉了,这个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紫禁城这次送来的不仅是好的片子,而且还有好的机制。我们代表上海市委宣传部对北京表示祝贺,我希望加强我们两地的合作。我想京沪合作会促进中国电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沈然、戚锰根据录音整理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