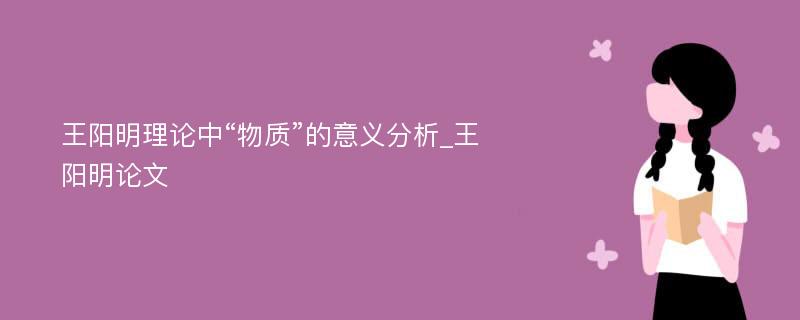
王阳明理论中“物”的含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含义论文,理论论文,王阳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王阳明的心学哲学中,源自《大学》三纲八目之四条目“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心、意、知、物”是具有理论建构性的核心概念,同时也是我们理解其哲学思想的着眼点和必经途径。王阳明之所以选择它们作为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结构性概念,其直接的历史原因与朱子极为重视《大学》有关。牟宗三认为:“此是以《大学》为主而决定《论》、《孟》、《中庸》、《易传》也。是故《大学》在伊川、朱子之系统中,其比重比以《论》、《孟》、《中庸》、《易传》为主者为重,对于其系统有本质上之作用,而在其他则只是假托以寄意耳。”①可见《大学》在朱子哲学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由于王阳明的心学系统是在批判当时居于权威地位的朱子理学系统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必然也同朱子一样以《大学》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主要文本依据,因此,他选择“心、意、知、物”这四个概念作为建构自己新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无疑是由于朱子的深刻影响。除了直接的历史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心、意、知、物”这四个概念恰恰是王阳明以“心物”关系为存在论基础的心学体系不可或缺的结构性概念,其内容与性质相当于原始佛学的“五蕴”理论或法相宗的“五位百法”理论,②其理论价值和意义是它们在以“理气”关系为存在论基础的朱子理学体系中所不具有的,当然也就不能像牟宗三那样认为仅仅是“假托以寄意耳”。
一、物的一般规定
在“心、意、知、物”中,我们首先分析王阳明对“物”的理解。他有关“物”的论说按年代顺序主要有以下几条。其一,《传习录》上:
爱曰:“爱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的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可无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③
其二,《传习录》下:
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④
其三,《答顾东桥书》:
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⑤
其四,《大学问》:
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⑥
王阳明以“事”释“物”的说法承继自朱子。朱子在《大学集注》里注释“格物”曰:“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⑦在日常的理解与使用中,“物”一般表示具有空间性的现象存在,“事”则一般表示具有时间性的现象存在,譬如《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一语,“本末”是表示空间性的概念,“终始”是表示时间性的概念。空间性现象如山川草木、桌椅板凳之类,时间性现象如人的各种身心行为、事物的变化过程等等;当然,时间性是构成一切现象的最普遍特性,所有的空间性现象都具有时间性,但并非所有的时间性现象都具有空间性,人的心理现象即不具有空间性。虽然“物”与“事”在日常生活的理解和使用中有各种各样的区别与习惯,但人们却并不在理论与生活的使用中做特别严格的区分,而是一般用“事物”、“事事物物”、“万事万物”来泛指一切现象,朱子、阳明皆是如此。朱子之所以特别指出“物,犹事也”,却是为了强调把人的实践活动之“事”包含在“物”的范围,从而使“格物”突出地指向人的实践活动。这既是由于朱子作为一名儒者重视实践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必有之义,也是由于他的理论主要渊源于伊川的缘故。伊川早已指出:“物,则(一作即)事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并且强调“格物”的主要指向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事接物而处其当当”,即人在历史与现实中的实践活动;但他并没有把山川草木等自然事物排除在“格物”的范围之外,他说:“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⑧朱子的“格物”范围大体继承了伊川:“或考之事为之著,或察之念虑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讲论之际,使于身心性情之德、人伦日用之常,以至于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⑨,一切社会与道德的实践行为、内在的性情与心理活动、书籍文册之记载、古今人物之事迹以及外在客观的天地鬼神、鸟兽草木之类,凡是“格物”所能指向的现象存在都属于“物”的范围。可见,朱子的“物”即《墨经》“有实必待之名”的“达名”或《荀子》“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的“大共名”⑩,相当于哲学上最广泛意义的“存在”范畴,用以指称包括物质、心理和社会现象在内的现象世界之全体。但是,朱子的“物”又具有鲜明的特征:一,由于朱子在“知”与“行”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因此“物”作为“格物”的对象仅仅是认识对象而不是实践对象,实践对象是作为“物”之“所当然”与“所以然”的“理”;二,作为“格物”对象的实践活动、心理行为、外在物体之间虽然有先后、轻重、缓急的不同,但它们作为认识对象或认识客体的性质是同等的,关系是并列的、平行的,都是作为“一物”而具有“一物”之“理”的独立现象;(11)三,在朱子的认识关系中,“物”作为认识客体尽管与认识主体密切相关,但其存在本身是预定的,根本不涉及“物”的存在根据问题,更不会将其存在与主体联系起来。
表面上,王阳明以“事”释“物”的说法似乎与朱子没什么不同,而且都是为了强调将“格物”的目标指向人的各种行为或社会实践活动,但与朱子仅是将“事”归属于“物”的范围不同,王阳明则是用“事”来规定“物”,也就是说,“事”不仅仅是属于“物”中的一类,而且本身就是“物”的全部。这一点决定了王阳明以“事”释“物”的观点与朱子的观点在相同的形式下具有不同的本质内容。首先,朱子的理论严格区分“知”和“行”,并讨论两者的先后难易等问题,认为认识与实践是两类不同的行为,认识是实践的基础,实践是认识的实行,而“物”只是认识对象而非实践对象,实践对象奠基在认识对象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观点则主张“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的“知行本体”(12),其实质是突显了“行”对“知”的优先地位和统摄作用。对他来说,无论“知”是指“知孝”、“知弟”的道德良知,还是“知饥”、“知寒”的感受知觉,或者是属于“见闻”领域的认识,都属于人的行为或社会实践活动,即都被“行”所涵摄。所以,作为与“存在”范畴相当的“物”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首先是实践的对象或实践的客体。(13)其次,既然“行”可涵摄“知”,认识行为是实践行为之一,那么像山川草木之类外在物质现象作为认识客体的同时又是实践客体,构成了实践客体众多内容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各种行为或实践活动之“事”是“物”的一般含义,山川草木等现象则是“物”的特殊含义,它们的关系是涵摄与被涵摄的关系,不是并列的、平行的,也就是说,它们作为“物”的所指具有不同的含义层面和范围。第三,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涉及“物”的存在论问题,提出“意之所在便是物”的观点,认为“物”是作为主体的意识之对象而存在的,把“物”的存在与主体联系在一起,进而把“物”的存在归附于主体的意识,说:“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这一关于“物”之存在根源问题的思想不仅彻底颠覆了朱子以理气关系为存在论基础的理学体系,为他建立以心物关系为存在论基础的心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成为我们理解王阳明心学理论中“物”的含义的一个导引。
二、物的四个含义
王阳明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出“意”是心的作用和功能,即它是表示主体的概念。主体在不同的关系中具有不同的性质,与之相对的客体就具有不同的含义,如:在认识关系中,主体是认识主体,客体就是认识客体;在实践关系中,主体是实践主体,客体就是实践客体。“物”作为“意之所在”即主体的意识对象正是表示与之所对的客体概念,因此我们就从主体的意识对象或者说客体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和理解王阳明心学中“物”的含义及其意指。
第一个含义就是指“事亲”、“事君”、“治民”、“读书”、“听讼”、“仁民爱物”、“视听言动”之类的人类行为、活动、实践之“事”,也就是王阳明通常对“物”的一般规定或说明。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活动是属于每种存在物的,每种存在物都有其特有的活动,石头有石头的活动,植物有植物的活动,动物有动物的活动,人也有人的活动(14),而王阳明则认为,活动只是属于人的活动之“事”,其他任何不属于人的活动及存在都被涵摄在“事”的范围之内而成为其一部分。所以,人的活动或行为就成为“物”的最一般、最普遍的含义,外延最广,内涵最少,相当于黑格尔哲学的存在范畴。当然,“事”的含义在实际的理解里已经蕴含有时间性、属人性、变化性等因素,根本达不到存在范畴的抽象程度,这是由于“物”在此不是认识论的最高抽象而是实践论的总体概括。
在王阳明那里,人的行为或活动又可从两个方面去理解和分析。一是把行为本身视为一个存在整体去认识,即行为是认识对象或认识客体,所形成的认识是关于行为主体、行为客体及其关系的知识,而一切关于人的行为或实践活动的理论就是从其中产生的,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日常与人论学时也是从这个方面看待行为的,即把行为看作一个认识的对象或探讨的知识内容。对行为的认识,最重要的是对行为者之行为主体的认识,因为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是行为主体,如佛学将行为分为身、语、意三个因素,身、语是假法,意是实法(15),即作为行为外在表现的言行依赖于作为行为内在主体的意识,王阳明也说:“身之主宰便是心”、“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强调行为主体对行为的主宰和决定作用。对行为的另一个方面的理解是把行为视为行为主体当下正在进行的具体行为。在此情况下,与前者注重主体不同而是注重客体,“物”是除行为主体外的其它一切存在,即行为客体,通常称之为实践客体,其中主要有实践对象、实践基础、实践条件三个因素。对王阳明而言,这方面的理解才是他所实际意指的含义,由此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包含于其中的“物”的其它含义。
第二个含义是实践对象,实践对象如果从实践主体方面来说即是实践的动机或目的。人的实践都是有目的的实践,目的就是通过实践所要实现的价值,也就是尚未实现、有待实现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在王阳明的道德哲学里,就是“至善”。《传习录》上:
爱问:“至善之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16)
至善、孝、忠、信、仁这些价值观念就是道德实践的目的或对象。其中,至善是道德实践的最高目的或终极对象,孝、忠、信、仁则是至善在不同类型的道德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其思想源于《中庸》释“止于至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人们在每一次具体的道德实践中,仁、敬、孝、慈、信等德目的每一次实现都是至善的实现,于是,至善及其具体德目就在每一次实现中从观念与理想的价值形态转变为现实与可感的价值形态。在这个意义上,“物”作为实践对象的含义也从理想转化为现实。此外,其它类型的实践也是如此,如读书,读书的目的是求知明理,知识之真与伦物之理的价值通过读书的过程就从理想的实践目标变成现实的知识。
第三个含义是现实的价值客体。观念和理想的价值是存在于未来的价值,需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实现,但是,即使它们的存在只是观念性的存在,却也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来源于过去的和现在的价值实在,由价值实在所构成的价值环境就是实践赖以进行的基础。其中,由于价值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状况差异,它们对每个具体的实践活动所起的作用就有大小轻重的不同:有的价值是核心价值,起着主导、支配和决定的作用,从而成为实践对象产生的价值根源;有的价值是边缘价值,起着辅助、配合的作用,仅是实践活动的一般价值环境。在王阳明的道德实践理论中,作为产生实践对象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主体方面就体现为道德实践的动力,所以他从道德实践动力的角度阐发实践对象的根源问题。《传习录》上:
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17)
诚孝的心便是对父母的深爱,王阳明以“事亲”为例说明子女对父母的爱是实践“事亲”行为的根据,而实现“事亲”行为的方式与方法则是发源于爱之根据的条件,就像树木的根与枝叶一样,是先有了根然后才有枝叶,不是先有枝叶然后种根。在这里,爱的价值不仅是实现实践目的“孝”的实践条件与手段的价值根据,而且是发动“事亲”行为的实践动力和产生实践对象的价值根据。任何一个其它类型的实践活动都是如此,都有其自身发生的价值环境,从中发起实践活动、产生实践目的并且在其中选择适当的实践方法去进行和完成实践活动,从而使实践对象从理想变成现实。
第四个含义是作为实践条件的客观世界,既包括具有时空性的物体实在、身体实在、社会实在也包括只具有时间性的心理实在。实践条件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两个方面:主观条件是人们内在于意识而存在的知识状态,客观条件就是外在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在具体实践中,内在的主观条件属于主体的能力,一般情况下不是主体的“意之所在”,即不属于“物”的领域,而客观条件则是主体进行实践活动所必备的客观实在环境,无疑是属于“意之所在”的“物”。
在上述“物”的四个含义里,实践客体是实践主体所参与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之“事”的一般含义,即对“物”的含义的一般性总体概括,其具体的内容就是其它三个含义,即实践的价值对象、实践的价值基础和实践的客观条件。它们之间虽然含义不同、结构有别、关系复杂,但都被包含在实践客体的含义之内而成为其组成部分。王阳明的道德实践哲学特别重视其中作为实践价值基础的含义,如“事亲”中的“诚孝的心”,因为对他而言,“孝”的价值观念作为实践对象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孝”的动机是不是“诚”的,是不是发源于对父母的“深爱”,只有“深爱”做动力根据才是“诚孝”的道德动机,才会实现“孝”的价值。但是,他为了达到与保持道德动机的真实性,把道德实践的重心放在主体内在的意念即价值观念上,从而一方面造成外在客观世界在其道德实践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朱子理论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成为一种极为边缘的因素,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了“物”的价值观念含义,并且成为其理论的核心含义与本质含义,在其“格物论”里甚至是唯一含义。可以说,“物”的含义重心向意念、动机即价值观念的转移是王阳明“格物论”的创新基础,也是其心学理论的标志性特征。此外,“物”的观念含义不仅仅指价值含义,而且还指其它类型的观念含义。《传习录》下:
后有人问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诚无物’,程子曰:‘物来顺应’,又如‘物各付物’、‘胸中无物’之类,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18)
此中的“物”字都不是指单纯的外在事物,而是指“意之所在便是物”的意识对象,其所意指的意识对象既有外在的人情事变、声色名利等实在事物也有内在的意念、想法、知识等观念事物,所以“意之所在便是物”的观点不仅使“物”的存在内在化、意识化而且使“物”的含义扩大到可以意指一切意识对象,即凡是可以对象化的事物都属于“物”的范围;这是从“意之所在便是物”的角度对“物”的含义的形式规定,其内容可囊括上述所有含义。
三、物的两种含义类型
为了厘清“物”的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在王阳明道德实践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接下来还需要辨析两个问题:一是实践客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即牟宗三所说“行为物”与“知识物”的关系;(19)二是存在与价值的关系。(20)
前面已经提到,认识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属于实践的行为,具备实践活动的所有要素。比如,读书的求知明理行为,其行为的内在动力是对知识与道理的欲求,其主观动机是获得知识与明白道理,其主客观条件是已有的知识和书籍、光亮及安静的环境,其成果是知识与道理的增长与深入,因此实现了读书的目的。另一方面,所有的实践行为都以已有的知识为主观条件,都同时伴随有对实践自身及其它一些相关事物的认识活动为手段。比如,在“事亲”行为中,王阳明谈到关于温清的道理。《传习录》上:
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的条件。(21)
只要有了“诚于孝亲的心”这个道德实践动机与目的,那么人们自然会去思量父母的寒热,自然会去求取关于温清的道理。求取温清的道理是认识行为,其目的是实现温清道理的知识价值,这个目的的实现即获得温清道理又是实践温清行为的主观知识条件,而温清行为的实践正是具体的“事亲”行为,“孝”的目的就在这些具体的温清行为过程中得到实现,因此认识温清道理的行为是“孝亲”行为的手段,温清道理的知识是“孝亲”行为的条件。牟宗三将“事亲”实践中的认识行为区分为两种,一是:“依阳明,‘事亲’为一物,实即一行为。在此‘行为物’中,必有‘亲’一个物为其中之一员。‘事亲’这个行为物,必带着‘亲’这个知识物。……知亲固是一种知识,而要去知亲,则亦表示是一种行为。这行为就是成就知识或使吾获得知识的行为”;二是:“即在成就‘事亲’这件行为中,同时亦必有致良知而决定去成就‘知事亲’这件知识行为。即‘事亲’固为一行为物,而同时亦为一‘知识物’”。他总结道:“是以每一致良知行为中不但有一副套之致良知行为而去了别知识物,且每一致良知行为自身即可转化为一知识物因而发出一致良知之行为而去指导这个知识物。”(22)前者是对实践客观条件的认识,后者是对行为自身的认识,也就是第一个含义中提到的以实践行为自身为对象的认识。这个区分并不局限在致良知的道德实践领域,也适用于所有实践领域。因此,实践客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实践客体是认识客体的一部分,因为举凡山川草木、人伦日用、善恶美丑、念虑臆想之一切“意之所在”的对象都是认识客体,而认识客体又以知识内容的形式作为实践的主观条件作用于实践客体。
在“物”的含义中,行为物本身是一个较为空泛的概念,其实际内容表现为其它三个含义:实践对象、实践基础、实践条件。实践对象是价值观念,实践基础是价值实在,它们都属于价值范畴,而实践条件是包括外在物体、内在心理以及社会现象在内的客观实在,属于存在范畴,也就是说,“物”的含义可以分为存在和价值两类含义范畴,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存在和价值的关系问题。
在朱子那里,物的存在由理与气两个元素构成,因而物也就具有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23)
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24)
又说:
性之为善者无害气质之有不善,气质之不善者终亦不能乱性之必为善也。(25)
按朱子的说法,天地之性是形而上的本体之性,是至善无恶的理,气质之性是形而下的物性,是有善有恶的理气之杂,其中的善来源于理,恶来源于气,即气质之善性是本体之善的体现,也就是说,气质之性包含本体之性在内并成为现实的物性。(26)若从本体上看,物的存在依赖于本体之性,因为有体才会有用;若从气质上看,气质之性依赖于物的存在,因为有物才会有物之性。物是存在范畴,善恶是价值范畴,因此从本体之性角度说,存在奠基于价值,从气质之性的角度说,价值奠基于存在,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存在和价值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共在。这就表明,世界只是一个存在世界,价值或是内在于存在或是依附于存在,既不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也不属于“物”意义上的存在范畴。因此,他的“即物穷理”的格物论就是即万物之存在以穷究本体的至善之理,而不能离开物的存在去穷理,其中自然含有即外在自然物的穷理。
王阳明早年按朱子的“即物穷理”方法格亭前竹子得疾不果后,直到三十七岁“龙场之悟”时才悟到朱子格物论的问题所在,即价值与存在的依存关系。《传习录》下: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成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中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27)
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28)
《传习录》上:
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29)
“龙场之悟”使王阳明认识到,至善之理乃是内在的心之本体,不能被外在化为依存于事物的理,更不能混同于事物之理,朱子格物论的问题症结在于:他混淆了性理与物理的界限,视它们为在本质上同一的事事物物的所以然与所当然,即价值之理就等于事物之理,两者都依存于事物的存在。因此,王阳明认为,即使格得如草木之类的事物之理也与至善之理没什么关系,价值之理与事物之理不同,并不依存于事物的存在,所以应当将价值从事物的存在中分离并独立出来。虽然后来王阳明还是一直从理的角度理解价值,如“孝之理”、“忠之理”等等,但“孝之理”、“忠之理”的价值之理依存于“孝”、“忠”的价值实在,如果从“意之所在便是物”的角度看,仁义礼智、善恶美丑之类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实在都可以成为意识的对象,并且都具有或以感性因素为基础,因此都可以属于“物”的范畴。这样,“物”就有了两个类型的含义:存在含义和价值含义。“物”的存在含义和价值含义也可以称之为存在物和价值物,或存在世界和价值世界,它们共同构成了人类的生存世界。可以说,价值与存在的关系从依存到并存的改变是王阳明哲学革命的重要理论根据,在哲学史上的意义十分重大。
价值与存在的依存与并存的问题同样也是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柏拉图的“分有说”认为“善”是最高的理念,被每个事物所分有,它就像朱子的“天地之性”一样内在于事物并规定着事物,也就是说,事物依存于价值,价值为存在奠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认为,每个事物都有目的因,而“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30),由于他反对目的因可以脱离具体事物,并认为“恶”来自事物自身,所以,就像朱子的“气质之性”依存于事物一样,价值依存于或奠基于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价值与存在依存关系的观点一直是主宰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想,直到在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理论里仍然如此。胡塞尔说:“在真正意义上,只有客观化的行为才是针对对象,针对存在物或不存在物的,而评价行为则针对价值,更进一步说,是针对肯定的或否定的价值。当然,事情有两面,或二者本质上消融在行为中:价值有它的对象的一面,同时也有它特殊的价值的一面,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如果价值本身成了判断知识的对象,那么价值一面本身就被客观化了、具体化了。”(31)胡塞尔认为,客观化行为针对的对象是评价行为针对的价值的基础,即使仅在评价行为中,价值既有对象的一面,也有价值的一面,前者仍然是后者的基础,而且后者也可以成为客观的认识对象,但它的客观性依赖于前者的客观性。可见,价值以存在物为基础、奠基于存在。
在同为现象学家的舍勒那里,在他根据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建立的感受现象学和价值论的伦理学中,价值与存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从依存关系转变为并存关系,价值获得了相对于存在的独立性。首先,舍勒将价值从存在物中独立出来:“我也可以原则上接触到像适意的、诱人的、可亲的,还有友好的、雅致的、高贵的这样一些价值,同时却并不将它们想象为事物或人的特性”(32),价值不是存在物的特性,而是一个独立于存在物的领域。其次,舍勒认为,在生活中,对象的价值先于对象的存在被把握:“可以说,对象的价值走在对象前面;价值是对象自己的特殊本性的第一‘信使’。当对象本身还是含糊不清时,对象的价值就已经可以是清楚明白的了”(33),这一点与王阳明以实践客体涵摄事物、以价值客体优先于存在客体的思想是一致的。最后,舍勒将价值物与存在物并列起来:“善业(价值物)与事物具有同样的原初的被给予性”(34),两者都是原初性的,没有谁依存于谁的奠基关系问题,因此,“世界原初就是一个善业,就像它是一个‘事物’一样”(35),即:世界既是一个存在物的世界也是一个价值物的世界。
注释: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18页。
②“五蕴”之“色、受、想、行、识”,“五位百法”之“色法十一、心法八、心所法五十一、不相应法二十四、无为法六”与“心、意、知、物”都是以心物关系为基本结构的理论。
③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页。
④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90-91页。
⑤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47页。
⑥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972页。
⑦朱熹:《大学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页。
⑧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3、372、188、193、247、193页。
⑨朱熹:《朱子全书》第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27-528页。
⑩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4、228页。
(11)如:朱子说“欲致其知者,须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这个道理是如何,又推之于身,又推之于物,只管一层展开一层,又见得许多道理”(《朱子四书语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0页),心、身、物的关系是平行的,要分别去穷它们的理。
(12)王守仁:《王阳明全集》,1992年,第4页。
(13)实践对象指实践的目的,实践客体指除实践主体外的一切客观存在,后者包含前者;与实践不同,认识对象一般就是认识客体,都是指认识主体指向的客观对象。
(14)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译注者序,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x-vii页。
(15)熊十力:《佛家名相通释》,上海: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16)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2页。
(17)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3页。
(1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91页。
(19)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4、178页。
(20)价值也是一种存在,因此存在范畴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广义的存在包含价值,狭义的存在不包含价值。
(2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3页。
(22)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第178-179页。
(23)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55页。
(24)朱熹:《朱子全书》第二十三册,第2688页。
(25)朱熹:《朱子全书》第六册,第982页。
(26)参见陈来:《朱熹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41-146页。
(27)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20页。
(2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19页。
(29)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2页。
(30)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3-4页。
(31)胡塞尔:《伦理学与价值论的基本问题》,艾四林、安仕侗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32)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粱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2页。
(33)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粱康译,第19页。
(34)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粱康译,第23页。
(35)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倪粱康译,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