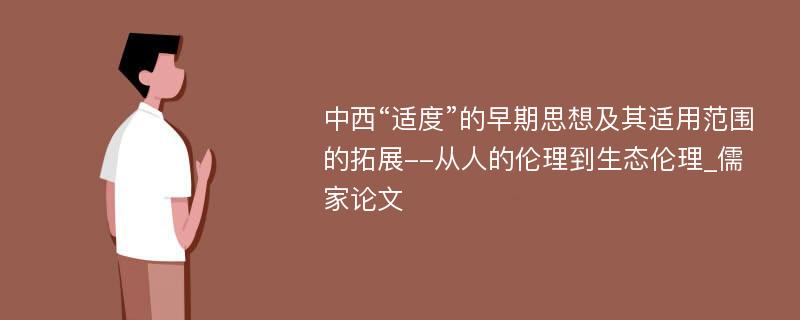
中西早期的“适度”思想及适用范围的扩展——从人间伦理到生态伦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适用范围论文,中西论文,生态论文,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相互遥远的中西方的早期,或者说在雅斯贝斯所称的“轴心时代”,先哲们不约而同地都提出了以“中”为中心的高度近似的“适中”、“适度”的德性伦理,为我们提供了不同文明之间具有可公度甚至是心同理同的适切例子。
我们先从文化翻译的侧面看一下中西译介“中庸”的简要情况。亚里士多德加以系统发挥的作为其伦理学关键词的“中”(mean)观念,中文一般译为“中庸”和“中道”。出自严复之、孙严群之手并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都是用“中庸”来翻译和理解亚里士多德的“mean”的;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周辅成先生主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90年代出版的苗力田先生翻译的《尼各马科伦理学》,则都采用了“中道”的译名。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中道”虽然没有“中庸”影响大,但二者在意义上的接近使二者的互换成为可能,这就使用“中庸”和“中道”翻译和理解亚里士多德的“中”观念,都具有正当性并各具特色。但是,在把中文的“中庸”译成英文时,问题就似乎复杂了。辜鸿铭曾译为“central harmony”,即“中心的和谐”,与此不同,詹姆斯·莱格译为“docrine of mean”,E.R.休斯译为“mean-in-action”。由于休斯类似于辜鸿铭把“中”也理解为“central”,因此他的译语的意思就成为“生活中功能的中心”。此外,埃兹拉·庞德则译为“持守中道”和“永不晃动的枢纽”。(注:有关这一点请参阅杜维明的《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见《杜维明文集》第三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388—391页。)
以上译法的微妙差异,集中在“中间”和“中心”之异。照许慎的解释,“中”的本义是“内”,它与外相对。与这种位置和空间意义上的“中”相关,“中”还有“中间”的意思。现代汉语所使用的“中”,一是指一个范围的内部;二是指与四周的距离相等。与“中”的意思相联系,“中间”的主要意思,一是指内,二是指中心,三是指事物两端之间或事物之间的位置。“中心”一是指与四周距离相等的位置;二是指事物的主要部分和主导性因素。由于在“中间”的意思中包括有“中心”的意思,所以用“中心”去理解“中间”并非空穴来风。但把“中间性”转换成“中心性”(central),整体上就偏离了“中庸”之“中”即“事物两端之间”或“事物之间”的基本意义。“中庸”更深层次的意义,恰恰也是从这一基本意义引申出来的。因此,把“中庸”或“中道”的“中”,译成“中心”则不够恰当。
对照中西的“中道观”和“适度”思想,以下几个方面是可以明确指认和强调的。一是双方都有一个启示性的源头,它肇始和铺垫了未来。希腊诗人潘季里特(公元前6世纪)在一首祈祷诗中说出了中道和适度的经典性名言:“无过不及,庸言致祥。生息斯邦,乐此中行。”毕达哥斯认为“中庸”是一切事情的最佳境界,他在《金言》中所说的一句金言就是“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梭伦在肯定“自由”和“强迫”的正当性时,对之所加的限制是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德谟克里特意识到两个极端和过度,都不是有益的选择(“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不定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愉快的”;“当人过度时,最适意的东西也变成了最不适意的东西”)。由此来看古希腊人有“凡事不要过度”的名言和亚里士多德何以推重和广演“中道”和“适度”,就不难理解了。在中国,中道和适度的思想也有很早的起源。《尚书·洪范》有“皇极”,传统释“皇”为“太”和“大”;释“极”为“中”,“皇极”就意味着“大中”之道。《正义》说:“施政教,治下民,当使大得其中,无有邪僻”;“凡行不迂僻则谓之中”。《洪范》更有“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的名言。《正义》亦从“中道”加以理解,说此句是“更言大中之体”、“若其行必得中,则天下归其中矣”。即使是《洪范》篇有后来甚至是春秋战国时代加入的内容,但由于《左传》襄公三年有引用《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之文字,故可证其来久远。《尚书·大禹谟》有“允执厥中”,这里的“中”所讲的就是“中道”。《大禹谟》被认为是伪《古文尚书》部分,接受这种判断,“执中”的思想自然就要往后推。但有趣的是,《论语·尧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把这句话与《大禹谟》所说的“天之历数在汝躬”和“允执厥中”相比,所看到的类似值得玩味。即使说《大禹谟》是晚出,但《论语》所记载的“执中”的思想恐怕也有很早的起源。
二是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儒家都以“中间”或“中”为根本来建立自己的“中道观”和“适度”思想。“中间”或“中”原是表示具体可指的空间及东西所处的位置。“中间”或“中”要通过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它一开始就与量度分不开。 “中道观”和“适度”把这种具体的“中间”和“中”转化为衡量和判断人处事待物是否合理和正当的抽象尺度和原则。符合“中间”或“中”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和不正当的。不符合“中间”或“中”,又以与之相对立的“两极”(或两端)而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极”的“过度”,一是另“一极”的“不及”。“中间”或“中”与“两极”彼此互为前提,三者构成了处事待物的三种方式,其中的“中”是最好的,而作为过度和不及虽然彼此也相反,但都是不好的。这是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如他这样说:“凡行为共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过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是德性,即遵守中道。三者互相反对。其间,两过恶是两极端,它们彼此相反,但它们又都和中道的或适度的倾向相反。”(注: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1、297页。)同样,这也是孔子儒家所主张的,如孔子称赞舜时说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两端”和“中”就构成了三种不同的方式。又如孔子评价子张和子夏,说他们一个是“过”,一个是“不及”,“过”如同“不及”都不理想,只有“不过”又“及”的“中”才是理想的。再如孔子所说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其中的“中行”是最好的,而作为两极的“狂”和“狷”都失之于偏。一般来说,在二元对立的价值结构中,善恶、好坏、美丑等这些截然相反的两极,虽然它们有程度上的“比较级”,如比较好、比较坏,是处在善恶之间,但它们却不是相对于两极的“中间”。在二元结构中,其中的一元是最好的,越朝向这一元则越接近于理想,但在三元结构中,“中间”则是最好的状态,越接近“中间”则越理想。中西“适度”思想正是不约而同地建立在三元对立结构中。
三是亚氏和孔子儒家从与两极相对的“执中”中,更进一步走向了一般性的“适度”和“适当”的观念,这也正是一般所说的“恰到好处”、“恰如其分”的意思,如宋玉描写的美人,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就是说不高不低、不瘦不胖,达到了一种最美的境界。亚里士多德说:“若是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于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亦即最好的中道。”(注: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01、297页。)这里所说的“中道”,强调的就是“适当”,它不再拘泥于往往带有一定机械性的“中间”,而是在时空等多重关系中达到了“正好”的境界。亚氏谈论消闲和娱乐的中道说:“消闲和娱乐是一种交往,这里显然存在着过度、中道和不及。把玩笑开得太过分就变成为戏弄,而一点玩笑也不开的人实属呆板。对那些玩笑开得有分寸的人,这种中间品质称为圆通或机智。它所以为机智,因为有触景生情、见机行事的本领。……它所以为圆通,因为不论说什么、听什么都合乎分寸,都中人意。”(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5页。)合乎“分寸”,就是“适度”,就是不令人难堪,使人身心都感到愉悦。《中庸》说的“喜怒哀乐之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把“中”与“和”并列起来,“中”在这里是指人的自然情感在天然状态下的不偏不倚和适中,“和”是指自然情感在表现出来时都合乎“节度”,用朱熹的解释就是“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孔子注重“礼”的“和谐”(“和为贵”)和恰当,反对教条化的一味讲究形式和格式,强调君子对于天下的事务如何去做,没有“具体的”一成不变行的规定,如何“适宜”和“适当”(“义”)就应该如何去做。《论语·里仁》载:“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是要求人们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来作出恰当的判断和安排。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还有孔子所说的“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这里所说的“时”和“可以”,也是强调“适时”和“可行”。史伯和晏婴以及孔子所说的“和而不同”、“质胜则文野,文胜则质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重点也在于主张不同因素的合理调和及互补,以求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朱熹也这样来解释“中道”:“所谓中道者,乃即事物自有个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答张敏夫》)与“适度”和“适当”相反的是一般所说的“过度”、“过分”、“极端”、“偏激”、“偏颇”等,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所谓“竭泽而鱼”,所谓“贪得无厌”、“得寸进尺”等,都超过了应有的限度。据此,作为从“中间”或“中道”状态衍化出来的“适度”和“适当”,反而也有了一个相反的对立面即“过度”和“过分”。“过度”的“度”和“过分”的“分”,就是肯定有一个恰当或恰好的限度和分际,越过了就是“过”。如“过火”,就是没有掌握好恰当的火候。《老子》二十九章讲“夫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认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主张“去甚,去奢,去泰”,孟子讲“仲尼不为已甚者”,这里的“甚”,都是指“过度”和“过分”。在此,“中道”已经不限于一种三元结构中,它可以是多种因素和条件之下达到的和谐、平衡和恰到好处的“适度”。
四是亚氏和孔子儒家的中道观,都有比较宽泛的适用范围,但中心则是指人的德性和品质。正如人们所知的那样,亚氏的中道观也是一种政治观。按照这种政治观,最好的政体只有以能够“顺从理性的指导”的“中产阶级”为中心才能组织起来,因为处在极富和太贫两个极端的阶级都不能“顺从理性的指导”。但亚氏“中道观”所说的那些合乎中道的东西,主要还是指伦理和道德方面:“事物有过度、不及和中间。德性的本性就是恰得中间。德性作为相对于我们的中间性、中道,是一种决定着对行为和情感的选择的品质,受到理性的规定。并非全部行为和情感都可能有个中间性。德性就是中道,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正确。”(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第32页。)如勇敢、节制、乐施、慷慨、温厚、公道、荣誉、大方等,在亚氏那里,都是合乎中道的美德和善良的品质。孔子儒家的中道观,所指涉的范围当然也不限于伦理道德,它也是为政的原则和处事的合理方式,但主要是一种德性,正如孔子所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道”作为一种“德性”,在亚氏那里,是后天修养的结果,而不是人的先天自然本性:“人们自然具有的是接受德性的能力,先以潜能的形式被随身携带,后以现实活动的方式被展示出来”。(注: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第25页。)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这里的“性”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先天的善良本性,它与亚氏所说的潜能(或潜在的“才质”)类似,这种才质提供了为善的可能,但它并不等于现实的“善”;“习相远”也与亚氏所说的后天的习惯和实践类似。
整体上说,亚氏和孔子儒家以“中道”为核心的“适度”思想,是人间伦理,是主要适应于社会生活而被阐发的,但现在我们应该扩展它的应用范围,把它推广到生态伦理之中。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强烈地意识到了资源枯竭、生态失衡和环境破坏等严重危机。一般认为西方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之上的“主客”二分和分裂,是造成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科学和知识一方面增加了我们控制和驾驭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相信自然就像是自己手中的玩物那样可以任意摆布。人类在从自然中获得巨大力量的同时,也把自己潜伏的无限欲望刺激了起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欲望,也就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进步和发展被作为头等大事来谋划,经济的速度和效率被作为根本目标来追求,获得利润、利益和财富是最大的动力,这不仅是合理和正当的,而且通过科学的力量也是可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能让环境轻松,让生态复苏,让大地安静。我们居住的地球空间没有丝毫加大,但我们让地球变化的时间大大加速了。我们强迫稳定的环境空间跟得上飞速的时间之轮,就像我们不停地敲击仿佛是静态的乌龟,要它赶上永不睡觉的兔子那样。可以肯定,人类对自然和生态采取的无限制的开发甚至是掠夺性行动,远远超过了自然和生态所能承受的程度,自然和生态已经用它们的方式在回敬人类的霸权行为。
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西方在“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之一,就是建立起了“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中国的学者们也加入到了“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的讨论之中。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开始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生态”及“环境”思想和智慧。人们强烈地意识到不能再蛮横和粗暴地对待“自然”和处置“自然”,需要“尊重自然”,需要尊重自然的“权利”,需要承担起对“自然”的“义务”。这就把“权利”和“义务”这种原本属于人类社会的观念扩展到了“自然”之中,“自然”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客体,它同时也获得了主体的意义。
有人认为,人类对环境和生态的尊重和保护,说到底仍然是人类出于自身的安全和生存考虑,“自然”最终也仍是我们功利性和手段性意义上的对象。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从人类的立场出发,保护和尊重“自然”,当然也是尊重和保护人类自身;但从自然的立场出发,尊重自然确实就是尊重自然,就是肯定自然的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目的”。人类不能只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就像个人不能总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一样。
有一些观念也需要改变。如,经过达尔文的动物世界的“生存竞争”再到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竞争”,“竞争”的思想和价值观,对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影响是非常大的。它不仅使人与人之间具有了强烈的竞争感,而且也使人与自然变成了一种生存竞争关系。现在我们需要从“生存竞争”的观念中走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及“合一”,与自然“共生”、“共存”。再如,世俗化之下的“消费文化”,以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大量开发和使用为条件,但存在于“自然”中的资源和能源却不是无限的。我们的“消费文化”如果继续要求无限的消费,自然最终将倾家荡产,人类也将无以生存。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种与自然的可承受性相适应的合理和健康的“消费观念”。要求有限消费实际上就是要求节制人类的无限欲望。这不是主张对人的生理“自然”进行压制,而是反对“放纵”人的生理自然。现在我们往往注意的是人与外部自然和生态的关系,而忽视了人与自身生理性“自然”的关系。
问题集中在如何调节我们的自然欲望,如何建立合理的消费观念,说到底即如何化解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如何使人类与自然共生共存。我们需要引入新的观念,“适度”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近代以来人类对自然的行动往往表现为不知收敛的“过度”和“过分”,那么克服过度和过分行为的最恰当方式就是“中道”和“适度”。因为对自然的“过度”和“过分”行为,显然不能用另一个极端即“不及”和“不足”所代替,否则人类的基本生活条件和需求,就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和满足。现代文明对自然类似于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式的掠夺,迫切需要我们把“适度”的人间伦理扩展为生态伦理。根据“适度”生态伦理,人类要节制对自然的过度开发行为,使自然本身得到休养生息;人类的消费观念应该从高消费走向“适度消费”,人类的自然欲望满足,应该从纵欲走向“适欲”。可以相信,“中道”(或“中庸”)和“适度”对于人类处理与生态和环境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适用的。
总之,如果我们不想继续受到自然和生态的报应,我们就必须承担起对自然和生态的义务,对我们的行为有所节制,“适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人类如果能够以“适度”的美德对待自然,那么他就能够维持自然及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平衡,自然和生态也能够承受起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