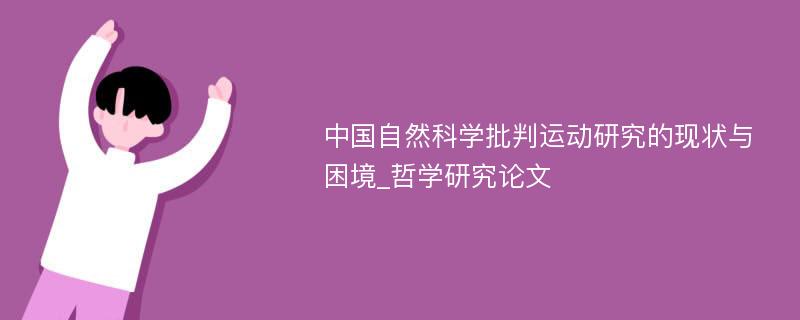
中国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研究的现状和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自然科学论文,困境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1)01—0040—06
1949年春天,华北大学农学院乐天宇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米丘林学会”,并在其出版的《农讯月刊》上公开号召“把米丘林的成果稳步地移植到新中国的大地上来。把魏斯曼、孟德尔、摩尔根的陈旧的反动东西埋葬到历史的坟墓中去”,由此拉开了中国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序幕。到粉碎“四人帮”前后,批判运动持续了近30年之久。同时,对这种批判运动的研究前后却持续了近50年。但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热潮。而且,不利于中国当代科技史、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全面研究。因此,认真总结半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研究的状况,找出所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境,对于进一步推动这个领域的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状
对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研究,以“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为分水岭,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1976年)
50年代初期,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一书出版,明确认为语言学不是上层建筑,不具有阶级性,由此引起了对自然科学特点的讨论。根据斯大林对上层建筑的定义,苏联理论界提出自然科学本身不属于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随着斯大林的去世,苏联开始重新评价和纠正过去在自然科学领域进行的各种批判。这些论文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引起了国内理论界和科学界的关注。当时,《健康报》、《人民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文章,从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立论,分析批评了“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和米丘林学说是社会主义的”、“摩尔根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等错误观点。这是自然科学批判运动开展以来发表的首批学术性的论文,标志着对这场运动研究的开端。
对学术与政治、自然科学与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理论本身是否有阶级性问题比较集中的研究则是始于1956年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问题座谈会。于光远在会上的两篇发言明确指出,“学术上自由,政治上也是自由的”、“‘百家争鸣’就是扩大自由”[1](第228页)、“哲学不应该站在自然科学之上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1](第242页),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会后不久,黄青禾、黄舜娥、陈英在《人民日报》、《农业科学通讯》先后发表了对这次会议中各种争论的全面述评。龚育之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一文认为,要注意防止在正确地批判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错误地否定真正的自然科学事实和理论,以及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不久,龚育之又撰文指出,哲学的任务,主要不是去堵塞和限制自然科学的道路,而是为自然科学问题的解决从思想上去开辟更多更宽广的道路。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初步阐述。此外,许良英、范岱年在《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中,强调了在学术争论中“一切要以事实为根据,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思想。这些论述在当时格外引人注目。对青岛会议召开起过重要作用的是黄青禾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1935~1956年苏联生物学界的三次论争》。这篇调查报告相当深入地论述了苏联生物学界两派之争的基本状况。在当时,是国内外同类资料中编写较早的一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针对50年代末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反右倾中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做法,60年代初,随着中共中央批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的试行以及其他领域政策调整的展开。一方面,对这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偏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纠正;另一方面,学术界纷纷发表文章,对自然科学批判运动开展以来产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如李宝恒和胡文耕在《哲学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与“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论文,比较深入地探讨了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对“代替论”进行了批评。龚育之《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一书,对自然科学与政治、自然科学与生产、自然科学与群众以及自然科学与哲学这四个方面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此期间,还有不少自然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自然科学与世界观》一文中,龚育之论证说,“对歪曲自然科学成果作出的哲学结论,同自然科学成果本身,必须加以区别。既不能因为机械论的世界观是以对牛顿力学的绝对化理解为基础,而否定牛顿力学的价值;也不能因为许多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歪曲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成果,作出不少唯心主义哲学的结论,甚至宗教结论,而否定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巨大成就。”并且明确指出,“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尤其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驾凌于自然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不是用固定的思想框框去束缚和限制自然科学的僵死的东西”[2](第134— 137页)。这些真知灼见不但在当时,即使现在看来也是相当深刻、振聋发聩的。有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在“科学十四条”的试行过程中,龚育之搜集并编译了九辑《关于苏联自然科学领域的思想斗争的若干历史资料》,对苏联建国以来如何处理哲学和科学、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比较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此外,哲学研究所会同上海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大量人力编辑了《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领域思想动向的历史资料(1953—1963)》、《全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会议文集》、《控制论哲学问题选辑》、《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等8辑内部资料, 为深入研究作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和历史借鉴。1966年以后,由于“文革”纲领“十六条”中提出了包括“自然科学理论战线”在内的“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观点”进行彻底批判的任务,因而此前发表的关于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和关于“百家争鸣”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均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观点”和“反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除了对相对论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重点批判外,批判范围日益扩大到了其他科学研究领域,如宇宙学、量子力学、极限论、基因论、信息论、人工智能、环境危机论等。通过查阅当时的文献可以看出,除了少数自然科学家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内进行了小心翼翼就事论事的论述之外,没有一篇从科学本身之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理论文章。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作是编译和整理了一些相关资料。如《外国自然科学哲学摘译》、《数学手稿》、《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思想体系的对话》、《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生命是什么》、《爱因斯坦文集》以及马、恩、列、斯、毛语录集《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等。
总的说来,由于受政治斗争需要的影响,这一时期的研究,尽管有许多资料和文献作基础,但在方法上却局限于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甚至革命领袖的有关语录来诠释和论证学术与政治、自然科学与哲学以及自然科学本身是否有阶级性等基本问题。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理论深度也不够。龚育之曾经对这一阶段的研究作过严肃的反思:“由于许多事情是亲历过或调查过,在提供材料方面可能还算较为充分和准确,在判断的正确程度和概括的理论深度方面,那是很不够的”[3](第348页)。
第二阶段(1976年以后)
“文革”结束后一两年,发表了大量揭批“四人帮”破坏自然科学的文章,但无论是公开见于报刊的还是内部资料,都带有感情色彩,理论认识比较欠缺,基本倾向是政治大于学术,宣传重于研究,有些甚至带有“革命大批判”的语言,离学术研究的要求尚有一定距离。如《化学通报》1977年第6 期发表的《“四人帮”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就很有代表性。但总的说来,学术界已经开始解放思想,在理论上、方法上和研究内容上逐渐拓宽了视野,有了一定的突破。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之后的20年,情况的变化很大,取得了不少成绩,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发表了许多论文。如《科技日报》1986年开辟《为了忘却的回顾》专栏,先后发表了唐有祺等的《“双百方针”与批判共振论》等15篇文章。经统计,《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的有关论文共计41篇,有些是比较有价值的。如屈儆诚、许良英的《关于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运动的初步考察》一文,从社会历史背景、批判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具体过程、特点以及对这场批判运动对整个科技界和思想界产生的影响做了实证性的考察。李佩珊等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经验》一文首次把对苏联国内遗传学批判有关情况作了叙述,以及这场争论在中国的经历。刘兵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上的《文革中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一文,对该刊所发表的各类文章分别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说明了文革期间科学被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严重程度。顾昕的《文化价值与科学》一文首次以西方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探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与科学精神气质的背离是造成“文革”期间科学蒙难的根本原因,是一篇角度新颖的文章。此外,一些人物评传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如刘克选、胡升华的《叶企荪的贡献与悲剧》一文,对物理学家叶企荪的生平、活动和学术思想进行了详细考察,揭示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无所适从的悲剧人格。
2.整理和公布了部分资料。也许这是到目前为止最有价值的工作。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周林等编写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首次汇印了一大批重要的历史文献和回忆材料。李佩珊等编写的《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汇集了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全部发言记录,并附有包括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记录在内的许多历史材料。将这两次会议记录放在一起,对比较研究具有重要作用。龚育之、柳树滋主编的《历史的足迹》一书,对苏联20年代以来在自然科学各领域开展批判运动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搜集、编译和整理。它既是一部有关苏联自然科学领域哲学争论的历史资料,也是一部反映中国过去对苏联这方面历史研究情况的历史资料,比较全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任元彪等编写的《遗传学与百家争鸣》是对当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参加者及有关人员的追踪调查。他们中有中国遗传学会历届理事长、副理事长和大部分理事,有两派之争中公认的代表性人物。其观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遗传学界、生物学界对两派之争和有关问题的各种看法,是一部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该书收录孙小礼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及在哲学领域所开展的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为背景,论述了苏联40年代对整个自然科学领域进行大批判的全貌。此外,还有柳树滋编译自苏联1990年《自然》杂志的“准备已久突然停开的全苏物理学家会议”,首次披露了多年来未曾公开的秘密。在资料整理方面有较大影响的工作还有严博非编的《中国当代科学思潮》一书,收录了1950年至1991年国内主要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共102篇, 展现了中国当代科学思潮的基本流向,收录比较全面,有一定的代表性。
3.召开了几次有一定影响的研讨会和纪念会。1978年,龚育之在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上,作了题为《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历史情况和经验》的长篇报告,系统地回顾和评价了自然科学批判运动在苏联和中国的历史。应该说,这是“文革”结束后第一篇有思想深度的学术论文[16]。1981年召开的“应该由谁评定科技成果与人才”研讨会探讨了科研成果和人才的评价应该坚持科学自身的标准而不应该使用政治标准和哲学标准的问题。1986年,《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中国遗传学会先后在北京召开了“贯彻‘双百方针’,促进学术繁荣”研讨会和“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暨‘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纪念会”,不但对历史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对学术与政治、科学和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些直接对话和交流,推进和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4.一些学术专著、论文集、机构史、学科史、回忆录、人物传记等作品中也融进了相关的研究。如龚育之的《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科学·哲学·社会》,赵红州的《政治科学现象》,樊洪业的《科学业绩的辩伪》,陈建新等的《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钱临照、谷羽的《中国科学院》,路甬祥的《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李佩珊、许良英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第二版),许良英、方励之主编的《爱因斯坦研究》,于光远主编的《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黄顺基、周济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等等。这些相关研究,拓宽了视野,活跃了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困境
几十年来,国内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国史和党史研究中其他领域相比差距较大,面临着许多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料欠缺。目前所依据的一些资料,绝大部分都曾是公开出版过的,内部资料比较欠缺。尤其是档案材料,所能看到的微乎其微。“大鸣大放”和“文革”期间的许多大、小字报、传单当时没有很好收藏,现在也没有进行广泛征集和整理。许多当事人和亲历者所知道的重要情况极少有人采访整理。尤其是参加这场运动的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如乐天宇这样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其去世前却也没有人对他进行采访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重要资料也将随之散失。因此,应尽快加强口述历史资料的抢救。最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接的“知识创新工程”中把“50~70年代自然科学批判运动资料整理”立了项,三年后将有成果面世。当然,在资料搜集和整理中,还应尽量避免错讹的问题。只有建立在坚实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才能保证研究成果不至于空洞无物。
2.理论深度不够。有关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成果尽管不少,但真正有学术见解,能够做出深入分析的理论成果不太多,甚至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成系统的理论专著。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存在着选题重复、资料陈旧、重述轻论、观点雷同的不足。如对历史不厌其烦的叙述,对资料人云亦云的罗列,而对深层的原因则缺乏深入的探讨。
3.视野狭窄。对于研究的对象,从涉及到的学科上看,主要局限在遗传学与相对论两个领域,对其他领域则少有关注;从地域上看,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从被研究的人物上看,主要限于上层的科学家、政府官员和中央领导人。而对各省、市、地、县以及底层科技人员、教育工作者有关情况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据笔者所知,除了工厂之外,这场运动实际上涉及到了全国许多乡村,一些偏远乡村的农技人员甚至成了“摩尔根分子”、小学民办教师也成了“爱因斯坦黑线”上的人物。随着“五·七”干校的开办,以及一批科技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被扫地出门、关进牛棚、遣送回乡,这场批判运动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乡村不断得到继续。如果不对这类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就难以看到自然科学批判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全貌,所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片面的和抽象的。没有研究的广度,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
4.方法陈旧。从公开发表的各种研究成果来看,几乎清一色采用的是传统史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实际上,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SSK)、现代历史学(如“格群分析”理论)、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解释学、符号语言学、现代政治学、科学哲学等学科中,都有比较成熟的方法可以借用。在海外,就有不少学者用知识社会学方法、符号语言学方法以及后现代主义语境方法等研究中国的“文革”。“历史即方法”,如果在方法上有了突破,那么国内的研究自会有另一番“百花齐放”的景象。
5.缺乏国际学术背景。在西方汉学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非常热门,尤其是对“文革”的研究硕果累累,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于中国的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美、日、英、法和瑞士的学者都有所研究,一些海外的中国学者和台湾岛内学者也做了相关工作。然而,国内至今仍然没有这方面的评介,更没有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不了解国际学术背景的研究,只能是闭门造车。因此,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海内外学术界的直接对话,将有利于弘扬学术研究的开放精神,使国内目前的研究跨上一个新台阶。
6.对某些事件和人物的客观评价问题。如,如何看待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作用?从公开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来看,几乎是千篇一律地认为,这是一次开得“相当成功的学术会议”,是一次“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宣言”,是一次“政治民主、学术自由”的盛会,起到了“伸张正义”的作用等等。然而,这次会议的效果究竟如何呢?随后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就作出了事实上的回答。所以有人认为,这次会议从根本上说算不上一次学术会议[4](第38—41页),甚至认为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引蛇出洞”[5](第740页)。此外,还有对“米丘林”学说的客观评价问题。 乐天宇以及当时运动中的一些“走红”人物,其后期思想与前期思想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作实证研究,过多地使用情绪化的语言、缺乏学术上的冷静和思辩,无疑将会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引向歧途。
7.思想禁区有待突破。目前,对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研究,学术界亟需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加强学术自主性。如时至1996年,任元彪等对几位科学家的采访录音未能被受访者允许公开发表;在1986年举行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暨‘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纪念会”上也有几个发言未被当事人允许公开发表;近几年,有些博士候选人试图以自然科学批判运动为主题做学位论文,但由于思想上顾虑重重,害怕拿不到学位而最终放弃。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学术界多年来形成的杯弓蛇影、作茧自缚的心态,但总还是让人隐约感到政治干预学术的不良后果。因此,坚持“双百方针”仍然任重道远。
8.对自然科学批判运动产生原因的分析过于简单化。这场运动历时近30年,其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技界和教育界。产生的原因必然是多方面的。与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环境、政治意识形态、东西方“热战”和“冷战”、技术霸权、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等都有着一定的关系,有着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的复杂根源。然而,国内的研究主要局限于苏联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政治与学术、自然科学与哲学等关系问题上。如此,将不可能有学术上的 真正突破。
9.研究人员结构不合理。从学圈上来看,几十年来,基本上是自然辩证法学圈内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而且以这场运动的亲身经历者居多。尽管他们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文献和资料,但由于许多人身处历史的漩涡中,甚至在运动中多次受到冲击,以及后来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在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各自的偏见,甚至情绪化的语言溢于言表。这些因素无形中制约了研究的客观性。
因此,应尽快打破自然辩证法这个小学圈,让其他学科的学者融入进来,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尤其重要的是要大力培养和扶持青年学者,让他们以历史审视者的身份,以全新的学术思想、学术风格和学术方法,更加客观冷静地对这场运动进行重新拷问。
收稿日期:2000—1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