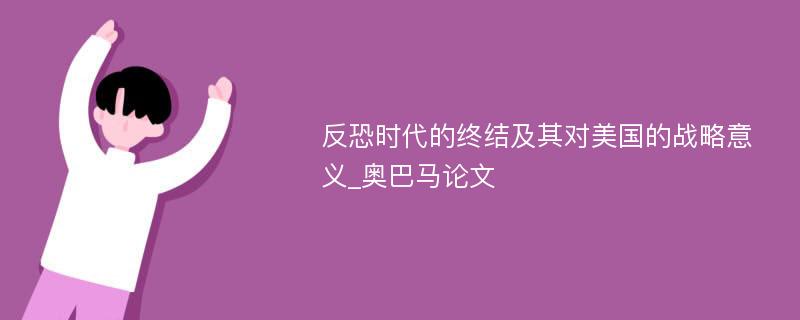
“反恐时代”的终结及其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反恐论文,战略意义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本·拉丹被击毙和美国全面启动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为标志,长达10年的“反恐时代”大体告一段落。在“9·11事件”十周年之际,评估过去10年美国的战略得失、展望未来10年美国的发展方向,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反恐时代”对美国的影响
2001年“9·11事件”的突发,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恐时代”。尽管“反恐”并非过去10年美国全球战略的唯一,但恐怖主义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全新挑战、美国应对恐怖主义所展开的全新布局,确实使美国的内政外交深深打上了反恐烙印,“反恐”也因此成为美国的战略优先和重中之重。以“反恐时代”界说过去10年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应当并不为过。
“反恐时代”对美国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它改变了美国的安全关切,使恐怖主义及与之相关的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首次上升为美国的头号威胁;它改变了美国的安全战略,使以单边主义为特征、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先发制人”正式成为国家大战略的核心;它改变了美国的政府结构,国土安全部、北方司令部、国家情报总监等新机构、新人事设置应运而生,开创了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它改变了美国人的社会心理乃至政治生态,曾经构成“美国精神”内核的乐观主义、自信心、包容力都在减弱,而不正常的焦虑感、脆弱感、不安全感却在上升,《美国爱国者法案》及《恐怖分子监视计划》等立法所引发的相对安全与绝对安全、自由与安全、安全与发展等矛盾成为美国人回避不了的重大议题;它也改变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布什以“反恐划线”,追求“黑白分明”,迫使他国按照美国的意志站队,虽得逞一时,但最终令世界寒心,使美国对世界的号召力、凝聚力下降,美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作风不得不有所收敛。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美国的国际地位。10年下来,遭遇“9·11”恐怖袭击和“9·15”金融海啸两度重创,美国虽仍为“一超”,但已难“独霸”。无论承认与否,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下滑是过去10年国际政治的最重大变化之一。
“9·11事件”是美国的重大悲剧,并极大消耗了美国国力,但过去10年美国凭借转危为机的超强能力及“反恐”提供的难得机遇,也因祸得福,获取了不菲的战略收益。通过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美不仅展示了军事实力、检验了新式武器、锻炼了作战队伍,而且历史性地挺进中亚,全方位地进入中东,其全球地缘掌控力得到大幅提升。通过领导“国际反恐联盟”,形成美国主导、大国协作、小国服从的国际政治新格局,一度令美国软硬实力同步增强。同时,顺势推进了拉姆斯菲尔德主导的“军事转型”,使超强军力更具后劲和可持续性;开启了赖斯策划的“外交转型”,在大国中率先进行外交机构、涉外人员、对外使命的全面变革,为美继续“领导世界”奠定了基础;并实践了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为特征的“布什主义”和将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外交高度融合在一起的“新布什主义”,不啻为新世纪美国如何谋霸进行了战略上的试验。
然而,凡此收益一度给人以错觉,使人们认为美国无所不能,世界开始进入单极独霸或“新罗马帝国时代”;更给布什政府以幻觉,使之以为美国可以为所欲为,借反恐谋求更大的战略目标。结果,布什政府未能正确把握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也未能正确回答“他们(恐怖分子)为什么恨我们”这个根本性问题,未能正确认识“国际反恐联盟”形成的真正原因,反而将大国联合反恐视为对美国的无条件支持,把阿富汗战争的速胜理解成美国在军事上的无所不能,并滥用美国民众的受害心理和爱国热情,断送了反恐前两年开创的大好局面,走上了超越反恐、出兵伊拉克、改造中东的不归路,最终自食其果。
回顾过去10年美国的“反恐”历程,从布什2002年《国情咨文》抛出“邪恶轴心”说,将伊拉克、伊朗、朝鲜并称为“邪恶轴心”开始,美国的反恐战争就已偏离航向;而伊拉克战争在未得到联合国授权、未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证据、未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情况下逆势发动,美国的“反恐”就实际上异化为“谋霸”,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
美先是将“反恐”同打击异己相结合,为此形成“恐怖分子—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庇护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邪恶轴心—暴政前哨”这样一个打击链条,结果越反越恐,把恐怖主义打成了网络,使恐怖袭击在全球蔓延。不仅如此,美国借反恐谋霸还激起朝鲜、伊朗两个美国定性的“邪恶轴心”不得不考虑以发展核武寻求自保,造成全球核武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化趋势难以阻遏。
美将“反恐”同地缘战略相结合同样产生了负面效果。阿富汗战争的结果是美军历史性地进驻中亚,从而挺进到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伊拉克战争的结果,则是美国在中东落脚扎根。紧接着,布什政府一面抛出所谓“大中东计划”,准备以伊拉克为中心、以色列为依托实施历史性地改造中东政治版图的宏伟计划,一面则炮制所谓“大中亚计划”,准备以阿富汗为桥梁,将中亚、南亚连接成一片,打造所谓稳定的能源通道。结合冷战后美国地缘战略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既定轨迹,美国在通过科索沃战争搞定欧洲后,显然致力于战略东移,企望乘势将中东、中亚也牢牢控制住。中亚“颜色革命”的渐次发生、美俄新冷战的悄然上演、伊朗核危机的全面升级,主要就是美国这一战略催生的结果。
“反恐”异化的第三部曲,则是将“反恐”同“文明冲突”相结合。布什一再声称美国无意同伊斯兰世界发生“文明的冲突”,但他将反恐提升到反击极端伊斯兰主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新高度,无异于“此地无银”,因为极端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之间以及所谓的“新型意识形态战争”同“文明的冲突”之间很难划出明确的界限。
回过头看,“反恐”的异化对世界不是福音,对美国也是得不偿失。首先,上述收益与其说是美国的胜利,不如说是代表新保守主义、传统军工能源集团、进攻性现实主义精英等少数利益集团的胜利。他们的胜利没有赢得满堂喝彩,却导致美国的“分裂”,埋下政治和社会“极化”的祸根。这一后遗症至今仍在发酵。其次,美国的硬实力虽得到部分发泄,但元气大伤,软实力则全面受损。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式自由民主的可信度、美国领导各类联盟的能力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其后果是,美国通过所谓“文化霸权”、“柔性霸权”、“仁慈霸权”继续保持“一超”地位的效能大打折扣。从长远看,这恐怕是对美国强权的最大伤害。最后,伊拉克战争的轻启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沉重负担、给中东局势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给美国全球战略带来的重大失衡,至今仍未得到解决,远非一个“走”字了得。
而从更长的历史视野评估过去10年,对美国而言,最深刻的教训还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延滞了美早应开启的体制性变革,致使各种问题积重难返,造成今日美国“发展方向之困”;二是断送了美重塑国际政治新局的大好时机,使“无极世界”异常混沌,美国自身也深受其累。
先看体制性变革的延滞。周期性体制变革本是美国崛起并称霸的法宝①。冷战结束后,美国由“两极”之一而成“一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借助全球化浪潮走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身份与环境的变化本应促使美国与时俱进展开新一轮体制性变革,但遗憾的是这一变革终究未能展开。如果说克林顿主政时期因忙于享受“冷战红利”、沉醉于“新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而缺乏改革的动力,那么布什时期未能启动重大改革的根本原因则主要是忙于反恐和战略扩张。诚如布什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坦言,原本立志做一个“文教总统”的他却因“9·11事件”而阴差阳错地成为“战争总统”。②结果,其在一心有所作为的社会保障制度、移民制度、选举制度等深层改革方面几乎一无所成。于是乎,体制性弊端经年累积,终至引发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目前看来,本轮金融危机远非华尔街的危机,其背后反映出的金融泛滥、房产泡沫、虚拟经济等,实是一场波及整个经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危机,以致美国的发展出现方向性困惑。经济上,出口倍增、实体回归、基础建设、投资未来,凡此方略看似步步在理,无奈知易行难,缺乏尽快缓解当前困局的捷径;政治上,两党恶斗、党内分化、党外有“党”,使传统两党政治变异为小集团政治,极端派得势,温和派噤声,任何重大立法都会因引起政治斗争而难获通过。在效率优先的全球化急速变动时代,“美式民主”运转不畅,呈现“部分失效”;社会上,贫富差距拉大,极化现象加剧,穷人反对减福利,富人反对增税收,中产阶级要就业,非法移民要权益,金融寡头、军工集团、劳工团体等利益集团各成气候,在重大问题上互不相让;思潮上,极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涌现,财政保守主义、国防保守主义、社会保守主义等保守主义回潮,思潮激荡,政论激昂,关于国家发展方向的大辩论已然拉开序幕。如果没有“9·11事件”,很难说美国定会早些改革。但可以断言,因为“9·11事件”,美国的体制性变革被严重耽误,导致迟来的奥巴马“新政”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另一个战略失误则是错失重塑国际政治新局的大好时机。“9·11事件”后,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大国都在第一时间对美国表达了同情,并很快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联盟。一时间,美国同各大国同时改善了关系,并因此很快在阿富汗战场赢得重创塔利班政权的胜利。各国也抓住“9·11事件”带来的机遇,一面拉近与美距离,一面加速国内发展。“恐怖与反恐”成为国际政治主要矛盾,大国战略合作成为国际政治主旋律,“后冷战”开始向“后后冷战”或某种新时代迈进,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同步展开,世界面貌焕然一新。遗憾的是,布什政府错把各国对美国的反恐支持当成对美国重大战略行动的无条件支持,并滥用国际反恐合作带来的信誉和收益,将战火从阿富汗延烧到伊拉克,并从伊拉克扩展到打击“极端伊斯兰主义”、抛出“邪恶轴心说”、推进“大中东民主”、策动中亚“颜色革命”。结果,恐怖主义迅速向全球扩散,中东、中亚乱象丛生,朝核、伊核问题此伏彼起,文明冲突由预言变成现实,大国政治矛盾重被激化,大国合作新局被很快断送,国际政治格局再度陷入传统安全困境。这一局面对世界不利,对美国也绝非好消息。美国国际形象受损、感召力减弱、霸权地位下滑,莫不与此大有关联。而因此催生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亚非拉世界新一轮觉醒、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等等,更从深层次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进而实质性影响美国霸权的命运。
二、“反恐时代”的终结及其对美国的意义
可见,“反恐时代”对美国霸权命运的影响是至为深刻的。因此,尽早结束反恐、终结“反恐时代”就成为美国多数人的共识。然而,已然与伊拉克战争、中东民主化计划纠缠在一起的反恐战争,并非主观想要终结便可轻易了断的。布什执政后期其实已在有意识地朝终结反恐方向努力,包括启用盖茨出任国防部长、宣布伊拉克撤军计划、慎用“反恐战争”术语等等。但是,靠布什政府自我纠偏显然不切实际,同时,国际恐怖势力也不会因为美国的战略转向而轻易收手。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直主张尽早结束“反恐”、尽快启动“变革”的奥巴马得以开创历史、入主白宫。终结“反恐时代”便理所当然成为其施政重点和战略优先。为此,奥巴马三管齐下,一手加速伊拉克撤军进程,以期撇清“反恐”与大中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斩断中东战线这根乱麻;一手启动“阿-巴反恐战略”,以正本清源、集中资源,回归“反恐”的主阵地,清除“恐怖”的真土壤;一手综合施策、软硬兼施,全面利用军事、情报、经济、政治、外交资源,试图短期见效。应该说,奥巴马政府的反恐策略取得了实效,其重大标志,就是藏匿近9年的本·拉丹终被击毙,曾经承诺的阿富汗撤军计划准备兑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长达10年的“反恐时代”大体告一段落。
但是,“反恐时代”的终结与其说是客观现实的结果,毋宁说是主观意愿使然。姑且不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或根源远未根除,“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伊拉克局势难以稳定,单就恐怖主义的核心力量“基地”组织、塔利班而言,其并未因本·拉丹之死而土崩瓦解,反而仍在屡屡制造事端,令美军、北约军队时有伤亡;巴基斯坦局势如何演变、美巴关系如何异动,也为今后反恐形势投下阴影。可以说,“反恐时代”虽告一段落,但反恐斗争依然任重道远。正如冷战结束后美国花了相当长时间消化俄罗斯、中东欧遗产一样,反恐仍将成为“反恐时代”终结后美国相当长一个时期的战略重点。
然而,从大战略选择上,美国不得不终结“反恐时代”。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及经济低迷,使美国难以继续承受看不到终点的反恐战争。美国国债上限超过GDP总量,同布什时期因反恐泛化而大举借债深有关联;③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不仅未起拉动经济、扩大就业之效,反而拖累经济、扩大赤字,使尽快结束伊拉克、阿富汗战事成为美朝野共识。④奥巴马政府尽管深知目前从两场战争中抽身稍嫌仓促,也不得不做此选择。另一方面,国际体系变迁深度拉开,西方世界整体深陷危机、新兴大国群体崛起势头迅猛、亚非拉板块普遍酝酿觉醒、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中心,从大战略角度权衡,美国必须尽快从反恐和中东、南亚抽身,因应这一更具长远战略意义的挑战。
如果说过去10年美国聚焦反恐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必须,那么,随着国际形势的全新变化和国内形势的全面恶化,终结“反恐时代”就具有十分紧迫的战略意义。正如布什政府有心借反恐谋霸,将单纯的反恐战争引向谋取新霸权的改造中东、中亚大战略一样,奥巴马政府终结反恐,便同样可以重新布局“后反恐时代”的美国全球战略。
综而观之,“后反恐时代”美国全球战略的主线已然清晰可见。其一,在对威胁和挑战的评估上,国际恐怖主义已从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转变成众多威胁或挑战之一,新兴大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政治挑战、气候变化等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挑战等,也是美国必须同时面对、同等对待的安全威胁。
其二,在对自身实力和国际格局的判断上,逐步认识到美国实力的有限性,强调要综合、平衡、巧妙地运用软硬实力,防止一味单干、蛮干;承认世界力量的多极化趋势,追求国际合作,谋求多伙伴框架下的主导作用,即所谓“平等中的第一”(first among equals)。
其三,在安全战略和地缘战略选择上,强调打击恐怖主义与应对新兴大国崛起并重并有意向后者倾斜,在兼顾中东、南亚与东亚的同时,加大战略重心东移力度,将亚太作为未来的地缘战略重点。同时,加大对海、空、天、网等“全球公地”的抢占和布控。
其四,在战略手段的运用上,在突出军事实力的同时,更加强调军事、外交、经济、对外援助、情报、外宣等手段的综合运用。
凡此传递着一个重要信息,即美国的全球战略呈总体收缩态势。这既是对“反恐时代”美国力量过度扩张的纠偏,也同奥巴马本人的战略观、世界观不无关系。但更深层的原因,乃在于美国国内正面临一场结构性危机,国家的发展方向也正面临半个世纪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三、美国的发展方向
终结“反恐时代”、谋划未来发展,不仅是奥巴马政府集中思考的大战略问题,也是美国战略思想界热议的话题。但从目前的态势看,美国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似乎仍不明朗。
2008年大选,美国民众之所以将奥巴马推上总统宝座,原本是指望他能尽快使美国摆脱困境,“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不料近3年的实践显示,奥巴马虽竭尽所能,却未能满足人们的期待,美国的发展方向愈加迷惘。
客观上讲,奥巴马“新政”的总体思路和方向基本符合美国现阶段的需求,他将“重塑美国实力基础、重修美国国际形象”作为战略重点,也同世界潮流大体合拍。其之所以成效不彰,原因有三:其一,变革的策略有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恢复经济、增加就业是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关键点,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奥巴马着力不够或不到位。他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放在“最难啃的硬骨头”医保改革上,虽最终得以勉强成功,但政治代价巨大,不仅加剧了同共和党的对立情绪,而且未赢得中产阶级的理解和支持,医保改革的获益者最终享受成果也尚需时日。结果,其他改革或多或少因此受到影响。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未能惠及为美国提供90%以上就业的广大中小企业,使美失业率至今仍在9%以上高位徘徊。将教育、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倍增计划作为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支柱,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其对新能源的过分关注,也招致“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批评。总之,奥巴马的改革倡议不可谓不多,改革思路不可谓不明,但美国经济形势和就业形势仍然堪忧。
其二,变革的支持力量不够。在联邦层面,过去10年累积下来的政治“极化”现象开始生出恶果,两党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阵线分明,以致出现奥巴马签署而成法律的医保改革方案共和党无一人投票支持、在国债上限问题上共和党也出现一致对外的“几十年未见之政治怪像”。在地方层面,基础设施建设、医保、新能源等奥巴马倡导的政策,难以在州一级贯彻落实,包括加州在内的六七个州随时面临政府关门的危机。在社会层面,因利益集团分合、贫富差距拉大、利益诉求各异,奥巴马的重大改革也难获最广大民众支持。美国历史上成功的变革无不有赖两党的精诚团结和民众的普遍支持,而在奥巴马的变革中二者均缺。
其三,变革的时机不利。欧日等西方阵营面临比美国更艰难的政经形势,难以依赖;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市场潜力巨大、投资热情高涨,但囿于美国内政治掣肘,短期内无法转化成拉动美国经济的重要推力;而在全球化、核武化的当今时代,指望通过大规模战争手段转嫁风险和矛盾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
由是观之,奥巴马“新政”的前景堪忧,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其本人2012年大选能否成功连任,而且攸关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实际上,美国经济形势并非没有出路,单是奥巴马推动的让富人增税一项,即可使美国新增数千亿美元财政收入;伊、阿战事的停息及大规模撤军的实现,也会给美国政府减负;巨额的国防支出也是可以缩减的选项;一旦松动对华高技术出口禁令和放宽对美投资限制,美国的出口和就业形势也会大有起色。
美国之所以明知可为而不为,或者想为而不能为,根本原因还在于其国内政治和现行体制。对内,金融寡头和大垄断集团同政府联姻,导致政府的改革无法触及根本,反而使造成危机的罪魁祸首因祸得福。如,奥巴马上台后的巨额金融救助资金大多流向了华尔街和福特、通用等大垄断财团,并未使急需救助的中小企业获益;对外,强权政治、霸权心态、意识形态外交仍然根基牢固,使得一些原本可以通过放低姿态、放下身段轻易做到的事情无法做到。结果,奥巴马虽表面拥抱多伙伴世界、倡导巧实力战略、呼唤微笑外交,但在涉及美国霸权根基的各个方面,与前任仍并无二致。
一个困境难解同时又不愿丢弃霸权地位的美国将何去何从?2012年大选或许会给出答案。如果说2008年大选是一场是否要变革的“路线之争”,那么,2012年大选则很可能成为决定美国霸权命运的“方向之争”。问题是,美国人在思考未来方向的时候,是否能够跳出美国思维,而从世界大势的角度去思考和把握。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最不愿看到的结果,是1951年美国外交大师乔治·凯南在芝加哥大学演讲所说的一段话:
“我有时在想,是否可以把民主国家(指美国)与史前时期的巨兽相提并论。这个巨兽有庞大的躯体,但脑部只有针尖大小。它舒舒服服地躺在史前的泥洼中,对周围的环境不闻不问。要使它发怒也不很容易,你甚至要扯断它的尾巴,它才感到它的利益受到干扰。然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巨兽的蛮力不但会致其敌手于死地,也会捣毁它自身赖以生存的土壤。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它事先对周围事务哪怕多有一丁点关注,就可以避免不可收拾的境地。然而恰恰相反,它从来是从漠不关心的极端转向暴跳如雷的另一个极端。”⑤
但愿美国能理性反思和正确决策,不至再次走向另一个极端。
注释:
①由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等领导的改革,奠定了以《宪法》为基础的“美式民主”及一整套符合美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外交模式,确立了美国特色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由老罗斯福、威尔逊领导的“进步运动”,解决了美国进入工业化、都市化、垄断化、国际化“大转折时代”面临的系列难题,使美国完成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成功实现崛起;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则是一场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体制性变革,奠定了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发展的基础,美国由此而成西方霸主。
②[美]乔治·沃克·布什著,东西网译:《抉择时刻:乔治·沃克·布什自传》,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
③据统计,美国国债从2001年1月小布什上台以来的5.7万亿美元猛增到其离任前2008年12月的10.7万亿美元。参见: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Bureau of the Public Debt (December 2010),"The debt to the penny and who holds it",Treasury Direct,Retrieved March 2,2011.
④据美国军控与不扩散中心统计,自2001-2009年,美国国防预算从3330亿美元猛增至7060亿美元。截至2008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中的花费达8726亿美元。相当于1170万美国人1年的医保费用,1160万儿童在公立小学1年的学费,350万大学生4年的学费。参见:http://armscontrolcenter.org/policy/securityspending/articles/supplemental_war_funding/.(上网时间:2011年9月10日)
⑤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expanded edition,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p.66.
标签:奥巴马论文; 奥巴马演讲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伊拉克战争论文; 乔治·沃克·布什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