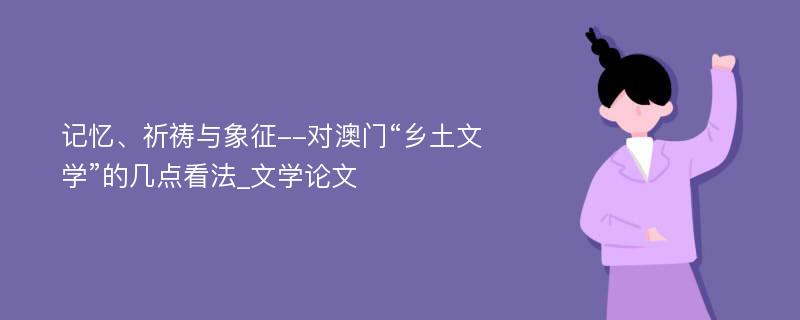
记忆、祝祷与象征——关于澳门“土生文学”的几点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生论文,澳门论文,几点论文,象征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6)02-0130-07
一、土生文学:文化意义大于人种学意义的文学景观
在澳门,“土生”的概念,指在漫长的岁月中来到澳门的葡萄牙人繁衍出的一组欧亚群体。如果将“土生”定义为“在澳门出生的欧亚混血儿”①,这个概念要大于中—葡混血的范畴,这种说法也许更包容和开放,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感觉,更加深入的辨析只能有待人种学研究艰苦漫长的调查取证。金国平先生在1993年翻译了安娜·玛里亚·阿马罗关于“土生人”起源的专著,即《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这为我们理解“土生人”这一群体的产生、变化提供了帮助。译者认为:“在澳门开埠以来四个多世纪中,三个不同的群体——华人,葡萄牙人,澳门人——在澳门这一弹丸之地上朝夕相处,却又老死不相往来,完全自成一体。作为历史和东西方交流的产物的‘澳门人’这一群体有其十分独特的人类、人种及文化特征。有关他们的专著绝无仅有。”② 专著无论是从历史资料、人类生物学资料还是人种学资料上的研究,都给人扎实可信之感。例如无论是通过对“土生人”抽样的血清研究,还是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方言、习俗、服饰等方面的考察,对于“土生人”的溯源及其变化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根据安娜·玛里亚·阿马罗的分析,葡萄牙人与马来妇女的结合是“土生人”族群最早的源起,随后,日本人、印度人、帝汶人入居澳门,使这一族群的遗传本底更加丰富起来,而葡萄牙人与华人之间血缘混杂的加剧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土生人”的谱系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而且,所谓典型的“土生人”文化特征也逐渐融会到澳门文化之中,研究者不无遗憾地说,“这一切正在消退,濒于灭绝,原因是当地的澳门人③ 已向西方和任何一个社会等级的华人的文化模式持开放的态度”④。
显而易见,安娜·玛里亚·阿马罗的研究态度始终是站在以葡萄牙为中心的角度来论述,这使她的人种学的研究无法不带上后殖民的色彩,所谓向“任何一个社会等级的华人的文化模式持开放的态度”之说,其实不如说是几百年来华人的文化生活的地理人文环境使然。即便是澳门中文世界对他们的接纳也是有一个过程,诚如金国平先生说,“中文口语中通常称之为‘土生’。这一称谓不无贬义”,所以起码可以说,双向的文化模式的开放态度才是交流沟通的前提。另外,安娜·玛里亚·阿马罗的研究似乎在强调“土生人”的源头与华人血缘的非直接关系,然而这个“土生人”在人种学意义上的式微却又与华人血缘的融入、华人文化圈的融会不无关系。现在从已有的土生文学作品来看,其作者大都是中葡混血儿,故事涉及的基本上是葡萄牙人与中国人的故事,这些作品实际上就构成对土生人“起源”的一种记忆,从繁复的遗传底本简约为中葡混血,多种文化的交融简约为中葡两种文化的交融,这不仅可以看到四个世纪以来以中华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华人文化圈的影响,而且可以看出“土生人”生存发展中文化选择的必然性,确切说是相关的文化记忆。因此,对于“土生文学”的研究,除了重视、挖掘其文学价值以外,文化融会交流方面的意义也许是更重要的,它实际构成了一种文化意义大于人种学意义的独特文学景观,在中文世界里开拓了“土生文学”研究的汪春认为,“土生人”典型,因为是中西文化“渗透融合的历史积淀和典型范例”,“有清晰的文学面貌,有条件确立其独立的文学形象”⑤。
即便在命名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相关人种学与文化学意义的双相纠缠,关于“土生人”(Filos da Terra)——金国平先生说,“本人认为‘澳门人’可为它的中译之一”,应该说,“澳门人”是更加能够凸显文化交融意义的称谓,而“澳门人”的文学,这种用葡语写作的文学与其说归入海外的葡萄牙文学,不如说正是澳门文学“创世纪”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澳门这个中文媒体为主导、葡语仍然存在的世界的重要文学读物,其汉译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中文读者所认识,“澳门人”的文学实践实际上已是中国文学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如果用“澳门人文学”来直接命名,不仅容易混淆澳门文学的作家群,实际上也无法传达出这一独特的澳门作家群创作的文化意义。因此,尽管不如人意,“土生文学”的这种命名仍然是可行的。而“土生文学”中这样一种另类的“澳门人”形象,无疑丰富了“澳门人”形象的谱系,然而这样的认识并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在有关“澳门人”文学形象的探讨中甚至被遗忘,例如有论者认为:“本土作家笔下都未曾塑造出一个‘活的’、能震撼人心的澳门人形象”,“翻阅许多作品。我们很容易找到‘澳门人’的统一形象:朴素、热情、善良,还有一些儿胆小怕事”⑥。在这里,土生作家并未进入论者的视域,自然将这样一种土生作家塑造的“澳门人”排除在外。中西文化交融之地的澳门显然是研究者对澳门文学提出较高期望的一个背景,这样的背景无疑异质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背景,亦可由此提出“土生作家”的本土意义和相关“澳门人”的象征与启示价值。然而仅仅对“朴素、热情、善良,还有一些儿胆小怕事”的“澳门人”形象表示失望,不能说明论者是自觉地站在一个丰富的“澳门人”的立场去思考澳门小城的文学问题。对怎样才能“解开长期以来对‘澳门人’观念的束缚,从此带来创作艺术的解放”,重视对“土生文学”的研究,也许是一个有益的切入点。
二、祝祷与歌唱
在意蕴与情调上,土生文学总的来说充满祝福、祈祷,体现出浓郁的抒情色彩。对澳门这一片与土生人休戚相关的处所的礼赞,显示了土生文学题材上的鲜明特色。
对于这一特殊族群的澳门人的“起源”与“起源”之地的共同关注,几乎是土生作家不约而同的心态,这首先是他们对澳门充满了一种神奇的感觉,在族群的精神谱系上从葡萄牙认同逐渐过渡到澳门—中国认同,但不论怎样,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对澳门的恋情。持续不断的澳门恋情本身就可以直接成为一种题材。以诗歌来说,若瑟·多斯·圣托斯·费雷拉(1919-1993年)的诗作《幸福的花园》⑦ 中表达了这样的感觉:
我们的澳门,圣地,\是一个备受祝福的花园\那儿更布满美艳的鲜花,\传遍优美的歌声。\幸福健康的花儿,\因主之名我们种植她\我们的祖先更以他们的泪珠\来浇灌花儿、使她们光亮柔媚。\心中尽管忧伤,忧愁至极,\灵魂也痛苦得阴暗失色\是否人们都笨拙得\把自己扔到凋谢的花丛里呢?\澳门,基督徒之家,\大家仍都住在这里,\心中各自拥有自己的信仰。\看到信仰与爱意的共存,\就会更因此而对上天作出感谢\更不同意她的消亡\澳门,幸福的花园。
诗作的作者生于澳门,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为澳门土生,对于诗中的“我们”,从诗歌中的宗教背景的渲染,以及作者的态度来看,显然是葡萄牙人的“我们”,这说明作者的认同倾向,是“我们”使澳门“光亮柔媚”,但是这个“我们”,也是包括澳门这个土生人特殊族群诞生之地的“我们”,而“心中各自拥有自己的信仰”,则涵盖了更广阔的澳门人。在他的后期诗作《未来》中他担忧的“澳门的未来”,实际上是包括了中国人、葡萄牙人、土生葡人的未来。如果说费雷拉的倾向导致他对澳门回归的困惑使得后期的诗作更多是“‘帝国斜阳’的伴奏曲”⑧,那么,李安乐、马若龙等人则表达了更多的澳门—中国认同,从中看到一种维系澳门人的中国情感。最为典型的是李安乐的《疍家女之歌》,诗歌开始展示的是关于澳门在文化交汇到来之前的存在景观:
澳门诞生以前\我已在这海面划行,\在这小小的疍家船上,\养家活口谋生。\常去妈阁上香,\祈求妈祖赐福,\日子过的快活,自从来了‘牛叔’。
诗中的主体是居住在水边的船女,这是中国南方的水上人家或居于水边人家的女儿,代表着在汉文化区域里非常贫穷、非常边缘的群体,然而即便如此,却也足够证明在关于澳门之为特殊意义的澳门之前的主体性存在,诗中自然也站在文化交汇的立场上来看待“鬼佬”的到来:
这些西方鬼佬,\乘着三桅船来到,\给人们送来了,\沙甸鱼的鲜纯美妙。水手们来到这里,\言词温文有礼,\蓝眼睛含着温柔,\向阿妹们表露爱意。\在我们疍家船上,\水手们喝得半醉,\唱起了美妙的歌儿,\为我们的阿妹干杯。\从喜欢咸鱼,\到把马介休爱上,\这就是叫做‘澳门’\这名字的地方。
诗歌赞颂了“鬼佬”与疍家女的爱情,诗歌最后回到了关于“起源”的说明上:“正是这份坚定的爱情,能征服一切,不可战胜,就在我们疍家船上,诞生了第一个澳门‘土生’”。诗人在关于“澳门”的命名以及“土生”的起源上,以诗叙史,完全出自诗人诗心的愿望与想像,无视这漫长的澳门历史中存在的中葡的冲突甚至流血,这里的关键是其态度决定着一切,回望过去漫漫的历史烟云,逐渐迎来的融洽的文化存在形态,使诗人大胆将“澳门”命名的内涵定义在一个中国疍家女与西洋水手的爱情故事之中,取起美好融洽的意义,从而表达了文化交融的意义,因此,祝福、赞颂、祈祷的态度决定了诗人的情节设计和表达。作为中葡混血儿的马若龙——画家、诗人,既有《大三巴遗址》这样象征对其西洋文化血统的缅怀之作,又有朴实无华、揣摩自身的中华文化遗传因子的诗作,如《祖母的镜子》中,对于“镶著红木镜框\一派考究的中式装潢”的祖传镜子,诗人发出这样的概叹:
我的中国祖母\很久未在那面中式镜中\出现在我的眼前\她随同最后一场雨\随同那收获的稻禾\一去再也不复返。
此外,散淡不失沉缓的格调,同样能够成功地表达祝祷的情感,在这方面,澳门土生葡人女教师晴兰的《流浪者之步》⑨ 可以作为代表,试看前三节:
阳光透过青青竹叶\轻抚沉睡的泥土\巨人的榕荫下\那些洁净的老人悠闲下棋\青草地的边缘\信奉基督的姑娘阅读孝经\玩雀的男人\期待着鸟鸣之后的沉静\我思索着那些空中的生灵\不管是否关在笼中\至少,不要有名称\澳门的一切都有双重的名号\贾梅士公园也叫白鸽巢\带着梦幻的清晨奏响多重乐曲\都市般的乡村带上竹林的帽子\花布围裙清扫着林荫小路。
晴兰的这首诗,白描的部分最有力量,例如“信奉基督的姑娘阅读孝经”,“贾梅士公园也叫白鸽巢”,这正如颜色形状各异的板块,恰如拼拼图一般,奇妙、自然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对澳门这种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融合景观的抒写,表达了土生文学作家的祝祷心态,这或许是来源于在漫长的岁月中不同族群共生共存的需要,而在文化与宗教中具有亦此亦彼特征的土生人,感同身受,容易对不同的风俗人情有一份贴近与体认。在这方面,江道莲的短篇小说较为突出地表达了一个土生作家的体认与祈祷。在她的小说《西洋鬼》⑩ 中,作者截取寒冷街景的几个镜头或场面,描绘了生活在澳门底层的人群,在饥饿、寒冷中接受“西洋鬼”的帮助,得到“西洋鬼”的救助的故事,作者以第三人称的叙事,却不能掩饰作者的一份欣慰:当人们得到救助的面包以后,“不像刚才那样寒冷了。甚至孩子们萌生了玩耍的欲望。好动的孩子捡了些树枝在远处点火生了篝火。起初火势不好,一片烟雾,后来柴不那么潮湿了,最后那火苗的热烘烘喷到那些身体最僵冷的人的身上”。对于平常专横的西洋鬼此时的同情,“从这些感激的口中终于冒出了这些话:——菩萨保佑这些‘西洋鬼’吧”。自然,这并不意味着作家回避矛盾与冲突,江莲达擅长描写不同种族恋情的悲剧情感,对中西通婚家庭中的文化冲突及其对子女的影响的刻画也是细致入微。不过,即使在叙述文化冲突与悲剧事件时,作者表达的惋惜与期待则是清晰可见的。在《怀念之隅》中,专制的中国父母受到了作者的批判,因为不能赞同女儿自由恋爱,更不能容忍与西洋人的恋爱,致使女儿走上了绝路。同时,作者也歌颂了这种超越种族界限的纯真爱情。《施舍》中被牺牲的母亲,特别表现在她的儿子离开澳门前甩给母亲一个硬币这样的细节。因为儿子要去西洋学习,要认同的是父亲的谱系,而不愿意看到出身低下的母亲。如何看待这类中西通婚家庭中中国女性的悲剧与种族的关系?种族隔阂的因素自然不能排除,其实小说无意加深种族的隔阂,对不平等社会进行控诉才是小说的着眼点。这一倾向与安娜·玛里亚·阿马罗的说法有相似之处:“澳门人的自成一体从来不可能是种族偏见的结果,而是纯粹的社会偏见的产物”(11)。
进一步说,土生作家祝祷的心态与抒情的欲望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土生作家那里,抒情不仅仅是对事物本身的一种情绪上或心理上的感应,抒情还被赋予了象征的含义,例如在土生作家关于爱情、友情的颂扬,是被限制在特定的中葡关系或中西关系上来考虑的,没有这种关系,就没有土生的源起。可以说,这方面的主题内涵,由此构成了所谓“澳门性”的一种内涵与象征。因此爱情、友情等的抒写,是和一个族群的起源相关,就有一份感恩、自豪在内,这一份抒情不是没有重量的。飞历奇的小说《疍家女阿张》,荣获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1950年颁发的菲阿幼德·安尔梅达“百花诗文学奖”。“澳门号”炮舰上的水兵曼努埃尔与疍家女阿张的爱情故事,分离的结局并不意味着悲惨,并不能减少小说在两人关系中建立起来的美好情感。首先,是阿张拯救了曼努埃尔对美好情感的向往,这个在世界各地漂泊的浪荡水手,在遇到阿张之前,“他的心灵沉沦了,身上最美的感情泯灭了”。正是阿张的温柔、善良,沉默、接纳、承受使他有所震动。显然,阿张这个形象代表了作家对中华民族女性的理解与认同,甚至代表了一种阿张即澳门的认知,这个南方中国小城,不是默默承受与接纳着外来者吗?当然,小说的重心在于渲染两人对于女儿梅来的出生与抚养的问题上建立起来的情感。梅来,这个“土生”女儿,不用说,是连接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纽带,更重要的是,其本土性的存在离不开亦此亦彼性的言说。这就是小说关于爱情抒写的内在动因。同样,友情也是在相同或相似的内涵中来抒发的。飞历奇的《镜海垂钓》写的是葡国人“我爷爷”与中国海盗之间的故事。“我爷爷”性情豪迈,是“具有贵族时代澳门人的缺点与品格的”,他挥金如土、散财聚众,性格中最鲜明的一点是“侠义”,这使他在“中国人”被中国海关追捕的时候,能够挺身而出,担待风险,巧妙渡过难关。“中国人”的回应充满了“知恩图报”的意义,不但挑来一推东西,“框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水果、火腿肉、威士忌、白兰地与餐酒,一包包香烟和小雪茄,还有许多古巴雪茄和糖果”。更富于戏剧性的是专门送给“我奶奶”一条鱼,“当把鱼破开时,从它鲜嫩的肉中跳出一只镶嵌着钻石与翡翠的手镯”。不仅如此,“我爷爷”和中国人的友谊日益加深,“在我爷爷生活中某些棘手的关头再次考验了这种友谊”。小说关于“我”的先人的故事,实际上更深的用意在于抒发澳门之情,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这就是十九世纪末澳门生活的一个侧面”。无独有偶,在爱蒂斯·乔治·玛尔丁妮的散文《废墟中的风——回忆澳门的童年》中同样记述了“我”的葡国先人与中国人的友谊,这些友谊在各自人生的艰难时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跨文化的文学“镜像”
土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在其文化视野的研究,这显然符合研究对象的特点,即土生文学的文化价值的挖掘要大于其文学价值的阐释,这正如汪春所说:“研究土生文学并不仅限于对其本身价值的确立,也是对澳门整体文化的一个补充,更是对澳门文学的一个补充”(12)。但是这个“补充”,我认为尽管有具体的作家作品构成,然而更重要的是象征的意义大于具体的描述,对于澳门文学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发展更富于启示的意义。这样,当作家在“我是谁”的表述中,其语境也同样是适合澳门文学的,而在具体的作品中查看到土生作家的跨文化意识的特征,同样也构成对其他澳门作家的询问。
土生作家的身份问题有血缘的、国籍的、族群的、文化的影响,这些东西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可能是更加含混的,不易描述的,所受到的影响是多因素的。然而,不管怎样复杂,也不论语言形式,土生文学是“澳门的”这一事实,则表明土生作家的身份与“澳门的”有着紧密的、重要的关联,这就是跨文化身份的识别、感受与体认。在“澳门的”语境下,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其实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作家的创作有意识、无意识都体现了这种跨文化认同的驱动,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跨文化认识的文学“镜像”。不妨说,澳门文学可以从中照见自己的文化属性。
李安乐的诗歌《知道我是谁?》里这样吟唱:
我父亲来自葡国后山省,\我母亲中国道家的后人;\我在这儿出生,欧亚混血,\百分之百的澳门土生!
我继承了些许贾梅士的优秀,\以及一个平常葡国人的瑕疵,\但在某种场合,\却又满脑的儒家孔子。
长着西方的鼻子,\生着东方的胡须,\如上教堂礼拜,\也进庙宇上香。\既向圣母祈祷,\也念阿弥陀佛。\总梦想有朝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中葡诗人
因此,我的后代,\拥有国际血统,\他们将在美丽的土地上,\到处播下种子。
诗中从观念到生活方式试图说明自己的文化身份,例如所谓“道家”、“儒家”、“孔子”,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价值观念的符号,作者未必深究其义,具体到“进庙宇上香”等,也未必需要亲自体验,却可以明确表达文化身份的中国来源。既有中国文化又有葡萄牙文化、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具有亦中亦西的“文化间性”特征,是土生作家从属于澳门半岛的文化“根性”,使他们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拥有一种跨文化意识,在自我的矛盾甚至冲突中加以思考,表达其价值选择。
在这方面,江道莲的小说可以是很好的例子。在《感情的冲突》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四十开外”中年女性“抛弃”丈夫的故事,小说选取了离别的时刻以突出“她”的矛盾与抉择。多年前,当她从美国回来时,“她便公开声称谴责一夫多妻制度”,然而结婚以后,她的丈夫抛弃了诺言,开始纳妾,“他对她大耍中国男子汉大丈夫的威风,告诫她不是在美国”,当丈夫破产的时候,他已有四房偏室。男人三妻四妾这种文化与受过西洋教育、追求男女平等的文化虽然有冲突,但是江道莲并没有概念化地去处理这个问题,作家将这个问题还原到日常生活中去进行,当孩子八岁的时候,这一日常生活的结果是她的“粗糙的手,布满皱纹的脸,灰白的头发和干瘦的身体”。显然,传统中国文化对女性的奉献与牺牲的要求,是作为日常生活本身来理解的,身在此中的“她”不可能越过。然而事情还必须由结果来判定,为了孩子的成长,决定带孩子去美国投奔舅舅这种理由,则可以看作是满足“她”对这种日常生活中牺牲女性的文化价值的否定。即便在这种时刻,“她”的内心活动仍然体现了人性的或不如说更中国女性的特点,即牺牲精神:“她是否可以遗弃“那个老头”,她“后悔自己的决定”。所幸作家心明眼亮,描写了那位丈夫在一堆娇艳女子面前的丑态,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位女性追求新生活的问题。江道莲生于澳门,在小说中她对两种文化有关女性问题的把握能力清晰可见,她对事情的简单勾勒、对人物的心理刻画显示了她的跨文化意识,将理解与选择恰当地表现了出来。相形中,小说《长衫》的悲剧处理,女性形象珍女的毁灭给人带来更强烈的震动。珍女在嫁给阿忠之前,到过美国,接受了新式教育,回来时已是挺秀优雅的女子,这使得阿忠相形见绌。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乱年代,珍女为了一家人的活命,做了陪舞女。阿忠既无能力找事做,又无法接受珍女这样养家糊口的办法,结果在疯狂的情绪中将珍女杀死。小说讲述“自我”有所觉悟的女性在中国家庭中的毁灭,这样的毁灭在常态的生活中被察觉的程度则要轻微一些,如上面分析到的《感情的冲突》。小说取名“长衫”用意颇深,“长衫”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是在婚礼上,这件“绣着各色花枝的黑缎长衫”,衬出了她“令人心旌摇荡的曲线”,表达了珍女自我欣赏的态度;第二次出现是在决定做舞女的时候,“她从柳条框里取出了那件珍藏起来的婚宴穿过的细瘦、绣着花枝的黑衣”,说明自我救渡的勇气;第三次出现是阿忠杀害珍女后,“看见了那件挂在门后的黑色缎长衫在随风飘荡”,这件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的长衫,实际上寄予了作者对珍女的惋惜,看到了女性价值在一个中西文化交汇场寻找切入点的困难。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视点在非土生作家的其他澳门作家那里,没有得到相应的表达与思考,这正说明土生作家的跨文化身份使其能够穿越一些文化的屏障,表达自己对命运的思考。
澳门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一般被理解为“抒写对半岛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反映澳门人以及从大陆、海外迁澳的华人的精神心态,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本土气息,这就是澳门作家所说的‘澳味’”(13)。地域性特征如果不反映跨文化境遇中人的精神状态,那么这个地域性特征则很难说是“澳味”的。因此,澳门土生文学不仅是澳门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澳门文学中的“他者”,从这样跨文化的文学“镜像”中照见的东西相信可以促进澳门文学自身的思考。
注释:
①饶芃子:《澳门土生文学作品选·序》,汪春、谭美玲编《澳门土生文学作品选》,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01年。
②④(11)安娜·玛里亚·阿马罗著,金国平译《大地之子——澳门土生葡人研究》,澳门文化司署,1993年,第3页、第102页、第103页。
③指土生人。
⑤⑧(12)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338页、第351页、第382页。
⑥廖子馨著:《我看澳门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16~117页。
⑦引自汪春、谭美玲编:《澳门土生文学作品选》,澳门大学出版中心,2001年。下文未另注明的引诗均同此。
⑨珠海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作家协会编:《澳门世纪行》,珠海出版社,1999年11月。
⑩江道莲著,金国平译:《长衫》,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13)江少川著:《台港澳文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