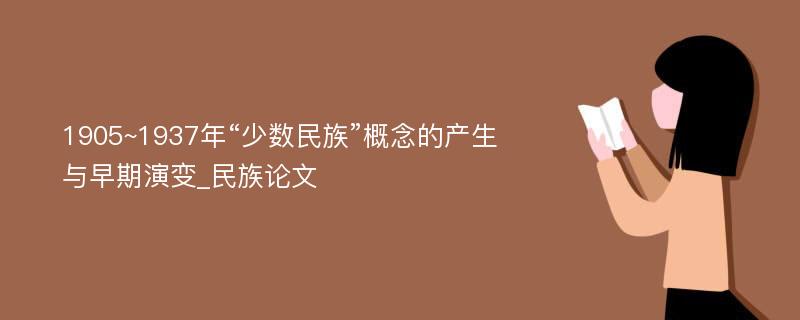
“少数民族”概念的产生与早期演变——从1905年到1937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生与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名称的产生及其与实体的相互关系,包含民族划分和认同等诸多问题,一向为学界所重视。由于人口总量相对较少,我国汉族以外的55个民族习惯性地被称为少数民族。表面看来,“少数民族”仅具人口多少的统计学意义,实则只有从“多数民族”的角度出发,才有少数民族观念,汉族和少数民族体现了对应划分的民族关系。此事看似简单,实则牵涉一个重大问题,即“少数民族”概念的由来。①
以往学术界较少考察“少数民族”作为一个后出集合概念的渊源流变,通常不分古今差别,比如,对它和非汉民族其他指称如“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的联系与分别,缺乏清晰的比较鉴别等,② 容易将复杂历史简单化。本文试依照时空顺序寻究“少数民族”概念在中国演化的早期进程,③ 希望借此深入理解外来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曲折进程,进一步认识少数民族问题的客观规律。
一、由满、汉对比而生“少数民族”
中国的现代民族概念,主要是清末以来受西方民族理论影响才普遍使用的。④ 当时满、汉民族关系日趋紧张,从人口多寡、文明程度等对比角度出发,汉人尤其是排满论者,容易产生“汉”多“满”少的民族观念,直接催生“少数民族”概念。其中,许多观念都来自日本。
韩锦春指出,1905年刊载于《民报》的《民族的国民》一文,已经使用了“少数民族”一词。⑤ 此文出自汪精卫,他根据民族同化的史实,归纳出民族关系的四个公例:“第一例,以势力同等之诸民族融合而成一新民族。第二例,多数征服者吸收少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三例,少数征服者以非常势力吸收多数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第四例,少数征服者为多数被征服者所同化。”以此衡量中国,谓自黄帝迄于明,“我民族实如第二例所云:多数民族吸收少数民族而使之同化”,明亡以后,“我民族”降至第三例中的地位。⑥ 结合排满语境,可知“我民族”为汉族,“少数民族”即汉族以外诸民族。
与革命派进行种族革命论战的梁启超,也承认这四个公例。梁、汪两人所用“民族”与“国家”概念,主要源于德国学者伯伦知理有关国家学说的日译文本。两人都可能看过吾妻兵治节译的伯伦知理原著《国家学》,以及美国学者巴遮斯著,日本人高田早苗、吉田巳之助节译,但吸收包括伯伦知理在内的德国学者对于英文nation理解的《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两书。⑦ 虽然这两本书都提及现代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在数量多少、实力大小、彼此关系等方面的情况,但并未明确提出四个公例。⑧ 汪精卫曾说,包括四个公例在内的内容,“皆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所标之公例也”,⑨ 表示并非己见。或许仍与日本有关。1917年,陶亚民摘译日本人中村久四郎所著《极东之民族》而写成的《民族之意义》一文,论述了一个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关系的种种情形,其中就有这四个公例。⑩ 可见汪说确有所本。
梁启超主张在“小民族主义”之外,实行“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他提出,只有以汉族为中心吸收满族,合汉、满、蒙、回、藏、苗为一大民族,才能达此目的。(11) 革命派也开始改变激烈逐满的态度,承认一国之内不可能只有单一民族。汪精卫参照伯伦知理以一族为中心而统御全国的学说,认为蒙、回、藏诸族能力薄弱,只有以汉族为主体建立民族国家,进而容纳其他民族,才能妥善处理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可惜“少数无能之民族”满族“腐败无能”,唯有推翻清廷,方能达此理想。(12) 刘师培认为,多个民族同隶一政府之下,最不公平的是政权握于少数强族之手。“及少数之强族失其强权,势必与多数之民族同化”,故只要君统覆灭,少数“满人”必然同化于多数汉人,无需驱逐。(13) 时人正是借用外来民族理论有关民族人数多少、实力对比的观点,来理解和处理当时汉族和满族及其他各族的关系,进而引申出“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大、小民族主义这样相对应的概念的。
“少数民族”一词出现后几年间并不多见于各种言论,但将“满人”看作中国境内人口为“少数”的“民族”,并以此作为排满的重要依据,却是汉族排满论者共有的思想,其来源仍与日本有关。
章太炎早在1901年就表示,因为“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所以要排满。(14) 这种观点被排满革命论者广泛援引。“满人”五百万源出何处有待考察,不过,有关满、汉人口比例的文字,早已在日本人的著作或译著中频频出现。那珂通世著汉文本《支那通史》说:“(支那)各种民口不详,大约汉人三亿六七千万,满人、韩人各千余万,鞑靼、图伯特各数百万,江南诸蛮数十万。统计全国,盖不下四亿,而其十分之九,汉人也。”“(满人)较诸汉人,不过百分之三”,“汉人虽众,势力反不及之也”。(15) 中西牛郎则认为,汉族“对满洲之征服者虽外观宛如奴隶,然仅一千万之少数之满洲人,对三亿七千万之多数之汉族,智力富力,则被征服者之汉人,遥优于征服之者之满洲人。是则今日政治之实权,渐渐移归汉族之手,亦不足怪。若今日之支那帝国,除去汉族外之人口,不过今日三十七分之一,茫茫邦土,与朝鲜、安南陷同一之命运而已”。(16) 此言出自翻译,原意是否如此还有待查考,至少在译者看来,汉族是多数,“满人”是少数。
排满革命论者普遍认为,满族是“少数”、“劣等”的民族,应该服从“多数”、“优等”的汉族。蔡元培说,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少数满人”中虽有一二开化者,但明显不如“多数汉族”,(17) 邹容在《革命军》中说:“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使贼满人而多数也,则仅五百万人,尚不及一州县之众。”(18) 胡汉民解释《民报》的主义时指出,以往“满人”不但以“少数恶劣民族”钳制“吾多数优美之民族”,而且强迫同化汉人,这种状况既不合理,也不能持久,未来不论是否驱逐满族,汉人都不能永远沦为被征服者。(19) 陈天华表示,其见解之所以从政治转向种族,“盖政治公例,以多数优等之族,统治少数之劣等族者为顺,以少数之劣等族,统治多数之优等族者为逆故也”。(20) 黄孑民将1903年的政见分为旧政府党、平民党和新政府党三种,后者“挟民族之见,以为彼族以少数压制吾族之多数,彼必不肯平等以自削,必不得已则将实行其与赠家奴。故居今日欲达吾辈之目的,非破坏旧政府而建设新政府不可”。(21) 1906年底,孙中山阐述民族主义时说“因不顾少数满洲人之专利”,所以发动民族革命。(22) 不过,他将排满限定为排贵族特权,重在推翻帝制,而非整个满族。
满、汉民族的权利分配与各自人数比例不符,也是革命派反对君主立宪的重要理由。清朝官制分别满、汉,官缺往往满、汉各半。朝廷下令实行预备立宪,试图调和满、汉。立宪派主张,立宪后“以政治权分配于数个之民族,使人人皆有国家主权之一分”。(23) 意思是,各民族成为平等的立宪国民。问题在于,如何才算平等。
杨度说:“据千九百三年政治家年鉴统计,中国之人数实约四万(万)二千余万。此四万(万)二千余万中,满、汉之人乃占四万(万)一千余万,蒙、回、藏三族合计,尚不过九百余万,实为四十一与一之比例。将来分区域准人数以举议员,所举出之数,亦必略与此比例相等。”(24) 他将满、汉一起计算,大有承认满、汉一体之意。宋教仁认为,立宪国人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满人”只有汉人的两百分之一,选官“亦应适如其率”。(25) 田桐主张,应以“满人”五百万与汉人四万万的比例,来选举各自国会议员的人数,而今汉人官少权小,“满人”独享权利,汉人独无权利。(26) 卢信说,权力分配如股份公司分股,要按满、汉人数比例,而非满、汉平均分配权力。(27) 清朝官缺往往满、汉各半,令革命派认为朝廷无诚意立宪。
总体而言,只要存有民族划分思想,对比之下,汉族就容易产生“汉”多“满”少的观念。因此,上述诸人尽管政见不尽相同,但都站在汉族立场,认为自己是多数的民族,满族或其他各族合起来是少数的民族。清末民初,国人还称西南苗夷民族为“原始民族”、“劣等民族”、“未开化民族”、“半开化民族”,称边疆诸族为“四邻民族”、“边境人种”,隐含“弱小”、“落后”、“边缘”等意思。(28) 这些指称虽非针对所有非汉民族,但同样是基于汉族立场而言的“他指”概念。
武昌起义前后,种族革命思想一度继续传播,“少数民族”概念时有出现。胡朴庵认为,近三百年来,汉人“以多数民族伏处于少数民族之下”,但亡国不等于帖服,汉人应光复江山。(29) 1911年11月12日,宋教仁在和袁世凯所派与武昌民军谈判的代表蔡廷干、刘承恩辩论国体只能为民主时,强调:“满洲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国,束缚我汉人,残杀我志士,使我汉人日就弱亡,吾族纵不言复仇,亦不应戴之为君主”,“况夫以少数劣等民族,断不能统治多数优秀民族”。(30) 1912年10月,陈耿夫仍以“满人以五百万之少数民族”压抑四万万汉人,为清朝灭亡的重要原因。(31) 大致延续此前革命派对满、汉民族的认识。
虽然清末“少数民族”概念出现时泛指汉族以外诸族,但实际不离排满革命的语境。民初以后,民国政府并没有像清末革命派宣扬的那样,按照各民族人口比例来设计政治制度,只是较为笼统地规定人民不分种族,一律平等。当时“五族共和”口号盛行,社会各界倡导消融种族界限,平等相待,类似满族少数的提法和“少数民族”概念变得少见。
二、国际视野下的“少数民族”
从1919年开始,“少数民族”被用来对译英文词汇minority,描述欧洲民族问题,使用频率提高。国民革命时期,“少数民族”又和从共产国际世界革命视野中的“被压迫民族”概念转化而来的“弱小民族”一起,被国共两党作为国内非汉民族的泛称。从此,“少数民族”的内涵外延开始复杂化。
据张其昀说,“少数民族”的名称,“中国本未有之”,它是从美国政治地理学权威鲍曼(J.Bowman)的《战后新世界》(New World,1921年初版)一书中的英文词汇minority翻译而来的。(32) 实际上,说此前中国没有“少数民族”名称自属有误,但说其出自翻译,却道出了“少数民族”的另一思想渊源。
《战后新世界》1922年春开始翻译,竺可桢专门在《史地学报》做过介绍,该刊推荐说:“是书已由本会地学同志六人合译,不久可望付印。”(33) “本会”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实际翻译者是张其昀、胡焕庸、王学素、陆鸿图、诸葛麒、吴文照、黄静渊、向达。此八人就读于南京高师,共同修习竺可桢的世界地理课程,受竺氏启发,合译了鲍曼此书。他们将凡尔赛体系中的Minority Treaty,译为“保护少数民族条约”。由于1924年鲍曼还有所增补,张其昀等将新增内容补入,“此书之成,任叔永、朱经农、程寰西三先生,皆尝惠予教益,实深感谢”,中译本经竺可桢校订,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再版。(34)
不过,早在1919年,国人就用“少数民族”描述欧洲民族问题。欧洲民族分布犬牙交错,相互成见极深。由于各帝国实行强迫同化政策,自18世纪民族主义勃兴以来,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一国之内,种族、语言或宗教与该国大多数人不同的少数人,往往遭到歧视压迫,对其权利保障逐渐形成国内立法与国际条约两种形式,然均效果甚微。一战后,“民族自决”、“归复故土”运动兴起,新兴各国纷纷成立,很多民族随疆土重划而改变国籍,其待遇问题自然成为欧陆各国关系的重要内容。(35)
巴黎和会期间,为了使德、奥签订条约,协约国在民族问题方面煞费心思。《申报》介绍了对德和约草约。草约规定,德国承认波兰独立并予其海岸线,将上西利西亚、西普鲁士、波森省、维斯土拉河左岸等地割让给波兰,波兰与协约国共同规定保护“种族上或宗教上少数人民”的条款。(36) 所谓“少数人民”,指由德国割让领土给波兰,划归波兰的原德籍日耳曼人。
对奥部分和约的“政治条款”则规定:奥国承认捷克斯拉夫、巨哥斯拉夫(即南斯拉夫)独立,部分领土归入罗马尼亚,这三个国家允诺与协约国及共同作战国订约保护本国内“种族宗教方言”属于“小部分之民族”;奥国应“承认视保护少数民族(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之义务,为国际同盟有裁判权之国际关系事件。奥国担保对于奥国内各项居民不分家系、国籍、语言、种族或宗教,概予以生活与自由之完全保护,并许其信仰自由。凡属奥人,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在法律上皆系平等。无论公私事件,各种语言皆许其自由运用,不得加以限制。奥国对于非操德语之奥人须予以适当之便利,俾在法庭上得用其自有语言。奥国人民在种族上或宗教上或语言上属于少数者,得与其它奥人享受同一保护”。“凡关于以上诸端之规定,由国际同盟保护之”。(37) 这些条款分散在正式的对奥圣日耳曼和约中,与“少数民族”对应的英文词汇为minorities。(38)
当时国内各大报对以上条款的翻译不尽相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北京《晨报》,奉天《盛京时报》都将与上一段带有着重号的“少数民族”对应的词汇,翻译为“小国”。(39) 笔者以为,他们起初或有国籍问题,但并非国中之国,“小国”的译法容易引起误解。而上海《时事新报》称,对奥和约除“正约”外,还有保护罗、南、捷三国“少数居民”的其他“诸约”。(40) “少数居民”一词,也无法反映出欧洲民族国家和民族认同的复杂关系。故以上两种译法多不流传。
其实,《申报》早已用“少数民族”一词分析欧洲民族问题。1919年3月28日,该报登载的《巴黎和会议事记》评论道:“东欧数区,民族杂处,国籍主义无处施行,他日合约似宜规定各国应保障其国内少数异族之权利,许其保持固有之语言风俗,以避冲突。少数客民既不横遭压抑,自可与本地民族日形亲睦,相处既久,定可融化一炉,而多数人之语言风俗,逐渐为少数人所采用矣。再,各国宜设法使散处四方不满意于当地治权之少数民族各得其所。”文中所说“少数民族”、“少数异族”、“少数客民”三者或许并非完全指同一种族群,实则都被视为“异己”和“客居”者,同样面临争取平等待遇问题。在国联框架中,陆续签订保护少数民族条约,或作同样承诺的主要有中东欧十四个国家,少数民族问题从此更广为人知。故胡愈之1934年说:“虽然少数民族早已存在,但是这个名词却在从大战以后,方才普遍行用的。”(41) 清末的英汉词典在翻译minority时,多指出有“少数”(The smaller number)之意,却鲜见直译为“少数民族”或“小民族”。(42) 表明minority虽早为国人所知,但译成“少数民族”,主要是欧战后的事。
欧洲少数民族或没有参与所在国的缔造过程,或没有共同享有国家政权,与统治民族分属不同的民族群体,也没有共同的民族认同。尽管各国都承认各民族一律平等,但少数民族在担任公职、宗教信仰、使用语言、服兵役等诸多方面,仍受歧视或限制,他们往往也不打算和多数民族友好。国联框架下的少数民族国际保护制度本身存在严重缺陷,保护条约依然徒具空文。(43) 一战后欧洲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妥善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后来德国进攻捷克,便以此为借口。
随着国内对巴黎和会、国际联盟介绍的增多,用“少数民族”来指称欧洲民族问题的做法愈发常见。(44) 1924年初发布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以“少数民族”泛指国内非汉民族,“少数民族”被重新用于称呼国内民族,其中不无共产国际的影响。十月革命后,苏俄民族理论也传入中国。1919年,北京《晨报》介绍了苏俄政府在1918年1月18日宪法会议宣布的政纲。它规定俄罗斯劳兵农共和国是各民族联邦国,以各民族自由同盟为基础,劳农政府“排斥压迫小民族及殖民地”。(45) 1923年11月,张国焘撰文认为,十月革命“不但解放了被俄皇、贵族、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俄国工人和农奴,同时也解放了被大俄罗斯民族压迫下的十数弱小民族”。(46)所谓“小民族”、“弱小民族”当指俄国境内人数较少的民族。借鉴苏俄民族理论,自然会受到将俄国境内民族区别为“大俄罗斯民族”与“小民族”的观念的影响。
国民党一大宣言虽以共产国际的俄文决议为蓝本,但综合对比共产国际决议原文、俄文翻译和宣言草拟者等情形,可知“少数民族”概念并非出自共产国际,而是清末排满思潮。但与清末排满不同,孙中山接受了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他坚持建立单一制统一国家,所承认的民族自决,是指国内各民族有高度自治权。他在建国大纲中规定扶植“国内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本意是指出汉族在人口数量、文化程度等方面,皆为革命主要力量,汉族不能蹈袭帝国主义压迫手段,而应帮助弱小者,从而建立相互协作的关系。共产国际则以其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为指导,要求国民党承认民族自决权,将来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共产国际用来指称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和国家的“被压迫民族”概念,被中国人习惯转称为“弱小民族”后,又被共产党率先且习惯用来指称国内非汉民族。1926年底,中国共产党才在自己的文件中首次使用“少数民族”概念。在共产国际、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合作用下,“少数民族”在北伐后期具体化为满、蒙、回、藏、苗诸族,继而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开始被称之为“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国民党一大宣言民族主义对内方面的表述存在高度妥协,与建国大纲又有很大差异,成为后来国共两党发生激烈争论的重要原因。(47)
通过国民革命,“少数民族”与“弱小民族”被当做中国非汉民族的统称,同时存在于国共两党的文件中,但双方对它们所指对象的认识,都具有较大的模糊性,对象、意涵等仍未固定。
三、抗战前十年中国人的“少数民族”观
“九·一八”事变后,康藏纠纷仍持续不断,新疆“四·一二”事变和内蒙古自治运动接踵而至,借鉴苏联和欧洲的民族问题理论,制定专门的民族政策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将苏俄民族理论引入中国时已引起激烈争论,时人对欧洲“少数民族”与国际“弱小民族”又常混淆不清,进而深刻影响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知和相关政策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问题,所用“少数民族”概念则有其独特的时代内涵。(48)
1928年7月,中共六大确立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政纲,通过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大会“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49) 六大通过的党章规定,在少数民族“当地”党部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部”,“在当地党部指导和监督下工作”。(50) 这是“少数民族”一词第一次写入党章。
为贯彻六大精神,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组织问题中专门提出“少数民族问题”,认为它极重要,“如上海的英美日等国人民,及印度,安南,朝鲜,台湾人民,‘满洲’的朝鲜及日本人,山西,顺直的蒙古人,四川的藏人,甘肃的回民,云南的苗族等。安南只有中国华侨支部而无安南党,马来岛、菲律宾亦是如此”,要求“各地党部应特别注意调查他们的生活状况及风俗习惯,以供给党关于少数民族策略决定的材料”。(51) 此处所指“少数民族”分为境内和国外两大部分,及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有关民族问题的具体决策,就只针对境内了。(52) 纲领性文件和政府决策的规定以及机构建置的制度保证,使“少数民族”的意涵、对象趋于相对固定。
日本学者松本真澄认为:“满洲的朝鲜人的祖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下,因为他们本来应该是实现独立的nation(民族),所以用中国共产党原有的把共同居住于国内的ethnic群体作为对象的民族理论是无法解释的。”而“满洲”朝鲜人的抗日意识和运动,与共产党的反帝斗争革命路线完全一致,考虑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将来是否拥有独立国家的问题,自然被提上日程,因为六大虽“承认民族自决权”,“却未触及任何民族,没有详细说明承认哪些ethnic群体的自决权”。(53)
以上分析有助于理解共产党把东北的朝鲜人纳入“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原因,但不能说明为何将“上海的英美日等国人民”等都称作“少数民族”。事实上,共产党所指的国外“少数民族”,就是国际“被压迫民族”或“弱小民族”,以及在华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员和组织。1927年2月,针对上海韩国同志会十余人请求编入中国党部,而上海区委长期置之不理的情况,瞿秋白就批评说,民族问题不但具有“政治上的总意义”,“亦是党的程度之测量表”。(54) 此后,共产国际不断强调东北地区的高丽人,以及安南革命斗争等对共产党的重要性。(55) 1930年3月,中共中央在给云南省委的信中指示,“党的发展”应该设法深入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去,“尤其重要是越人”,强调要“在安南工人群众中建立强国的基础”,“与安南党建立兄弟党的良好关系”。(56) 满洲省委的“少数民族委员会”,工作对象即在当地的韩国民族。(57) 1934年1月,毛泽东列举的“少数民族”,其中就包括“高丽人,安南人”。(58)
与此同时,国人对国际“弱小民族”和欧洲“少数民族”的认识,也陷入模糊。前者是指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如朝鲜、印度、安南、阿富汗、波斯、埃及、菲律宾以及中国等。然而,1930年国联开会讨论欧洲少数民族问题时,“北平所有一切的大小报纸,无一不大书特书记载着国际联盟讨论弱小民族问题”。“少数民族与弱小民族绝对不同,今竟视为一体”,“认为是一个东西”。(59) 胡愈之也指出二者截然不同,“譬如中国人是弱小民族,但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不能称为少数民族。在波兰境内的日耳曼人是少数民族,但绝不是弱小民族”。朝鲜亡国后加入日本国籍,成为日本少数民族,但在华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因未取得中国国籍,不能称作少数民族,只能称为外侨。(60) 其实,即便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取得中国国籍,也不符合他所说的少数民族的定义。就此而论,胡愈之的认识同样带有模糊性。
认识到这些概念存在差别者对此则区分看待。张明养说,国际关系中的少数民族并非泛指,而仅指欧战后形成的少数民族,他们既与“弱小民族”不同,也与旅居国外的“少数侨民”各异。苏联实现了民族平等,并无所谓少数民族问题,欧洲多数国家的做法却与苏联相反。(61) 此话背景是,1934年波兰在苏联即将加入国联之际提出少数民族保护条约应普遍化,遭到反对。胡愈之说,苏联不签订此种条约,乃因境内没有少数民族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以一个民族为统治主体,少数民族往往处于被压迫地位,苏联人民则不因种族、信仰、语文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在苏联,既无所谓多数民族,自然更无所谓少数民族了”。(62)
然而,事实要复杂些。欧洲的少数民族,逐渐形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曾经建立民族国家,随领土割让归入他国。第二种,未曾建立独立国家。表面上看,后者较为单纯,不具有国际性。但事实上牵涉广泛,往往超出一国范围,犹太人问题即显例。当时有人指出,不能因为两者表面的差别性,而抹杀背后本质的统一性,“即整个欧洲少数民族问题乃是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不过,亦不能因而“把欧洲‘少数民族’与‘弱小民族’相等”,否则将是“滑稽的”。(63) 从苏联和东欧相邻各国各族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趋势看,苏联境内波兰人、犹太人等的待遇问题,归入欧洲少数民族问题的框架来理解亦无不可。
中国的国情与欧洲、苏联有着本质区别。中国现代各民族的祖先绝大部分共同栖息在中国版图内,早已彼此往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互有征伐、平等交流和自然融合,循环演进,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同属中华民族。193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煽惑蒙、藏、回诸族脱离中国以及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的阴谋,国人纷纷表示愤慨和担忧。有人认为,应当慎用民族概念,否则正中帝国主义利用民族自决口号分裂中国的阴谋。著名学者顾颉刚即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视汉、满、蒙、回、藏等为文化差别,而非民族不同。(64) 既然如此,从逻辑上讲,自然便无“少数民族”。
另一部分人则持不同看法。如地理学家王成组认为,民族差别不必一定妨碍国家领土完整,欧美多民族国家比比皆是,东欧少数民族问题更闹得沸沸扬扬,其中确有引起分裂者,但多数不然。“中国境内的民族,以人口论,汉族早已占有特殊地位,非汉族的各支合计不足百分之二。这样小小的百分数,无论看做少数民族,或是属地民族,都不会显得严重,何以竟会引起分裂的危险?”日本自己清楚中国东北地区人民不能尽称“满洲人”,却造出“满洲国人”的怪名词。冀东自治阴谋,更与民族立场无关。只是在内蒙,利用了民族隔阂而已。他并不反对将蒙古人、“满洲人”、西藏人等一律称为中国人,但认为若忽视各民族间的差异与分别,事实上有许多不便,只有认清各民族特性及其特殊环境,才能对症下药。“以事实论,中国的民族不容易完全同化,也不宜于绝对同化。因此名称的差别,不必避免,也不能避免”,若纯粹为了消除政治上的流弊而否认此点,所定政策不仅不能取得实效,反而可能引起反感。(65) 两种观点虽然都旨在保持中国领土完整,但思考问题的角度则刚好相反。
一般人使用“少数民族”概念时,通常并未察觉观念背后的复杂性,因而较为随意。后来反对用“少数民族”称呼国内民族的张其昀,在1935年时认为,中国各族互相同化了的即“汉族”,占绝大多数,反之即“少数民族”或“幼稚民族”,二者共同混合成“中华民族”。(66) 时人多以“所有非汉民族”为少数民族的对象,但也有不同看法。洪恩齐谓我国的民族群,“除汉族之外,还有其它民族,其中人数最多的要算蒙古族、西藏族、突厥族和满洲族。这四个民族和汉族合称中华民国的五族。五族以外还有人数较少的民族,分布在各地方”。(67) 民初以来,“五族共和”口号广泛传播。以“五族”以外的族体作为“少数”的民族范畴,显然是“五大民族”观念的逻辑发展。
不过,既然现代民族理论源自近代西方,使用民族概念不可避免会受到外来观念的影响与制约,回归国情就必须先区别中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致力于实现孙中山晚年提出的,团结国内各族融和成为一个新中华民族的理想,有意限制和消解分别国内民族的思想意识。(68) 为了消除共产国际的影响,1929年国民党三大确立总理遗教,有意避开一大宣言,处理国内民族问题仅以建国大纲为准则。随后,又明确向蒙、藏声明不能实行苏俄式的民族自决。(69) 故而抗战前十年,罕见国民党称国内族群为“少数民族”。
国民党人还质疑“弱小民族”名称。1933年,南京政府命人草拟宪法草案。拟稿人吴经熊草拟的宪草中,有“国内之弱小民族应扶植之”(70) 字样。行政院参事吴颂皋批评说,虽然建国大纲有此规定,“实则国内各民族,既曰一律平等,当然不必再有‘强大’与‘弱小’之分别,这是很明显的事”。(71) “弱小民族”的对立面原是帝国主义,因为不欲被指责有征服压迫和强大弱小的歧视之嫌,国民党人后来较少用“弱小民族”指称非汉民族。(72)
由于共产国际的深刻影响,共产党在国内民族问题上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七·七”事变以前,共产党言论中的“中华民族”大多指汉人。(73)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主张汉族和少数民族联合成立统一国家,未提自决口号。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明确认为汉人和几十种“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八路军政治部编辑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在此基础上指出,“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74) 随着对多民族国家历史国情认知和把握的深入,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概念的认识和使用,日益体现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内涵,而突出了族别性人口少数的直观意思。
四、结语
近代中国人使用的“少数民族”概念,主要有清末排满革命思潮,一战后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条约”,以及共产国际的民族与殖民地理论三种主要的思想来源。它们原本渊源各异,意涵有别,通过混同使用,内涵外延交叉影响。今人或不难正确理解与区分,当时人能明了各自渊源者,尚有所区别对待,对中外国情相对隔膜者,则往往等同理解。后两者作为国家关系的内容,多伴随国家分化组合与领土分割,均适合民族自决原则。欧洲“少数民族”和所对应的多数民族分属不同的民族群体,相互间的历史关系没有发展出共同的民族认同;共产国际所指的“被压迫民族”或“弱小民族”,对立面是资本帝国主义,反映的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而我国现代各民族的祖先绝大部分共同生息在中国版图内,早已彼此往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互有征伐、平等交流和彼此融合,循环演进,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同属中华民族,如果全盘套用这些外来民族理论,必然削足适履。
清末时期,“少数民族”被汉人泛指中国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受排满革命思潮影响,又具体多指向满族,原本带些蔑视和排斥意味。或许由于这种“他觉”缘由,在相当长时间内未见被指称者有此认同。国民革命期间,“少数民族”被写进国共两党共同制定和遵循的国民党一大宣言,结合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开始被广泛使用。抗战前,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认知大体形成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主张将国内各民族进行区分,并有“汉族”与“少数民族”之分,在此基础上再将所有民族统称为“中华民族”;另一种是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国内不作民族区分,力图避免以欧洲、苏联的民族问题理论衡量中国。两者都旨在维护保持国家领土完整,但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全面抗战爆发后,国人整体上从国际视野转向本国国情来认识和处理本国民族问题。至于如何真正回到国情借鉴外来民族理论,找出适合自己的道路,依然有不同的声音。
注释:
① 有学者曾追溯“少数民族”概念的首先使用者和相关文献背景,对本文颇有启发,参见金炳镐:《我国“少数民族”一词的出现及使用情况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年第4期;韩锦春:《试论我国辛亥革命前在民族理论上的一些思想观点》,《民族研究》1987年6期。
② 拙文《国民革命与少数民族问题》(《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考察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少数民族”概念的由来,它与“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概念的异同等内容,因论述需要,本文还将涉及这一问题。
③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作为自我认同的民族符号,得到中国人空前一致的认可,国人整体上从国际视野转向本国国情来认识和处理本国族群问题。对“少数民族”概念的认知及争论的重心,相应发生转变。自1905年出现到1937年,可作为考察“少数民族”概念演变相对独立的时间阶段。有关“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参见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④ 参见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
⑤ 参见韩锦春:《试论我国辛亥革命前在民族理论上的一些思想观点》,《民族研究》1987年第6期。
⑥ 精卫:《民族的国民》,恂如编:《汪精卫集》第一卷,光明书局1929年版,第4-10页。
⑦ 参见孙宏云:《汪精卫、梁启超“种族革命”论战的政治学背景》,《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⑧ 参见[德]伯伦知理著、吾妻兵治译:《国家学》,善邻译书馆·国光社1899年版;[日]高天早苗译、朱学增等重译:《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商务印书馆1907年版。
⑨ 参见精卫:《民族的国民》,恂如编:《汪精卫集》第一卷,第5页。
⑩ 参见陶亚民:《民族之意义》,《地学杂志》1917年第2号。
(11) 参见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第2册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影印,第75页。
(12) 参见精卫:《研究民族与政治关系之资料》,《民报》1907年第13号。
(13) 参见何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50-951页。
(14) 参见章炳麟:《正仇满论》,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95页。
(15) 参见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第二章《人种之别》,上海东文学社1899年版(原书无页码)。
(16) [日]中西牛郎著、上海普通学书室译印:《支那文明史论》,1902年版,第3-4页。
(17) 蔡元培:《释仇满》,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78-680页。一说该文为章士钊所作,存疑待考。
(18) 邹容:《革命军》,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5页。
(19) 参见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民报》1906年第3号。
(20) 陈天华:《绝命辞》,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6页。
(21) 《黄孑民综论中国志士之党派》,《经世文潮》1903年第6期。
(22) 参见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23) 罗福惠主编:《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论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24) 杨度:《金铁主义》,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0-371页。
(25) 参见宋教仁:《清太后之宪政谈》,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页。
(26) 参见恨海(田桐):《满政府之立宪问题》,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549-550页。
(27) 参见卢信:《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罗福惠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8) 参见杨思机:《国民革命与少数民族问题》,《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
(29) 参见朴庵:《二百六十年汉人不服满人表》,《中国革命记》第一册,上海时事新报馆1911年版,杂录第1页。
(30) 佚名:《袁世凯尚敢言和乎》,《民立报》1911年11月20日。
(31) 参见耿夫:《是可作亡清纪念品也》,《民谊》1912年第1号。
(32) 参见张其昀:《“少数民族”名词的纠正——并论中国边疆问题》,《申报》1946年3月24日。
(33) 竺可桢:《欧战后世界各国新形势》,《竺可桢全集》第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7页。
(34) 参见[美]鲍曼著、张其昀等译、竺可桢校:《战后新世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译者序第11页。
(35) 参见严继光:《欧洲少数民族问题》,《民族》1934年第2卷第1期。
(36) 参见《欧洲媾和草约之概要》,《申报》1919年5月10日。
(37) 参见《对奥和约记》,《申报》1919年6月3-4日。
(38) 1919年9月10日签订的对奥圣日耳曼和约,第三部分“欧洲政治条款”第五项为PROTECTION OF MINORITIES,第69条第一句话规定:“Austria agrees that the stipulations in the foregoing articles of this section,so far as they affect persons belonging to racial,religious or linguistic minorities,constitute obliga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and shall be placed under the guarantee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参见奥地利外交与贸易部档案。Treaty of Peach between the 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s and Austria; Protocol,Declaration and Special Declaration(St.Germain-en-Lay,10 september 1919).http://www.austlii.edu.au/au/other/dfat/treaties/1920/3.html。2010年12月25日引用。
(39) 参见《协约国对奥议和之条约》,《大公报》1919年6月5日;《对奥和约内容》,《晨报》1919年6月5日;《协约国对奥媾和之条约》,《益世报》1919年6月8日;《对奥媾和之条约》,《盛京时报》1919年6月7日。
(40) 参见《签定对奥和约之情形》,《时事新报》1919年9月15日。
(41) 胡愈之:《少数民族问题》,《胡愈之文集》第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19页。
(42) 如颜惠庆主编:《英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08年初版,1935年3月缩本初版,第1448页。
(43) 参见[英]华尔脱斯著,汉敖、宁京译:《国际联盟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53页。
(44) [美]培德氏原著,石泉谭震泽、宁远杨钧译辑:《巴黎和会实录》,寰球书局1919年版,第146、197-200页;[美]狄隆著、秦翰才译:《巴黎和会秘史》(下卷),世界书局1921年版,第164-180页。
(45) 王孰闻:《劳农政府治下的俄国》(续),《晨报》1919年4月26日。
(46) 参见张国焘:《俄国革命六周年纪念与中俄关系》,《晨报副镌》1923年11月8日第248号。
(47) 详情可参见杨思机:《国民革命与少数民族问题》,《学术研究》2009年第12期。
(48) 有人注意到当时共产党使用不同概念称呼“少数民族”,但并未分析其缘由。参见金炳镐:《我国“少数民族”一词的出现及使用情况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年第4期。
(49)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7-88页。
(50) 《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87-88页。
(51)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讨论组织问题结论》,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09页。
(52) 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66页。
(53) [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168页。
(54) 瞿秋白:《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4-545页。
(55)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56) 《中共中央给云南省委的信》,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117页。
(57) 参见初兴佳主编:《中共满洲省委八十周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98-201页。
(58) 参见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210页。
(59) 鸿:《弱小民旅[族]与少数民族》,《三民半月刊》1931年第5卷第9、10期合刊。
(60) 参见胡愈之:《少数民族问题》,《胡愈之文集》第三卷,第319页。
(61) 参见张明养:《少数民族问题与边境政治学》,《中学生》1934年第49号。
(62) 胡愈之:《少数民族问题》,《胡愈之文集》第三卷,第324-325页。
(63) 迺莒:《欧洲少数民族问题》,《新创造》(北平)1935年第2卷第4期。
(64) 参见黄天华:《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抗战前后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4-1061页。
(65) 参见王成组:《国难期间之中国民族问题》,《华年周刊》1936年第5卷第39期。
(66) 参见张其昀:《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竺可桢等著:《科学的民族复兴》,中国科学社1937年版,第38页。
(67) 洪恩齐:《国境内各民族的地理分布》,《大公报·史地周刊》1937年5月28日第138期。
(68) 详见杨思机:《以行政区域统驭民族:国民党国内民族政策管窥——兼谈国民党对西南夷苗请愿的处置》,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庆祝中央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第二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论文集》,2011年5月,第517-525页。
(69) 参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15页、765-767页。
(70) 吴经熊:《中国制宪史》,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第796-797页。
(71) 吴颂皋:《读了所谓“民族之拥护”与“民族之培养”以后》,《时代公论》1933年第65、66号合刊。
(72) 立法院修正的各种宪草初稿,就再未见“弱小民族”一词。参见吴经熊:《中国制宪史》,第891、924、957、979页。
(73) 参见[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第203-204页。
(74)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第625-626页,第807-8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