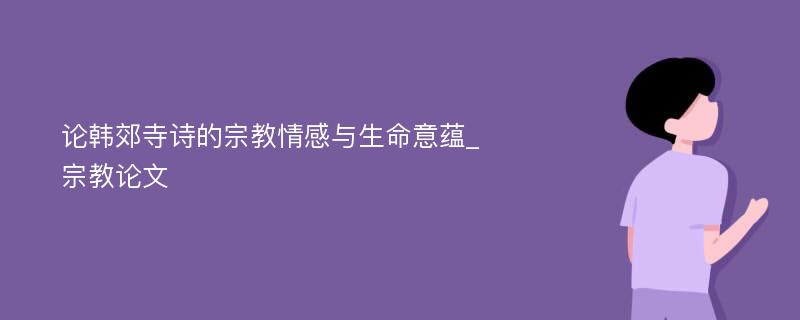
论汉郊庙诗的宗教情绪与人生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宗教论文,情绪论文,人生论文,论汉郊庙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词 古典文学;汉代;郊庙诗
宗教想象与艺术想象、宗教的理性情绪与艺术的感性精神相融为一,在史前期是普遍的现象,这从仍然流传的古代神话中多少可见其端倪。由于人们祀神时必须借助一定的形式娱神和自娱,使宗教与艺术联姻。宗教离不开艺术,而早期艺术不是,也不可能是为艺术的。人们在以不自觉的艺术表现寻求心理上的功利满足的时候,面对浩浩长空、茫茫大地以及已知、未知的世界,通常表现出宗教的热情。在社会与自然的困扰中,人们正是从宗教憧憬中得到精神的寄托和安慰,把它视为力量的源泉。宗教与艺术在先秦时期交织表现在诗、乐和舞中,而这三者又是难解难分的。成熟的诗歌读本《诗经》同时为乐歌是公认的事实,经过屈原艺术处理的《九歌》曼歌曼舞式的祀神、娱神是典型的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诗人把对于祖先、神灵的崇拜,无形中演化为艺术创作的热能。当然,不是所有的宗教行为都要借助艺术来表现,借助艺术者有它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民情风俗的因素。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宗教指的是原始宗教。
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从诗歌的艺术表现中,可以感受到它们产生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意识状态。稍作审视,可以知道,传说中的少昊之际,民神相杂,家为巫史、享祀无度是最初的宗教行为和意识的表现。然至西周,原始宗教明显沾染了政治色彩。神的多元化,祭神和祭祖的联系——祀后稷以配天,祀文王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助祭——以人的切实行为突出了神的地位。神与人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在创造神的时候,赋予神类似人的生活、人格和意志,从而使神在本质上是人自我的表现。和这相一致,神的君临下界,并借统治者来实现,自然地使原始宗教意识和行为主要从统治者身上得到反映。汉承秦世,楚汉相争未决,刘邦知秦祠白、青、黄、赤四帝,声称天有五帝,“待我而具五”,于是立黑帝祠,并因自己重祀敬祭,令天下百姓按时祭天帝与山川诸神。祭祀并非以牺牲为礼即足,祀神而娱神的传统延续到汉,产生了后人所称的郊庙歌。
作为汉诗一支的郊庙歌被蔡邕称为《郊庙神灵》,被郭茂倩视为郊庙歌辞,是典型的贵族乐府。汉代的郊庙歌相传有五种:《宗庙乐》、《安世房中歌》、《昭容乐》、《礼容乐》、《郊祀歌》。今存只有《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
《安世房中歌》原名《房中祀乐》,汉惠帝时改名《安世乐》,班固《汉书》照录时,定名为《安世房中歌》,相传是汉高祖刘邦的妃子唐山夫人所作。它与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等人所作的《郊祀歌》有所不同,《安世房中歌》是庙祀之歌,《郊祀歌》则是郊祀之歌。
人们崇拜宗教的心灵作用和主观意识,使语言表现是苍白乏力的。《安世房中歌》的宗教崇拜主要体现为具有伦理、政治意识的祀祖敬天情绪。诗中对于孝德颇有溢美之意。孝德原本作为儒家所重的伦理行为和规范,有着巨大而广泛的社会作用。但在《安世房中歌》中,因其所祀的对象不是现实的人,而是超越了现实的死者的灵魂,又通过死者的灵魂来表现活生生的人带有某种功利的思想,使其染上了宗教的色彩。宗教崇拜是在强化崇拜者自身的意识和行为,《安世房中歌》突出地颂扬了皇帝的品性和武功,确实折射出惠帝及其后的最高统治者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诗中出现的“帝”,同时是宗拜者精神的、物质的偶像。诗的16、17章分别写道:“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子孙保光。承顺温良,受帝之光。嘉荐令芳,寿考不忘。承德明德,师象山则。云施称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乐,受福无疆。”这里的“帝”有双重涵义,一指自然的天,二指帝王。西周已开以帝王配天的先例,天作为已逝帝王的象征而存在,与民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上面可以看到,祭祀者是从福、寿来感受祖先的力量,并在崇拜祖先中充满了钦羡、企慕的情怀,使诗中的“帝”作为宗教映象有了真实的意义。宗教映象在本质上是人为的精神虚象,但诗人在表现的时候,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超现实意义的现实心理特征,并在所谓的“承帝之明”、“承帝明德”中,赋予了“帝”物质的生命。正因为如此,崇拜者才能得到心理的补偿或心理的平衡。
“乃立祖庙,敬明尊亲”。《安世房中歌》作为庙祀祖先之歌,诗人的宗教情绪在歌颂祖先中得到渲泄,诗人的宗教意识在歌颂祖先中得到表现。作为宗教偶像的“帝”似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它高凌于尘世之上,以超人间的灵光照耀着人,人显得那么弱小,仿佛只有依靠它的力量,才能够拓展自我的生活道路。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是强大无比的神,另一方面是弱小无比的人,靠人才得以实现的神成为人的庇护者,越是这样,人的宗教情绪就越强烈。
《安世房中歌》意耿耿于已逝而被神化的皇帝,《郊祀歌》则有较为广泛的内容。《郊祀歌》19章,语意晦涩,故司马迁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史记·乐书》)之说。但它们是祀神歌则毫无疑问。19章中,首章“练时日”是迎神曲,末章“赤蛟”则是送神曲。其主体分祀后土、春、夏、秋、冬之神,泰元、天地、太阳诸神。在如是的多神崇拜中,诗人因是奉诏而作,崇拜多神的意识也表现为帝王意识。诗里流露出的“百姓蕃滋”的思想,折射出普遍的民间情绪。很明显的是,诗人不重表现宗教形象,而把浓厚的宗教情绪贯穿在现实功利的欲求中。
在这里,春的枯槁萌生、夏的万物繁茂、秋的含秀垂颖、冬的草木凋零,都注意到季节的特征。其它的情形也大体相类。人们以对自然的体验去体验神,自然的超人力量演化为神的超人力量,或以超人的力量赋予用精神构筑的原始宗教之神。在众神中,尤尊的是天地之神,《惟泰元》写道:“惟泰之尊,媪神蕃禧,经纬天地,作成四时,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阴阳五行,周而夏始。云风雷电,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绪。”元尊是天神,媪神是地神。这里是对天神、地神们统治天地、造作自然的歌颂。《天地》一章,诗人以极大的热情表现了对天神、地神的崇敬,铺排了祀神、享神的华美、宏大的场面以及祭祀者欣喜的情景,“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祀神、娱神的景象宛然目前。祀神、娱神的兴盛,使郊庙歌中的宗教映象得到显示;而华辞丽藻、歌舞繁会的艺术表现,使郊庙歌自有其特色。
二、以孝开数百年家法与成仙的憧憬
郊庙歌里的宗教映象以人的人生情绪和意识为内蕴,是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迷惘状态中的反映。按理,它与人的理智和情感不相容。然而,在郊庙歌中,人的理智和情感不断得到表现。如在祀日神的《日出入》中,以表现神与人的娱神情绪暗示神不同于人:“日出入兮安穷?时世兮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兮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兮冬非我冬。”太阳东升西落,春夏不同于人间的春夏,秋冬不同于人间的秋冬,它们的生命是无穷的,人的生命则是有限的。相形之下,有着人寿有限的惆怅。本来,人的情感渗入祀神歌是必然的,但人对于人生的清醒认识而产生的情感远不同于迷惘中的情感。在宗教崇拜的表现形式中,人表现了现实中的自我,那么,宗教的意味就稀释了。《日出入》是如此,而武帝把歌颂天马、灵芝、白麟等内容引入郊庙歌,也是如此,这不仅冲淡了郊祀歌的宗教情绪,而且可见祀神的非严肃性。
就《安世房中歌》与《郊祀歌》的宗教情绪论,二者有不同的趋向。前者,神高居于上,显现出宗庙的肃穆和人的崇敬;后者,神降临于下,显现出自然的散漫和人的欢娱。本来,二者用途不同,自然导致它们蕴含的宗教情绪的差异。然而,诗里的宗教情绪以人生情绪为本质,揭示了这种差异的关键所在。《安世房中歌》产生于西汉初年,而《郊祀歌》则产生在西汉中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氛围,培养的人生情绪就不相同。
西汉高祖之际,“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大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人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汉书·礼乐志》)。从这里可以窥见的不仅是宗庙之乐的运用,而且可见西汉初年对祭祀祖宗的重视。西汉以孝治天下,尤以汉初为然。刘邦贵为皇帝,享有天下,就认为父子相亲是人道之极,以天下统一、平安为父亲教训的结果,故尊父亲为太上皇。而他又是“重祠而敬祭”(《汉书·郊祀志》)的人,不可能不把道德意识引入祭祀活动。《安世房中歌》以孝德为宗,反复表现“孝”及其功用,并把它集于皇帝一身。如说“大孝备矣,休德昭清”;“大矣孝熙,四极爰臻”;“清明畅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抚安四极”等等,无一不首先是具有宗教意识的人生观念,然后施用于社会政治。而孝就其自身来说是敬、养以及忠实于父辈、祖辈,父、祖“仙逝”以后,则演化为神灵,继续他们生存时对后代的庇佑,所谓“受帝之光”、“承帝之明”等就有这方面的意义。“孝”本身的血缘凝承力,使诗中所称的皇帝之功,在名义上成为先祖之功。然而,祭祀中的先祖毕竟是虚幻的存在,尽管其自身也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凝聚力,但更多的是祭祀者主动赋予的。当祭祀者以貌似谦和、实则欣然自得的神情祭祖的时候,也是在颂扬他们自身和生活现实。以孝德自誉“竟全大功,抚安四极”,“乌呼孝哉,案抚戎国”,在于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和人对道德的依附,以致社会应该是道德社会,人生应该是道德人生。这样,《安世房中歌》的人生情绪就在以自身为前提的情况下超越了人自身,使人与社会融为整体。这种思想虽不源于汉,倒也符合汉初的大一统意识,并影响于后。沈德潜曾评价它:“首云大孝备矣,以下反反复复,屡称孝德。汉朝数百年家法,自此开出”(《古诗源》)。
汉初,经历频仍的战乱,民贫国疲。“文景之治”是随之而来的重要经济恢复时期。武帝承之,以卓越的文治武功使西汉有了空前绝后的鼎盛。较之于以前的几位国君,武帝具有浓厚的崇神意识和趣味,自我也因迷恋人生而陷于对神的极端向往。武帝即位之初,就特别重视祭祀鬼神,他采纳毫人谬忌的建议,以天神“泰一”为尊,供奉郊祀。然而,他对神的礼遇,不仅有一般人对神的顶礼膜拜,且具有一般人很难办到的自我神化。他力图使自己既是精神上的神,又是物质上的神。在他之前,秦始皇有过疯狂地寻求仙人,以使自己成仙的意图和行为,汉武帝则信任方术之士李少君、少翁、栾大等人,有着类似或超越秦始皇的疯狂。其中作祟的有原始宗教情绪的冲动,主要则是人生情绪的强烈表现,并与前者呈交融状态。在武帝,祀神的人生情绪远胜于宗教情绪,是因为他把神视为真实的存在,能够援引人成为神。公孙卿曾对他说,神仙无求于人主,人主求之,“其道非少宽暇,神不来。言神事,如迂诞,积以岁,乃可致”(《汉书·郊祀志》)。于是,各郡国都清除道路,修整宫馆,名山神祠,以待神仙的降临。武帝曾听取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间,董仲舒的天人相合理论在客观上促动了武帝对神的向往。《郊祀歌》19章的享神,既是祭神,又有希望神降临的心态,并且在“日出入”里还蕴含了人生短促的深切感伤。这正是《效祀歌》祀神最基本的人生情绪。人生是短促的,武帝君临天下,硕大无朋的权势,奢侈豪华的生活使他对人生短促认识得更为深切,求仙以预于神列就更为急迫。他以咏大宛的“天马”——汗血马入郊祀之歌,把它视为太一神所赐,有着文颖说的“武帝好仙,常庶几天马来,当乘之往发昆仑也”(《汉书·礼乐志注》)的动机,这就使他至少是一度或者常常脱离人的社会性,追求个体的、永恒的生存。人不可能脱离社会,也不可能成为神仙,但在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和情绪的冲动下,不能不说是对人自身的清醒认识,求神的迷惘在于看到人终会归于虚无。这与《安世房中歌》的人生情绪迥然有别。
三、为敬乃娱神,因娱而敬神
祭神少不了要娱神,汉祭高祖、文帝、武帝除均奏《文始》、《四时》、《五行》外,还各有舞曲。郊庙歌合乐而奏或唱,自然具有敬神与娱神的双重性。按理,敬神是为敬乃娱,娱神是因娱而敬。汉的郊庙歌,《安世房中歌》重在敬神,《郊祀歌》则重在娱神。
《诗大序》曾释颂:“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安世房中歌》在语言表现上虽比《诗经》的“三颂”远为活脱,但其何尝不是在“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呢?细审《安世房中歌》,内蕴的“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的成功喜悦,以传达自我的丰功伟绩和欣喜情绪,表达对神的崇敬。诗中所述的“成功”,当是高祖平定天下,具象为“四极爰臻”、“其邻翼翼”、“盖定燕国”、“案抚戎国”,不说这些均赖武力征伐,而以四邻倾服透露了孝德之治的伟力。这粉饰了自我,又沟通了人与神之间的必然联系,让神分享人的成功和喜悦。因此,《安世房中歌》在语言表现上具有欢快的基调:“劳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都荔遂芳,窅窳桂华”,祀神的环境装扮得这样华美、典雅。德则是“休德”,荐则是“嘉荐”。虽然说它为颂声,但摆脱了传统颂诗语言表现上的板滞、僵直,无论是四言、三言还是七言,都明快庄重:“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雀,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它所突出的是人的情绪与对行为本身的憧憬,只是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所谓水归大海,民怀高贤,在于强调对德治的倾心依附,出自怀德,才有心理上的愉快。而“冯冯翼翼,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慈惠所爱,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绰永福”,则以慈惠为天之则、人之则、治国之则,以求延长福祉。始终不离孝德,是《安世房中歌》的庄重所在,以此贯穿十七章,民服德,是民德与君德的相通;君以孝德敬神,是君德与神德的相通。君的中介作用,使民怀君德最终意味着怀神德,从而具有敬神的趋向。《安世房中歌》并非没有娱神的意味,它本身就是乐歌,使娱神的意味不言自明。而且诗的第二章“《七始》《华始》,肃倡和声。神未宴娭,庶畿是听。”就是娱神的具体表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以歌娱神,仍以敬为前提,“肃,敬也。言歌者敬而倡谐和之声”(颜师古语,见《汉书·礼乐志注》)。
《郊祀歌》19章所作的年代不一,譬如《天马》二章,分别作于元狩三年和太初四年,《景星》作于元鼎五年。其内容不连贯,风格不一致是可以理解的。其中,因有武帝所好而出现的内容的随意性,削弱了祀神的庄严。《宋书·乐志》曾说:“汉武帝虽颇造新歌,然不以光扬神考,崇述正德为先,但多咏祭祀见事及其祥瑞而已。”可见武帝在祭祀上的随和态度。《郊祀歌》不乏对神的崇敬,在祭祀中希冀神的庇佑。《朱明》祭夏神说,如果万物繁茂,则“广大建祀,肃雍不忘,神若宥之,传世无疆。”《惟泰元》祭泰元神,对其多有颂辞。然而,祭祀本身较多地蕴含了人与神情绪的交流,人要以自己的欢快感染神,使神也欢快。作为迎神曲的《练时日》以欢快的笔调描写神的降临,神的威仪、光彩的超凡脱俗,极容易使人产生欣羡的情绪。假如说,因其是迎神曲而具有娱神的特殊性,可置而不论。《天地》中的“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则明显地表现出把人之乐赋予神,使神在乐人之乐时自娱。
《郊祀歌》的娱神情绪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祭神中想象神之乐。《天门》所描写的月星灿耀的天界神境,《华烨烨》、《五神》的神游,都表现出神的高贵、轻盈和华美。也许因为如此,才使人产生跻身于神仙之列的玄想。其二则是以非神物娱神。武帝得大宛汗血马,自贵即足,却要把它与泰一神联系起来,认为它是泰一神所赐,作歌以入郊祀;斋房生灵芝,则认为是天气之精。这种牵强附会关键在于人心理上存在的对神的爱恋。
武帝不严肃的祀神态度在当时就受到主爵都尉汲黯的批评。汲黯认为王者作乐,当上承祖宗,下化万民,不宜以写诗为祭祀之乐,武帝很不高兴。他本来就立乐府,采歌谣,广收民间乐曲,不以庄重为意,以致其时的“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汉书·礼乐志》),可见武帝浓厚的娱神情绪。
话说回来,敬神在于自敬,娱神在于自娱。前者,统治者使自己的统治意识和地位得到强化;后者,在自娱中导致了乐府的悲剧。性不好音的哀帝即位以后,郑声尤甚,他以“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汉书·礼乐志》)为由,要罢乐府官,重新审定郊祀之乐,以剔除郑卫之声。后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的努力,乐府未罢,而罢了不合经法之乐和郑卫之声。由于没有重制雅乐取代郑卫之声在民间的地位,民间依然流传郑卫之声。
四、汉郊庙诗宗教情绪的反动
西汉思想观念总体上是从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过渡到以阴阳五行与伦理道德为支柱的新儒学。新儒学的定于一尊,本质上是求社会政治上的一统,加强民心的趋同。虽然说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互为感应理论在于强调人的道德或善的实践,但其中浓厚的神的意识与方术之士的仙人之说相一致,不同的是后者更贴近人生。武帝的成仙追求远离了原始儒学,也与新儒学不同。他身处儒学经化的时代,却在思想上超越这个时代,追求自我永恒的生存,并在娱神以自娱中,客观上又削弱了人对神的宗教性向往,突出了人的自身。荀子曾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这话不错。但应该注意到,人借乐自我表现或以乐感化人心,有着人本能的追求和意识的作用。通过郊庙歌来看汉初至武帝时代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存在持续、渐进而潜移默化的过程。结果是,汉哀帝在强制之下也无法改变人心的趋向。可以说,当人心趋于郑卫之声的淫乐,乃是人的社会责任感淡化,社会凝聚力松弛,一个王朝的解体就不可避免了。
一个王朝的解体,其思想意识不会随之消失是众所周知的道理。西汉末年,董仲舒的神学世界观与社会上流行的谶纬之说相结合,形成新的神学思潮。刘秀借武力与谶纬而登上东汉第一个皇帝的交椅,竟然“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汉章帝时,仿西汉宣帝石渠故事,召开白虎观会议,终成《白虎通义》,使谶纬神学成为官方哲学。尽管许多人迷恋于此,然而王充举大旗反谶纬,疾虚幻。后继者则有王符、仲长统等人。这一场思想界激烈的斗争旷日持久,王充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对于宇宙、人生等的认识自然过人,但不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谶纬之学也不是不涉及人生,只是以妄作的预言,把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引入了邪路。而能够比较普遍地反映人生情绪的仍然是诗歌。
东汉乐有四品,其郊庙歌沿袭西汉郊庙歌的精神,而今传的民间乐府和文人诗,则集中反映了时人对于人生的认识。不容否认,西汉的郊庙歌与东汉的民间乐府、文人诗因时代、作者、创作目的及功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然而,后者在继承前者人生精神的时候,走到了极端。
东汉乐府民歌、文人诗有三大主题:重视男女情爱、重视人生享乐、重视个体生死,从而与西汉郊庙歌中的宗教映象和对神的憧憬都决裂了。
在男女情爱中,主旋律是女性对男性的爱。如乐府的《上邪》、《长相思》、《古诗十九首》的《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都表现了缠绵悱恻、坚贞不渝的女性之爱。而在一些反映夫妻生活的诗如乐府的《艳歌何尝行》、《妇病行》、《焦仲卿妻》更是表现了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恋情。现实生活总是严峻的,在人生旅途上,男女相爱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但在当时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社会氛围里,男性突破这种观念表现了对女性的痴情。观念表现的本质是人们着眼于现实生活,以现实观照自我,以致在生活的大舞台上,演出生死相依的真切悲剧。人不恋生而恋死,不追求苦闷的、忧郁的生存,毅然赴渲泄情绪、满足情感的死亡,需要巨大的勇气自不待言,生活的真实与宗教意识确实难以吻合。刘兰芝死了,焦仲卿也死了。
而在重视人生享乐、重视个体生死的汉诗中,生活真实与宗教意识的不一致更为明显。重视人生享乐、重视个体生死具体地表现为人生如寄,所谓长生不老、生命永存不可信,企望成仙也不可信。“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应当饮美酒,披丽服,秉烛为乐。就人生论,这是消极、颓废的,诗人透切地认识人生,领悟出人生应当和不应当的生活态度与行为。只是他们都囿于自我的圈子,被忘却或被忽视的是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它的发展,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前行。但另一方面,在“服食求神仙”的社会气氛中,诗人没有背离生存的现实,去求永恒的生存,又有其进步意义。然而,这样一种人生观在抛弃神仙、注重自我的过程中,与宗教意识也割裂了。进而言之,人自觉自我生存的最终幻灭,并以诗歌来表现自我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情感,显示了宗教意识的幻灭根本上是人生的幻灭。
虽然“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汉书·郊祀志》,具有社会的普遍性,社会对于孝义的推崇以及无人无祖,在每个人心里都会有遗传或非遗传的印痕,借此表现自我的生活理想,自我在生活中的行为和遵循共同的伦理准则,但郊庙歌力图消抹人与神的隔膜,希求神赐福人间,终究不过是心理上的。它们具有某种现实意义的同时,也具有很大的非现实性,而其它的汉诗则在表现生活时完全保持了和神的距离。汉人感于哀乐,以诗抒情言志,以乐感化人心,移风易俗;汉诗除了《古诗十九首》和部分文人诗外,具有抒情言志和移风易俗的双重功用。因为诗歌内容上的差异,诗人意识趋向的不同,郊庙歌在宗教情绪中具有更多的理性,而且宗教意识中不无浓厚的政治成分,像《安世房中歌》对于孝德的注重,就突出了以孝德治理社会的一面。而《郊祀歌》则蕴含着一定的社会理想。
非郊庙歌没有表现宗教意识和情绪,这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是紧相联系的。诗人把现实生活和自我情感视为创作的源泉,在诗中表现现实和人生。不像郊庙歌本于现实,却在对现实作虚化、变形的表现时,升华到非现实的境界。于是,汉非郊庙诗宗教映象的幻灭就是自然的了。
需要说明的是,汉诗贯穿西汉和东汉,虽然两个朝代都以儒家思想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但二者的意识形态各有特色,并影响到诗人及其诗歌。东汉没有类似于西汉的郊庙歌,而东汉的祭神祀鬼一如西汉兴盛。在现传的其它诗中,主要是东汉诗,诗人们不以宗教情绪为本,表现的是他们的人生孤独,苦闷的真实难以演化为宗教情绪的虚幻,诗人有诗人的意志。
收稿日期:1994-0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