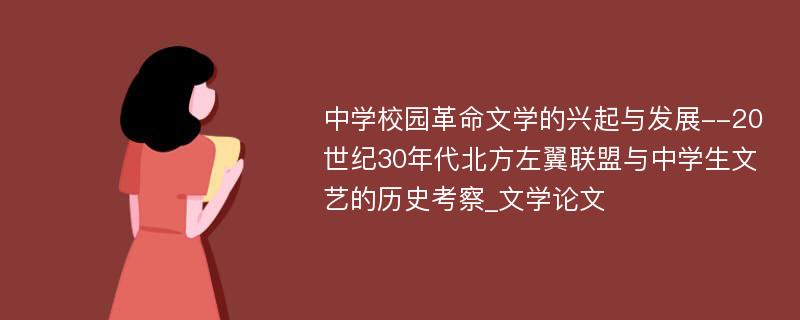
革命文学在中学校园的兴起与展开——北方左联与1930年代中学生文艺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中论文,中学生论文,文艺论文,年代论文,校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述及南北两地左联,其差异常被提起:上海左联多知名作家,北方左联“多数是大、中学校的青年教师(如潘训、张喆之等),而占最多数的则是大、中学校学生中开始从事文学写作的(如:于伶、宋之的、端木蕻良、王瑶等)”,“这群学生居多数的盟员,就组成了北方左联”。①此中透露的历史信息是,在北平这个城市,中学生和中学校园是左翼文学运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文艺群体和文化空间。但北平诸大学里有哪些左翼教师、哪些学生团体、哪些刊物,所记材料还不能算少,上述回忆中列举的学生就全是大学生;而左翼文学运动与中学校园的联系,则被一笔带过,难知其详。在左翼文学的历史图景中,包括普通中学、师范与职校的中等学校与中学生是怎样的存在,值得考察。
结社与办刊:中学生文艺团体及其精神空间
从最初的筹建到以后活动的展开,北平各左翼文化团体都与这座城市的中学校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聂耳主持的“北方乐联”成立大会是“借西四北面一教会女子中学二楼的教室做会场。这天从门口到楼口,都布置有女学生警戒”;②“平津木刻研究会”和“北平美联”可以说发端于艺文中学,许崙音、唐诃、金肇野等左翼青年不但让在该校任教的国画大家王青芳拿起木刻刀,自号“万版楼主”,北方左翼美术界的盛事“平津书画·版画联合展览会”、“木刻讲座”也都首发于这所中学。许崙音病逝后,熔炉社、平津木刻研究会、《庸报·另外一页》、《华北日报》艺术周刊社、北平漫画协会等革命文艺团体发起的追悼会亦是在艺文中学举行;北平左翼戏剧团体“呵莽剧社”和“新球剧社”的“演员多半是今是中学的师生”,剧社的负责人中陶也先和魏照风为该校学生,俞竹舟则是该校美术教师,而中学生陶也先同时也是“北平剧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③;“担负北方全部分的文化斗争的任务”④的北方左联在外地的分支机构中,较多被人提起的是天津支部和保定小组,而天津左联的缘起与中心无疑是南开中学,重要的参与者还有女师、甲种商业学校和中日中学等中学校园里的师生;至于保定,也常被看做一个文化城,时人也如此谈及这个小小的古城:“学校和学生在保定是占重要地位的。而所谓学校,也就可以说即是中学”,尤其是第二师范,“学生多注意于社会问题,造成了共党的大本营”。⑤也因此,保定左联小组中,徐盈在农学院读书,但与申春忆及当年左联旧事,他说“当时左联活动的中心不在农学院,而是在保定第二师范”。⑥梁斌在保定并未参加左联,但当时也是一位热衷革命文学的文艺青年。晚年他曾忆及保定二师的左翼文学活动:“1932年秋,第二师范曾成立了几个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世界语学会”,而且,“那时,青年人爱三五个志同道合的自己出钱办个刊物,在小书摊上代卖,也有自己拿着串斋卖的,一边走一边喊:‘九大枚一本……’”。⑦梁斌的回忆道出了1930年代中学校园里的文学风气,以及左翼文学在这一文化空间兴起与展开的主要方式:革命文艺青年的结社与办刊。梁斌所谓“志同道合的自己出钱办个刊物”也可看做以刊物为中心的文艺社团。保定二师的社团名称也颇具时代特征:1930年代的左翼学生社团多称为读书会、研究会或学会。
现代中国的文艺青年结社乃时代风气,而中学校园里文学社团的兴起自有其独立因由。1935年2月到3月,在《北方日报》副刊《长城》上,曾有一次规模不小的“中学生文艺论战”,参与者多为中等学校学生。在文艺对中学生有益还是有害的问题上,论战双方针锋相对,但有两点认识却颇为一致:一是“一般中学生都爱好文艺”;二是“怎样将正确的文艺传导于中学生呢?”对于这个问题,双方答案完全相同。北方左联下属团体泡沫社的张腾和乃光如是说:“诸君都以为唯一方法是在学校里组织文艺研究会,而使国文教员指导之”;“中学生应联合爱好文艺的同学自动的组织文艺研究的团体”。⑧
激进的中学生虽与校方多有矛盾,但他们对社团的诉求应该说普遍得到了掌校者的支持。论及现代大学,时贤常表彰蔡元培以大学校长身份“花那么多心思和时间在关心、支持学生社团”。⑨其实,民国大学校长、教授参与中学教育者颇多,大学教师也常兼职中学,在许多观念上大学与中学其实颇为相通。至少在支持学生结社方面,中学与大学似乎倒并无“根本区别”。南开校长张伯苓是南大校长,也是南中校长,是我们说明这一问题的好例子。张校长“对于学生课外组织、团体活动,无不协力赞助,切实倡导”,将张校长所指的学生,理解为南开学校之所有学生——大学生与中学生,应该不算过分。之所以如此支持学生结社,是因为在张伯苓看来,“国人团结力薄弱,精神涣散,原因在不能合作”、“识有个人,不知团体”,因此“鼓励学生自动组织各种社团”,目的是培养学生“通力合作,团结负责”的习惯与精神。⑩中国的教育家以“教育救国”为嚆矢,中学校园里的外国校长虽然与之教育理念并不完全相同,但同样鼓励学生课外结社。自1919年始在教会学校育英中学任副校长达三十年的美国人ErnestT.Shaw,从学生兴趣和锻炼学生“自动工作”的角度谈论学生结社的意义。在他看来,“无论如何精心设计安排,课程都远远无法满足学校内众多学生的兴趣”。比起课程与个人,课外的“社团更有助于学生发展自己独特的兴趣”,因此“学校采取鼓励学生结成正式或非正式社团的政策”。(11)自1929年至1948年,育英中学每年出版一册年刊,每册《育英年刊》中所记载的学生社团都有二十余个,而且这还只是校方组织或支持的“正式”社团。
鼓励学生结社不仅是中学掌校者的教育理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持。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等学校训育实施纲要》第七条规定:“指挥组织学生自治会及其他各种集会,以训练青年四权之运用。”(12)
学生渴求社团、掌校者鼓励、政策支持,学生、校方与政府有如此共识,当然会带来中学校园社团的兴盛。1922年江苏省立一中校长陆殿扬曾对全国20个省份的69所中学进行调查,学生组织与社团即是其调查内容之一。据其《各省中学校学生活动事业统计表》:69所中学共有各种形式的社团460多个,平均每校设立社团近7个。(13)而且,这些学生团体大多是学校组织,还并未包括爱好文艺的中学生自发结成的文学社团。而北平小报《中学新闻》则刊有大量中学文艺社团的消息,由此也可看出1930年代中学生结社的风气与特点:
市立一中高二文科的几个同学,见到了文坛的寂沉,同学们精神的散漫,于是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文艺团体——北园文艺社……因为学校的爱护,社里的经费还不成问题,现在他们正在努力着他们的处女作品——《北园》创刊号。
辅中一甲新组文艺社:课余文艺研究社。因经济关系,暂不刊印,仅将原稿置图书馆中,任人批阅。
各种研究社及文艺团体占大多数……成绩最佳的还是文艺团体……资格最老的健青社……每星期出一张壁报。(14)
社团需要精神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结社总是和办刊互相勾连。但校方虽然支持中学生结社,却不可能为每一个学生社团提供经费,资助其出版社刊。《中学新闻》提及的北园文艺社有校方提供经费,实属幸运,但并非中学生文艺社团的常态;梁斌回忆中所说的自费出版刊物,在中学校园常见,但难以持久;“将原稿置图书馆中,任人批阅”也是情非得已之事;而最廉价最方便的壁报应是中学生文艺社团最为常见的园地之一。同在北平市立一中,艺风文艺社就没有北园文艺社那么幸运:“高年级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近日合组一个壁刊,定名《艺风》,每两周发刊一次……完全用笔抄录,内容有诗歌、散文、小说等。”(15)
论及报刊,文学史家关注的是印刷文化,但在校园文化空间之内,手抄壁报可称是中学生文艺社团重要的文学生产方式,和最常营建的精神空间之一,在中学生群体的文学生活中占据着颇为重要的一章。只不过壁报一般只有一份问世,乃真真正正的“孤本”,在空间上传之不远,在时间上存之不久,当时既无深远影响,后世又难睹其貌,也就难以进入史家视野,但它毕竟是现代中国文学生活的一角,虽然我们只能借当事者的回忆想象壁报之于文艺青年及其社团的存在。日后以《红日》闻名的吴强有一段文字,详细追述了他中学时代的一个左翼文学青年社团和一份走出校园的壁报,值得引述:
我和正风中学“左联”小组的几位盟员姚木紫、徐碧山、张凌云、刘毅慈等创立的春风文艺社,办了一种墙头文学刊物《春风》,用整张的图画纸,由善写小字的刘毅慈同学书写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誊录发表的作品,当时已是知名作家的何谷天(周文)的短篇小说《热》,就发表在《春风》的第二期上。这个左翼的刊物,由徐碧山配以插画和美术报头,以它特有的内容和形式,受到读者们的热烈欢迎。在正风中学本校挂出之后,观看的同学很多,沪西其他中学知道了,便要求移到他们学校去悬挂;这样,这个墙头刊物,便在沪西中等学校里发生了广泛的影响。(16)
除却壁报,在中学校园与中学生文艺群体关系最为紧密的出版物是校刊。伴随新式学校而兴起的校刊这一出版物,确实堪称现代中国一道独特的文化史与文学史风景。校刊的作者群为本校师生,以学生为主体;主要发行于校内,全校同学人手一册,“如有愿意多得一份半月刊者,可出代价购买。代卖处:本校号房。……然购者仅限本校同学”。(17)除此之外,校刊也多赠送一些文化机关,以及与其他学校校刊交换。因此,现存下来的校刊封面多印有“请交换”或“赠阅”的图章,这也是校刊走出其“母校”的主要途径。不管是作者还是发行,局限于校园的校刊当然无法产生更大的影响,但对于校园内学生群体常态的文学生活而言,校刊无疑是其最易贴近和最为重要的文学生产空间。
前文我们曾引述张伯苓谈论南开学校的文字,在谈及学生社团之前,张伯苓还曾专门提及学校的出版:“学校为训练学生之写作能力,增加学生发表思想之机关,自始即鼓励学生编辑刊物,会有会刊,校有校刊,或以周,或以季,种类甚多。”虽然对大多数中学而言,恐怕难有实力做到“会有会刊”和“种类甚多”,但若说1930年代凡稍有规模的中学即“校有校刊”也并非妄言。东北大学附中训育主任如此描述当时各校竞相出版校刊的风气:“近来国内各校出版物,几如汗牛充栋。不论其是季刊、月刊、半月刊、周刊、日刊,内容之优劣,暂且勿论,都有一种蓬勃之气象,活泼之精神。”而谈及校刊之于学校的意义,他的说法也许会让后人跌破眼镜:“国家强弱,系夫人才;人才盛衰,系夫学校;学校优劣,实有关乎校刊。”(18)风气如此,以至于南开女中的雷主任以为不出版校刊,则“女中在天津各校有落后的嫌疑”。(19)
除去偶有的例外,如北平温泉中学的《谷光》、潞河中学的《协和湖》,校刊基本以校名命名,大多属综合性刊物,常常发布学校通知、刊载校闻、通报图书馆所进新书、以及各学科讨论等等。但无疑,校刊中占比例最大的是中学生的文艺作品。大同中学校刊《大同双旬刊》编者自我批评该刊内容“偏重文艺和缺乏理科稿件”,“这的确是个不好的现象”,但编者真正不满的却是“‘大同论坛’、‘书报评介’及‘剧本’都没有”稿子,也就是说编者真正想要的恐怕还是杂文、书评和剧本这些文学作品。(20)甚至像《协和湖》那样“办成纯文艺的”校刊也并不少见,当这种办刊倾向被批评为“是一个错误”时,编者回应说:“我们以为这话很对。但得声明,这期也还是纯文艺的。事实上这无办法。编者同人,老实说都是爱好文艺的。”(21)由爱好文艺的学生主持,也正是校刊的一个特点。
对于众多没有能力出版刊物的中学生文艺社团来讲,借校刊一角来建立自己的文学园地无疑是最佳选择。育英中学的“哪里去”文学社就是在校刊《育英半月刊》附出《哪里去文学社特刊》。史家一般将现代报刊分成三足鼎立的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和同人杂志,而校刊不属于上述任何一家,它有自己独特的运作模式。校刊并非面向社会的公开刊物,其作者是在校师生及离校校友,颇有自家园地,他人莫入的架势。大同中学的《大同周刊》即因被“认为本刊的稿件大多是校外的”而遭遇同学指责。(22)但在现代社会,不管是用有形的法规条文,还是用无形的俗成约定,欲将社团与刊物限制在一个狭小空间,也委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育英半月刊》就常登载艺文中学学生王云和(笔名耿明、君芜等)和吕奎龙的作品;而“哪里去”文学社的核心人物、《育英半月刊》的编者李景慈(笔名林慧文、阿茨等,在沦陷区北平文坛以笔名林榕名世)也常有文字见于《大同周刊》;王云和、吕奎龙和李景慈又与《大同周刊》的编者耶菲、颖灿等联合起来,走出各自的校门,共同主持小报《觉今日报》副刊《文艺地带》,直至结成在北方左联后期颇为活跃的文艺社团泡沫社。该社社长谷景生(笔名谷峰)是北方左联书记,主持社刊《泡沫》的谷牧(笔名牧风)为左联组织委员,而上述艺文中学、育英中学和大同中学的几位中学生不仅是泡沫社成立的基础,事实上也成了社团最重要的成员。原本封闭的校刊和校园难以彻底封闭,经由一份小报副刊、一个社团和对革命文学的共同信仰,中学校园与北平这座城市的革命文学史图景联系到了一起。
教育体制与国文教师
如陈平原所说:“风云激荡的思潮,必须落实为平淡无奇的体制,方能真正‘开花’、‘结果’。”(23)文艺社团在中学校园的兴起与兴盛,与教育者的教育观念有关,同时也与教育体制密不可分。虽然校园里激进革命文艺青年的欲求和体制多有矛盾,甚至他们自己制造着与体制的对立,但能在校园这一文化空间结社办刊,能有一方精神园地倡言革命与革命文学,“做不平之鸣”,“仗着固有的天真,用显微镜放大社会的一切原子,将所见所闻和由直觉所感受的,赤裸裸的喊叫出来”,(24)其实也首先得益于体制。简单说,学生社团与刊物的遍地开花也源于中学“选科制”与“训导制”或称“训育”的实施。
1922年11月,《学校系统改革案》以大总统令的形式颁布施行,其中“中等教育”项下第十三条规定:“中等教育得用选科制。”北平私立育英中学的选科会自我表彰的成绩就是中国歌剧研究会、国际研究会、文学研究会、英文文学研究会、新剧团、新闻团等各种学生团体的建立。(25)这些学生社团的形式是“学生自由加入,由校内外聘请专门人才分任指导”。(26)我们在前文提及的陆殿扬所调查统计的学生社团应该就是这种学校组织、学生加入、教师指导的学校“正式社团”。当然,其中文学社团的指导者就是该校的国文教师。1931年育英中学“新文学研究会”的导师即是在该校任教的诗人罗慕华。
虽是校方组织的“正式社团”,也不必想象成校方会以指导为名干涉为实。应该说,这些文学社团中的学生与导师依然自由选择着社团往“哪里去”。育英中学的“新文学研究会”就如此回应这个时代的文学走向:“青年们一听到新文学,便很容易想到‘Y姊’‘A弟’的肉麻文字;实则革命文学已占掳了新文学的重要地位,那种肉麻文字,早就为人摈诸文学之外。”(27)中学校园里革命文学的兴起,同罗慕华一样的众多国文教师无疑是其推波助澜者。
研究北方左联的日本学者近藤龙哉多次陈述一种意见:“北方左联的源流之一是在开封集中的一些人。”(28)此说是否成立姑且不谈,就我们的论题而言,构成北方左联“源流”的这些人的职业值得关注。近藤龙哉所谓集中在开封的人主要是指潘漠华、李俊民、招勉之和胡齐民。当时李俊民在河南省立第二师范执教国文,其余三人皆在河南省立一中任国文教员。应该说,这并非历史的巧合,因为如果对1930年代文艺青年的公开职业做一个调查统计,恐怕会以中学国文教师为最多,至少在以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左翼文学运动中确实如此。江风在回忆中曾谈起北方另一个城市济南的多所中学:1933年江风考入济南高中时,“胡也频、丁玲都已离济赴沪了,但那时留在该校教书的进步青年作家和学者仍然很多,其中有段耀林、陈翔鹤、张友松、王祝晨。另外,还有李何林、王冶秋和李俊民老师。山东其他学校也有,如何其芳在莱阳乡师教书,李广田在济南一中,陶钝、万曼在济南一师……”(29)由这份名录也可看出,中学校园里不仅聚集了众多文艺青年,而且不少是左翼文艺青年。开封、济南尚且如此,文化城的北平当然更不可能例外。潘漠华和李俊民到北平后,与北方左联的另一位创始人段雪笙皆任教翊教女中;同是北方左联创始人的谢冰莹当时在师大读书,但兼职安徽中学;北方左联执委陈璧如在艺文中学……而且,在北平各大学任教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在中学兼职也颇为常见,孙席珍、齐燕铭、傅克兴(原名傅仲涛,笔名非白)就都在私立大同中学教授国文。北方地区各中学的国文教师多左翼知识分子,“北方教联”功不可没。不同于上海,北平诸左翼文化团体中,“教联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
参加教联的还有许多是北师大的学生,他们在实习期间或毕业以后到北平的中学里教书,像宏达、志成这些学校里都有教联的同志。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公开宣传进步思想,讲抗日的道理,国民党特务一来,就讲点别的作掩饰。还有一部分教联的同志在北平呆不住了,就到大名、保定、太原等地去教书,有的在学校里当上主任教员,有的还当上了校长,在那里又团结起一批学生,建立进步团体,发展一批新盟员。(30)
国文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为文学史研究者所关注,从教科书切入是一条常见的思路。但问题是,民国期间自始也未有官方的统一教材,教科书的出版与编纂属于商业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因此落实到各校教学实际,对于各书局出版之教材,“或采或不采,大都任教员主张”。(31)可以说,体制的缺失为新文学与革命文学进入中学校园的文化空间留下了空隙,国文教师在课堂内外的文学活动也因此成了勾连文学与教育的关键之一。北方左联的丁浩川曾在蠡县高小“担任两个班的国语,我并不采用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审定的国语课本,而是把自己所喜爱的文章印发给学生做教材(别的国语教师也是这样做)”;与丁浩川同事的另一位国文老师同样“是从左翼文艺杂志或苏联短篇小说的译本上选取一些富有战斗性的短篇文章”作为课文。(32)丁浩川的学生梁斌也如此回忆自己的老师:“丁老师是崇拜创造社,崇拜郭沫若同志的。课文大部分选讲《创造月刊》和《太阳月刊》上的文章。”(33)育英中学的王元化似乎并不怎么喜欢母校,但弟子为其作传时,还不忘为其国文老师阎蕴之专设一节:“他教元化他们读鲁迅,还有一些翻译文章。元化觉得别的课都机械无趣,唯阎先生的语文,让他沉迷。”(34)
虽然站在纯文学的立场,有时贤称20世纪为“非文学的世纪”,但若从文学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着眼,至少20世纪上半叶其实也真正堪称“文学的世纪”。以中等教育而言,翻阅那一时段各校《课程标准》对国文教学的规定,也可看出那是文学与教育最为亲密接触的黄金时代。将欣赏甚至写作新文学列入教学大纲,用当今中学教育的眼光来看恐怕会觉得匪夷所思,而在当时却是司空见惯。辅仁大学附中《国文教学纲要》规定国文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有养成创造新语及新文学之能力”。(35)而且国文教学不仅被细分为精读和略读,甚至开设现在大学中文系专业课的中学也并不少见。育英中学有文学史专职教师,北平师大附中开设“学术文与文学文”和“文学概论”课。前者引导学生“读文学文,预养其阅读赏鉴之能力,备日后课余时,能以文学作品为良好之伴侣”;后者“设科用意”是“使学生明了文学与人生之关系,认识文学与时代之影响,并指导学生对于文学之创作、鉴赏与批评”,其教授内容为“对于新兴文学之研究,注重文学思潮之介绍,及建设批评之鹄的,不以一家一派之学说为限(如温齐斯特之《文学评论之原理》、韩德生之《文学研究导言》、厨川白村之《苦闷的象征》、本间久雄之《新文学概论》、及晚近卢那卡尔斯基之《文艺与批评》等,各有其立场与观点)”。(36)国文课在民国中学教育中一直是占学分最高、课时最多的重头课。(37)如此看待国文,又有如此实践,当然会激发学生的文学热情,以为“要想国文有进步,认识人生,可必得去爱好善美的文艺”,(38)由此造成了中学校园浓郁的文学空气,同时,也为左翼作家进入中学课堂提供了契机。
在中学校园如此的历史境域与机遇中,“语文教学,对一个进步教师来讲,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因为“它不像其他课程,要照课本传授,很少插话。语文教学则不然,教材可以选择,思想可以发挥。一个革命教师,他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时事以及革命文学等”。(39)虽然1930年代中学课堂内外的教学实际与文学活动已无法重现,但当时师生留下的众多回忆材料却为我们想象与重构历史现场提供了可能。季羡林对其中学老师胡也频的国文课堂有颇为生动的记述:
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只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孩子听得简直着了迷。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40)
韦君宜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每每提及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南开中学的国文老师田骢:“我们有南开中学自编的国文课本,同时允许教师另外编选。田先生就开始给我们讲上海左翼的作品:丁玲主编的《北斗》,周起应编的《文学月报》,然后开始介绍鲁迅,介绍鲁迅所推荐的苏联作品《毁灭》,还有《士敏土》,《新俄学生日记》等等。他讲到这些书,不是当文学作品来讲的。”(41)
年轻的左翼作家在国文课堂上热情张扬革命文学,其结果就是中学校园里更年少的革命文艺青年群体的产生。中学生的季羡林开始写作“革命、革命、革命之类”的《现代文艺的使命》以及“普罗”的《文明人的公理》;胡也频在济南高中的另一位学生冯毅之则追随老师参加了左联,流落到北平后成为北方左联的党组成员;潘漠华在开封的学生苏凡和耶菲也辗转到北平参加了北方左联;韦君宜的同学上了田骢的国文课,“看了左翼的书……就开始写开放的文章了”;大同中学的学生写文章则不忘“孙席珍先生的口头语”:“意志沃罗基”。(42)谈及北平私立大同中学,就我们所知,前期北方左联的成员徐盈就是在该校读书时由孙席珍介绍而参加左联的;而北方左联中后期,大同中学更是有了左联小组,组长耶菲,颖灿为该小组成员。(43)
除去课堂内滔滔不绝地传革命文学之道,作为国文教师的左翼作家于课堂外对中学生文学活动的组织同样值得关注,而这些活动的基本形式就是结社与办刊。开封河南省立一中的潘漠华、胡齐民与招勉之“推动爱读新书的同学组织读书会,高年级同学自动报名参加,一年级是由级任教师从每班各推荐两人参加”,潘漠华班上被推荐上去的就是耶菲。这个读书会后来被称作“寒诗社”,出版提倡普罗文艺的《火信》社刊。(44)胡也频在山东高中“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有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过节一样”,而且“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胡先生还没有满足,他准备出一个刊物”。
在上述回忆中,季羡林没有提到这份已不知刊名的杂志出版几期,抑或根本就未曾问世。不说学生,南开中学的四位国文教师田骢、万曼、戴南冠和姜公伟组成四月社,出版《四月》杂志,这份简陋的只有十几页的刊物也仅在五月出版两期。资金不足、缺乏发行渠道、只能在校园传播,再加上当局的查封,因此其生命也就难以持久,这是大多数左翼校园刊物共同的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校园刊物“同学们差不多都买来看了”。(45)钩沉考察这些文学史碎片,我们可以想象中学校园内革命文学的历史图景:一方面是校园刊物萧条寂寞的命运,而另一方面却是师生热情参与的革命文学在中学校园的兴起与展开:潘漠华等人在开封组织学生成立读书会,购买阅读上海出版的左翼书刊。学生“除了看书以外,还拼命写稿投到壁报上,写了便拿去请潘批改,然后发表在壁报上”;(46)大同中学的齐燕铭和傅非白不仅多次为校刊撰写文章,支持学生研究拉丁化新文字、介绍苏联革命文艺,甚至为校刊选择木刻插画并设计封面,可见其热心与投入;齐燕铭、赖亚力等教师还在大同中学组织学生成立健进读书会,指导学生阅读“艾思奇大众哲学,斯诺西行漫记等禁书”。(47)健进读书会的成员耶菲和颖灿也正是中后期北方左翼文坛最活跃的作者。
孙席珍在回忆录中曾谈及大同中学及其掌校者与北方左联的联系:“在国民党伪党部里边,也有个别比较开明的人士,如许孝炎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们表示同情,比如编印刊物等等,暗中也为我们开绿灯,给予一些支持、照顾;他曾主办过一所大同中学,那里有好几位师生是北方左联的盟员,他虽心知,却并未公然限制他们的行动。”(48)许孝炎,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1930年代任职北平市党部,国民党CC系属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北平分会副评议长,主持平津地区民族主义刊物《平明杂志》和《觉今日报》。由他掌校的大同中学不但有左联小组,该校校刊由左联小组长耶菲编辑,而且《觉今日报》副刊《文艺地带》也成了这个左联小组和北方左联下属社团泡沫社的文艺阵地。
在北平的左翼文学史图景中,不仅由国民党市党部官员掌校的中学与革命文学产生了联系,“连汇文中学、贝满中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也参加了进来”。(49)尼姆曾如此谈及基督教与她熟悉的中国革命青年的关系:“在今日中国,虽然拒斥基督教是一种风气,但众多革命的进步的学生,那些年轻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却常常受到这种宗教所蕴含的理想主义的影响。不过,让这些青年人真正感兴趣的应该说是基督教的哲学观和伦理观,而非纯粹的宗教教义。而且那些确实受了基督教思想影响的青年,大多和那些参加共产党的人一样,最初都是基于人道主义的天性和同情被压迫者的正义感。”(50)易社强反对尼姆的观点,认为“她对这一现象的说法有些过分”,其理由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基督徒……在‘一二·九’运动中占最重要地位的也并非基督教学生”。(51)但问题是,只关注与“一二·九”运动关系密切的燕京大学,视野未免狭隘。在整个现代中国政治的、文学的革命运动中,还有更多的教会大学、中学参与进来,杨刚所著自传体长篇小说《挑战》就可看做对尼姆上述说法的形象诠释。小说主人公黎品生是一所教会中学的学生,“这所外国人办的学校和它的基督教却打开了她的心扉,并将改变她的思想”。这位豪门娇小姐的走向革命,“基督教使人人认识到彼此是平等”就是其最初的精神启蒙。(52)北平私立育英中学的学生们更是宣称“基督教是富于革命的宗教”,其理由也同样是它的平等观念,认为基督教“是促成人类平等的宗教”。(53)其实理由也许并没有那么重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中心命题,不管是空间、群体,还是宗教,都只能算是时代的细节,最终都会百川归海、殊途同归,走近时代主题。教会学校大多有学生组成的团契这一宗教团体,1935年育英中学的学生回顾一年的团契活动如下:“演讲会有二十余次,如袁永贞女士讲《学运的意识》、许地山博士讲《时代的认识》、陶希圣先生讲《一九三六年当前几个先决问题》。”(54)宗教组织且如此,可见时代风气所向。明乎此,李景慈等人从这所教会学校走进左联、参与到革命文学中去,也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讲述革命文学的故事,想走近1930年代革命青年的文学生活,中学校园这一文化空间内的许多历史图景都值得驻足。
注释:
①参见陆万美《忆战斗的“北方左联”和“北平文总”》、杨纤如《北方左翼作家联盟杂忆》,分别收入《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342页)和《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5页)。
②陆万美:《隽永的纪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③魏照风:《新球剧社的前前后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期。
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成立宣言》,《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46页。
⑤闻天:《保定的学校教育》,《中学生活》1934年第9期。
⑥申春:《关于保定左联小组》,收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研究资料集》,1991年,第263页。
⑦参见梁斌《关于保定左联》、《远千里同志十年祭》,收入《笔耕余录》,第128、150页。
⑧张腾:《怎么办?——并答文平、萧启文、温宜、禾子诸君》;乃光:《“中学生爱好文艺”的几重原性及改善方法》(下),分别载于1935年2月24日、3月7日《北方日报·长城》。
⑨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⑩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载1944年《南开学校四十年纪念校庆特刊》。傅国涌编《过去的中学》以及李桂林、戚名琇、钱曼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之《普通教育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二书收入本文,皆视本文为中学教育文献。
(11)参见Ernest T.Shaw,Why Student Organizations?和《学生团体与学生生活》,两文分别收入育英学校学生自治会编辑1931年和1932年《育英年刊》。
(12)参见杨同芳著《中学训育》,世界书局1941年版,本书附录中收入《中等学校训育实施纲要》等多种教育法规。
(13)陆殿扬:《全国中学校状况调查统计》,《新教育》第5卷第5期,1922年12月。
(14)参见晓春《文艺社与演讲会——中同学新成立的两个团体》、《辅中新组文艺社》和联芳《文艺团体在正中》,分别载于1933年11月9日、1934年4月19日、1934年10月11日《中学新闻》。
(15)梦中人:《一中每周杂谈》,载1935年1月17日《中学新闻》。
(16)吴强:《回忆与感想》,收入《左联纪念集1930-1990》,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17)《本刊启示》,《大同半月刊》第3号,1931年5月4日。
(18)刘继烯:《弁言》,《东北大学附属中学校刊》第1卷第1期,1928年4月。
(19)尔琼:《写在前头的话》,《南开女中月刊》创刊号,1931年5月。
(20)《编者的话》,《大同双旬刊》第1卷第2期,1934年12月10日。
(21)白逵:《编辑后记》,《协和湖》第4卷第1期,1935年10月。
(22)《编后》,《大同周刊》第2卷第6—7期合刊,1936年4月13日。
(23)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4)编者:《为本刊敬告读者》,《大同学生半月刊》第1号,1931年3月5日。
(25)张僧魁:《写在学生生活团体的前面》,《育英年刊》,1933年。
(26)张佑臣:《本校沿革志略》,《育英年刊》,1929年。
(27)《新文学研究会》,《育英年刊》,1931年。
(28)参见近藤龙哉《左联成立大会》和《北方左連につぃて——成立期を中心に》(《关于北方左联——以成立期为中心》),分别收入《左联研究资料集》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九十七册,昭和六十年三月(1985年)。
(29)江风:《我的共产主义思想蒙师李俊民同志》,《李俊民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56页。
(30)(49)张磐石:《我所了解的北平左翼文化运动》,《北方左翼文化运动资料汇编》,第276、273页。
(31)张鸿来:《国文科教学之经过》,《师大附中成立40周年纪念特刊》1941年。作者自1913年即在北平师大附中教授国文,并曾任主任,即校长。
(32)丁浩川:《丁浩川教育文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0页。
(33)梁斌:《怀念丁浩川老师》,《笔耕余录》,第89页。
(34)胡晓明:《跨过的岁月:王元化画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文中将阎蕴之误为阎润之。
(35)《私立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概况》,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出版1936年版,第56页。
(36)参见《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一览》,1931年。
(37)以1929年和1932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为例,前者规定初中13门课程每学期总计180个学分中,国文36分,占总学分20%;高中150个学分,国文24分,占16%;后者规定初中每学期15门课程,每周共计35课时,国文6课时,占总课时17%,高中每学期17门课,每周总课时34,国文5课时,占15%。
(38)乃光:《“中学生爱好文艺”的几重原性及改善方法》,《北方日报·长城》,1935年3月7日。
(39)李俊民:《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李俊民文集》,第364页。
(40)《忆念胡也频先生》,邓久平编《季羡林散文全编》(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41)(45)韦君宜:《不能忘记的老师》,任文贵、杨北楼选编《长相思:名人笔下的老师》,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47页。
(42)吁:《从“穷”说到“浓厚大同的学术空气”》,《大同学生半月刊》第1号,1931年3月5日。
(43)耶菲:原名周德成,后改名周新武,1916-2000,河南息县人。在河南省立一中读书时因从事革命活动入狱一年半,出狱后于1934年进入大同中学,1936年考入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抗战后曾任中共豫东南工委特委青年部长兼息县县委书记,1945年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兼北京广播学院首任院长,关于其详细经历可参阅《周新武纪念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颖灿,1916-1995,原名姜方生,浙江象山人,殷夫表侄,为纪念殷夫自名殷参。1933年入北平大同中学读书,抗战后到延安,任鲁艺编审委员会编辑,1978年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详细经历可参阅高鸿列和刘希圣作《殷参》,收入《辽宁党史人物传》第四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4)耶菲:《忆念我的老师潘漠华》,《周新武纪念文集》,第592-593页。
(46)苏凡:《漫长的记忆》,《左联回忆录》(下),第559页。
(47)林志:《林志回忆录》,http://linzhi.home.sunbo.net/show_hdr.php?xname=JPR8TV0&dname=UQMlV31&xpos=6(林志网上灵堂)。林志,1914-2006,1931年进入大同中学读书。
(48)孙席珍遗著、吕萍整理:《悠悠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
(50)Nym Wales,Inside Red China,New York:Doubleday,1939.p.171.该书在纽约出版的当年,即由胡仲持、梅益、林淡秋等八人译为《续西行漫记》,1939年4月由复社出版。
(51)John Israel.Donald w Klein,Rebels and Bureaucrats:China's December 9ers(《中国一二·九一代》),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
(52)《挑战》是杨刚1944年至1948年在美国用英文写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冠商的中译本。本文引述文字出自该译本第127、47页。
(53)编者:《圣诞节前献词》,《育英半月刊》第3卷第3期,1934年12月16日。
(54)苏汉臣:《一年来的育英团契》,育英学生自治会编《育英年刊》,1935年。
标签:文学论文; 文艺论文; 1930年论文; 中学生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大同社会论文; 结社自由论文; 大学社团论文; 艺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