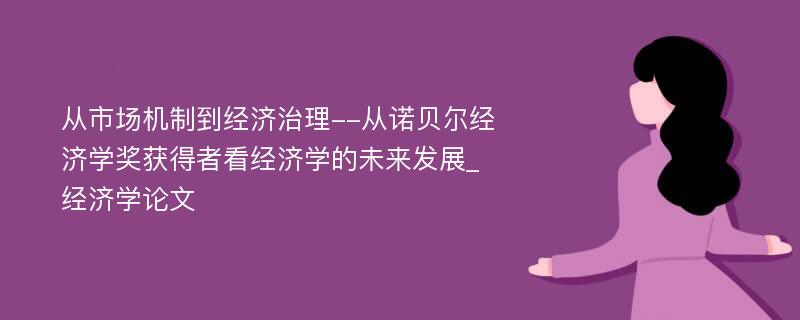
从市场机制到经济治理——从奥斯特罗姆获诺贝尔奖展望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斯特论文,未来发展论文,市场机制论文,经济学论文,获诺贝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兼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及法学教授奥利弗·威廉姆森由于对“经济治理”的贡献而分享了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获奖者勤奋耕耘,严谨治学,在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取舍方面思想开放,不受学科界限的束缚。他们游刃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博采众家之长,但自始至终专注自己所选择的研究课题,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奥斯特罗姆对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的实证研究和威廉姆森对企业边界的阐释广为业内所传诵。两人著述等身,享誉学界;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其学说有理有据,自成一家。他们的获奖也是名至实归。
在2007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主流经济学饱受各方攻诋,凯恩斯主义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位主将,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或许昭示经济学一个新的未来的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界备受推崇,它在我国的地位和影响力远超过它在新古典经济学一统天下的西方经济学中的从属地位。今年新制度经济学在诺奖中胜出,这对经济学未来的流变和归属有什么样的启示呢?本文侧重于从奥斯特罗姆获奖的角度展望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早年一直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先后获该校学士(1954)、硕士(1962)和博士(1965)学位。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埃莉诺在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主持的政治学研讨课(Seminar)上与她这位未来的丈夫相识。文森特1950年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取名“政府与水:一项关于水资源在洛杉矶发展过程中对政府制度和实践的影响”。深受文森特的影响,埃莉诺的博士论文“公共企业家精神:地下水资源管理的案例研究”,以海水对洛杉矶地下水的侵蚀为背景,探讨了人们如何组织公共企业来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该论文以扎实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为事实基础,立意新颖,分析严谨,从而分享了1965-1966年度美国西部政治学会的最佳博士论文奖。
1965年,文森特被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聘为教授。但是印第安纳大学却没有给随夫而行的埃莉诺任何正式职位。埃莉诺第一年以访问助理教授之名挂靠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以后的三年里她为政府系的助理教授和研究生辅导员(Graduate Advisor),到1969年,政治学系才聘请她为副教授。1973年埃莉诺辅助丈夫文森特创建了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工作坊(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随着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工作坊的成立,埃莉诺于1974年晋升为政治学系教授。她为人谦和,学风扎实认真,因而深受同事爱戴。埃莉诺于1980-1984年担任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并在1989-1990年度再任执行主任。在2006年,埃莉诺老当益壮,远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创建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al Diversity),并担任研究教授(Research Professor)。
在过去的30多年中,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工作坊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的主持下不断发展壮大,是美国研究公共选择和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镇。目前,该工作坊下设应用理论、社会—生态系统、实验方法、持续民主的政治经济学、社会网络分析等多个研究小组,每周一中午定期举行研讨会。自2008年起,每周三中午另加一场研讨会。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工作坊广邀天下才俊做专题研究报告或短期学术访问。其2008年度预算高达130多万美元,真可谓财力充足,人才济济。2009-2010年度,有5位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河海大学和贵州财经学院的中国学者在该工作坊访问。
二
美国大学的工作坊制度首创于芝加哥大学,后为各个大学和研究中心所接受。工作坊处处开花结果,蔚然成风,是美国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学术研究之所以能独霸全球,傲视群芳,其工作坊制度功不可没。虽然每个工作坊有自己的指导理念和运作方式,但无一不以学术交流为最高宗旨。学术文章在投稿之前,学者能够被邀在相关的工作坊做报告,和同行切磋、讨论,是十分宝贵的机会。由于工作坊的运作一般不受人事行政的约束,在经费许可的条件下,主持人可以广邀坊内坊外的名师大家和后起之秀做学术报告。工作坊一般对外开放,参加者一律平等。学界泰斗和刚入道的莘莘学子闻道有先后,得道有深浅,但在工作坊研讨会上无身份之别,任何参加者只能以理服人。一个好的工作坊往往为崇尚自由、服膺真理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学术创新的磨刀石和思想交流的天堂。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而言,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工作坊为她将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平台。
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出,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工作坊强调理论分析和公共政策的有机结合。在倡立该工作坊的建议书中,文森特明确指出该工作坊的宗旨在于发展一套可用做分析工具的政治理论,来指引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的设计和实施。这种指导思想和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界学术主流大相径庭。从五六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帝国主义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抬头。以公共选择学会(Public Choice Society)于1965年的成立为标志,政治学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攻破的第一座壁垒。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最核心的原则是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选择的一种独到视角可适用于理解人类的任何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被视为具有广泛的应用性,不仅能解释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虽然奥斯特罗姆夫妇是公共选择学会最早期的核心成员,埃莉诺在1982-1984年度还当选为公共选择学会会长,奥斯特罗姆夫妇并非全盘接受经济学帝国主义。他们一方面积极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尤其是以科斯“企业的性质”为基石的组织经济学,和科斯—张五常—诺思一脉相承的华盛顿学派对国家理论的贡献,并且,他们是美国政治学界早期接触并引入博弈理论的倡导者。另一方面,基于他们早期对公共水资源以及后来对地方政府,尤其是警察局的经验研究,奥斯特罗姆夫妇强烈地感受到现实世界与经济学模型有很大的距离。
毋庸置疑,理论模型有它的独到优势。一个好的理论模型能奇妙地化繁为简,凸显我们所关注的主要因素,而淡化其他枝节。但是,理论模型毕竟并非现实世界本身。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接受由理论模型推导出来的结论可以直接应用到具体问题上。相反,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建立于理论模型上的结论都有它天生的缺陷:逻辑严密,但容易引人误入歧途。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对任何现实问题,我们可以轻松地建立多个模型。就像同一个地球,我们可以有很多地图一样,各自有不同的用途。当我们长期沉浸于某一个模型中,习惯性地用一个模型来思考,而且把自己与现实世界隔离,以至于“梦里不知身是客”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逐渐忘却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作为以实证研究为主的政治学家,奥斯特罗姆夫妇坚持长期不懈地关注真实世界。他们自始至终没有忘记任何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只不过是工具,而研究的对象和我们应该关注的中心永远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难怪诺贝尔奖得主Vernon Smith(2003)在高度评价奥斯特罗姆夫妇的毕生学术贡献时强调他们是扎扎实实的科斯主义者(有关科斯与主流经济学差异请参阅拙著“Coase on the Nature of Economics”[2003]一文)。
三
毫无疑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成名作是1990年发表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公共资源在传统经济分析中地位相当尴尬。一方面传统经济学认定公共资源的产权定义模糊,既非国有,也非私有,因此导致租值耗散。这种悲观的看法在哈丁(Hardin,1968)的宏文发表之后更是铁板上钉钉。“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时洛阳纸贵,成为经济学关于公共资源的定论。在奥斯特罗姆的这部著作中,哈丁的观点是她立论的起点和靶子。正是通过对“公地悲剧”的批判,奥斯特罗姆树立了她自己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公共资源的产权定义模糊”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被揭穿为假命题。在一系列文章中,张五常(Cheung 1969,1970;张五常,2002)指出,非公非私的产权也可以足够清晰地被界定。对诸多公共资源而言,准入度和使用强度在乡规民约中都有明确厘定,并非无限制、无条件地对任何人开放。相反,正因为公共资源的巨大价值,当事人会通过各种合约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以期将租值耗散控制到最低水平,从而避免或减少悲剧的发生。埃莉诺后来翔实、系统的经验研究也恰好印证了张五常的理论分析。可惜,张五常的合约理论和后来公共资源的实证研究之间的互补关系不易被觉察,主要是由于张五常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角度很不同,前者从租值和合约理论出发,后者立足于公共资源的案例和实证研究,也难怪二人失之交臂。
从传统经济学理论来看,公共资源即使暂时地侥幸避开了哈丁所预言的灭顶之灾,也是陷于非稳定性平衡之中。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譬如人口增长、技术革新、价格波动等,公共资源在制度变迁上面临两重选择,或国有化,或私有化。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这部著作中,奥斯特罗姆总结了自己和前人对公共资源的经验研究。在收集、整理来自世界各地数千个公共资源的成功管理实例之后,奥斯特罗姆发现公共资源作为一种产权选择制度远非传统经济学理论所认定的那么脆弱。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历史年代、有很强的地域、时间和文化代表性的个案给了她极大的信心和鼓舞。她以此为基础,大胆发动了对传统理论的挑战。经过对传统理论的细心梳理,奥斯特罗姆发现了传统理论的陷阱:
其一,公共资源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制度安排。通过对多个制度变迁个案的详细调查,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包括她早年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洛杉矶地下水资源管理,也有失败的教训。奥斯特罗姆发现区分成功和失败案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事团体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任何个人和团体行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制度框架下发生的,一个制度框架往往由多个制度安排层层相嵌。譬如,在一个国家,约束力最广泛的制度是宪法;在宪法下,又有各项专业法律和地方法规。在公共资源所在地,除上述法律法规之外,一定还有非正式的习惯法、乡规民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一个能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群体其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及时、灵活地调整、改变地方性的制度安排,从而减少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因此,在一个子稳良性运转的社会里,我们看到地方条令、行规乡约适时地、自下而上地调整、变动,以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则保持相对的稳定。
其二,传统经济学理论所看中的国有化或私有化这两种选择都依赖于一个共同的制度基础,即一个强势的国家政权,包括以此为基础的法治。但是国家机器并非生而有之。另外,公平高效的国家机器,包括法律,即使建立之后还有巨大的执行和运作成本。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在其运作过程中更有额外的交易成本。正因为传统经济学理论事先假定国家、法律和市场等制度的存在,而且各自都在理想无成本状态下运行或执行,国有化或私有化才变成惟一的选项。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模型错当成现实,从理论模型推导出来的答案往往束缚,甚至误导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求解。奥斯特罗姆一辈子扎根于公共资源的实证研究,深谙公共资源的成功治理之道。在她所研究的案例中,有些已经持续存在达数百年之久。当理论和现实冲突时,她毫不犹豫地站在现实这一边。
四
个案研究最大的潜在贡献来自它对现行理论的挑战,从而开启新的思路,但个案研究本身不能证明或树立一个新的理论。由于个案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不足,奥斯特罗姆凭借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工作坊为平台,广泛地层开与其他学者的长期合作。借助重复博弈理论(repeated game theory)、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和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奥斯特罗姆和她的合作者,包括众多博士生和博士后学者,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来证实在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公共资源的成功治理之道并非特例,而是可以在实验控制条件下得到重复和验证。虽然很难说奥斯特罗姆在这方面的贡献有多少原创性,但其科学的态度,严谨执着的治学精神跃然可见。
一条贯穿奥斯特罗姆毕生研究的主线是制度多样性(Ostrom,2005),这也是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工作坊的核心研究主体。这条主线上承其博士论文对水资源和公共企业家的研究,中接奥斯特罗姆夫妇对“多中心”(polycentric)的阐释,下启以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为结构核心的“制度分析和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理论范式。制度多样性原则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在任何人类社会中,和谐和效率无不建立在多样性的制度之上。单就每一个制度而言,都有其长处和不足,而且随时间和场合的变化而变化。世界上没有什么金钥匙能打开所有的门,社会的复杂性呼唤制度多样化。正由于没有一种制度安排享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制度的多样性带来社会的“多中心”化。不同领域和性质的社会问题产生相应的制度安排,各自有自己的运作逻辑和游戏规则,而都在社会这个巨大的复杂系统里相互冲撞,相互磨合。虽然我们目前对这个社会大系统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仍懵懵懂懂,比较制度分析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任何制度安排,政府也好,市场也罢,都不应该垄断治理权。犹如生物进化依赖物种变异和多样化的原理一样,制度多样化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之道。政府以强权手段打压制度创新,破坏制度多样化而图求长治久安不异于自毁长城,南辕北辙。
在她长期研究公共资源的学术生涯中,奥斯特罗姆一贯坚持经验的、归纳的研究方法,少有高深莫测的数学模型,代之以大量案例事实和各种实验证明公共资源的可持续性。这些研究表面上看来似乎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远离开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研究生,对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成果知之甚少。即使笔者所在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也有不少经济学人甚至不知奥斯特罗姆为何人,况且她还是本校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创办者和中心主任。
虽然制度多样性和经济治理只是在最近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崛起才变成经济学中的显学,其实,经济学对经济治理的关切可是由来已久。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社会分工”结尾时所指出的:“拜社会分工所赐,在一个治理完善的社会里,各行各业的产品极大丰富。其所创造的财富惠及芸芸众生,包括最底层的社会民众。”斯密的这个洞见可圈可点,遗憾的是,虽然有关斯密及《国富论》的评论可谓汗牛充栋,但似乎很少有学者对斯密的这个观点表示出任何特殊的兴趣,更谈不上有什么理论跟进和完善。显而易见,斯密在这里强调,社会分工所蕴涵的创造财富的巨大潜能只有在一个治理完善的社会里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但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进一步论述如何才能完善地治理一个社会。很可惜,在李嘉图之后,经济学明显转移注意力。资源配置理论了取代“国富论”,比较优势法则(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代替了社会分工,经济学逐步演变成罗宾斯(L.Robbins,1936)所说的“选择的科学”(science of choice)。即使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被简化成“看不见的手”。我们知道,《国富论》只是斯密宏大思想体系中的一根台柱。《道德情操论》可以说是另外一根支柱。在他雄心勃勃的著书计划中,《国富论》之后,斯密还计划有专著论述法律和政府的历史演进过程和运作的一般原理。或许是这个计划太过宏大,斯密的这本专著最终没有完成。难怪斯密在临终时,躺在病床上对朋友抱怨说,“我这一生做得太少了”。
五
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一切经济问题简约为资源配置:在给定目标、资源稀缺的约束下,经济人如何优化资源分配以求最大程度地达到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的需求。这种以选择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它独到的视角。当今执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之牛耳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更是把它推而广之,演绎出一幕精彩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剧。其优点大家耳熟能详,毋需笔者在此赘言。然而,这种经济学视角也有诸多盲点,往往被人忽视。其一,目标给定这个前提条件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奠基人之一的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1935)所言,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目标的不断改进和成熟。经济学假定目标不变无异于画地为牢,把自己从现实生活中隔离开来。其二,资源稀缺这个前提条件也有误导性。诚然,没有稀缺性(scarcity)的约束,经济人无须选择,经济学的存在要大打折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经济生产正是对稀缺性的挑战和突破。财富的增长和稀缺性相辅相成,构成经济生活的两面性。从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成长经济学(growth economics)和均衡经济学(equilibrium economics)的大致轮廓清晰可见(有关成长经济学和均衡经济学的论述,参见Kaldor,1980)。前者以研究财富的增长为己任;后者专注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二者基本上是脱节的,其间的有机联系乏善可陈。古典经济学经李嘉图之后更是逐渐陷入均衡经济学的单一模式。其三,由于新古典经济学视资源配置为所有经济问题的实质,整个经济体系运转所依赖的制度安排必然下放到从属地位。由此而引发的后果是,本来是人类任何行为一项不可或缺的硬性限制条件,即制度安排,却变成一根毫无约束力的松紧带。在一般经济学研究中,产权、市场、企业、法律和国家等制度都假设存在,而且经济学中有关制度安排的假设完全服从于资源配置机制的研究所需,基本与现实脱钩。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这种做法并没有错。但是由于忽视了对制度安排的经验研究,由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我们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变成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同时,当经济学家对制度安排作假设时,他们不免习惯性地以他们所熟悉的制度环境为参照。这样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经济学家以为所有经济都是在他们所熟悉的制度环境下运作,从而压制他们对制度多样性的敏感和关注。
另外,新古典经济学传统把经济活动简化成市场和价格机制的运作。从传统经济学理论来看,市场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定价机制。供给和需求两股力量整合成马歇尔所说的剪刀而共同决定市场价格。由于经济主体,包括个人和组织,跟随价格的浮动而舞动,在市场经济这个大交响乐中,市场成为指挥家手中的指挥棒,协调各方当时的行为和对未来的期望。在任何市场经济中,市场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但是,完全站在市场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非市场制度,包括企业、国家和法律,从而把所有非市场制度都看成“次优选项”(the second best)或者市场替代品则犯了市场单一主义的错。在市场单一主义看来,除非市场失灵,所有市场替代品都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这些替代品惟一存在的理由是模仿市场的运作,以期望能够最大限度还原市场。因此,即使当制度安排出现在传统经济学分析中,它们的角色也早已事先确定,完全隶属于市场,因而不但没有形成对市场单一主义的挑战,反而强化了市场垄断经济活动中制度安排的基本假设。这也难怪主流经济学经常被批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六
以科斯“企业的性质”(1937)为开山石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在于打破市场单一主义,承认制度多样性,大力弘扬比较制度分析。从方法论上看,传统经济学奉行经济学帝国主义,相信用于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可以推而广之,应用到研究经济活动外的人类行为,譬如法律、家庭和宗教。比较制度分析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经济活动本身受到各种制度的影响。因此,除非我们切实把握实际经济运行中的种种制度性限制条件,否则我们难以理解和解释经济行为本身,更遑论解释经济活动外的人类行为。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往往由不同的社会学科来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学必须把其他学科纳入进来,协助经济学研究法律、家庭和宗教对经济的影响,而不是像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宣扬的走出去的策略。在这方面,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代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坚力量。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的获奖是因为他们对经济治理的研究见解独到,成绩斐然。但治理本身是一个超越经济学的错综盘结的大课题。两年前,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因他们在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 theory)方面的卓越贡献而分享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机制设计理论是用现代博弈理论和信息经济学来补充和完善市场机制在各种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的运作。其一个核心概念是激励兼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任何制度设计必须和经济人的利己性相一致,否则将难以为继。但是,在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人群有不同的经济动力。奥斯特罗姆在她公共资源的案例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即团体成员除了关注自己的利益之外,往往也关注团体的整体利益、公平分配以及其他成员对自己的评价和看法。如果机制设计理论假定经济人仅仅关心一己私利而忽视经济人的其他利益或道德诉求,我们一定会被理论误导。因此,我们要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激励兼容和治理。
治理的对象,即经济活动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人。如果治理简化为一个经济学问题,经济学简化成市场运行问题,而市场运行又进一步简化成机制设计问题,那么有血有肉,有情感、道德和社会关系的人性将被肢解、剥离,仅剩下利己性。这样层层简化当然极大地推进了经济学演变成一门类似于现代物理学一样的科学,但是,如果它对人性的把握有很大的偏差,我们不禁要疑问,这样建立起来的科学究竟有多少价值?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曾经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在制定研究计划和确立研究方法时,没有什么比我们对研究人群所持的人性的假设更重要(H.Simon,1985,p.303)。
阿尔弗雷得·马歇尔在其宏著《经济学原理》中开宗明义,强调经济学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当然,马歇尔所说的人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即科斯(1984)所说的“man as he is”,并非经济学所假设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除非经济学回归到以人及其人创造的、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各种制度为研究对象,关注真实生活中经济的运转和演变,否则经济学难以摆脱目前的窘境,而沦为“没有数的应用数学”(applied mathematics without numbers)(McCloskey,1994)。
由此看来,我们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首先,经济人的道德品质是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我们必须摈弃那些认为道德与市场经济和经济学无关的错误观点。诚然,通过机制设计,我们可以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合约。但是,由于各种交易成本无所不在,天下没有完全的合约(complete contract)。而且现实生活中的经济人不仅仅逐利,而且有情有欲,受家常伦理、社会关系、道德情操的约束。其个性丰富多彩。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设计一个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合约。其次,经济学研究向来首要关注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忽视了市场经济何以可能是一个更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一旦我们不能假设市场经济的先验存在,我们出发点首先是如何建立市场经济,让社会分工和交易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在这个问题上,经济人的道德品质和市场经济赖以生存的制度保障,包含相宜的政治制度、法律观念、文化价值、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二者不可或缺。并且,只有在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的条件下,我们才能研究市场经济如何运作,譬如市场定价,资源配置,技术、产品和组织的创新。在一般实证研究中,我们不一定如此按部就班。大多数经验研究肯定更多地关注市场经济如何运作。但在理论思考层面,我们不能忘记市场经济何以可能更为重要。最后,各种不同的制度安排(包括市场、企业和国家、合约、法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既相互替代,又相互补充,共同完成治理的目标,使市场经济不但得以高效地运转,而且能不断发展,适应新的环境。经济学中把国家和市场放在对立的敌我两面,彼长此消,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今年的两位获奖者奥斯特罗姆和威廉姆森和其他无数无名英雄共同扎实、严谨和孜孜不倦的努力扛起了新制度经济学这面旗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因此不再局限于定价机制和资源的最佳配置。如果经济学能够应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涉及、但没有明确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即如何完善地治理一个社会,给社会分工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保障,从而能释放其巨大的创造潜力,造福于芸芸众生,经济学就可以永远摘掉“沉闷的科学”(dismal science)的帽子,而堂堂正正地成为一门“希望的科学”(hopeful science)。
标签: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诺贝尔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奥斯特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罗姆论文; 市场机制论文; 法律论文; 诺贝尔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