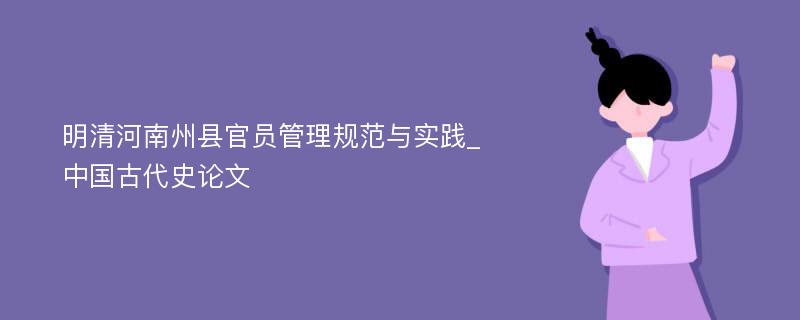
明清江南州县官员的行政规范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明清论文,官员论文,州县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州县的责任 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江南,是个范围极小的地理空间,却是唐宋以后整个中国最为繁荣的地区,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都较有代表性,是一个州县行政较为成熟、行政实践又较为复杂的地区。除了社会经济与文化上所具的代表性外,江南的“政治”意义也很重要。① 明清时期江南州县衙署的环境、行政实践等工作的复杂性,多有难以语言形容者。②而民间百姓对官员的最好期许,或许应该如周忱(1381~1453)抚吴时的成效,所谓“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③无论对朝廷还是对地方,州县官员都有责任努力做到这一点。清人曾说:“天下之治乱系乎民,民之治乱系乎牧令。盖牧令者亲民之官,官不能治民,则民之疾苦日甚,天下所由多事也。”④州县官的责任可谓重大。 在一般的理想视野下,地方行政工作中有“吏治必称循良,亲民莫如州县”之说。况且江南系全国财赋重地,州县行政于催科、抚字尤难,非常需要好的官员前来当政。⑤江西人万谷春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莅任吴县知县时,姚希孟(1579~1636)给他去信鼓励说:“此时之敝地冣易于治耳。若吴之赋,额差减于长洲,而征输稍不费力,则催科、抚字正不必分为两途。”⑥ 而州县正印官对地方的影响,又涉及各个方面。万历十九年举人、常熟人管一德曾有总结:“县之教化风俗,俱由令尹而造。贵家巨姓可颐指一邑,而犹俛而听于令;市井豪椎埋为奸,道路以目,亡敢诘者,唯令剔伏;庠序学校,惟令广厉;百万编氓,阽危凋瘵,烦冤郁苦,惟令拯纾;即不幸有兵革倥偬,而转战婴城,亦惟令捍御。其于法甚尊,而于情甚亲者,毋如令也。”⑦ 州县官员要应对地方巨室、土豪、文化教育、刑名狱讼、弭盗治安等工作,需具有一定的掌控能力,这就对其人选有相当的要求。倘不得其人,就有可能“弊端百出”甚至有“灭门州县”之虞,成为“地方之害”。⑧ 据明末《重刻官员品级考》的说法,知县多由部检校、都察院检校、苑马寺主簿、上林苑监典簿、卫经历、府经历、布政司照磨(降官)、博士、部照磨、都司都事、州判官、县丞、光禄寺典簿、署丞、监事、录事、副兵马、京县丞、太仆寺主簿、行太仆寺主簿、京府经历、盐运司经历、都察院照磨、通政司知事、京县主簿、按察司知事、国子监典簿、鸿胪寺主簿、学正、教谕这样有经验的官吏升任。⑨但也有不少知县由新科进士等人担任,从政经验与官场知识相对薄弱。 就明代而言,州县长官莅任时都需熟读朱元璋时代颁定的《到任须知》册,内容包括祀神、田粮、仓库、公廨、官房、生员数、官户、吏典、词讼、警迹等三十一条⑩,在官衙中要了解这么多的地方重要事务,才能有效地施政。 到任之初需要住歇地方,若无“公馆”,可以吩咐前站花钱租赁民房,而不能住宦宅,以免欠下人情。到了莅任境内,就要礼房准备县佐、儒学及各士夫举监详细之履历册,以备了解地方。在正式上任前一天,要准备“交盘”工作,由吏书们将库内现存实在银数照两院循环簿造册两本,以便交接。到任一二日内,要接见地方士绅、拜见上司等。(11)甚至收罗阅读地方志书(或称风俗志),以为了解地方各种情形的重要参考。(12)这些工作,其实也是制度或习惯上的要求,多为有经验的官员们所熟知。 明人认为,“邑令最近民,抚之即生,虐之立瘁”,(13)责任十分重大。归有光说:“夫为令,如婴儿乳哺,饥寒燥湿,唯乳母知之。又如良医按病调剂,分毫不爽,乃可已病。”(14)一位好的牧令就应该如乳母、良医一般用心。地方即使有再大的情事,也要“安妥闲静,与小民处置”,凡事要详慎,使百姓知道“胜负在理”。(15)遇到每一件事以解纷为主,对兄劝友,对弟劝恭,对亲邻劝和睦,要讲情理,“然后可以为民父母”。(16) 新官上任时,当然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熟悉与应对。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设立各项簿册,即上司来文号簿各一扇、词状号簿各一扇、各上司比较前件簿一扇、各房吏书年貌籍贯三扇、代脚色册一扇、各房候缺吏一扇、门子民壮皂隶阴阳生各役一扇。(17)这些工作都为官员本人的有效施政作准备。 弘治十六年(1503),朝廷以法律的形式重申:“凡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务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但有钱粮未完者,不许给由。”到万历元年,朝廷又规定:“今后外官考满到部,行户部查勘钱粮,完过八分以上者,方准考满,不及分数者,不准。”(18)这些要求,无疑都加重了州县官的负担。万历年间吴江知县刘时俊就说:“吴中财赋,每完在八九分间,即称足额以为常”,但居然仍有人虚称“十分”,向民间起征,弊窦百出,他上任时发出的征收单上要求的完成数是8.5分,须在限期内完解。(19)明末嘉善名宦陈龙正比较过嘉兴地区与苏松一带的输税问题,觉得都亟须整顿:“苏、松贵家多懒完官物,粮则有军储,折色则倚势不纳。嘉禾不然,士夫顾乐输将,而细民之刁者与奸胥通,积岁不完,每赦下,必赦旧逋,则奸民欣然相庆,而善良如期输办,毫不沾恩。二方之弊,各不可不整顿。”(20) 至于衙门每天工作的日程,则是以敲击一种竹筒(“梆”)和一个小铁棒(“点”或“云板”)的声音来发布和限定的。黎明前,在内衙(州县官宅邸)敲“云板”七遍,外衙敲“梆”一遍,衙门大门打开。此时,书吏、衙役长随都必须到岗。清晨,敲云板五遍,竹梆两遍,案牍分给书吏,衙门职员均开始办公。接着,州县官主持“早堂”,接受并分派案牍,接受衙门职员们所呈的书面或口头报告,讯验被捕系的罪嫌或将要解送到别的衙门的囚犯,接受任何诉讼。然后,州县官回到他的办公室(“签押房”,意即“签批文件的房间”),在那里接受或签批文书,包括与当日将要听审的案件相关的书状。(21) 二、钱粮与民生 大概成化、弘治以前,地方里甲催征粮户,都是上纳粮长,统一收解至州县,粮长也不敢多收斛面,粮户更不敢掺杂水谷糠秕,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可是后来的情况就变了。嘉靖十六年,常州府知府应槚推行“并征均则法”,希望达到“原额不失,均摊有定,无独累之苦、欺蔽之私”的目的。其中有“立柜头”一条讲道:“先年收头,将银两径收私家,任意侵费。今令各县置柜,窍其上方,纳户于包封上自填姓名银数,当官秤收,给票付照。不到者,不许隶卒下乡催扰,止令排年各催其甲,凡勾摄公事,专属见年里长。”(22) 应槚推行的新办法,明显是针对州县地方一直存在的钱粮欺蔽问题。这类问题暂时在某些官员的努力下会得到缓解,但无法保证其长久的效力。后来顾鼎臣(1473~1540)向朝廷条陈的奏疏中,再次指出官府催征岁办钱粮的弊病,便是一个明证:“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23) 隆庆二年进士、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在四年的上疏中也指出,“今庙堂之令不信于郡县,郡县之令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济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在这样的处境下,地方官再贤能,“安养之心渐移于苛察,抚字之念日夺于征输”,最终受困的仍是普通百姓。(24) 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桐乡人李乐认为“天下极冤最枉之事”,就是带征钱粮一节:“凡知县、知州在任,止该清理任内钱粮,任以前自有官在,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并责备后官? 行取文书一到,合于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钱粮不完,上司留着他在。”在万历年间,对地方官的要求是对前任各届官员拖欠的钱粮,都能带征完纳。他感叹道:“天下只是这几个百姓,百姓只有这些皮肤,前面太宽,后面太紧,直是赶到大坏极乱、不可救药便了。”(25) 其实明代对于仕宦阶层的法网是很密的,可是到了地方“以故事虚文应之”的官员却很多,原因就在于地方官缺乏责任感,“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吏们奉行的“不过已往之旧牍,历年之成规”,最终都形成了吏治不振的局面。(26)倘要州县官事事亲历亲为,那他所感受的压力与困苦是可想而知的。很多懒惰的官员就将政务委诸佐贰官,而佐贰官“往往奉承堂官,狐媚厚馈,堂官暱之,因而滥批词讼”,甚至委托征比钱粮,佐贰官更得以需索“见面钱”、“松刑钱”,最后官府恶名都会落在州县官头上。(27) 而对于地方民生的救护,本属州县官乃至朝廷的重要职责。除赋役负担方面尽力为民纾困外,其主要表现就在救荒时期。 例如,嘉靖元年出现的饥荒,曾迫使朝廷至地方发起了许多救护工作。像这样大规模的救济活动,需要国家的强力支配,方能于更广的地域范围内展开。该年赈济工作的杰出表现者,是时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的席书(1461~1527),他向朝廷提供的救荒对策就是赈粥法,区别灾等、灾户,进行相应的救济:“臣日夜筹划,今有司仓廪既虚,户部钱粮又难遍给”;最合适的应对方案就是赈粥法,在南直隶等地,按大县设粥十六所、中县减三之一、小县减十之五的规模展开。赈粥法不但不浪费,而且见效快,不仅适用江南,更可以推广至全国。(28)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席书上书之时,已被派往江北赈济。但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要求江南地区一体施行;户部官员也很认可席书的方案,赞成通行。(29) 可以发现,到明末,州县官员的救荒工作中大多推行赈粥的方法。明代中后期流行的“煮粥诗”云:“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30)说明了它的可行性。但煮粥法十分忌讳大群人口聚食一处,“须逐乡而煮,分图而食”。(31)在崇祯十四年的一次大灾后,湖州府地方采取的一大措施是“厂籴”,但是立粥厂(即粥场)似乎更为当时所推重。在救荒期间,政府还迫令大族及豪富之家分担赈灾的部分责任,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涟川沈氏家族,独立承担了一个粥厂的赈济任务,除领取赈银、维持粥厂外,所需费用“皆出自囊物”,最后才“勉力竣事”。(32)这一事例表明了当时像沈氏这样的乡间地主所具的财力。但赈粥法的流弊也不少。在朝廷“勘荒官”到来前,地方上其实就已做好了准备工作,连夜在“勘荒官”经过的地方,置地设粥厂,并立旗书写“奉宪赈粥”四个大字,集合饥民等候这位“勘荒官”来“鸣钟散粥”。官未到时,只好“枵腹待至下午”;官一离去,煮粥活动当即结束。(33) 所以,陈龙正认为,有时散粮的办法胜于煮粥。但按照时势差异,很难制定成法,大致上只有四条规则可循,即“小荒先散粮于乡,大荒兼煮粥于城市,当道会期而煮粥,乡人画地而散粮”。(34)同时他提出了对赈粥法的改进方案是担粥救赈法,其优点是“无定额,无定期,亦无定所”,派人分挑至通衢要路及郊外地方,施行救济,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这种方法可以避免粥厂救赈中的弊端。他举例说,苏州府等地在施行煮粥的过程中,因没有充分考虑到其中的弊病,出现了哄斗杀人的情况。不过,“粥担法”针对的主要是流移贫民。(35)饥荒时期最易酿生变乱,何况此时王朝阽危,更需要由州县官府联合地方领袖,加强社会稳定的工作,赈济饥民似乎显得尤为重要。就在崇祯十七年崇祯帝死讯南传、弘光帝在南京建立临时朝廷时,嘉善地方就以乡宦陈龙正为代表,仍在积极进行社会救济工作,陈本人就捐出了五百石米和千两白银。(36) 三、清、慎、勤的问题 从三国时代以降,朝廷对地方官员的要求,多不出清、慎、勤三字的范围,为官以清为本。所以到清代,州县衙署的讼堂上多书有“清慎勤”三字匾额(37),以为训诫。 当然,清代州县长官的行政准备,多与明代相仿。康熙时期曾任山东郯城县令的黄六鸿,对自己的为政有着很高的期许。从政伊始,即重拾以往一些良吏的言论,无非是上不负皇恩、下造福百姓的内容。后来将他的郯城的从政经验,制成《福惠全书》。这是一部比较能够全面反映一个地方县衙行政与治体的资料集,角度全是从县级最高行政长官而言,故可以作为一种地方官的思想体认。(38) 在省级官员看来,所谓县令下车伊始,务当提纲挈领,择要施政,像江南的震泽县,正经界、清词讼、缉盗匪、禁枪船、兴水利等工作是知县行政过程中必不可缓之事。(39)曾任平湖知县的王凤生说,“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难于此时”,莅任之初的工作是十分关键的。(40) 不少行政长官,都希望能够成就良好的吏治。甚至是地方公共的空间处所,未必都需要由州县官员承担责任的部分,在有的官员看来,也应该仿效社会贤达人士,义捐钱粮进行维护,如明人所言:“陆而除道,民不病行;水而成梁,民不病涉,皆为政者之责,非有责于民也。”(41) 而一般的从政业绩,最终都会由朝廷来进行考核。例如在清代,每三年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大计”。每一名州县官的评估报告,均由其直接上司知府、直隶厅州同知或分巡道写出,然后呈交给布政使和刑按使;藩臬二司再附上他们的评语(“考语”)并呈交给总督或巡抚。督抚复审报告、批准或修正评估意见,然后上交吏部。其政绩显著者列为第一类,评为突出而特殊(“卓异”)的向吏部推荐,甚至被皇帝召见(“引见”)。(42) 康熙十四年任嘉定知县的平湖人陆陇其,撰写《“有仪轩”歌》,说道“恭宽信敏惠,斯须不可离”,(43)颇能反映像陆陇其这样吏治勤敏的地方官员的一些看法。而官声较好、得到江南士民称颂的慕天颜,据说因为陆氏在其做寿时未曾送厚礼,所以“独劾嘉定知县陆陇其不协于舆论”,尽管称其“操守绝一尘,德有余而才不足”,但左都御史魏象枢却认为,“今之有司,惟操守为难”,既然陆陇其操守一流,“何不留以长养百姓”,不要使廉吏灰心而贪风日长。(44) 知县职任的重要性,为时人所深识。清人曹尔堪的短论,可以代表很多人的心声。他说:“吏道难兼,清刚者未必仁惠,勤慎者未必果决,经猷恢扩者未有文章。文章末矣,功名不尽从帖括也。往时重循吏,士当释褐后,乐为县令。三年报最,入登言路,与天子相可否,循级而升政府枢机,身握天下之本,盖劳勋久而能任大事,剔历深则能断大议,国计民情,物力练习……皆得力于县令也。”(45) 在康熙看来,“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豪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 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46)廉吏好官,其实就是向民间索取相对较少的官吏。而且,知县在面对民众遭受侵扰甚至破家的危难时,应该有慈念之心,让他们少受官衙诉讼之累,即使已经累及词讼,也应该及早结案,使之不伤元气,而无愧于“父母官”之称,不要成为谚语所云的“破家县令”。(47) “破家县令”与“灭门刺史”一样,是民间久已流行的俗谚,(48)提示州县官应该怀有的警醒意识。道光年间,曾先后任元和县知县、川沙厅知事的山阴人何士祁,讲述了其在衙门日常办公的一般情形:“冬春辰初、夏秋卯初,必发二梆,然后至签押房,阅视上日所送片稿及批词、公文、禀信、稿件。饭后看审案卷籍。未刻发二梆,审理堂事。晚则查核账簿,标记刑名、钱谷簿,查看门簿。或无堂事,则与幕友酌商地方事宜,或考订律例,或检阅史传,或赴市廖村野以察民风。至朔望拈香,必宜早起,期会出入必有定时。与民约者,尤在必信。习以为常,历久不怠,则内外人等皆知官之所专心者在于公事,而诸务就理矣。刻刻振作,犹恐有失。”(49)何氏讲述自己日常从政安排的同时,似乎也在显示其为官的理念与从政的目的,并希望通过这样持之以恒的工作,与民以“信”。 在民众的心目中,州县官本是老百姓的依靠,是“父母”,是亲民之官,“为一州则一州之民生所属,为一县则一县之民生所属”,应该“事事裁决精当,而后上之道府,达于院司”。(50)这也是王朝统治者对他们的期望:“一个衙门一个官,在朝廷本意,原是叫他们替百姓判断曲直,调处是非。”(51) 尽管官吏群体的薪俸比较低微,但许多官吏仍希望厉行节俭,有人还表示“衙内多一日宴乐,外间即多一日愁苦”,(52)意义十分深刻。但不良州县行政的事例实在不少,多因“知县不能约束书吏,致酿重案”。(53)所以州县官的操守,在地方政治生活中就显得意义重大了。 成化五年,长洲知县余金到任后,“群吏以其儒者,颇易之,作奸如故。公以理教戒,率者居半,因稍加惩艾,即皆改行焉”。(54)显然,大多数衙门的工作人员,经常存在这样的认识,即所谓“官看三日吏,吏看三日官”。(55)如果官不久任,一切的因循苟且就会导致太多的弊端。(56) 海盐人郑晓(1499~1566)认为,明代自嘉靖朝以后,“其贪墨奸佞依阿卑谄者,安享荣禄。即有论劾,行贿得解,职任如故,旋复升转。以故今之大臣,实难展布。上为内阁劫持,下为言官巧诋,相率低头下气者以为循谨。千金双璧络绎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声矣。”(57)讲的是京官,地方官就更厉害了。 吏部尚书赵南星在天启三年的上疏中,无奈地指出这种“贪黩成风”似已无术可禁。下官参谒上官,“辄令行户随之置办下程,饼师、酒保皆受其累。而又有喜于作威者,不问事之大小,一怒辄折人之肢体,伤人之性命。”偏偏这些人,却常得举荐,“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故赵南星认为,“今日之忧”是在郡县之内。(58)尽管读书人“仕而求富贵”,符合古谚所谓“人不衣食,君臣道息”的言说,无可厚非,但作为朝廷命官,就要讲刚正之气。那些府、卫、州、县佐贰首领,见到通判以上者,都呼“老爷”,视己为奴仆,但并非真的甘心为奴仆,民间倘要“以士君子之行望之”,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鼓舞士气、维护世道、保障民生,就要从正士风开始,廉干称职的地方官员应该得到奖荐优擢。(59) 在清代,地方州县官员的情况,可以常熟、昭文地方人士所论为例:“盖常邑夙号繁难,令大率岁一易,坐席未暖即捧檄欲行,不暇为经久计。昭邑虽或久任,以同城故,遂亦因循,而丞、尉无论矣。”(60)这表明,很多州县官深知在一个地方履职不会太久,在有限的任期内要进行所谓的改革调整,既不可能,也无必要。他们的心思全在将来如何升迁、仕途如何发展上,因此在地方工作中就缺乏责任心,多因循旧习而已。 四、衙署生活管理 在州县官衙服役的家人,往往“丰衣美食,华车肥马,顾盼自雄”,以为是为主人装扮体面,殊不知“这便是主人做贪官的幌子,其家人可知,主人之居官更可知矣”,(61)需要引起官员们的警惕。那种“吏安其职,民乐其业,刁讼不兴,苛政不作”,被时人简直视作小康之世的理想了,因为这在实际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清初时上海人叶梦珠指出:“本朝初定江南,设官委吏,习闻弘光之风,不复寻先朝之度,当事者往往纵情任意,甚而惟贿是求,讼师衙蠹,表里作奸,赋役繁兴,狱讼滋扰,郡县胥吏,得以狎侮士林,旧日朱门无不破家从事,数十年之间,士风靡弊极矣。”(62)身历明清两代更替的叶梦珠,对于州县行政的变化有着深刻的体悟,“惟贿是求”一句就揭示出了地方政治腐败的关键。在州县衙门中,佐杂官吏经常插手钱债等案词讼,蠹书玩差,从中勾串渔利,扰害乡民。(63)州县正印官对此自然负有一定的监管责任,对其下属应予有效的管理和约束,让他们职有专司,“每日黎明俱要齐集办公,不得托故不到,夜则轮流值宿,以便本县办理事件”,随时传唤,随叫随到。(64)衙署门子之选也要谨慎,衙门中传话、窥伺人皆由门子,门子就被视为“众奸之线索”,而江南地方门子“多以慧巧充之”,应该责革,“留忠贤者听用”。(65)也绝不可令小幕客渔利、家人藉端勒索乡民,以致民力不堪,激而上控。(66) 另外,在管理公共仓库时,官方要小心火烛,毋许闲人住宿;早晚还需检验封条,如有破烂,就要开仓查看,然后再加封条。(67) 新官到任时所用的铺陈银器等,三日后选合用的可以留下,但要“即时补价”。倘要全部退出铺陈银器,需要出告示说明:“本州县到任后,里长备办铺陈等项,俱一一退出。若收头不散小民,许指名告治。”生怕里长在其间科敛小民。(68) 衙门中的厨房,一般也被认为繁难之极,日常调度、下乡工作时的伙食安排、厨房中的同事关系等都需谨慎,“论署中闲住朋友,切莫心焦生怨”,也颇为要紧。而肉米油炭等物,都有官价,各州县自有定规。(69) 但是,衙门中买东西,“皆与半值,名曰官价”,有的甚至分毫不给。(70)所有日用食物布帛等项,在吏胥手中,往往是不依照时价,只付市价的十分之四五,也有勒派取用,并不发给一钱者,“短给而称为官价,白用而号曰当官”,以致行户赔垫,贾贩吞声,官既喜其省钱,役亦乐夫中饱。(71)这是很需要州县官反省而时刻注意的。在归有光任长兴知县时,衙门使用比较俭陋。他说:“衙内日取百钱,令卒出市,日不过斤肉蔬菜。去家三四百里,二子守庐舍读书,间岁来省,绝不与外交接。居二三日,便去。去自买小舟,肉不过二三斤,米不过一斗,衙前人共知之也。日常纸赎,多听告免。”(72)于公于私,归有光的操行都堪称地方官的代表。 按照制度规定,县衙中一应的薪米蔬菜等物,当然都要按日发价平买,不能赊取一物,否则假如有买办指称衙门赊取,以及亏短克扣、转换潮银的,查出后就要枷号重责,不能轻贷。(73)在康熙、同治等时期,都曾特别规定,衙门公馆中的床桌、棕垫、竹椅,往往都是借用的,“着各色铺户开单交付,工房事毕,工房照单交还,本户不涉地方”;向民间“借用”的县衙办公用具,到该地方官卸任时,仍要按约归还。(74) 五、官员的困境 对“大朝代”之王朝统治者而言,(75)江南不仅是收入的源泉,也是问题的频发地带,(76)官场陋习颇多。(77)而州县行政的繁难与民生的艰辛,又构成了江南社会生活的另一个面相。归有光的总结十分到位:“世以江南为富,而不知其民实贫也。”(78)后来姚希孟也说过:“三吴名为殷繁,实乃虚耗。”(79) 应该看到,在晚明的江南地区,仍有不少表现出众的知县,为世人所敬重,其事迹更被地方文人所记录而流传后世。比如,浙江东阳人王鈇在嘉靖三十一年任常熟知县时,“甫至即问民疾苦,新约刺剔蠹弊,吏民畏怀,咸趋事恐后”,而且亲率士民百姓积极抗倭。再如,嘉靖三十八年担任知县的黄嘉宾,其政绩也很不错,当地人管一德对黄氏在地方上加强治安、平抑物价、清理欺隐田粮、重视救荒等方面的良政,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80) 以归有光而言,其于嘉靖四十四年考中进士,被授职长兴知县。彼时的长兴知县空缺已久,政事都由胥吏把持,胥吏们勾结地方豪强,将地方赋役负担都转到贫民身上。履职不久的归有光即感到了多方面的压力,其“用古教化为治”的行动受到阻碍。对归有光的“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81)归有光因此多被官场中其他同僚与上级所排挤、诬谤。他在一份《乞休申文》中,详述了为政的困境及其被迫乞休的原因。年已六十的归有光,尽心从事行政工作,却得罪了下属老吏、官场同僚及上司,最终被迫乞休。(82)归有光应该不属海瑞指斥的那些“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给过往”的官吏之列,也不能“剥民以媚人”,(83)在官场中落得如此下场,似也正常。 而年轻的袁宏道在吴县任上,面对的都是多如牛毛的钱谷问题、茫如风影的人情问题,“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让他“几不知有昏朝寒暑”,感觉自己不成人形。(84)尽管吴县治于苏州城,这里的繁华生活,画船箫鼓、歌童舞女、奇花异草、危石孤岑、酒坛诗社、朱门紫陌以及振衣莫厘之峰、濯足虎丘之石都与他这个知县无关,他必须时时面对那些所谓“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85)工作之繁忙,让他深感自己不过是一个“奔走之令”,生活“最苦最下”。(86) 嘉定人娄坚(1567~1631),曾为三位前后相继的嘉定县官员呈请列入名宦祠崇祀,并将他们的杰出县政与德风作了扼要的概括。像朱廷益与熊密都曾任嘉定知县,王廷举曾任县学教谕,在县政表现上各有不同,大多都能做到为民请命、洁己爱民、赈济饥寒、征敛有法、宽仁为政、剪除凶暴等基本的为政之旨,且又“廉不为名”,深获地方士人的敬重和追思。(87) 万历二十七年(1599),进士出身、淄川(淄博)人韩浚接替王福征,出任嘉定县知县。在任期间,因为政深得民心,获朝廷表彰。同时,他还主持编纂了《嘉定县志》(万历三十年刊)。地方士人觉得也应思韩知县之为政而颂其美德,就由当地人娄坚写了一篇“考绩序”,送给韩浚。其开篇写道:“淄川韩侯,为予邑之期月,政令肃然,慢者知戢邑无逋赋。又二年,则废坠毕举,俗用丕变,虽小人罔不革面矣。报政于朝廷,得受训辞,以其官封其父母。于是邑之搢绅先生思所以颂厥盛美,而属予为之叙。……”(88)而根据韩浚主编的地方志记载,万历年间嘉定县田赋折漕的前后努力中,朱廷益、熊密、王福征到韩浚等知县,都颇有贡献,也可以说都有恩于地方百姓。(89) 在明清时期,“民间事少”可能是许多官员的“至愿”,而猾吏奸书则“利在多事”。(90)吏治清浊,关系民生休戚,可以说“属员之贤否,尤视大吏之贪廉”。(91)吏胥的作奸犯科,其实“全视乎官之性情,所贵喜怒不形,使彼无所揣摩。”(92)所以历代官吏的从政体会中,都会不厌其烦地讲到如何防范这一群体的作奸犯科。明人说过,除州县正印官员,“佐贰常有擅受民词,差人下乡者;或衙门积弊,相沿已久;或士夫所托,无可如何,亦未可尽责之佐贰也”(93),将一切的责任都推到了正印官员的身上,而轻视佐贰官吏的律己与律人之责,可能也是有失偏颇的。归有光认为,要堵截胥吏们在地方上的谋利之途,主要就在人命、强盗、粮长、徭役四个层面,这是州县官员们应有的防范意识。(94) 而朝廷对官员的要求中就说,“州县为民父母,上之宣朝廷之德化以移风易俗,次之奉朝廷之法令以劝善惩恶”,在地方上本应具有很高的权威(95),不可轻易让不良下属败坏地方风气。民情的上通下达,是作为“亲民之官”的州县官员的基本责任,其一言一动都能让百姓共见共闻,才堪称“亲”。(96)据说,同治年间的一位昆山知县在上任后,即行清厘案牍,遍历四邻,察访情形,询问疾苦,可能暂时达到了“民情通则上下不致隔膜,书差亦不能从中把持”的良愿,而深获上级官府的赞赏。(97)但要使明清时代的州县官都像海瑞那样,能恪尽职守,作为一名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具牺牲自我的精神,是不可能的,实际上这种精神的作用也至为微薄。(98) 注释: ①邹逸麟:《谈“江南”的政治含义》,收入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7~182页。 ②参冯贤亮:《明清江南州县的衙署》,载《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81~407页。 ③[明]撰人不详:《云间杂志》卷中,奇晋斋丛书本。 ④[清]方大湜:《平平言》,但湘良《序》(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八年刊本。 ⑤[明]娄坚:《学古绪言》卷二十《乞祀朱、熊、王三公于名宦呈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明]姚希孟:《文远集》卷五《书牍·万吴县拙庵》,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9册,据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张叔籁等刻清阁全集本影印,第334页。 ⑦[明]管一德编:《皇明常熟文献志》卷二《县令志小序》,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⑧[清]方大湜:《平平言》卷一,“造孽莫如州县”条,光绪十八年刊本。 ⑨何朝晖:《明代县政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⑩万历《大明会典》卷九《吏部八·关给须知》,万历朝重修本。 (11)[明]佘自强:《治谱》卷二《到任门·住歇、各履历册、交盘清查、拜士夫、往见上司》,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12)[日]滨岛敦俊:《方志与乡绅》,《暨南史学》2003年第六号,第241~242页。 (13)[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七《杂著·邑令箴》,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14)[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九《公移·乞休申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930页。 (15)[明]佘自强:《治谱》卷四《词讼门·居官第一须知》,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16)[明]刘时俊:《居官水镜》卷一《杂说》,“续情说”条,万历间刊本。 (17)[明]佘自强:《治谱》卷二《到任门·置各项簿》,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18)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二《吏部十一·考核一·官员》,万历朝重修本。 (19)[明]刘时俊:《居官水镜》卷一《理县事宜》,“征收之法”条,万历间刊本。 (20)[明]陈龙正:《几亭外书》卷四《乡邦利弊考·吴俗输税之弊》,崇祯间刻本。 (21)详参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锋译:《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22)万历《常州府志》卷六《钱谷志三·征输》,万历四十六年刻本。 (23)《明史》卷七十八《食货志二》。 (24)《明史》卷二百二十七《贾三近传》。 (25)[明]李乐:《见闻杂记》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万历间刻本,第207~208页。 (26)[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97页。 (27)[明]佘自强:《治谱》卷五《钱粮门·戒佐贰比粮》,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28)[明]席书:《席文襄公奏疏·南畿赈济疏赈粥》,收入[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百八十三,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29)《明世宗实录》卷三十四,“嘉靖二年十二月甲辰”条。 (30)[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煮粥诗”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05页。 (31)[明]佘自强:《治谱》卷十《杂事门·煮粥》,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32)[明]沈氏:《奇荒纪事》,民国《双林镇志》卷三十一《文存》附“条议”,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铅印本;又载蔡松纂:《双林镇志新补》(不分卷),“艺文”,嘉兴图书馆藏民国四年稿本。 (33)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44页引《康济录》。 (34)[明]陈龙正:《救荒策会》卷七《煮粥散粮辨》,上海图书馆藏崇祯十五年洁梁堂刻本。 (35)[明]陈龙正:《救荒策会》卷七《粥担述》。 (36)[清]佚名:《武塘野史》,不分卷,“崇祯十七年甲申”条,清抄本。 (37)[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七,“清慎勤匾”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569页。 (38)详参[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光绪十九年文昌会馆刻本。 (39)[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四《署震泽县禀到任后筹办地方大略情形由》,宣统元年南洋官书局石印本。 (40)[清]王凤生:《学治体行录》卷上《莅任》,道光四年刻本。 (41)[明]浦杲:《义衢记》,收入万历《嘉定县志》卷十九《文苑考上·文编一》,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42)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60页。 (43)详参光绪《嘉定县志》卷二《营建志·官署》。有仪轩,康熙十二年嘉定知县赵昕在县衙中始建。 (44)《清史稿》卷二百七十八《慕天颜传》。 (45)[清]曹尔堪:《魏塘政略序》,载嘉庆《嘉善县志》卷二十《艺文志下·杂文》,嘉庆五年刻本。 (46)[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三《纪耗羡归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40~141页。 (47)[清]汪辉祖:《学治续说》,“宜勿致民破家”条,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5页。 (48)杨联陞:《明代地方政府》,收入氏著:《国史探微》,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49)[清]何士祁:《补缺》,载[清]徐栋辑:《牧令书辑要》卷二《政略》,同治戊辰江苏书局刊本。 (50)[清]方大湜:《平平言》,卞宝第《序》(光绪十三年),光绪十八年刊本。 (51)[清]李伯元:《活地狱》,“楔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页。 (52)[清]叶镇:《作吏要言》,道光许乔年刻本。 (53)《清文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三,“咸丰四年八月甲子”条。 (54)[明]王锜:《寓圃杂记》卷三《记守令》,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页。 (55)[明]陆人龙:《型世言》第三十回《张继良巧窃篆、曾司训计完璧》,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04页。 (56)[明]叶权:《贤博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8页。 (57)[明]郑晓:《今言》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1页。 (58)[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九《总宪疏·申明宪职疏》,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59)[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二十《典铨疏·鼓舞士气安民生疏》,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60)光绪《重修常昭合志》卷十四《公廨志》,光绪三十年刊本。 (61)[清]叶镇:《作吏要言》,上海图书馆藏道光许乔年刻本。 (62)[清]叶梦珠:《阅世编》卷四《士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3~85页。 (63)[清]丁日昌:《丁禹生政书·藩吴公牍》卷一《饬禁佐贰杂职衙门擅受民词由(三月十四日行)》,香港:志濠公司,1987年,第1页。 (64)[清]佚名:《州县须知》卷三,“堂规二十则”,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65)[明]佘自强:《治谱》卷十《杂事门·访事法》,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66)[清]汪辉祖:《学治续说》,“官价宜有检制”条,第86页。 (67)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本,第207页。 (68)[明]佘自强:《治谱》卷二《到任门·收发什物》,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69)蔡申之:《清代州县故事》,第210页。 (70)[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九《总宪疏·申明宪职疏》,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71)雍正《钦定州县事宜》,“免行户”条。 (72)[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九《公移·乞休申文》,第932~933页。 (73)[清]佚名:《州县须知》卷三,“堂规二十则”,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74)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八《田赋下·役法》,光绪四年刊本。 (75)杨联陞指出统治中国的全境或其大部分,且传国久远的朝代,可以算是大朝代。参杨联陞:《国史诸朝兴衰刍论》,收入氏著:《国史探微》,第14页。 (76)[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28页。 (77)[清]丁日昌:《丁禹生政书·藩吴公牍》卷九《通饬各属毋许馈送酒席互相宴饮由》,第111页。 (78)[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十一《送昆山县令朱侯序》,第254~255页。 (79)[明]姚希孟:《文远集》卷十一《书牍·叶长洲(乙丑)》,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9册,据国家图书馆藏崇祯张叔籁等刻清阁全集本影印,第402页。 (80)[明]管一德编:《皇明常熟文献志》卷二《县令》,万历三十三年刻本。 (81)《明史》卷二百八十七《归有光传》 (82)[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九《公移·乞休申文》,第928~929页。 (83)[明]海瑞:《海瑞集》上编《淳安县政事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页。 (84)[明]袁宏道,钱伯城笺校:《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锦帆集之三·尺牍》,“沈博士”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19~220页。 (85)[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锦帆集之三·尺牍》,“兰泽、云泽叔”条,第211页。 (86)[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五《锦帆集之三·尺牍》,“汤义仍”条,第224页。 (87)[明]娄坚:《学古绪言》卷二十《乞祀朱、熊、王三公于名宦呈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明]娄坚:《学古绪言》卷三《赠邑侯韩使君考绩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9)万历《嘉定县志》卷七《田赋考下·漕折始末》。 (90)[明]刘时俊:《居官水镜》卷一《理县事宜》,“驭役之法”条,万历间刊本。 (91)[清]赵申乔:《赵恭毅公剩稿》卷六《告示·严饬官方以肃功令示》,乾隆二年赵侗斅刻本。 (92)雍正《钦定州县事宜》,“防胥吏”条,同治七年江苏书局重刊本。 (93)[明]佘自强:《治谱》卷九《待人门·待佐贰五段》,崇祯十二年胡璇刻本。 (94)[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九《公移·乞休申文》,第932~933页。 (95)雍正《钦定州县事宜》,“听断”条。 (96)[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五《札饬查明开征不贴简明告示各州县详记大过一次》。 (97)[清]丁日昌:《抚吴公牍》卷十三《昆山县禀到任后清厘案牍下乡察访情形》。 (98)[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