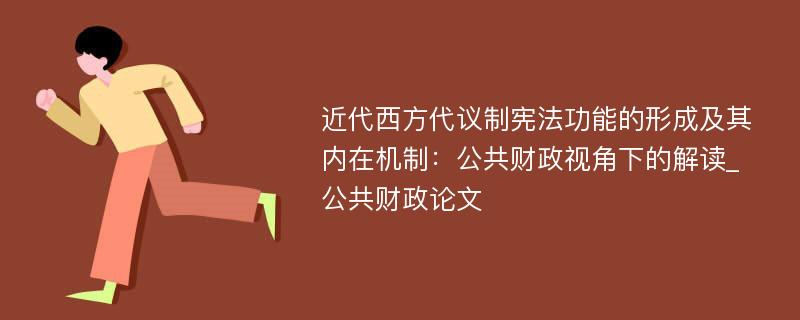
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种基于公共财政视角下的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代议制论文,宪政论文,机理论文,近代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宪政,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舶来品。我们对于宪政认识得还不够深不够透,缘于对西方宪政的模式及其内在机理还缺乏历史的考察和深入的分析。西方宪政的奥秘和机理究竟是什么?答案不在历史之外,而在其宪政的形成历史之中。尽管西方宪政的模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变化相当复杂,但确有规律可循。西方古典、中世纪时期的宪政模式,强调的是行政权力要依司法而行事,而近代西方的宪政模式强调的是行政权力要接受议会的监督和约束。究其宪政模式变化的深层原因,在于近代以来对行政权力进行单一的司法规制已不合时宜。因为,无论从国内需要,维持地方秩序,统一度量衡,还是从国际需要,争夺殖民地,发展海外贸易,都需要加强国家的行政权力,并给行政权力的行使以更大的灵活性。政府刻板的依司法行事只能造成政府行为的低效率,从而无法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也就是说,司法与行政是两回事,行政权力在司法领域要守法,而在政治领域则要根据时势的需要应有所变通,但又要有约束。近代西方国家对行政权力的强化和约束,主要是通过代议制建构国家公共财政实现的。而从宪政史的角度看,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内在机理就在于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
一、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
(一)西方古典、中世纪时期的司法型宪政模式及其弊端。在西方,宪政体制渊源于古希腊的雅典,不过雅典是通过直接民主来实施宪政和建立公共权力的,雅典的宪政模式只适于小城邦,并不适合庞大的地域国家。而当罗马帝国出现时,由于帝国不可能在其庞大地域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而又没有建立起代议制的宪政组织机构,从而使罗马帝国无法建立具有公共性的国家权力,为维护公共需要,它只能走向帝制,开始强调“国王的意志即法律”、“国王不受法律限制”。从行政效率来考虑,帝制不乏其合理之处。然而,帝制又与罗马的司法公平发生着冲突,因为“王在法之下”是罗马法治精神的基本原则。如此以来,行政效率与司法公平二者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影响罗马帝国后期发展的体制悖论:“罗马法成功地将人际关系植根于法律之上,却无法将同样的模式转用在政府的活动上面。……共和体系纵然会用严格的法律,来约束官员的活动,到后来,却承担不起帝国的政治责任,惟一的解决办法只好让皇帝掌握无限的权力。罗马人民理论上依然是帝国权威之源,这正如他们同早期的行政长官是同样的关系;可实际上,却不存在实现民意的合法途径。这意味着,他们再无法凭借法律手段,把皇帝及其大臣约束在法律范围以内。惟有道德制裁一端可以运用;然而这样的社会长期重法律而轻伦理,道德制裁力量太弱。”① 中世纪西欧存在宪政,我们勿庸置疑,但中世纪西欧的宪政模式,依然是强调“王在法下”,即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权力,其局限也是明显的:“所有中世纪宪政的根本缺陷是,除非诉诸暴力革命或以之相威胁,它便无法对事实上践踏臣民权利(毫无疑问不属于国王合法权力范围)的君主执行惩罚。”② 由此,我们从中可以窥探出西方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司法型宪政模式的弊端:行政权力过分受司法约束会使政府丧失效率,而行政权力的过分鼓胀又会侵蚀民众的个人权利。事实上,“所有的古代民族,都无法在这种极端下面维持平衡,这样,古代民族虽然企图创造植根于法律的社会,却难免失败。”③
(二)代议制宪政模式在西欧中世纪城市中的萌生。近代西方宪政的基本模式是代议制,而“近代立宪主义的实际存在首先出现于11、12世纪西欧的城市法律制度。”④ 也就是说,代议制最先起源于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市政大会乃是自提比略以来的第一个代议政府;实在是他们,而非《大宪章》开今日民主政治的先河。”⑤ 由于在中世纪西欧没有不设防的城市,所有的市民都必须共同关注城市防御,并通过议会的形式来共同承担防御经费,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场重大的体制革命。“因为纳税者这时是根据自己的能力为公共事业纳税,而不是为诸候的个人利益缴纳专断的封建税。这样,税收就恢复了它在封建时期所丧失的公共性质。为了估定与征收这种税款,为了应付随着城市人口增加而产生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设立或选举市参事会很快就成了必要。……12世纪时,各处的市参事会都成为公共权力机关所承认的组织,并且成为每个城市中相沿的制度。”⑥ 由此可以看出,税收是代议制之母,代议制主要是基于税收和公共财政的需要而产生。正如孟罗·斯密所指出:“中世纪城市之新政治形式,乃一种代议政治”。⑦ 中世纪城市正是通过代议制完成了财政的公共化建构,并从根基上确保了城市行政权力的公共性,从而也就开创了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先河,并为近代西方民主形式提供了样板。正如萨托利教授所指出的,近代西方民主并不是古希腊式的民主,即直接民主,而是代议制民主,人们之所以会轻易地忘掉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区别,是因为人们为求简洁而只说“民主”。⑧
(三)代议制宪政模式在近代英国的确立。近代欧洲,伴随着争夺海外贸易和维护国内秩序的需要,使得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单位发生了变化,即由地方性的城市转变为地域性的民族国家。此后,民族国家的主权理论一直是市民阶级用来对抗中世纪教会和封建领主,消除地方割据的有力武器。起初,市民阶级的要求在于增加而非削弱国家的权威,而对国家的组织形式并不关心,只要国家能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保证社会健康发展,他们便愿意无条件服从于国家。也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人们可以有秩序而没有自由,但他们不能有自由而没有秩序。”⑨ 而随着以国王为代表的行政权力对市民阶级人身和财产的一次次恣意践踏,市民阶级才认识到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和规范,并应由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机构来监督和实施。即,开始强调“对治理权,要在中世纪的法律限制外,再加一道现代政治控制”。⑩ 然而,中世纪的政治文化强调的是,政治事务乃是国王的专利,非国王外,“任何人不得捣乱神秘的国家和政府事务”。(11) 即使是议会也不得染指政治事务,从而也就决定了,“中世纪议会的权力根本无法与现代的议会相比,管理公共事务的责任仍然在于君王的执政官员,同时即使最无能的君王,也不愿承认这些议会代表是平等执行政府事务的参与者。”(12) 也就是说,现代议会并不同于中世纪的议会,后者是王室行政系统的附属物,前者却是拥有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权力的独立政治机构。作为一种革命性变革,1688年英国的宪政危机最终引发了英国议会由中世纪议会向现代议会的蜕变。从此,英国的议会开始代表全体国民,开始为国民的利益并以国民的名义反对国王。(13) 通过代表人民,英国议会被注入了新的意义,成为了政治机构,开始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监督,对政府的行政权力构成了有效监督和约束,从而也标志着英国新的宪政时代的来临。即,议会的政治责任开始取代司法责任而成为新宪政的组织原则和模式。英国光荣革命后,议会被确立为财政与立法的终极权威,成为英格兰政制中的一个常规和正式机构,“常任议会时代由此开始”。(14) 光荣革命开启了议会“至高无上”的时代,它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英国民族国家政府的组建问题:现在的国王是“议会中的国王”,而不再是王朝政府时“单独的国王”。(15)
(四)代议制宪政模式与公共财政紧密相关。作为事实,近代英国议会也是经历了长期税收斗争和财政危机后,才最终确立起其政治地位的。正如伯克所指出:“这个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从一开始正是主要围绕税收这个问题而展开的。”(16)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废除了王朝财政体制,将国家财政置于议会的管制之下,完成了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此后,议会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纳税组织,而开始成为对税收征用有决定权和使用有监督权的政治机构。议会开始有权知道拨款的使用情况,最终改变了国家财政与王室收入混淆在一起的中世纪财政体制,完成英国的财政体制由中世纪王朝财政向近代民族国家公共财政的蜕变,“议会也最终成为英国宪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7) 通过代议制宪政模式使得议会与行政之间形成了分权与制衡,最终确保行政权力的行使“仅仅是为了公共福利。”(18) 英国的代议制宪政形式,奠定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基本模式。美国、法国等国家宪政变革的导火索事实上也都是由财税问题引燃的,而其国家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规范,也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完成的。1763年,英国议会与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发生冲突时,北美代表者强调税收唯一的合法机构应当是殖民地议会,而不是英国议会。《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国“未经我们同意便向我们强行征税”。实际上,这个保证英国民族避免王室专制的议会,对北美殖民地实施的却是一种专制的权力。所以,伯克指出:美国人反叛英格兰,“跟英格兰人1688年反叛詹姆斯二世,属同一性质”。(19)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仍是由财税问题引起的。路易十六为了筹集税收,迫不得已于1789年重新召开自1614年以来从未召开的三级议会,然而却引发了法国宪政革命,路易十六步英国查理一世的后尘,成为因忽视和践踏税收宪政原则而被送上断头台的又一个牺牲品。最终,近代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都是通过效仿英国代议制宪政模式而走向宪政道路。故此,宪政史家波拉德将议会称为英国对文明的最大贡献。(20)
二、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内在机理
(一)公共财政的本质及其宪政意义。公共财政主要包括国家财政的公共提供和公共支出两个方面。公共财政本质是一种有偿财政,是纳税人基于对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采用让渡其部分财产所有权为代价来获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手段。从本质上说,公共财政蕴含了纳税人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也就是说,国家的征税权力是与其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相对称的,人民的纳税义务是与其享有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相对称的。公共财政国家,“可被看成是个人参加而结成的合作联盟,形成联盟就是为了解决社会共存的问题并且按照民主和公平的方式解决问题。”(21) 换言之,近代西方国家的社会契约论精神,正是通过公共财政体现的,公共财政理论认为,人们向国家纳税——让渡其财产的一部分,为的是能够更好地享有国家的公共服务,国家财政不具备公共性,国家也就不具有合法性。因为,“权利与义务二者的范围与性质决定了国家政体的性质”,(22) 正像狄骥所指出的,国家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但“这种公共权力绝不因它的起源而被认为合法,而只能因它依照法律规则所作的服务而被认为合法”。(23) 故此,公共财政在某种程度上就构成了现代国家合法性的一块重要基石,没有公共财政,就不能保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也就不能确保国家权力仅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性和责任性,国家权力也就谈不上具有宪政品质。对于公共财政在近代西方国家宪政中所起的根本性作用,马克思曾作过经典论述:“究竟为什么财税、同意纳税和拒绝纳税在立宪主义历史中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正像农奴用现钱从封建贵族那里赎买了特权一样,各国人民也要从封建国王那里赎买特权。……为了保障自己的这些自由,他们保存了经过一定期限重新确定税款的权利——同意纳税的权利和拒绝纳税的权利。在英国历史中,可以特别详细地探求出这一过程。”“所以,在中世纪社会中,赋税是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国家之间的唯一联系。由于这一联系,国家不得不对资产阶级社会作出让步,估计到它的成长,适应它的需要。在现代国家中,这种同意纳税和拒绝纳税的权利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对管理其公共事物的委员会、即政府的一种监督。”“因此,部分地拒绝纳税是每一个立宪机构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我决不想否认这一点:使查理一世上了断头台的英国革命就是从拒绝纳税开始的。以宣布北美脱离英国而独立告终的北美革命也是从拒绝纳税开始的。……拒绝纳税正是社会对于威胁其基础的政府所采取的一种自卫手段。”(24) 公共选择理论学者布伦南和布坎南也都认为:“财政约束实际上可以代替选举约束,也就是说,即使在选举约束失效时它们仍然有效。”并一再强调“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英国议会通过限制君主的税收而处于支配地位,这是我们的政治遗产的一部分。”(25)
(二)议会对公共财政的组建。根据社会契约和公共财政精神,纳税人和征税国家二者的正当逻辑关系应该是人民先同意纳税,然后国家才能征税。同时,税收的使用也只能用于国民的公共服务,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公共财政体制下的纳税人对税收的征收和使用,有了解和知悉的权利。如此看来,近代西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是由公民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决定的,财产所有权归国民,国家的征税就要遵守“国民的同意”和“无代表则不纳税”原则,而任意征税就是对国民私人财产的一种掠夺。于是,在近代西方国家权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出现了一种背反现象,从国内和国外的实际要求出发国家行政权力需要不断扩大,但由于其前身是王朝国家,国家权力具有明显的国王私人属性,使其无法从金融和财政上为其权力扩大提供物质保证。因为,王朝国家的财政制度并没有区分清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与国王的个人收入和支出,从而使人很难确切地知道哪些是国王个人的花销,哪些是国家的支出。结果造成,国王不愿将其收入花在公共事业上,人民不愿将其赋税用于国王私人花销上,而使国家陷入了“宪政危机”(Constitutional crisis)和人民税收抗争。而此时人民的税收抗争的重要特点是:他们并不是简简单单地一次性削减国家的税收和支出,而是明确立宪约束,以保证国家税收和财政收支的公共性。事实上,近代西方国家的公共财政建构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利益分化过程中的公共利益实现问题,是与私有财产的形成和社会认可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国,“公共”一词也只是从17世纪中叶才开始使用的。(26) 正像亨廷顿所指出的,在一个私有制的社会,“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公共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27)
近代西方各国在公共财政建构的探索中,最终找到了代议制手段,近代西方国家无一不是通过代议制来完成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代议制与公共财政建构可以说是一对孪生体。因为,伴随着近代西方国家私有财产的发展,必然引发私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冲突,而代议制正是平衡和协调二者关系的桥梁。事实上,代议制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私与公之间的分离存在着内在关联。历史表明,并不是为了实行代议制而有必要作出私与公、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划分,相反,代议制倒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标志与产物。也就是说,代议制只有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真正分离时才能产生和存在。代议制产生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历史过程中,其基本使命在于划清国家权力与私人权利的边界,作好二者的利益平衡。因为,不恰当地强调政府权力,个人权利就会受到威胁;过分强调后者,政府权力软弱就难以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所以,严格地讲代议制产生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标志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分离,而在于它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的互动搭建了协调机制。因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伴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使得国家不能直接参与经济生活,参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而只能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即通过税收的形式获取财政收入,“公共事务几乎没有一项不是产生于捐税,或导致捐税”。(28) 而此时,代议制是政治国家获取财税的根本组织。议会通过对税收的征收和使用进行组织和监督,来保障税收取之于国民,用之于国民,从而也就能提高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因为国民相信赋税是缴纳给自己的,因此愿意纳税。”(29) 从而能将财富从民众手中过渡、转让到国家手中,并最终增强国家的力量,而现代民主国家的力量正是建立在税收的基础上。现代民主国家通过代议制来组建公共财政,使得“所有宪法政府本质上都是有限政府”,但“限制政府并不是要削弱它”。(30) 而专制主义国家则不同,尽管理论上专制主义的国王可以权力无限,实际上它常常是难以作为。由于专制主义国家财政体制的公共性不足,使其难以有效地获取公民的税收,结果也就无力动员国家的全部财力。事实上,“旧制度正是因为不堪财政困难的重负而垮台的。”(31)
(三)议会对公共财政的监管。随着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人们开始对经济生活、对私人利益给予更多兴趣,而日益缺乏对政治生活的关注。在一次次受挫后,有产者发现只有通过集体抵制,才能防止行政权力的“权力寻租”,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也就是说,若欲有效地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便必须创立某种外在于行政权力的组织机构,它受社会委托、代表民众来“专职”监督政府行为,而议会正是这种组织。近代以来,“正是靠了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各社会阶级逐渐意识到其政治义务,西方世界逐步创立了有组织的公民社会”。(32) 议会能将社会多元利益集团整合起来,形成有效的社会组织,并通过具体的公共财政预算,来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监督,从而将政府的活动纳入议会的政治框架之中。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33) 近代国家议会的主要专职之一,就是对国家公共财政进行监管。因为,鉴于公共财政直接关系到对纳税人的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或剥夺,对整个社会及个人权利的保护来说关系极为重大,由议会来负责,而不能委任于其他机构,尤其是行政机构不能滥用征税权。正像孟德斯鸠所指出的:“如果行政者有决定国家税收的权力,而不只是限于同意而已的话,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这样的行政权力就在立法最重要的关键上成为立法性质权力了。”(34) 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议会代表着纳税人的利益,反映着纳税人的呼声,有权对政府要不要征税、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怎样征税等重大税收问题作出决定,有权监督政府的税收使用情况。同时,近代以来随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日益增大和每年国家财政花销变动不居,使得仅由议会制定的法律来规定捐税是不够的。法律可以保持稳定不变,捐税却要根据时势需要随时调整。如此以来,人民要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保证其公民地位就应对国家的行政花销加以约束和监督,这不仅要依靠明文规定的法律,而且还要依靠更加直接的和更加经常性的组织监督,这便是议会在近代以来成为一个常设性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要维护纳税人的权利,就要对政府的财政花销给予有效监督,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之所以严格保留税收立法权及监督权的最重要理由。对此,人们已达成共识:代议制的适当职能不是管理——这是它完全不适当的——而是监督和制约政府。(35) 即,“议会并不只是制定规则或以立法的形式公布某些决定,议会主要是一个辩论和批评政府的场所,是主要的自治工具,这是它最为重要的职能。”(36)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近代西方国家宪政形成的经验可以得知,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依赖税制的变化,依赖于国家公共财政的形成。事实上,只有站在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高度,才能更深刻理解和把握近代西方国家代议制宪政功能的形成及其内在机理。因为,近代西方国家伴随着对私人产权的形成和确认,必然会产生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分与对峙。代议制通过公共财政的建构在权利与权力的对峙中开启了制度创新,从而使得权利与权力在对峙找到了连接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在对立中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即,“市民社会通过议员来参与政治国家,这正是它们互相分离的表现,并且也只是二元论的统一的表现”。(37) 一言以蔽之,代议制下的公共财政,是人民依社会契约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财产而使国家具备财力来满足人民公共需要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最终弥合了征税主体——国家与纳税主体——人民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消极对立局面,使得二者开始趋向和谐一致、彼此相得益彰。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代议制既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二元结构分离的标志,又是二元结构得以联结的纽带,并因此而成为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基本模式。
注释:
①③(12)(32) [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黄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50~51、36页。
②⑩(11)(13)(14)(19)(30) [美]C·H·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8、74、92、78、89、4、119页。
④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9页。
⑤ [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信仰的时代》(中册),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89页。
⑥ [比利时]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64年版,第91页。
⑦ [美]孟罗·斯密:《欧陆法律发达史》,姚梅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⑧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等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316页。
⑨(27)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23页。
(15) [美]道格拉斯:《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罗仲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6)(17)(20) [美]理查德·派普斯:《财产论》,蒋琳琦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80、147页。
(18) [美]格瑞特·汤姆森:《洛克》,袁银传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2页。
(21) [美]詹姆斯·M·布坎南、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类承耀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22) [美]H·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23) 张学仁:《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07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3~304页。
(25) [澳]布伦南、[美]布坎南:《宪政经济学》,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26) [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28) [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7页。
(29)(3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1、164页。
(31) [法]雷吉娜·佩尔努:《法国资产阶级史》(下册),康新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45页。
(35) Birch,A.H.,An Essay on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Representative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Toronto,1969.P17.
(36) [英]W·Ivor·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6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
标签:公共财政论文; 代议制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英国法律论文; 英国议会论文; 宪政论文; 税收原则论文; 政治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