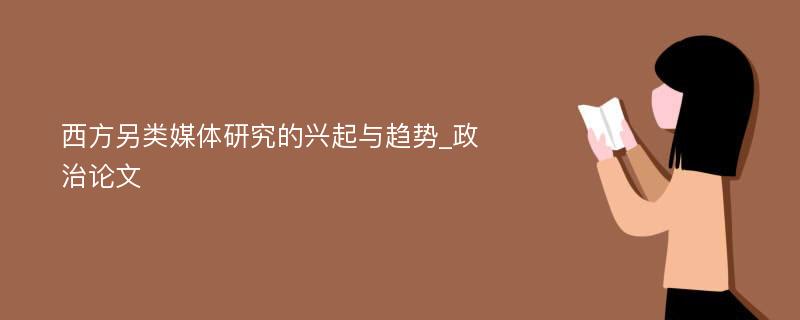
当前西方另类媒体研究的兴起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另类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1)05-0017-09
“媒介具有权力”是20世纪初西方传播研究确立的一个普遍的理论假说。当商业媒体的报道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舆论场中占据了绝对的权力的声音,并因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下日益加剧的跨国家、跨行业、跨媒体的兼并和垄断而导致民主传播赤字不断上升时,众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大声疾呼的批判声中,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表达了过度商业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浪潮会极大损害媒体民主发展的忧虑,并期望以“富媒体,穷民主”的隐喻在反讽当下媒介现实的过程中唤起全社会对媒体所有权及传播民主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正是在这种警醒性的批判声中,一股挑战主流商业媒体信息发布权力、观点主导权力和私有制所有权权力并代表普通民众发声的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开始兴起。这类媒体的媒介行动主义者正是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对“主体”和“自治”等概念的表述和实践描绘中,发现了挑战主流商业媒体文化霸权以及建构自主传播渠道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他们在批判媒介圈地的基础上,将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在争取传播公地并期望实现与媒介资本决裂的自治传播实践上,并形象地提出“不要恨媒介,成为媒介”等行为主张。这种积极乐观的行动主义传播理念与实践诉求,使另类媒体不仅成了推行重建传播公地这一理想的实验田,而且大力推进了批判性的媒介素养教育,为提升公众的主体批判意识打开了一扇门。
基于上述另类媒体对媒介现实的挑战和传播理念的更新,对这类媒体的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后,随着这类媒体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大力推动下逐渐形成“哪里都有我们”的全球传播态势,学界对其研究的著述也更为丰富。本文以近25年来西方另类媒体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为依据,深层分析另类媒体兴起的媒介环境与实践诉求,试图在解析当前西方另类媒体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剖析其存在的权力意义,并提出未来其研究展开的重心和方向。
一、另类媒体兴起的媒介环境与实践诉求
“老大哥”,一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1984》中的虚构人物,通过控制全社会的大众传媒来监视所有人的隐私,并利用自己对新闻、信息和流行文化的控制来制造一个顺民的社会。如果说这种对传媒的人为操纵只是奥威尔小说中想象的场景,那么反观当下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控制权日益集中的现实,这难道不是如今西方全球性媒体景观的真实写照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媒体的控制权在国家政府逐渐放松管制的表象下,日益由少数私人公司的巨型跨国公司所控制。1983年,美国学者本·H·巴格迪肯(Ben H.Bagdikian)出版的《媒体垄断》(The Media Monopoly)一书,正是对50家超级联合公司如何主导美国大众传媒现实的真实呈现。当此书于2000年发行第六版时,这些媒介垄断公司的数量已由原来最初的50个下降到6个。①
在追溯这股媒体兼并之风的源起时,不少传播学者将时间的钟摆调回到大众化报刊替代由国家意识形态主导的党派报刊从而使大众媒介走上商业化发展的19世纪中期。然而,走出“媒介中心主义”本位后,历史学家却在还原媒介圈地扩张与传播公地萎缩的现实面前,通过回溯公地和圈地的进程,呈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自由主义者努力推动媒介兼并浪潮的更深层的历史关联。
公地和圈地是一对不断变化的概念,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到当下的反商业主义全球化的漫长历史时期,这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从特指走向泛指的过程中不断扩大化。尽管圈地的进程分散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在14世纪至19世纪间发生于英国的圈地运动被视为世界圈地历史坐标的原点,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所言:“剥夺英国农民的农业生产地并将其赶出原先以耕作为生的土地是整个圈地运动过程的开始。”②也正是在这种圈地开始的进程中,人们见证了英国大部分公地资源及公地制度的消亡。③事实上,圈地运动并不是英国的特有现象,随着时间的推进,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蔓延,这一进程本身对原有的生产和再生产体制、文化、领土及时间造成了断裂,原先基于满足当地市场和社区共同体需求的地区差异经济生产,被着眼于满足地区、国家及全球市场的资本主义统一生产链所取代。正是基于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被圈占的对象从最初的自然资源扩展到一切能在私有化、商品化过程中产生资本增值的事物,大众媒介亦不例外。
回顾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史,直至19世纪以前,以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作为交流工具一直是上流社会的精神特权。然而,19世纪初期,伴随工业革命和政治民主化的进展,西方发达国家涌现出了第一批面对普通大众的“便士报”,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传媒的结构和性质。除了占非主导地位的公共广播电视的存在外,绝大多数媒体大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企业,其主要财源不是政党报刊时期的财政补贴,而是商业广告,并因经济独立而被誉为除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之外的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力,从而在隐性的经济控制代替显性的政治控制的转变过程中实现了媒介控制方式的改变。正是在这种控制方式的转换过程中,市场经济力量主导下的媒介商业化圈地进程悄然开始,并于19世纪末的报业垄断时期达到第一次以纸质媒体为主导形式的媒介圈地高潮。不过鉴于当时存在保护更多竞争者进入媒体行业的主张,媒体的寡头统治局面和全球传播帝国并没有形成。直至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后,在要求更多私有化、商业化以及解除管制的市场自由主义的呼声中,西方传媒集团开启了跨国家、跨行业、跨媒体的以多元媒介融合为主导形式的第二次媒介圈地高潮。媒介兼并之风发展至今,当下的世界新闻传媒市场基本上掌握在迪斯尼、时代华纳、索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和贝塔斯曼这六家跨国公司的手中。
面对全球传媒帝国的建立,当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将自由市场与民主画上等号,并认为媒体的跨国发展会带来更多的媒体民主时,批判学者们却在民主的阶级划分过程中看到了“联合媒体爆炸式发展与公共生活逐渐萎缩之间富媒体—穷民主的悖论式命题”。④如果说媒体民主有利于媒介权力的拥有者,那么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无疑是媒体民主的受益者,但是,若将民主与社会上占多数的普通民众联系在一起,那么代表当下精英民主观的商业媒体民主却成为了一股反民主的力量,即媒体由少数人控制,民众的声音无法在媒体中得到充分表达,参与式民主无法突破哈贝马斯期待中的那个由白人有产者主导的公共领域而在草根阶层的另类公共领域中实现。
正是为了挑战认为商业媒体是反民主力量的批评,基于对媒介民主传播赤字这一现实不满而产生的媒体改革运动不断兴起。然而,囿于将媒体民主改革的期望寄于主流商业媒体在微观机制的变革而忽视其赖以生存的宏观环境,这些运动因而无法完全实现其改革的初衷。伴随这些改革运动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后,一些媒介行动主义者充分意识到,新闻公共哲学的实现有赖于媒介体制的变革,正是在主流商业媒体无法实现去私有化、商业化的所有权制度转变而无力践行更彻底的参与式民主的现实面前,他们尝试通过自主创办独立的另类媒体来实现媒体的公民控制。这种公民控制既代表了更多社会上的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又彰显出一种更彻底的社会控制,即在另类媒体创建和运作过程中,一方面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通过反霸权运动在市民社会中争取文化领导权;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领域,通过非商业化的运作将媒体的经济属性与存在意义“嵌入”社会公民的需求之中,而不是将媒介作为“自由调节市场”的赢利工具,从而以行走于国家和市场控制之间的自主传播来实现以价值理性为引导的重建传播公地的理想。
那么究竟什么是另类媒体?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曾将另类媒体简单化地定义为来自主流商业媒体之外的选择,然而,这种消极的剩余范畴的定义意味着“另类”就是被不幸限定在永久的边缘状态。于是,超越以主流商业媒体为定义参照的视野,从另类媒体的新闻内容、民主运作以及行动目标等层面来界定其内涵,才能真正发掘另类媒体的生存形态。首先,在新闻内容的制作方面,“另类媒体非但自己不标榜主流商业媒体一直宣称的客观性,反而公正声称反对或怀疑主流的、制度化的政治,它们希望能代表那些认为自己的观点在现存的本地或全国性传媒中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群体”⑤;其次,在民主运作方面,与主流商业媒体的等级分工相比,另类媒体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尝试以合作民主的形式进行自我管理,并在制作新闻、节目的编辑事务中贯穿这种精神;最后,在行动目标方面,另类媒体倡导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批判性评价以及提倡社会变革,期望在积累式的行动中推动公民在自主传播过程中实现政治赋权。
二、另类媒体理论研究的视角与路径
与以大众传播为目标的大众媒体的研究相比,另类媒体的研究曾较为边缘。鉴于近年来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此起彼伏,媒体民主改革运动的不断推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媒体扩张以及另类媒体对传播机制和社会变化产生的影响,对这类媒体的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起步,并以1999年西雅图事件中诞生的独立媒介中心的举世闻名为契机迅速发展起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西方国家的一些大学在新闻传播学、媒介与文化研究、社会学等领域开设另类媒体的课程,讲授另类媒体在实践中呈现出来的传播、文化、社会等现象及问题,并将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师米特齐·华尔兹(Mitzi Waltz)于2004年出版的《另类媒体与行动主义媒介》(Alternative and Activist Media)一书作为教材。另外,由英国爱丁堡龙比亚大学创意工业学院的克里斯·阿顿(Chris Atton)与乔治亚大学格莱德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F.Hamilton)合作编写的关于另类媒体的最新教材《另类媒体新闻学》(Alternative Journalism)也已正式出版。
其次,研究另类媒体的专著不断涌现,主要的代表作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学者独著是以另类媒体作为整体对象来进行考察的,如约翰·唐宁(John Downing)的《激进媒介:另类传播的政治体验》(Radical Media: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1984)与《激进媒介:反抗传播的社会运动》(Radical Media: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2001),克莱门西亚·罗德里格斯(Clemncia Rodriguez)的《媒介平台中的裂缝:公民媒介的国际研究》(Fissures in the Mediascape: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Citizens' Media,2001),克里斯·阿顿(Chris Atton)的《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2002)与《另类互联网》(An Alternative Internet,2004);第二类学者独著主要以特定国家的另类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如蒂·蒂·哈勒合(Dee Dee Halleck)记录美国另类电视媒体现状的《手持记录:社区媒体不可能的可能所在》(Hand-held Visions:The Impossible Possibilities of Community Media,2002),安妮·伍兹沃思(Anne Woodsworth)的《加拿大的另类新闻业:自1960年以来地下的、革命的、激进的和其他另类系列出版物之名录》(The Alternative Press in Canada:A Checklist of Underground,Revolutionary,Radical,and Other Alternative Serials from 1960,1972),以及由阿方索·古穆西奥·达格龙(Alfonso Gumucio Dagron)记录拉美传播运动的《变革的浪潮:参与式传播带来社会变迁的故事》(Making Waves:Stories of Participatory Communication for Social Change,2001);第三类文著则是按主题将对另类媒体的研究汇成文集,如由凯特·科耶尔(Kate Coyer)等三位作者于2007年合作编著的新作《另类媒体手册》(The Alternative Media Handbook,2007)等。
最后,以另类媒体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多,其中《语言与传播调查》(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2000)、《媒介历史》(Media History,2001)、《澳大利亚国际媒体》(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2002)、《媒介、文化与社会》(Media,Culture and Society,2003)、《新闻业:理论、实践与评论》(Journalism:Theory,Practice and Criticism,2003)、《媒介发展》(Media Development,2003)、《新闻学研究》(Journalism Studies,2005)七份学术期刊曾开辟特刊,专门探讨另类媒体。
从数量上看,虽然研究另类媒体的文献不断增多,但由于仍处于起步阶段,分析的切入点和视角比较单一,然而,其主要观点和思路在一些代表性著作中可以得到清晰的呈现。
1984年英国学者约翰·唐宁出版的著作《激进媒介:另类传播的政治体验》可被视为系统研究另类媒体的起点。全书按地域分章节分别介绍了美国、葡萄牙、意大利、东欧各国历史上的各类另类媒体。在叙述中,作者主要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在政治意义层面将另类媒体具体界定为激进媒介,通过研究激进的印刷和广播媒体,他认为作为社会运动的传播介质,激进媒介是由政治积极分子因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创建的媒介,其意义在于它有潜力通过集体行动唤起人们的政治意识,从而改变社会。2001年修订版本的《激进媒介:反抗传播与社会运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印刷及广播媒介,将研究范围在媒介形态上扩展至公共演讲、舞蹈、歌曲、涂鸦、服装、街头戏院、木刻、传单、海报、壁画、电影、录像、互联网等,在地理空间上延伸到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中国、伊朗、爱尔兰、墨西哥、摩洛哥、尼日利亚、俄罗斯等。与1984年的著作相比,虽然本书的内容在历史背景及地理空间的维度上得到拓展,但是全书的主旨与前书基本保持一致,即强调在社会运动的历史语境中考察激进媒介在政治组织及行动上的意义,其重要性不仅体现 在激进媒介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内容上,更在于其嵌入社会运动的组织形态上。
针对约翰·唐宁的研究,克里斯·阿顿(Chris Atton)认为1984年的著作由于写于1989年苏东剧变发生之前,因此,文著中描述的针对政党和国家压迫性力量而产生的激进媒介是社会运动在实践中传递信息和行动号召的载体。虽然另类媒体的形态和案例在2001年修订后的著作大大增多,但主要是历史形态的描述,如:18世纪、19世纪英国的政治漫画、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德国劳工的歌曲等,强调的主要方面仍然基于针对政治上的压迫而唤起政治行为以改变社会,这一点从文著的副标题“反抗传播与社会运动”(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即可看出。这种对政治层面的过于强调使其忽视了以文化方式呈现的、非政治性的另类媒体,这种媒体的存在并非要产生政治层面上的行动效果,更多的是通过其生产的方式、传播的内容来展现创作者个体的态度和立场,这类另类媒体多以“迷志”(fanzine)的形态存在。为了突破约翰·唐宁对激进媒介过于政治化方面的强调,克里斯·阿顿在《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2002)一书中呈现了作为文化现象存在的另类媒体。与此同时,他将对另类媒体研究的时间段界定在1990年以来,强调除了注重另类媒体通过工具性话语挑战并改变社会关系的潜能外,还要关注另类媒体的内容是如何生产的,换句话说,他认为另类媒体本身的组织形式及生产过程同终端的内容话语同样重要,因此,他在书中从经济生产的角度介绍了另类媒体的运作过程,并将另类媒介放置于新社会运动的大背景下,考察公众在参与组织决策及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
与约翰·唐宁相同,克莱门西亚·罗德里格斯在《媒介平台中的裂缝:公民媒介的国际研究》中承认另类媒体可以使普通公众在政治上赋权,当他们成为创建媒介的主体时,便更有能力代表自己和所属的社区表达观点和意见。如果说约翰·唐宁对另类媒体的描述更强调其在社会运动中传递的信息对社会及政治的影响力的话,克莱门西亚·罗德里格斯则在汲取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的批判教育学及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激进民主理论之后,更注重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将另类媒体具体界定为公民媒介,这与克里斯·阿顿对公众在另类媒体中主体性的强调相契合。但克莱门西亚·罗德里格斯在肯定公众主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另类媒体存在的意义不仅体现为反霸权信息的角色,还体现为传播过程中引起的社会互动,即公民通过另类媒体开辟的空间和平台参与到社会生活和政治决策过程中,重新形成对自我、他人及周围环境的身份认同。
与克莱门西亚·罗德里格斯的“多元激进民主”这个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角度不同,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F.Hamilton)在2008年出版的新著《民主传播:形式、方案与可能性》(Democratic Communications:Formations,Projects,Possibilities)中另辟蹊径,跳出主流/另类的简约二分法,将另类媒体与民主传播之间的关联放在历史和文化的坐标中,通过社会学的文本/结构主义分析以及历史/传记的案例分析,从16世纪英国的传播谈到当下的批判性阅读,考察另类媒体实践形成的条件、资源以及另类媒体所代表的民主传播持续的可能性。
梳理当下研究另类媒体代表性专著的主题思想以及相关论文,可以清晰地归纳出考察另类媒体生态的几种认知视角和研究路径。
视角一:另类媒体的本体研究。这种角度的研究大多从另类媒体本身出发,从微观层面考察另类媒体的定义、消息源、报道内容、生产过程、组织结构、劳工关系、受众群等方面。由于在描述过程中常以主流商业媒体作为参照对象,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与主流媒体的生存状态形成一种静态的对比,从而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本质主义。比如,在报道内容的研究上,认为另类媒体的报道就是主流媒体忽视或不予报道的内容;在劳工关系上,认为与主流媒体专业记者的知识劳工地位相比,另类媒体的工作者具有更富于创造的主体性。事实上,现实中的问题比简单对比更为复杂。例如对于劳工问题,在另类媒体工作的志愿者并非都对主流媒体持敌视态度,他们中的有些人往往以在另类媒体工作的经验作为跨入主流媒体的铺路石,这种情况下,难道另类媒体与主流媒体之间没有关联吗?再如另类媒体的受众群问题,虽然另类媒体为社会普通人群和边缘人群提供了表达意见和观点的平台,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受众只以另类媒体作为新闻获取的渠道。有研究表明,另类媒体的受众对主流商业媒介的接触比对另类媒体的接触更多,与此同时,另类媒体的组织者往往也要利用主流媒体的消息来获取自己的新闻源。所以,割裂主流媒体与另类媒体的关系会使研究处于表象与停滞状态,而究其原因,主要是对另类媒体的考察往往将注意力放在了“另类”这个角度,而忽视了另类媒体作为新闻业而运作的整体传播机制和媒介大环境。现在,有研究开始超越简单的二元划分的结论,在主流媒体与另类媒体的关系考察中动态的分析另类新闻业的运作过程。如:另类媒体如何寻找新闻源?如何报道新闻?另类媒体的记者确实是独立的而不受到主流媒体新闻实践与方法的影响吗?
视角二:从社会运动的角度对另类媒体反信息霸权和政治赋权角色的分析。这类角度通常关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因某种特定社会运动而产生的另类媒体,考察这类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偏重于分析这类媒体传递的内容意义,如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媒介、1994年墨西哥萨帕塔起义(Zapatista Movement)中的另类传播等。
视角三:从民主传播的角度考察另类媒体在创建过程中突显出来的公民的自我教育及民主参与的主体性。这类角度通常从参与式传播切入,考察另类媒体作为传播组织在自我生存状态下所突显出来的生产过程意义及社区互动性。
视角四:从文化意义的角度分析非政治性的另类媒体所体现的创作者的态度、立场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等。这些另类媒体并非直接诉诸政治内容和行动,而是在文化突围和社群身份建构上彰显力量,如原住民媒体、迷志、同性恋及少数族裔媒介等。
视角五:从技术革新的角度分析另类媒体拓展传播空间的潜能和力量。这个角度的分析通常与新媒体研究紧密相关,考察互联网、开放源代码、手机短信等媒介新技术如何帮助另类媒体在基于社区传播的基础上形成全球联网,从而降低另类媒体的经济成本并扩大其影响范围。
综合分析这五种切入视角,另类媒体的本体研究容易陷入媒介中心主义而忽视另类媒体源起的深层背景;政治层面的赋权分析将重点放在作为权力的媒体在反抗政治压迫过程中的抵制力量,较少关注另类媒体自身的组织及运作过程所彰显的民主力量;民主传播角度切入的另类媒体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治赋权角度的不足,但由于对民主理念解释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民主诉求观;至于技术革新角度的分析则容易将注意力放在新技术与新媒介的形态上而滑向技术决定论。
除上述五种主要的分析视角外,另类媒体的理论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研究美国和欧洲另类媒体的学者和文献较多,研究拉丁美洲另类媒体的学者较少,这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克莱门西亚·罗德里格斯(Clemencia Rodriguez)、罗伯特·韦斯卡(Robert Huesca)、阿兰·奥康娜(Alan O'Connor)、阿方索·古穆西奥·达格龙(Alfonso Gumucio Dagron),其中克莱门西亚·罗德里格斯是一位一直坚持通过实地考察和参与式体验来研究拉美另类媒体的学者。与拉美另类媒体的研究相比,亚洲、非洲另类媒体的研究更少,如金姆(Eun-Gyoo Kim)和詹姆斯·汉密尔顿(James F.Hamilton)对韩国的新闻游击队(Ohmy News)的研究,以及中国台湾学者如成露茜、冯建三、管中祥、胡元辉等对当地另类媒体与政治运动、关注弱势群体声音等方面的研究。这种从数量上呈现出来的研究不平衡状态,一方面既与世界不同地域另类媒体存在的多少及活跃的状态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不同地域差异化的社会运动、传播生态与媒介制度息息相关。
三、另类媒体存在的权力意义与研究趋势
在20世纪以来科学主义盛行的市场经济逻辑下,考量主流商业媒体的规模效应主要通过专业调查公司测评所得到的诸如“发行率”(纸质媒体)、“收听率”(广播媒体)、“收视率”(电视媒体)、“点击率”(网络媒体)等指标的精确数据来衡量。然而,鉴于另类媒体目前较小的规模和通过公民捐助得到的较少经费额度,无法实现量化的测评,那么如何来评估它们的影响力呢?另类媒体的行动主义者认为,作为主张维护媒介公共性、实现媒体作为传播公地的实践主体,另类媒体需要跳出主流商业媒体将精确测评数据打包卖给广告商进而使受众成为被广告商消费的商品终端的主导性媒介生产逻辑,以累积式的行动方略代替媒体经济数字影响力的测评来彰显它们作为一种具有双重民主诉求的“媒介权力”存在于当下的意义。
什么是媒介权力?作为媒介权力的另类媒体在社会构成中代表一种怎样的力量呢?在主流的行为科学研究范式那里,媒介权力多被具体化为媒介效果、影响力等多种可测量的目标,因而,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枪弹论”、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和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zarsfeld)的“有限效果论”,以及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E·Noelle-Neumann)支持的“强效果论”成为诠释媒介权力大小的理论模型。由于这种对媒介权力研究的路径始终离不开一般的受众,因此,和其他权力形态的研究相比,媒介权力的研究范围被大大缩小,并且会因“影响”、“效果”代替“权力”从而使“媒介权力”研究陷入到“效果决定权力”的单一研究体系中去。而在批判研究范式中,从法兰克福学派到《权力的媒介》(Agents of Power:The Role of the News Media in Human Affairs)的作者J·赫伯特·阿特休尔(J.Herbert Altschull),都在将媒体定位于传播工具的路径中针对现代传播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操纵、支配进行批判。⑥这两种对媒介权力的审视都是从媒体本身出发,权力被不言自明地界定为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以及意识形态领域控制他人的能力。这种权力的界定并没有建立在权力本身特有的概念体系上,而是直接地不假思索地移用了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对于权力界定的一部分内容。如果说,媒体可以被用来作为权力运作的工具,那么媒体自身呢?
针对上述媒介权力理解的工具性偏向,尼克·库里德里(Nick Couldry)和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媒介权力概念。一种观点认为,媒介权力是指外界力量运用媒介的文字、声音、画面、网络的传播来争取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力,在此,媒介只被视为权力争夺的工具,而媒介自身却没有任何权力。这类观点除了表现在上述所说的两种研究路径里,还在曼纽·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信息网络社会的理论中有所体现,即认为“在信息加快流动的空间里,接近媒介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但是媒介自身却没有权力”。⑦另一种观点却在将“媒介视为社会过程”⑧中肯定媒介本身就是权力主体,但是它拒绝在自由民主传统中视媒介为所谓第四权力的陈词滥调,而视其为需要被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本身,是复杂社会中诸种社会权力形态中的一种,⑨基于此,媒介权力正是在媒体与社会各方关联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在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权力束缚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着反向操控。在第二种对媒介权力观点的理解基础上,尼克·库里德里认为,另类媒体的实践嵌入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之中,作为相对于主流媒体来说的另一种权力主体,它具有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象征权力,即其所表征的民主参与实践使其有能力挑战主流商业媒体制度化、垄断化、专业化这个被“自然化”了的前提假设,对平衡社会中的媒介权力关系起到重要作用。⑩
在区分了两种视角后,两位学者进一步诠释了与两种视角相对应的两种媒体形象(11):一种是“瀑布”,一种是“接近瀑布建造的加工厂”。前者的“效果”取决于瀑布上游的水量、高度、河流流速,也就是媒体外部力量;后者的“效果/产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加工厂本身的机制、规律和方式。顺承这种比喻区分,加拿大传播学者罗伯特·哈克特(Robert Hacket)通过划分“经由媒介的权力”(power through the media)及“媒介自身的权力”(power of the media)进一步对媒介权力形态进行了阐释。(12)如果说,媒介权力本身是一项重要的关于社会冲突的主题,那么媒介权力研究应当调整其重心,不仅包括外部力量对媒介的影响,更要分析媒体自身的权力机制。
正是上述三位学者对媒介权力第二种意义的诠释和比喻,开启了对另类媒体作为媒介权力研究的新视角。具体到另类媒体的媒介权力意义考察来说,除了要看到另类媒体本身传递的内容信息外,更要注重它运作的机制对媒介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当其内容和空间层面的意义融入社会运动的行动中时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基于此,另类媒体的权力意义摆脱了主流行为科学对效果测评的实证研究范式,将媒体民主这个直接涉及媒介公共性的实质问题作为关注和实践的目标,通过反信息霸权的内容民主、参与式传播的空间民主以及社会运动的行动民主来挑战主流商业媒体的文化霸权和市场至上的经济逻辑,以此唤起公众对主流媒体报道内容批判理解的主体意识以及在自主参与传播过程中实现自我赋权,从而形成以公民为传播主体,自主创办媒体,自行报道新闻内容,自觉维护媒体民主机制的自治于国家和市场控制的传播实践。
由此可见,作为当下一种修正主流商业媒体弊端的机制,另类媒体在自治传播实践中彰显出一种带着反抗力量却表征着积极、进步意义的媒介行动镜像,它不仅提供了被排除于主流媒体体制外的民主发声的管道,还激发了民众自发性参与社会改造的意愿与行动,推动了其主张的“双重民主化”目标的实现,即“在它们为主流媒体冷落的人们提供传播途径的范围内,另类媒体通过使传媒系统多元化,一方面增强了传媒系统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媒体民主化来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13)事实上,这些所有的实践诉求只为尝试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即在媒介圈地浪潮下如何通过自主传播实践重建传播公地的理想。在探究这个答案的路途上,需要行动的不只是另类媒体本身,公民主体批判意识的觉醒以及参与性行动的支持,是重建传播公地最重要的生力军。在跳脱出“主流—另类”这种简约的本质二元论后,另类媒体的理论研究下一步需要追问和探究的核心焦点在于:另类媒体所彰显的媒介权力的过程意义如何呈现?作为公地的传播如何成为可能?传播公地如何重建?这既代表了一种理论与现实结合视域里对人类传播秩序和媒介权力生态的终极关怀,也是另类媒体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的意义标识和路径取向。
另外值得强调的一点是,今后对另类媒体的研究还需跳出方法论民族主义,在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框架下以全球和动态的视角来审视当下一些引起人们警惕的自称为“另类媒体”的组织。例如,以英特新闻(Internews)为代表的总部设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主要是美国)的独立媒体发展组织,声称通过提供捐助、媒体培训、媒介设备等物质和人力资源向全球众多地区提供当地独立媒体成立和运作的各项支持,其宗旨是促进信息在世界更大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以满足当地民众多元化的信息需求。然而,这个组织不仅从美国政府若干机构、欧洲委员会以及一些美国大公司和基金会那里获得大量的资金资助,(14)而且在支持当地另类媒体组建和传播的过程中,通过倡导“促进新闻自由和民主发展”这个隐含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口号,在世界众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开展新闻培训与教育工作,这对当地民众认同和接受西方新闻自由民主观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功用。随着近来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局势的变化,这类带有“地方(总部)——全球(发展方向)——地方(本土化支持)”发展态势的所谓独立媒体组织越来越被发展中国家所警觉。因此,研究另类媒体不能只关注其媒介技术形态层面的另类,更需要将其放置于特定的世界传播秩序、特定的国家范畴、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运动等具体背景中,来考察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过程、传播形态、传播权力的本质表现。
注释:
①Ben H.Bagdikian,The Media Monopoly.Published Boston,Mass.:Beacon Press,2000,p.x.
②Karl Marx,Capital(Volume 1).New York:Vintage,1977,p.669.
③J.M.Neeson,Commoners:Common Right,Enclos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1700-1820.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p.5.
④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谢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9页。
⑤Tim O' Sulhvan,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London; New York:Routledge,1994,p.10.
⑥何双秋、魏晨:《媒介权力的多样性探析》,《新闻界》2006年第1期,第37页。
⑦Manuel Castells,The Power of Identity.Oxford:Blackwell,1997,pp.312-317.
⑧Nick Couldry,The Place of Media Power:Pilgrims and Witnesses of the Media Age.London:Routledge,2000,p.16.
⑨Nick Couldry & James Curran(eds.),Contesting Media Power: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3,pp.3-4.
⑩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Cambridge:Polity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1991,pp.163-170.
(11)Nick Couldry and James Curran(eds.),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Lanham,Md.:Rowrnan & Littlefield,2003,pp.5-6.
(12)Robert A.Hackett and William K.Carroll,Remaking Media:The Struggle to Democratize Public Communication.New York; London:Routledge,2006,pp.21-31.
(13)Janet Wasko,"Introduction:Go Tell it to the Spartans," in Janet Wasko and Vincent Mosco(eds.),Democratic communica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Age,Toronto:Garamond Press,1992,p.7.
(14)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