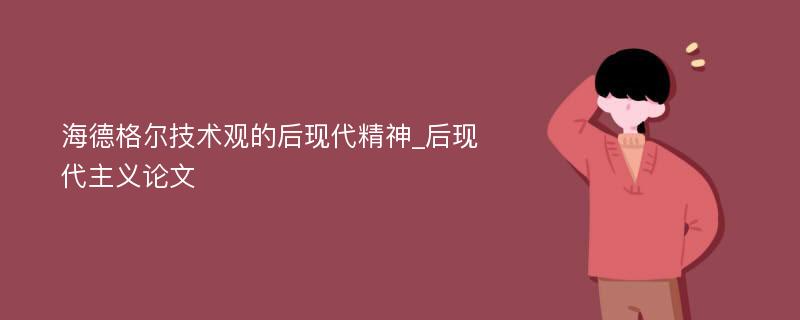
海德格尔技术观的后现代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后现代论文,精神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5-0035-06
海德格尔是存在主义哲学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代表,也是西方哲学家公认的由现代跨向后现代的桥梁。他的存在论哲学根源于现实,又服务于现实,充满了极强的现实的人文关怀精神,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启迪着人类在应用技术的过程中的人文精神。
一、技术的本质是座架:海德格尔技术观的精髓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中有许多哲学反思的东西,应该以一个非技术人的身份从哲学上考察技术。他是一个信守苏格拉底传统的哲学家,善于提出问题而并不希望像实证主义那样解决问题。他关注的是“存在”问题,事物与存在的关系,事物与技术的关系,“存在”是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主线,从“存在”出发追问技术的本质也是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技术哲学思想内容丰富、蕴涵深刻,是建立在对技术的人本主义批判立场上的艺术审美观、生态伦理观及未来发展观。
技术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要精确地回答起来却又很难。无论在我国的辞书中还是在一般的教科书中,关于技术的定义主要都是指人类为满足自己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以及其他非生产活动的需要,运用自然和社会规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手段及方法的总和。在西方,技术一词源于希腊文techne,意为“工艺、技能”。最早将科学与技术做了区分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技术称作“制作的智慧”。从上面的解释中足以见得人们对技术的认识停留在对技术的要素探讨和人的活动的特征的认识之上。海德格尔从人与技术的关系中推论出技术的本质,这是他在技术哲学的发展史上对技术在本体论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他认为,技术是一种真理或展现,其本质是以对象化的方式展现世界。技术不仅是手段,而且是展现方式的一种。为了揭示技术的本质,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展现方式概括为摆置和促逼,并进一步指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Ge-stell)。海德格尔的技术观冲破了传统的“纯工具”的技术观,将技术的本质认识提升到真理的领域加以探索,认为“技术不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解蔽方式。……解蔽之领域,亦即真理之领域”。[1](P931)将技术理解为工具和人的行动,海德格尔称这是人类学的技术观。正如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指出:“按古老的学说,某物的本质被看作某物所是的那个什么。当我们问技术是什么时……尽人皆知的两种回答其一是技术是合目的的工具,其二是技术是人的行为。……通行于世的关于技术的观念——即认为技术是工具和人的行为——可以被叫做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2](P925)当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的工具性规定并没有向我们显示出技术的本质,它不过是被看作技术的基本特征而已,要寻求技术的内在本质规定性,必须到解蔽那里去寻找,解蔽即追求真理的过程,解蔽是真理的展现。技术不仅仅是表象和直观,它既是一种认识,又是一种实践,技术既不是技术的东西,也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一种“解蔽”的方式。关于“座架”,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中诠释道:“源初地把群山展开为山的形态,并且贯通着起伏毗连的群山的东西,是聚集者,我们称之为山脉。我们的这样那样的情绪方式由之得以展开的那种源初聚集者,我们称之为性情”。[3](P937)海德格尔以群山、性情为比喻,强调座架“聚集”的特性,这个聚集指的就是自然和世界在技术展现中呈现出的多种方式。由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海德格尔所说的在技术的本性中根植着和成长着拯救,即“哪里有危险,哪里也有救”。[4](P946)“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以“预置”的方式展示物,构造世界,使得“物”都成了“持存物”。正是这种“预置”的去蔽方式将表面看起来都是“改造世界”的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区别开来。仔细考究这种思想与技术一词的来源也是一致的,因为技术一词在希腊语中的主要意思不是制造和操作,而是“解蔽”(aletheia),是“带上前来”的意思。[2](P234)
海德格尔生活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革命性”时代,伴随科技的日新月异,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变化,技术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鲜明,海德格尔对技术问题的论述集中在1949年他发表的4篇演讲即《物》、《座架》、《危险》、《转向》之中。他反对传统观点认为技术是中性手段或人的活动的“纯工具”的简单回答,论证了技术是一种真理或展现,特别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展现。海德格尔所说的现代从时间上讲包括近代和现代在内,现代技术的产生不完全是因为人的需要和愿望,而是因为现实物使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向技术操作开放,才引起了技术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技术的特点,提出了技术既不是工具性的,也不是自主性的,而是建构性的现代技术理念,成为现代建构主义的先驱。
反思是现象学的最显著特征,纯粹现象学来源于纯粹“反思”,是关于“纯粹意识”的科学。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分析方法则关注的是“存在”,他的思想是从研究“此在”的存在——人的生存分析开始的。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及存在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决定了今天人们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的深刻关注。海德格尔认识到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有脱离人控制的危险,强调指出:“人们要‘在精神上操纵’技术,人们要控制技术。技术愈是有脱离人类的统治的危险,对于技术的控制意愿就愈加迫切”。[1](P348)同时呼吁人类控制技术、建构技术的客观必要性和紧迫性。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及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对技术的奴役作用,海德格尔以其独特的视角做了深刻的揭示。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时代的一切东西都打上了现代技术统治的烙印。人周围的一切,包括人本身都丧失了自己独立的对象性而沉沦为技术的“持存物”。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在其本质中实为一种负诸遗忘的存在的真理之存在的历史的天命”,[1](P348)“座架乃是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弄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事物作为持存物而解蔽出来”。[3](P29)座架被认为是一种支配人逼索自然的神秘力量,人的主体能动作用丧失,人被带入危险的边缘,人成了受“座架”支配的工具。海德格尔根据技术的本质主义,得出了技术的异化理论。当然,我们应该肯定海德格尔对技术哲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的技术异化及其对技术异化的人本主义批评,而这种批评并不是拒斥技术,而是正视技术本质中的危险,通过揭示和谴责这种危险,为人类从技术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做好条件准备。这种解放并不意味着抛弃技术,而是对人与技术的关系的一种修正。[4](P97-102)
二、技术批判的辩证否定:海德格尔技术观的后现代精神
关于后现代主义在理论界有许多理解。通常的观点主要有二: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以反传统哲学为特征的思潮;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以后结构主义和新实用主义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的建构。本文的观点立足于第一个立场之上。
我们知道,后现代主义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它作为一种时代哲学既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思,又是对信息时代的回应。它以建设性的维度推崇创造性和辩证否定的方法论,倡导对世界的关心爱护,强调个人、他人、他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重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强烈愿望和思想精华,是全新的时间观和未来观。建设同时意味着否定。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思想中,具有否定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们并不是要绝对地拒斥一切,而是一种积极的否定。后现代主义在本质上超越现代主义就是要超越主体与客体二分的哲学,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透视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不难发现他的技术观中洋溢和挥洒着宏大的后现代精神。
海德格尔在分析技术时把技术的“座架”本质与现代人的无家可归状态联系在一起。他在20世纪60年代答联邦德国《明镜》杂志记者问时说,现代技术已经把人类从地球上连根拔起。海德格尔思考着人类的命运和环境对人的生存的影响,反思和批判技术的疯狂给人类造成的不幸。海德格尔认为完全支配近现代技术这种揭示的乃是逼索,是对自然的掠夺和压迫。这里所谓的“逼索”即“强求性的要求”是指现代技术把“有用性”作为对事物的评价标准,而割舍了物体的其他性质。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指出:“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形式与质料的交织首先就从罐、斧和鞋的用途方面被处置好了。这种有用性从来不是事后才被指派和加给罐、斧、鞋这类存在者的。……有用性是一种基本特征,由于这种基本特征,这个存在者便凝视我们,亦即闪现于我们面前,并因而现身在场,从而成为这种存在者。一个落入有用性中的存在者总是一个制造过程的产品,它是作为一件为什么的器具而被制造的”。[1](P248-250)“强求性的要求”在侵害事物的存在的特征中,使事物被迫放弃它们的真正的存在,就像空气被强求交付氮、土地被强求交付矿石一样,现代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对自然、对事物的观念,人类把自己生存依托的自然世界变成无限掠夺的源泉,将人与大地的关系变为紧张对立的两极。“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坐落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出来,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1](P23)人处于现代技术的座架,导致了技术的滥用,他们只关注向大自然索取,而毫不顾忌这种过度索取对自然产生的严重后果,其最终将使人类陷入“无家可归”的状态。海德格尔认为,座架占统治地位,便有最高危险。面对人类因技术滥用所导致的种种危机,海德格尔在寻求拯救的良方。他明确指出,通过技术,人与自然形成了主、客体的分化。人以一种主体身份破坏了人与世界的原初统一,人站在世界的对立面征服自然,并通过技术渐渐堵塞了人通向存在的澄明之途。从发展观的角度分析可见,现代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步入了人类中心主义,而造成了今天人类生命家园的危机。面对技术的应用给人、社会、自然带来的严重影响,海德格尔同样持有一种积极的批判态度。他在《关于技术问题》等著作中认为,天、地、生命、神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但是技术打破了这个整体,造成了他们的分离和对立。人应该沉思地生活在地球上,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当思思维着的时候,思就行动着。思想本身就是较高意义上的行动。人应该通过思寻找到解救生态毁灭的办法,使人诗意地生存于地球之上。他认为技术就是一种拯救的力量,“技术之本质必然于自身蕴含着救渡的生长”。“我们愈是邻近于危险,进入救渡的道路便愈是开始明亮地闪烁……”。[1](P946、954)同时,他把对技术的决定性解析与艺术领域的沉思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人类提出一条从技术统治到审美解放之路。
海德格尔这种批评显然具有人类学的关怀意义。他以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所特有的人文关怀和冷峻目光,对科技发展的善有着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并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作用,持有较为清醒的批判意识。海德格尔开创了对技术和技术社会进行哲学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思想时代,他直接对技术考察提出的生态环境伦理思想,也是他对后现代主义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海德格尔的技术观体现了“精神”概念中所具有的终极价值目标及意义,充满了智慧和幽思,洋溢着艺术审美价值和技术批判的乐观主义精神。他的技术哲学思想是在辩证思维指导下的一种全新的未来观和发展观。首先,他的技术观不仅表现为一种时代的哲学观,而且体现出辩证否定的方法论;其次,他在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反对主客分离,突出了和谐统一的有机主义思想;第三,他对技术与技术社会的反思与批判,促使人类更加科学地认识技术的价值,启发人们以崭新的思维视角理解技术本质中的危险,在技术的价值论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第四,他的思想是对二元论的、超自然的现代精神的一种超越的“后现代精神”,这种精神不是一种对以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为中心特征的现代精神的简单的复归,而是让社会的、道德的、审美的、生态的考虑不再单一地服从经济利益,具有鲜明的未来利益的基础。尽管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观点各异,对海德格尔的评价各有千秋,本文的立场是积极的,就像我们今天对后现代精神扬其精华、弃其糟粕的道理一样。当然,我们今天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的积极解析,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揭示其理论思想的内涵,更重要的在于本着发展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探寻其思想理论的现实指导意义,使其技术哲学思想对今天的社会实践及人类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展示其思想的深邃和对当前社会的现实启示。
三、技术的社会建构:海德格尔技术观的现实启示
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并没有停留在单纯的技术乐观主义或技术悲观主义立场上,这一点为我们今天审视当代技术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离不开技术的推动,技术不仅表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而且表现出政治价值、军事价值等,这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技术的本质特性,合理开发、使用技术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人类在今天也不能忘却技术的负面性,尤其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人类应该坚持发展的伦理观、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以一种可持续发展观、高尚的道德观使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造福于人类。正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人具有非凡的自决能力,这种能力也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谋利,也可以用来作恶。海德格尔提出的生态伦理思想显现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有机主义精神,人与世界、自然的关系决不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两极,人类应该站在更高的意义上认识和实践人与自然、世界的和谐。今天,人类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生存与发展面临的环境危机,生态恶化已在客观上促进了人类发展意识的觉醒。
尽管许多人对后现代主义持否定的态度,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后现代主义在某些观点上对我们今天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正如大卫·格里芬所言:“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是‘后现代化’了”。[5](P20)
分析海德格尔技术观产生和形成的时代背景,不难发现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人类所处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时代,空间技术、物理技术、原子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技术对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鲜明,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海德格尔在他哲学生涯的晚期走向对技术的追问,技术主题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中日益凸显出来,成为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伴随不断前进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及通讯技术为先导的一场高新技术革命首先从美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爆发兴起,以后席卷全球。这场高科技革命产生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乃至思想道德观念,将引发一场空前的社会变革。人类在面对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无限益处的同时,也不能不学习哲学大师的反思和批判的头脑,学习大师们冷静思考问题的品格和风范,以发展的视角对当代技术进行反思,审慎地考察技术的应用价值,深刻地认识技术本质中蕴涵的危险以及探索如何采取对策防止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资源危机乃至人类生存的危机,以确保技术造福于人类,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在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中表现出一种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思想态度,这种思想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及现代人类的生活具有如下启示意义。
首先,人类对技术的理解不应仅停止在“纯工具”的认识之上,技术的创造、使用及控制都应该以人类的生存和存在为根本目的,人类并不是技术的工具,人类研究、开发和改进技术的目的是解放人类自己而不是使自己陷入更加危险的边缘。由此可见,海德格尔技术观体现了深厚的人本主义意蕴。
今天,人类已经迈进21世纪,对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的步伐越来越快,技术在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鲜明。怎样合理地研发及控制和使用技术,使之朝向人类的合理需要的目标发展,在客观上已经在激发人类反思技术价值的同时,在实践中加速了技术哲学的应用伦理研究转向。海德格尔的人类终极关怀的思想态度是技术伦理态度的具体展现,为我们今天在实践中建构技术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上的启示。
其次,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思想在对技术的负面作用进行深刻反思的同时,从哲学的层面上启示我们对技术的反思和追问要尽可能地避免工具主义的片面思维。探索和论证海德格尔的技术观的后现代精神,就要从其对现代性的批判着眼,发现他的批判分析是“一种独特的后现代主义”,是“对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整体性批判”。他并非像传统的现代性批判的那样“对近现代技术做出工具主义解释、因而给技术加上了工具主义的目的的批判,反过来反而强化与纵容了近现代技术的工具性力量,无情地违逆了张扬人道主义的初衷”,[6](P211、213、211-212)而是从形式上看具有内在超越意义的对现代性批判的一种解构,但实质上是倡导在摧毁基础上重新奠基文化基础的一种“回归前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建构的实际意义。
尽管由于历史和思想家思维的局限,海德格尔在寻找拯救途径之时把其归为“思”,反映了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但是,海德格尔的“栖居”之思深刻地反映了他的伦理学思想,正如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所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的“意义无非是把现代已受到威胁,以至于行将消失的人生的秘密重新赋予人生而已”。[7](P3)海德格尔对人之“栖居”的关切是其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我们今天对海德格尔技术观的探析,宗旨在于使其思想的合理成分指导现实的技术发展,促进技术对人类积极作用的发挥,使人类超越技术发展带来的困境。
1989年9月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21世纪科学与文化:生存的计划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一份由与会科学家签署的《关于21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指出:当前人类面临的形势是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之间的平衡已经濒临崩溃,人类面对地球生态系统的衰竭和人类生活质量恶化的时刻。“造成我们今天这些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科学上的进步。这些进步基本上于本世纪初叶已获得。它们以一种传统机械论的方式归纳展示宇宙,并赋予人类一种驾驭大自然的能力。直至不久前,大自然已经提供了不断增长、似乎永无竭尽的物质财富。人类醉心于对这种能力的利用,因而出现了改变自己的价值,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新能力所提供之物质潜力的倾向”。[8](P297)
的确,不管是向自然界索取资源进行物质生产,还是向环境排放废物,都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人类保护自然环境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所有这些向我们展示的是科学技术的价值观转向,单纯以一种传统机械论方式展示技术的价值是片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也必须从传统的机械论科学观发展为整体论的科学观,使人类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准确地评估资源的使用价值,把握地球的负载能力及人类对它的恢复能力,以支持地球的生命来维系人类的生存。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人类应该结合实际来建构技术,通过道德的法律的规范约束、国家权力的正当干预、社会舆论力量的监控及科学的管理手段和科学技术共同体的自律,形成全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确保技术的健康发展和积极意义的发挥。
[收稿日期]2003-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