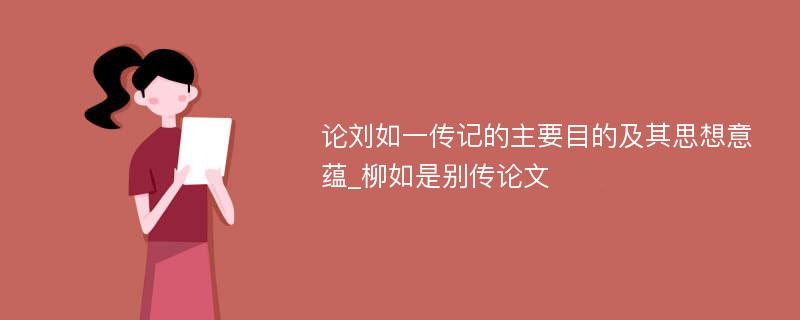
关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撰述论文,别传论文,主旨论文,寓意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这是中国学术史中的代代相传的佳话。但是,左丘与孙膑的传说,毕竟离我们十分遥远了。著书故事的真实性,也很难去考证清楚的。然而在本世纪中叶的中国,却有一个当代史家,在失明膑足的情况下,用了十年的光阴,完成一部八十余万言的大书奇书。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与他的最后著作《柳如是别传》。1964年夏,该书完成初稿时,陈寅恪先生已七十五岁,正如助手黄萱所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慨。”有陈先生和他的著作的真实存在,使我们相信左丘所代表的传统,依然在中国纯正的知识人血脉中的慧命相续的存活。但是,《柳如是别传》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著作?陈寅恪先生为什么在晚年花这么大的心血来为一个名妓作传?这本书在陈先生的著作,以及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近年来,有关上述问题随着陈寅恪学术与思想的逐渐被理解,不仅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且引发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相信,名著的命运,正是随时间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其内涵。所以,陈先生的这本书的命运也是如此。在这篇文章里,我打算就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意见,稍加疏理,述其大要,最后也表达个人对这部书撰述主旨与思想寓意的一点想法。是为引言。
一、《别传》的撰述主旨研究综述
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关于陈寅恪的研究论著呈逐渐上升趋势。《别传》的研究也正走向深入。笔者根据目前的资料[1],将有关《别传》撰述主旨的意见归纳为七类,简要介绍如下:
(一)辨诬说
汪荣祖于七十年代撰写的专著中,认为寅恪之歌颂柳如是,同情钱牧斋,可谓是翻案文章。书名由《钱柳诗笺证》而改为《柳如是别传》,原因在于“寅恪于钱柳极为同情,甚觉未得历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长篇幅为之洗刷烦冤。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不仅赞美其才艺,更服其气节。”黄裳在一九八二年写的《关于柳如是》一文,也认为这本书的性质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著作。陈寅恪因为同情柳如是,所以撰作此书为柳如是辨诬。这一说法,本来可以代表那些原先多少从野史笔记或道听途说知道一点关于柳如是其人其事,但又并没有通读(更谈不上细读)《别传》的人们的直接印象。但是黄裳虽然对于钱氏的抗清事迹以及柳如是的政治才华多有肯定,但却又认为陈寅恪的辨诬是不值得的。在他的心目中柳如是毕竟只是个放诞不羁的风尘女子,末代交际花一类的人物。她与陈子龙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名士与名妓的风流生活;而她最终归钱牧斋,也不是基于爱情,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考虑。黄裳明确表示不能同意陈寅恪先生的辨诬。他认为柳如是则由原先的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子,变而为一个大地主的夫人,并不值得为她申冤。而河东君柳如是之所以做出许多蔑视封建礼法、使当时的正人君子们攒眉怒目的事,也不过是腐朽的地主阶级本质的表现,并不值得陈先生为之曲辨的。黄先生的文章体式,属于书话而不属于书评。书话作者往往借一本书进行自己的杂文散文的写作,他有权不顾原书作者的用心,也不必理解原书作者的用心。甚至要求书话的作者去通读原书,或许是一件过于认真的事情。更何况,关于地主阶级云云的说法,带有过去时代的思想斗争气息,很难说是严肃的学术讨论。只是作为历史对于一部名著的接受痕迹,这里也聊备一说。
(二)自遣自证说
汪荣祖又明确提出自遣自证说。关于自遣,他认为“寅恪投射一己于三百年前,犹如观剧者与剧中人同化,实为其兴趣不坠的源渊。……而于神往之际,伤古抚今,常常不能自己。因寅恪之思想虽有新的一面,但在情感上甚是依恋旧文化与旧社会,自五四以还即觉扦格不入。晚年社会与文化之变动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浑忘现实之痛苦。寅恪笺释钱柳诗得到精神上之乐趣,自无可疑。”关于自证,他说:“《柳如是别传》一书卷帙浩繁,考证烦琐,集寅恪一生著述‘笔法’之大成。寅恪欲藉此书自验学术之深浅以及留示后人其史学方法的范例。”他还举证说,书成之后,陈寅恪嘱其助手黄萱写文章总结他如何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这正是当事人表明此书的撰述动机的直接证据。依汪氏此说,《柳如是别传》并无学术思想史上重大的深意,只是一部十分偶然、充满个人学问经历特殊因素的著作,至多只有史学方法典范意义。
(三)复明运动史
持这一说法的有王钟翰、王永兴、何修龄等人。这些人或是明清史研究的专家,或陈寅恪先生的高足。他们对于《柳如是别传》的重视,正标志着对于《柳如是别传》理解的深入。早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有关陈寅恪的讨论会论文集中,何修龄就有《柳如是别传》读后的专论,就笔者所见,这是第一篇系统评价《柳如是别传》的专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从表面上看,全书以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为最长,占整个篇幅的五分之二,比第五章《复明运动》还多出将近一百页。但根据作者在本书第一章《缘起》中所说的力求窥见钱柳在亡国之后的“孤怀遗恨”,以及珍惜引申其中“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可以说,“第五章《复明运动》实际上是全书主旨所在。”何修龄评价说:关于复明运动“以往人们知道的只有其中个别的或少量的史实,单个人反清复明的思想情绪,个人或极少数人自发的反抗等局部活动,人们知道的还有各地规模不等的群众武装起义,却没有明确意识并提出过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这种长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复明运动、民族抵抗运动的潜流,更不知道这种运动曾在‘绸缪鼓瑟之小妇’推动下展开。”而陈寅恪提炼出许多史实,发现许多“待发之覆”,并加以考证、研究,把隐藏得很深的历史真相揭示出来,“是一项全新的发掘和概括,一项重要的科学成果。”王永兴拈出《柳如是别传》中“然此文主旨在河东君一生志事”一句警策语,指出所谓河东君之“志事”,正是陈寅恪不断提到的“三户亡秦之志”,或曰“哀郢沉湘之旨、复楚报韩之心”,或曰“东海麻姑之感,西山精卫之心”。河东君虽坚持参加复明运动,而未能获得成功,但陈寅恪不以成败论英雄,尊崇气节是柳如是一生志事的主要表现,也是她的立身之本。而陈寅恪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撰著此书,阐扬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意义与欧阳永叔著《五代史论》的学术思想意义相同。王钟翰进而在陈寅恪的基础上继续考辨,补充材料,认同陈寅恪关于钱柳因缘由言情之儿女,变而为爱国之英雄的说法,并提出柳苟不择钱则名不扬,钱不得柳助而反清复明之志不坚,两者相得欲彰的新见,以张大陈寅恪关于钱柳共同参预复明运动的观点。总之,“复明运动”说,明显地比上面的两种说法提高了很大的一个层次,更能真实切近地理解《柳如是别传》的宗旨。
(四)颂红妆的女性史
蔡鸿生,孙康宜等人持这种看法。关于“复明运动”的说法毕竟将《柳如是别传》中柳如是与陈子龙,柳如是与宋征舆,柳如是与程孟阳、谢象三等人的诗词情缘与交往因缘放在一个比较次要的地位,而《柳如是别传》毕竟又用了大量篇幅对于柳如是的情史与生活史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爬梳考证。这些考证却与复明运动应无直接的关系,那么,陈寅恪为何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来细辨河东君艰难处世、择婿人海、为争取婚姻幸福而斗争的过程呢?蔡鸿生、孙康宜等人从女性史的角度提出,这本书的宗旨乃在于陈寅恪先生晚年对于“红妆”的关注,从著《论再生缘》到《柳如是别传》,正是一种自觉的治学旨趣的选择。但是同样是“女性史”,其中又有不同的强调重心。蔡鸿生更为看重的是女性悲剧史以及女性中蕴藏的英雄气质。悲剧史是表明“红妆”的历史中往往含有人性与社会的冲突、理想与时代的冲突,“胭脂泪中凝聚着民族魂”。陈寅恪早年对于崔莺莺的研究,对于秦妇的研究,以及对于琵琶妇的研究,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同一系列探索。不同的只是《柳如是别传》是对于“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一曲赞歌。“侠气、才气和骨气,在柳如是身上,可说是三者合一”,“奇女志与遗民心的结合”,使本书成为可歌可泣的女性史颂。孙康宜的重点在于从十六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的崛起与成熟这一背景看问题,认为这本书中经过陈寅恪深入细心的掘发所呈示出来的陈柳诗词情缘,是晚明情观新变所促发的一场文化变革的一种结晶。柳如是所代表的歌伎文学传统与名士文学传统的融合,所达到的极深细优美的情感世界,是该书最为精彩的成就。姜伯勤也认为《柳如是别传》的这一特点与国际史学界对于妇女史的关注是同步发生的,是通过一系列女性形象的研究,来阐发思想超越的理想人物。余英时也强调了在陈寅恪的心目中红妆女性的政治与美学意义,是与男性世界形成相当大的区别的,这里有陈寅恪的现实关怀。总之,“颂红妆的女性史”这一说法包容了“复明运动”说,既注重具有性别特征化的情感世界一面,又重视女性意义中呈显出的精神价值与政治道德意义一面,凸显了陈寅恪自己所声称的“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学术新变的意义。
(五)知识分子史、人格心态史
吴宓、周勋初、姜伯勤、李劼等持此说。1961年,吴宓到广州会见老友陈寅恪,谈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情况。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由于这段话具有当事人口述性质,所以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披露之后,成为论者广泛引用的权威性说法。这个说法明显将“颂红妆”作为一种表面现象,或一种叙述策略,其真正的深层关注则应含有知识人心态史的更多更深含义。而这个含义的核心,是在易代之际有关文化与道德的基本命运的抉择。周勋初说:“读过《柳如是别传》之后,可知这部著作虽用传记的形式写成,实际上却是一部反映明末知识分子动态的史诗。”作者以天翻地覆的历史事实为轴心,通过柳如是的奇特经历,展开一幅巨大的历史画卷,“让读者看到,在这动乱的年代里,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怎样在严酷的命运面前抉择自己的归宿。寅恪先生对柳如是身边的这些士人,以其对待国家命运的态度为准,予以表扬或贬斥,从而起到了‘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作用。”姜伯勤一方面从国际史学趋势来强调“心史”的新史学意义。他认为陈寅恪的“以诗证史”不仅与传统学术的“诗史”概念不同,而且与陈寅恪自己早年的“以诗证史”方法不同。“在陈寅恪的史学道路上,以《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为起始,陈寅恪广义文化史研究,已经偏重制度文化史、偏重以文化解释种族的中心议题,转向以研究社会风习的时代情感、社会转变中的价值变迁为重点。”一方面强调心史又是作为传统的文化观念,“表达的是民族的心灵历程、在民族危机时所必须保持的‘气节’、在民族危机时保存故土文化而进行的‘夷夏之辩’,…‘心史’这个中国史学中的独特范畴,带有很强的民族文化情结。”李劼认为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人格的历史。这种新的历史叙述可以认为是对于传统的《资治通鉴》式帝王将相历史的颠覆。其重大意义在于真正“对于精神人格的张扬,而不是其他任何主题,成为《柳如是别传》最为兴味深长之处,成为其主旨所在。”人格心态史的说法可以说是由吴宓的“深意”一语引申而来,特别注重这本书的超越一般史学的文化思想意义,以及现代思想文化史寓意。
(六)明清文化痛史
刘梦溪近年发表一系列研究陈寅恪的论文。关于《柳如是别传》,他在诸家群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明清文化痛史”的新说。他认为此书实际上是陈寅恪自创的一种修史的新文体,特点是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内容宏博、史事纷繁。陈寅恪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融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作者更辉煌的学术目标是通过立传来修史,“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生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的角度写就的南明史,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如果说《论再生缘》是一种尝试,《柳如是别传》则是这种新文体的完成。刘氏的说法重在发皇表彰陈寅恪的学术文体创新意义。对于那些批评《柳如是别传》文体繁冗、考证繁琐、篇幅过长、牵扯过多的意见,刘文应是为陈寅恪找出了一种似乎是作者衰年变法的理由。但是“痛史”的说法明显过于宽泛而不易得其要领。一部书的主旨由于分散到方方面面去,这本书的主旨无疑也隐而不彰了。
(七)自喻自悔说
余英时早在五十年代即对这本书作了非常富于创见的研究。他的最为独到的心得,是认为陈寅恪的晚年作品,应通过他晚年生活与价值系统才能求得相应的理解。而方法正在于透过陈寅恪晚年诗文的考释,来理解陈寅恪的价值系统,然后通过这一系统,来理解《柳如是别传》的主旨。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读解途径。但余氏却并不满足于此,更将所谓“价值系统”的问题简化为一个“北上”或“南下”的去留问题,这就使他对这本书的观点带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偏执,甚而使他在某些问题上带有胶柱鼓瑟的机械意味。譬如他认为此书的主人公钱、柳,正是陈寅恪对他自己与陈夫人的自喻,在此基础上,将此书说成是表达个人特定的身世与命运的一种伤悼与悔恨之作。这就不仅是推论过深,而且按照余氏的一个说法:“陈先生晚年歌颂‘红妆’,尤其是对柳如是倾倒备至,实已远远超出了理智判断的范围。”——客观上也有意无意中抹杀了此书最起码的性质,即学术著作的基本性质。平心讨论余氏的说法,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虽有理据却不免有夸大之嫌。如以钱、柳喻陈、唐这一说法,余氏最有力的证据有四条,一是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陈寅恪的诗句:“谁使英雄休入彀,转悲遗逸得加年。”(自注云:明南都倾覆,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金陵。未几牧斋南归。然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也。)余氏认为这里“夫子自道”的成分很大。但是我们知道陈寅恪并没有“入彀”,而陈夫人也并没有“独留”。河东君之志可以推知,而陈夫人之志,在陈寅恪,则是无须“推知”的。二是《柳如是别传》《中秋夕赠内》(1955)诗末两句:“终负人间双拜月,高寒千古对悠悠”,用的是牧斋《初学集·移居诗集》中的“永遇乐”词语。余氏提问:“陈先生在什么地方最后竟背负了陈夫人呢?我们今天所能推测的只有两人在去留问题上的歧见而已。”我们且不谈另有人可以“推测”这里的“终负”不一定就是“背负”,而也可能是“此生辜负”之意,也可能包含四十年代的去英国而未成的遗憾等。更何况即使这里是以钱柳喻陈唐,也不能说明整书以钱柳喻陈唐。三是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认为钱柳对于郑成功的态度有冷热不同,余氏也用来说这是比喻陈、唐对于去留问题的严重分歧。并用陈先生自己的话:“河东君及牧斋之性格,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暗示“迟疑”二字正是陈先生自己的夫子自道。但熟悉陈寅恪生平的人恐怕不会认为陈在去留问题上是“迟疑”的,也不会认为“怯懦”是他的夫子自道。四是《缘起》中陈寅恪诗句“孺仲贤妻药里亲”,余氏考出用的是牧斋《和东坡诗》“徒行赴难有贤妻”,以及《己丑元日试笔》“孺仲贤妻涕泪流”,这自然是不错的,但也只能得出“共患难”的意思,而不能进一步引申夸大出在陈寅恪心目中钱柳就是他们夫妇二人。余氏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即使我们认定以上有关钱柳与陈唐的比喻都是真实的,也并不能以诗词写作完全代替著作写作,前者是文学作品,后者毕竟是考史论著,如果可以取代,则《柳如是别传》恐怕有三分之二的篇幅不必写,不但陈子龙与柳如是的诗词因缘的长篇考证成为多余,此书所借柳如是的故事所展开的明清之际政治、经济、宗教、文艺、军事的广阔画面也成为多余,此书关于历史真实的许多发人未发之覆,也成为可有可无的陪衬。所以,余英时的“自喻自悔”说,确很难令多数学者首肯。
二、我对于《别传》作意的几点理解
我认为对于《别传》主旨的理解,首先必须区分三个层面,一是事实的层面,一是意义的层面,三是文体层面。事实层面是基于此书的性质是一部学术著作,意义层面是基于此书含有陈寅恪个人的存在感受与思想寓意。这两个层面的区分也符合陈寅恪自己关于“古典今情”的撰述思想[2]。诸家对于此书的看法,或是在事实层面有所忽略或混淆(如余氏、汪氏等),或是在意义层面有所遮蔽与缺漏(如王氏、刘氏等)。关于事实的层面,我认为需要在上述“辩诬”说、“复明运动”说、“人格史心态史”说以及“明清文化痛史”说等之外,补充一个很重要的“情史”说。只要是认真通读过这本书的读者都一定会重视陈寅恪花了很大的功夫去考证河东君与陈子龙、与宋辕文、与程孟阳、与汪然明、与钱牧斋等人的文学因缘、生活交往。陈寅恪对于河东君十三岁(崇祯三年)自盛泽归家院出,到二十六岁(崇祯十六年)入居绛云楼这一段时期的,如何择婿人海、争取婚姻自由的生活史与情感史,作了极为细密精到的考述,清洗烦冤、探隐发覆,完整恢复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奇女子的生活真相与性格真相。其中贯穿的主题是“男女相知”与“自由精神”。这一以“情史”的重构为中心的历史发覆工作,其意义应不下于陈寅恪对于“复明运动”的历史、明清文化史的发覆工作。这是诸家说《别传》所重视不够的。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意义,请参看拙文《从凤城到拂水山庄》,此不赘述。
关于意义层面,应高度重视与细心解读陈寅恪自己在《缘起》中说明此书作意的诗歌。一是《咏红豆》中“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3],既已表明这是长达二十年的“相思”,于是我们不可以仅仅将《别传》的思想意义局限在四九年以后。这里的“相思”应是有关中国文化的相思与乡愁。从这个意义上看“明清痛史新兼旧”,这个“新”字,应指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化新痛史。对于陈寅恪,在四十年代昆明时期郁结于心的红豆因缘,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忧患意识。如果我们对于四十年代的学术风气有所了解,则不难懂得当时一流学人心目中的“明清痛史”究竟为何。这里只举一个例子。1943年,陈寅恪的好友陈垣致方豪的信中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素乎患难,行乎患难,愿同人共勉之。”[4]从《日知录》到《鲒埼亭集》,正是从经世之学到“故国之思”,正是可以用来说明“明清痛史”的文化情感含量的加重。“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这个“万古愁”,古典与今情即顾亭林所谓“万古之心胸”,依然是民族文化忧患意识。二是《题牧斋初学集》诗最末两句:“枯兰衰柳终无负,莫咏柴桑拟古篇”[5],柴桑指陶渊明。陶集《拟古》第一首:“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是陈诗的古典。枯兰衰柳的今典即中国文化的命运。不负枯兰衰柳,与莫咏拟古篇,都是表明诗人对于文化的承诺。即表明对于中国文化的乐观信念与坚守信念。即《缘起》中所说的此书“乃效《再生缘》之例,非仿《花月痕》之体也。”[6]《花月痕》是中国第一部以妓女为主要人物的长篇小说,讲的是个人的怀才不遇与功名渴望。陈寅恪的意思是此书乃效《再生缘》使中国文化再生,而非写作发抒个人命运不济之牢骚。“珍重承天井中水,人间唯此是安流”,正是说出此书所保存的“心史”,其核心即“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使中国文化再生的关键。如此看来,陈寅恪用来说明《别传》作意的两首诗,一首重在“温旧梦”,即长期郁结的文化相思之梦;一首重在“寄遐思”,即长存内心的文化复兴之思。如此理解陈寅恪有《书竟说偈》中所谓“痛哭古人,留赠来者”[7],虽不中,亦不远矣。
关于意义层面,还应重视的是这本书的书名。从原名《钱柳诗笺证》到《别传》,不仅表明作者对于写作对象的事实层面的认识深化,而且表明意义层面的深化。中国史传写作传统中,合传非常讲究对象或事件的内在一致性。太史公的若干合传,遭后人诟病或表彰,正表明这是一个不可不讲的“史例”。《别传》的书名可以避免钱柳合传的不相称。一方面,不是陈子龙,不是袁崇焕,而是柳如是,成为明清痛史的主角,这又是对于男性中心史的颠覆。另一方面,柳如是最为核心的气质,是陈寅恪在全书中反复强调的她的自由精神,这一点,极具现代精神。我们知道,沉重的民族感情与现代的自由精神在现代思想史中一直是一个文化难题,但在陈寅恪这里不成为难题。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没有冲突。陈寅恪不啻为现代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支点,对于重塑民族魂、士人魂有着深切的启示。这就是这本书书名《别传》实际上指向“儒士”[8]即知识人的深切寓意。
现在再从文体层面去看。《别传》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亦文亦史(兼史学写作与文学写作于一身)的新文本。这一文本具有历史发覆与文化想象两种功用,绝大满足了陈寅恪的学术性格与心灵世界,即透彻的客观了解与深沉的主体感受(参拙文《存在感受与学术境界》)的统一。《别传》的核心是情史,但这个情史,是以男女相知相思情史,寓托文化相知相思情史。是具有中国文学中最为深细优美的心灵世界与中国史学中最为沉痛悲壮的兴亡史事的合一。历史发覆中包含前述社会史考证、政治史考证、心态史考证等。文化想象包含古典与今情。古典中的体验即温旧梦、神游冥想,与古人同呼吸,达到一种陈寅恪所谓“古今交融、真幻合流”的奇妙感受。今情即呼唤一个快要灭亡的伟大文化。这个文化的精神与美应该保存下来,但却不断遭受各种侮辱与践踏。这个文化的魂灵即寓于知识人(即儒士)之中,其内核即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慷慨多气、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品格、自尊自爱独立自由之人格、优美深细的情感心灵世界,以及博学多识的文采风流,“河东君一人之身,可以当之而无愧。”[9]陈寅恪对于河东君柳如是的文化想象,是本世纪对于中国文化最伟大的文化想象,《别传》是一个伟大的富有二十世纪思想的文化叙事,《别传》在现代中国学术经典中的性质,即应由此定位。
注释:
[1]笔者所见专著与文集有:朱傅苍《陈寅恪传记资料》(全二册,香港1977)汪荣祖《陈寅恪评传》(江西1991)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评证》(台北1983)《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1989)《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大,1989)《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1994)《〈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1995)以及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1995),陈定宇《学人魂》(上海1996)。所见单篇文章有刘梦溪《以诗证史、借传修史、史蕴诗心——《柳如是别传》的学术精神和文化意蕴及文体意义》(《中国文化》第三期)鲲西《别具一格的传记文学》(《读书》1982.7)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读书》1993.5)李劼《悲悼〈柳如是别传〉》(《读书》1993.4)黄裳《关于柳如是》(《学林漫录》1982)。以下不另注。
[2][3][5][6][7][8][9]《柳如是别传》P10-12,P1,P2,P4,P1224,P144,P376。
[4]《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