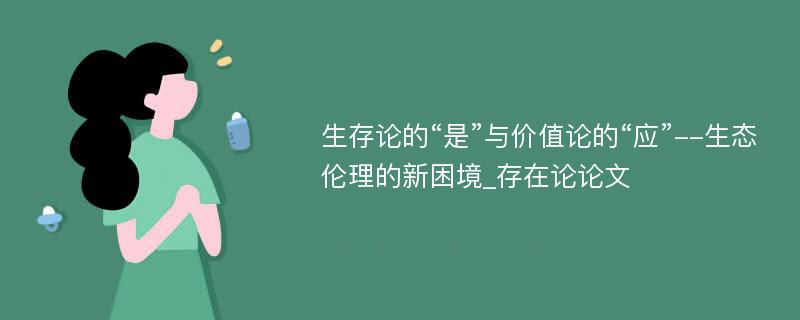
存在论之“是”与价值论之“应该”——生态伦理观的新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伦理论文,困境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6-0036-05
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关于自然价值与生态伦理的探讨成为中外生态哲学界研究的热点。生态伦理思想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学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并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生态伦理的价值主体是自然本身,二是生态伦理的价值主体应是人类而非其他。这些分歧的实质,是人道主义同自然主义的对立。生态伦理学研究的理论冲突集中表现为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的冲突。自然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完全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尺度,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与此相反,人道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则把人类整体的长远生存利益作为生态道德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尺度,把人道原理作为生态学深层的价值论基础。
一、存在论之“是”能否推导出价值论之“应该”
在“人类中心”与“环境价值”之间的关系上,需要弄清楚以下具体问题:关于存在命题与价值命题的区分。也即“是”与“应该”的区分,这里的“是”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指事物存在的“事实”、事实固有的客观属性和客观规律性; “应该”则是一个价值论、目的论、伦理学的概念,它表示的是伦理的规范和人的实践行为的选择。从逻辑上说,事实(“是”)要能够有效地充当行为的理由,就必须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前提。事物的存在属性只是一个“中立”的事实,它只就自身的关系来说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因而不能充当行为的理由。“应该”或“不应该”的道德选择直接依赖的正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因此,如果缺少价值论的根据,单从存在论中是找不到道德原则的根据的。
能否从“是”中推导出“应该”?或者说,能否把“应该”完全还原为“是”?这是生态伦理观所面对的一个最主要的理论难题。生态伦理观把生态自然规律(“是”)作为人类保护自然的道德行为(“应该”)的终极根据,因此,如果它不能令人信服地从自然规律之“是”中推导出道德行为的“应该”的话,那么,这种伦理观受到怀疑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些生态伦理学者从品质伦理学的思路出发,试图从人的最终道德根据来解决生态伦理的基础问题。① 保罗·泰勒就“生物中心伦理”做了严格的哲学论证。泰勒的中心原则是:“当其要表达和体现具体的最终道德态度时,我称之为尊敬自然时,其行为的品德就是好的和道德的。”② 从泰勒的这一思想中,可以看出,泰勒的生态伦理的基础奠定在人的“最终的道德态度”,他认为之所以有生态伦理学,或曰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在于人的好的品德。泰勒的生态伦理学不是从自然的生态描述中而是从人的最终道德态度中寻求依据。然而,在美国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那里,“是”与“应该”的区别则被不加证明地轻而易举地消除了。他认为,从“是”到“应该”“是一个瓜熟蒂落的价值飞跃”。“这里的‘应该’并不是亦步亦趋地从‘是’中推导出来的”,“但同时,‘是’与‘应该’的截然二分又不复存在了”。罗尔斯顿也承认,这的确“令伦理学家困惑而又惊奇”,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我们只要拂去了盖在‘事实’上的灰尘,那里的‘价值’似乎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③ 罗尔斯顿的这种解释,对于习惯于理论思维的伦理学家来说,是不能不感到困惑而惊奇的。
从自然的“是”中,推导不出道德的“应该”。想从自然的“是”中推导出道德的“应该”,这是在错误的起点上走向黑暗。道德感本身是自然进化流程中最高的“是”,是具体的人际伦理、生态伦理“应该”的来源。如果要消除“是”与“应该”的界限,应从这个最高的“是”入手,而不是立足于罗尔斯顿所谓的自然有机体稳定秩序的“是”。罗尔斯顿自然有机体稳定秩序的“是”只是自然的“是”,虽可引发人的道德“应该”,但它不是生命进化流程中最高的“是”。从最高的“是”中,就能够得出生命的具体“应该”。这些具体的“应该”不是从利益出发,不是经济上的精明算计,而是从人的内在本质上要求人必须遵从这个最高的“是”去“应该”,这个道德上的“应该”由于源于最高的“是”,故其本身就属于“是”,是“是”的进一步具体展开。我们说离开对人类利益的关注,就不能从“是”中推导出“应当”,这并不意味着“应当”与“是”毫无联系。我们只有承认了生态规律的真理性和不可抗拒性,才能发现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对人类生存利益的价值性,因而为了人类的生存利益才能得出“应当保护生态自然”的道德选择。就是说,从人类长远的生存利益出发对生态自然事实(“是”)的价值评价,是把生态自然的“是”同“要保护生态自然”的“应该”联系起来的价值论基础。总之,从自然的“是”中推导不出伦理的“应该”,只有将人类道德的“应该”视为自然生命进化流程中产生的最高“是”,生态伦理才会有自己真正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最高“是”中,人类尊重万物的“应该”才不会受制于人类的经济利益,而是源于生命内在的本质要求、源于对宇宙智慧高于人类智慧的敬畏。只有这样,真正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才可能诞生。
二、自然抑或人类是价值世界的中心
针对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们进行了多元的分析和思考,其中,对环境问题的人文反思是学界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许多学人都把目光聚焦于此。在对环境问题进行人文反思的过程中,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把矛头指向了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的一种观念——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一场新的价值观的革命,把人类看成是生物共同体中普通的一员,如个体生物、物种、自然存在物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存危机。关于“人类中心”的概念,与任何理论问题一样,也要首先有一个定性的把握。人类是不是、或者是什么样的“中心”?对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它大体上是一个关于世界存在的、“实然的”描述与判断,还是一个关于人类行为的、价值或“应然的”观念?把握存在论与价值论的区分是一个基础,只有弄清概念是在何种意义上形成或成立的,才能够合理地判断其是非得失。
从存在论的意义看,世界(大自然、宇宙)是没有或无所谓“中心”的。根据已有的科学知识可以知道,茫茫宇宙是无限的,它并无中心;我们人类生存的地球是以太阳为中心在运转着;而地核则是地球自己的天然的物理中心……这一切都与“人类中心”无关。相反,对于宇宙大自然来说,地球上人类的存在,无论从空间、时间还是从绝对力量上看,都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相信上帝或造物主者除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肯定“人是世界存在的中心”,否则便是一种极端的无知和危险的狂妄。一般说来,学术界在这个层次上并无真正的分歧,有意地主张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情况,可能实际上并不存在。存在不等于价值。如果注意到存在论与价值论两种命题之间的基本区别,那么我们对于“人类中心”现象就要有一个清醒的客观的判断。一方面,看到它是、并且仅仅是一个价值命题,不可用它来否定或取代关于普遍存在的根本命题;另一方面,承认它作为人类的价值原则,总体上是必然的、合理的,不可以企图用某种理由而废除之。讨论中有时出现把两类命题相互混淆或等同的情况,比如用“自然界是否先于人类或比人类更有力”之类的存在判断来直接肯定或否定“人类中心”观念,在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包括主张以“天道论”取代“人道论”的论点,由于其论证只是强调了一种(不是全部)存在的事实,以此为理由来否定一个普遍的价值判断,就必然显得缺少足够的说服力。
另一个是关于价值的本性和本义。价值概念本来是用来表示同存在论关系不同的一种特殊类型关系的概念,价值关系是一种不同于存在论关系的特殊关系:存在论意义上的关系是一种自在的关系,而价值关系则是发生在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是客体适应主体要求(而不是主体适应客体要求)的关系,是主体以自身需求为尺度对客体的评价和选择关系,是主体的“为我性”的表现,因而是一种“自为关系”。存在论关系是建立在自然原理基础上的,而价值关系却是建立在人道(人的生存之道、发展之道)原理基础上的。
按照我们对价值现象的理解,认为这一概念的本质和特殊性,就在于它充分地表明了人的主体地位。价值就是以人的主体性(“为我”目的性、需要、能力等及其发展)为尺度的一种关系。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人类整体或某一部分人,这一点总是具体地、历史地、多样化地表现出来的)的意义”。也就是说,在所谓价值和价值观念的领域中,正是人(实际上也唯有人)普遍地居于最高的、主导的地位,人是根据,是尺度,是标准,是目的。人类形成“价值”这一概念的本义,所赋予它的涵义和功能,应该说就是如此。这正是价值命题的一般特征和普遍含义,是理解和应用一切具体价值概念的基本前提。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认为,当某一“价值”概念被说成或解释成是在人的尺度以外、或以非人的东西为尺度的时候,我们有理由怀疑它所说的不是“价值”,或者概念被弄得虚假了,被误解了。
科学研究表明,人是从自然界产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同自然界一起发展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揭示了人从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细胞学说表明,地球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都由细胞构成,而且都是从一个原始细胞库传下来的,构成人类身体的基本单位(细胞)同自然界所有生物体的基本单位是同样的,分子生物学更在分子层面证明了人和其他生物的统一性,人和所有其他有机体的遗传物质都是DNA,所有细胞核使用的都是一套意义相同的密码,也就是说,人同其他所有生物有相同的遗传物质和通用的遗传密码。科学揭示了人的生物学本质,他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靠自然界生活,受自然规律制约。生态学,特别是人类生态学表明,“社会—经济—自然”是一个复合生态系统,在这里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两者的关系并不是以哪个为中心,或一个对另一个的主宰和统治,而是两者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客观规律。它要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汤因比关于人类历史有两个主要过渡时期的思想,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生至人类中心主义的形成,表示人类在生物学方面的提升获得成功,这是第一个过渡时期,现在人类面临第二个过渡时期,即“向新意识的过渡”。它以人的新意识的产生为特征,或许这种新意识就是生态意识或环境意识,即把保护生态环境、追求人类持续发展作为社会价值目标,或社会价值的前提。它表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提升。这种提升将使人类走向一个新时代。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种新的价值观指导自己的行动。人类以这种新的价值观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开始摒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黄色文明”和“黑色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
三、价值的整合与超越:可持续发展观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涉及根本的价值取向问题。二者对立的焦点是:一方面,自然有无独立的客体价值?其客体价值是否可以不依赖于人或不与人发生关系而表现出来?要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是否必须肯定孤立的客体价值?另一方面,人的主体价值与自然的客体价值是否具有平等的地位?我们既要满足人类的合理需求以实现人类的主体价值,又不能以破坏和污染自然为代价来否认自然的客体价值,那么,人类的出路何在?
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与贯彻。可持续发展观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更承认人对自然的保护作用,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采取了一种价值整合的态度。
一方面,可持续发展观汲取了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自然具有独立的客体价值”的思想,承认自然不仅具有工具价值,也具有内在价值,但又不能把内在价值归于自然自身,而提高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性质。④ 人类也是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自然大家庭中的一员,人类无权利去占有与主宰自然,或者说人类无占有与主宰自然的权利。从逻辑上讲,既然人类并非自然的主人,自然就不能被人类视为私产,以供人类占有与主宰。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促使人们开始把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当成自己生存发展的内容和标志、权利和责任之一,当作入全面健康发展目标中的一个有机成分加以珍重和保护,使人类进一步思考:如何保护和优化人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以保障人自身?当然我们决不可能为了自然而保护自然,而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其实质是保护自己的“无机身体”,是人类对自己与自然的真正的一体化,“在这种一体化中,人仍然是‘中心’,是人自己一切价值观念的中心。但这一次所达到的‘自我中心意识’,却是一个更广大、更长久的‘人类自我’——人与自然界的一体化——为主体的意识,因此也是更加理性的、全面的自我意识”。⑤ 事实上,自然的客体价值在于它自身又在于它对人的意义,问题只是这里对人有意义,应当不仅考虑对当代人还要估计到对后代人的意义,不仅是考虑到对人的局部和眼前利益有意义,还要对全局和长远利益有意义,这样来讨论尊重自然价值同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关系,才是既现实又清楚的。⑥
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承认“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人类所特有的“能动作用”,承认人的主体价值,承认人类在这个统一整体中占有的道德代理人和环境管理者的地位。这样,就避免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中所带来的困难,从而更具有适用性。人与自然通过实践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双向价值交换,人类要享用自然当然就要改造自然,因为自然不会主动满足人。就算自然有其独立的客体价值,人类要尊重自然价值,按自然发展自身的要求来对待自然,这不等于说,人应如自然动物一样,不要去改造自然,只要适应自然就行了。倘若如此,岂不是剥夺了人之为人的权利了?人类不应只扮演享用者,更不应扮演自然的征服者,而应扮演自然的管理者。管理好自然是人类的神圣使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制度、合理的行为模式、合理的价值观念,使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损害自然的和谐,因为自然的悲剧往往是社会悲剧的延伸,反过来又加重着社会悲剧。人类要履行好管理自然的使命,做一个称职的自然管理者,担任自己与自然关系的主动协调者,自然意志的忠实表述者,自然法则的自觉执行者,消除工业文明酿就的人与自然的隔膜与敌视。⑦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观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可持续发展思想强调的发展不是单一的无限度的发展,而是“可持续”的发展。这一持续性不仅指向人类及其未来,而且指向与人相伴而存的自然,这就使人的发展具有了高度的前瞻性,因而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较多了一份理智,少了一份狂妄。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可持续发展思想强调的是“发展”,将发展放在中心,剔除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需求的压抑,使人的需求能够得到不断的满足,因而它比非人类中心主义更合理、更进步。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真正架起了人与自然的桥梁,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自发走向自觉。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由于缺乏改造和控制自然的能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自然的明显制约,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都是在自发状态下进行的,并没有认识到应当如何处理这一关系,只是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断地改变着其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则建立在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合理分析之上,它以一种更为理f生的方式去自觉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目的直指未来,从而在更为合理的层面上规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的含义。⑧ 作为理性的人应该主动地适应自然规律,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约束自己的行为,将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一个和谐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以人的意志为本。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⑨ 胡锦涛更明确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建设自然就是造福人类。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⑩ 所以,我们既要尊重自然的客体价值,又要保护人类的主体价值,实现二者的整合,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留下一个适合于后代居住的地球。
注释:
① 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林官明、杨爱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② 《环境伦理学》,第157页。
③ W·F·弗兰克纳:《伦理学与环境》,《哲学译丛》1994年第6期。
④ 闫增强、陶昆刚、秦炳慧:《可持续发展的伦理价值观综述》,《生态经济》2005年第7期。
⑤ 李德顺:《从“人类中心”到“环境价值”——兼谈一种价值思维的角度和方法》,《哲学研究》1998年第2期。
⑥ 陈昌曙:《哲学视野中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53~57页。
⑦⑧ 刘湘溶、李培超:《论自然权利——关于生态伦理学的一个理论支点》,《求索》1997年第4期。
⑨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9页。
⑩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科学时报》2004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