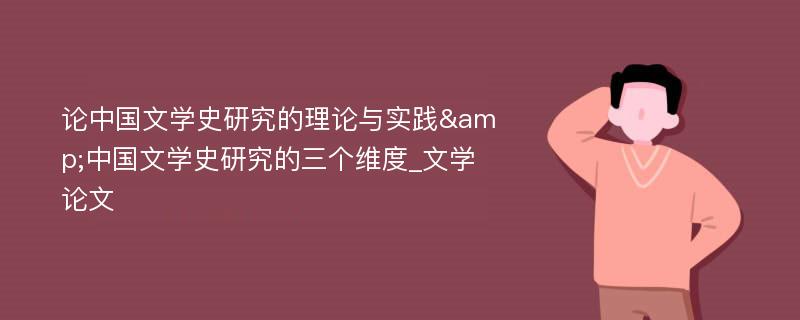
“中华文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笔谈——中华文学史研究的三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论文,笔谈论文,维度论文,文学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中华文学史,当然是指包括了中国各民族、各地域的整体文学发展的历史,其中要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它不能只是汉民族文学的历史,而应涵盖中国境域内其他各民族文学的历史;二是它需要探讨、描绘各民族文学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碰撞、影响、交融等层面的历史关联。如果要真正对中华文学史展开有效的研究,我以为有三个主要维度必须得到足够的关注。 一、各民族文学的特色研究。这是中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不首先弄清各民族文学的内涵、特色与面貌,就无法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主流文坛很少关心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加之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以记载其文学活动及创作,留下来的文献也相对较少,因此以前的所谓中国文学史也就是汉民族文学的历史。这显然不是中华文学真实的历史面貌,因此当今的中华文学史研究也就必须要扩展视野、扩大对象,进行各民族文学史的独立研究,勾画其独特面貌与发展历史。最近三十年,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朝鲜族都有了自己的文学史或诗史,但研究中也还存在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中有两点应当在此提出来进行讨论。一是民族与区域的关系问题。有许多地区存在着多民族的现象,比如青海,既有藏族、蒙古族和回族,也居住着汉族,因而要撰写青海文学史就必须关注其境内的各个民族。而同一民族又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区域,比如藏族,不仅西藏是其集中聚居区域,而且四川、青海、新疆也居住着大量的藏族人口。如果写藏族文学史,仅仅涉及西藏一个区域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深入讨论。因为这两个因素是互为影响和密切关联的,不在学理上梳理清楚,就会影响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二是民族文学研究中的评价问题。每一民族在研究其自身的文学史时,都会带有偏爱本民族文学的情感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进行学术评价时却必须加以理性的控制,不要刻意拔高其创作成就。民族文学研究,其目的主要在于发掘本民族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独特性以及形成此种独特性的各种原因,而不要比较各民族文学成就的大小与地位的高低。对于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家或理论家予以重点论述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这些人体现了上述所说的独特性。但就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刻意拔高与虚为溢美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 二、中华文学通史的叙述方式。中华文学通史的研究重点与叙述方式,应该与地域文学的研究有明显的差异。各个民族的文学研究,都希望在中华文学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较为重要的位置,其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将所有的民族和地域文学都纳入中华文学史的叙述格局,就其实际情况看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中华文学史应该是一部以汉民族文学发展为主线,包容了相关民族与地域文学的历史。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一部汉族文学与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史。所谓关系史,是说作为中国文学发展主线的应该是汉民族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作家数量、创作水平和理论深度上看,还是从作品传播与读者接受的层面看,汉民族文学作为中华文学发展的主线,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中华文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又绝非汉民族一个民族所能承担与包容的,而是由众多民族共同参与而共同促成的。秦汉之前的文学格局,乃是一个各部族文学之间碰撞交融的结果,当时的吴越、荆楚与东夷等地域,实质也属于后来的民族文学,但经过碰撞交融,后来都被整合进主流文学里来了。因此,所谓的汉民族文学本身就是民族与地域文学交融的结果。在后来中华文学的发展中,某些历史时期少数民族的文学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由此,各个民族的文学是否能够纳入中华文学史的叙述格局,其标准应该是是否与主流文学史发生了接触与关联,是否为主流文学的发展发挥了作用和作出了贡献。在这一点上,不仅各民族的文学不是等同的,甚至各个地域的文学也不是等同的。在民族文学中,对主流文学发展促进最大的应该是蒙古族和满族,这两个民族都曾一度成为统治全国的力量,其对当时文学的属性构成与发展推动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像藏族、维吾尔族和回族,尽管没有达到蒙古族与满族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也由于其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文学创作的鲜明特征而对汉民族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区域文学也是如此,在明清两代,文学的重心一直在向东南的吴越一带倾斜,那时的主流文学甚至就是吴越文学,在主流文学史中吴越地区的作家群体、文学流派也得到了更多的彰显。因此,在研究各民族文学时,理应是系统完整的,而且不存在优劣的问题;而在进行中华文学通史的撰写时,必须以介入主流文学的多少和深浅作为叙述的选择标准,否则将无法进行学术操作。 三、具有聚焦作用的易代之际研究。中国文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是无处不在的,但其方式却不尽相同,有时以温和的方式进行,有时则代之以激烈的对抗方式。比如宋代,整个王朝几乎都伴随着汉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对抗,宋夏之间、宋辽之间、宋金之间、宋元之间,几乎与宋王朝的兴亡相始终。而宋代文学的爱国主题、危机意识、内敛特征均无不打上这种对抗的烙印。但是,最能体现各民族文学之间冲突与交融作用的乃是中国历史上的易代之际。因为朝代更替是一种激烈动荡的政治变迁,又往往伴随着民族的对抗与冲突,许多平时被遮蔽隐藏的文化元素都被推到无可回避的历史前台,考量着几乎所有的文人,于是文学的民族交融便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我曾经在《易代之际研究的学术价值与难点所在——兼及张晖之〈帝国的流亡〉》(《中国文化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其价值包括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士人选择的多元、文化价值的重估与思想观念的复杂、文学风格的多样与审美形态的趋新。其难点则包括了文献的缺失与错讹、历史跨度过大所造成的认知模糊和研究者所居立场的难以把握。从民族文学交融的角度,对上述看法还可以做出补充。在人们的日常理解中,民族文学交融往往是通过作家间的相互影响与作品的相互阅读而实现的;而在易代之际则往往采取的是激烈对抗方式,是通过血与火的形态来实现的。但必须要认识到,对抗也是交流,通过对抗也可以进行民族间的融合,并激发出巨大的文学活力。比如宋元之际,蒙古族的强大军事实力导致了金王朝和宋王朝的灭亡。基于情感倾向与政治立场,许多文人采取了不与元王朝合作的态度,并构成规模可观的遗民群体,留下了大量的悲愤感伤的作品。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元曲质朴畅达的风格使其成为元代广受欢迎的文学表达形式,而诗歌创作也从宋调转向了唐调,这无疑是民族文学交融的结果。有时这种交融是通过巨大的政治代价与悲愤痛苦的情感折磨来实现的,但它依然是民族文学的交融,是通过对抗方式实现的交融。比如元代灭亡南宋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废除了科举考试,这使得许多文人都失去了进取的机会而深感人生的绝望,从而不得不转向诗文的创作。这也是一种变化,是一种不得已的变化,却依然是文学发展演变的一种动力。也正是这种文化与文学交融方式的独特性,造成了易代之际文学交融研究的难度。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研究者往往会站在汉族的立场来看待和评价易代之际的文学问题。比如像文天祥、陈子龙这些作家往往能得到正面评价,而像戴良、王逢、钱谦益、吴伟业这样的作家则往往被忽视或贬低。至于那些少数民族作家,也许在承平时期会被研究者关注,而处于易代之际的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那些有所谓“入侵”身份的作家,就很少有机会被关注。其实,从文化交融的层面,则无论是坚守汉族气节者,还是徘徊于对立双方者,乃至身处敌对政权的作者,都应得到系统的研究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其中当然有文人品格与政治立场、文化坚守与现实关怀之间的种种矛盾,需要认真思考与反复拿捏,但易代之际无疑是一个具有巨大学术空间与研究价值的领域,从而构成了中华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在此,只是提出了几个我自己认为比较重要和相对熟悉的方面,并不是说中华文学史研究只包括这些层面。我认为它是一个极为丰富的重要学术领域,需要学界更多的人加以关注与研究,才能取得可观的学术成就,并提升其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