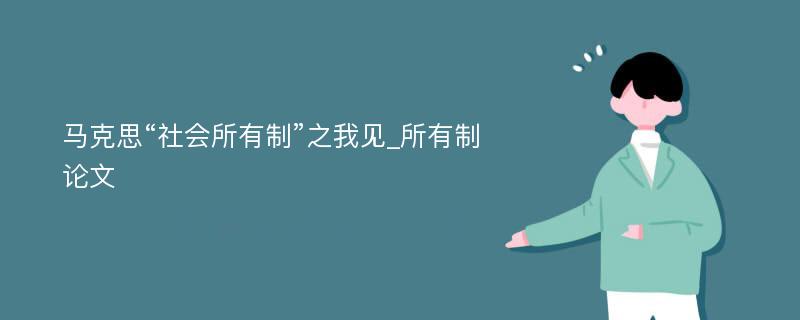
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所有制论文,我见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和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一)问题的提出
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问题的研究,历来分歧颇大。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人们重新提出和研究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问题时,分歧和争论仍很大,特别是对“社会所有制”或“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更大。
过去在我国经济学界流行的看法是,认为这里的“个人所有制”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主要依据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论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马克思那段话之后说过:“可见,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得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 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第1 版第128 页)在80年代以来的争论中,有人对此提出了疑义,认为指的是生产资料,并申述了种种理由(见戴道传:《论公有制基础与个人所有制》,《江汉论坛》1981年第8期;林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研究》,求实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期第54页)。但仍然有不少人坚持认为,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就是“指生活资料已不是为资本家所把持,而是归工人个人所有”。在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理解为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的人中间,对个人所有制的理解也不尽一致。近几年,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越来越多。一些人不仅坚持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只是指消费资料归个人所有,而且推论说,如果认为这里包括生产资料,那就等于主张私有制,就是为主张私有化的人提供理论根据;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个人所有制”只能是指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并以此为根据认为当前所有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把国有资产分解,分配到每个人手里(在价值形态上),以实现个人所有制。此外,也有的人为了避免“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被用来为重建私有制辩护,而回避这种提法,或者甚至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提法说成是马克思的疏忽、误用或某种借用,而否定这一提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都涉及到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的理解问题,也涉及到改革的方向问题,这就使我们不能深入系统地重新研究马克思有关未来社会所有制的问题。
(二)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和研究方法
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必须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提法。而要弄清楚他们对问题的基本提法,又必须首先弄清楚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的导师、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他们是在尚无社会主义实践的条件下,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得出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代替的结论,设想和预见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消灭以后的未来社会所有制的。他们的研究方法总的来说是科学抽象法,是演绎的方法,而不是实证分析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对于这种科学抽象法,马克思本人有过专门论述,这里不赘述。这种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就是排除各种干扰因素,在“纯粹状态”下考察对象。马克思说:“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际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第8页)他们在研究设想未来社会生产关系时,是以19世纪中叶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以英国的物质生产力为背景的。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英国,在工业中不仅早已通行着机器大生产,而且生产集中已经十分发达。在工业生产领域,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神奇的发展。至于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也占居统治地位,个体农民的比重很小,已无足轻重,农业已由中世纪的手工业技术转变到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上来,农业生产力在向工业看齐,从而出现了各个社会领域生产力水平的均一化。正是根据这种工农业生产的全面社会化的发展趋势,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被社会所有制所否定、所代替。在这里,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就必须舍弃社会生活中的非资本主义因素,因此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最少受干扰,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最为典型的英国作为研究对象,从英国的实际出发,通过理论抽象,再现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历史趋势。为了研究和设想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马克思并没有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必须运用科学抽象法。马克思正是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基础,通过理论抽象,撇开未来社会可能存在的不成熟阶段和暂时因素,而设想出一种纯粹形态的或典型形态的新型所有制,即“社会所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考察过当时生产力社会化程度不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德等国。他们针对那里还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经济的情况,指出:这些国家要经过“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635页)。在他们看来,由集体所有制走向社会所有制, 不需要很长的时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设想和推断出的未来社会所有制,不可能怎么具体,必然带有很高的抽象性和原则性。尽管如此,但决不能说他们设想的未来社会所有制是脱离实际的空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所有制的基本提法,除了与私有制相对的“公有制”以外,最一般的提法是“社会所有制”。这一点集中反映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以及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序》中谈到这部著作的特别重大意义时也强调了“社会所有”。他指出:“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一致用以概括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3页)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概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矛盾发展的趋势时说:“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社会所有”(《列宁选集》第2卷第599页)。这表明,恩格斯以及列宁与马克思一样,确认对未来社会所有制的最基本的提法是“社会所有制”,而不是别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的真正含义和它的基本前提,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解了:人们常常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二、“社会所有制”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一)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究竟是指什么?
“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或“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基本概念。关于这个概念的最本质的规定性,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之中。在那里,对社会所有制有一段最为概括的说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7页)。紧接着,马克思又指出:“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在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中被译为“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的所有制”(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人民出版社1963 年12月第2版,第842页,着重点是原有的)。从原文看,“社会的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较之“公有制”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如果联系到马克思在十年以后对这段话的解释,那就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重提那段话时指出:“我在关于原始积累的那章中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在那一章末尾,我把生产的历史趋势归结成这样:它‘本身以主宰着自然界变化的必然性产生出它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因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个体生产者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的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130页)由此不难看出,经过“否定的否定”,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实际上也就是“社会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在作为最后一种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被否定以后或者说同“传统所有制彻底决裂”以后,新出现的所有制只能是“社会的所有制”。而在那时,“个人”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不复存在,每一个个人已由分散的、孤立的、单个的个人成为社会的个人,就是说,“个人”与“社会”达到了高度和谐,以至融合为一。这样,在社会化生产和社会化劳动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就成为同一种所有制。因此,马克思有时称这种所有制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他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有将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说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同上,第48卷第21页)。
这种“社会所有制”只能合理地理解为马克思设想和预言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所有制。这里所说的“未来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的科学抽象,是一种“纯粹的”典型形态,它反映的是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大同世界”。因此,作为这样一种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的“社会所有制”也是一种理想的“纯粹的”典型形态。它的实现途径、过渡形态以及种种具体因素等等都被舍弃或抽象掉了。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1)社会所有制的实现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 就像“主宰着自然界的变化的必然性”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2)它是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就为基础的”,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第605页)。(3)社会所有制是彻底废除私有制或者说“同传统所有制彻底决裂”的结果。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谈到“彻底废除私有制以后将产生什么结果”时指出:“由全体社会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而有计划地尽量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全体成员需要的规模;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情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灭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交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一切都将是废除私有制最主要的结果”。
这也就是在未来“社会所有制”下的大致情景。(4)社会所有制是一种由整个社会共同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或“现有生产力的总和”的所有制。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是单一的也是唯一的所有者主体,而且它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因此“社会所有制”必然是唯一的所有制形式,这也就排除了任何其他所有制形式,诸如后来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等等存在的可能性。(5)既然社会所有制就是整个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那么在这种所有制下也就不可能存在“所有者”和“非所有者”的区别和对立,所有社会成员人人都是占有者也就成为自然的事情。在这里,“社会占有”和“个人占有”、“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就成为一回事。
(二)为什么社会所有制也就是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
这个问题似乎很费解,也是产生歧义的症结所在。因此,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有人认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个人所有制”的提法是一种疏忽或误用。这是一种误解。其实,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社会所有制”。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就说过:“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6页)他和恩格斯还指出, 在未来社会“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资料的总和”(同上)。以后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多次阐明这一思想。直到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巴黎公社“曾想把现在主要作为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把实现“社会所有制”界定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强调“个人”和“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是与他们关于“个人”与“社会”、“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及其关系的思想分不开的。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人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同样是摆脱生产资料的奴役状况而获得解放的过程。而社会的解放和个人的解放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恩格斯指出:“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状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89页)
马克思把人的发展与“三大社会形态”相适应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成三大阶段,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1)“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2)“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3)“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4 页)这里所说的“最初的社会形态”或“第一大社会形态”大致可以被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诸社会形态的概括,“第二大社会形态”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第三个阶段”或“第三大社会形态”即指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与“三大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相适应,马克思把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的阶段。这是一个包括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以前各个社会阶段的漫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人的活动和发展依附于各种特殊的群体,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为依托的。人的依赖关系在历史上最初表现为原始社会的氏族和部落的血缘关系,以后则发展为奴隶社会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关系、封建社会封建主和农奴的阶级关系,以及与这些阶级关系并存的等级关系和种姓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包含着“个人之间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同上,第104页)。在这里, 个人的发展受到他所属群体的整体地位的状况的制约,“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这种“人的依赖关系”,是以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联系的。归根到底,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因而,在这个阶段上,“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这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第一次摆脱了人身依附,人不再是以附属于某一群体的特有身份生存和发展,而开始以独立的个人的身份来安排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对于劳动者来说,自己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人,具有“独立性”,但他又必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这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制和商品经济,使得人们都卷入普遍的交往关系,即“形成普遍的物质交换,全面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便隐藏在这种普遍的交换关系或“物的联系”之中。而人们对这种物的关系和联系无法控制和掌握,只能服从和受制于它。于是便产生了“物的依赖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分工的空前发展,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这一方面导致独立化的私人生产者和社会的对立,另一方面又造成劳动者及其活动的片面化和畸形化。这样,分工这一历史上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开始显示出了局限性即对人类生产能力发展的消极影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过去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6 页)这一段论述,既适用于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也适用于第二阶段。就是说,无论是“人的依赖关系”也好,“物的依赖性”也好,归根到底,就在于“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87页)。第三个阶段是人的“自由个性”的阶段。 “自由个性”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这是实现“社会所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不仅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而且摆脱了“物的依赖性”即物对人的支配,从而真正独立地、自由地存在和发展自身,按照自己的个性特点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由分工造成的物对人的支配,“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而要“个人重新驾驭物”, 就必须有“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同上,第23卷,第649页)、 “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同上,第3卷,第77页)和支配。 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内容。在这里,社会即“自由人的联合体”将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作为社会或“自由人联合体”成员的每个人也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得到解放,个人也得到解放。这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与社会结合的主人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80页)。 实现这一目标是现代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事业的历史使命。但现在的现实条件决定了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三)“社会所有制”的前提条件
恩格斯说过:“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同上,第278 页)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社会所有制”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作为未来的理想,作为一种科学假说,是有其前提条件的。只有具备了这些前提条件,它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否则,是无从谈起的。那么,实现“社会所有制”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概括地说,至少需要具备以下前提条件:
——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这不仅包括产品或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这样的生产力水平的数量规定,而且包括作为社会生产力重要因素的“人”和“物”在质上的极大提高以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技术组织形式的最优化。现在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的社会生产力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比当年高得多的社会生产力没有达到实现“社会所有制”所需要的水平。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已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趋势,但距离社会所有制得以实现的那种社会生产力还相当遥远。
——彻底消灭社会分工,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对立、阶级差别,消灭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等等。这里特别重要、然而以往常常被忽视的是关于彻底消灭社会分工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所有制”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设想是与彻底消灭分工紧密相联系的。或者说,实现社会所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以消灭分工为前提条件的。如果不彻底消灭分工,“个人占有生产力的总和”就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9页)他们还形象地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同上,第37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到目前为止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85页)只有消灭分工, 改变人们“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的状况,才能实现“个人全部占有生产力的总和”,才能有“社会所有制”。恩格斯指出:要实现社会所有,使社会和每个人都得到解放,“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89页)。
——随着分工的消灭,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也不复存在。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 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得更加明确:“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恩格斯:《反杜林论》第278页)
——国家已经消亡。国家总是和阶级的存在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预言,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去,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这就是说,“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无国家的社会。在国家尚未消亡以前,是谈不上“社会所有制的”。
我们从上述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社会所有制”差别甚大,不可相提并论,不可同日而语。无论以何种形式,把现实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说成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所有制”或重新建立起来的“个人所有制”,都会陷入误区而产生混乱。
标签:所有制论文; 恩格斯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生产资料所有制论文; 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本论论文; 反杜林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