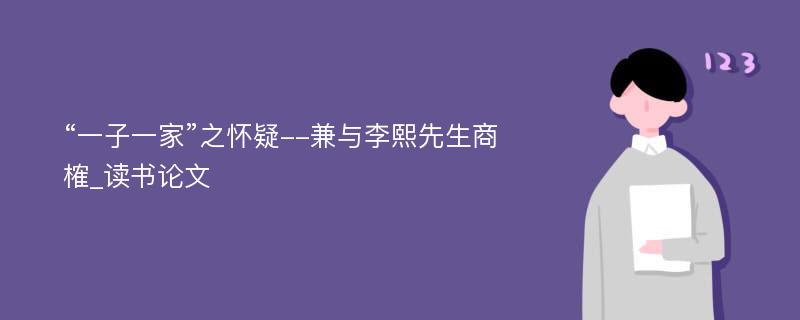
“一子賅括一家”說之獻疑——與李銳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子賅括论文,與李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秦諸子研究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份。李銳先生《“六家”、“九流十家”與“百家”》(載《中國哲學史》2005年第3期,以下簡稱李文)對先秦百家和兩漢六家、十家做了比較研究,涉及到諸子研究的若干元理論,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的觀點,讀後頗有啓迪,這對推進諸子研究是有意義的。但對李先生的百家和六家、十家總體評價筆者不敢苟同,對該文涉及的諸子研究若干元理論筆者也有异義,此將另文論之。現僅對“一子賅括一家”說冒昧獻疑,非好辯,實事關先秦百家諸子情境大勢的認知和判斷,事體重大,以期有益于先秦諸子百家研究。
“戰國時代,論及‘百家’時,子是家的代表,舉一子可以賅括一家”是李文的中心論題,這是李先生以《莊子·則陽》稱季真、接子爲“二家之議”,《韓非子·定法》說申不害、公孫鞅是“二家之言”爲案例得出的結論,視爲戰國表達百家方式的基本義例,也是區分百家與六家、九流十家表達方式的重要標識。“‘百家’與‘六家’、‘九流十家’,同是用‘家’,其實意義並不相同”。“季真、接子二人,申不害、公孫鞅二子,就是‘二家’,是所泛稱的‘百家’中的二家,與‘法家’等說法無關”。所以地位相當重要。可以說,李文基本運思路向和許多重要結論都是建立在其上的,在李先生其他研究諸子文章也將之反復重申。①由于該命題主要不是說戰國出現和存在著這種表達方式,而是把它作爲戰國表達百家方式的基本義例。因此,我們首先研究戰國表達百家方式,然後再進行“一子賅括一家”的意藴分析和地位評價。
戰國已經出現了以一組人物去評價諸子、表達百家的表達方式,孟子發其端倪。《滕文公下》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朱、墨翟不是同一流派而是兩個流派的人物,孟子把他們並列成爲一組,其組合原則顯然是他們有某種學術思想和學術活動的相似性、共同性。孟子這種思路和方法被莊子荀子繼承,並且更規範更集中擴展運用于諸子流派分類。《天下》在論述道術爲天下裂,諸子各得一隅成爲百家後,又把諸子分組再具體分叙,有一人爲一組,有二或三人爲一組,後者分別是墨翟和禽滑釐、宋鈃和尹文、彭蒙田駢和慎到、關尹和老聃。《非十二子》評點十四位諸子分成七組,它囂和魏牟、陳仲和史鰌、墨翟和宋鈃、慎到和田駢、惠施和鄧析、子思和孟軻、仲尼和子弓。莊荀分組的人物構成有兩種類型:一是同一流派的人物,此占少數;一是不同流派的人物此占大多數,是一組人物構成的主綫。這意味從這裏將導致和産生能够包括不同流派的學派,莊荀這種分組模式和思路對後世影響是很大的。
李文也承認戰國已經出現這種表達方式,並且認爲它與六家說相去不遠了,但並没有給予其獨立的表達方式地位,而歸屬于“一子賅括一家”表達方式。說《天下》的“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等,與《成相》的“慎、墨、季、惠”一樣,都是舉一子賅括一家的,只是“多了‘之徒’‘之屬’這樣的表達”。其實,一組人物表達方式和一子人物表達方式是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分別以一組人物和以一子爲家爲存在單位,如果按照《定法》《則陽》的表達語境,則《天下》的彭蒙、田駢和慎到,《非十二子》的惠施和鄧析,將不是一家而是三家和二家,這很有區別。
李文還認爲一組人物表達方式是晚出的,在“一子賅括一家”後。很可能在“《孟子》、《尸子·廣澤》、《呂氏春秋·不二》”後,“將不同學說之間的相似點揭露出來以進行批判,也變得流行,《荀子》或可爲證”。按《廣澤》和《不二》是李文“一子賅括一家”的個例,《天論》和《解蔽》也如此,故李文引考證說它們是荀子在稷下時作,《非十二子》是荀子晚年居蘭陵時作,這種晚出論更需要商榷。它不僅是對一子和一組人物表達方式産生先後的判斷厘定,還是對它們與百家關係的認識理解。且不說《廣澤》和《不二》是否就是在《天下》和《非十二子》前,更重要的是,在最早啓用百家概念的《天下》中,百家概念與一組人物表達方式恰恰是同時出現、相互對應的。莊荀是最早啓用百家概念者,同時也是規模運用一組人物表達方式者。《天下》和《非十二子》是具有最原初最直接意義的解讀百家的文本,《天下》尤爲如此,這是我們今天研究百家概念應當注意的。《天下》在概述道爲天下裂,“百家之學時或而稱道之”,“百家往而不返”後,緊接著是論禽滑釐、宋尹、彭田慎、關老等一組人物對道術的認同運用,百家概括泛論在先,一組人物具體分叙在後,這種闡述形式已經明確表明,一組人物是百家的主要角色承擔者,所謂百家主要是通過一組人物而面世表達的,它們有內在關聯性。一組人物是爲了表達百家,百家須用一組人物去展現,因此,不能離開百家去認識一組人物,也不能分離一組人物去論述百家,一組人物不是與百家無緣而起孤立而生的。這就要求我們應該立足于百家面世去研究一子和一組人物表達方式的産生先後,離開百家面世而論述它們的産生先後對于本論題没有意義。即使是一子表達方式産生于前,但在《天下》那裏,一組人物表達方式是與百家同時並列的,如果没有其産生,所謂百家也就不成爲百家。因此,我們不能把一組人物排斥于表達百家方式之外,只說“一子賅括一家”是表達百家方式不符合百家面世的實際情况。百家恰恰是以一組人物而不是以一子爲表達方式的,在這個基本問題上,李文是顛倒了。
一子和一組人物表達方式與百家關係問題,實際上是對先秦諸子和百家存在關係和大勢的審視和認知問題。中國思想史上,諸子和百家都是對周末以降王官失守學術下移時期思想者活動狀况的描述和概括的概念,有意藴內涵和指稱特色的相通關聯性,人們常常把它們連舉並稱不分軒輊,視爲同一性質和序列,如諸子百家、百家諸子,這是正確的,無有疑義。它們也分別是對子和家的泛指統稱概念,諸和百都是喻子和家的其多其盛。子和家則是指涉思想者學術角色身份,它們有相通關聯也有重要區別,並非完全等同,有細析分疏之必要,尤其是對某些研究目標和研究對象。在本專題,離開了子與家的分疏厘訂,是難以論述百家的,實可視爲研究百家的預設前提。
子與家的區別首先是它們指涉對象存在的載體單位不同。大體說來,子是以思想者個人爲載體單位,是指涉個人的存在;家則是以思想者形成的學術共同體爲載體單位,是指涉學術共同體的存在。顧藎函說:“諸子所以稱爲子者,乃是指其人而說的,並不是指派別而說的。”②以思想者個人還是以學術共同體爲載體單位是子與家的基本區別,由此還衍生出其他區別。其次,比較子的産生家是晚出的,總是先有思想者再産生由他們組成的學術共同體,子産生于家之先,無子則無家,子産生存在是家産生存在的基礎。在一子基礎上逐漸形成了一組子即家。在角色身份表述上,也是先有子概念再有家概念。至于百家則是莊荀設計和創造的新概念,其産生已是戰國時期了(作爲一種概念的諸子産生更晚,在西漢)。這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百家面世前思想界已經有了子的廣泛且有效運用,莊荀又爲何設計和啓用百家呢?思想史上任何新概念的産生都是事出有因,應運所生的,百家的産生是需要解决怎樣的具體問題,針對怎樣的具體情境呢?
百家是要處理和解决子的承擔使命所難以進行和完成者,否則百家的面世没有必要和没有意義。實際上,在莊荀那裏,百家的設制啓用和規模運用已經明確地顯示了一個目標取向,即主要是學術共同體而不是解决和處理思想者個人問題,其學術使命是對其時長足發展諸子活動狀况的概括總結和整合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說,百家和諸子是概括總結和被概括總結、整合提升和被整合提升的關係。百家明顯地表現出對于諸子的統攝性和包容性,在《天下》中百家是與方術對應的,方術是道術分裂的結果,道術和方術都是《天下》設計製造的知識系統和思想系統,道術是天下之公器,不爲一家所私,它在分裂後可從不同角度去認知把握,此即形成方術。許多學者把方術理解成一家之言,即形成爲流派的家,大抵正確。道術可爲一家從某一角度所認知把握,方術作爲道之一端,某子可以認知把握,另一子也同樣可以,故方術不能歸于或等于一子。在《天下》那裏,道術包括涵蓋著多家方術,而方術也包括涵蓋著多子,所以,家比較子更合宜于叙述對道術的認知把握和方術的産生形成。正唯如此,道術天下裂後,並非直接過渡到子,而是以方術爲中介再到子,其順序關係是道術—方術—子,《天下》分疏區別家與子意旨是明確的。
《天下》和《非十二子》評點一組人物時没有明確地稱其爲家,如同《則陽》《定法》稱季真、申子等爲家一樣,但若從其內涵意藴及其顯現展開看是必然稱之爲家的。家的稱謂是重要的,没有把一組人物稱謂爲家表明莊荀畢竟没有跨出這一步,但內在理路更重要,它導致和决定著其必然會稱謂爲家的,莊荀没有完成的事,兩漢史家完成了。因此,我們應該重視但不須泥拘于稱謂的表達形式,更要重視形成表達形式的內在理路。還需指出,莊荀雖然没有把一組人物明確地稱之爲家,但實際上也做了與稱之爲家的相似相通工作,這就是稱之爲者。者是我們研究先秦百家表達方式不能忽視的重要概念。
中國思想史上,最早稱謂諸子學術共同體的概念是者而不是家。者在春秋晚期就出現了,諸子中最先形成學術共同體的儒家和墨家常常被稱爲儒者和墨者。墨子是最先使用者的,《非儒·下》曰:“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儒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人也。”《公孟》曰:“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于嬰兒子哉。”“問于儒者,何故爲樂。”其後,孟子也稱墨家爲墨者,《滕文公上》曰:“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吾聞夷子,墨者。”者的用法以後獲得普遍使用,直至漢初,《六家要旨》的六家並不都是稱爲家的,仍然是沿先秦義例,稱儒墨爲儒者墨者,“儒者博而寡要”、“墨者儉而難遵”。其後,《劉子九流》和《隋書·經籍志》也是用者稱呼諸學派。者和家是通用而互换的。
莊荀也同樣沿襲者的義例去稱謂儒墨。《知北游》、《盜跖》、《儒效》、《王霸》、《禮論》等此例甚多,不需枚舉。《天下》論叙一組人物時雖然没有稱之爲家,但却是回溯古例,將之稱爲者。“南方之墨者”爲“別墨”,“惠施”、“桓團、公孫龍辨者之徒”,“天下之辨者相與樂之”,“辨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等等。而且《天下》把者的稱謂擴展到儒墨之外,把名家稱爲辨者,這是没有師徒傳授關係僅是學術宗旨相似者,者稱謂擴展到無師徒傳授關係層面。李文正確指出,“桓團、公孫龍辨者之徒”與“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有重要區別,《天下》對者的古例用法,有內涵深化和外延擴展。雖然還没有進一步把宋尹、田彭慎、關老等一組人物也一一稱爲者,尚没有普遍化系統化。
《天下》没有把一組人物稱之爲家,對者的采用也有限度,這一情况透露和體現出百家作爲一種反思和概括其時諸子狀况的新概念,其研究和啓用尚處于初始階段。李文說:“打開先秦至漢初的子書,最常見的是百家。”這種對先秦學術思想發展情勢的估計和判斷有誤。實際上,其時最常見最頻繁出現的思想者角色身份概念是子,而不是家,是子撲面而來,而家廖廖可數。真正規模使用百家概念者實只有莊荀兩家,《戰國策·趙策》只是提到“刑名之家”,《尹文子》有儒、道、法、名等稱號,但還没有直接稱爲儒家、道家等。除此外,則只有《則陽》和《定法》的“二家之議”了。家的使用也很少,這種情况遠遠不能與子的使用情况相比較,對于這種存在和發展情勢我們應該有足够的認識和具實的闡述,不能忽視家和子是有所區別的稱謂,也不能忽視在家的産生面世前就有子的普遍應用,更不能無視子的存在,而把子的一切都歸于家並且按照家的模式去理解和闡述。我們對家的産生和存在情勢不宜理想化。
因爲缺乏對家與子的必要分疏區別,對春秋以降子的存在和發展情勢也缺乏應有的認識判斷,李先生把“一子賅括一家”表達方式的適用範圍擴大。把《解蔽》“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云云、《天論》“慎子有見于後而無見于先”云云、《尸子·廣澤》“墨子貴廉”云云、《呂覽·不二》“老聃貴柔”云云,一概說成是“典型的以‘子’爲‘家’之代表的表達方式”。其實,《尸子》和《呂覽》全書都没有百家和家的概念,既無此概念又如何能說舉子是爲賅括家呢?况且《不二》說:老聃等“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③,明言此是就其爲子而論的。百家和家都是晚出的概念,直至戰國晚期只有少數思想家啓用之,要被思想界所認同接受,尤其是普遍規範使用是有一個過程。其時思想家也有家和子混同並用的不規範用法,《徐無鬼》中惠施對莊子說:“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令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辨。”則爲一例。更重要的是,子本身就是一個有別于家的獨立論述對象,論子不一定必須對應觀照和歸結于家,戰國思想家論子不論家的情况很多。即使莊荀自己,有以家爲論述對象,也有以子爲論述對象,並非全然都是只論家不論子的,《解蔽》和《天論》就是明顯地以子爲論述對象的。李文實際上是把點評具體人物的表達方式都說成是表達家,這有失偏頗。李文上述舉例,都是論述子而不是論述家的。
探究和把握“一子賅括一家”之家的內涵特色很重要,在一子說成是一家後,這種家有怎樣的內藴特色,是怎樣的家之爲家者,就成爲認知和評價該命題的關鍵。實際上,它作爲一種表達家的方式只說到問題的一半,即指出了某子的存在載體單位是家。還没有問題的另一半,即此家的命名稱謂,這是更重要的一半。如李文所言,季真、接子、申子和商子都各爲一家,但此等一家是如何命名稱謂的呢?家之爲家總是要有命名稱謂的,命名稱謂不是家前面“一”之數字所能代替的。懷特海說:1、2、3等數字“可無分軒輊地表示”和“應用到任何適當的一群實念(體)上去”。④對此,《則陽》、《定法》原文没有交代,李文似乎也不視其爲問題,但它却相當重要。而且,一家無命名稱謂還導致百家也是無命名稱謂之家的累總。李文把一子爲一家作爲表達百家的基本形式,也就是把無命名稱謂的家作爲表達百家的基本形式。由此組成的百家必然是無命名稱謂一家一家的彙集,一家無冠名導致百家都無冠名。因此,當李文强調“說先秦有百家,决不是什麽誇張之說”時,是否應該考慮這裏的家應該有命名稱謂呢?否則“雖然當前尚看不到一本著作提及所有的百家之名”的設問,所謂“所有的百家之名”的“名”及其被“提及”,又能從何說起呢?
在中國思想史上,給事物對象命名稱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現在,我們需要從正名理論視角去審視和評價“一子賅括一家”。
1.“一子賅括一家”難以給其家命名稱謂。
“一子賅括一家”没有給其家命名稱謂,實際上也難以給其家命名稱謂,因爲該表達方式難以用家的命名稱謂方法去稱謂其家。這裏仍然要進行子與家的分疏,應該看到,子和家的命名稱謂方法是有區別的。按照正名理論,命名稱謂的産生和確定過程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過程,在其産生初始階段雖然有追求和符合對象內在意藴的機制,但也有隨意性,命名形成後必須經過語言共同體的選擇和認同才能確定。約定俗成才能審定名的宜和不宜,與實的符和不符。經過約定俗成確定後的名一般不輕易弃捨和改更,蘇輿說,在“未有名之先,牛可以爲馬,犬可以爲馬”,但一旦經過約定俗成確定後,則“犬性獨則獨從犬,羊性群則群從羊,不可易矣”。⑤牛馬犬稱謂就不可混用了。從約定俗成的結果看,被後人一直或基本沿用的子的命名稱謂方法是直呼其姓,如孔子、申子、商子等。因爲子以思想者個人爲指涉對象,可呼其名,諸子的區別只在子的姓。“子之爲名,本以稱人”⑥,“古人系姓而稱,必曰某子,或曰某氏,而稱家不能系姓”⑦,說子稱系姓而家稱不系姓,大體正確。而家的命名稱謂方法是用能够涵蓋學術共同體的思想觀念或活動行爲的共同意識,因爲家以學術共同體爲指涉對象,共同體是多位思想者的結合體,不宜以其中一子的姓去命名,即使他是該共同體的創始人或關鍵樞要人物,諸家的區別只在于不同的共同意識。“自六經之外,世之學者,各以其道術名家”⑧,所謂道術就是表明思想觀念的共同意識。
在“一子賅括一家”表達方式中,當把季真、接子、申不害和商鞅各說成一家,且要命名稱謂其家時,若按照子的命名稱謂方法,則應稱爲季真家、接子家、申不害家、商鞅家,這種情况思想史上没有出現過,這說明它不符合約定俗成的規則。若按照家的命名稱謂方法,因爲此家由一子構成並没有學術共同體的共同意識,也難以啓用。兩種方式都難以采用。比較一下《天下》是必要的。如果《天下》進一步把一組人物提升和發展爲家時,該如何命名稱謂此家呢?能够稱之爲宋研尹文家、田駢慎到彭蒙家嗎?這比稱季真家接子家更困難,以一子之姓去命名稱謂家都很困難,何况以多子之姓。但《天下》没有按照子的命名稱謂方法,却按照家的命名稱謂方法給一組人物命名稱謂,雖然這是有限度的運用。當《天下》追溯和采用者這一古例,稱一組人物爲墨者、辨者時,也就是給其命名稱謂了。在這裏,者是一組人物的載體單位,墨、辨則是一組人物的命名稱謂。墨、辨,與儒一樣,都是家而不是子的命名稱謂方法,儒、墨、辨都是能够涵蓋學術共同體的共同意識。應該看到,《天下》以“道術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去說儒;以“居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去說墨;以“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辨者之囿也”,“散于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辨爲名”去說辨,都是不同程度地從發生地域、活動行爲和思想特徵等層面揭示了儒、墨、辨三家各自的共同意識。
2.“一子賅括一家”的家不是私名別名的家。
“一子賅括一家”的家没有命名稱謂,按照命名概念分類,它是類名、共名性質的一家,而不是私名、別名性質的一家,如同它類名、共名性質的一匹馬,還不是私名、別名性質的一匹黑馬一匹白馬一樣。只有命名稱謂的家如儒家墨家等才是私名、別名性質的家。正名理論認爲,對某物命名稱謂是使某物能够標識自身和區別他者的重要依據,有“別衆猥而顯此人”的重要作用,私名、別名的産生反映出對于對象事物內在本質和外在形態的理性認知把握的深入具體。從“別”即對于事物分析區別層面看,只有到了私名、別名階段才可以說是到了“止”的階段。
更重要的是,命名稱謂還是對象作爲個體性具體存在的重要標識,無命名稱謂的對象不能說是個體性具體存在的對象。所謂私名、別名産生目的之一就是爲了指明對象是個體性具體存在,類名、共名標識對象是類存在而不是個體性具體存在。《墨經》說在達、類、私三科名中,唯有私名“是名也止于實也”,其對象才是個體性具體存在,才止于實。如臧就是個體性具體之人的名稱,譚戒甫解釋:“臧是私名,這個名即限制在這個實上。”⑨沈有鼎解:釋除私名外,“任何名都不能看作專‘謂’一件東西”。⑩《墨經》這個觀點被後代學者所認同。
先秦的私名別名與現代西方哲學的專名有相通相似之處(11),從專名理論詮釋更有利于問題的闡述。羅素論專名時說:“一個專有名稱基本上只能指一件事物”,專名鎖定在某個具體存在物身上,與類名是指某一類的所有事物不相同。專名“只有這個名稱所指的事物存在的情况下才有意義”(12),它是以該對象的個體性具體存在爲前提而産生的。因此“從理論上說,唯一可以代表一個殊相的詞是專名”,所謂“專名則可以定義爲代表殊相的詞”,這就是說:“只有藉助專名才能談論某個特定的殊相。”(13)明確指出只有使用專名才是研究某個個體性具體對象。换言之,要研究某個個體性具體對象則必須藉助和依靠于專名。
現在從私名、別名(專名)理論去反觀“一子賅括一家”的家了。首先,此家是不能彰顯自身區別他者的家,因爲家没有命名稱謂,所以無法區別此一家與彼一家,季真與接子、申不害與商鞅,他們的家没有區別。如果一定要追究他們的區別,那只有返回到子,即申子和商子等的區別。申子作爲一子與商子作爲一子是有區別的,而申子作爲一家與商子作爲一家却没有區別,因爲子有命名稱謂,其命名稱謂的姓即申和商就是區別的標識。從“別异同”角度看命名稱謂比較存在單位更重要,在存在單位確定後,即申子和商子皆爲家時,他們的存在單位是同一的,都是家。此家與彼家的區別只在于對于家的命名稱謂,而不于其存在單位即家。其次,此家也不是個體性具體存在的家。季真和接子、申不害和商鞅當然是個體性具體存在者,但這不是作爲個體性具體存在家的角色身份,而是作爲個體性具體存在子的角色身份出現的,因爲家無命名稱謂而子有命名稱謂。無命名稱謂的一家是不確定的一家。正如羅素說,“一個人不是指許多人,而是指一個不明確的人”,它是一個“不明確地指稱”。(14)一人是這樣,一家也是如此。
家的個體性具體存在及其命名稱謂是家之爲家的兩個基本構成要件,從“一子賅括一家”的家没有命名稱謂,也不是個體性具體存在的家,所以難以表現家與子的區別相异。而且,此家作爲存在單位的構成數目本來也只是一人,說季真是一家,此家的構成數目只是季真一人(15),構成數目相同,主詞(一子)和謂詞(一家)有同一性,因此說此家是家與說此家是子没有多少區別,說季真、申子等各是一家,實際上仍然是說季真、申子各是一子。(16)其實,《則陽》《定法》的本文語義與注家疏證也都是把此家說成和詮釋爲一子的。《定法》篇末說“二子之于法術,皆未盡也”,明確地把申商二家說成是二子。趙以夫注《則陽》說:“則吾于二子之論,又安能知其所自化哉。”(17)林希逸注曰:“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爲其說。”“二者之說,皆未免于物累。”(18)羅勉道注曰:“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19)都是把家疏證爲是可以與子互换的一種子的用法,這是正確的。“一子賅括一家”其實是古漢語中一家是一人用法的具體應用,這種用法在兩漢史家運用到學派分類時,發生了用法衍變。
3.“一子賅括一家”衍變成二次學派分類。
讓我們再回到子與家的分疏。由于子與家的指涉對象不同,導致它們對各自對象的表達方法的性質有別。子以學者個人爲對象,故表達方法相對直接單一,没有多樣性和複雜性。一子即是一人,一人也即是一子,没有其他情况。家以學術共同體爲對象,故表達方法相對曲折多樣,有多樣性和複雜性。家是多子組成的共同體,也可以爲成一家之言的一子所代表標識(如那些“行無師,學無友”的獨行之士和個體思想家(20));是某一學派的整體,也可以是學派的分枝即派別。顯然,它們各自內藴和展示的子與家的區別是不同的。也正唯如此,古漢語中曾經有過的一家是一人的用法,也被采用到兩漢史家的歷史人物和學派分類的表達中。如《史記·封禪書》曰:“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此數目單位是家,張守節《史記·正義》說:“〈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此數目單位是人。人代替了原來的家,一人和一家互用,封禪者七十二家也就是封祥者七十二人。《漢志》把家是學術共同體和家是學者個人兩種用法並列分用,“諸子十家九流,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的家是指學術共同體,“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篇”的家是指學者個人。一百八十九家即是一百八十九學者個人,不是說一百八十九個學術共同體,故逐一羅列一百八十九人的姓名及著書書目。《漢志》的《六藝略》、《諸子略》等也采用這種用法,已經通用。
《漢志》“凡諸子百八十九家”與《則陽》《定法》“一子賅括一家”的用法有同亦有异。其家都是由一子構成,都是指涉學者個人,都是屬于古漢語的一家是一人的用法。其异是家的命名稱謂,《則陽》《定法》的家没有命名稱謂。從形式上看,“凡諸子百八十九家”也没有給家命名稱謂,但實際上有,因爲它是一總述性概括,其前已經對每家所屬學派分類歸屬了,每一家都是已經命名稱謂九流十家中的一家,而不是没有學派分類歸屬的一家。如說晏子是一家,因其前晏子已經歸屬儒家,故此一家乃是儒家類的一家。冠名已明,不需再稱,這與《則陽》《定法》的季真申子等其上没有分類學派統轄的情况大不相同。此异是不宜忽視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只是二次分類,是隸屬和派生于“九流十家”一次分類的,正是這種二次分類的設計安排,才使命名稱謂問題獲得變通性解决。“九流十家”作爲一次分類是莊荀一組人物爲家的分類模式和思路的演化發展,“凡諸子百八十九家”作爲二次分類也說明了古漢語的一家是一人發生了用法衍變。“一子賅括一家”的內涵意藴决定了它只適宜于學派的二次分類,而難以適宜于一次分類。
①《九流:從創建的目録名稱到虛幻的歷史事實》說:“在先秦,每一個自成一家之言的學者都可以成爲一‘子’,而這一‘子’,也就是一‘家’的代表。”“一子就是一家,其實是以子爲家的代表。”(載《文史哲》2004年第4期)《古代中西方的“學派”觀念比較》說:“‘子’是‘家’的代表(‘家’又或稱‘氏’),舉一‘子’可以賅括一‘家’。”(載《中國哲學史》2007年第4期)
②顧藎函:《國學研究》,上海:世界書局,1931年,第2頁。
③此據高誘注本。高誘曰:“舊本無此十一字,孫雲:李善注《文選》、賈誼《過秦論》、陸士衡《豪士賦》序皆有,今據補。”
④懷特海:《科學與近代世界》,北京:商務印書局,1997年,第30、20頁。
⑤蘇輿:《春秋凡露義證·天地施》,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472頁。
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雜史類》。
⑦江瑔:《讀子卮言》卷二,1917年。
⑧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63頁。
⑨譚戒甫:《墨經分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頁。
⑩沈有鼎:《墨經的邏輯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23頁。
(11)《斯坦福哲學百科全書》“荀子”辭條說:荀子的別名是“思考專名”問題,後期墨家的私名也是在“區分專名與普遍詞項”。轉引自陳波《荀子的名稱理論:詮釋與比較》,載《社會科學戰綫》2008年第12期。
(12)羅素:《人類的知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87頁。
(13)轉引自[美]M.K.穆尼茨:《當代分析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171頁。
(14)羅素:《邏輯和知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49頁。
(15)所謂一家的構成數目是一子,可以即是季真一人,也可以如李先生說的季真所代表和賅括。即使季真有門人左右,也是隸屬附從于季真的,因爲他們都不是成一家之言者,故不能稱之爲一子。兩漢史家的一家爲一子也作此解。
(16)需要指出,家作爲指涉學者存在單位的專有概念,與成一家之言的家有不同的內涵意藴,兩者有區別。說成一家之言者都可以爲一家是正確的,但一家之言的家並不指涉對象的存在單位和身份角色,而是對對象的思想學術的價值評價,是思想價值概念而不是角色身份的概念。因此,它並不是區分家與子的界判,成一家之言者並不必然以家爲存在單位,也可以以子爲存在單位,家和子都可以是成一家之言者的角色身份。如說申子是成一家之言者也可以是成一家之言的子,子作爲有思想有學問者的美稱,不能成一家之言豈能爲子。所以,成一家之言者並不是說其角色身份就是家而不可以爲子。
(17)載褚伯秀:《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八十七,《道藏》本。
(18)林希逸:《南華真經口義》卷二十六,《道藏》本。
(19)羅勉道:《南華真經循本》卷二十四,《道藏》本。
(20)《列子·仲尼》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張湛注“無家”曰:“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傅斯年說:“獨行之士,此固人自爲說,不成有組織的社會者,如陳仲、史鰌等。”“個體思想家,此如太史儋之著五千言,並非有組織的學派。”《史料論略及其它》,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0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