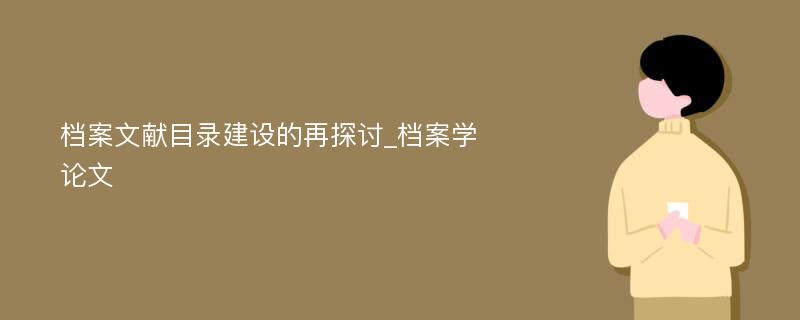
档案学文献目录建设再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目录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学文献目录对档案学研究有事半功倍的功能和效果,而我国目前的档案学文献目录建设则存在一些不足,亟需改进。
1 档案学文献目录的现状
档案界已经在档案学文献目录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有的档案学文献目录主要是以下这些:
1.1 许多刊物上载有档案学文献目录。主要表现是指档案期刊上的每一期目录和年终“总目录”。此外,还有一些索引性质的刊物上登载有一些档案学文献方面的目录,比如《(人大)报刊资料索引》、《全国报刊索引(哲社版)》和《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中的档案学文献目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档案学词典》以及《中国档案年鉴》等书也对一些档案学书籍做了简单的介绍和述评,1986年四川大学出版的《档案学论丛》也登载有雷荣广的《解放前档案、文书著作要目选编》。
1.2 出版了一批档案学文献目录书籍。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曾内部出版过《档案学论文著作目录》,可以查找1959年以前的主要论著的出处;档案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了由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资料室编的《档案学论著目录(1911—1983)》,又于1994年出版了由侯俊芳主编的《档案学论著目录(1984—1993)》;刘文杰先生于1987年出版了《中国档案学文书学要籍评述(1910—1986)》(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于1984年和1989年出版了由董秀芬主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49—1980)》和《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1981—1985)》;1991年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编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出版发行学论文索引(1949—1985)》;等等。
1.3 出现了载有档案学文献目录的光盘和网络数据库。清华大学主办、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电子杂志社编辑出版、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制作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数据库(英文简称CAJ-CD),是我国第一个以电子期刊方式按月连续出版的大型集成化学术期刊原版全文文献检索、咨询评价系统,从1996年12月开始正式发行,此前则有第1卷第1、2、3期共三期试刊光盘。该光盘数据库收录了以档案学核心期刊为主的一二十种档案杂志,我们可以通过“中国期刊网”来检索其目录。万方数据库也同样可以检索出一些档案学文献。
中国人民大学书刊资料中心编选了《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成为国内最有权威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专题资料库,从1997年开始,按季度汇集100多个专题全文于一张光盘内,可以按专题类别提供服务,[2] 从其网络中也可以检索档案学文献。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制作了光盘《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数据库》,收录了1992—1999年间的7万多条论文目录。深圳南山图书馆网站上建有“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书目数据库”,收录了档案学科的一部分文献。
值得一提的是,超星图书馆收进了一批档案学著作,不仅可以检索出目录,而且还可以全文阅读。一些杂志还把刊物的目录在网络上公布了,甚至公布了一些文章的内容。这些目录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对档案学文献的检索与统计。除了以上的文章目录外,还可以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网站检索档案专业的书目。
2 现有档案学文献目录的不足及改进
综观档案学现有的目录,经过无数人辛苦的努力,已经是硕果累累。最为显著的是,我们已经可以检索从1911年到现在的大部分文章,早期的可以借助《档案学论著目录》等目录性书籍,后期的可以从中国期刊网、维普资讯和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中查找,档案专业的书籍则可以借助国家图书馆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检索系统查找。但是,我们发现这种状况存在着种种不足,下面试针对这些不足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以期档案学文献目录建设得更加完美。
2.1 目录分散,应有一个完整的系统。通过上述简介,可以发现无论是论文还是书籍,这些文献的目录都是分散的。我们要检索出任何想要的材料,就必须经过不断的查找。所以,有必要建设一个档案学文献系统,把档案界的科研成果尽量地收录进去。
以前,曾经有人呼吁建设档案科研网,[3] 时过境迁,这种呼声已经淹没于历史的浪潮中了。后来又有人提出建立“中国档案系统文献信息资源中心”的构想,[4] 但也迟迟不见学界的回应。而由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国家档案局技术部共同开发的“全国档案报刊文献及科技成果信息检索系统”虽然已于2002年初对外开展查找服务,但其使用效果如何,档案界有多少人去用这个系统尚不得而知。至少有相当数量的档案研究人员是不知道有这个系统的。另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也对外开展资料的查找和文章的提供,不过费用比较高,一般的人往往望而却步。因此,有必要建设全国性质的档案学文献目录系统。
这个系统可由国家档案局、中国档案学会或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牵头组织其成员包括各级档案(馆)、档案学会和高校档案专业院系,还可以与图书馆界、情报界合作,共同做好这项重要的工作,建立起档案学文献目录的数据库,及时、全面地收录包括把档案专业报刊、书籍以外的档案学文献并形成其目录体系,建议档案界借鉴图书馆界的呈缴本制度,建立起报送制度,并纳入国家档案事业统计的范畴,要求广大的档案工作者特别是档案报刊杂志社及时地向有关部门与负责人报送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等科研成果,并运用互联网进行公布。
2.2 目录仅收录了论文和书籍,应吸纳各种档案学文献。当今的及其文本类信息资源包括图书、期刊、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专利文献、研究报告、政府出版物、标准文献、产品资料和文书档案10类。[5] 这些文本文献中都有许多档案学方面的内容,不容忽视。特别是学位论文和研究报告,尤其需要加以重视。
学位论文是1977年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产生的,是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学生为获取学位,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科学研究、科学试验成果的书面报告,是评审学位申请人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学位授予的主要技术文档。这些“灰色文献”是围绕某一学科的重点或前沿问题进行创造性研究和探讨、并加以总结的产物。学位论文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开拓性,其内容新颖、专业性强、信息量大、情报价值高,是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科技文献。但是,学位论文却有其封闭的特性,印量有限,交流范围狭小,获取困难,因而利用率不高。所以要在收藏完整的基础上,加强学位论文的价值宣传,并建立良好的服务系统。[6] 档案学学位论文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截止到目前,我国已有6所高校可以授予档案学博士学位了,有20多所高校能授予档案学硕士学位,授予档案学学士学位的高校则有30所。虽然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需要加强,但硕士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却值得关注。因此,我们要对档案学硕、博学位论文予以重视,将其纳入视野,作为重要的学术资源来对待。
随着学术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加强,学术界有了课题和项目的倾向,科学研究计量的深化更促使课题和项目的申报和争取日益火热。档案界也不例外。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课题,还是各个省级的项目,竞争都很激烈。虽然不是显学,但是我们这个学科也能或多或少地分到一杯羹,笔者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上的资料了解到,2006年以前的档案类项目总共28项,[7] 加上国家档案局以及诸多的省厅级方面的课题,应该是不少的。这些项目都是值得关注的。进行项目研究,最后都会形成有研究报告甚至出版(发表)论著或其他形式的效果。而目前我们对众多已结题的项目却知之不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可以公布或公开的成果没有及时公布或公开。为了把握科研信息,了解学科前沿,有必要对科研报告等不同形式的科研成果进行著录,以期学界共享。
2.3 目录类别单一,需要多样化建设。目录按其揭示文献的程度可分为:题录、提要目录、文摘三大类,题录是揭示文献题名、著者、出版情况的目录,是一种简明的文献报道形式,常用于报道单篇文献;而提要目录,又称解题目录,是对每一文献撰写有内容提要的目录;文摘则是以简明扼要的文字摘述文献的主要内容和原始数据,向读者报道最新研究成果,传递文献信息,为读者提供决定文献取舍依据的一种检索工具。我们前面所说的目录形式多是题录性质的,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一般的题录信息,我们还要编辑出版发行更深层次的目录,要向提要目录与文摘方面前进,更要继续深入,建设许许多多的带有工具性、资料性、评述性的档案学文献目录。
苏州大学的张关雄老师发表过《外国档案管理著作(1981—1995年)述评》(《档案学研究》2001年第1期)与《档案文献编纂学著作(1981—1999)述评》(《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2期)这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里,张老师不仅列举了近二十年里出版的外国档案管理和档案文献编纂学方面的著作,而且重点评价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可以说是述评外国档案管理和档案文献编纂学著作的创新型论文。王德俊先生也曾在《北京档案》2001年第2期上撰写短文《若干现代档案学著作简介》,介绍了几本重要的档案学著作。张煜明老师也曾对2004年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佳作做了评述[8]。
四川大学的刘文杰老师撰写了《中国档案学文书学要籍评述(1910—1986)》一书,该书不仅列举了二百六十多种著作(包括我国翻译出版的国外档案学著作),而且对所举各部著作,一一述评其成就得失;陈兆祦先生先后主编了《最新档案工作实务》、《中国档案管理精览》、《当代中国档案学文库》和《现代档案工作实务》等书,集档案学研究成果于一体,成为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他们几位的做法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我们可以对以往发表的文章或出版的书籍集中列举并评述一番,叙述其提要,并“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然后编辑公布,或者,把以往的书评集结成书出版,甚至把一些商榷性文章组成文集出版,总之,形式是多样的,我们不必拘泥于形式,关键是要把档案学文献目录建设好,使广大读者看了能受益匪浅。
目前,一些高校给档案学专业的研究生开了诸如“档案学名著选读(或导读)”、“档案学著作述评”等类课程,但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教材,教学质量往往会受影响,如果我们加强档案学文献目录的建设,尤其是内容提要层次甚至是提要加述评性质的目录建设,那么,不仅这类课程会锦上添花,而且对于其他读者和档案学研究来说,也是大有裨益的。吴慰慈先生主编的《图书馆学书目举要》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该书分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信息组织、文献目录学、图书文化学等几大部分,介绍了各个部分的相关书目。相邻学科的快速发展也促使我们要考虑《档案学书目举要》一类书籍的编纂和出版。
2.4 目录过于综合,应有专题性目录。现在的档案学文献越来越多,而人们需要的多是专题性的材料,所以应往这个方向发展,倡导专业化和科学性。
档案学文献虽然日益增多,但精品并不总是与之成正比的。研究发现,现在大部分档案学的文章原创性不强,没有多少吸引力,更有一些是不当作品,也许是几篇文章凑出来的,甚至是剽窃抄袭而来,学术严重失范。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学术规范,提高学术道德,强化学术意识,另一方面,要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
由专业研究人员从事档案学学术探究,不仅要对某个具体的方向做深入的研究,而且首先要了解该问题的前期成果,这就需要有专题的档案学文献目录。否则许多人都对某一问题进行探索,就会从零开始,再次检索以前的科研成果。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极大浪费。因此,有必要加强专题目录的建设。
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访谈和调查研究等形式确定档案学经典著作目录,使一些档案学名作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经典”是作为传统的核心在文本意义上的反映。西方档案学界确定荷兰《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在档案业作为“经典”的地位,这对整个欧美档案业的规范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全宗和来源原则等档案学基本理论甚至被冠以档案业“圣经”的称誉,可以想见其得到公认的程度。这些源自异域并在我国档案实践中长期受到尊重且已本土化的原则,不也应该成为我们档案传统中值得珍视的内容吗?[9] 因此,需要尽快明确档案学的经典著作。档案学术经典化将会有益于档案学的深化和大众化。
2.5 目录建设要以人为本。无论是档案工作的发展,还是档案学研究的前进,都离不开档案人的辛勤耕耘。说到底,人才是第一位的。所以档案学文献目录建设不仅需要一批具有奉献精神的人来从事,而且这个建设更要体现出对档案人的尊重和服务。
档案学人,无论多么有思想,有创造力,最后都会落到论著上来。哪怕主要是教书育人,他(她)的档案学思想也会经过众多弟子的再传播,最终变为“白纸黑字”。因此,档案学文献目录建设首先要对众多专家学者和学子予以关注,然后才是对其科研成果的著录。在对档案学论著进行描述时,我们要对档案学进行学术经典化判断,使档案学名著确定下来,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地去创造并描述另一种档案学成果,那就是对现有著名档案学者进行访谈,做档案学的口述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