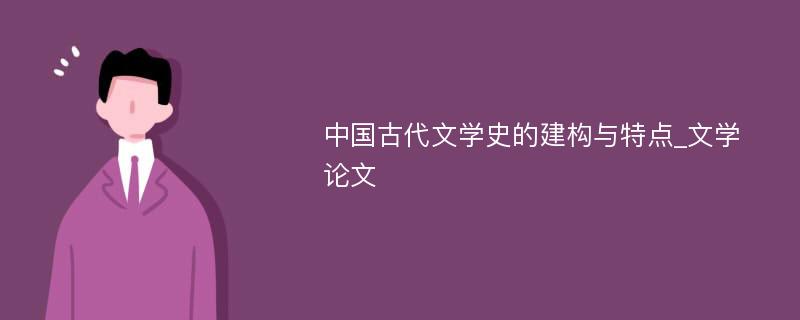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注:如朱德发、贾振勇:“文学史的总体构成不外两个大层面,一是文学发展本身即文学史的本体,一是编纂者对文学演变过程的发见即文学史本体的认识。”(《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陶东风:“如果要最简单地概括一下文学史的构成层面(维度),那么,可以说文学史是由文学史的本体与人们对这一本体的主观认识和评价构成的。”(《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注:如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就用较多的篇幅论述文学史原生态这一概念及其研究方法。)。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论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所谓构建,只是一个权宜使用的词,它的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指主观使用自己的认识系统来整合纷繁的客观事实,来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对于客观事物的描述系统。承认文学史是构建、阐释的成果,并非否定文学史的客观性,将其看成完全相对的东西。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文本书写的真正奥秘,存在于主观的文学史认识系统与客观的文学史本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以上的看法,只是对近年来文学史性质研究的一个总结,这种认识的达成,也许可以看作是学界对文学史科学的一次自觉。当然关于文学史性质的讨论,也深受史学界关于历史本体与史学之关系的研究的启发。
认识到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具有阐释与构建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扩大回顾文学史学的视野,文学史的回顾、构建与书写,与文学批评、文学鉴赏一样,是人类文学活动中的一种基本的实践形式。尽管对文学史全史的书写始于近现代之际(注: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历史。),成熟的文学史研究学科体系也是此后形成的,但是古代的作家、批评家等对文学史的建构,却是自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至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内,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成果是构成现代的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文本撰写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近代以来的文学史学建立,是引进西方的文学史学研究的方法及观念的结果,是对旧的文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革命。所以,尽管近代以来的文学史撰写本身经历了多次的体系与观念的嬗变,但是它们作为旧的文学史学的否定这一性质却一直没有很大的变化。也因此,在这一新的文学史研究的系统中,对传统文学史学的成就的评价总体上说是偏低的,甚至有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传统的文学史学的存在。所以,反思与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史研究、构建的成果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如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一书,对“传统文学史观之演变”与“近代文学史观之变迁”作了宏观式的鸟瞰,在这方面有开拓性的意义(注: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93页。)。郭英德等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古典文学研究史这一概念,也对各时期的文学史研究作了专门的介绍(注: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新近出版的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等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注: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也设《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一卷。但一般的看法,基本上是将其看成近现代文学史科学形成之前的一种前学科状态,认为它缺乏系统性与科学性。其实,传统的文学史学,不仅其实际的成果构成了现代的文学史研究与构建的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且作为一种传统的学术形式,自有其相对自足的独立的学术系统与学术规范。尤其是各时期文学史研究与同期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即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的一大特点,同时也反映出文学史构建的普遍性的规律。
二
传统文学史学得以发生的根本性原因,即在于人类回顾历史的天性和文学的继承发展规律。对于文学进行史的回顾与构建,是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学是与文学史同条共贯而生的。当然,作为一种学术,文学史学也与其它学术一样,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转变。
与任何意识及学术的渊源一样,文学史学的渊源也几乎是不可穷尽的。设想当先民以最原始的方法保存他们的祖先创造的神话与诗歌时,事实也是在对文学作一种史的回顾。“诗三百篇”的原始的编纂,虽然主要是依据歌诗的音乐性质与发生地域来分类,但编纂中不可能完全不发生诗歌史的意识,如商颂、周颂、鲁颂这三颂的分类,就明显地昭示了颂诗的发展阶段。所以关于《诗经》成书过程中诗史意识的问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从春秋战国到两汉的儒家诗学,虽然把主要精力敢在研究诗的文化性质和具体的诗歌作品的训释上,但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注意到对诗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的研究,并且开始了自觉的诗史构建,他们的成就构成了传统文学史学的第一批文本。《毛诗序》不仅讲到了诗的发生原理,还建立了从先王之世的充分体现诗道的教化功能的风、雅、颂到王道衰微时代的吟咏情性的变风、变雅这样一种诗史演变的历史逻辑,同时也体现了与尊尚先王先圣的历史观念联系在一起的重古轻今、重前轻后的文学史观,对后世的文学影响极为深远。郑玄依据《毛诗序》的上述诗史理论,具体地将《诗经》编为“诗谱”,其《诗谱序》则是第一篇系统的诗史著作,可以说是集儒家一派诗史研究之大成。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考察对象不限于《诗经》,而是延伸到更久远的诗歌发展历史,即虞、夏的时代。虽然他关于《诗经》前的诗史的推测,多付阙疑,无多成果,但其所表现出的力求把握诗歌发展的全史的意图,作为一种学术意识是很可贵的。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标志着我国古代诗史学的正式建立。汉儒文学史方面的成就的取得,与史学的发展分不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史学的自觉在文学史学方面的体现。汉代的史家,也为文学史的构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班固《汉书·艺文志》不仅体现了文学史料学的成果,也对诗、赋、小说家等文学门类的历史作出了一些论述。如其对古诗演变为辞赋的历史的勾勒,就是文学史方面的一个重要见解(注:班固《汉书·艺文志》:“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尽管他对战国以后诗道衰落的原因的解释不太准确。由此可见,汉代是我国古代文学史学的初建期,其文学史研究的最核心的观念与方法就是立足于政教的文学价值观的源流正变之学。这一史观对后世影响很大,其认为王泽衰而变风、变雅起,诗道微而辞赋起的观点,也差不多完全被后来的文学史构建者所接受,尤其是深为唐宋复古派的诗人所认同。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传统的文学史学正式确立的时期。如果说汉代的文学史学可分为经学家与史家两流,则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则可分为文论家与史家两流。两流的不同,主要体现于学术的分野与著撰的形式方面,至于基本的文学史观,则是比较统一的。这时期文学史学的进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一、“文”的范畴的完全确定,促成了文学史的全史观念的建立,并发生了全史回顾的视野。汉代的文学范畴不太清晰,比如“诗”原本是界限最分明的一种文体,可有时被统合于“乐”,有时又被统合于“经”,只有班固《汉书·艺文志》是诗赋合称,似乎突出了“文学”的类别概念,但又并不包括《诗经》。至于其它杂文,也都各自为界。所以,汉人没有一个将各种文体统一在一起的“文学”概念,自然也没有一个统一各种文体的“文学史”概念。但汉末以来,文学的整体渐显清晰。其最突出的标志,即是曹丕《典论·论文》首次提出“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注:曹丕《典论·论文》:“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据《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二)。),第一次触及到文学的本体与整体,文学中部分与全体的关系,是极了不起的理论创造。自此之后,对于文学的本体的体验、论证与寻求,成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一种自觉意识。而创作与批评中文体意识的空前强化,则是此期的另一重要特点。所有的魏晋文论,无不显示出对文的本与末的同时的重视。可见“本”与“末”这对相依相存的范畴,实为魏晋文学思想的大纲。同时也是此期文学史构建的大纲。二、文学的发展问题成了重要的课题。汉儒也意识到诗歌的演变问题,但完全从政治教化影响于诗歌这一角度来讲。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发展史观,一方面对汉儒的上述研究方法作了扬弃的继承,扩大了对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它对每一时代的文学与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都作了系统的论述,并总结出文学史发展的外部规律,“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更重要的是,魏晋南北朝文论家很深入地探讨了文学史发展的内部规律,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和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为主流的文学史家的刘勰、钟嵘、沈约、萧统等人,都论述过文学在艺术上是不断发展的。如刘勰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文心雕龙·通变》),沈约论定“自汉至魏,四百余年,文人才子,文体三变”(《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认为“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萧统也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选序》)。文学摆脱了儒家崇尚先王之道思想下的是古非今的文学观,揭示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文学史研究的体系和方法趋于成熟,文学史在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中同时获得了自己的位置。以史家文论来看,由范晔与沈约分别创立的文苑传和文学传论体例,为后代南北朝及初唐史家所继承,实为托体于全史中的文学专史。文论家不仅研究文学的整个发展历史,而且在研究各种文体与文学因素时,也极其显著地贯穿沿波讨源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的繁荣,是与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取得分不开的。某种意义上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学代表了传统文学史的最高峰,至少就其学术形式而言是这样。
汉儒的文学史研究,与同时代的文学创作关系不大。虽然依附于经史之学,作为文学研究的独立性不够,但从形式来看,倒很接近我们今天的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史研究,完全是由同时代的文学发展促成的,一些重要的史观和对文学史的重要判断,也都与当时的文学发展密切联系着,如钟、刘对文学史的一些看法,就深受齐梁之际文学风气的影响,即有体现时风的一面,又有力图通过正确的文学史系统的建立来指导当代的文学道路的一面,这是传统文学史学的深化,也确立了传统文学史学的基本意趣。但是,由于此期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的独立性程度较大,钟、刘及史家文论家,在建构文学史时,作为批评家与史家的历史客观的意识也比较强,所以此期的文学史学,相对于后世的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史学来说,反而体现了更多客观、科学的学术研究意识,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的意趣更为接近。这种看似超前的学术现象,其实与我国学术与文学发展的大趋向有关。我国古代的学术的最早形成,为西周王官之学。春秋战国时期,王官之学衰微,诸子之学随着士阶层的兴起而盛行。至汉代,诸子之学转衰而经学兴起,魏晋则由经学与子学的一部分转为玄学。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子学、史学一直还是重要的学术形式,并且融合玄佛之理,思想方法更为精致。由此可见,唐代以前的文化中,学术传统远强于文学传统,事实上,唐以前的学者与思想家的人数与成就,都要远远超过文学家。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兴盛,固有其它多方面的原因,但从大背景来看,正是因为此期学术传统之强大。所以此期的文学研究,也比后来的唐宋时期具有更自觉的文学史学的学术意识。
三
唐代的文学史学的特点,是文学史的建构与当代的文学发展主题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家尤其是文学潮流的代表人物成了文学史的主要构建者,从此以后,一直到近代客观研究的文学史学兴起之前,这一派事实上成了传统文学史学的主流。
唐初高祖、太宗年间,出于资治、显示王统及成一代之学术等多种目的,撰修《周书》、《隋书》、《晋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等八部史书,从史学上看,是继承南北朝史而集其成,因此也完全沿承了南北朝史书以文苑传、文学传论来描述文学史的模式,从这一点可以说是南北朝文学史学之余波。而且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八史”也多是继承前代史家之说,在描写具体的文学史时,也基本上是采取接着前人所描写的时段继续说下去的作法,《隋书·文学传序》就是这样做的:
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是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
凡是前人已经沦定,不再重叙,即所谓“前哲论之详矣”,主要的精力放在前史修成之后的南北朝后期的文学史之叙述。这是唐初八史的一种断制,正反映了他们重视历史系统的完整性与客观性的史家的学术观念,与后来的文学家的文学史叙述是不同的。但是,在建构文学史时,八部史书比较一致地显示出研究前代文学以为新兴的唐王朝文学发展指示道路的意趣,从这这个角度来看,又是开启上述的文学史建构与当代文学主题紧密结合的主流倾向。其中对齐梁以来绮靡文风的批评、南北文风的不同及融合之可能性的探讨、文学史与治运之间的规律性的关系的寻究,则为八史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理论兴趣之所在。初唐八史以后所修的正史,虽然也沿承文苑传及文学传论、文学传序的体制,但已经不能做到南北朝至唐初那样自成一派,其在文学批评史的地位差不多是无足轻重,其对文学发展的实际影响更是微乎其微。正史文论的兴衰,实为传统文学史学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单纯从学术的形式来看,唐人在文学史学方面的学术意识,反而不如南北朝史家、文论家之自觉,不仅唐初史家文学史学后来无继,就是文论家一派的文学史学,也再没有出现钟、刘那样的大家巨著。唐末有张为的《诗人主客图》,算是一种诗史著作,但也只局限于对中晚唐一段的几个流派的勾勒。所以,衡之以今天的文学史学的学术标准,说唐代是文学史学的衰微期也无不可。非但唐代,逮至宋、元,也没有与钟、刘意趣相近、成就相媲的文学史家的出现。只有严羽《沧浪诗话》对诗史作了一次比较完整的叙述,但严氏之诗史建构,完全是从当代的诗歌创作的问题意识出发,体现的仍然是作家建构文学史的意趣,只不过是他稍微增强了理论建树与历史研究的意识而已,所以其作为文学史学的客观性、系统性,都无法与钟、刘相比。只有到了明清时代,这种情况才有改变,出现了学术研究的目的性很明确的一类文学史著作,尤以胡应麟、许学夷、胡震亨等人对于诗史的研究为代表,代表了传统文学史学的学科独立的趋势。
但是,从唐宋时代的文学史建构的主流即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密切结合、作家建构文学史这一方面来看,唐宋时代在文学史的建构、具体的文学现象、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与作品的研究,其实际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以前阶段。可以这么说,唐宋时代,一个作家在艺术追求过程中的自觉性的标志,就是从不太自觉地继承发展到自觉地站在文学史高度对自身在艺术上的继承与发展的方向与方式做出明确的判断,从而建立了作家个人的一种文学史观。而其最终文学成就的高下,也取决于其文学史之是非高下及对文学史把握的深度与广度如何。唐人主流的诗歌史构建,是与唐代诗歌发展的进程一致的。初唐魏征等史家,最关注的是南北朝后期的文学风气,其主要的论点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书·文学传序》),认为南北两派的文风互有长短,如能“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可见他们最深刻掌握到的,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一段文学史。此外的先秦汉魏晋的文学史,不过是沿前人之成说而已。到了陈子昂,随着复古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的深入,显示出超越齐梁,直接汉魏的继承观点,而其对诗史的有机的建构,也上溯到汉魏诗史中去。其《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对诗史做出一个重要的判断: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
通常理解这一段话,都只是将它作为一种创作主张来看,认为陈氏提倡汉魏,否定齐梁。这自然是对的,但是这段话同时也是陈氏的一个诗史建构。实际上他的重要观点是认为汉魏风骨之衰落,或者文章之道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根据这一观点,他将汉魏以来的诗史分为汉魏、晋宋、齐梁三大阶段。这种文章之道或诗道逐渐衰微的观点,对后来诗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构成了唐代复古派的一种基本史观。李白《古风》其一和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也是采取这样的认识方法的,尤其是自居易,以“六义”为诗歌之道,将《诗经》以后的整个诗史分成“六义始刓”(周衰秦兴)“六义始缺”(骚辞)、“六义浸微”(晋宋)、“六义尽去”(齐梁),对陈子昂的诗道衰微说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李白等盛唐诗人,对陈子昂诗史建构的一个发展,就是由汉魏经典进一步上溯到风雅之祖,这正是由初唐到盛唐复古的文学创作实践的深化。另一方面,从近体诗歌的发展历史出发,唐人也客观地接近建构从建安到初唐诗体及诗歌艺术的发展。《新唐书·宋之问传》的这段论述,实际上正是概括了唐代注重近体这一派的诗史建构:
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杜甫的诗史建构,则可以说是集上述两派之大成。与陈、李一派宗旨相近,但具体的方法与观点有很大的不同的,是杜甫通过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建构的文学史观,杜甫的重要论诗作品,如《偶题》、《戏为论诗六绝句》、《解闷五首》等作品,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杜甫的诗史体系。他的“别裁伪体亲风雅”的主张,与李白、白居易一致,但是在具体的史观和继承的方式上,则是风雅为源,汉魏、齐梁并重。所以与他的创作集大成相一致,他的诗史建构也是唐人中最近全面客观的,值得我们作专门的研究。在散文方面,唐人对于散文史的建构,也完全是与古文实践的发展相联系。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些重要的文学家在文学史建构方面的成就,其实一般作家,只要在艺术上有自觉的继承中求发展的意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文学史的一番建构。
四
宋人研究文学史的学术风气,比唐代有很大的提高,其成就主要表现为诗话一体的出现,诗话虽不是系统的文学史著作,并且其撰著的主要动机仍然是供创作者借鉴。但体制灵活,理论、批评、谈艺、考史俱备,实为集中宋代文学史研究成果的渊薮,值得我们很好地去整理。除此之外,宋人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及先秦重要典籍的研究,也更多地体现向文学还原的特点。所以宋代之诗经学、楚辞学,也比前更多地具备文学史学的特性。如郑樵《通志》在论《诗经》艺术的性质时,提出“诗在声不辞”的重要观点,实为前期诗史研究的重要发现。朱熹的《诗集传》,也在《诗经》文学史真相的还原上做出突出的贡献。宋人对唐人诗文集的整理、选编、注释,也都是属于客观的文学史研究范畴的成果。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在乐府诗史将近终结的时代,为乐府诗作了一个总的整理,不仅是一个文学总集,同时也是一部乐府专史。
宋人在文学实践方面的面向文学的意识,比唐人更为自觉。宋人处于古代文学的高峰之后,正统文学诗、文、辞赋都已经完成艺术理想的圆满实现,中国文学史的主体部分发展图景已经呈现出来,所以宋人不能不在面向文学史的前提下展开他们自己的文学发展课题(注:参见拙文《论黄庭坚诗学实践的基本课题》,《漳州师院学报》1997年第1期。)。另一方面,宋代的学术风气很浓厚,宋代的文学家,也比前代文学家更多一份学者的气质与知识结构,所以宋代的文学创作中“学”的意识很突出,不太说“作者”而喜欢说“学者”。而宋学的整体特点是尊古中开新,崇尚传统,重视渊承,所以整体上看,宋代作家的文学史修养,较之唐人,实为倍蓰。所以,宋代文学史学的主流,仍然是作家建构的文学史。以宋诗代表作家黄庭坚而论,他有极为自觉的诗歌史意识,其个人的诗歌创作道路,也是一个不断地向诗史回顾的过程。在其诗歌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中唐至北宋的“古文诗派”、中晚唐近体诗、杜诗、魏晋诗歌,都有过很深入的汲取,不仅如此,他的整个诗歌艺术渊源还扩大到《诗经》与屈宋辞赋,他是很自觉地走着杜甫的集大成的艺术道路,只不过比杜甫更加强调个人风格的建立。因此宋人说他是“荟萃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注: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历代诗话》本。),其所体现的诗歌史方面的深厚的造诣,至少在当时,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诗史的建构也很能体现作家建构诗史的特点:
夫寒暑相推,庆荣而吊衰,其鸣皆若有谓,候虫是也。不得其平则声若雷霆,涧水是也。寂寞无声,以宫商考之则动而中律,金石丝竹是也。维金石丝竹之声,国风雅颂之言似之;涧水之声,楚人之言似之;至于候虫之声,则末世诗人之言似之。(注:黄庭坚《胡宗元诗集序》,明万历刊本《重刻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二。)
他将诗史分为三种类型:国风雅颂、楚辞、后世诗人之言。这其中仍然体现唐人的诗道渐衰的诗史观,但又鲜明体现他自己提倡“情性为诗”、追求“兴寄高远”的美学理想。在论到诗歌经典时,他崇尚陶、杜,并说“建安数六七子,开元才两三人”(注:黄庭坚《再用前韵赠子勉四首》,《山谷内集》卷十六。),并认为近百年诗虽非毫无建树,但不宜作为经典来学习(注:黄庭坚《与赵伯充》,《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十五。),开了后来严羽一派尊尚汉魏盛唐诗歌的先声,对后来的诗史建构影响十分深远。
正如唐人是中古诗史建构的奠基者,唐代诗史的建构也是奠定于宋人,历其后的元明清三代而臻于完成,纲目俱备。关于唐诗的研究历史,陈伯海先生的《唐诗学引论·学术史篇》已经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注:陈伯海《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这里着重从诗史建构与诗歌史发展的互动关系来考察。虽然我们现在将唐代诗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认为唐诗史的完整建构始于唐代之后。但对于唐人来讲,他们不仅在建构风、骚及中古的诗史,同时也在不断地回顾本朝的诗史,杜甫《论诗六绝句》对王、杨、卢、骆“当时体”的论定,就是他研究本朝诗的一个成果;李白的《古风》其一:“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曼。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虽是印象式地回顾了本朝诗史,但表达了“删述”的愿望,正是系统建构诗史的意图。传统文学史构建的最大特点就是辨别源流正变,标举诗道、文道,亦即李白诗句“宪章亦已沦”的“宪章”。唐诗史建构中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盛唐诗歌作为唐诗发展高峰,李、杜、王、孟等人作为唐诗最高典范的确定。它的第一层学术积累,实是中晚唐诗人学习盛唐诗的结果,大历十才子之学王、孟,确立了王、孟之诗史地位,而李、杜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则是通过韩愈、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大家名家对他们的继承与发展而呈现出来的。唐末五代诗境趋于浅狭,诗道偏颇,在诗歌的继承方面又重新回到杜甫曾经批评过的“递相祖述”的局面,虽然这时唐代诗史已经完成,但从作家文学史的建构来看,对唐诗史反而失去了整体性的把握,我们看刘昫《旧唐书·文苑传序》这样一个正式的描述文学史的文本,却没将唐诗和唐代文学的整体轮廓呈现出来(注:《旧唐书·文苑传序》在论唐代文学时说:“爱及我朝,挺生贤俊,文皇帝解戎衣而开学校,饰贲帛而礼儒生,门罗吐凤之才,人擅握蛇之价。靡不发言为论,下笔成文,足以纬俗经邦,岂止雕章缛句。韵谐金奏,词炳丹青,故贞观之风,同乎三代。高宗、天后,尤重详延,天子赋横汾之诗,臣下继柏梁之奏,巍巍济济,辉烁古今。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蕡之对策,王维、杜甫之雕虫,并非肄业使然,自是天机秀绝。”),就可知这时对唐诗史认识的肤浅。
从诗歌史的建构来看,宋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也是宋人建构唐代诗史的过程。宋初的一个阶段,所关注的主要是中晚唐的一段诗史,其晚唐体取法最近,基本上是五代诗风之延续,白体与西昆体,分别以白居易与李商隐为取法对象,开始更主动地寻找唐诗的典范,对唐末五代“递相祖述”的诗风有所突破,其中像王禹偶等诗人,对盛唐杜甫也已有所取法。庆历诗坛的主流派,一方面明确地将唐末五代的诗歌流弊作为否定对象,开了宋代主流诗学轻视晚唐的先声;另一方面则取法韩孟诗派而力求上溯李杜,初步形成宋诗的风格,而其对唐诗史的把握也趋于全面。元丰、元祐诗坛的各大家,在诗学的取法上开始向整个诗史展开,其对唐诗的继承也是在确立典范的同时,兼顾各家各派。从上面对唐代和宋代诗人学习唐诗、建构唐诗史的论述可以看到,唐诗经典的论定、唐诗各发展阶段特征的认识,是中晚唐至北宋诗史的产物。我们通常认为唐诗分期的理论是严羽最初奠定的,从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说,也许可以这样说。但唐诗的分期,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成果,严羽的贡献在于他汲取他的时代唐诗学的普遍知识,对唐诗史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论定。以后南宋、金、元、明都以自己时代学习唐诗的经验深化了对唐诗发展史的认识,至高棅《唐诗品汇》最后确定四唐诗的分期理论。可见,唐诗史的完整的建构,是中晚唐迄宋、元、明、清数代诗家的成果。唐诗研究的成就之所以超过后来的各代诗研究,重要的原因就是古人已经对其发展史作出准确的分期。当然,宋、元、明、清各代的唐诗研究成就,远远不止于这一个成果,在四唐诗分期的框架下,唐诗史的研究日趋完备,最终出现《诗薮》、《唐音癸签》、《诗源辨体》等重要的诗史著作,为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是唐诗史,宋诗及元、明诗史,也都在它们发生以后的时代得到构建。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文学史,除了小说、戏曲的历史,古人的研究比较薄弱外,正统文学的诗词、骈散文、辞赋,古人的研究都很丰富。虽然我们所采用的学术形式为古人所无,思想方法也为古人所没有,但是我们对文学史的基本建构来自传统文学史学,无数的学术观点,也是承自古人的。像唐诗分初盛中晚四期,在今天似乎已经是一种常识,但这一常识却是古人长期探索的结果,它的合理性在于不是简单地从历史分期为文学史(分期)借来一个外壳,而是真正能够展示唐代诗歌发展趋势的科学的分期。
通过对传统文学史学的回顾,我们发现,文学史的呈现与建构,从根本上讲,是文学发展的结果。前一代文学历史,通过后一代的文学的发展而自然地建构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代的文学的发展,不仅在创造自己时代的文学史(就文学史的客观的一面而说),同时也在书写前代的文学史,这种书写有时就是文学史的本身,并不依赖于作为学术形态的文学史文本。当然,文学史的建构与呈现不只是逐代完成的,事实上,一代的文学,不仅在书写前一代的文学史,而且也在对其前的所有的时代的文学史进行继续建构,有时还对前代人的文学史建构作出颠覆性的重构。所以,文学史在文学的发展中,不断地被书写、回顾、建构乃至重构。文学创作在不断地发展,文学史也在不断地建构,一次次地重新被阐释、被挖掘,文学也通过这种建构,逐渐地接近文学发展的规律,建立正确的史观,并且对文学史获得比较客观的认识。所以,建构文学史的最大的、最有效的动力,恐怕是来自文学自身的发展。所以文学史的建构与文学自身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们研究传统文学史学时最应关注的。
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比较多地具备了客观的、科学的性质,并且与现实的文学创作分流。但是,仍然受着上述的规律的制约,现代以来的文学史建构,是与现代文学的发展相联系的,受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刻影响。支配着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的文学史观,就是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成果。正是因为现代新文学的出现,我们为一切的古代文学画上了终结号。更引人深思的是,由此而带来一个重要的、事实上完全是经验性与非学术性的史观,认为古典形式的文学发展上的生命力,终止于现代文学发生之顷。这个古代文学史的终止符和与之相应的这种史观,影响了我们对整个古典文学史的重新建构。值得深思的是,这次建构,与历史上无数次的建构不同,不是在古代文学自身的有机生长的历史中构建,而是在与古典文学之间虽不无渊源但究竟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的现代文学中构建。与此相关,这一次的构建与历史上无数次构建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将整个现代文学之前的文学史,作为一种完全过去了的,即“古代”的文学史来构建。由此而引起了文学史观的革命,一种摆脱古代文学本身的古代文学史的构建。在其赢得比古人更为系统、客观的同时,是不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比古人更远离了古代文学史的真相?唯其如此,回顾传统的文学史学是重要的。
张晶评议
钱志熙教授的发言《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对文学史的构建及其特点做了颇为系统的阐述,既有很强的学理性,又有具体的历史脉络的勾勒。这个发言,无疑是有明显的文学史学的价值的。
文学史的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历数古代文学界的学术会议,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文学史观等问题,屡屡成为会议的重心。不仅是一般的议论,而且不少学者积极实践,创造出了一批文学史的成果,成为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转折的鲜明标志。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场文学史的论争,尽管在文学史观念上使问题更为深入,也更为明朗化,但说实话并没有多少实在的推进。倒是近年来的文学史学的提出,使文学史理论的研究不仅延续,而且进一步学理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志熙先生的这篇文章,当然属于文学史学的范畴。其中关于文学史学的有关命题的提出,有关规律的阐释,如认为文学史具有“构建”的性质,并将以往关于文学史观念中“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置于一个新的认识框架中,且能上升到颇为哲学化的高度,指出“文学史研究、文学史文本书写的真正奥秘,存在于主观的文学史认识系统与客观的文学史本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之中”。应该说,从学理性上而言,志熙先生的这篇文章对文学史学的建设更具有了“形而上”的高度。不仅是停留在学理构建上,志熙先生还将文学史的建构活动做了历史性的描述和定位。这对于文学史学的进一步成熟,都是有益的贡献。
从旁看来,使我感到不够满足之处在于:志熙先生将文学史观中倾向于主观还是倾向于客观的论争,纳入到辩证关系之中,这当然体现了作者的更高一层、也更公允的学术思维;但是“辩证”不宜停留在一般的思辨层面,而应从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中提炼出一些具体的方式。也就是“构建”的内容应该得到进一步的阐明。这当然不是仅仅在思辨的圆圈中可以完成的,但却是文学史学要解决的问题。这样,文学史学的提出和建立,方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吴承学评议
读之甚快意,有登高望远,开拓心胸之感也。
论文恢宏大气,识见卓荦。文中大笔勾勒出传统文学史学渊源流变之线索,于各期文学史学特点及其演变之把握亦多独到之见。本文内容易与一般的批评史研究重复,然作者善于别开生面,在研究视角与观念上出新。比如从各时代文学史家身份之变化,看到文学史学术的演变;从文学史研究与同期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传统文学史学的特色,并提出颇多创见。本文不惟有开拓文学批评史研究之功,并兼有追溯现代文学史学基础之意也。
然“体大”者不易“虑周”,文中有些问题点到为止,尚待深入。如对于宋代以后各时期的文学史学虽略有涉及,而语焉不详。当然篇幅所限,难以“求全责备”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