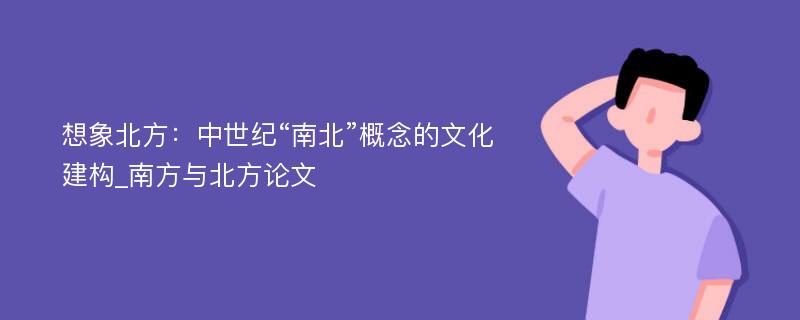
想象北方:中古时代“南/北”观念的文化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观念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化想象中,“南方”与“北方”的形象已经相当固定了:北方通常被视为粗犷、豪放、严峻,南方则温柔、旖旎、充满感性。这两组特质不难和传统所规定的性别特征联系起来,把南北之别等同于男女之别。本文旨在说明这些形象并非“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是在南北朝时期开始形成的文化建构。这一建构过程到6世纪已基本成熟,在南北统一的隋唐时代最后定型。
在进入讨论之前,有几点内容需要澄清。首先要指出,中国文化想象中的“北方”与“南方”没有一个固定、明确的地理界限,只是和实际的地理环境大致相当;就连这种“大致相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体现。换句话说,“南方”与“北方”是内涵模糊的文化概念,引起的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联想。如果我们一定要给“南方”划出疆域,长江也许可以算是某种界线,因此“南方”又称江南,泛指长江以南的地区。但是,长江以南的地区相当广大,而在关于“南方”或“江南”的文化想象中,岭南或者蜀地扮演的角色都不能说十分突出。因此,我们对“江南”的文化幻想,可以说是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的。这里重要的是历史感:也就是说,意识到“南/北”的概念随着华夏帝国实际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对一个现代中国人来说,东三省当然包括在“北方”之内,但在5世纪,“北方”主要指北魏政权控制下的地区。
因为长江在芜湖与南京之间呈南北流向,又出现了“江东”的说法,这一说法在三国时期扩大为对整个孙吴政权统治下地区的称呼。自东晋以来,“江左”一词也很常用,不过,在4世纪到6世纪之间,“江左”不见于诗,只见于文,诗歌通常不取“江左”而取“江南”。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江南”一词是在梁代诗歌中才开始频频出现的,而梁朝正是浪漫化的“南方”形象逐渐成型之时。
其次要澄清“南”与“北”这两个概念在南北朝时期的使用范围。南北对峙三百年间,南北之间的边界常常发生变动。但无论实际地理疆域如何,这种政治局面造成了强烈的“南/北”意识。在这一时期,北人/北士、南人/南士的说法日益常见。当然我们必须注意这些说法的使用语境。在南方,“南人/南士”可以指相对于北方移民来说的南方本土人士。又如5世纪末江淹的《待罪江南思北归赋》,“江南”指福建,“北归”指回到都城建康。但与此同时,无可否认的,也出现了意义更广大的“南方”与“北方”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双重对立。在五六世纪,人们常常有意识地进行南北对比,这种比较在6世纪末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里得到集中体现。归根结底,南与北这两个概念是相对的,不仅相对于彼此而成立,而且其本身内涵也决定了它们的相对性。本文谈到的“南北”,是公元五六世纪作为对立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南北,它们取决于政治疆域而非地理疆域,并最终成为纯粹的文化概念,直至今天仍然操纵着我们的文化想象。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诗经》《楚辞》中已经存在着“南方话语”,但它和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南方话语”具有重要的不同:早期文化语境中的“南方”不是相对于“北方”存在的,而是相对于“中原”存在的。换句话说,在六朝以前,南方从来都没有成为汉文化的中心。“南方”与“北方”作为文化概念的构筑始于南北朝时期。只有在这时,特别是到了5世纪以后,尽管它们各以正统自居,相互蔑视与诋毁,南方与北方才在政治与文化上首次处于对等的地位。
如前所述,本文重点在于探讨南方与北方的形象的生成,集中于南朝边塞诗和所谓北朝乐府对“北方”文化形象的塑造。在边塞诗里,“边塞”专指中国的极北或西北,既和南北朝时期南北之间的实际地理边界毫无关系,也和南朝的南疆或西南边陲全不相干。早期边塞诗都是由从未到过边塞的南方诗人创作的,它是文学体裁内在发展的结果,也体现了南朝诗人建构“文化他者”的企图。至于“北朝乐府”,一般来说被认为代表了强健豪迈的北方特色,但它们绝大多数都是由梁朝乐师演奏和保存下来的。这些乐府诗与其说代表了北方特色,还不如说代表了南方人眼中的北方、南方人出于一己动机所着力塑造的北方。无论南朝边塞诗还是这些乐府诗,都是对于南北形象的生成起到关键作用的文本。但在讨论这些文本之前,且让我们先探讨一下隋唐作为北人王朝在保存、传播、评价南北朝文学过程中扮演的中介角色。
征服者的文学观
隋唐都是北人王朝,这对我们理解六朝文学意义重大。隋唐官方话语对南朝宫廷文学特别是梁朝宫体诗批评十分严厉,这样的批评态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些统计数字,我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印象。
初唐史官为《南史·文学传》所写的前言,长度仅仅是《北史·文苑传》前言的十分之一,这相当有力地说明北方文学被赋予更加重要的地位。然而,从现存的文学作品数量看来,这一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现存北方诗文数量极少,除去《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魏书》之外,如果不是有庾信、王褒、颜之推以及其他一些由南入北的作家留下的作品,北方文学作品数量还要更少。在现存作品中,邢劭、温子升、魏收这所谓的“北地三才”全都生活于6世纪,而且深受梁朝宫廷文学的影响:邢劭服膺沈约,魏收则渴慕任昉。①温子升现存诗歌11首(包括残篇在内);邢劭9首;魏收16首。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不是多产作家:温子升有文集39卷,邢劭31卷,魏收68卷。②
这些数字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初唐编写的史籍对南北朝文学的评判,与初唐类书如《艺文类聚》《初学记》(二者都是唐前文学的重要资料来源)的编辑方针十分不同,“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萧纲的作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唐代官方话语对萧纲的宫体作品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是《艺文类聚》中却收录了萧纲的大量诗文。萧纲存留到今天的诗作约250首,这对于作品保留下来极少的唐前作家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相比之下,北方作家创作了大量作品,只有少量存留下来,而就连这一小部分还有赖于魏收的《魏书》——魏收本人善属文,这或者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喜欢在史书中收录文学作品。但史传中收录的作品多以章表文件为主,而且史传在收录个人作品时,赋的比例又远远大于诗歌的比例,这就容易给后代学者造成一种错误印象,认为北朝文学多实用性,而且作赋多于做诗,这其实是没有考虑到文学资料来源的性质而得出的偏颇结论。总之,我们发现初唐类书对北方文学表示出强烈的偏见。
8世纪的刘餗在《隋唐嘉话》中记载说,徐陵使北,魏收托他把自己的文集带到南方去。徐陵在南归途中把魏收的文集投入长江。从者问他何故如此,他回答:“吾为魏公藏拙。”③这则故事不知可靠性如何,但它很可以拿来作为北方文学命运的象征:连一个流传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就被埋没了,后人根本无法对其总体情况作出判断。张彝(461—519)曾向北魏皇帝献上七卷他做地方官时“采风”收集到的诗歌,现在全部佚失,只有献诗上表还存留下来(保存在《魏书》卷64的张彝本传里)。然而,在书写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些佚书考虑在内,也必须考虑文学作品的资料来源。
主编《艺文类聚》的欧阳询(557—641)是南人,但《艺文类聚》的编者包括不少北人,如裴矩、赵弘智、令狐德棻皆是,令狐德棻还是太宗信任的史臣之一。因此,《艺文类聚》对北方作品的排斥不能说是南人的合谋,只能说显示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口味压倒了意识形态的判断。初唐诗风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是对梁陈宫廷诗风的延续。
但无论具体实践如何,初唐史臣对南朝文学作出的评判对“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形象建构具有关键作用。《隋书·文学传》序言和《北史·文苑传》序言中表示出来的意见,为后人对南北文学的判断奠定了基调: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绮”与“刚”很容易被纳入传统的性别分类:被征服的南方柔靡而女性化,征服者的北方孔武刚健。史臣理想中的诗是南北的结合:
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结合文与质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但放在初唐语境中来看,这一想象中的结合显然代表了统一帝国的新诗学。把南方等同于“文”、北方等同于“质”是较为特别的做法,但当我们把这种描述和一系列文本进行对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形比这种简单的二元结构所显示的要复杂得多。
想象北方:边塞诗的诞生
中国文学理论向来重视对实际经验的表现,但是,边塞诗的诞生和实际经验毫不相干。宇文所安在《盛唐诗》中谈到:“诗歌中的中亚主要是一个文学主题:和这一主题联系在一起的风格,构成了边塞风景的因素,诗人对这些因素应该做出的反应,都来自一个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创造这一传统的诗人们从来没有去过边塞。”④换句话说,边塞诗的始作俑者,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方诗人。
需要强调的是,边塞诗中的“边塞”有具体所指:中国的极北或者西北地区。⑤南疆从历史上来看征战不断,却从未成为边塞诗的主题。边塞诗可以追溯到鲍照,⑥但是到了梁朝才开始真正兴盛。在鲍照之前,虽然有一小部分关于征战的诗篇,边塞诗的传统并未建立,“边塞”也还没有等同于一个特别的地理区域。相比之下,鲍照的边塞诗主要描写极北边塞气候的严寒和战争的艰苦,也常常选择汉朝作为这些诗篇的时代背景,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代陈思王白马篇》即是。对鲍照来说,“边塞”不仅属于另一空间,也属于另一时间。
现代学者王文进在《南朝边塞诗新论》一书中把这一情形归结为南朝诗人对中原的留恋和恢复北地的愿望。⑦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边塞诗是对遥远浪漫的“异地”的构筑。对于南朝诗人来说,写作边塞诗的乐趣在于对北地苦寒富有想象力的铺张描写,对他们只在史籍中读到过的边远地名进行一一列举:这是典型的对“文化他者”的建构,而这种对于文化他者的建构反过来是加强自我文化身份的手段。在后文我们将看到,写作和欣赏南方乐府,体现了同样的身份建构欲望。
我们可以通过乐府《从军行》的写作历史来说明这一观点。最早的《从军行》仅存片段,系于公元3世纪的宫廷乐师左延年名下,首句为:“苦哉边地人。”西晋诗人陆机《从军行》的首句袭用了这一开头:
苦哉远征人,飘飘穷西河。南陟五岭巅,北戍长城阿。深谷邈无底,崇山郁嵯峨。奋臂攀乔木,振迹涉流沙。隆暑固已惨,凉风严且苛。夏条焦鲜藻,寒冰结冲波。胡马如云屯,越旗亦星罗。飞锋无绝影,鸣镝自相和。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苦哉远征人,抚心悲如何。
陆机对军旅生活的描述包括了南与北、夏与冬、山与水。这清楚表明,诗人目的在于囊括士兵经验的整体。
到了5世纪,颜延之和沈约分别写作《从军行》,和陆机一样以简笔勾勒南北征战。相比之下,吴均(469—520)的《从军行》显示了重要的区别:
男儿亦可怜,立功在北边。阵头横却月,马腹带连钱。怀戈发陇坻,乘冻至辽川。微诚君不爱,终自直如弦。
传统因素历历皆在:战马,武器,寒冷,富有浪漫色彩的遥远地名如陇坻、辽川。即如首句,也是对传统《从军行》首句的呼应。但吴诗篇幅较短,不像陆、颜、沈约等那样用辞高华,显然自觉地使用了通常和歌谣词曲联系在一起的直言风格(“男儿亦可怜”与梁代乐府中的“男儿可怜虫”呼应;“直如弦”是对东汉童谣“直如弦,死道边”的引用),这一特征使他在当时得到“有古气”的名声。⑧最重要的是,和先前的《从军行》相比,吴诗通篇只写“北边”。
梁朝边塞诗描写“北边”已基本定型。何逊(?—518)想象中的北方边塞出以工整的对句:“阵云横塞起,赤日下城圆”(《学古》)。云之浓密,令人想到军容;云之横亘,又与夕阳之垂直下落形成对照。何逊的诗句显然影响了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晚唐诗人李贺更是在《雁门太守行》(这一乐府诗题是在梁朝才初次和边塞联系起来)中把云与日的意象锻炼成名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何逊的后辈诗人萧纲(503—551)在其《从军行》中对压抑的黑云作了新的处理:
云中亭障羽檄惊,甘泉烽火通夜明。贰师将军新筑营,嫖姚校尉初出征。复有山西将,绝世爱雄名。三门应遁甲,五垒学神兵。白云随阵色,苍山答鼓声。逦迤观鹅翼,参差睹雁行。先平小月阵,却来大宛城。善马还长乐,黄金付水衡。水妇赵人能鼓瑟,侍婢初笄解郑声。庭前柳絮飞欲合,必应红妆起见迎。
萧纲的诗杂用五七言句,展现了一条清楚的叙事脉络,结果是一首节奏明快而意气昂扬的诗篇。现实地理中毫不相属的地方在诗中交织在一起,强调“经验真实性”的论者如颜之推也许会不以为然,⑨但这也正说明了边塞诗中的地名不过是符号而已,它们来自前人的作品和史籍,构成了一幅文学的版图。
萧纲的诗以征人还家的情景结束。把“闺怨”题材纳入“边塞”诗,既不说明“宫体”主将必然笔涉闺情,也未必像有些学者所说的,仅仅是出于审美需要而已。⑩我们需要看到:对家园或者女性空间的描述可以说是边塞诗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突出了远在边塞的男性空间。这个男性空间是对平凡单调家庭生活的逃避和脱离,男性的行动自由与女性窄小拘束的行为空间不仅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前者也是只有相对于后者才成立的。南方男性诗人的边塞诗,通过描写家中的妻子,旨在向读者表明男性在这两个不同的空间里都是主人;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写法也在无意之中加深了北方与南方的“性别分裂”。
萧纲的《从军行》显然给年青一代的北方诗人卢思道(535—586)留下了深刻印象。卢思道的同题作品,与其说展现了作者对北方实地的经验,还不如说表现了他对文学传统的熟悉。虽然有些学者坚持认为“现实生活的经验”使得北方诗人的边塞诗鲜明生动,这些诗却往往只是边塞诗传统因素的拼盘,而且实在不见得比南方诗人的作品更有感染力。文学传统的力量远远超过了现实生活。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我们注意到卢诗的开头与萧诗开头何其相似:两位诗人都选择了一个戏剧化的开场画面,把笔力集中在烽火的意象上。(11)卢思道的技巧表现在他把边塞诗中常见的地名、意象、典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虽然拼凑补缀,全诗却浑然一体,保持了明快流畅的节奏。
时至梁朝,边塞诗的传统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因此,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南疆的诗篇。在梁朝苏子卿一首题为《南征》的诗里,我们发现诗人只能以否定形式描写南方边塞,譬如说寒冷气候的缺乏:
朝游桂水,万里别长安。故乡梦中近,边愁酒上宽。剑锋但须利,戎衣不畏单。南中地气暖,少妇莫愁寒。
隋朝诗人薛道衡的《豫章行》写到南征,但是除了开头三联之外,余下的二十八行诗全部都在描写征人妻子,因此与其说是边塞诗,还不如说是闺怨诗更恰当。我们在诗中也根本找不到南方边塞的意象。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外是另一隋朝诗人孙万寿的《远戍江南寄京邑亲友》。孙万寿曾“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在军中任职,郁郁不乐,遂作此诗抒发牢骚。全诗约八十行,可谓长篇,但诗人用了大量篇幅描写思乡情绪,而且,诗人笔下的“江南边塞”仍然充满了文学传统的回声,开篇即指出那是属于屈原、贾谊的南方,并把南朝诗人谢朓的“江南佳丽地”讽刺性地翻改为“江南瘴疠地”。这样的颠覆反而构成了对传统的强调。
到了6世纪后期,北朝不断出兵江南。明余庆(?—618),一个由南入北的诗人,为“南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三边烽乱惊,十万且横行。风卷常山阵,笳喧细柳营。剑花寒不落,弓月晓逾明。会取淮南地,持作朔方城。
因为是在描写边塞征战,诗人情不自禁要谈到寒冷,但是诗中唯一寒冷的是“剑花”——剑锋的寒光。朔方是汉代的北方边镇。在南北朝时期,从一个北方人眼中看来,南方自然是真正的边塞,然而诗人却不得不用一个北方的地名——在边塞诗传统中常见的地名——来传达他对南方的距离感和陌生感。(12)
南朝诗人对遥远北地的想象充分显示了建构文化他者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和南朝诗人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息息相关。最后就连北方诗人也接受了南方边塞诗的意象和语汇,而南方边塞诗对北方的想象对中国文化中“北方”形象的塑造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北人征服了南方,但是南人却言说了北方。
王褒(513?-576)在江陵创作《燕歌行》,“妙尽关塞寒苦之状”。梁元帝萧绎等人纷纷继作,后来江陵沦陷于西魏军队,王褒等人也被擒获到北方。史臣称王诗“至此方验”。(13)看来,在不止一种意义上,现实是对艺术的模仿。
造作的雄健:“北朝”乐府
北方的雄健形象,在一组所谓“北朝民歌”中得到加强。这些歌诗其实属于“梁鼓角横吹曲”,收入僧人智匠(约6世纪中后期)的《古今乐录》,保存在《乐府诗集》中。鼓角横吹曲乃“军中之乐”,在朝廷仪式中,或者作为皇家仪仗队的一部分,由宫廷乐师在马上演奏。鼓吹有时也作为高级荣誉赏赐给诸侯王或大臣。
现代学者往往继承传统说法,极力强调这些乐歌的“北方性”,把它们视为北方特质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精神的反映,与南方温柔细腻的汉文化形成对比。(14)这种二元对立观却没有考虑到这些乐府诗的音乐分类在歌辞的选择中起到的作用。换句话说,“鼓角横吹曲”既是军乐,自然一定要歌咏战争、武勇和对兵器的热爱,因此,被包括在“鼓角横吹曲”中的乐府也就不宜被视为“典型北方音乐”的代表。
在我们详细分析这组乐府诗之前,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对很多歌诗的来源我们不能确知(有些很有可能的确来自北方),也不打算勉强论证这些乐歌“实际上”都是由南方乐师创作的。本节的重点,在于探讨南人在选择、演奏、保存和传播这些乐府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乐府当成“北歌”处理,而必须认真考虑南人的中介作用,这在传统文学史叙事中是一个被忽视了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不应该追问这些歌到底是北歌还是南歌,而应该问为什么南方人要选择在南方的宫廷演奏这些歌。第二,音乐和歌词的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即使这些歌诗的音乐可能来自北方,歌辞本身却不一定来自北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确定不疑的文本依据证实这些乐府的来源。
因为梁鼓角横吹曲充满北方地名,有些学者试图以此来证明这些乐府来自北方。(15)但是前文对边塞诗的讨论已经告诉我们在诗中运用北方地名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从未去过北方的南方人照样可以写出以北地为背景的诗篇。“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常常被人用作鼓角横吹曲源自北方的证据,但这两句诗引发了很多问题。在南北朝时期,没有哪个北方人会以“虏”自称,因为这是汉族对非汉族、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有的学者以为这首诗是从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汉语翻译者因此选择了一个贬义词来翻译鲜卑歌者的自称。这一解释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只引发了更多问题。为什么一个鲜卑歌手要唱出这样的句子?这首歌的基调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自豪和对汉儿的蔑视,还是对自己“不解汉儿歌”感到自卑与焦虑,还是遥望洛阳的孟津河,看到“郁婆娑”的杨柳,与北地家园形成对比,从而产生望乡情结?(16)我们可以为这首歌设想出很多种语境,但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最重要的是问一问:在众多北歌中,梁朝乐师为什么特地选择这首歌为梁朝贵族演奏?南方人为什么喜欢听到“虏家儿”“不解汉儿歌”的宣言?如果梁人把这首歌理解为鲜卑歌手自豪的宣言,为什么还要把它包括在梁朝的军乐里?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虏家儿”虽然不解“汉儿歌”,汉儿却可以理解“虏儿歌”,并从而感到一种文化优越性。这也许正是南人要把这首歌包括在鼓角横吹曲里的原因之一。归根结底,这些歌是否“来自”北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到它们是“关于”北方的:它们代表了梁朝人对北方的想象,对“典型北方人”的想象。
《古今乐录》编于568年,因此568年是这些乐府的创作下限。但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些乐府的创作年代一无所知,唯一可以基本确定创作年限的是《高阳乐人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高阳”乃是智匠所说的北魏高阳王元雍(?—528)的话。汉代宫廷乐师李延年据说曾经受到西域“胡曲”的影响,“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时至魏晋,仍有十首流传。(17)其中《折杨柳》和《陇头》二题都出现在梁鼓角横吹曲中。无论如何,我们在阅读这些乐府时应该记住,这些歌从曲到辞,哪怕是同题歌辞,都未必来自同一个历史时期或者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下面,我们且来具体检视一下梁鼓角横吹曲中的一些曲辞,以见鼓角横吹曲的来源混杂,未可简单地以“北歌”一概而论之。
梁鼓角横吹曲的第一曲题为《企喻》,共四章。“企喻”通常被视为鲜卑语的音译,也曾出现在北魏宫廷乐《真人代歌》里,只是我们不知道同题梁曲的歌词是否与《代歌》重合。(18)《旧唐书·乐志》言:“梁乐府鼓吹又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净皇太子曲。与北歌校之,其音皆异。”(19)“音异”可指音乐的改变,也可指歌辞的改变。
下一曲《琅琊王歌辞》共八曲,第八首云:“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乐府诗集》卷25称广平公为姚弼(?—416),然考4至6世纪之间曾有数位广平公,未详孰是。(20)《琅琊王歌辞》第一首描写一个男子对其武器的热爱: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这种夸张的阳刚色彩,建立在对沉迷于醇酒妇人的“孱弱”男子形象进行颠覆的基础上,很容易就可以拿来代表南人想象中的“典型北人”。然而,我们同样不难想象,一个善于戏剧化地表现雄豪之气的南方诗人如吴均,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这样的歌辞来。
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仅仅从文本上来看,我们往往很难分辨《琅琊王歌辞》的来源,比如第二首:
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裲裆。
“阳春二三月”的字样在南方乐府中极为常见,比如系于谢尚名下的《大道曲》就是以“阳春二三月”开始的。这让我们对《琅琊王》的曲名发出疑问。在东晋南朝,当人们听到或者看到“琅琊王”一词,最直接的联想恐怕不是别个,而是“琅琊王氏”。另一方面,“琅琊王”也可以指称诸侯王。虽然琅琊在江北,但是在南北朝时期,“琅琊王”引起的联想还是主要与南方相关。东晋诸帝,包括晋元帝在内,有六位在登基之前都曾被封为琅琊王,在这一时期,皇子被封为琅琊王可以说具有相当的政治重要性。(21)所以,我们实在不必像有些学者所做的那样,努力在北朝寻找琅琊王的踪影,何况北方原本也找不到那么多的琅琊王。即如投奔北魏的司马楚之(?—464)被封琅琊王,还是因为他的晋朝宗室背景。北魏的另一位琅琊王元绰,是535年受封的;北齐的琅琊王高俨(557—571)则是569年受封的。从时间上来看,他们不太可能是梁鼓角横吹曲中《琅琊王》一曲的始作俑者。
下一曲《钜鹿公主歌辞》,题下三曲,每首两行七言,读起来比较像是一首歌的三节,而不是三首独立的乐歌。《旧唐书·乐志》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似是”姚苌(330—394)时歌,但特别强调“其辞华音,与北歌不同”。
下两曲均题为《紫骝马》,但智匠称后曲“与前曲不同”。我们现在仅从曲辞上已经不大容易看得出两曲的差异(都是五言四句),只能推测说,差异大概表现在音乐或演奏方面。关于《紫骝马》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前曲六章,后四章“十五从军征”云云读起来好似一首十六句的五言诗,有清楚的叙述脉络;(22)相比之下,后曲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与无数南方乐府极为相似。二,《紫骝马》这一乐府诗题在梁朝开始出现于宫廷诗中。萧纲、萧绎兄弟都曾以此为题赋诗,萧纲的《紫骝马》乃《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之一。梁鼓角横吹曲中的《紫骝马》,从乐曲到曲辞,都未必起源于北方。
下一曲《黄淡思》,曲名意义难晓。智匠怀疑“黄淡思”源自“黄覃子”,李延年所造曲之一。《晋书》记载了一支4世纪时流传于荆州的乐曲,题为《黄昙子》。(23)《黄淡思歌》都是情歌,其中第三首则描写了一艘豪华的广州龙舟:“江外何郁拂,龙洲[按洲、舟在中古汉语里乃同音字]广州出。象牙作帆樯,绿丝作帏繂。”
《东平刘生歌》仅三句:“东平刘生安东子,树木稀,屋里无人看阿谁。”据《乐府诗集》卷二四:“《乐府解题》云刘生不知何代人,齐梁已来为《刘生》辞者,皆称其任侠豪放,周游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剑专征,为符节官,所未详也。按《古今乐录》曰梁鼓角横吹曲有《东平刘生歌》,疑即此《刘生》也。”南朝乐府《西曲歌》中有《安东平》曲:“东平刘生,复感人情。与郎相知,当解千龄”(这里的“东平刘生”可以视为刘生其人其事,也可以视为曲名)。“东平刘生安东子”和《安东平》曲分明有渊源关系,而且,从现存资料来看,对《刘生》这一乐府诗题的兴趣是从梁朝才开始的。谭润生因为《刘生》作者多为梁、陈人,又因为梁元帝《刘生》把刘生描写为长安游侠儿,所以断定此“刘生”非鼓角横吹曲中的“东平刘生”,实则东平刘生又何必不能周游长安,又何况所谓的东平刘生本来就可能是传说人物呢?《刘生》作者几乎全都是南方人,正好说明“东平刘生”本是南方诗歌题材。
梁鼓角横吹曲又有《折杨柳歌辞》五曲与《折杨柳枝歌》四曲,前文所引“我是虏家儿”即其中之一。其第一首,“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旧唐书·乐志》记载略有不同,并云“歌辞元出北国”。(24)然而乐府旧题本有《折杨柳行》,可以上溯到公元二、三世纪。《晋书》提到西晋太康(280—290)末年京洛流传《折杨柳》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擒获斩截之事”(25)。南方乐府的《西曲歌》中《月节折杨柳歌十三首》,每首都有“折杨柳”的叠句;《读曲歌》中也可见到“折杨柳”字样。可见《折杨柳》恐怕只有在“源出中原”的意义上才能说是北曲。
《幽州马客行》可能是另一乐府旧题。保存在《艺文类聚》中的《陈武别传》提到休屠胡人陈武从其他牧羊儿那里学会了很多歌谣,如“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关于陈武的记载甚少,我们只知道他大约是4世纪人。诸葛亮(181—234)据说好为《梁父吟》;东晋时袁山松(?—401)则曾经润饰过“旧歌《行路难》曲”。(26)《幽州马客行》共五曲,其中第三、四、五首都是情歌。现代学者谭润生在《北朝民歌》一书中把这些歌定为北歌,但相信它们受到了“南方影响”,因为其中有“郎著紫袴褶,女著彩裌裙”“黄花郁金色,绿蛇衔朱丹”字样。谭氏以为这样“宛曲巧艳”的字句“已失率真之情”,并因此断定“此歌辞曾受南方民歌之影响”。(27)这样的论点表明南方代表文化/北方代表自然这样的二元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代文化想象,以至于学者们想象出来的北方必定寒冷、荒凉、野蛮、单调,就连一点点色彩的存在都被视为南方的影响。这实在是一种无视历史事实的天真态度。
以上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梁鼓角横吹曲中包含的乐歌,从曲到辞来源都很复杂,往往难以辨别南北。但是,人们往往执著于传统观点,不去反省有些观点反映出来的文化、地域、民族与历史偏见。著名学者刘大杰的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北方的情感多是直率的热烈的,没有南方那种隐曲细密的手法。北方人并不是不讲恋爱,但是他们的表现方面是与南方不同的。”刘氏又引梁启超论“北歌”的话作为佐证:“他们(按指北人)生活异常简单,思想异常简单,心直口直,有一句说一句。”(28)事实上,不是北人“思想异常简单”,倒是这样的观点显得“异常简单”,也把复杂的社会现实与文学现象简单化了。
还有时,南朝乐府与北朝乐府之间的“差异”被理解为民族差异:学者一方面夸张了鲜卑民族的单纯、天真、“缺乏文化”,一方面把汉民族想象为羞涩、含蓄和扭捏。这样的环境决定论和民族决定论观点实际上充满了不自觉的民族和文化偏见。要是我们能够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对现存的文本进行检视,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
即如《幽州马客行》的第三首:
南山自言高,只与北山齐。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
谭润生氏根据诗的第一、二句,即断定这是北歌,(29)不解何故,大概是因为看到“南山”“北山”的字样,联想到了南方与北方;但这种联想,只能说明是“南方”=“女儿”/“北方”=“郎君”的传统文化想象在作祟。再说,如果北山/南山代表了北人/南人,北人歌手又何必称南山与北山“齐”呢?南人又何必收这样的歌在他们的军乐里呢?
如果说歌中情愫热烈奔放、代表了“典型”北方女子的声口,则我们可以拿这首歌比较一下系于东晋著名作家孙绰(314—371)名下的《碧玉歌》: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难,回身就郎抱。
或者南朝乐府中的《孟珠》:
望欢四五年,实情将懊恼。愿得无人处,回身与郎抱。
或者《前溪歌》:
黄葛生烂熳,谁能断葛根?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
这样的歌辞,其直率热烈,是丝毫不逊色于“南山自言高”一曲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首系于北魏胡太后(?—528)名下的《杨白华歌》,据说是胡太后为了她叛北入南的情人而作,歌辞充满了缠绵温存: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很多学者因为觉得这不符合北方女子“直爽坚强”的传统形象,遂不得不强作解释说这是受到了南方文化的影响。然而,这种“北人必定如何、南人又必定如何”的笼统概括其实是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认识到,“南/北”的文化形象在南北朝、隋唐时期被逐步建构,渐渐深入人心,而现代学者和读者对“南北”所作的文化联想,其实无不承自这一时期。
在南北朝时期,南人出于政治需要,把北方的形象塑造为蛮荒、朴野、自然,这些价值观本身即存在褒贬暧昧之处。但南人之本意,在于强调北人之疏野,以求突出南人之文明,以正统汉文化的传人自居。南人自视等同于“文化/文明”(culture)的代表,置北人于“自然”(nature)的地位,这正与南方贵族把南方本土社会身份低下的女子(“小家碧玉”)塑造为热情洋溢的“自然”形象遥相呼应。在这一公式里,我们可以说:
北方鲜卑=“低级”文化=“自然”=南方平民女性
南方汉人=“先进”文化=“文明”=南方贵族男子
但是“自然”(nature)本是一个意义暧昧、可褒可贬的范畴:从否定方面来看是粗疏野蛮,从肯定方面来看是质朴天然。因此,在初唐时期,作为征服者的北人接受了“自然”的定义,但着力消解其“荒蛮”的一面,强调其“质”的一面,这样一来,虽然继续把南人置于“文”的地位,文/质的二元对立却产生了新的意义,在“质”映照之下的“文”,已经不再是完全积极的“特权概念”了。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南/北的二元结构最早在南北朝时期形成,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我们的文化想象和文学话语。南北对立从原本是政治与地理上的分裂很快转化为文化上的隔阂,北方与南方政权都在积极地、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对抗现实中的政治敌手和想象出来的文化“他者”。一方面,我们看到南朝政权,特别是在梁武帝长期和平的统治下,致力于“文”的建设,使自己区别于也优越于被他们蔑称为“虏”的北方王朝;另一方面,北人也在极力强调自己作为中原汉文化继承者的正统地位,孜孜矻矻于经学的研究,并把他们的南朝对手藐称为“夷”。隋唐统一中国之后,南人所一力推行的“南文/北武”被“南文/北质”的二元结构所代换。文/质这对概念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已有很长的历史。“质”被视为基本的范畴,“文”的基础;但是,人们也充分认识到“文”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文”,“质”会显得粗野,甚至会失去自己的独特身份。就像《论语·颜渊》中子贡回答棘子成的那样:“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选择“文/质”这一对概念来代表南/北,使初唐史官处在两难之境:在歌颂北方之“质”的同时,他们对南方之“文”的态度未免显得暧昧不清。
到了后代,在南北朝时期逐渐成型的“南/北”形象不仅成为人们对南方与北方先入为主的认知方式,而且进一步塑造了社会现实。文本所建构的形象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作出价值判断的标准,构成了人们的期待视野,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与决定人们的行为。我们不应该执著于“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单项信仰,而应该考虑一下“文化”如何在多种意义上生产“自然”。我们的思维必须跳出“南/北=文化/自然”的二元结构,转而去检视这一结构是如何生成的。
[附注:本文是书稿《烽火与流星:梁代文学与文化》的一部分。书稿英文版将由哈佛大学东亚中心出版社2008年出版。]
注释:
①《颜氏家训》卷九,王利器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页。
②据《隋书·经籍志》卷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79页。
③《隋唐嘉话》卷三。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比如张鷟(658—730)在《朝野佥载》卷六里记载庾信除了对温子升、薛道衡、卢思道略加赞许之外,对其他北方作家一概嗤之以鼻。
④《盛唐诗》,耶鲁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阎采平也指出边塞诗缺乏“现实”基础。见阎采平《梁陈边塞乐府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
⑤谭优学的《边塞诗泛论》认为边塞主要指长城一带和河西、陇右(今甘肃省)地区。见《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不过,辽西和燕地(今辽宁、河北)也在边塞诗中占有一席之地。
⑥鲍照的同时代人已经认识到鲍照对边塞征战题材的爱好。稍后江淹在写作《杂体三十首》时,选择模拟鲍照的诗题就是《戎行》。
⑦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版,第84页。阎采平在《梁陈边塞乐府论》一文中、刘汉初在《梁陈边塞诗小论》一文中,都曾试图分析边塞诗盛行于南朝的原因。阎认为这和北朝乐府的影响有关。但是这一论点缺乏有力的文本证据,因为梁陈边塞诗和现存所谓的“北朝乐府”绝不相似,而且,很多五六世纪南方诗人采取的乐府诗题来自汉魏旧曲,这些汉魏旧曲在南方也多有保留。至于边塞诗中多用北方地名,更不足以说明受到乐府影响,因为这些地名在史籍和早先的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刘汉初则强调梁朝诗人多在社交场合下集体赋诗,“以文为戏”。但问题是这种情形本身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梁朝诗人特别喜欢写作边塞题材。见《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⑧《梁书》卷四九,第698页。
⑨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强调“文章地理,必须惬当”,并挑出萧纲《雁门太守行》中四句诗“鵞軍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馬,小月送降书”加以褒贬。王利器以为这是褚翔(505-548)诗,非简文帝诗,并举《乐府诗集》为证。不过《乐府诗集》所录褚翔全诗有一部分出现在《艺文类聚》卷四二“乐府”中,正作简文帝诗。手抄本文化中一诗分署不同作者之名乃是常事,然则此首《雁门太守行》正不必遽定为褚翔所作。
⑩见王文进《南朝边塞诗新论》,第98—121页。
(11)北周赵王宇文招(?—580)所作《从军行》残片,首句完全是萧、卢二诗首句的翻版:“辽东烽火照甘泉”。
(12)在16世纪冯惟讷辑录的《古诗纪》(卷一三六)中,“淮南”一作“河西”,但是《文苑英华》(卷一九九)和《乐府诗集》(卷三二)两种较早的资料均作“淮南”而无异词。
(13)《周书》卷四一,第731页。
(14)略举数例:李开元、管芙蓉的《北魏文学简史》,太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80页;王运熙的《乐府诗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473页;周建江的《北魏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页;曹道衡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7页;或谭润生有关北朝乐府的专著《北朝民歌》,台北东大图书1997年版,第316—334页。
(15)见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页。
(16)萧涤非认为“汉儿”是贬义词(《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280页),这缺乏说服力,因为第一,“汉儿”与“虏”不同,有时带贬义,有时是中性词,其语气是受到上下文语境限制的;第二,为何南朝乐师要为南朝汉人贵族演奏一首贬称汉人的歌曲?
(17)《晋书》卷二三,第715—716页。十曲为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
(18)《魏书》卷一○九,第2828页。《代歌》有53章流传至唐,其中只有六章“名目可解”,其中就包括《企喻》。现代学者田余庆认为梁曲中的《企喻》与《代歌》中的《企喻》无关。详见其《拓跋史探》,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19页。
(19)《旧唐书》卷二九,第1072页。
(20)包括石勒(274 333),苻熙(4世纪),张黎(5世纪),游明根(419-499),以及一位北齐贵族高盛(?-536)。
(21)这六位东晋皇帝分别是:元帝(317-322在位),康帝(343-345在位),哀帝(362-366在位),废帝(366-371在位),简文帝(371-373在位),恭帝(419-420在位)。
(22)智匠附注:“‘十五从军征’以下是古诗。”明人冯惟讷的《古诗纪》和张之象(1507—1587)的《古诗类苑》遂都把“十五从军征”以下十六句抽取出来,当成一首独立的“古诗”。现代学者逯钦立也同样把这十六句作为独立的一首诗放在《全汉诗》中。虽然学者们习惯于视“古诗”为“汉诗”,我们必须记住,从4世纪到6世纪,“古诗”被用来指称那些作者与年代不详的诗,而这些诗可以创作于东汉,也可以创作于魏晋。
(23)(25)《晋书》卷二八,第847、844页。
(24)“快马不须鞭,反插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路旁儿。”《旧唐书》卷九,第1075页。
(26)《三国志》卷三五,第911页;《晋书》卷八三,第2169页。
(27)(29)《北朝民歌》第66—67、66页。
(28)《中国文学发展史》,台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43页。
标签:南方与北方论文; 文学论文; 南北朝论文; 琅琊王氏论文; 中古汉语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从军行论文; 艺文类聚论文; 紫骝马论文; 刘生论文; 魏书论文; 琅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