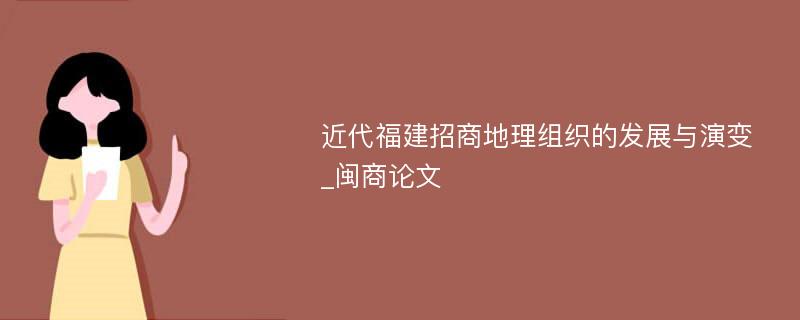
近代闽商地缘组织的发展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近代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14)02-0022-10 1921年9月1日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上说:“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智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要看它的社会组织是否完备,就是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健康的社会组织。近代闽商组织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样态,大体包含三个方面:一是传统的会馆、公所继续存在、时有兴建,且呈现出兴盛局面,这类组织既集中于省城福州,也在像厦门、泉州、龙岩、建阳等地有所体现。二是伴随着近代商战的时代潮流,福州、厦门建立起了商务总会,该两商务总会均受到《商会法》的推动,且由政府干预组建,它们统管全省各地的商务分会,实际上是建立起了对全省商会的集中管理。这些商务总会受到传统会馆、公所、同业公会的积极影响,或者说承继了传统会馆的基本遗产,厦门总务总会就成立于广东会馆内,福州的商务总会建于下杭街,也是会馆集中之区。三是福建商帮还将他们的组织建到了国内各地、海外各地。举凡上海、苏州、天津、烟台、宁波等地都有福建商帮的集合场所——福建会馆。在南洋各地,福建会馆鳞次栉比,彰显了近代福建商人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的强大能力。在与台湾的贸易中,福建商人尤其是闽南商人积极有为,规模巨大,除了建立会馆、公所外,在沿海港口还多建立了郊行及其郊行会馆,这类组织只出现在台湾、厦门等沿海港口城市以及闽南商人足迹所及的南洋区域,几乎只与海洋经济贸易活动存在关联,且内部相互信任多,运行有效。 一、传统会馆、公所在近代的继续发展 福建商帮是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之一,在建立商人会馆方面,福建商帮具有倡始性,尤其在江南的苏州、上海等地,数量与规模均较大。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外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增多,福建商帮势力进一步壮大,兴建与扩充会馆、公所的努力进一步得到彰显。① 福建的商人既有山地商人,又有沿海商人,因而形成了大商帮中的小商帮,可谓帮中套帮,有的会馆下又或依行业分帮,有的会馆下又或按地域集结,前者如苏州的三山会馆内又有干果帮、青果帮、洋帮、丝帮、花帮、紫竹帮等,后者如潮州的汀龙会馆分成篓纸纲、福纸纲、龙岩纲、履泰纲、本立纲、九州纲、运河纲、武平纲、上杭纲、莲峰纲、永定纲、白沙纲和袍季等,在汉口的福建会馆由巷岩福、龙川福、致和福和宝树福所组成,在重庆的福建会馆内又有文华会和鄞江会等。②举凡纲、岩、福、会等都是商人集体力量凝聚的组织,它们均可以在会馆组织之下滋长。 在浙江宁波,临海的天后宫于乾隆二年(1737年)由福建商人建立,咸丰十一年庙毁,同治十年(1871年)福建商人林益谦等又行重建。③上海的开发与发展离不开福建商人的努力,由泉漳商众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建于咸瓜街的泉漳会馆,由建宁、汀州商人于道光五年(1825年)建于翠微街的建汀会馆,由福州、建宁商众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建于福州路的三山会馆和由莆田、仙游商众于光绪年间建于南市复兴东路的兴安会馆等都鲜明地记载了近代以前福建商帮在开发上海事业中的历史功绩。 在山东烟台,闽商凭借妈祖信仰在此站稳了脚跟,并带动以天后宫为中心的区域迅速成为城市中心,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人加入进来。“本埠各会馆之兴筑,以潮州会馆及福建会馆历时最久,建筑亦甚宏壮……两馆内均供有天后圣母像,于年年中元节期,举办盂兰大会,故俗称潮州会馆为东盂兰会,福建会馆为西盂兰会。”福建会馆及潮州会馆呈闽粤建筑风格,格外引人注目。福建会馆由福建商人自1884年动工,至1906年落成,占地3500多平方米,原为三进庭院,建筑材料取自福建泉州,由当地工匠雕刻后海运至烟台组装而成。该会馆坐南面北,很显独特性,因为馆内供奉妈祖,须面朝大海,保佑渔民,普度众生。烟台福建会馆竭力谋求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妈祖与蓬莱八仙信仰相互结合,迅速实现了妈祖信仰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在建筑雕饰上,福建会馆亦尽量将当地人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融入其中,以求达到教化效果。福建会馆的楹联是文化展示的一个重要平台,楹联内容或警世,或崇神,或赞誉乡贤,强调两地交流产生的双赢效果。譬如“熙朝崇祀典鲁近闽并一席,湄岛现慈航江河海普护千艘”。山门右门楹联:“作庙象尊严观神威同般施布,入门加敬谨荷庇佑早切归依。”山门左侧楹联“俎豆荐他乡何异明礼修故里,灵神周寰海依然宝炬济同人。”山门之前,面向大殿处石柱有楹联:“从八百英里航路通来揭耳鼓闻韶是真邹鲁海滨何分乐界,把二十世纪国魂唤起放眼帘阅史直等衣冠优孟同上舞台。”天后殿前六根石柱三副对联:“地近蓬莱海市仙山瀛客话,神来湄渚绿榕丹荔故乡心”;“榕嵩荷神庥喜海不扬波奠兹远贾,芝罘崇庙祠愿慈云永驻济我同舟”;“潮馆近为邻作庙后先隆俎豆,曹碑同此孝惟神功德普寰瀛”。这些对联无不体现了福建与烟台、南北方的联系与交流。1902年在市中心的天后宫由八大家自发成立了大会,堪称烟台市最早的商会组织,大会主持商品统一价格及各商号的公益事宜。1906年改名为总商会,1910年改为商务会,1920年政府注册为烟台总商会。 在台湾,银同会馆创建于道光二年(1822年)祀妈祖、吴真人、陈圣王、五文昌、朱夫子、蓝先贤等神。在彰化有汀州会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汀籍总兵张世英及汀籍人士捐助而成,主祀守护神定光古佛。三山会馆创建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三山会馆为清代福州人来台南所捐建。在淡水,有汀州会馆,为道光三年(1823年)汀州人张鸣岗等捐建。光绪十九年(1893年)《鄞山寺碑记》说:“昔汀人在沪尾街后庄仔内,于道光三年建造庙宇,名为鄞山寺,供奉定光古佛,为汀州会馆。”在台湾,由于闽粤移民比较集中,故这里有泉郊会馆、厦郊会馆、汀州会馆等。④ 根据方志记载和实地调查,福州历史上共有66所会馆。按现在区属划分:鼓楼区有32所,台江区有31所,仓山区只有3所。按馆属分:本省的36所,外省的29所;全国18省,省内24县,都在福州设立会馆,有的一地多馆,如江西人在福州建的会馆,在鼓楼北角楼和鼓东路各有一座,在台江有昭武会馆一座、南城会馆两座,江西会馆一座,平南会馆三座,可见江西商人将福州作为贸易出海口的事实。浙江木业商帮在仓前桥头建“安澜会馆”,俗称“上北馆”,浙江运木商帮还在泛船浦文藻巷建“浙船会馆”,俗称“下北馆”。会馆有的是联省合建的,如石井巷的两广会馆、三山会馆、闽浙会馆、闽陕会馆、奉直东会馆、蜀滇黔会馆等;江浙两省的绸布业公帮在福州城市内外各合建了一个会馆,因是跨省性的,不标“江苏”或“浙江”名称。城内的会馆在春育亭(俗呼“仓前河沿”,在通湖路和光禄坊交界处),邻近三山驿,故叫“三山会馆”,在南台的会馆也用此名,分别呼为“城三山馆”、“台三山馆”。浙江人还在鼓楼的三牧坊、西门外和南门下醴井分别建了浙江会馆、浙绍会馆、闽浙会馆。由此可见浙江商人在福州的势力。有的会馆是地缘性的会馆,如建郡会馆就是由建宁府所隶属的建安、瓯宁、崇安、浦城、建阳、松溪、政和七县共建的。又如台江下杭的南郡会馆,即由泉州、漳州、厦门等闽南籍商帮集资建造的。有的会馆是同业会馆,如安澜会馆是由浙江木材商兴建的,石塔会馆是京果行商会捐资重建的。 在福州,还有外国商人的会馆。如琉球会馆,馆址在太保境和状元街之交的旧水闸口(今台江第五中心小学后门)外。由于福州与琉球贸易往来频繁,琉球馆(福州人对柔远驿之称呼,始建于明成化年间,重建于康熙六年(1667年),址在今馆后街40号福州第二开关厂)附近就有七姓十家联合组成的行会组织,专门经营对琉球贸易。据郑祖庚《闽县乡土志》记载:“李姓四户,郑、宋、丁、卞、吴、赵各一户,代售球商之货。”按规定琉球贡船贸易商品要委托他们代售,不能私下与老百姓直接贸易;琉球人所需的货物也由这十家承办,这样“十家排”几乎垄断了中琉贸易。这十家商人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合资建立“琼水会馆”,即琉球会馆。“迄于清代,河口仍在琉球商人集居之地,故老相传,当贡船来闽时,其地繁华殷盛,曾为全城之冠。”⑤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古田米商陈必光牵头,在台江购得地皮,创建会馆,到1904年,古田商帮的其他分支包括红粬帮、茶帮、焯帮亦加入会馆的建设,1904-1908年,建成正门、四面风火墙、石戏台、天井、酒楼、拜亭、大殿等部分,1909-1913年进入局部维修阶段,并对栋梁、戏台基座和拜亭等进行金硃上色。1914年又购得右侧既有库房(又称西跨院)扩充规模。整个工程历时十年,共筹集款项18287两7钱3分5厘,耗资18889两3钱8分8厘。显然,在福州商务总会建立之后,会馆仍继续兴盛并发挥着作用。 同治十年编成的《汀龙会馆志》为我们提供了福建商帮会馆运行的典型个案: 汀龙会馆倡建的起因在于:“汀龙二州密迩毗连,据闽江之上游,下与潮属为邻,地壤相接,且鄞汀一水南流直通潮郡,舟楫往来,众皆称便。凡商贾贩运,托业于斯者,歌乐土焉。盖时当承平,清晏日久,海国江乡,无复向时鲤波瘴雨矣。由是议建会馆,将上以妥神灵,下以通乡谊,岁时祭赛,樽酒言欢,联一堂桑梓兄弟,甚盛事也。佥曰:宜然,因而相地裁定,鸠工庀材,自春徂秋,九阅月而告竣。考其时岁在癸未,为乾隆二十八年。” 会馆建成之后,规模就颇为庞大,成为潮州地方最大的会馆。“馆在潮州城开元街之西福胜庙右手下畔,坐北朝南,馆门当街,正中为天井雨坪,左右二廊,道光戊戌年改建东西二酒楼,正厅堂为奉祀天后圣母,正殿左耳厢为财神殿,右耳厢为福德祠,均祀木祖,设神龛,前为天井,俱有门与酒楼相通,则财神殿左横屋一直深与馆基等,上为客厅,咸丰癸丑年改修,兹仍京都汀州乡馆堂额为旅萃堂,厅屏后为小眠房,厅前开小天井,左出留天空,下开一水井,中用花窗屏扇隔一小厅,坐东面西,为祭祀更衣所,厅右隔小房,再出为厨房,中开大门当街路,门外左侧抽一厕所,馆后并左右俱黄姓房宅,馆右抽开小巷以通,然路墙檐下有滴水坑出街沟,馆门距街正对照墙一面,其墙下基址属馆内地。”会馆通过祭祀天后、财神、福德正神等聚合会众。 汀龙会馆的内部运作告诉我们:其在“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等方面都有章可循,井井有条。它虽并不设立全馆公项,但在会馆的统一布置下,可以支使各纲来分担款项。另外又让各纲有自己组织祭神活动的机会。且看每年各纲庆祝前后分祭及敬神定期,就可见其中既有轮流坐庄,也有协作行动,从而保证了祀事的不辍与规模。从正月初五日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26次神祭活动,其中有饮宴、演戏等活动,大体情况是: 正月初五日 福纸纲祈神,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二月初一日 运河纲祈神,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十八日 上杭纲分祭,预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十九日 运河纲分祭,预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日 九州纲分祭,预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一日 本立纲分祭,预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一台。 三月二十二日 龙岩纲分祭,预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一台。 三月二十三日 汀龙众帮公祭,厌祝圣母千秋诞辰。预期各纲董理公择帖,请主祭与祭各执事前一夜习仪,众办主与祭执事二便席。是夜演戏,各纲分办酒席预祝,二十三日卯刻致祭,辰刻主与祭执事二面席,午刻饮福二席,由众办,其余各纲早晨观祭,午刻饮福,酒席俱各纲自行分办。是日演戏连宵,亦各纲自办夜席庆祝。 三月二十四日 篓纸纲分祭,庆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五日 福纸纲分祭,庆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六日 履泰纲分祭,庆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七日 武平纲分祭,庆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三月二十八日 莲峰纲分祭,庆祝圣母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六月初三日 福纸纲预祝土地福德神诞,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每年秋九月 汀龙众帮公祭,庆祝圣母飞升,章程与春季同。 九月初六日 上杭纲分祭,预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初七日 延河纲分祭,预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初八日 九州纲分祭,预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初九日 汀龙众纲公祭,庆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连宵。 九月初十日 汀龙众纲预祝财神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十一日 莲峰纲分祭,厌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十八日 延河纲庆祝财神诞辰,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九月二十二日 福纸纲补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连宵。 九月二十三日 本立纲补祝圣母飞升,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十二月初一日 运河纲酬神,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十二月二十四日 福纸纲酬神,午刻饮福,演戏壹台。 换袍季每年演戏壹台,午刻饮福。⑥ 于娱乐中寓教化,促整合,祭祖活动成为聚会活动的载体。在各纲内,经费的收支与管理都有具体规条,从而保证了其规模的稳定与扩大。 会馆的管理是“依其里邑之所近”联络为纲,在汀龙会馆之下分为篓纸纲、龙岩纲、履泰纲、本立纲、福纸纲、九州岛纲、运河纲、武平纲、上杭纲、莲峰纲、永定纲、白沙纲和袍季等。会馆根据每年开支的预算按不同的比例分摊给各纲,包括不同节日的祭祀与演戏也分别由不同的纲来承担。如馆规规定:“汀龙众帮未经抽厘,并无公项,其馆中神前香灯,每月额定壹千五百文,守馆工食每月额定边银壹两零五分,均照向规以三分派龙岩纲、本立纲、履泰纲,共派缴四月,篓纸纲派缴四月,福纸纲派缴四月,闰月均派。”“汀龙众帮春秋庆祝公祭香蜡戏金及主与祭执事二席及费照向规以九份派,篓纸纲派缴三分,福纸纲派缴四份,龙岩纲派缴一份,履泰纲派缴一份,倘有修葺馆宇亦同。”“馆中众帮并未议额有津贴花红程仪及各项喜资,倘有甲科以上及出仕现任司道各大员至馆行香悬匾者临时酌议。”“馆中奉祀圣母神像,袍服制绣更换及费俱由换袍季内措办。”这样便把具体责任都落实到各纲头上。各纲根据贩运集团的特点,或向会员征帐饷银,或买房出租办店以取得收入。如福纸纲饷规规定:“各庄福纸由上山采办盖用各字号戳记,所有双合纸黄纸每四十二张为一刀,每五十刀为一片,合二片共壹百刀为一捆,船送至东关,每捆完纳银四分陆厘,大包各庄纸每八十四把为一球,每球完正饷银三分八厘,向规每饷银壹百两加耗银解费三两,补库平银三钱。至道光十六年再议每百两加费银四两,合前共加银七两三钱,纹佛各半缴完。”⑦通过上述比较稳定的收入再加上房屋店面的租金来达到“答神庥而联乡谊”的目的,由此,会馆的兴盛就直接意味着商业的兴盛,会馆的规约为商业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台湾福建商人地缘组织形态的多元化 台湾岛是福建商帮尤其是闽南商帮最主要的商业贸易活动场所之一。以闽南商人为主体的闽商进入台湾岛从事商业活动,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入明以后,随着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环台湾海峡交易圈的商业活动逐渐增多。尤其是林道乾、颜思齐、郑芝龙等海盗商人集团先后入据台湾,有力带动了环台湾海峡交易圈的商业活动。明末荷兰人占据台湾,以大员为进入环中国海交易圈的据点,“设市于台湾城外,泉、漳之商贾始接踵而至焉”。⑧闽南商人大量进入台湾地区进行商业活动。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驱走荷兰人,据守台湾抗清。郑氏集团在台湾的经营,不仅带动了明末清初闽南商民向台湾移民的第一次高潮,而且大大推动了台湾商业的发展,奠定了闽南商人在环台湾海峡交易圈的主导地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氏降清后,清廷治台时期开启,大批的闽南商民移居台湾,台湾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正是在清廷治理台湾的200余年间,福建南部漳州和泉州地区的闽籍台湾商人群体逐渐形成。 自康熙二十一年(1683年)起,大批闽籍商民通过合法(官渡)、非法(私渡)途径,移居台湾,掀起台湾大规模垦殖浪潮,台湾商品经济日渐繁荣。然而,在清领台湾的前170余年间,台湾对外贸易基本上局限于台湾与大陆之间,尤其是集中于台湾海峡两岸,即台湾与福建大陆地区之间,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台湾海峡经济圈。福建商人尤其是闽南商人活跃于台湾的各个商业领域,其中尤以郊商最具实力。尽管这些闽南商人大多“家在彼而店在此,领本而来,寄利而往”,但其中亦渐有部分商人随着定居,随着繁衍后代接续家业而逐渐土著化。如泉州锦铺黄氏家族,自康熙后期渡台经商,后大多定居鹿港,开设新旧“锦镇”及“锦源号”、“锦丰号”等商行,至道光、咸丰年间,锦铺黄氏郊商进入其繁盛时期。 有些此前来台从事农业、为官、从教的人员也转而经商,成为商业大族。如祖籍同安的杨氏家族其迁台始祖杨咸曲携同胞弟咸先,于乾隆年间移居台湾彰化,从事垦殖,育有三子,三兄弟除务农外,开始兼营商业,其后,家族后代中经营商业者渐众,至道咸年间,已是台中彰化地区较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名望的家族。⑨新竹郑氏家族也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事例。该家族祖籍福建漳浦,明末迁居金门浯江,第三世五兄弟中,国唐、国周和国庆三兄弟于乾隆中期渡台,初居后垄。其后,国唐之子崇和与国庆之子崇科迁居竹堑。崇和以耕读起家,设教竹堑。其子用锡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中举人,道光三年(1823年)中进士,由此走入仕途,改变了郑氏家族之发展途径。此后,郑氏家族的族人或励志攻读求取功名,或购置田产成为地主,或经营商业发家致富。其中用锡家族中,置有四大商号,各造有角板乌艚巨船,航行天津、上海以及吕宋、槟榔屿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各港湾。 在台湾的闽商组织中,“郊行”组织自具特色,如北郊、南郊、糖郊,同时也有会馆、公所,还有1860年代至1880年代之间出现于竹堑地区的“九芎林铺户公记、中港金和顺公记”等“同街的准商人团体”以及1880年代成立于竹堑的船户团体“金济顺公记”⑩,这些都是属于商人自组织类型。 郊最早出现于雍正年间台湾的安平港。当时就有北郊、南郊、糖郊等号称台南“三郊”之商人团体。由18世纪至19世纪之间,台湾府城见诸文献的“郊”越来越多,有学者统计清代台湾府城曾经出现过22个郊。在台湾府城福建港口之外,台湾其他沿海或内河港口城镇,也陆续成立了郊,这些城镇大致位于鹿港、艋胛、大稻埕、新竹、新庄、通霄、大安、后龙、大甲、淡水、基隆、宜兰、澎湖、凤山、盐水镇、嘉义市、笨港、斗六、屏东、梧栖等处。当然这些城镇中的“郊”并非都可一概而论。18世纪前半台南已经成立“三郊”,18世纪后半至19世纪初的鹿港,则在乾隆四十二年已出现“泉、厦郊户”名称,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则已设立至少八种“郊”名。 基本可以认定,以郊来称呼商人团体的民间习惯,只见于清代台湾与厦门等闽南地方以及闽南人移民的某些东南亚地区。除了台湾许多港口城镇多以郊命名商人团体之外,19世纪前半道光年间(1821-1850)的厦门,也存在“洋郊、北郊、匹头郊、茶郊、纸郊、药郊、碗郊、福郊、笨郊”等所谓“十途郊”,以及“广郊”等等其他名称的“郊”。 郊基本上由商人自愿加入,属于民间自我组织形态。光绪年间澎湖台厦郊金利顺、金长顺所定《郊规》说:“无论大小生理,听从志愿入郊。和心同志,整顿郊规,永远遵行,始终如愿,勿坠厥志。则生母之明鉴,馨香万世;而我郊户之通亨发达,亦蒸蒸日上也。”充分反映了郊由成员志愿加入之基本原则;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郊也会被地方政府赋予某些协助地方行政的职能,因而也在原先的“志愿性”外略微加入了一些强制性。在实际交易中,糖郊商人与糖廍商人往往有度量衡方面的纠纷,糖廍佃户与蔗糖地主之间也会出现度量衡纠纷。这表明郊主要整合的是贸易商人,与生产商人往往形成相互的对垒。 糖郊作为贸易商人组织,对物价时常能做出及时的反映,1896年,一位日本人针对鹿港“泉郊会馆”成员的共同经济活动而作了以下评论:“一逢物价发生变动时,即发现其应变非常迅速,同业间都一致立即改定价格,其敏捷程度到底不是日本本邦人所能企及。” 林玉茹通过“鹿港郊商许志湖文书”,对清末在鹿港、泉州与厦门之间经商的郊商许志湖有所研究,郊商作为一种贸易代理商,往往能“透过互通市场消息来决定配运、采办或卖出商品的时机”,这些商人自身从事或是委派伙计定期常驻于大陆与台湾的两岸商港,不仅在各港口从事“配运”商品的工作,也以书信传递商品行情、订购商品数量、讨论商品物价,乃至于结催金钱债务,甚至安排搭船人员以监看预防船长与水手侵吞己方货物。这些商人经过较长期的互动而逐渐形成了商人团体,并以“郊”作为自身团体的“自称”,久而久之,诸如“北郊、南郊、厦郊、糖郊”甚至是“金长和郊、水郊、散郊”等不同的郊名,便成为港口城镇里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称呼这些商人团体的“他称”。事实上,从事“配运生理”的商人成立“郊”团体,还带有海上运输以分担风险的好处。如咸丰、同治年间的“堑郊”诸商号,即“已有合雇船只装载米、糖等货物至大陆内地发售的现象”,而“合雇船只可以共同分摊航海贸易风险,降低运输成本,因而更强化堑郊商人的结社行为,堑郊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组织”。这个“堑郊金长和”即是由港市郊商所组成的商人团体,它是一种“水郊”,而其经营活动主要便是“配运本地土产,以交付来堑的船户”。 清代台湾郊的成立与演化,也与清政府管理商船与渔船、抽征关税与船税乃至于规定台湾米粮“配运”大陆各地等制度有密切关系。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重开江、浙、闽、粤四个海关,以迄乾隆年间所谓“西洋来市、东洋往市、南洋互市”改革,到嘉庆、道光年间,乃至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以下的开放通商口岸,清政府进行了种种关务、税务与船务管理等改革,与此同时,台湾也渐次由鹿耳门、厦门对渡,增添鹿港与泉州对渡、八里坌与福州对渡、开放基隆通商口岸等等一系列的开放变动。这些两岸间的关务、税务等政策的变动,都在影响着往返台湾从事进出口商业的商人,因而,郊的形成与演化,也多少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从而重新形塑了这类商人团体的组织与功能。 如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鹿港《重修天后宫记》立碑,碑文后附捐款人除了当地“泉郊金长顺、厦郊金振顺、布郊金振万、糖郊金永兴、染郊金合顺、油郊金洪福、南郊金进益”之外,还列出了“泉厦郊行保合捐”等字样。所谓“行保”,指的是清乾隆朝以后采行于广州十三行洋商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一种保商制度,这一制度在广州起源于乾隆十年(1745年),历经嘉庆、道光年间略有变动,但保商“最初的任务,就是在海关的期间内,如果承买夷货的行商不能及时交纳税款,则由保商负责进口税的完纳。但是渐渐地,他对所保的船只及船上的人员之行为也负完全的责任”。这表明,郊与清代海关管理制度具有关联性。 在清代粮食平粜与港口船只管理政策上,郊在相关的“禁港”制度中扮演了颇为明确的角色。如《淡水厅志》在记载当地“商贾”有“北郊、泉郊、厦郊”等所谓“三郊”名称,即一并写道:“其米船遇岁歉防饥,有禁港焉。或官禁,或商自禁;既禁则米不得他贩。有传帮焉,乃商自传,视船先后到,限以若干日满,以次出口也。”(11)显然,郊已涉入米船“禁港”以及“传帮”等港务行政。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一封“鹿港郊商许志湖文书”的货函,即清楚写到鹿港当时“泉厦郊观此米局如此之变,致即传禁”。(12)也正因为有这些要与港口税务机构乃至地方政府打交道的地方,故有些在地方上影响力较大的郊,即在内部设有专门的“稿师”,聘请“主稿行文先生一名”担任此职位。(13)同时,有时为了让更多成员轮流应付地方政府交付过多的行政事务或承担的公费支出,郊商也要更密集地抽签,如台南三郊在同治元年(1862年)即由每年抽签轮流董事一年,改为“十三家轮值,每次一月”(14)。这种“稿师”与抽签轮值董事的制度显示,郊在演变过程中日益显然的官方职能色彩。 台湾各港郊中,公产多有设置。以台湾府城为例,当地商人在十七、十八世纪之间仍只是捐建庙宇,并未要公开成立“郊”。如“水仙宫”这个后来与台南三郊关系十分密切的庙宇,“在西定港口。开辟后,商旅同建,壮丽异常”。这栋“壮丽异常”的庙宇,在当时地方人士看来,仍只是“商旅同建”,并未视其为邻的专属建筑物,但后来的发展却使水仙宫逐渐成为台南三郊的专属建筑物,甚至专门辟出一块空间供做台南三郊办公之用。公产对郊确实至关重要,公产的捐集、开支却又与苏州的会馆、公所有所区别,它更依赖于郊内部的相互信任,不需要立碑记录,或者出版征信录加以介绍。 在“郊”之外,清代台湾由商人捐建的“会馆”也不乏其例。如在台湾府城,即有粤东人士创建的“潮汕会馆”(建于雍正七年1729年)、两广商民捐建的“两广会馆”(约建于光绪元年1875年)、福州商民合建的“三山会馆”、浙江宁波造船业者捐建的“浙江会馆”。在彰化县城,也有“汀州会馆”(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三山会馆”(建于同治七年1768年);在鹿港,则有官兵与绅商合建之“金门馆”(建于乾隆五年1740年)、泉州郊商合建的“泉郊会馆”、以及厦郊郊商合建的“厦郊会馆”;在澎湖,则有商人于当地水仙宫内附设了“台厦郊事业会馆”;在淡水,则有“汀州会馆”(约建于道光三年1823年)。上述11个会馆里,除了一座“潮汕会馆”以及两座“汀州会馆”(各位于彰化与淡水)这三座会馆,并未表明记载是否为商人捐资兴建之外,其余会馆都与商人有关系。特别是台南的“浙江会馆”、鹿港的“泉郊会馆”、“厦郊会馆”以及澎湖的“台厦郊实业会馆”,其与商人的关系都十分密切。虽然清代台湾商人团体以“会馆”命名者的数量,少于同时代的苏州,但还是有一些商人团体将其专属建筑物命名为“会馆”。 以上所述,显示福建商帮组织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不过,他们虽因为各自面对的政策环境、社会形势和各自处境而有所不同,功能也各有侧重,但均走过了自发、壮大到进入官府系统的过程,“官民相得”的趋向是较为明显的。 近代福建商民散居海外,却建构起了一个环中国海闽籍商民跨国贸易社会网络。往台湾的移民先是单身男子为主,道光以后转变为父子、兄弟、携带眷属,甚至家庭、家族支房整体移民的转化。其次,先行移民更带动乡族、家族成员的后续移民,形成移民链。他们移居到新地区,继续以血缘与地缘纽带凝聚起来。 首先,通过合伙制建立商业联系。大多数商人可以兼营垦殖、商业、渔业、航运等等,网络规模与效益均由此得到彰显。 其次,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活动、文化娱乐活动,可以扩大商业网络规模,通过联姻、与官方合作等方式,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据林玉茹研究,竹堑的福建商人时常与地主、士绅一道,捐资修桥、铺路、筑亭,设立义冢、义渡、义仓,资助养济院、育婴堂、回春院等慈善机构,捐建文庙、考棚,或是捐献学田、儒学公款、义塾仓谷,而且还通过本人或家族成员进入仕途,充当保人、参与维护治安、参与地方公共工程建设、参与街庄自治事务等多种方式,与官府合作,并且建构了多种多样、联系紧密的婚姻圈,由此构筑起竹堑在地商人极其有效的社会网络。 再次,参与、主持所在地的祭祀圈、信仰圈活动,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从遗存至今的碑文看,商人不仅是历次修建寺庙的主要捐献者,而且还按营业额“就本抽分”,或捐资建置寺庙田产、房产,以其营运所得,构成寺庙日常开支(添置香油、购买斋粮、举办祭典等)的主要来源。更重要的是,商人还出任寺庙管理组织的各种要职,积极参与寺庙修建的组织、寺庙产业的管理、维护寺庙的秩序和环境以及主持祭祀活动。(15) 三、近代海外各地的福建地缘性商人组织 近代以来,尤其是小刀会起义失败之后,闽商由上海部分退却,大量转圜至于南洋、台湾。在环中国海各地建立起了一个华人跨国网络。 晚清以降,福建商帮是活动区域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支力量。除中国大陆沿海和台湾各主要口岸外,海外则以菲律宾的马尼拉、宿务,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槟城、怡宝、吉隆坡、新加坡(海峡殖民地),印尼(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爪哇、三宝垄、泗水、望加锡以及日本的长崎、神户、福冈、下关为主要活动场所。 清咸同以后,闽商一直借助血缘、地缘纽带,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合伙经营、家族经营以及乡族经营等激发他们建立起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空间。 泰益号文书显示,祖籍福建金门的陈世望出身于一个“累世经营贸易”的商业世家。其曾祖父在乾嘉年间便从事中日间的海上贸易。其父陈国梁(发兴)于道咸年间,开始从事中日贸易,咸丰十一年(1861年),陈国梁与7名福建同乡合资建立了泰昌号商行,主要从事进出口批发代理业务。泰昌号创立初期,其账簿上尚无以交易商号登录的交易物件,但已登录了160名交易者的名字,大多为其福建同乡。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仅就该行残存的账簿来看,有交易记录的贸易客户已有96家,散布于日本本土的长崎等地(56家),中国台湾的营口(4家)、天津(3家)、烟台(5家)、上海(12家)、厦门(2家)、香港(2家)、台北(2家)以及新加坡(3家)和海参崴(4家)等地,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环中国海的商业网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陈国梁脱离泰昌号,独资创办泰益号商行,并把业务交给其子陈世望。从残存的泰益号账簿来看,泰益号商行在其创建和发展初期,从泰昌号商行继承了散布于日本长崎和中国沿海的营口、天津、烟台、上海、厦门、台北及香港等地的30余家客户,并进而尽力扩展它的商业网络,尤其在台湾和东南亚地区。至清末民初,在台湾,泰益号计有贸易客户129家,其中台北58家,台南26家,基隆20家,澎湖10家,新竹6家,台中3家,东港3家,阿猴3家,打狗2家,凤山3家。在东南亚,计有贸易客户47家。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新加坡,有33家。其余的在巴达维亚有3家,槟榔屿有3家,泗水有2家,菲律宾有1家,霹雳有1家,婆罗洲有1家,地址不详的有2家。此外,在日本本土,因应由日本对外贸易口岸变动引起的旅日长崎华侨大多向神户迁移的新局面,泰益号商行也急剧扩展神户的业务,与22家商号建立了贸易联系。 据朱德兰教授的研究,泰益号所属金门帮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间的海产贸易中执牛耳地位,基隆瑞泰商行、三合和商行等多家台湾商行,就透过泰益号的精英网络从事海产品贸易。而何荣德等10家台湾商行则透过同样的网络,经营台湾大米、砂糖的出口贸易。在台北,则有源顺行、金联发商店、时春商行等台湾商行,同样经由泰益号经营网络,从事日本的海产品、台湾的大米、砂糖以及大陆的豆类产品、中草药材等商品的进出口贸易。由此可见,在日据台湾,占据台湾对外贸易尤其是对日贸易主导地位的情势下,福建商人和台湾商人共筑、共用的环中国海经营网络的变形及其功能的发挥。 当“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贝”时,沿海居民便竭力“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工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敛诸岛银钱货物百余万入我中土”(16)。海外贸易的高额利润赋予了福建海商的生命意义,他们在探索中不断扩宽商路。对海外贸易由畏惧到习惯乃至逐渐形成传统。设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新加坡福建会馆、兴安会馆,嘉庆六年(1801年)设于马六甲的福建会馆,光绪三年(1900年)设的兴安会馆等都是福建海商发展壮大的实物证据。 日本成为华人移入的重要国度。在1623年就有江西富商欧阳云台捐地兴建兴福寺,作为三江同乡(江西、浙江、江苏三省)祭祀与宴集的地方,接着当时在日本最多的福建商人也分别于1628年和1629年建立了泉漳帮的福济寺(俗称泉州寺)和福州帮的崇福寺(俗称福州寺),而人数较少的广东商人则一直到1678年才以铁心和尚开基的圣福寺(俗称广州寺)作为本帮聚会与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四帮寺庙被称作“四福寺”。 “四福寺”内各有设置,如兴福寺设妈祖堂,内祀天后圣母(两旁有千里眼、顺风耳二婢)、关圣帝君(旁立关平和周仓)以及大道公(又称三官大帝),福济寺则有青莲堂,内祀天后圣母、关帝和观音菩萨。崇福寺更有妈祖堂和关帝堂(即护法堂)。前者内祀天后圣母和大道公,后者祀关帝和韦驮、观世音。圣福寺有观音堂,同祀关帝、天后圣母和观音等。在佛庙中奉祀天后适应了当时日本崇佛教抑别教的国策,却又保持了乡土神的至尊地位,可以看做是会馆的早期形态。人们每年都举行天后圣母和关帝诞辰的活动,以增进同乡间的友谊。遇灾则对同乡实行收管、提供食宿。又为死者提供墓地或负责送回故里归葬,还对纷争进行调解、仲裁。后来三江帮在兴福寺创建了“和衷堂三江公所”,福州帮成立的“三山公所”也与崇福寺的运营相关,泉漳帮在原来的“八闽会馆”基础上改建为“星聚堂福建会馆”,广东帮于1874年创立荣远堂岭南会所,光绪十年(1884年)甲申改称广东会所。 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重建长崎八闽会馆碑记》中可见八闽会馆是日本华人会馆中建立最早的一所。其中说:“八闽会馆始建迄今殆百年之久。为我帮商族议公之区,良辰宴会之所,由来久矣。”(17)随后,三江会馆于1868年在长崎建立(18),另外还有岭南公所、三山公所的设置。在大阪、横滨、函馆都设有三江公所。在神户有广业公所、八闽公所,在横滨、神阪、函馆有中华会馆,这些都适应了华人商人要求团结的心理。在神奈川(即横滨),1868年,已有了华人的会议所,1887年,三江帮成立“三江公所”,曾一度吸收福建侨胞加入;1918年,福建籍华侨成立了“新兴福建联合会”;广东帮于1898年建立“亲仁会”,它网罗了广东帮的各界领袖人物,其下又按县籍不同而设有“三邑公所”(南海、番禺、顺德)、“四邑公所”(开平、恩平、新会、台山)、“要明公所”(高要、高明)。神户的福建商人先是成立了“建帮公所”,后又于1870年成立“八闽公所”,不久改为“福建商业会议所”,广东侨胞于1877年成立“广业公所”,后曾称为“神户广业堂”,又称“广东公所”,后扩建为会馆,三江帮的“三江公所”亦扩大为“三江会议公所”。在大阪,1882年,三江帮的华侨创立了“三江公所”,1916年扩大为“大阪中华北帮公所”。广东籍侨胞在1896年成立了“大阪广帮公所”,因其中有几家神户的广商加入,故亦称“神阪广东公所”。福建帮于1906年成立“福邑公所”,但不久解散。 1815年,在越南河内兴建福建会馆。1817年建立的《福建会馆捐题录》和《福建会馆兴创录》两碑,碑文中有32名捐款人姓名,董事王新合(晋江人)捐银1100两,名列榜首;捐款人中有同安县7人,龙溪县5人,晋江、诏安各4人,海澄3人,安溪2人,长泰、南安各1人,失载2人,共捐银3604两。(19)边河的关帝庙、福建会馆、广东会馆合称三大祠。在西贡,有光绪年间成立的福建中华理事会馆(即西贡福建公所),成立于清光绪年间,凡闽籍华侨均为该会馆成员,下属有福建义祠、福建学校、福善书院等。西贡还设有三山会馆(福州府人建,祀奉天后妈祖)、二府会馆(漳泉二府华侨所建,祀奉土地神)、温陵会馆(泉州府人所建,祀观音)、霞漳会馆(漳州府人所建,祀天后)。 缅甸多福建侨商,建有温陵会馆(1912年)、仰光三山会馆(1912年)、安溪会馆(1920年)、永定会馆(1921年)、瓦城三山会馆(1922年)、旅缅惠安会馆(1923年)和旅缅同安会馆(1927年)。 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前身是1828年由漳浦县人薛佛记和陈送率福建帮众乡亲建立的漳泉人公墓恒山亭,负责解决当时在新加坡的福建人的丧葬问题。1830年恒山亭设于石叻律,创建了大伯公庙,并设有董事,总理与值年炉主头家,每年相互选举或轮流充任。1839年,体现福建人乡土信仰的天福宫在直落亚逸街落成,祭祀妈祖,不久恒山亭也迁至天福宫,福建会馆日益成型。海澄人陈金钟从1840年开始成为天福宫的首任炉主,具有一定的凝聚力。1846年海峡殖民地(英国人建于1826年,包括新加坡、马六甲和槟榔屿)政府封他为太平局绅,反映了其作为联系中介的作用。恒山亭在发展过程中曾一度把服务和联络的对象扩大到当地所有的华人,但由于会馆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是福建人,因而福建的地域性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总体上看,近代以来,南洋地区是福建商帮的主要活动区域,华人会馆也主要集中于这一区域。但随着闽商足迹的进一步拓展,闽商会馆也逐渐散布到欧洲、美洲乃至澳洲等地。在荷兰,地域性的会馆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来自福建东部(福州、连江、长乐、福清等地)的新移民主要经营餐馆业,取得一定发展,从而建立起会馆组织。1998年4月,旅荷福建同乡联合会终于得以成立。 近代福建商人组织化倾向更加明显,其发展呈现出新的样态:传统的会馆、公所继续存在、时有兴建,且呈现出兴盛局面,这类组织既集中于省城福州,也在厦门、泉州、龙岩、建阳等地有所体现,还存在于闽商所流布的沿海各地和南洋地区,其旺盛的生命力彰显出传承中华文化的跨时代意义。 福建商人在其“所托足之处,类皆建有会馆,所以联商情而敦梓谊,法至良意至美也”。会馆成为福建商人形成群体力量的重要标志,各会馆的规约则大体揭示了福建商人发展壮大的奥秘。同治时期《汀龙会馆志·馆志序》中说:“或曰会馆非古制也,而王律不之禁者何耶?予曰:圣人治天下,使民兴于善而已,会馆之设,有四善焉,以联乡谊明有亲也,以崇神祀明有敬也,往来有主以明礼也,期会有时以明信也,使天下人相亲相敬而持之礼信,天下可大治,如之何其禁耶!”(20)可见会馆注重传统优良道德修养的维持,体现了通过自我管理实现社会有序的目标。 会馆多以“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而起,崇乡谊,敦信义是建馆的最初宗旨。会馆成了“劝诱德业,纠绳愆过,所以风励流俗,维持世教”的场所,明清福建商人以“诚”、“信”确立自己的形象,义利兼顾,以义兴利,因而开辟了商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福建商人会馆颇强调会员对会馆及其商帮的义务与责任,颇强调会首的“品行端方”与“办事公正廉明”,颇强调建立良好的商业信誉,亦颇强调团体合作、信息交流与急公好义、共同发展。会馆倡导一种团体精神与协作精神,也有利于商业活动中矛盾纠纷的协调和化解。会馆制定的规约往往亦旨在建立公平的商业秩序,建立起良好的商业信誉。 福建商人会馆在“团结商人,保全信义”的基础上,遇到“凡受国家法律有不完全之处,或贪婪官吏对于人民有苛酷之事件”,皆力求为会员争得“保全生命财产,判断曲直之权利”。有人说:“凡所以联乡情,敦友谊,求自治,谋公益者,皆不能不于会馆公所是赖。”(21) 福建商人会馆多设置义冢,为客死他乡者解除了后顾之忧,会馆经常举行祀神、演戏、过节等文化娱乐活动,通过会众集资达到增强会众凝聚力的目的,福建地域文化既奠定了在当地的地位,又实现了与当地文化的交流与互摄,如作为闽人乡土神的妈祖逐渐走出乡土神的局限,而成为全国通祀神,又如福建人的种烟植蔗培薯技术亦纷纷为当地所吸收,依凭于会馆的商人几乎成为地方文化的使者,遍布东南亚的福建商人会馆还多致力于教育,更为中华文化的弘扬作出了贡献。 台湾商人通过捐资纂修族谱,购置祭田,维护和加强与福建大陆家族成员的关系,通过捐资参与举办祖籍地的公益事业,兴办教育,提高在祖籍地的声望,通过合伙经营,建构基于共同经济利益的人际关系,通过参加或捐助祖籍地的各种敬神祭拜活动,维护和加强与乡民的关系。 通过两岸对渡,往来于台湾与祖国大陆的闽商在保持传统的会馆、公所等组织形态之外,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郊行”及“郊行会馆”,有效地整合了区域性、行业性的商人,显示了闽台贸易的特殊性与创新性。 在南洋各地、东亚各地、欧美乃至非洲各地,福建会馆鳞次栉比,彰显了近代福建商人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的强大能力。 “只要有商会通讯录,走遍世界都不怕”。近代闽商进一步组织化既使闽商相互间具有了一个颇具商业价值和情感联系价值的网络纽带,同时也使闽商能联合、爱慈善、善经营、敢冒险的集体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通过闽商组织凝聚成的这种闽商精神迅速转化为闽商的文化财富和文化符号,护佑着闽商走向更大的辉煌。 由此我们认识到:“闽帮”走四方,靠的是“无远弗届”的开拓精神、义利兼顾的职业道德以及诚信无欺的人格面貌,这不仅使他们创造了福建商帮历史上令人瞩目的辉煌,亦必将激励当代,走向未来。 ①黄福才、李永乐:《论清末商会与会馆并存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清代康雍干巴县档案选编》(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③民国《临海县志》卷十一《祠祀》。 ④周宗贤:《血浓于水的会馆》第七章,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1980年。 ⑤傅衣凌:《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见《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第59页,民国三十七年艺声图书印刷所版。 ⑥⑦同治《汀龙会馆志》卷一,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由旅潮长汀人康晓峰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⑧蒋毓英:《台湾府志三种》卷一,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页。 ⑨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117-127页。 ⑩(15)林玉茹:《清代竹堑地区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动网络》,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179、189、185页。 (11)陈培桂:《淡水厅志》卷十一,《风俗考》,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3年,第299页。 (12)林玉茹、刘序枫编:《鹿港郊商许志湖家与大陆的贸易文书(1895-1897)》,第160页。 (13)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编、林真译《台湾私法·商事编》,页12:台湾府城“三郊议事公所”所设置“稿师”规章。 (14)石万寿:《台南府城的行郊、特产、点心》,私修《台南市志稿·经济篇》,第80页。 (16)《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三。 (17)(18)宋越伦:《留日华侨小史》,中央文物供应社,1953年,第13-14,17-18页。 (19)周均美:《中国会馆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年,第223页。 (20)同治《汀龙会馆志·馆志序》。 (21)《中国经济全书》第二辑,宣统二年(1900年)版,第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