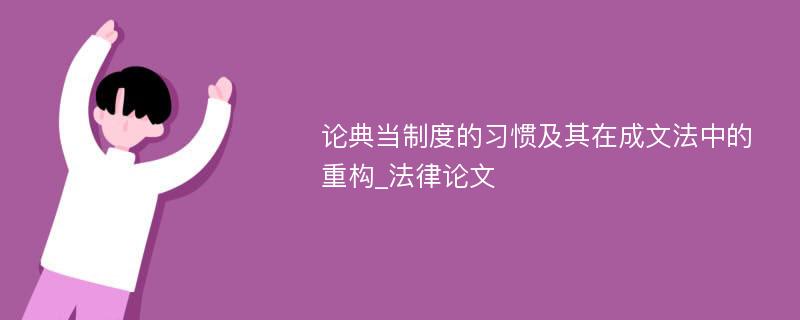
论典制习惯及其在成文民法上的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文论文,民法论文,重构论文,习惯论文,论典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14(2008)01-0095-(08)
伴随着“西法东渐”,典制历经了由习惯到制定法、由纯然的东方习俗到与西来的民法制度相融合的转变。直至我国《物权法》的颁布,典制再次与作为制定法的民法相互分离,而回归其纯然的交易习俗的性质。在这个跌宕起伏的过程中,典制历经了诸如“典权的性质”、“典权在成文法上的废存”等一系列的争论。这正如梁治平先生所指出的,“(对于典权)诸多此类的争论,既表明典之制度的复杂性,也暴露出现代民法制度在将一种异己物(就民法原本出于欧洲之历史、文化与社会而言)完全纳入自己体系时的无力”。[1]94正是因此,《物权法》将典权排除于物权的制定法体系之外,使之与制定法的再次分离,更是为典制平添了一分神秘感与诱惑力:典制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制度?蕴涵于典制当中的交易理念究竟是什么?典制“当初”是如何被纳入到民法的“用益物权”体系之下的?在《物权法》颁布之后,对于作为交易习俗的典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所有这些盘问,均离不开这样一个事实,即典制是在我国“本土”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始终与其所赖以产生、发展的社会与法律观念息息相关。因此,对于上述问题的阐释,应当在历史以及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下来进行。就此以观,《物权法》的颁布,使得典制摆脱了长期以来被制定法强加于其上的“用益物权”的性质,这恰恰为我们考察典制的“本来”面目,提供了契机。
一、罗马法与中国固有法:作为他人物上支配前提的物之归属观念的比较
中国的固有法律思想,很早就产生了“归属”的观念。荀子有云:“礼起于何也?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则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2]礼论然而,这个旨在实现“定分息争”之社会目的的归属观念,在法律上通过“产”、“业”、“财”等概念来表明对于物的拥有,[3]83而始终未能抽象出一个类似于罗马法上的“所有权”的概念。正如日本学者寺田浩明所指出的,传统的中国“土地法秩序中成为交易对象的并不是具有物理性质的土地本身,而是作为经营和收益对象的抽象的土地,即‘业’”。[4]302因此,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上,“归属”观念乃是以“物之支配”来表述的,它是通过“我可以独立地支配此物”来表明“此物归属于我”。
与古代罗马法进行比较,在罗马法早期,法律观念上也存在着以“物之支配”来表述“物之归属”的思维模式。以役权为例,罗马法上的役权是由土地公有制之土地使用规则演变而来。“罗马古时,土地属于村社所有,分给各个父权制大家庭耕作后,各个土地使用者为了耕种的便利和其他需要,对已分割的土地,在使用时仍保持未分割的状态。”[5]390在抽象的所有权观念产生之前,以“可得支配特定之物”为特征的耕地役权,是以“共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当时为了土地耕作之便利,对于“通行的道路,流水的水沟,利用者可享有共有权。故耕作役权很早便被列为要式移转物。”[5]390随着抽象的所有权观念的产生,“所有权”这一概念被赋予了独立于“物之支配”的“归属权”的内涵,成为“对物最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in potenza)主宰”。[6]194由于抽象的所有权概念摆脱了物上具体支配形态的束缚而得以独立存在,物之支配便丧失了其原先的确定物之归属的准据意义,而仅仅被视为所有权的“权能”。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这种“权能”所表彰的具体的物之支配,可得与抽象的所有权相分离,且这种分离并不会影响到所有权本身质的规定性,“凡我所有之物,无论我是否现实地支配之,该物均归我所有”;另一方面,所有权权能与所有权的分离,导致了“他物权”概念之产生。如乌尔比安指出的,“使用权(usus)属于一个人,无使用权的收益权(fructus sine usu)属于一个人,而所有权(proprietas)属于另一个人,这是可能的。比如,某人有一块土地,他将使用权遗赠给铁裘斯,后来其继承人又通过遗赠或以别的方式将收益权给予你。”[7]147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制度上“所有权”与“他物权”区分的形成,有赖于法律观念上“归属”与“支配”的分离,即“抽象的所有权”观念的产生。相应的,在未能萌生出这种抽象所有权观念的社会,由于不存在一个超越于物之支配型态之上的、抽象的“物之归属”观念,所以其往往以具体的物之支配方式来确定物之归属,即凡得以一定方式支配于物者,均为物的“所有者”。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基于一个物可得由若干人实施支配的事实,一物之上可得并存若干“所有者”。抽象的物之归属观念的阙如,又使得各个“所有者”之间支配权利呈并列关系,而不会产生类似于“归属——支配”的原生与次生观念。例如,在古日耳曼法上,“于一个不动产上,恒有数个收益物权,同时并存。每一物权,皆各有其Gewere(即物之管领力——笔者注),故于同一不动产上,自不妨有数个Gewere,同时成立”。[8]55无独有偶,我国明清时期土地租佃当中的“一田两主”,亦是这种依托于物之具体支配的归属观念的典型代表。
所谓一田两主,是指“把同一地块分为上下两层,上地(称田皮、田面等)与底地(称为田根、田骨等)分属不同人所有……底地所有人的权利,是每年可以从享有土地使用收益权的上地所有人那里收租……而且,上地底地的所有人,各自处分其土地时,相互间没有任何牵制,这是通例”。[9]411“永佃权产生之后,地主为了保证地租来源的稳定,一般不允许佃农把佃耕的土地自由转让……但是,随着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私相授受’(私下转佃)日益成为不可变更的既成事实……一旦永佃权的自由转让成为一种‘乡规’、‘俗例’,它就具备了一定的合法性”。[10]100于是,“一田两主”的概念,便为这种合法性,提供了依据。由此可以看出,“一田两主”所采用的“习惯法律”技术,是通过将承佃人塑造为“土地拥有者”的方式,以实现其自由转佃之目的的。为躲避“一物不二主”,便将土地一物二分,使出佃人与承佃人各自成为“上地”与“下地”的拥有者,从而达到“各自处分”、“互不牵制”的效果。进一步分析可见,在出佃人与承佃人之间的租佃关系中,后者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其地位仍然是耕种他人土地的用益者,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舍此不能解释“上地所有人”拥有可得向“底地所有人”收取地租的权利。既然承佃人仍旧是“他人”土地上的耕作者,那么如果从罗马法的视点以观,其有无另行转佃的权利,这仅仅是其“权能”大小的问题,而无需将其与“物之归属”挂钩。但是,由于我国固有法律观念上不存在抽象的“所有权”概念,因而无法在“用益物权”的概念之下,将“物之支配”分离于“物之归属”的概念之外。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当他人在物上存在着足以对物主构成限制的“支配”时,我们的祖先唯有通过使之成立“物之归属”的方式,以表述这种支配的存在。
中国古代社会的这种名为“取得他人之物的归属”,实为“就他人之物而支配”的情形,并非仅限于对于他人之物的用益。事实上,在就他人之物为债权担保的场合,这种情形仍然存在。与他人之物的用益相同,由于我国固有法律观念上不存在“担保物权”这样一种可以与“所有权”并行不悖的权利的概念,因此欲在他人之物上获得债的物上担保的利益,就仍然不得不通过取得物之归属的方式进行。而要取得物之归属,则发生在担保设定人与债权人之间的那种交易,就不得不依托于“买卖”的形式。然而,与普通的买卖不同的是,在以担保为目的的“买卖”中,出卖人其实并无永久性的让渡物之归属的意思,这就使得债务履行后的“回赎”成为当事人之间必不可少的约定,由此便形成了我国传统社会交易中的“活卖”。
二、“活卖”与“出典”:以物之归属为载体的物上担保
所谓“活卖”,是指附有“回赎”约款的土地买卖。据学者考证,这种交易形式最早见于六朝,[11]311自明代以来,活卖交易进一步成熟。及至清代,其开始由民俗习惯上升为实定法制度。[10]30-36在明代,土地的“推收”(国家确认的土地归属移转手续)由元代的“依例投税,随时推收”[12]户部变更为在“大早黄册之年”,即每十年造册登记各户丁口财产时,同时办理土地推收。[13]卷六八土地交易与推收过户之间存在的时间差,在客观上给予了当事人在办理推收之前,变更乃至解除土地交易的回旋空间。例如,“卖主在推收之前,可以借口卖价不敷要求加找田价,或者借口无从办纳钱粮要求加贴,或者由于经济情况好转要求回赎,而买主在推收之前,又可以把田地转卖给第三人等等”。[10]32可见,这个回旋空间的存在,导致了“活卖”与以“一卖千休”、“寸土不留”为特征的“绝卖”之间的分离愈加明显,从而使当事人之间“非永久性让渡物之归属”的“买卖”交易成为可能。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为“适应活卖与绝卖分离的发展趋势,在法律上明确绝卖与活卖的不同权利义务,推广使用活卖文契与绝卖文契。”[10]34其中,绝卖为专用文契,“契内都要声明‘听凭买主永远管业’,或者进一步声明‘永无找赎’、‘永断瓜葛’之类,以表示卖主与土地切断关系”。[10]34相应地,活卖文契则“契内必不言绝卖,切往往有回赎(或定年限或五年限)字样”。[1]95-96至此,绝卖、活卖不同的权利义务的确立以及各自适用文契的推行,标志着当事人“暂时性”移转物之归属的意思,可以通过类型化的交易形式,得以实现。
“活卖”与“绝卖”的两分,赋予了我国传统的买卖交易以更为广泛的经济意义。由于买卖的目的并不是局限于(如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物之归属的永久性地移转,因而“活卖”具有了愈来愈鲜明的“工具性”意义,该意义使得当事人可以在买卖的框架之下,实施并无买卖(绝卖)意思的经济交易——这就是“借买卖之名,行担保之实”。详而言之,在我国古代的农业社会,土地是人民生计的根本保证。“尽管明清以降民间土地交易极其频繁,但是其性质始终不是商业性的。在绝大多数场合,出卖土地无非是因为无食、乏用、粮钱无着等,而这意味着,出卖土地之行为往往是不情愿的和无可奈何的。在此情形之下,其售卖价格虽低但是可以赎回的活卖便可能成为一种可选择的买卖式样而与绝卖并行不悖。”[1]98由此可以看出,活卖中出卖人出卖其物,意在价金之取得,即筹措款项的目之实现;而“回赎”约款的存在,则表明出卖人无意于永久性地保留其所得之价款,而有日后“返还”之考虑。因此,该项价款事实上具有“借款”的性质。进而,买受人所取得的“可得回赎”的物之归属,其意义就在于当“回赎”事实没有发生时,买受人手中的“所有权”,可以使其安居“业主”的法律地位:这不但可以对买受之物实施“自主占有”下的支配,而且可以在出卖人无力还款时抵消该项交易的风险,即发挥担保作用。
以买卖之名,行担保之实,是我国传统习俗中一个司空见惯的做法。例如,我国固有法制中的“抵押”,即所谓“指地借钱”、“靠产揭钱”,其最终的债之担保目的的实现,便是依靠“买卖”的形式。详而言之,在民间习惯上,“指地借钱”对于债权人的保障,仅仅在于当债务人无力清偿本息时,债权人可以“将其田地收管,收租抵利”。[1]104至于其余未偿的本息,债权人是否可以在所抵的土地上,有优先受偿之权,则各地习俗不同。[14]302、344与此同时,在债务人同时存在若干债权人,并因欠债过多而无力偿还的场合下,民间习惯上还存在着类似于破产制度的“尽产摊帐”之说,即将债务人所欠债款,在各个债权人之间分摊,在后者部分受偿的情况下,消灭前者债务。由于“抵押权”人优先受偿的地位并不稳定,倘遇债务人“摊帐”,其利益常常遭受损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国习俗上的“抵押”并无严格的“优先受偿”的效力,因此要使得债权人的担保利益具备“物权”意义的保护,就不能不寄托于债权人对所抵土地的“归属”的取得,即通过“买卖”的名目来实现,这就是我国清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抵押而预立卖契”的缘由。在交易实践中,以买卖形式实施抵押的方式多种多样,其共同之处在于,在债权债务关系发生时,当事人订立绝卖文契,但同时以债款本息的清偿作为限制该绝卖契约发生效力的条件,这个条件或者记载于浮签,粘于卖契之上,谓之“死约活签”;或者载明于卖契最后,谓之“死头活尾”;或者在卖契之外的借据上另行书写,谓之“死契活抵”,等等。[1]102可见,这种“死”中有“活”的卖契,其实仍是“以绝卖作为债务不履行的结果”的活卖,而借活卖以行担保的交易习惯,在“预立卖契的抵押”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活卖与绝卖相互分离,促成了活卖与典的融合。由于活卖中当事人意在担保,而没有立时绝卖的意思,所以当事人的这种有别于绝卖的意思,就有可能用另外一个与绝卖相距更远的概念来取代,这就是“典”。典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是一种借债的担保方式,其所具有担保的意义,从长期存在的“典”与“质”、“当”等词的并用习惯上即可得到反映。[15]然而,典之概念的存在,事实上并不意味着我国传统法律当中“担保物权”观念业已产生。换言之,典制上的债权担保,其实并不是建立在于物之归属之外直指物之交换价值的“他物权”观念的基础之上,而是以“活卖”的机制作为担保作用发挥的依托——与“预立卖契的抵押”相同。因此,明清时期的典制,几乎是活卖的再一次表述——“回赎本就活卖而发生,而出典人备出原典价以收回典产亦袭用此文字。土地买卖中间环节如找贴及相应之契式,也被借用来表述从典到(绝)卖各种环节的契约关系。”[1]100而且,“典与活卖混同,契纸上只有微小的区别,有的在卖契文末写上典字,有的文字与卖契一样,但中人不画押,不加注意,是难以辨认的”。[10]42这就是我国明清时期极为盛行的“典卖合一”的交易形式。“典卖合一”习俗之所以能够盛行,仍与我国传统的“归属”观念密切相关。如前文所述,我国传统的“归属”观念,乃是以“可得对物实施支配”作为内容的。从这个观念出发,债权人因典契所得之可回赎的“典权”,其实与因活卖契据所得之可回赎的“所有权”,在交易的效果上并无不同①。因此,债权人因此所得到的对于债务人移转之物的支配范围,是一样的,即都是以“业主”的支配范围实施“管业”——由此便解释了在典之关系中,为什么承典人会拥有远远超出大陆法系民法上用益物权人的,几乎不受限制的支配空间的原因;另外,典与活卖在官方的手续上的趋同,也强化了其两者之间的同质性——“订立活契时,地权不必推收过割,卖主仍旧承担粮差义务”。[10]273而明代刊刻的民间日用杂书,如《家礼简仪》,便在卖(买)田契式后说明:“如典契,亦仿此式,不用割除。”[10]42
然而,同时应当看到,由于“典”在概念上脱离了“卖”的范畴,所以进一步强化了活卖中当事人有别于现时绝卖的意思,并使得“典”与“绝卖”在概念上的对立,更加明显。这不仅使“重孝而好名”的中国人可以免受“出卖祖产(哪怕是活卖)”的舆论指责与心理压力,而且因典与绝卖的进一步对立,出典人的回赎权备受重视。在习惯上,未约定期限的典权,只要典契上未曾载明“到期不赎,视为绝卖”的字样,出典人可以随时回赎;“甚至业经约定典期者,至典期届满后,原业主无力回赎时,其当事人间之典权关系,依然存在,毫无影响,迨而后原业主回赎时,典主不得予以拒绝,以至有一典长至百年以上者”。[16]1026民间“卖在一朝,典在千年”、“一典千年活”等典制谚语,均因此所生。
三、“用益物权”与“即取得所有权”规则:民初制定法中的典制
清末民初,我国开始继受大陆法系民法,并掀起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法典化浪潮。在这个浪潮中,典制经由“民律一草”、“民律二草”以及民国民法典,开始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演变,并且首次接受来自于西方法律观念的审视与改造。在这个我国固有习惯与西方成文法制的碰撞过程中,典制逐步偏离了其原有的运行轨迹,并在成文民法中被加以重构。
第一,“典”与“卖”被截然分开。随着大陆法系民法“所有权”观念的承袭,我国传统习俗中的“买卖”(包括“绝卖”与“活卖”)被看作是西洋民法中“抽象的所有权”的变动原因。换言之,从抽象的所有权观念以观,无论是“绝卖”还是“活卖”,其首先引起的应当是“所有权”的转移。与此同时,本来与活卖具有相同性质的典,却基于其不同于“卖”的概念,以及当事人对立于立时绝卖的意思,被赋予完全不同于买卖的“另一种”后果。显然,在严格区分“自物权”与“他物权”的民法观念下,这种支配于物上的权利既然不是因买卖所形成的“自物权”,那么它就应当具有“他物权”的性质。由此,“典卖合一”的习俗在成文法中被割裂。
第二,由“不动产质”到“用益物权”。基于典与卖的完全分离所引起的问题就是,作为“他物权”属性的典权,在大陆法系民法担保物权与用益物权两分的他物权体系中,应当处于何种位置呢?在清末民律一草的制定中,负责物权编起草的日本学者志田钾太郎与松冈义正博士,认为中国传统之典权,性质为移转物之占有的不动产担保物权,遂在民律一草中,以“不动产质”来表示典权。民国初期的民律二草,物权编的起草者黄右昌教授复于不动产质之外,另行规定典权制度。[17]136及至1929年,“民国民法典”《民法物权编》立法理由中,明确说明民法典在质权中将仅设立“动产质”及“权利质”,而不动产质将以典权取代之。同时,《民法物权编立法原则》第10条规定,“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而为使用及收益者,为典权人”,[18]770、774从而奠定了民国“民法典”将典权定位为用益物权的基础。
第三,限制典权的期限。我国典制习俗,在典权未约定绝卖条款时,回赎期限不受限制,故有“典在千年”之说。回赎权的永续性,使得“找贴”成为了“典”与“绝卖”之间的必经环节——未经找贴,基于回赎权的习惯上永续性,典物之绝卖就不能发生。“实际上,活卖值贱……很多都不只加找一次,有二找、三找而未断的,有经过五次以上找断后又要求再找的,江西雩都便有‘十找九不敷’之说。”[10]35-36典制习俗中对于典价与(绝)卖价之间差价的强调,本质上就是对于“绝卖的发生,必须要以出典人最终形成永久性地让渡产业的意思”这一判断的强调②。然而,如此的典期与屡找不绝的找贴,不利于社会关系的稳定,也易生纠纷。因此,自清代以来的制定法,都对于找贴采取了限制的态度。然而,民初“民法”对于找贴的限制方式与清代制定法则迥然有异。
首先,从回赎权的限制条件来看,乾隆十八年间,清政府订立条例规定:“自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前,典卖契载不明之产……若远在三十年以外,契内无绝卖字样,但未注明回赎者,即以绝产论,盖不许找赎。”[19]卷九在这里,“盖不许找赎”的后果,系以典契“未注明回赎”为条件,因此该项规定尚有“依合同约定推知当事人的意思,并以此推知结果为依据做出立法处理”的立法思想。比较而言,1929年民国“民法典”《民法物权编立法原则》第13条规定:“出典人于典期届满后,经过两年,不以原典价回赎者,典权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权。典权未定存续期间者,出典人得随时以原典价回赎典物,但自出典后,经过30年不回赎者,典权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权。”[18]773可以看出,民国立法乃是将“到期不赎”作为典权人“即取得所有权”的唯一条件的。至于当事人是否有“回赎”或者“绝卖”的意思,一概在所不问。于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成为了典权人的“即取得所有权”的唯一依据。
其次,从“找贴”之于“绝卖”发生上的意义来看,依清代例律,“如契未载绝卖字样或注定年限回赎者,并听回赎,若卖主无力回赎,许凭中公估,找贴一次者,另立绝卖契纸。若买主不愿找贴,听其别买,归还典价”。[19]卷九在这里,在典契上注明有“回赎”约款的,依清律并不能因典期届至而自然发生绝卖。因此,承典人欲取得典物,必须通过“公估找贴”后的“绝卖契纸”。进而,倘若承典人不愿找贴,则“绝卖契纸”无由产生。这时,承典人只能将典物“别买”他人,以卖价受偿典价——在卖价高于典价时,超出部分出典人尚能收取。比较而言,民国“民法典”对于找贴亦有规定,其第926条规定:“出典人于典权存续中,表示让与典物之所有权与典权人者,典权人得按时价找贴,取得典物所有权。”然而,民国“民法典”所规定的“找贴”,是以倘若在典期内无法达成“找贴”合意,则承典人一概“即取得所有权”的后果为背景的——那么承典人既然可以无需找贴便依法律之强制规定“即取得所有权”,其又何必与出典人达成找贴合意?事实上,民间典制中的“找贴”,在此已经名存实亡。民国“民法典”在典权制度中所采取的此种立法手段,无疑是立足于“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强化社会经济秩序,以期“快刀斩乱麻”之功效。然而,通过与清代相关立法的比较,我们还是能够发现,立足于本土习惯的清代立法,其是在典制固有的交易理念的基础上,对典制加以规制;而民初立法则是立足于西方民法观念,对典制所进行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传统典制中的规则内在交易观念被加以剪裁,以期与“民法”的结构与观念相“适应”,甚至典制中所蕴涵的意思自治——其核心就是“交易的结果取决于交易者的意志”——在成文法之法定主义观念下,亦被予以忽略。事实上,这种立法价值趋向在民国初期的民事立法活动中极为盛行。在民律二草制定之时,政府修订法律馆总裁江庸曾就前清民律一草之所以必加修订,提出理由谓“前案仿于德日,偏重个人利益,现在社会情状变迁,非更进一步以社会为本位,不足以应时势之需求……”[18]748及至民国民法典民法总则制定之时,当时中央政治会议所厘定的立法原则也云:“自个人主义之说兴,自由解放之潮流,奔腾澎湃,一日千里,立法政策,自不能不受其影响。驯至放任过甚,人自为谋,置社会公益于不顾,其为弊害,日益显著。且我国人民,本以自由过度,散漫不堪,尤须及早防范,籍障狂澜……”[18]756由此不难理解,在通过制定法对于典制习俗进行改造时,立法何以对于个人利益的保护至为不足,哪怕为秩序之追求而牺牲即使是大陆法系民法亦极为看重的“不动产所有权”也在所不惜的原因。
四、《物权法》背景下的典制:“所有权担保”的实现方式
将典权认做是用益物权,其实是在大陆法系民法的逻辑框架之下,典与卖绝对分离的结果。详言之,当典与卖割裂并相互对立之后,典权人对于典物的支配地位,便由原先“典卖合一”之下与买受人并无不同的“业主管业”,变成了“非所有人的物之支配”。进而,原先无非是典权人作为“业主”的“管业”范围,自然被理解为“他物权人”的“用益权能”。与此同时,当典跻身于西方之民法物权体系之后,其所固有的“担保”意义开始受到“典型”担保物权观念的质疑,即承典人“不能”如民法的“债权人”那样,“请求”出典人偿还典价——典制习俗上“典价低于(绝)卖价”的事实在此被忽略之后,以实践(而不是法理)为出发点的习惯法之形成过程中的“不必”,被理解为成文法上的“不能”。于是,典价之返还不再被视为债务之履行,进而典权被赋予了“主权利”的性质——典价之返还可以引起典权之消灭这个明显的事实,进而也被忽略。经此改造之后,制定法上的典之交易,便如我们今日所见到的那样,成为出典人与承典人就对方不动产和典价的“相抵利用”[20]了。
将传统典制纳入西方民法“用益物权”的体系,其牵强的痕迹是显而易见的。从“用益物权”的角度来观察,既然典之关系是出典人的典物,与承典人的典价之间的“相抵利用”,那么当事人于未来“相互返还”从对方取得的财产,就应为“相抵利用”交易当中的应有之意。由此出发,不仅出典人应有权通过返还典价而要求对方返还典物,而且承典人亦应有权通过返还典物而要求对方返还典价——这仍与典制中仅出典人回赎之权的特征不相符合。退而言之,即使通过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强令仅有出典人有权回赎,那么在出典人未能回赎时,承典人也只能基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法理,留置典物、拒绝返还,其又如何能够就此取得典物的所有权?再退而言之,将承典人取得典物所有权后果,与当事人“以用益他人之不动产为目的”的意思隔绝开来,而再次归诸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从而赋予承典人的典物取得以“原始取得”的性质,那么就典制的当事人双方而言,其典权交易的最终的结局,或是重新收回典价、典物,或是取得、丧失典物归属。无论何种结果发生,其作为典之交易的最终结局,必定对于承典人的交易目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既然如此,典之交易又如何能概括为“以用益他人之不动产为目的”的交易?
上述的“典制的用益物权化”所存在的内在矛盾,乃是无视典制固有担保意义的必然结果。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向对方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便将以丧失某物作为代价时,无论这种交易以何种面目出现,也无论对方是否可得对该物进行用益,该物实质上就是对方取得该笔金钱的担保物,此为交易之公理。如前文所述,典权交易作为在出典人在“粮钱无着”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典价的授受具有鲜明的“借款”意义;而以典价之返还为内容的回赎,本质上即属于“借款之清偿”。相应的,倘若出典人不回赎典物,则听凭业主继续管业,乃至最终丧失重获典物的机会,这无非是典权“担保效力”的表现;至于出典人回赎典物,则典权消灭,其则为“主债权消灭,担保权消灭”的担保“附从性”的表现罢了。进而言之,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典制的担保机理系在于“让与担保交易”,即通过财产的“活卖”,使得债权人(典权人)取得担保物(典物)的所有权。由此,担保物(典物)便脱离了债务人(出典人)责任财产的范围,不再作为担保人(出典人)的一般债权人之债权受偿的物质基础。这样,无论是出典人返还借款(典价)而交还典物,还是出典人到期不赎而继续典物之用益,典权人总能够基于对典物的独占而立于“不败之地”——前述我国传统交易习俗中,债权人为了避免债务人“尽产摊帐”的风险,借“活卖”之名以行担保,并以“绝卖”作为债务不履行的结果的交易习俗,亦是出于同一机理。综上,通过对典制担保机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传统典制并非是一种“用益物权”,而是一种“所有权担保”的形式③。
典制作为一种以“所有权担保”为内在机制的担保交易,意味着我国《物权法》没有规定“典权”制度的事实,并不代表典制从此将在我国的社会经济的舞台中销声匿迹。相反,典权制度在《物权法》中的阙如,意味着典制从此脱离了物权法定主义的强制,自民初以来即被强加于典制之上的“用益物权”的桎梏终于得以解脱,这恰恰为典制内在的“所有权担保”机制的发挥与实现,开拓出法律空间。
首先,在《物权法》没有规定典权制度的背景下,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典权交易”仍然为法律所认许。在当事人的担保交易中,倘若出于某种特殊需要,如当事人意欲使债权人占有作为不动产的担保物,并且以对该物的用益冲抵债款利息,那么“抵押”这种典型担保即无法满足当事人的利益需求。此时,“典权”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交易形式,可以弥补物权法定主义之下我国物权立法“用益质权”上的立法空白,并为实现当事人的担保交易目的提供法律上的途径。
其次,在《物权法》没有规定典权制度的背景下,以“所有权担保”为内在机理的典权交易,获得了回归传统上“典卖合一”之交易方式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典权交易的合同在《合同法》中将属于一种“无名合同”,因而应当适用“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合同法》第124条)。又由于“交易习惯”可以成为合同解释的依据(《合同法》第61条),所以从传统的“典卖合一”的习惯出发,典权合同可以被理解为当事人之间具有“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这就意味着,在《合同法》分则中,与“典权合同”最相类似的有名合同乃是“买卖合同”,因而典权合同可得比照“附回赎特约的买卖合同”来类推适用,并因而可作为所有权变动的依据;进而,因典权交易而产生的典权,遂获得了“负担回赎权的所有权”。如此一来,在以典制为依托的不动产担保交易中,承典人广泛地支配典物的权利,能够从“自物权”的角度得到说明,这使得典权人以其对典物的用益支配抵销债款之利息成为可能,并可与抵押形成“互补”之势。相应的,由于典物脱离了出典人责任财产的组成部分,不再作为出典人的一般债权人受偿之担保,典权交易的担保目的也因而得以实现。
再次,在《物权法》没有规定典权制度的背景下,以典制为依托的“所有权担保”交易,克服了一般让与担保中“担保权说”与“所有权说”的困扰,有利于法律关系的明晰。详而言之,在一般的让与担保中,倘若强调当事人担保交易之意思而采取“担保权说”,则不仅排除掉了担保人就担保物进行用益以抵消债款利息的可能,而且无法解释担保人何以能够将担保物从设定人责任财产中分离出去并优先受偿的担保功效;反之,倘若强调交易的让与形式而采取“所有权说”,则在形式上担保设定人与物之间的权利联系又被切断,其过于薄弱的法律地位,不仅阻碍其对物上的交换价值的进一步的支配,如再行设定抵押,而且还使其面临在担保权人再次处分担保物的风险。由此可见,让与担保的“所有权说”,在确定了担保权人的担保财产“归属”地位的同时,担保人的法律地位却模糊了起来:既然在让与担保交易中,债权人乃是担保财产的主人,那么担保人在担保物上究竟有什么权利?其“担保”之交易目的如何体现?比较而言,在典权交易中,承典人在取得典物的所有权之后,出典人的法律地位则可以附着在典制中固有的“回赎权”之上,而“回赎权”则无疑成为表彰当事人“担保交易”目的的核心标志。由于回赎权在性质上可以直接被视为以“典物之买回”为内容的债权请求权,故而“返还典价、回赎典物”的典制规则,就可以通过“买回请求权”的途径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回赎权凭藉其“不动产债权请求权”的性质,还可得适用《物权法》上的“预告登记”制度,从而获得对世效力,进而成为附着在承典人所有权上的一个“物上负担”。如此一来,以典权为依托的不动产担保交易,会形成泾渭分明的“出典人回赎权——承典人所有权”的对峙格局:前者可以再行抵押,而后者可以全面支配;同时前者作为后者的物上负担,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最后,在《物权法》没有规定典权制度的背景下,以典制为依托的不动产担保交易,同时也克服了一般让与担保的“清算困境”。在物上担保权实现的方式上,典型担保物权,受到“流质约款禁止”的限制。其之实行,以清算为必要;而让与担保,则是以担保人继续保有所有权,作为担保权实现的方式,因而无法受到“流质约款之禁止”的约束。在这里,让与担保的弊端至为明显:既然此种交易的目的在于债之担保,那么不经清算之受偿,必将丛生流质之弊。比较而言,而我国传统典制中的“找贴”、“别卖”,恰恰提供了现成、完备的“清算”方式。详而言之,“找贴”与“别卖”均是以“典价低于典物价值”这一事实为其存在的基础,故而无论当事人是否在典权合同中明确约定,基于合同的“习惯解释”,其两者均可被视为典权合同中的条款。进而,出典人“要求找贴”的权利,具有“形成权”的性质,其不以承典人的同意为要件。当事人就找贴价不能达成合意的,自应由第三人评估作价,或者“别卖”典物,以价金扣除典价后如有剩余,应向出典人返还④。就此以观,典制固有的“找贴”、“别卖”规则其实与“折价”、“变卖”等担保物权的“典型”实现方式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五、结语
在我国百年来西方法制移植的历程中,典制是中国传统交易习俗的遗产,一次又一次地面临“民法”这个外来法律的审视、解读与定性,其与成文民法的关系,也是历经了一系列的变迁离合。在今天,在民法业已形成我国私人交往关系之基本法律框架的环境之中,典制凭借其悠远的历史传统而超然于民法的框架之外,几无可能。因此,以“民法”为视角对这一历史遗产的分析和判断还将继续。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应当纳入我们视野范围、并作为理论分析起点的,不应当是民国民法典所展现给我们的,业已经过成文法重构的“典权制度”及其所给出的“定论”,而应当是我国历史上特定的经济、法律和文化背景下的传统典制本身。将典制视为一种“所有权担保”的形式,不仅是基于“筹措钱粮”的典制交易目的,以及我国传统的“典卖合一”的交易习惯,而且在“抽象的所有权”观念缺位的我国传统社会,“担保”而立“卖契”是实现债权人担保物之排他性支配的唯一途径。正是由于“所有权担保”的功能的实现,只需以“让于”和“回赎”这两个至为朴素的交易观念为条件,而无需复杂的法律技术,这使得典制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历经年而不衰;在今天我国的民法体系中,以“用益物权”为视点的“典权”制度,可能会因租赁等其他民法制度的取代而丧失社会意义,但是以“所有权担保”为内在机理的典制,则会在典型担保物权的法定类型之外,因“所有权担保”本身的社会需求而历久弥新。
收稿日期:2007-06-18
注释:
①有学者常常执著于“典权”与“所有权”之间“他物权”与“自物权”的性质区分。其实,这种区分在当时的语境之下,是没有意义的。详而言之,在继受西方民法之前的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在交易中的“设定物上担保”意思,尚无法通过移转“所有权权能”的技术来实现,而只能凭藉移转“物之归属”本身来完成,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债权人取得以“物主”身份实施“管业”的地位。与此同时,基于债权的暂时性,“物上担保”也应当具有暂时性,因而作为该担保的载体,即债权人所取得的物之归属,也就具有了暂时性的特征,这就是其“可回赎性”。换言之,当事人所具有的不同于“立时绝卖”的担保意思,只能够通过“回赎约款”来体现,而不能够通过否认债权人的(哪怕是暂时的)业主地位来体现。
②事实上,绝卖的意思是在找贴后才最终形成的。例如在明末清初,闽北土地的活卖交易中存在着的“‘找’、‘贴’、‘断’、‘洗’、‘尽’、‘休心断骨’”(本文参考文献[10],第273页)等不同性质的找贴,表明出卖人就是在这种多次找贴的过程中,才逐渐形成了与买卖物的归属渐离渐远以至彻底断裂的意思的。
③事实上,在人类法律文化发展的早期,以移转物之归属的方式,为他人设立物上的担保,此乃常见之现象。例如,在罗马法幼稚时期存在的“信托”,(本文参考文献[6],第341、361页。)又如7世纪以前日耳曼法上的“所有质”。(本文参考文献[8],第144页。)由此可见,在“抽象的所有权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权与所有权权能相分离的观念”产生之前,由于债务人不可能在保留物之归属的同时,使他人享有用于担保的“他物权”,所以让渡物之归属与他人,其实是满足社会生活中的担保需求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当事人有别于一般的买卖的担保意思,则必定表现为对于保留债务清偿后重新取得担保物的权利的约定——这其实是法律发展过程中的规律,中国如此,西方亦然。只是西方的这种“所有权”担保,很快就在罗马法的抽象所有权观念下,过渡为“他物权”担保了,而中国的典制则在长期对外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始终延续,并且成为在今天横向的时间轴线上“独有”的交易习惯罢了。因而,从担保交易的机理上讲,将典制认做是我国“独有”的交易习惯,未免言过其实。
④民国时期最高法院的一项决议,其内容是当事人在典契上注明“到期不赎听凭典权人出卖典物以收回典价之条款”的情况下,法院应认许之。且典权人所得价金超过典价者,其超过之数,应返还出典人。(本文参考文献[16],第1040页。)由于民国民法典未对“别买”问题做出直接规定,所以民国最高法院在此排除了“到期不赎,即取得所有权”规则的适用,做出了符合传统习惯的决议。此项决议,殊值赞同。
标签:法律论文; 所有权的转移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民法论文; 所有权保留论文; 法律制定论文; 土地买卖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