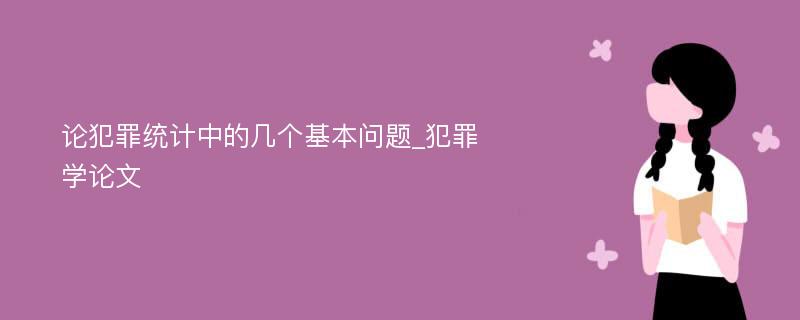
论犯罪统计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79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6522(2006)0 3—0085—05
一、犯罪统计对犯罪学研究的意义
犯罪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对大量个别现象的研究来取得普遍性的结论,统计是观察大量个别现象的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所以统计是实证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犯罪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它主要通过对犯罪现象的观察获得关于犯罪原因的一般性的原理原则,而犯罪统计“就是这类观察中最有效的一种手段”,[1] 以致有的学者认为“将犯罪现象做大量的观察的学问称为犯罪统计学”,[2] 离开了犯罪统计就不会产生犯罪学,更不会有犯罪学的发展和进步。犯罪统计对犯罪学研究的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三点:
1.测量犯罪状况及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失程度
犯罪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司法机关需要不断地监测这种不安定因素的规模、程度、水平、特点及趋势,以便采取相应预防、打击和控制措施。应用统计方法测定这些因素则可以达到对社会犯罪状况有一个整体的、综合的、准确的、深入的了解。例如通过对犯罪现象的统计分组,可以将复杂的犯罪现象划分为性质相对简单的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在一般意义上认识犯罪总体的量,而且能在特殊意义上观察犯罪总体中不同种类的犯罪的分布状态和特征,确定犯罪现象的结构,从而加深对犯罪现象的认识。用犯罪统计也可以向居民通报犯罪案件的数量、种类、发展和分布的情况,向居民指出成为被害人的危险性和可能性。例如20世纪末随着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明显暴露,诱发犯罪的因素陡增,通过犯罪统计我们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案率上升至80年代前半期的8倍,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不仅国际上已有的犯罪种类在我国皆已出现,而且重大刑事案件明显增多,接连发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单位、运钞车、珠宝行为目标,持枪抢劫巨额财物的恶性案件,出现了我国自建国以来的第五次犯罪高峰,[3] 居民成为被害人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大大提高,防范犯罪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
犯罪现象降低社会生活的质量并给社会造成损失,从犯罪统计中可以推测出这种损失的数量及其分布情况。这种损失可以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4](P183) 直接损失是犯罪行为对被害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失,例如在夜间的拦路抢劫对被害人人身、经济和心理造成的损害;另外这种犯罪会在居民中产生普遍的恐惧感,使他们不敢在夜间上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间接损失则是通过居民个人和国家对犯罪行为作出反应所造成的。例如居民为了防止入室盗窃而安装的防盗门和防盗窗,或者在室内安装的报警器以及参加防盗保险等所增加的支出;国家为了打击和控制犯罪而拨给警察、检察院、法院和监狱等司法机关的财政支出等。犯罪统计可以提供犯罪造成损失的数字,根据这些统计数字政府能够决定愿意冒哪些犯罪行为的风险,并且为了打击那些犯罪行为愿意投入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2.分析犯罪原因
分析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犯罪统计可以说明居民参与犯罪的规模,它为提出犯罪成因的假设和理论提供数据基础。如将犯罪统计与一般的人口统计数据作比较,就能从中分析到诸如工业化、摩托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社会和经济因素对犯罪发展的影响。
菲利在其专著《犯罪社会学》中提出了犯罪饱和现象:一定的社会必然会存在一定数量的犯罪现象。菲利没有对该现象作进一步的解释。通过对发达国家犯罪统计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犯罪率最高,日本的犯罪率最低。而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正式社会监督(我们将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称为正式社会监督,将刑事司法系统以外的但对控制犯罪有一定作用的社会组织称为非正式社会监督)最为强大,但美国崇尚自由,强调保护个人隐私,非正式社会监督的力量相对较为弱小;日本恰恰相反,日本的正式社会监督的力量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末端,但日本如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崇尚集体主义,个人是作为集体成员来思想和生活,即个人对集体负有责任,因而非正式社会监督的力量强大。两个国家的犯罪率与正式社会监督的力量成反比,而与非正式社会监督的力量成正比。[4](P263— 278) 这恰恰揭示了犯罪饱和现象的内在规律,一定的社会为何会出现一定的犯罪,主要是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这对处于转型阶段的我国尤其具有启发意义。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时期,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直接决定了我国的社会结构和犯罪率的高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尝试了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被打破了,企业大量倒闭,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同时国家对农村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而缺乏必要的保护,导致农业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与这些社会问题相伴随的就是犯罪率的急剧增加,这就是第五次犯罪高峰。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是我们改革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有调控的市场经济,建立起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而不是对自由竞争放任自由,听任人们两极分化,而后者将是一种极其不稳定的社会,必然存在着极高的犯罪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可以保障大多数人即使在市场的自由竞争中也能有一种基本稳定的生活,这对于预防、控制犯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的深刻认识,党和政府才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
3.预测犯罪动向与趋势
根据犯罪预测使犯罪控制的目的、手段和方法与发生变化的社会情况相适应。如果不进行犯罪预测,现行的刑事司法系统长此下去将不可避免地会失效,犯罪控制就始终只能凑和着去适应实际上已经出现的犯罪变化,这样一种反应式的、没有预见性的、非超前的行动会造成高额代价,使刑事司法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犯罪预测是刑事政策的基础,没有准确的犯罪预测就不可能有合理的刑事政策。
犯罪预测可以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预测。长期预测可以转变为中期预测和短期预测。长期预测只说明犯罪发展的主要本质方面以及总的趋势,中期预测的目标是要深入查明直接面临的实际变化,而短期预测则致力于为以后几天、几周和几个月做出具体决定,没有长期和中期预测就不可能进行短期预测。
犯罪预测主要有三种方法:外延法、模拟法和综合的制度分析与预测。外延法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犯罪统计的时间顺序从过去延伸到将来,其出发点是设想社会制度基本稳定,在过去和现在已经对社会造成危害的犯罪现象,也会在将来继续起存在。模拟法是把各种犯罪变量同各种社会和人口统计的变量联系起来,模拟各种社会和人口统计因素对犯罪动态的影响及其结果。未来不仅是过去和现在的简单继续,犯罪在其动态发展中会出现转折点、新情况和新的犯罪类型,同时必须借鉴其他国家已经取得的经验。最精确的犯罪预测方法是综合的制度分析和预测。首先,它设法确定在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里,一切对当前的犯罪发展具有重要性的人口统计、社会经济以及其他要素,在查明这些要素对犯罪发展的影响之后,预测关于整个社会制度的未来发展以及一切对于犯罪发展具有重要性的变量,最后才能预测未来犯罪的大概规模以及可能的结构与分布。
今天,我国犯罪学理论研究的不发达与犯罪统计研究的落后有关。犯罪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实证科学以统计为基础,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限制,研究中缺乏实证研究的条件和难以获得有关的统计资料,这导致犯罪学研究只能进行抽象的理论构建,无法对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犯罪问题提供有效的答案,即犯罪学的研究“多年来一直停留在定性的研究和分析上,严重约束了对犯罪问题研究的纵深发展”,[ 5]这也是今天犯罪学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犯罪统计的概念和种类
犯罪统计就是运用社会调查研究的基本方式之一——统计调查的原理和方法,说明、比较、分析犯罪现状和趋势,进而探讨犯罪原因的犯罪学研究方法。统计调查是指一种利用结构化或标准化的调查方式,调查大量样本,收集数据资料,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调查研究方式。[6] 也有人将它称为“问卷调查”、“社会调查”或“定性调查”。
犯罪统计一般来说包括四个环节:第一是研究设计。当确定了研究任务与目的之后,首先开展的工作是进行研究设计。研究设计是对整个研究工作进行规划,并制定出研究的具体策略,确定研究的最佳途径,选择恰当的调查研究方法的过程。第二是统计调查。统计调查是根据研究工作所提出的统计任务以及前一阶段所设计的调查工具,收集有关被研究对象——犯罪或犯罪人或其他调查对象的数据资料的过程。第三是统计整理。统计整理是对统计调查得来的资料与数据,加以科学汇总,使其条理化、系统化的过程,以便进一步地统计分析研究。第四是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是对经统计整理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数据的描述分析结果与推论统计结果,并进一步得到有关犯罪与犯罪人现象总体的推断结论。
根据犯罪统计是否直接为犯罪研究目的而进行的,可将犯罪统计分为第一手统计和第二手统计。第一手统计是指研究者为犯罪研究的目的而进行的犯罪统计,如西方国家犯罪学在隐案研究中常用的自报调查和被害人调查都属于这种统计。第二手统计是指统计者并非直接为犯罪研究的目的,而是为其他的目的而进行的犯罪统计,事后用于犯罪研究。对于第二手统计,研究者在使用时应十分小心,因为它不是为研究的目的而搜集的,它的数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能直接作为分析的依据,如警方的立案统计主要说明警方在社会治安方面的工作成绩,由于存在着犯罪黑数,它并不能真实反映社会上实际的犯罪状况。
根据犯罪统计主体的不同,可将犯罪统计分为官方的犯罪统计和非官方的犯罪统计。官方的犯罪统计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作的犯罪统计。它属于第二手统计,包括:警方的立案统计、检察院的起诉统计、法院的判罪统计和监狱的服刑统计。非官方的犯罪统计是指司法机关以外的主体为各种目的而进行的犯罪统计。它主要是研究者进行的第一手统计。
在各种犯罪统计中,官方的犯罪统计是最重要的,它是我们估量一个社会犯罪状况的基本依据。因为除了国家以外,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有条件在全国的范围内进行如此系统、大规模的犯罪统计。西方国家的犯罪统计主要是由国家来进行的,例如美国的统一犯罪报告(Uniform Crime Reports)、德国的警方犯罪统计、日本的犯罪白皮书等等,它们都是公开出版的,为研究者研究犯罪问题提供了基本的资料。我国还没有类似的由政府出面统一进行的、系统的犯罪统计,这就难以对我国犯罪的实际状况作出准确的评估。地方的司法机关因工作的需要也进行犯罪统计,但由于工作业绩的压力[7] 以及缺乏科学的统计方法而极不准确,即使这种统计也是不公开的,研究者无法得到。这种情况是导致犯罪研究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自己动手进行犯罪统计,但由于受条件和能力的限制,这种统计只能作为官方犯罪统计的补充和修正。
三、司法机关犯罪统计中的“漏斗效应”
在司法机关的犯罪统计中:即警方的立案统计、检察院的起诉统计、法院的判罪统计和监狱的服刑统计存在着统计数字递减的现象,我们将其称作“漏斗效应”。
由于警力所限,警方很少主动发现犯罪,它主要通过被害人或证人的报案获悉社会上已发生的犯罪。社会中实际发生的犯罪可能因为以下原因而不会为警方所知悉:一是犯罪根本没有被人发现,如小偷偷了东西,失主没有察觉;二是被害人受到恐吓而不敢报案或被害人认为警方不能破案而不报案;三是人民不认为是犯罪,如一些落后偏远的农村盛行买妻,周围的邻里都知道某人买了媳妇,但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没有人会去报案。由于以上三个因素的影响,警方的立案统计少于社会上实际发生的犯罪。
警方获悉犯罪后,就要组织警力对案件进行侦破并逮捕犯罪嫌疑人。不同案件的破案是不同的,一般来说,轻微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低,而严重刑事案件的破案率高。这是由于警方对不同案件的重视程度不同造成的。当社会上发生严重犯罪时,警方会受到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如社会舆论的呼吁、上级限期破案的要求,迫使它必须集中警力及时破案。轻微案件给警方的压力小的多,破案率也相对较低,如自行车盗窃案的破案率低于5%。案件侦破后,警方将它认为已构成犯罪的案件移送给检察院,由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起诉。由于存在破案率和犯罪嫌疑人没有被警方抓获等问题,警方提交检察院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要少于警方立案统计的犯罪数量。
检察院对警方提交的案件进行审查后,无非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不起诉,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存疑不起诉三种情况;另一种是向法院提起公诉。因为存在不起诉的情况,检察院起诉统计的数量必然少于警方提交审查起诉的犯罪数量。法院受理检方提起的公诉案件后,开庭对案件进行审理,审理结果也无非两种:无罪判决和有罪判决。所以法院的判罪统计要少于检察院的起诉统计。有罪判决可以分为有罪免刑判决和有罪处刑判决。有罪处刑判决又包括判处管制、拘役和缓刑三种不需在监狱服刑的情况。所以监狱的服刑统计要少于法院的判罪统计。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刑事诉讼过程也是司法机关筛选和过滤犯罪行为的过程,它最终只能将社会上发生的全部犯罪中的部分犯罪的犯罪人送进监狱服刑。与此相对应,随着刑事诉讼的进程,司法机关的犯罪统计也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警方的犯罪统计少于社会上实际发生的犯罪,检方的犯罪统计少于警方的犯罪统计,法院的犯罪统计少于检方的犯罪统计,监狱的犯罪统计少于法院的犯罪统计。以上这种递减的趋势被西方的犯罪学学者命名为“漏斗效应”。[4](P188) 根据“漏斗效应”我们可以自然得出结论:警方的立案统计最接近社会上实际发生的犯罪数量。故警方的犯罪统计对犯罪学的研究是最有价值的。
四、犯罪黑数与隐案研究
如前所述,警方的犯罪统计要少于社会上实际发生的犯罪数,所以警方的犯罪统计只能反映社会上实际发生犯罪的大致轮廓。警方的犯罪统计与社会上实际发生的犯罪数的差值在学理上被称为“犯罪黑数”,而警方统计在案的犯罪数在学理上被称为“犯罪明数”。犯罪黑数是指警方获悉的犯罪数与社会上实际发生的犯罪数的差值。警方没有获悉的犯罪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根本没有被人发现或察觉的犯罪;另一种是虽然已经被人发觉但却没有报案、因而警方没有获悉的犯罪。前者在犯罪统计中被称为“绝对犯罪黑数”,由于绝对犯罪黑数已经没有办法搞清楚了,因而它对犯罪学的研究没有意义,在研究中可以将它忽略不计;后者在犯罪统计学上被称为“相对犯罪黑数”,相对犯罪黑数可以通过一定的社会调查方法加以查明,所以在犯罪黑数中,只有相对犯罪黑数才对犯罪学的研究有意义,我们所研究的犯罪黑数也仅限于相对犯罪黑数。
“犯罪统计可以引导刑事政策的制定”,[8] 但犯罪黑数的大量存在会影响人们根据犯罪统计对犯罪实际情况的准确评估,从而使刑事政策的制定缺乏可靠的基础。根据国家“七五”社科规划的重点项目《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课题组的隐案调查显示,我国的犯罪黑数问题相当严重:犯罪明数最多只占实际发生犯罪的三分之一,但不同案件的犯罪黑数差距悬殊。一般来说,重特大案件的犯罪明数较接近实际,如杀人、强奸、爆炸、涉枪等严重侵犯人身、公共安全案件的隐案较少,犯罪黑数约占实际发生的10%:而轻微案件的犯罪黑数极其巨大,如盗窃非机动车、扒窃等侵犯财产案件的犯罪黑数约占实际犯罪数的90%。[9]
由于犯罪黑数对犯罪学研究的影响巨大,因而对犯罪黑数的研究就成为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对犯罪黑数的研究在学理上被称为“隐案研究”。在西方最早对隐案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比利时人凯特莱,他在1835年提出了“衡比定律”:即在犯罪明数与犯罪黑数之间存在着一种固定不变的比例关系,即明数大的犯罪隐案的数量也大,明数小的犯罪隐案的数量也小。衡比定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人们所接受,这就导致了隐案研究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后来证明衡比定律是错误的,现在西方的犯罪学者主要通过两种方法对隐案进行研究:一是从犯罪人的角度对正常居民进行的自报调查(Self - Report - Surveys); 二是对被害人进行的被害人调查(Victimization Surveys)。
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学者首先开始使用自报调查的方法对隐案进行研究,研究者在正常的居民(主要是青少年)中选择一定数量的对象,在较长的时期(3年、5年甚至10年)进行跟踪观察,并定期向被观察者提问,询问他们在生活中是否有过违法行为。研究者通过自报调查发现:违法人们行为的普遍特性,区别仅在于多数人是机遇性违法者,少数人则是顽固不化的“惯犯”;一般来说,前者违法行为的性质较轻,而后者违法行为的性质较为严重,因而后者比前者更多地被警察发现,但两者的隐案率(隐案率/实际违法数)都极高,前者约98%,后者约90%。[4](P207—209)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的一个犯罪学专家委员会——美国法律实施和司法管理总统委员会建议开展被害人调查。研究者在一定的区域,如在一个市的范围内甚至在全国的范围内,选取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家庭进行抽样调查。研究者登门拜访每一个被调查的家庭,向该家庭的一名成年人了解在调查前的一年中是否有家庭成员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向该被害人了解他被害的详情和案发前后被害人的安全感、对犯罪的恐惧心理、对司法机关的态度的变化以及是否向警方报案,如果没有报案,那么要了解被害人出于什么原因没有报案。调查发现:被害人不报案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两种考虑,即刑事司法系统能够对个人做什么和报告犯罪将会付出什么代价。[10] 被害人调查提供了研究隐案的一种新的方法,同时也奠定了被害人学的方法论基础。
收稿日期:2006—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