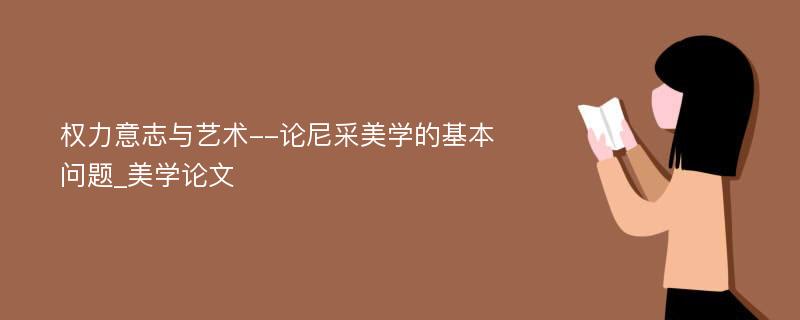
权力意志与艺术——论尼采美学的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美学论文,意志论文,权力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人尼采崇尚极北高山之气,其文本也如北极冰川般扑朔迷离。百年来国内外解人虽多,但举其要者大致如下:国内研究始于20世纪初,刚开始时研究者们注重对超人说的引入,二战后开始批评权力意志思想,80年代以来的尼采热又偏向于存在主义这一维度的阐发,90年代晚期开始关注尼采的政治哲学。而尼采与西方思想史的关联始终是国内研究的一大弱点,这方面尚有待于深入细致全面的梳理。西方研究在这一点上相对而言更为全面也更有力度。同时在尼采美学思想研究中,尤其是在国内研究中,尽管有一些有见地的佳构妙思,但仍存在以下不足有待弥补:多集中于前期思想,既缺乏后期美学思想的阐发,又缺乏前后思想的贯通,更缺乏对其内在哲学学理的剖析,同时还缺乏对尼采与现代艺术的关联之把握,其实尼采对现代艺术的批判始终贯穿于其前后作品之中。而将尼采的权力意志说与其艺术观打通并置入整个西方思想史中的梳理更未曾见,本文便试图在这一视角上有所前进。
我将立足于尼采的文本并将尼采置入整个西方思想的历史中,以找出尼采的位置。这一定位既区分于海德格尔的尼采定位,即所谓的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又有别于后现代的解读,如德里达的没有尼采只有尼采们的思想;同时也不同于国内前不久的一种微言大义的解释,它将尼采定位为基督教的。在将尼采归于现代维度的同时,我还将尼采与马克思、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了区分。同时,本文还尝试找出尼采的醉与柏拉图的灵感、普洛丁的灵见以及康德的天才的差异,而尼采的权力意志也在与“二元世界”、“终极世界”以及巴门尼德的存在的同一性的对立中显现出来。另外,本文认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以文字形式显现的交响乐,并尝试从其文本和其人自身找出一定的依据,而此前的观点都认为该书模仿了《新约全书》的结构,或干脆认为尼采学舌耶和华。
尼采思想的核心无疑是权力意志与艺术。权力意志思想尽管在尼采晚期才明确形成,然在《悲剧的诞生》中已初露端倪。权力意志的核心是力,这个力是创造与生成的。同时,这位哲人终其一生都极为推崇艺术,这在其早期和晚期著作中都可找到依据。而艺术在尼采那里表达为醉,醉是力的提高与充溢之感,即存在者的创造与被创造。从而权力意志与艺术在尼采那里便获得了同一性,这一同一性不同于巴门尼德的以思想为基础的存在的同一性。如果说尼采对西方思想史有所翻转的话,便体现在这里,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对苏格拉底以来思想的翻转。后者体现为“二元世界”,近代康德哲学是其高峰,它表现为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对立,而美学作为感性学只是退缩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从而尼采要将“二元世界”还原为“一元世界”,这个“一元世界”表达为感性的惟一性或纯粹性。
一、权力意志
权力意志是一个谜,解谜者众而谜底亦多。海德格尔从中探测出其形而上学的暗流,并溯流而上列出其谱系;德鲁兹将尼采思想解码为反编码,并以游牧思想命名之;而德里达干脆将尼采列入包括克尔凯郭尔在内的少数几位哲人群体,该群体中任何一人都大量繁殖其名字,并以签名、身份和面具嬉戏,换言之,德里达认为尼采没有单数只有复数。(Conway,Vol.2,p.107;Vol.4,p.78;Vol.1,p.118)由此可见,权力意志已成为一个问题,而解答的敞开并存于多重路径之中。这里将立足于尼采的文本,通过倾听权力意志的声音来对尼采还原,而权力意志自身将随着以下轨迹显现出来:已说的、未说的和要说的。
权力意志的曙光早在《悲剧的诞生》中已依稀可见,但尚未成型。该文多次以力、魔力、强大的力等语词来刻画酒神精神、音乐和悲剧之美以及宇宙的创造游戏,并认为作为音乐表现的意志是那种“审美的、纯粹沉思冥想的以及被动的情绪结构的对立面”,而且还赋予意志一种在永远洋溢的快乐中“自娱的艺术游戏”的意义。(1968a,pp.55、141)在《快乐的科学》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权力意志初步生成,并定位为“一千零一个目标”和“永不耗竭的创造的生命意志”(1954,pp.170、226),而且它必定出现在任何有生命的地方。在最后的遗稿中,权力意志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意义,它区分于物理学家所说的力,而是“不知足地意欲去显现权力,或运用和行使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驱动力”,并应由它来“定义界限,决定法度,明确权力的变化”。总之,“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1968b,pp.333、342、550)。
至此权力意志的边界逐步明朗化,即它相关于生命及其创造,它超越于现有的价值之外而又给予尺度,并且其内核是力。于是权力意志在以下层面得以澄明:与“二元世界”相区分,它给出了“一元世界”;与“终极世界”相分离,它演绎着永恒复返的游戏;与巴门尼德的存在的同一性相对立,它是生成又毁灭的悖论。权力意志既是否定的又是肯定的。
“二元世界”把世界一分为二:理式与万物(柏拉图),彼岸与此岸(基督教),物自体与现象界(康德)——前者真实且高,后者虚幻又低。对此权力意志反驳道:只有一个世界,而且是惟一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生命,理式、彼岸和物自体等都不过是对生命的责难与报复。“终极世界”认为,生命另有其目标,这目标反离生命而去,而且一千个民族就有一千个目标,一言以蔽之可曰真与善,最高的真是真理,最高的善是上帝。权力意志则针锋相对:没有什么最高与终极,一切的一切包括这一刻蝴蝶的翅动与海潮的拍响都是永恒复返的游戏,如沙之堡堆起又倾毁。在巴门尼德那里,存在必定存在,惟有存在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遇到了赫拉克利特,即存在又不存在的悖论打乱了他的思绪并顺流而下,到尼采那儿换上权力意志的红舞鞋,在“奥林匹亚的晴空”下,轻捷而沉醉地跳起足尖之舞。
权力意志是否定的,否定以往的价值之榜,所谓的真与善不过是谎言与伪善。在尼采看来,柏拉图的真正的世界是明白易懂的谎言,而古希腊的善不过是让生命沉浸于抽象的冷水浴中;基督教的真正的世界是精巧难懂的谎言,而中世纪的善无非是将生命变成驯兽场的一只病兽;哥尼斯堡的真正的世界尽管已经褪去了昔日的光芒,但仍是雾霭和怀疑论笼罩的旧的太阳,而近代的道德律令只不过是星空上的一只老鼠尾巴而已。权力意志又是肯定的,在否定旧榜之后,它要划定界限,确定尺度,在生命的崇高而上升之中,在“爱者”的命令万物的意志中,将产生新的道德。(1954,p.188)权力意志将在自身的嬉戏中明确权力的差别与等级,在力与力的差异中形成互动与流变。在这场永恒的创造之戏中惟一的动力是权力意志,惟一的尺度也是权力意志,而且这尺度这动力内在于权力意志之中。
总之,在权力意志之中,权力应是内核和本性。作为自我确立的新尺度,权力意志是“权力”,是一种支配的思想,围绕着它的是一种精敏的“灵魂”(ibid.),如同一条智慧之蛇围绕着一轮金色的太阳。而太阳是力的象征。另外这里的意志有别于此前的“意志”。普洛丁的太一是一个有意志的实体,康德的绝对命令的执行必须以自由意志为前提,费希特的创造非我的自我不仅有意志而且有力量。然而所有这些意志都不过是先验的意志,作为主体设立客体,作为理性决定感性,作为意识规范存在,总之是“二元世界”的产物。而权力意志中的意志被权力所规定,是力的生成与创造,这样一种创造同时就是游戏的,是永恒轮回的。此外叔本化的生存意志虽然表现为“一元世界”,但与权力意志仍不相同。前者是生命的保存,并且由于个体意志最终无法满足或无法避免满足后的厌倦而导致放弃意志,由此走向其对立面。而后者是生命的上升,它既承认个体生命的毁灭又肯定宇宙生命的生成。
二、艺术
艺术之于尼采的意义究竟显示于何处?这一问题将在以下形式中得到置换:柏拉图的灵感诗人与摹仿诗人、普洛丁的太一流射与万物、康德的天才与摹仿精神的对立。
尼采的全部美学思想都由醉展开。艺术来源于日神与酒神,二者可归结为醉。日神的醉是眼睛的醉,酒神的醉是全身情绪系统的醉。在醉中,奇迹显现,万物生灵,野兽开口,大地流蜜。日神与酒神的醉最终合而为一,于是诞生了悲剧。在悲剧中,个体解体的痛苦被复归世界本体的快乐所融化,因此带来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醉态。而悲剧的消亡归于酒神精神的丧失,即肤浅的科学乐观主义的出现。它视艺术为影之影,在理想国中诗人获罪,因为醉态妨碍哲学王的统治。从此醉意不再,生命开始向地狱坠落,而灵魂逐渐向天国升腾。
但作为生命的醉是每一个体生命无法回避的体验与存在。于是古希腊开端处的葡萄酒神的醉幻化为柏拉图的“灵感”、普洛丁的“灵见”和康德的“天才”。
在柏拉图那里,艺术来源于灵感,而灵感一是出自缪斯的亲吻,二是不朽的灵魂从前世带来的回忆。做诗不凭专门技艺和知识规矩,而是神灵之羽毛的轻触与点化,灵魂在迷狂中由此回忆起天上的美。于是灵感诗人是第一等人,摹仿诗人是第六等人,归于工匠之列。普洛丁认为,作为最高之美的太一像太阳,其光芒流射而形成万物,故物质世界的美不在其本身而在其分享到神的光辉。要见到最高的美不能凭肉眼,而须靠心眼,在灵魂的迷狂中才能达到灵见。在康德看来,天才是一种天生的心理能力,通过这种能力,自然替艺术定规则。天才的这种天生性与摹仿精神有本质区别,后者是可以通过摹仿学习的。
总之艺术或更高等的艺术来源于灵感与天才,而不是技艺与摹仿。前者是天生的、非理性的,它凭静观与洞见;后者是习得的、理性的,它赖学习与苦练。而无论是灵感、灵见还是天才,其显现情态都可归结为迷狂,迷狂即醉。
那么尼采的醉与其它的醉有何同异?相同之处在于都是非理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感官的醉,具体体现于眼耳鼻舌身等全身情绪系统,而后者排除了感官的作用,强调心灵的纯粹洞见与观照。前者是动态的,后者是静态的。前者来源于自身,内在于醉者,后者出自于神灵,是外力的作用。前者归结为生命,生活于大地,后者归根于上帝,漂浮于天国。
通过与其它的醉相区分,尼采的醉逐步清晰地凸现出来。作为艺术的起源和本性,醉贯穿艺术的始终,由此艺术的发生机制通过醉而得到规定。这样就一步步回到了此节开端的问题:艺术之于尼采的意义何在?亦即艺术的功用与地位如何?尼采在其思想开端处答曰:“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与真正的形而上活动”(1968a,p.31),并至其生命即将终结时仍重申了这一命题。
这位哲人终其一生都极为推崇艺术。他不仅曾直接创作音乐作品,而且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本身未尝不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欢乐颂。这部性灵之作与其说是摹仿了《新约全书》,不如说是摹仿了交响乐的结构。第一乐章在呈示部中展现了两个对比的主题:“三种变形”从骆驼到狮子到孩子流泻出肯定的主旋律,“道德之讲坛”则弹奏着否定的乐思,道德不过是催眠曲,朦胧着眼睛的睡者无梦亦无生命。在再现部中,“赠送的道德”又一次奏响了呈示部的主题,只不过加入了权力意志的和声。第二乐章带出了“夜之歌”的慢板,沉思的哲人在罗马的巴贝里尼广场的柱廊前伫立,述说着内心的寂寞与忧伤。紧接着“‘是’与‘亚门’之歌”在第三乐章加快了速度,古老的酒坛倾泻着所有关于葡萄的渴望,紫色的忧郁“憩息在未来之歌的祝福里”。第四乐章涌动着令人振奋的快板——“酩酊之歌”,生命向死神庄严宣告“再来一次”,在勇者之醉中升腾起永恒之气韵,生命的夜光杯荡漾着“玫瑰色的、棕色的黄金酒的芳香”。(1954,pp.336、433)
显然,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尼采的箴言体哲学文本获得了一种与其它箴言体迥然不同的风格——音乐式的。关注《看哪这人》一书的研究者应该会注意到,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章的第1节中尼采写道,“也许整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可以看作音乐”,在第6节中他又说道,“诗句因激情而战粟,雄辩变成了音乐”。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的创作间隙中还穿插着《生命颂》的乐曲创作,而当时尼采心中孕育着的肯定激情达到了最高程度(1989,pp.294、305、296)。就箴言体写作的哲人而言,尼采不是头一个,如帕斯卡尔就占其先,然这般音乐式风格恐怕还是前无古人。倘若尼采本人的音乐素养及德国深厚的音乐积淀被纳入视界的话,那么这种风格的出现便很自然。故而此处要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尼采为何要以音乐箴言体写作?可能的一个诠释是:尼采立意要把哲学变成艺术。因为在他看来,宗教、道德和哲学都是人的颓废形式,艺术才是那个反抗虚无主义的所谓“相反”的运动。那么除了在文本中一再重申这一命题之外,将文本本身变成一种艺术形式或带有艺术意味的形式便是水到渠成之举了。从而这部哲学交响乐以诗与思的和声叙述着这位哲人的一个重要话语:哲学作为反哲学的、诗意的。
由此可见,尼采的思想之战场尽管驱驰着千军万马,但艺术是最高的:“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1968b,p.452)。
三、权力意志与艺术的关系
艺术是权力意志的直接表达,权力意志又是艺术的尺度,权力意志和艺术在尼采那里获得了同一性。其原因将由以下考察而显现:艺术由艺术家、艺术创造、艺术品、艺术欣赏构成,其中前三者是主要的,灌注于它们之中的是醉,醉是力的提高与充溢之感,即存在者的创造与被创造,而权力意志本身就是力,是力与力的互动与嬉戏,从而权力意志与艺术是同一的。力是艺术的尺度,伟大的艺术都蕴涵着强大的力,而浪漫主义则是力的欠缺与衰败。
与以往的所谓接受者的美学相对,尼采提倡给予者的美学,即艺术家美学,创造者的美学。由此艺术主要由艺术家呈现。这也是尼采艺术思想的主要特点之一。尼采说道,“我们的美学至今还是一种女人美学,它仅仅是由那些艺术的接受者们阐发他们关于‘什么是美’的经验。在全部哲学中,迄今为止还缺乏艺术家”(ibid.,p.429)。很明显,在尼采看来,艺术问题是事关艺术家的问题,艺术家才应该是那个确定尺度的人。
对于权力意志与艺术家的关系问题,尼采这样表述,“艺术家这种现象最一目了然:——从中看到权力、自然等的基本本能”(ibid.,p.419)。这句话可以理解成艺术家是权力现身的最了然的方式,换言之,在艺术家身上可以直接看到权力。为什么在艺术家那里权力可以一目了然?关键在于何谓艺术家。家者,大家也,大师也。艺术之艺乃园艺、种植,其本意是人在大地上耕作,因而是人为的。相对于自然的给予性,艺术乃创造,即从无到有。因而在古希腊,艺术属于创造科学。由此看来很清楚,艺术家便是那个创造艺术的行家。而艺术家为什么能创造?尼采认为,“艺术家们,倘若他们有些成就,都一定是强壮的(肉体上也如此),精力过剩,像充满力量的野兽……在他们的生命中必须有一种朝气和春意,有一种惯常的醉意”(ibid.,p.421)。由此看来艺术家之所以能创造,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是因为其自身充满了生命的醉意与强健。
从艺术创造的层面看,艺术的诞生同样源于醉。伟大的希腊悲剧诞生于什么?诞生于日神和酒神精神。如前所述,二者最终都归结为醉。尼采以席勒的创造实践的自白为例这样阐明:“在创造活动之前,他眼前或心中并没有一系列哪怕是不经意安排的想象,而毋宁说是一种‘音乐情绪’”(1968a,p.49)。音乐情绪是什么,毋宁说是醉意。那么醉是什么?它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同力的过剩相应。日神之醉是“趋向幻觉之迫力”,酒神之醉乃“趋向放纵之迫力”。前者作为眼睛的醉而释放视觉、联想、诗意的力,后者作为全身情绪系统的醉而释放姿态、激情、歌咏、舞蹈之力。二者都在艺术家身上释放艺术创造的力。于是“阿尔基洛科斯这个热情燃烧着、爱着、恨着的人,只是创造力的一个幻影,此时此刻他不再仅仅是阿尔基洛科斯,而是世界创造力借阿尔基洛科斯这个符号象征性地表达自己的原始痛苦”(ibid.,p.50)。在巨大的创造力的冲动中,艺术家退场,艺术品隐去,而突出的是力。《俄狄浦斯》悲剧通过主人公的大苦难放射出“一种神奇的赐福力量,这种力量在他去世后仍起作用”(ibid.,p.67)。它引起的真正希腊式的快乐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乐天气氛弥漫全剧,从而带给观众的不是什么悲悯和恐惧的净化,而是全身心的力的陶醉。
权力意志作为力,由此便清楚地在艺术中显示出来。同时力也是艺术的尺度,它区分力的伟大与衰退。在尼采的艺术观那里,有一个问题始终要被追问,这就是:是由于过剩还是饥饿而变得富于创造性?前者是伟大的风格,而后者是浪漫主义。何谓伟大的风格?尼采的定义是,伟大的风格不屑于讨好和劝说,它就是意欲和命令,如同匹提宫的建筑艺术风格。(1968b,p.444)希腊悲剧是这种风格的典范。而浪漫主义与此相反,它不是强大的力,而是力的欠缺。在尼采看来,瓦格纳的音乐便是其代表。
四、尼采美学的现代意义
正如彭富春在《现代与后现代思想》一文中所指出的,思想乃是划界,这与肯定或否定的立场无关。(2000年a)于是在此探讨尼采美学的意义就是划界,指出它与传统美学的分离,划清它与现代思想的边界,并显示它与后现代思想的区分。
传统美学源于古希腊的诗学。作为创造科学,尽管它给予尺度,但这个尺度上仍刻着理论理性的洞见。中世纪只有神学没有诗学。在神学之天目俯视下,物质世界只反映着上帝的光辉,美由此归结为信仰者的实践理性。到近代,感性学作为感性的科学正式建立。然而这里的感性是主体感觉对象,其基础仍是那个“二元世界”。并且无论在康德还是黑格尔那里,感性都是被理性所规定的(尽管是近代的诗意理性)。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而且判断力一词本身仍隐含着知性的意味,正如他在天才与审美趣味之间更强调后者所显示的那样。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更明明白白地揭示了美的理性本原。由此而言,尽管感性学在近代获得了作为学科的独立的名字,但感性并没有获得独立自足性,它不是纯粹的、惟一的、本原的。总之,传统美学是被理性所规定的。
现代思想的主题敞开为三个维度:存在、心理和语言。其中存在是核心,它分别显现为马克思的社会实践、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马克思的存在是社会实践,即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它作为人的规定实现人的自由。但这个实现是将来时而不是现在时,因为当下的劳动是异化劳动,而对此的扬弃便导致共产主义。尼采的存在是权力意志,它是永恒的创造与生成,是世界大我的力与力的嬉戏,是日神与酒神的狂欢与陶醉。而海德格尔的存在经历了三个阶段:前期为存在的世界性,它意味着在世存在乃于无存在的悖论;中期为存在的历史性,它表明了林中空地那既显现又遮蔽的悖论;晚期为存在的语言性,它是道的沉默与言说的悖论,自身鸣奏着宁静的排钟。(参见彭富春,2000年a)
以尼采、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思想的意义在于对传统理性的批判(参见同上,2000年b),将理性转换成存在,并将“二元世界”转换成“一元世界”,总之共同以存在对抗理性。虽然在海德格尔晚期语言问题逐渐遮蔽存在问题,但他的语言仍是被理解了的存在。不过即便同属存在维度,尼采思想仍显示了其自身的边界。尼采的存在是个人存在,马克思的存在是社会存在:前者强调个体生命的体验,后者注重类的社会性。而海德格尔的存在是从思想来追问的。
现代美学将美、美感和艺术从理性的十字架上解放了下来。传统美学的诗意接受理性的尺度,而现代美学的诗意则接受存在的尺度,美从理性的显现转换成存在的显现。在马克思那里理解为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生活,在尼采看来美和艺术是权力意志的直接表达,而在海德格尔眼中美或艺术是真理的无蔽。由此现代美学不再是我感觉对象的那个二元分离的诗学和美学,而是生命体验、物我合一的反诗学反美学,其中没有艺术哲学,只有艺术问题,因为艺术哲学作为关于艺术的哲学也已随着传统哲学的消亡而引退了。
而后现代思想既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又反对现代的形而上学残余。它不仅解构一切而且拒绝建构自身。如果说现代思想在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之后仍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尺度的话(它典型地表现为超人、共产主义者和能死者),那么后现代思想正是要否定尺度的可能性和拒绝尺度的必要性,在工具语言和欲望语言的喧嚣中肢解自身。同样艺术和美在后现代思想那里碎裂为波普式的工具性和达达式的欲望性。绘画“还原”成颜料、画布乃至任何质料的偶然存在,骰子音乐(Aleatory music)在抛弃调性并超越多调性和无调性的同时,还瓦解了音乐的织体,使音乐变成了任由演奏者摆布的声响的支离破碎。
综上所述,尼采的意义在于:在思想的平台上,以诗意之刀从事着两方面的解剖。一是历史的解剖,由此摧毁着祭司假面式的传统智慧语言。一是现实的解剖,据而揭露了市场之蝇的工具性和欲望性。他的生成与创造的否定性不仅存在着向前的追溯力,也隐含着向后的启示性。于是尼采思想眩目如北极极光,透过后现代的迷雾望去,尽管暗淡,依然闪烁。
尼采的文本是蕴藉博大的,同时也是歧义横生的。这使得多种解读方式都可在其中找到依据,哪怕是一鳞半爪。尼采本人曾言道,他将因一再被误解而名垂千古,同时他要求自己的读者具备钢牙铁胃。诚哉斯言。不过,作为现代维度下的尼采自然也有其局限,那就是,批判了传统理性的理代感性究竟是不是纯粹而惟一的?如果是,那么相对于近代那个作为桥梁的感性,现代这纯粹而惟一的感性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是超人抑或只是人的碎片?而一个没有被思想和语言照亮的存在很可能是黑暗的。为什么博德尔呼唤“把智慧从现代世界之下的世界(阴间)引回世界,把智慧从后现代的暴力中解救出来,让它自由地显现”(参见彭富春,1999年)?因为杀死上帝的后现代的现代人终于发现:人在下降到幽暗无底的存在深渊之后,就有原始人所谓灵魂危险之虞。所谓灵魂危险是指潜藏在我们自我内部、即我们自我表层下面的未知的泰坦神族,狄奥尼索斯曾被这股幽冥的地下力量撕成碎片。尼采、凡·高等个人的生命悲剧值得深思。
标签:美学论文; 尼采论文; 权力意志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权力论文; 艺术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酒神论文; 灵感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