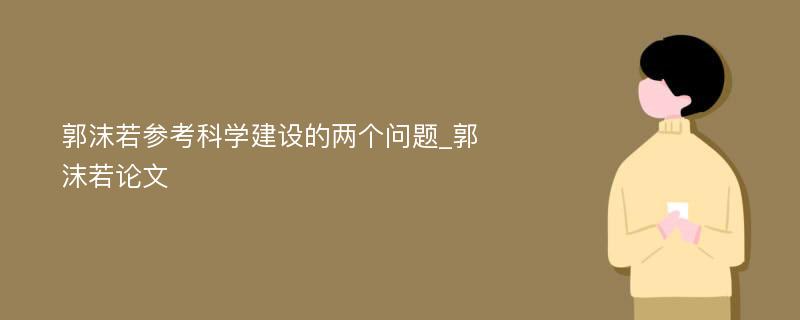
郭沫若资料学建设二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资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25(2003)02-0055-08
郭沫若资料学是创建郭沫若学的基础,值得高度重视。现将有关郭沫若资料学建设较 深的两点感触与思考写下来,请大家批评、教正。
一、发掘、发现另一个郭沫若
周国平有一段关于他与郭沫若儿子郭世英的短暂交往的回忆,读了让人思绪万千,感 慨不已。这是一段极为珍贵的文字,值得择其精要抄录:
“我在北大的最难忘的经历是认识了郭世英。这同时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我今天仍乐于承认,这位仅仅比我年长四岁的同班同学给我的影响大于我平生认识的 任何人。……他极其真诚,可以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 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 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 命攸关,令他饮食不安。同时他又是一个富于生活情趣的人,爱开玩笑,俏皮话连珠, 而且不久我还发现他热烈地恋爱。我是怀着极单纯的求知欲进北大的,在他的感染下, 我的人生目标发生了一个转移。我领悟到,人活着最重要的事不是做学问,而是热情地 生活,真诚地思考,以寻求内心的充实。”
“郭世英给予我的另一个收获是,他为我打开了通往世界文化宝库的门户。……在他 的床头不断地更新的书堆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正是在他的带动下,我开始大量阅读 经典名著,结识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海涅等大师。他对 现代思潮也有相当的敏感,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 。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 读名著的深远好处是把我的阅读口味弄精微了,使我从此对一切教条的著作和平庸的书 籍有了本能的排斥。……”
“一年级下学期,郭世英和校外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名为‘X’的地下文学 小团体,互相传阅各自的作品手稿。他常常也把这些手稿拿给我看,那是一些与流行文 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和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在他的影响下,我 也开始涂鸦。……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郭世英的言行很自然地被看作是离经叛道,从 而作为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受到了校方的注意。一个知情的同学怕受牵连而告发了‘ X’,这直接导致郭世英未能读完一年级就离开北大,被安排到了河南一家农场劳动。 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两年后他转学到了北京农业大学。我相信这是一种逃避,尽管后来 他十分诚恳地试图清理自己过去走的‘弯路’,但他内心深处明白,如果他继续从事哲 学,他是仍然无法避免与正统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然而,他终于未能避免为思想的 原罪付出血的代价,年仅27岁,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在‘群众专政’之下。”
“……我确实相信,如果不曾遇见他,我的道路会有所不同,我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 了却一桩夙愿,写出我所了解的这个郭沫若之子。”[1](p378—380)
上述这段自白,出自文林、海焘所编《中国新一代思想家自白》一书中的周国平自白 ——《关注人生的哲学之路》。如今,回忆者周国平已被读书界推戴为“中国新一代思 想家”,深刻地影响了他一生人生道路的郭世英,在1962年即开始饮食不安地思考“现 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等 超前性时代课题,结果因为“思想的原罪付出血的代价”!完全可以说,郭世英是与张 中晓、顾准、遇罗克、张志新们有着相同精神血缘的独立思想者。只不过,郭世英的超 前独立思考,至今还只是在周国平这段简短自白中偶现其冰山一角,而他的大量的宝贵
思考尚有待人们耐心地发掘。如果套用朱学勤的话来说,郭世英乃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周国平这段回忆,让我想起了郭沫若子女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郭庶英、郭平英的《回 忆父亲》,其中有几处文字谈及郭世英:“在我们兄弟姐妹中间,世英最喜欢文学,他 很早以前就可以写诗,写剧本,常常和爸爸一起讨论问题,而且他的性格豪爽,一旦知 错,改正得最坚决,所以爸爸格外喜欢他。……世英分明是被迫害致死,但把持农大领 导权的一小撮坏人竟组织人编写世英的所谓‘罪行材料’,给他扣上‘现行反革命’的 罪名。……爸爸深深理解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情,他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只是怀着巨 大的悲痛,把世英生前的日记用毛笔工整地抄写一遍,一共抄了八本。直到爸爸去世, 这八本日记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始终相信,历史总有一天会证明,世英决不 是‘现行反革命’,那八本工整的日记就是最有力的见证。现在,世英的问题终于得到 平反。今年5月,农业大学召开了平反大会,宣布世英是无罪的,宣布他当时就敢于指 出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的问题,那正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2](p504-505 )
另一篇是郭汉英的《<东方红>·<国际歌>·“无产阶级文化派”》,其中有这样几处 文字:“那是50年代初,我刚刚上初中。在一次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五一’庆祝活动 中,我突然发现《东方红》和《国际歌》的主题极不谐调。《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 太阳,称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却有力地宣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当时,自己对此感到吃惊而又不得其解。回 到家中,立即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父亲。而父亲对此似乎早有所思。他用赞许的眼光 看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说:‘《东方红》是一首民歌,体现着亿万农民对领袖的朴素感 情;《国际歌》是工人阶级的战歌,是巴黎公社的悲歌,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要求 ,它的提法是科学的。’停顿一下之后他又接着说:‘……现在的中国,九成是农民。 农民唱出了《东方红》,农民也需要《东方红》。这是中国的现实。’当时,我尚不理 解父亲讲法的含义。事后回想起来,他的讲法,道出了他对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基本问 题的思考与分析。其实,《东方红》和《国际歌》主题的对立,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必然面对的根本矛盾的反映。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九成是农民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怎样把一个基本上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具有发达工业为主导的 现代社会?……对于这些问题,父亲一直在思索,在分析。1956年,他对我说,‘新民 主主义阶段就这么过去了?这么大一个国家,生产力没有充分的发挥,要跨越历史阶段 谈何容易?’1959年面对我们炼出的‘蜂窝钢’,他说:‘单凭狂热是建不成社会主义 的。’三年困难时期,郭世英尖锐地问道:‘三面红旗之下,竟然有成千上万人饿死, 难道这是社会主义?’父亲摇了摇头,没有正面回答。作为史学家的父亲,当然知道判 断一个社会制度的性质,说到底要看支撑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的生命力 不仅在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更在于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的社会,充分 暴露了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父亲临终前不久, 一次他又和我谈起这些问题。父亲说:‘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看来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还需要通过实践,不断探索,才能找到真谛’。”[3](p150—151)
此外,1969年3—5月,郭世英死后不久,在间断了20多年后,郭沫若在一本英诗选集 的空白处,选择了其中的一些诗。其中有罗素·葛林的《默想》,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不能让我尊严的人性低头,/在那冰冷的无限面前跪叩,/我既年青而有爱情,求知 欲旺盛——/它们——只是在大气潮汐上的破片浮沉”;“我不能在无量数的星星面前 低头,/那无声的矜庄并不能使我投降。”郭沫若还对这首作了附白:“这首诗很有新
意,的确有破旧立新的感觉。我自己也曾有这样的感觉,但不纯。”[4]其实,这首诗 更像是郭世英年青心灵的独白。所以,有研究者认为,“这首诗在郭老心中引起了强烈 的共鸣。”“在当时,郭老的《英诗译稿》是译给自己看的。他用这种方法来排遣心中 的苦痛,也可以说,是在借他人的酒,浇自己的忧愁。更重的是,他要在这些抒情短诗 中去寻找暂时的安慰,去寻找‘人生的最佳境界’。”[5]该诗曲折地表现了郭沫若对 爱子郭世英的哀悼和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抗议。
如果将上述三篇回忆文章和郭沫若晚年译作《英诗译稿》结合起来思考、分析,大致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结论:
(一)与大多数报刊文字和人们印象中的郭沫若相对照,建国后在家中与儿女们一起, 还存在着另一个郭沫若。与孩子们在一起的郭沫若,真诚睿智,开明开放,关注中国的 未来,严肃地思考时代课题,也鼓励、引导孩子们共同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他与 孩子们多年来共同探讨的核心与焦点。这个郭沫若,与建国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郭沫若 ,和勤于思考的历史学家的郭沫若是相一致的,却迥然与建国后公共媒体上的郭沫若相 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主要是把“志于道”的“士”与“忠于君”的“仕”的 两种身份混淆在一起。郭沫若晚年的悲剧也与此有些相似,即是将两种难以相容的社会 角色(处身社会中心的政府要员与本质上作边缘思考的知识分子)的不同身份相互重叠、 缠绕,而造成某种精神紧张和人格分裂。那些身不由己的表态性“应制”“应景”诗文 ,反复地将其塑造成惯于引吭歌颂、乐于振翅战斗的“雄鸡”型公众形象,而将其作为 知识分子边缘思考的另一面遮得严严实实。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应该说这两个郭沫 若都是真实的。而且,人本来就是复杂的,只有多侧面的人才是立体的,真实的人。当 人们偶然地从大堆文字中,惊异地发现,在熟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郭沫若之外 ,还有一个“真诚地思考,以寻求内心的充实”的另一个作为思想者的郭沫若,自然地 倍感亲切,弥足珍贵。(这“另一个”思想者郭沫若,正可以与“致陈明远书信”中的 郭沫若相互印证。)
(二)郭世英的成长、成才,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家庭的影响应该是重要原因, 从遗传学角度看,在几个弟兄姐妹中,郭世英身上最多地继承了郭沫若的诗人气质和学 者基因,而且也最有才华。用哲学的语言说,郭世英简直就是《女神》时期的郭沫若的 “对象化”,难怪郭沫若“格外喜欢他”!所以他要把“世英生前的日记用毛笔工整地 抄写一遍,一共抄了八本。……这八本日记一直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我认为,建国后 的郭沫若,从深层看,依然是一种“外圆内方”型的人格,外表上一个劲紧跟时潮,可 是在层层包裹下,依然有一颗“真诚地思考”的心!只不过一般人根本无从察觉而已。 但是,“常常和爸爸一起讨论问题”的郭世英,却有这种条件和幸运。正是在父亲真诚 思考、不倦探索的潜移默化的濡染中,年青的郭世英开始了艰难的思想跋涉。深入地发 掘郭沫若与儿子郭世英的所有材料,包括那“字字泪、点点血”的“八本日记”,无疑 会帮助我们突破现有的郭沫若研究。
(三)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不能满足于“典籍”文献。因为以阐释学的观点来看,任 何“典籍”、“正史”,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都不可避免地有其固有的“先见”或“ 前理解”。由此,它们对历史必然地有所选择或删除。这样,它们在保存历史的同时, 也会有意无意地遮蔽历史。所以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考古 研究,无不强调在文字典籍之外,还要重视田野调查与实物研究。现代学术界将史料看 成是“人类活动的遗存”,将其分成文字记录、遗物遗迹和口碑等三大类。周国平、郭 汉英兄妹的三篇回忆性文章,即是从“口碑”整理成的非“典籍”性文字记录。它提示 我们,非“典籍”类“口碑”资料的可贵性。郭沫若建国后由于身份特殊,在公开场合 特别注意保持自己所应有的形象。所以研究当代郭沫若,特别不能仅仅依赖他公开发表
的作品或言论,为了真正走进郭沫若,很有必要多方发掘“口碑”,以期发现一个更加 有血有肉、有情趣、有思考、有困惑的活生生的郭沫若,以作为对那个一贯“紧跟”的 “雄鸡”型郭沫若的补充与矫正。
郭沫若研究整体上落后于鲁迅研究。这种差距,首先表现在对二者“口碑”史料的发 掘整理上,鲁迅亲朋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周海婴、许寿裳、孙伏园……等,均写 有回忆鲁迅生平、思想的著作。在这方面,希望郭沫若的亲人、朋友、同志、学生、下 属……,都能有一种紧迫感,加紧郭沫若“口碑”史料的搜集、整理与抢救。
二、留一部信史在人间
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思路。在这两 种不同学术思路的导引下,学者们有的重“考据”,有的重“义理”。孰是孰非,千百 年来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不过,如果站得更高一些看,二者在对立中又是可以统一起 来的。这里要紧的是将“学术研究”与“学术应用”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学术研究贵在 实事求是,学术应用则当经世致用。
遗憾的是,我们往往没有将这两个概念自觉地区分开,从而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往往带 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常常随学术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往往习惯于根据权威论断去选题, 选材料,有的甚至将之上升为一种方法论来推广,美其名曰“以论带史”。更极端者甚 至“以论代史”,从“论”出发改造材料,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地论证。很难想象这样 的学术研究会有多少生命力。实事求是是学术研究的生命。那种“月亮走我也走”的“ 研究”,是严肃学者所不屑为的。
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与此相反,一定是“论从史出”的。这样的学术研究才能揭示出 隐藏于事物表象下的深层的内在联系,这样的学术研究才称得上人类文明的花果。这样 的学术研究中,人类文明才会得以传承、延续与提升。也只有这样的学术研究,才能真 正可能被积极地“学术应用”。而一切随风摇摆的、似是而非的“以论代史”的“学术 研究”,则只能沦为“帮忙”、“帮闲”或“扯淡”而已。与其说它们这是“学术应用 ”,不如说是“学术制假”、遮蔽真实更贴切一些。
既然学术研究只能“论从史出”,所以对任何一门学科而言,史料、资料的真实性、 科学性、完备性乃是至关重要的。资料、史料是人文研究、人文著作的本源。所以梁启 超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如果没有真实、科学、完备的史料作为坚实基础,要 建立一门人文学科,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多年来我们有个学术误区,认为非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都是有阶级性的 ,所以首先要站稳立场,讲阶级性、党性。其实,学术乃社会之公器。举例说吧,马克 思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剩余价值规律,无产阶级固然可以应用它来推翻资产阶 级政权(如苏联),资产阶级也可以因此反思资本主义弊端,改善无产阶级生存条件,而 巩固、完善其政权(如美国)。同样,市场经济规律反映了工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资本 家们固然可以利用它来获取利润的最大化,社会主义中国不也可以利用它来为“最大多 数人民的利益”服务么?与之相反,一味强调学术的意识形态性的苏联,将学术视为政 治的仆从,只准教条主义地鹦鹉学舌,宣传政治,遮蔽真实,结果反而将强大的苏联折 腾得亡党亡国!同样,殷鉴不远,“文革”时期,“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张春桥、姚 文元、石一歌、梁效、罗思鼎之类,把持话语霸权,信口雌黄,指鹿为马,强奸学术, 结果不仅祸国殃民,而且还将自己死死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以自由地追求客观真理为其目的的(当然,实际上能否达到 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绝对真理永远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惟其如此,学术研究才格外 地具有魅力)。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广阔的心胸。郭沫若说过,“国境以外,也还有 人道,也还有同胞存在!”[6](p183)须知,包括郭沫若研究在内的任何学术研究,都是 属于全社会,都是造福全人类的;它们既不应该、也不允许、更不可能为某一个社团、 报刊,或某一个集团、阶级所圈定、包揽和独占。特别是像郭沫若这样一位为人类文明 所养育、而又产生过世界性影响的文化大家,他必然地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郭沫若的复杂性在于他不仅是学术中人,同时还是艺术家、革命者、思想战士和政府 高官。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中国舞台上,郭沫若的浪漫、激进、多变,往往令人眼花缭 乱,并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再加之历史的吊诡与个人的恩怨、党派的利害相牵连于一 起,有关郭沫若的笔墨官司,便“剪不断,理还乱”了。
所有忠诚学术、执着于创建郭沫若学的学人,面对这种困境怎么办呢?以个人的浅见, 学术的品格是求真唯实,首先应该从史料、资料抓起,科学地将郭沫若学的基础——“ 郭沫若资料学”建设好。只有这样,郭沫若学的创建才不是一相情愿的空想。
好在,这种关切在学术界已被越来越多的同行所认同,而且已引起学界高层的重视。 不久前在北京“郭沫若与百年中国学术文化国际论坛”上,与在京学者交谈中获悉,中 国社会科学院已批准一项重大社科课题,将拨出巨资,组织相当一批学人,计划花数年 之工,从年谱、资料长编作起,最后完成一部大型的郭沫若评传。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盛事。
学界中人往往有种偏见,以为写论文、专著才是正宗,才算真本事;而搞资料的,只 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小儿科”。我觉得这实在是一种浅见与偏见。
转瞬之间,自己已近老年。回首既往,多少也写过一点论著,它们真有真知灼见值得 传世吗?我感到汗颜。我相信,目前有关郭沫若的众多研究性文章著作,至少有90%以上 的,很快就会被时光淘汰而烟消云散。如果真能广泛搜寻材料,出以公心与良知,集多 人之力,秉笔直书,是完全能为郭沫若留一部信史给后世的。果能如此,以后千年万年 ,不管东方西方,如果有人要研究、审视、反思郭沫若,是都会以这部年谱、评传作为 基础,怎么也绕不过它的。果能如此,再对照现在众声喧哗的郭沫若研究,多数只不过 是些鲁迅所谓的言不及义的“嚷嚷”而已。到时候,目前的众多所谓郭学“研究”,大 概都只能落得“尔曹声与名俱灭,唯有信史留人间”的尴尬命运。
但是,要真正留一部信史在人间,也非一件易事。因为,这不仅与参与者、审阅者的 才学、胆识,甚至还与其思想境界、学术境界相关联。现存的一些郭沫若研究史料文献 中,即不乏正反经验可资借鉴。
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1年出版的《郭沫若少年诗稿》和《樱花书简(郭沫若一九 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家信选)》,就是两本忠实记录郭沫若思想生平的信史,不管其中 某些文字是否合乎时宜,一切均据实直录。据闻,编注者当年即颇顶住了相当压力。四 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上册、下册),青海人民出 版社1982年出版的《郭沫若在重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郭沫若书信 集》,都为郭沫若研究搜集和保存了的许多宝贵资料,是郭沫若资料学的珍贵基石。遗 憾的是,享誉甚高的《郭沫若佚文集》仅编了现代部分,当代部分尚缺如。
作为事外人的猜测,或许这是郭沫若的某些当代佚文有些不合时宜而让人颇费斟酌, 致使编者、出版者未能将此善举进行到底。或许出于相同考虑,国内几大出版社联合促 成的出版盛事,历时十余年才完成的浩大工程《郭沫若全集》,细加翻检,其实并不齐 全。其中不仅缺了译著、日记、书信等重要内容,而且在一些重要事由上,还对郭沫若 文献、史料作了相当的“净化”。现略举一二。
“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的世界性大事。它让人们大开眼界,原来人类可以如此“ 革命”、如此“神圣”地相互撕咬,甚至自污自虐!其个中因由,值得认真研究、反思 ,以期引为鉴戒,以免重蹈覆辙。如果说因为缺乏距离,至今难以对其深入研究,至少 我们应该争取对相关资料、史料,作相对完整的保存。郭沫若作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 面文化旗帜”,“文革”中他像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一样,对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这场运动及其出现的种种新事物、新精神、新气象,无不写诗填词高声颂扬;他对当时 所要打倒的“大工贼”、“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等,当然少不了口诛笔伐!将上述 这一切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全都是合乎情理、合乎逻辑的,要不这样反而不可思议 。1977年郭沫若按照惯例,将这些“文革”诗词编入《沫若诗词选》不久,“文革”即 被彻底否定。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沫若诗词选》编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5 卷时,即不得不从中删削去乱颂“文革”、错批“异端”的不合时宜的“文革”诗词21 首,如《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文革》、《“长征红卫队”》、 《大民主》、《科技大学成立革命委员会》、《歌颂“九大”路线》……等等。类似的 情况,还有郭沫若1959年编辑出版的文艺论集《雄鸡集》,在1984年编入《郭沫若全集 》时,也因个别文章不太和谐,如《斥胡风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努力把自己改造成 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未及收入。另外,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分校中文系辑录、内 部出版的《迎接新中国(郭老在香港战斗时期的佚文)》60余篇,也未收入全集。
我们党有规定:“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在《郭沫若全集》中作上述处理有其 合理性,也是能理解的——有些文字不利于正面宣传郭沫若。但是,作为学术研究,难 窥全豹,毕竟是一件憾事。有没有办法使二者兼顾,各得其所呢?
郭沫若作为历史学家,在其长达20余年的自传写作中,一直坚持这样的写作理念:“ 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 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7](p3,p7)也许这种通过一个人折射一个时代的 理念和方法,正是我们研究郭沫若的极好的指导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先 进人物,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对民族自强的现代化道路,作了不屈不挠的多 种探索。这一探索过程至今尚在继续。郭沫若即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探索方面的重要代表 人物,其生平与实践涉及到文学、历史、政治、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其时间跨 度从晚清一直到社会主义新时期。在主观上他分明想与时俱进、客观上却与我们民族一 道,走了相当弯路。郭沫若作为一面文化镜子,从中可以映照出我们民族现代化探索中 的多少正反经验啊!在中国现代文化界、学术界,很难找到郭沫若这样的蕴藏着如此丰 厚“含金量”的研究标本。太有必要为其留下一份完整的真实的历史资料了。
为此,建议中国社科院有关专家、学者在收集资料、编撰郭沫若年谱、评传时,作一 番文无巨细的佚文搜检、勘定工作。郭沫若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曾 三次从军,从政,此时他的一些形诸文字、载诸书报的讲话、报告,不一定有多少学术 价值,但于了解郭沫若的全貌及其在不同时期中的某些细微变化,是很有用处的,比如 “文革”中他在人大常委会关于“烧书”问题的发言等。今后大型年谱完成后,可否将 全集外的所有佚文作为年谱的附录,统一定价,配套出版?一般而言,购买年谱的人较 少,多局限于学术圈内。这样,将二者“捆绑式”配套发行,多半能限制其流传范围, 而与一般性阅读区别开。不知这些想法妥当否?欢迎批评。
相比之下,鲁迅研究界对鲁迅佚文的发掘用力甚勤,至今已很难有太大的作为。而郭 沫若研究在佚文发掘上,还有不小的空间。这既是我们的差距,也是我们的机会。希望 与郭研界同仁共勉:留一部信史在人间!
收稿日期:2003-03-31
标签:郭沫若论文; 郭世英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郭沫若全集论文; 东方红论文; 国际歌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父亲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