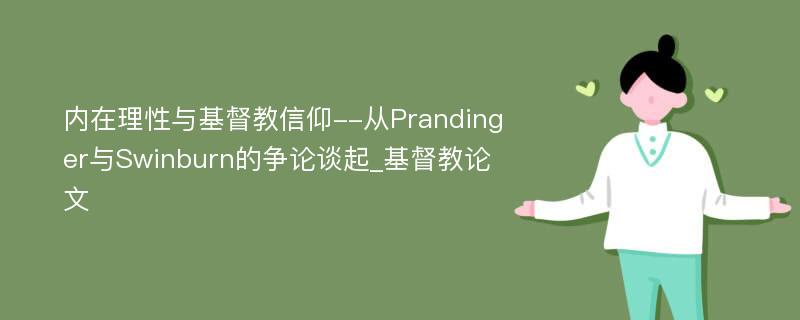
内在合理性与基督教信念——从普兰丁格与斯文伯恩的争论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恩论文,普兰论文,基督教论文,合理性论文,斯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10-0071-06
什么是“内在合理性”?怎么判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内在合理性?怎么判定一个具有基督教信念的人是否具有内在合理性?针对这些问题,普兰丁格曾经与斯文伯恩展开过激烈的争论。①斯文伯恩认为,内在合理性是与或然性相关的问题,它是我们对基本信念抱有多大程度的信心。与此相反,普兰丁格认为内在合理性不存在或然性,即我们总是相信一事物,而不是可能相信一事物。本文将论证,即使以普兰丁格的论证为前提,我们仍然可以在不违反内在合理性的前提下断定“一个事物的存在/不存在是可能的”,内在合理性具有或然性,同时它不必是斯文伯恩所谓的那种或然性概念。
一 何谓合理性
在《保证:当前的争论》中,普兰丁格开始探讨合理性概念的不同含义。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中,他要追问的是:在什么意义上,人们断定基督教信念是不合理的?显然,这里关系到人们把什么样的合理性/不合理性概念与基督教信念联系在一起。普兰丁格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表现为最终必须确定一个关于合理性的“规范性问题”。他探讨了五种合理性概念,分别是:(1)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意义上的合理性;(2)作为恰当功能的合理性;(3)作为理性衍生的合理性;(4)作为符合手段-目的的合理性;(5)阿尔斯顿从感知到信念的实践合理性。普兰丁格认为,我们并不是在这五种意义上将基督教信念判定为不合理的。相应地,当我们说一个具有基督教信念的人不合理时:第一,我们不是指他不是有理性的动物;第二,不是指他的理性器官发生了某种病理紊乱;第三,不是指他信奉的是理性推衍出的否定命题;第四,不是指他的行为与目的之间不一致;第五,不是指他在实践上是不合理的。
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批评中,普兰丁格发现了他们以及大部分基督教信念的批评者之间的共同点:基督教信念之所以是不合理的,是因为它产生于理性官能的一种微妙的功能紊乱(区别于上文中的病理式功能紊乱)。即“最好认为这些人是在抱怨,说基督教信念不是由恰当地运转,而是目的在于真理的认知过程产生的”。最终那个“规范性问题”被确定为:“基督教信念,不论是否是真的,无论如何没有保证。”②也正是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普兰丁格提出了有保证的基督教信念(warranted christian belief),从而确立了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
在五个合理性概念中,作为恰当功能的合理性和阿尔斯顿的实践合理性概念最为重要。前者与弗洛伊德-马克思的批评相关(从而与保证问题的提出相关),后者为“保证”概念提供了论证方法。
对于斯文伯恩来说,合理性既不是恰当功能的合理性,也不是实践合理性。合理性的来源是一致性,即一信念与其他信念之间是否具有一致性。一致性意味着无矛盾和可理解性。鉴于人类不断从经验中积累各种信念,合理性也就来自于不断在每一类经验现象中强化一致性。在这一点上,科学理论的信念和基督教信念是一样的。因此,对合理性的探讨只能得到一种或然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弱的起点,但是足以在此基础上展开宗教实践。
二 争论的焦点:或然性问题
根据斯文伯恩的观点,我们并不能通过单一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渐进的累积证明方式,也就是或然率的方式。不仅基督教信念,我们的许多日常信念总是包含着一个或然性问题。他认为,普兰丁格遗漏的正是这个问题。他写道:“我认为,困扰着无神论者与许多有神论者的问题并不是基督教信念是否具有普兰丁格所谓的保证,而是……根据我们的证据(evidence),基督教信念是否可能为真——如果普兰丁格曾经考虑到这个问题,那就好了。”③
事实上,争论是由普兰丁格挑起的。他在《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第八章中批评了斯文伯恩在《信仰与理性》、《上帝的存在》中提出的以或然率来确定基督教信念的观点。斯文伯恩的观点在于:相对于有关的背景知识,基督教信念为真的或然率高于基督教信念为假的或然率。相应地,S相信P,当且仅当他相信P为真的或然率高于他相信P为假的或然率。普兰丁格经过概率演算,指出历史论证中一个命题的或然率是不断缩小的,最终“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只是,我们的背景知识K(不论是历史的还是其他的,但不包括我们借着信仰和启示所知道的)完全不足以支持我们认真地相信G……我认为,这样一个历史理据的主要问题,就是我所称为逐渐缩小的或然率——在提出历史论证时,我们不可以简单地把中间命题加入K之中,所以只得继续一次又一次地计算新的乘积”。④
斯文伯恩的回应分为两点:第一,普兰丁格错误地估计了或然率的缩小。普兰丁格在《上帝的存在》中所论及的历史证据非常简短,在《启示:从隐喻到类比》中的论证也不够清晰。它只是程度较弱地引出上帝的存在,这些恰恰是普兰丁格在论证中使用的历史证据。例如:上帝让耶稣降生、受难、复活的唯一原因是启示的需要。他认为还有一些来自于基督教传统的基础事件能以更强的姿态引出上帝的存在。除了启示的需要,还有其他的原因存在。“这些(历史证据)不会减少上帝存在这个命题的最初的或然率,反而会增加这样的或然率:如果上帝存在,许多他在基督身上的作为就是真的。”⑤第二,指出或然率是一种事实,即使存在普兰丁格所说的“逐渐缩小的或然率”,公共证据(public evidence)仍然足以为信仰提供论证。斯文伯恩指出,宗教所需要的信仰是通过遵循一条道路而追寻一个目标,这是一种委身或承诺(commitment)。它所需要的只是目标存在并且能够被达成的机会,逐渐缩小的或然率不会妨碍到这一点。在此基础上,斯文伯恩指责普兰丁格没有认真对待圣经的历史批判主义研究,以及关于恶的难题。例如:我们已经不再从字面上相信“六日创世”,但是我们仍然从字面上相信“复活”。
总之,斯文伯恩仍然坚持,S的信念是内在合理的,当且仅当它根据S的证据来说是可能的。作为S基础信念的证据内容,要受限于S对其的信任程度,其他信任的证据会降低一个证据受信任的程度。因此,我们的基础信念起先都具有不同的可能性程度,一个起初具有较高可能性程度的基础信念,后来可能受到我们其他信念的影响而具有较低的可能性程度。如果你仍然坚持一个可能性降到半数以下的基础信念,那么你的信念就是内在不合理的。
针对斯文伯恩的回应,普兰丁格指出:斯文伯恩划分了“私人证据”(private evidence)和“公共证据”。前者是:S的信念是具有私人合理性的,当且仅当它根据S的证据来说是可能的。后者是:S的信念是具有公共合理性的,当且仅当它根据公共的证据来说是可能的。同时斯文伯恩把普兰丁格的基本信念全部理解为具有私人合理性的。这里的私人合理性就是内在合理性。如此一来,即使一个认为自己是有个玻璃脑袋的人,仍然可以享有内在合理性。(一个有玻璃脑袋的人的心灵世界在逻辑上是融贯的,其心灵与其行为之间也是逻辑一致的。)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断定基督教信念具有或不具有内在合理性,那并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普兰丁格强调“我相信”完全不同于“我可能相信”,我们的最基本信念不具有任何的或然性,我们对它们要么支付全额信任,要么收回全部信任。很显然,争论到最后,问题集中在:普兰丁格所理解的内在合理性究竟是什么?除了私人合理性之外,他给内在合理性赋予了什么内涵?他的内在合理性是否还能容纳斯文伯恩的或然性?
三 理性官能的恰当运转
根据普兰丁格的观点,内在合理性指的是:在经验中,我们所有相关的信念得以恰当地产生。这里关涉到两种信念对象,即两种经验:感觉映像经验和信念经验。前者与事物对我们感官的显现相关,它表现为事物是什么样的。后者与我们关于正确的感觉相关,它表现为正确是什么样的。普兰丁格举了三个关于信念经验的例子:你记得你去参加了在洛维斯比尔斯克的一个晚会,“没有任何狗是集合”与“正是你注意到在你面前的这一页书”。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其中没有感觉映像的参与,或感觉映像是不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突出了我们关于真或正确的感觉,所以它也被普兰丁格称为“冲动的证据”。内在合理性也就相应地关系到两个层面:第一,“形成与我拥有的感觉映像相适应的信念”,即形成恰当的知觉信念。第二,“在对信念经验的响应中形成正确的信念”,即形成恰当的信念的信念。
第一个层面的内在合理性意味着,“当这样一个映像以与看见一只灰象相联系的方式向我呈现出来时。这样,我不会形成这个信念——我是在注意到一只红鹳。”⑥否则,我就是内在不合理的。让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个思想实验,设想这样一种情形,大雾弥漫的早上,我有一个关于灰象的映像。当我几乎要认定我在注意一只灰象的时候。我忽然记得有几次,同样的情形下,我最终发现那是一只红鹳。于是我最终形成的信念会是,我在注意一只红鹳。假设我习惯这样的情形,于是每次当身处同样的情景之时,我的灰象映像都会对应着我在注意一只红鹳的信念。这里不存在任何内在的不合理性。
为了保证在映像与信念之间的一致性,普兰丁格可能的回应是:要么断定这里的映像恰恰是与一只红鹳联系起来的映像;要么断定这里的信念仍然是“我在注意一只灰象”。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思想实验中,对象是红鹳,映像是灰象,信念是红鹳。在第一种回应中,对象、映像和信念都是红鹳。在第二种回应中,对象是红鹳,映像和信念是灰象,判断是红鹳。
第一种回应比较容易处理。在我们的思想实验中其实涉及到被“信息语义学”称之为“错误表征”(erroneous representation)或“析取难题”(problem of disjunction)的情形。(如果不把普兰丁格所说的“映像”理解为备受批评的“感觉材料”概念,那么应该将它理解为表征。表征既是认知科学,也是意识和意向性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心灵特有的功能和状态。一种意向状态总是表征着一个特定的对象。所以,表征本身具有确定的语义性质,它可能表现为一定的真值条件、内容、指称,等等。)不同的对象可能导致同一个表征。我们对马的表征可以由牛或马所引起。相应地,对同一个信息对象,我们可能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表征。即,牛有的时候导致牛的表征,有的时候导致马的表征。在两种情况中,都有一个表征是错误的。也就是对确定的对象红鹳,在有的情形下我们可以把它正确地表征为红鹳,但是在另一些情形下我们可能会把它错误地表征为灰象等任何东西。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遵循着法则。⑦
在第二种可能的回应中,恰恰运用了上述错误表征的情形,即,我们对对象红鹳做出了灰象的错误表征,形成了关于灰象的信念,我们只是做出了“我在注意一只红鹳”的判断。如果这个回应成立,第一,这种信念失败的情形将是:我不相信“我在注意一只灰象”。然而,根据普兰丁格原来的论证,内在合理性失败的情形却是我相信“我不是在注意一只灰象,而是一只红鹳”(两者之间的差别,请参照“我不相信A”与“我相信-A”)。第二,这种回应将信念琐碎化。它将包含其他三种失败情景:即(1)我不相信是我拥有这一感觉映像;(2)我不相信这一感觉映像是被注意到的;(3)我不相信感觉映像本身。其中(3)不能被看作内在合理性的失败,这恰恰是许多宗教修行者的境界,而(1)和(2)是关于对信念经验的信念,也就是第二个层面的合理性。
在进入第二个层面的探讨之前,我们可以先总结一下。这里反驳的重点在于,即使我们违反普兰丁格的内在合理性在这个层面上的规定,我们的信念响应机制仍然可以是内在合理的。因此,普兰丁格的内在合理性概念是有问题的。当我们断定一个人持有一个基督教信念是不合理的,我们的意思仍然可以是:这是理性官能不恰当运转的结果。随着我们分析的深入,这一点会愈加明显。
针对第二个层面的合理性,普兰丁格区分了两种不合理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病态的怀疑论者”。这样的人和我们具有一样的信念经验,但是无法形成恰当的对信念经验的信念。例如:面对“没有任何狗是集合”这样的命题,A有很明确的它是正确的感觉,但是由于某种怀疑论的顾虑,他无法形成它是正确的信念,反而陷入怀疑之中。在这个情形中,A就是内在不合理的。第二种情形是,彻底的怀疑论者。要做到这一点,A就要在感觉上首先具有它是可被怀疑的内容,然后形成相应的怀疑论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认为自己的脑袋是玻璃做成的神经错乱者反而具有内在合理性。他的问题在于,没有形成恰当的感觉,他是外在不合理的。普兰丁格的结论是,当我们说一个人持有基督教信念是不合理的,我们既不是在内在不合理,也不是在外在不合理的意义上这样说。由此,他把第二个层面的合理性排除在考察的范围之外。
结合普兰丁格所提出的A/C模型来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当普兰丁格用这个模型来为基督教信念做担保的时候,他的论证仍然在第二个层面的合理性基础上展开,他正在应用已经被他拒之门外的那个情况。
四 A/C模型
A/C模型是普兰丁格对阿奎那-加尔文关于基督教知识论的重构,他认为,阿奎那-加尔文的理论包含着同一个模型,它本身可能为真,如果它为真的话,那么基督教信念就为真。简单说来,这个模型包含以下内容:第一,人对上帝具有一种特殊的认知机制(即加尔文所说的“神圣感应”),它是内在的。第二,当一些环境激发了这种机制,人就会形成关于上帝的信念。罪的作用有碍于这种机制的正常运转,所以对于非信徒来说,他们的认知能力出了问题。同时,普兰丁格这样来定义保证:“如果一信念的形成,是认知官能在合适的认知环境里恰当地起作用,其设计蓝图又是有效地导向获取真理——其中当然还包括避免错误,那么,该信念就获得保证。”⑧显然,非信徒不做判断、未能相信、不可知论的信念都是没有保证的。
针对有保证的不做判断与无保证的不做判断,普兰丁格各举了三个例子,由于人对上帝的认知机制与“其他可能产生信念的机制无异”,所以这几个例子都是从日常认知的角度提出的。关于有保证的不做判断是这样三个例子:(1)“宇宙其他地方是否有一些智能生物”;(2)感情不睦的夫妻各做一次关于吵架的倾诉;(3)“南极最高的山是否有16000英尺”。无保证的不做判断的例子是:(A)“我正在做什么事情”;(B)“我眼前是否有人存在”;(C)“我是否只存在了五分钟”。⑨我们可以把(1)、(2)、(3)的形式写作:我不知道X。而(A)、(B)、(C)的形式写作:我不知道Y。
结合上文所说的第二个层面的合理性,我们发现这里“我不知道Y”的无保证性完全就是第二个层面的不合理性。也就是说对于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眼前的对象、我的存在有一种正确的感觉,但是我不去形成相应的信念,反而悬搁我的判断。那么,认为基督教信念不合理的人,完全可以认可基督教信念具有内在合理性,但是坚持它没有外在合理性。即,一个拥有基督教信念的人,就像一个认为自己有一个玻璃脑袋的人一样。相应地,“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却具有外在合理性。这样的论证无疑把有神论归于内在合理性,而无神论、怀疑论、不可知论等归于外在合理性。这样的结果对于构建基督教信念的知识论地位没有任何决定性的意义,所以这必定不是普兰丁格的论证进路。
五 认知环境
换个方向进行分析,我们发现:X当中包含着非我的参照系统。而Y的内容始终在一个关于“我的当下”的参照系中展开。这种非我的参照系统,其实就是普兰丁格所说的合适的“认知环境”。除了把“认知环境”称为“特定环境”,他并没有就这一概念的内容做出实质性的说明,也没有提到如何判断一个认知环境是否是合适的。参考例子(1)和(3),这里似乎涉及一个外在的事实,它具有被探明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认知主体对这个事实不具备任何确定的知识。而例子(2)有所不同。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对“感情不睦的夫妻各自关于一次吵架的倾诉”保持不做判断是没有保证的呢?设想这次争吵之后,发生了一场谋杀,没有目击者,妻子被杀,丈夫是唯一的嫌疑人。根据你的经验,之前他们每次争吵都会以严重的家庭暴力结束,每次的受害者都是妻子。同时,你是这对夫妻的唯一朋友,即唯一一个了解这一切的人。这个时候你是否仍然能够有保证地保持沉默呢?如果不能的话,那么上述的情况就使认知环境变得不适于做出保证。在这个例子中,也有一个所谓的外在事实,但是它缺乏(1)和(3)中的被探明的可能性,因而变成了关于认知主体信念背景的对象。普兰丁格把它们不加区别地放在一起就是认为可被探明的外在事实是不重要的,这个认知环境应该是与认知主体信念背景相关的。现在的问题就归结到:是什么构成了认知主体的信念背景?
这个信念背景包含着“基础信念”,它是“非推论的”、“直接获取的”、与感知、记忆、先天信念一样,自发地在一种特定环境中出现,不用其他信念作为证据也可接受。⑩这也就是第二类例子中涉及的“我的当下”。斯文伯恩对此也有相似的说法,那就是它的“可信性原则”:“所有的宗教经验应当被其主体当作真的,因而应当视其为对显然对象——上帝存在信念的实质性根据。”(11)这一原则本身无须也不能被进一步证明。这是否意味着,就像斯文伯恩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信念之合理性总是要通过相对于一定信念背景(认知环境)的概率来得到说明呢?
答案是否定的。通过重构“认知环境”概念,取消概率性问题。首先,跟普兰丁格的观点一样,它并不是个外在的环境,就好像把老虎关进笼子里,然后一切工作就做完了,我们就安全了。其次,与普兰丁格不同的是,它需要在超越于内在/外在的意义上被理解,它与经验直接相关。
普特南曾经批评传统的认识论。根据这种观点,仿佛不依靠内在的东西我们就无法认识任何对象。他说:“这种表象理论直至今日都暗含着一种内在大屏幕的图画。”(12)所谓“我的当下”和“认知机制”讲的正是内在的“图画”和“内在大屏幕”的操作。这种经验观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问题,塞尔也论证道:“一旦我们把这种经验处理为以之为基础便可推出对象的存在的证据,那么怀疑主义就会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推理将缺乏任何证明。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内部和外部的隐喻才给我们设置了陷阱,因为它使我们倾向于认为我们正在处理两个独立的现象,其中一个是“内部”经验,关于它我们可以有一种笛卡尔的确定性;另一个是“外部”事物,内部经验必须为其提供基础、证据或者根据。(13)与此相反,直接实在论强调的是,当我们使用语言时,我们不是把涵义与符号联系起来,而是直接感知符号的涵义。句子指向它们的意义并不是因为我看到或听到的记号和声音内在地具有某些意义,而是被我们所使用的句子并不是一堆记号和声音的简单叠加。这里存在着公认的真。(14)这种“公认的真”就是认知背景,就是我们对实在的直接把握,它不是一种概念框架,而是非还原的。
在这样的图景中,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种情形,我不知道“我眼前是否有人存在”会变成有保证的不做判断。例如:最近发现我经常被幻觉所蒙蔽,我并不是每一次都成功地断定“我眼前是否有人存在”。事实上,普兰丁格也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中,如果一个人总是坚持“我眼前有人存在”会变为无法证实的。(15)因此,我的判断是有保证的,我的认知能力没有任何变化,改变的是认知背景。再设想,在一个可能世界中,一般人都由于上述情形而处于这样的不做判断中。如果一个人每次都坚持“我眼前有人存在”,这并不必然是他的某个认知机制被激发的结果,而是在他的经验中恰好总是能够成功地断定“我眼前有人存在”。(相反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我眼前总是没有人存在”。)这当然不能推导出幻觉必然不存在。正是因为他试图用偶然的成功取代所有可能的情况,所以我们才将他判为不合理,这当然不是他理性官能不恰当运转的结果。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某种基于公共证据的概率来有效地论证这个不合理。同理,这个与众不同的人也可以将其他人判为不合理的,他的理由也不是根据任何公共证据的概率。所以,A/C模型为基督教信念的持有者提供了很好的防守姿态,但是如果他要依据这个模型对非信念持有者的合理性做出判定时,就越出了模型生效的边界。一般人的判断应该是“我眼前可能有人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大多数时候,我们对于基督教信念的判定正是这种形式:“可能有上帝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这完全是有保证的不做判断。
总之,斯文伯恩与普兰丁格的争论集中于内在合理性究竟是否与概率(或然)相关。他们之间的分歧可以看作更深意义上的神学分歧,斯文伯恩来自于托马斯·阿奎那自然神学的传统,而普兰丁格来自于加尔文以来的改革宗神学传统。对于前者来说哲学与神学分享同一个对象,后者则认为没有信仰人无法达到最基本的认识标准,基督教并不需要自然神学。普兰丁格的A/C模型本身却是对两者的创造性综合,进而构建新的合理性概念。通过上文的分析可见:第一,普兰丁格反对把合理性理解为理性官能的恰当运作,其论证是有问题的。第二,普兰丁格根据A/C模型得到了保证概念,以此,运用他所排除的内在合理性概念来论证一种没有保证的情况。第三,通过重构认知环境概念,一方面我们可以取消斯文伯恩的概率问题;另一方面,仍然可以有保证地对事物的存在或上帝的存在做出或然判断。
注释:
①R.Swinburne,"Rationality and Public Evidence:A Reply to Richard Swinburne",in Religious Studies,Vol.37,No.2,2001,pp.203-222.
②④⑥⑧⑨⑩普兰丁格:《基督教信念的知识地位》,邢滔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76页;第310页;第127页;第211页;第211-212页;第201-204页。
③⑤R.Swinburne,"Plantinga on Warrant",in Religious Studies,Vol.37,No.2,2001,pp.207-208,p.210.
⑦即“非对称依赖性法则”,对这一法则的详细论证参见A.Fodor,Psychosemantics: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The MIT Press,1987,p.109.
(11)R.Swinburne,The existence of God,Clarendon Press,1989,p.154.
(12)(14)H.Putnam,The Threefold Cord:Mind,Body and Worl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02,p.46.
(13)约翰·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刘叶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76页。
(15)参见A.Plantinga and N.Wolterstorff ed.,Faith and Rationality:Reason and Belief in Go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3中,普兰丁格对“适义基础命题”(properly basic propositions)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