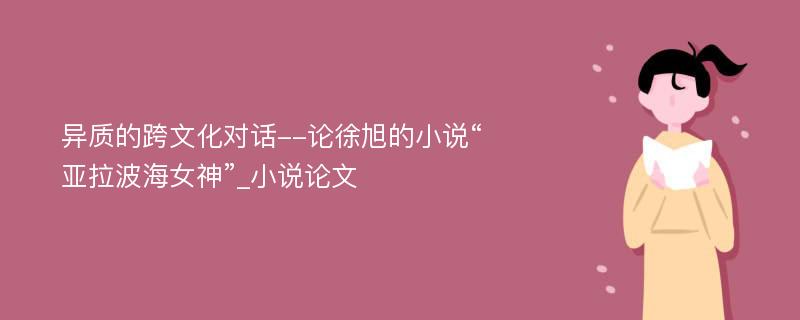
异质文化间对话:论徐訏海洋小说《阿喇伯海的女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神论文,海洋论文,异质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5)5-0102-06 一、对话:《阿喇伯海的女神》的研究新视点 《阿喇伯海的女神》是富有徐訏特色的一个小说,尽管难找到专论的文章,但它的基本特征已被挖掘。“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徐訏小说的异域色彩和浪漫情调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并广泛论及。”①小说刚好吻合上述两点。若按寻常的研究路径,哪怕文本细读的功夫一流,这个小说也难有再研究的价值;但是,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小说则有新的内涵与意义。 新读法就是把《阿喇伯海的女神》当做海洋小说解读,剖析海洋的意义。现代作家创作的海洋文学,从表层看,因为作家有海洋生活体验,海洋成为一种文学想象,如郭沫若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杨振声的《玉君》等;从深层看,留学所在国物质与精神的先进刺激学生大脑,他们必然会反思自身与民族,郭沫若海洋诗歌就有强烈的中国文化新旧更替愿望。徐訏在1936年赴法国留学,“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早已过去,他的涉海之路有不同于鲁迅、胡适等那一代人的意义。当海洋是一种连接不同文化或国家的纽带、更是异质文化的一个汇聚场域时,在叙事型的海洋空间,海洋想象可能是一种异域奇观,或者呈现为一种强势文化的霸权,也有可能是在不同文化间展开的对话。《阿喇伯海的女神》是一个展示异质文化间对话的小说,在海洋这个平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物或者说文化主体进行有效对话。对话,就是读解小说的新视点。 宁波作家徐訏以文化对话立场处理人物,这主要与他海洋文化的包容品格有关。开放、包容被学术界视为海洋文化的基本特征,从文化结构和精神看,他隶属于海洋文化。浙东海洋文化和他成长过程中接受的近代文化是他文化资源的基本构成,近代中国文化呈现由内陆向海洋转型的态势,一是文人由内陆走向海洋,二是他们吸纳西方海洋文化,浙东与近代两种海洋文化作用于徐訏,这使得他的开放、包容等海洋精神非常突出。就他的包容,有学者指出:“在文化问题上,他不主张以一种文化取代,克服另一种文化,也不主张一种文化拒绝与另一种文化对话,他强调‘实用’,充分尊重各种文化的存在价值与自足品位,重视各文化本身潜力的发掘。”②他的包容一以贯之,在60年代,徐讨论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戏剧改良问题,他主张:“改良不如另创新的,新旧并存,绝无坏处,观众自己取舍,不适的自然会自己淘汰。”③包容多元的文化胸襟决定了跨文化对话可能实现。因为包容,在文化冲突或交流中才不至于有文化沦陷为他者、或被强势文化消灭的现象出现,显然包容是对话的前提。从现实看,徐訏一直是一个对话型文人,在三四十年代,他创作了一系列中西对话的散文如《论中西的风景美》、《谈中西艺术》、《中西的电车轨道与文化》等,文化比较、交流、影响是这一组文章的主题,因此,当海洋叙事涉及两种以上的文化时,对话就是一种常态。 二、贯穿《阿喇伯海的女神》始终的七场对话 对话是小说的全部,一开始读者就被带到对话的境地。在阿喇伯海,阿喇伯巫女与中国留洋学生在航船甲板上对话,对话内容多半是哲学、宗教与爱,第一次对话的核心部分是阿喇伯海的女神,她是女巫所讲述故事里的一位女性。 在成为女神之前,她是海洋文化培育出的、心态开放的阿喇伯姑娘。首先,她的生活与海有关。她不是保守、封闭的女性,四处游历。因为开放,所以她听进孔子的话、读懂圣经、了悟佛理。如果从文化的大陆型与海洋型分类来看,她接受的文化为海洋型,这决定了她有开放胸襟。其次,当她在接纳其他宗教的时候,文化冲突在大脑中形成。她汇聚了多种宗教,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她并没有以超脱的态度对待冲突,而是认真地在海外求实证。女神的意义在于:在异质文化间发生有冲撞时,开放、包容是正道,不同文化一定要对话,否则,就有文化隔阂与悲剧发生。 第二场对话仍在留学生与巫女之间展开,对话的主题还是女神。在这次对话中,读者知道了女神的故事可能是巫女编造的也有可能是她的一个梦幻。本次对话是上次的延续,阿喇伯少女在跳海自杀的那一刻成了女神,在阿喇伯海她获得绝对自由,但她仍纠结于宗教问题。女神话题是下一次对话的由头。 在第三次对话中,一阿喇伯少女取代女巫出场。他们之间的对话从女神始,转而谈论中国宗教,由于这是青年人之间的对话,因此,话语由宗教自然过渡到爱,爱的信物则是指环。少女手上的指环是她母亲送的,从伊斯兰文化角度看这没有任何含义;留学生手上也有指环,它仅仅是主人买的一个玩物,并未包含爱或者宗教的内涵。不过,在后来的对话里,不但两个年轻人出现了交集,而且,异质文化也进行了有效交流、沟通。少女喜欢他的指环,在她的要求下他给她戴上。在有意无意之间,这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有了好感,以后将渐生爱意。有效的文化对话是指,从指环里他读出了阿拉伯人对子女的爱,如果说这是宗教的话,它就是一种普遍的宗教;她则知道在中国文化里指环是年轻人爱的凝聚,所以,她因为爱就喜欢、收受对方的指环。 在他们约会多次以后,小说叙述了第四次对话,话题围绕戒指展开,主题则是文化冲突下的爱。她手指上的戒指雕刻有一个阿喇伯民间故事的画面,故事说的是阿喇伯女子爱上一个异教徒,当地人在发现之后有两种处置方式。“一种是他们把这女子看作叛教的罪恶,将二人同时火毁或水葬;一种是如果女子肯用刀亲自将异教男子杀死,那么大家可以念经将男子超度。”就故事里的女子该如何作为,他们进行了一场跨文化对话,他们共同的看法是女子遇上了一个难题。故事的结局是,画面上在杀害爱人时内心矛盾且痛苦的女子找到了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她杀了男子又举刀杀死自己,临死前两人拥抱在一起,他们既获得了现世的爱在宗教里也获得永生。这个故事传开之后引发效仿,可怕的习惯随之取消。留学生在听完故事后说了两段话,对故事有精彩评述,他的话语引起她的共鸣,她将指环送给他,到此为止,他们已互送戒指,爱再进一层。总之,围绕一个话题,在爱的指引下,他们有着深刻且和谐的交流、沟通,并达成共识、增进感情。 随着爱意渐深,对话逐渐涉入实质问题,在第五场对话中女子的面纱是对话的内容。穆斯林女子戴面纱的目的在于凸显女性的贞洁、自重、虔诚,也包括有男性应尊重她的意思,因此,如果女子在男人面前掀开面纱或男子揭开女子的面纱,这表明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若非亲近关系的男子脱下她的面纱,这是一种宗教禁忌。留学生跟女子在甲板上观海上夜色,对话几乎零距离,面纱就是阻隔,有效对话必须突破宗教禁忌,不仅他希望脱开女子的面纱,而且她也鼓励他这么做,爱摧毁围墙。所以,从文化角度看,他们的关系接近亲密无间,这都是对话的结果,在脱下面纱后,他们就有深情的肢体接触。意料不到的是,面纱被风吹到海里,这是一件重大事情,从她说的“我怕我们间不是可以有这样的关系”来看,她预期的关系也就是到此为止、不可以结为婚姻的;但是,面纱丢失,有人会知道她的面纱被他揭开,他们触犯了文化禁忌,因而他们将面临选择上的困境,上次对话里戒指的故事是暗示,小说的后文正是戒指故事的延续与发展。 知道她面纱被他揭下即知道他们亲密关系的人是巫女,她是女子的母亲,第六场对话在巫女与留学生之间展开。看完整场对话,读者知道女儿与留学生的多次约会是母亲有意安排的或者她至少不反对,因为她是周旋在男人中间给男人看相赚钱财的巫女,女儿是她的学生,老巫女准备隐退,所以,留学生与女儿的约会是女儿出道江湖实习的好机会。在巫女的期望中,女儿在与留学生约会过程中她的意志会得到磨砺,因而灵魂纯净到可以抵御来自异性爱的诱惑;但是,事与愿违。从对话时她的语气和神态看,她对女儿极为失望,既然女儿面纱是他所揭而且心为他所吸引,她也只能按照伊斯兰的规矩:女儿应该跟他结婚。在对话中,他说出不能结婚的理由:一是他从中国文化出发认为,她是巫女的独生女,不能离开母亲,二是他突然记起家里还有妻与子。对第一条理由,巫女以女儿灵魂粗糙、心已为男人所属进行反驳,对第二条,她祭出阿喇伯文化禁忌,面纱是处女纯洁的象征。他既破坏了女性的贞洁而又不能同她结婚,难题最终只能依照阿喇伯风俗来解决,戒指隐含的寓意就要成为事实。 第七场对话是小说的结尾部分,对话核心内容仍是爱。三个人物都在场,巫女对留学生说:“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你们自己决定,一个是你死,还有一个是我叫我女儿死。前面就是海。”与戒指故事不同的是,母亲比较开明,允许他们结婚,与戒指故事雷同的是,如果不结婚,就有人死亡。他从中国文化立场阐释他选择死的原因:巫女只有一个女儿,他则有三个孩子,家族或个人生命的延续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巫女的女儿应该幸存;然而,女子也说:“不,这责任是我的。你有你的故园,你的家,你的妻子与孩子。”爱促使他们互相体贴对方,这是心灵的沟通,也正是因为他们融通了,所以,女子所言似乎也有中国文化色彩,即她从家的角度跟他对话,所说正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亲情。除了涉及中国文化,他们的对话还有伊斯兰教色彩。在跳入大海之前他说:“别了,爱,一切都是我的罪,请你原谅我。放弃现世,求永生吧。”他从宗教角度理解了他独死的含义,尽管他们没有现世,但是他们求永生。然而,她紧随他跃入大海,说:“爱,现在是我们的现世。”他们既有短暂现世,也获得永生。就生命而言,这是一个悲剧,由文化隔阂造成;但在宗教范围内,他们消解了悲剧。综上所述,第七场对话的两个文化场域两次实现了交叉,他们都进入对方的文化圈互访,爱是他们访问的动力,是有效对话之源。 由七场对话组成的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阿喇伯母女的影像神秘、模糊,这或许与对话只是一个梦有关。梦醒时分,船在地中海,由此看来,他的远航使他耳闻目睹阿喇伯风情,他才做梦。梦不遵循现实生活逻辑,所以,小说对阿喇伯母女的渲染主要体现在美丽上,究竟美到何种程度,小说没有详细描述;对中国留学生而言,这是美梦,更是对话的起因。二是对文化的交代倒是用了很多笔墨,如女神的传说、戒指的故事等,这为跨文化对话做铺垫。 三、对话理论观照下的《阿喇伯海的女神》 《阿喇伯海的女神》上演一个中国人与两个阿喇伯母女的对话,从文化上看,他们的异质文化间对话似乎预示了跨文化对话甚至文化间性问题迟早是文化研究界的热门话题,小说对该问题的介入凸显了它的先行意义。 多元和间性下的文化对话既是理论更是现实生活,当文学涉及该领域时,它也可以是一个研究视点。西方文化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蔓延,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话往往就是文化间的交往与对话,文化多元和文化间性普遍存在。有学者指出:“文化间对话并非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而是一种容易观察到的普通生活方式,它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在各种会议和工作场所中,都有多种文化的代表在其中。”④文化多元或间性的生活化存在于全球化时代是一种常态,文化对话的文学想象无疑会日益增多。从文化间性和文化多元角度看《阿喇伯海的女神》,本文无意区分两个概念的细小差异,而是将它们视为小说新读法的理论视点,由此窥视小说,挖掘其他学术角度难以发现的、小说在文化和艺术上的独创价值。 《阿喇伯海的女神》演绎的是中国文化与阿喇伯文化间的对话,对话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文化主体在与其他文化主体交往时并不以消灭、歧视另类文化为目的,而是将他者提升到主体地位。反之,如果存在有文化不平等,或文化主体被客体化,对话将无法进行。巴赫金就小说里的对话问题有独到研究,他明确指出在对话中,“人的客体性被克服了。……一个多元的世界展现在眼前,这里不只有一个,而是有许多个视点。”⑤换言之,因没有客体,交互主体性体现在对话中;由于对话的缘故,主体的文化身份得以展现,多元文化共存在同一空间。人物很快就进入对话状态,从对话的神态与语言看,双方都很尊重对方,人物间的互相尊重透露出他们没有将对方客体化的意愿,这为接下来的跨文化交流奠定基础。她是阿喇伯女性,代表了阿喇伯文化,他是中国人,代表了中国文化,在对话中他们的态度表明他们认同文化多元并存。她赞赏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并在中国住过九年,她还能说一口流利的北平、上海等地的方言;而他则欣赏阿喇伯人的聪明、数学头脑、女性的美丽。“文化霸权或文化中心主义”在他们中不存在,他们认可对方文化的价值,尊重另类文化的地位,所以,跨文化对话得以顺利展开,也可以说在对话中,文化多元成为事实。 中国文化与阿喇伯文化间对话的深广度与文化主体双方的开放度密切相关,即便各文化相互尊重,但若缺乏开放性,对话也不复存在,反之,文化主体若有着开放的胸襟,对话将透过表面深入实质问题。从他们的身份看,他是留欧学生,本来就是开放的产物,而她是全球流浪的女巫,不是一个保守的教徒,所以,他们实践跨文化对话具有可能性。长夜寂寞难眠的他们在甲板上有了对话冲动,这是一种初步的开放意识,随着话题的扩展,文化开放的口子越来越大,对话进入宗教层面,女巫所讲“阿喇伯女神”的故事包含了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纯粹回教徒的女子在与其他文化交往时,敞开心门接受了其他宗教的影响,而且容纳了异质文化,这个故事成为小说的核心,它恰好强调了对话中文化开放的重要性。当女儿代替巫女出场与他对话时,女神故事成新对话的开始,宗教话题延续,同时,爱成为对话焦点,他们的心态越开放,对话就越深入。 在文化间性视野下,文化主体不仅向内观照自己,而且还观察、体会对方,从对方的文化里发现自我,即彼此互为镜像。所以,有人指出:“不同文化的‘杂语’共存,还强调不同文化互为条件,在对方的存在中观照自我,个体文化的建构离不开他种文化,也就是强调在杂语中个体文化的个体性才得以显现。”⑥这种说法适用于《阿喇伯海的女神》。一般而言,中国的汉族人不信仰宗教或不是纯粹的教徒,但在对话中他从她的宗教文化存在里省察中国宗法社会,所以,他说:“中国人,孩子时代父母是宗教,青年时代爱人是宗教,老年时代子孙是宗教。”从他的语言里她领悟到中国的人伦观,她伸出手,展出母亲送给她的戒指,凸显所谓“中国的宗教”。显然,他们都从对方的文化里读解自己,这有助于对话产生共鸣并走向深入,因为这种做法既尊重、认同对方也亮出己方,有效的沟通技巧促使他们的关系日渐亲密。 在《阿喇伯海的女神》,文化主体有效地进行了文化间对话,异质文化在对话中实现了交互作用,它们甚至有实质意义上的彼此借鉴。文化间对话的目的不仅在于求同存异,更在于交互影响,这促使文化主体超越原有文化界限。譬如,留学生不断地赞赏伊斯兰母女的美貌,在伊斯兰文化中,女性美不在身体,但她们接受赞美,这表明她们冲破了文化禁忌。再如,巫女同意女儿与异教徒的留学生结婚,她原有的文化结构在多种文化对话中得以部分消解。就留学生而言,他接受巫女的安排,如不结婚他与巫女的女儿两人中就得有一个人死去,这反映出伊斯兰的贞节观进驻他的大脑。总之,小说里异质文化间的对话不仅有效而且深入,在文化上双方互相影响、彼此借鉴,文化实现了有限发展。 文化间对话显示,徐訏基于海洋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超前而敏锐地抓住了未来的热点问题:文化多元、间性及其实践。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认为他独创了一种思想对话的小说形式,徐訏的创作是否受他们影响还未可知,《阿喇伯海的女神》的对话显然是一种基于海洋文化和海洋背景的对话,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既有相同点更有独创之处。在海洋文化开放、包容基础上的对话是文化主体间的对话,呈现有文化多元和间性的特点。《阿喇伯海的女神》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来,留洋生活使得徐訏零距离地接触了多种文化,彼时文化冲突抑或对话在学术界还不是一个热门话题,徐訏却以小说的形式探讨该问题。在小说的操作上,徐訏设置了一个海洋空间,这是一个完全开放、包容的空间,非强势的中国文化与阿喇伯文化于其中展开双向交流,所以在异质文化间交往的探究上徐訏是一个先行者。 四、文化间对话的文学创新意义 在《阿喇伯海的女神》,文化间对话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它在小说中起到多种作用:情节在对话中发展、故事在对话中讲完、场景在对话中描述、人物在对话中刻画。因此,对话不仅有文化上的意义,它也是文学完成的一种途径。 小说对话都发生在航船甲板上,这是一个对话舞台,从总体上看,《阿喇伯海的女神》犹如一幕幕实验话剧。舞台是对话上演的场域,在巴赫金看来,“在戏剧里,这个独白框架自然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表现;不过正是在戏剧里,这个框架显得特别坚实牢固。”⑦如果真有这么一个框架,那它就是叙述者的独白;不过,也并非所有戏剧都预设了独白型叙述者,一些现代派戏剧往往是开放性的,无坚固的框架,它们只是提供了一个个的对话空间,而空间是开放的。《阿喇伯海的女神》是戏剧的变体,它的先锋性体现在:没有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即小说无坚固的框架,只有开放的空间,作为留学生的“我”、阿喇伯母女等都是对话中的文化主体,他们并没有被叙述者客体化,他们在小说里讲述自己以及对文化的理解,而不是单一地被讲述。 在文化主体的对话中,人物在讲述他们自己,包括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对宗教、文化的看法、对世界的认识等,他们的形象、个性或性格在他们的讲述中得以凸显。所有的人物,都由他们自己塑造或建构,即便是第一人称的留学生在小说中也只能叙述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不能讲述他人的故事。比如,当阿喇伯女儿替代母亲出场对话时,他一点不知道她们有何关系,直至母亲对他讲出真相,他才明白其中的内情。在对话中,读者了解人物身份,母亲是位巫女,从她说的话,读者还知道,她是一位见多识广、相对开放的阿喇伯女性,也是一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女性;在女儿的讲述中,读者得到的信息是:她是一位文化开放、勇敢、体贴、聪明的阿喇伯少女;在留学生的讲述中,读者知道,他是一位有志于改进社会、有着海洋文化开放胸襟的中国人。他们不仅讲述自己,还讲述文化,母亲讲过阿喇伯海女神的故事,女儿讲述了一个雕刻在戒指上的阿喇伯女子的爱情故事。在文化对话中,人物的思想、情感有冲撞、交流。关于“戒指故事”,他们的对话比较多,对话不仅让读者了解完整的故事、宗教上的禁忌,而且,他们对故事的解读突出了双方的文化差异。在他看来,穆斯林女子与异教徒相爱可通过私奔解决文化禁忌,这是中国式的读解;而她则从宗教角度谈该问题:逃跑失败,现世与永生都失去,叛逃成功只有短暂的现世没有永生。在差异中交流、沟通,他们最终达成一致,两个人的思想产生共鸣。综上,人物创造他们自己,对话是他们建构个人形象的唯一途径,在对话中他们讲述个人;另外,在对话交互影响的基础上,他们又修补个人形象,实现文化自我的创新。 对话不仅讲述文化主体,也讲述小说故事、推动情节发展。小说由七场对话组成,第一次对话是故事的缘起,最后一场对话是小说的高潮和结局,对话自始至终参与叙述。文化间对话完成了小说,它具有叙事功能,跨文化恋爱的故事在对话中被推进,对话讲述了他们相识、相恋、相爱、共同赴死过程。所以,这是一个文化对话体小说,没有对话,情节就无法展开。 海洋场域的文化对话是小说的内在结构,这种创新在现代小说中具有突出意义。严家炎先生在论述鲁迅的复调小说时认为:“鲁迅前期思想的基础是个性主义,但他同时也感到了作为思想武器的个性主义的脆弱。后来他接受了集体主义,但又从实践中似乎预感到某种条件下它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别称。这种种困扰着他的矛盾外化为作品时,就带来他的小说的极大丰富性与复杂性。”⑧与鲁迅不同,在《阿喇伯海的女神》,徐訏关注走出内陆、走向海洋的近代中国人所面临的中外交往中文化差异、对话、交互影响等问题;小说中的人物有特定的文化身份,他们的对话构成了文化多声部,但文化主体不是抽象的一般,而是血肉丰满的个人,在开放、自由的海洋,他们对爱情、文化、宗教等的看法有各自特点。总之,小说写文化却不沉闷、乏味,写对话突显了人物的主体性,写爱情展示了异质文化间交流,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具一格,研究者目前还未发现有同类作品,所以,徐訏文化间对话的想象开创了一种中国现代海洋小说新样式。 注释: ①陈娟:《徐訏小说中的西方形象》,《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6期,第138页。 ②吴义勤:《徐訏与中外文化渊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93年第4期,第146页。 ③徐訏:《关于新旧之争的检讨》,载《徐訏文集第10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9页。 ④杜维明:《文化多元、文化间对话与和谐:一种儒家视角》,《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337页。 ⑤巴赫金,白春仁、晓河译:《文本、对话与人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7页。 ⑥郑德聘:《间性理论与文化间性》,《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76页。 ⑦巴赫金,白春仁、顾亚铃译:《诗学与访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⑧严家炎:《复调小说:鲁迅的突出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