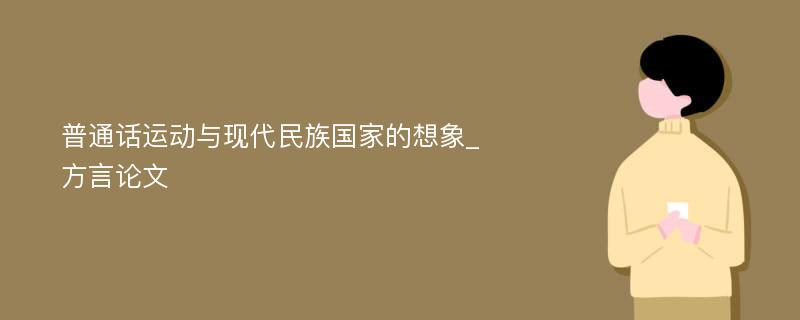
国语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语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0)04-0089-07
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则得益于印刷语言的诞生与传播。印刷语言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那些原先操着不同语言的人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能够相互理解了。“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形成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胚胎”。①安德森的论述对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兴起似乎更为有效,在欧洲各民族语言发展的现代谱系中,各个现代民族国家语言的诞生是以挣脱古老的神圣语言——拉丁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逐渐向地域方言靠拢,通过现代印刷语言从而建立起各区域的书面语言。换言之,欧洲现代民族语言的诞生是以地域方言替代神秘拉丁语的“祛魅”过程。对于晚清以降的中国而言,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印刷语言的产生和欧洲并不相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在现代印刷语言产生之前,已经有了自己公共的书面语言——只不过这一语言的表述体系是以占知识垄断地位的士大夫阶层的古典文言为主体。中国的现代语言运动从两个路径展开:一是推倒艰深晦涩的古典书面语言、建立言文一致的现代白话书面语言的书写体系;二是追求“国语统一”、使方言纷歧的区域语言向共同的民族统一语靠拢。与欧洲各国相比,中国近代以降的国语运动遭遇的问题更为复杂,“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始终存在着难以兼顾的紧张。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方言歧异,言文一致必然带来区域方言文学的张扬,国语统一(侧重于读音统一)也因标准不同带来向“谁”统一的纷争。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而言,与其说是印刷语言造就了民族意识,还不如说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危机意识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统一运动——以开启民智、普及知识为目的而展开的白话文运动,借助白话报刊和通俗读物这一现代印刷语言使普及教育成为可能。
一 普及知识与民族救亡
19世纪末逐渐展开的国语运动既是以普及教育、动员民众、挽救危亡、富强国家为目的,又蕴涵着完善民族文化符号系统、促进民族文化革新与发展的现代性旨归。国语运动包括汉字改革和国语统一两个相互依存、相互推进的方面。汉字改革旨在以逐步走向汉字拼音化的废除汉字运动和汉字简化运动,国语统一旨在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语音为基本音的汉民族共同语的语言规划运动。不论是汉字改革还是国语统一都是通过知识普及一般民众最终达到民族国家的富强。因而,探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有必要追踪晚清以降国语运动者如何通过现代语言革命以谋求知识普及的思想理路。
国语运动从两个层面展开,其一追求言文一致,即推广白话文,达到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一致;其二统一国语,即在全国推广统一的语言,达到语音、语法和语汇的统一。言文一致的最初动力,首先源于救亡图存的内在诉求,卢戆章集十多年之功精心研制出“切音新字”,目的在于让国民迅速识字以普及教育,从而达到“国之富强”: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文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供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②
这种唤醒民众、救助国家的崇高理想与严肃信念不能一概认为是天真浪漫之举,实乃出于知识普及与民族救亡的自觉。这种自觉的责任担当则是一以贯之,直到1906年,卢戆章仍“痴心不改”其原初主张:“倘吾国欲得威震寰球,必须语言文字合一。务使男女老幼皆能读书爱国。除认真颁行一种中国切音简便字母不为功。”③
知识者改良文字的动机莫不如此。沈学19岁研制切音字画,同样以谋求国家富强为根本,并以知识推广与普及作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历5年之功而成的《盛世元音》序指出:“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文字之易难,智愚强弱之所由分也。”。近人王炳耀于1896年著《拼音字谱》一书,自序中表达了其创制字母的深层动机:
是书拼音成字,书出口之音,运之入心,不由耳而由目,使目见者即明犹以口宣言,使耳闻者即达声入心,通别无难义也。各字读法,先声母后韵母,有左自右,自上而下。或先大后小,按音拼成,有识之士,虚心推行,始于家,继而乡,渐而国。合国为家,天下莫强矣。④
王炳耀当时是否形成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并不清楚,但他创制字母、普及知识以达到国家富强的观念则极为自觉。
应该说,近代以来中国知识者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与西方列强的刺激密切相关。以1840年震惊中国士人的鸦片战争为标志,民族问题开始成为困扰中国知识者的重大问题。尤其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以后,凭借船坚炮利,弹丸之地的日本彻底粉碎了中国这一老大帝国的千年神话,“保种图强”的呼声霎时弥漫于朝野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语言改良者均在1896年也即甲午之战后刊布其著作——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力捷三的《闽腔快字》,这看似巧合,却大有进一步研讨的兴味。甲午海战之后中国知识者的焦虑心态与谋求富强的心理吁求甚为强烈,受“中日甲午战争之巨大冲击,有识之士,已深感危亡迫在眉睫,谋求以自立自存,惟有共图富强。欲共图富强,又不能不唤起民众,结合群力。欲唤起民众,使人民共抒建国智能,自须使众民先有知识有技能……于是语文工具,首先必须健全而简易,因是普及知识实为当时知识分子觉醒后急求达成之重大目标,语文改良则是达成此项目标之必要手段。”⑤普及民众知识是语言改良和民族富强之间的一个中介,借助这一中介,语言改良和民族富强之间发生了直接关联,语言运动先驱者创制拼音字母绝非一时兴之所至,实质上寄托了他们谋求国家富强的严肃思考。劳乃宣1907年著成《简字全谱》,其自序中说得甚为清楚:“识字者多,则民智,智则强;识字者少,则民愚,愚则弱。强弱之攸分,非以文字之难易为之本哉!然则今日而图自强,非简易其文字不为功矣。”⑥这种通过语言文字改良以开启民智进而达到国家富强的思考路径,为许多国语运动者所共享。朱文熊在其《江苏新字母》的自序文中叙述创字动机,同样是出于国家富强的考量:“我国言与文相离,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国不能强盛。泰西各国,言文相合,故其文化之发达也易。”⑦
借助开启民智的重要一环,改良语言与国家富强直接关联,“言文合一”被视为“国之富强”的根本。如果说近代以来渐次涌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日益成为一种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话语,那么,借助这一日渐深入人心的合法性话语,语言改革运动也自然成为国人自觉认同、无可置疑的救国壮举。
晚清形成的这一基于知识普及、民族自强的语言变革观念,为以后的国语运动者所承续。钱玄同1925年《国语周刊》的发刊词指出:“我们相信这几年来的国语运动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药,因为有了国语,全国国民才能彼此互通情愫,教育才能普及,人们底情感思想才能自由表达。”⑧国语运动与挽救民族危亡的内在关联是靠民众教育的普及来完成的,这一运思逻辑仍可视作晚清知识者开启民智的思想余脉。三十年代以后,中华民族走向最后的危急关头,民族战争的烽火再次激荡起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为动员民众融入抗战救国的滚滚洪流,变革语言以普及知识从而进一步激发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遂成为又一波澜壮阔的变革大潮。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在为征求各界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书中强调:“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并进而呼吁国人积极推行大众易学的拼音化新文字,“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⑨张一麐把三十年代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作为“抗战建国的第一问题”,并充满自信地期待拉丁化新文字推行以后,“必能使我国文化,另有光明灿烂、不可思议之黄金世界。故以为抗战建国中第一之最大问题。”⑩语言文字每一重大改革无不表达了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诉求,而改革语言文字以普及民众教育则是达到这一诉求的基本步骤和中介。
二 “国语”和“国民”
晚清以来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之下被迫融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地理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更让传统士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绝非“天下之中心”,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逐渐进入个人的生活空间。1904年,陈独秀透过甲午战争与鸦片战争的历史风云猛然意识到:“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得脱呢。……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11)陈独秀的警醒之言在近代以来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至少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讯息——文化中国在遭遇世界体系的过程中是如何从只讲“私德的个人”催生出具有现代性的国家观念的。张东荪也有类似表述:“中国与之(欧洲)相遇,倘使以统一大地(即东亚)的中国与统一大地(即欧洲)的西方作文化的交流则情形必与今天大异……中国之受苦全由于他们(欧洲)忽自走上了民族国家的路子,而中国仍为一个‘天下’以致赶不上。”(12)梁启超说得更直接:“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13)民族国家对于处在救亡图存情境下的中国知识者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建立民族国家不但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自我保存的需要,也是中国人重建现代集体认同的重要方式。
国家毕竟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要建立一个富强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必须要求中国传统型个人身份进行一番彻底有效的现代性转换,“在此种全体化国力为竞争单位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民都要成为国家的有机体的一份子。个个‘人民’都得练成一个得力的‘公民’。”(14)晚清以降,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以及“群”、“社会”、“民族”、“国家”等范畴的引入,传统观念中只关注“私德”的个人相应地也被重新界定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如同“国家”一样,“国民”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中国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家者何?国民者何?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集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为国民。”(15)梁启超明确指出“深察祖国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必先铸部民使成国民,然后国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16)现代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存亡兴废问题被还原成为一个与各个国民素质密切相关的问题,民族国家的宏大想象与具体而微的国民形象建立起同构性的关联,无怪乎梁启超有如此的喟叹:“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17)国民的塑造与国家的存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国民是组成国家的细胞,国家是全体国民自我认同与自我确证的公共场域。既然二者如此紧密,那么,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就自然落实到新型国民的塑造上。
个人必须具备何种素质才能取得现代国民的资格?二十年代初,正值国语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国语运动的积极鼓动者甚为直接地说道:“凡为国民者,无一不当谙习国语,其理分明。若但能讲土话者,则仅可谓之土人儿不可谓之国民。故欲养成国民之资格,谙习国语其一也。以谙习国语为养成国民资格之一。”(18)这位国语倡导者饶有意味地运用语言和文化身份进行直接对应——能说“国语”的“国民”和只会讲“土话”的“土人”,国民/土人的价值等级显而易见,与之对应的国语/土话的语言问题也悄悄转变成为文化身份与价值地位的高下问题。关于“国语”和“国民”的表述,当时的一位国语倡导者说得更为明白:“‘国语’是国民所应说的。不会说国语的人就算欠缺国民资格的成分。”(19)当然,习得国语只是养成国民资格之一种,除此之外,普及民众知识、提高国民素质也是培养新型国民的重要手段和必备步骤,而这一工作在晚清以降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中早已从观念到实践各个层面渐次展开。
三 “统一国语”与“统一国家”
国语运动涵盖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个方面,言文一致在于使知识能够普及一般民众,通过现代新型国民的塑造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而国语统一试图通过造就一种全民通用的语言以达到团结国人之目的,借助语言共同体的形成以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语言认同,从而进一步巩固民族国家的统一。
1926年1月3日,全国国语运动在《申报》上打出了这样响亮的口号:“有统一的国语,才有统一的国家。”(20)这一口号极为鲜明地表达了“国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在同一日的《申报》上,有文章把“国家主义”和“国语运动”作为相互依存、殊途同归的两个方面加以论述:
近来有两种大的运动遍于全国,一种是国家主义,一种是国语。从事这两种运动的人不完全相同,因此有人疑心主张国家主义者对于国语运动漠不关心,甚至反对,这就不免神经过敏,或不明了国家主义的目的了。国家主义的目的是什么,不外“内求统一外求独立”八个大字,依着国家主义的目的,说明他与国语运动的密切关系,并表明我们国家主义者对于国语运动的态度。
方言复杂,是中国统一的一个大障碍,国语运动的主要目的在免除这个障碍,另外造成一种统一的语言,使全国的人个个便于交谈,不因语言而发生隔膜。这种目的完全是国家主义的目的“内求统一”相合,内求统一是个大目的,统一语言的目的,是从这个大目的推演到特殊事项的一种小目的。(21)
这里所论及的“国家主义”主要指五四以后盛行于中国、与民族主义相关的一种思想潮流。国家主义是建立“绝对主义国家”(或者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前阶段)需要的产物,它主张国家具有绝对的价值和权力,个人必须为国家做出必要的让步和牺牲。国家主义是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应运而生的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几乎难以分割,它是同一思潮的两个方面:对外张扬民族主义以抵御外侮,对内主张国家主义以统一“政令”;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存在的理由,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必然归宿。自民族主义诞生之时,国家主义也就相伴而生,二者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方面,可谓是携手互助、目标一致。正是在这一点上,国家主义的“内求统一”与国语运动“统一语言”达成了共识。
为建立独立自主、文明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必须整合多方力量以通力合作。国语统一也在这方面获取了“支援意识”:
天下事合力易成。独力则难治。力之能合,由于情之互契,欲情之互契,必赖语言之传达,语言者,沟通情意之利器也。世界列国,各有统一之国语,我国则反是。……兹敢正告全国国民曰:我国民不欲自强则已,若欲谋国家之富强,民情之一致,非先谋国语统一不可。(22)
这里把“谋国语统一”作为“国家富强”的必备条件,其论述思路与“普及知识”以挽救民族危亡的观念大体一致。但侧重点已大不相同,“普及知识”落实在语言上强调“言文一致”,而“国语统一”则更强调全民族共同语的建构,以交流感情、破除隔阂、团结整体。如此说来,语言不但关系到“感情之联络”,更关乎“国体之尊严”,语言交流已不再视为个人之间便利交流的区区小事,而是被链接到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框架中得以放大和强调。
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其共同体内部的成员必须借助可分享的共同资源建构并巩固其共同“想象”。自从中国被迫拖入了世界体系,其社会内部的关系也变得日趋复杂和深化,社会交往得到加强,由此推动了共同地域、共同语言等各个层面的同一“意识”。这一共同“意识”在国民中形成了类似文化纽带的“认同感”。二十年代日渐高涨的国语运动,就认识到并进而借用了“语言”这一能够强化共同体成员之间集体认同的丰厚资源:
国语是建国的基础,建国的要素,在普通的政治教科书中,都大书特书的是人民,土地,主权。人民在这三种要素中是最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国家存在的根本条件。但我们想为什么这些人和这些人组成国家,那些人和那些人组成国家,而这些人和那些人不能组成国家呢?这时我们总可想到一件事实,凡是同处在一个国家下面的国民,他们所用的语言文字一定是一致的,……语言文字的一致,是建国的基础,也是国家形成的原因。
国语的效用,可以团结民众的精神,一致民众的感情,使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大成一片,则民众帮助国家,国家帮助民众,这时才有和平幸福而言。(23)
这些论述尽管仍闪烁着“国家主义”的言词,但已经把“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做了更为恰切的论述和调整,国家是以保证民众的和平幸福为前提的,人民作为国家存在的首要因素,能够被组织在“国家”这一共同体之下并相互认同,共同的语言起着关键的作用。在社会学意义上讲,民族是由一系列文化符号所建构的“臆想”的共同体,认同这一共同体的各成员只有分享共同的情感才能承担共同的命运,而语言在这里被赋予了“一致民众情感”的沟通功能。
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而言,由于民族众多而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乃至同一民族内部也因地域不同形成了各自的区域方言,共同语言是解决民族认同的重大难题。语言学家赵元任就清楚地认识到汉语方言的纷歧之处:“从哈尔滨到昆明,从重庆到南京的官话区,言语还比较一致,可是东部和南部方言之间的差别,不亚于法语之于西班牙语,或者荷兰语之于德语。”(24)指出差别并非执意要否认汉语各方言应该隶属于汉语主干之下,但不同地域之间的语言差异确实大得惊人,如闽、粤方言之于北方方言。语言学上的“方言”(dialects)和我们汉字日常语汇中所讲的“方言”并不相同。在语言学上,“方言(dialects)”本意为一种“语言”内部细分出来的同一语言的变种(variants),而且这些语言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当一种语言的几个变种“方言”演化到彼此不能理解时,它们就成为各自独立的“语言”了。在这个定义之下,文艺复兴前后在欧洲发展出来的各种“地方语言”应该算是独立的“语言(language)”,而非“方言(dialects)”。循此思路,倘若从语言学的角度观之,以“相互可理解性”的标准去衡量,中国许多所谓的“方言”(如吴语、粤语、闽语)其实是各自独立的“语言(language)”,正如赵元任所说的“法语之于西班牙语”、“荷兰语之于德语”那样的区别。那么,国语统一运动所要建立的共同的“国语”——共和国成立之后谓之“普通话”——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而构建的呢?有研究者指出“所谓‘国语’或‘普通话’之成为‘标准语’,而闽南语、粤语沦为‘方言’,并非基于语言学上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特别是民族主义——的考虑。”(25)这一论述极为透辟地道出了语言运动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深刻联系。
迄今为止,没有哪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不对本国的语言进行“现代性”的规划和设计——虽然规划的方式和路径因各国国情不同可能会不尽一致。“自古以来,语言文字问题始终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关系到公民的人权。政府所制订的语言文字政策是对少数民族态度的具体化。在现代,几乎所有国家都要解决国家或民族通用语(官方语言、标准语、国语等)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26)因而,晚清以来的国语统一运动对于汉语语言的现代性想象与建构并非只是语言学内部的问题,实质上关系到民族复兴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宏大叙事”。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语运动常常得益于政府强有力的资助,显然是政府与国语运动家之间的“合谋”,而文学运动则似乎只能是文学倡导者的“单打独斗”。国语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合流是二者互胜双赢的壮举,国语运动借合流以扩大其声势,新文学运动则借合流奠定其合法性。胡适“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宣言无疑昭示出二者都有建立现代中国民族共同语的宏大构想,只是方法不同,思路相异而已。其间隐隐呈现的民族国家情怀也为后人所体察:“中国的近百年史,是说明了中华民族的垂危状态,新文学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发生,是为了担负时代所交给他们的一个急迫而重大的使命——把中国从死的漩涡里救出来。”(27)三十年代初有人更为透辟地指出白话文学运动与建立现代中国的直接关联:“白话文运动是战后受民族自决主义的影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革新并建立现代中国的表现。”(28)
应该说,无论是新文学作家还是国语运动家,他们在革新民族语言以建立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情怀是自觉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国语运动的积极推行者黎锦熙就说道:“现在统一告成,建国伊始,教育事业,民治之基,增修国音字典这件事,于普及民众教育,及统一语言,化除畛域,团结中华民族,增高国际地位,都具有重要的关系。”(29)到了国难当头、战火纷飞的四十年代,国语运动的目标仍“痴心不改”:“现在,贯彻初旨,策动方来,国语教育,仍不外乎两个目标:一曰谋教育之普及,二曰谋民族之团结。”(30)此时,为进行战时的民众总动员,识字扫盲运动与语言文字的普及化教育较之以前任何时期都显得更为紧迫,识字运动仍然是为了增强民族意识、抗战建国的需要。国语运动借助抗战时期的民众总动员走出了书斋、扩大了影响,而普通民众则通过学习注音符号不但获取了知识、增强了民族意识,也使国语运动的成果得以在社会中实践和推广。
抗战结束之后,语言学家魏建功于1947年主持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针对许多人对国语含义不明,他强调“民族共同所有的表现意思的声音是国音,民族共同所有的表现意思的图形是国字,民族共同所有的表现意思的编录是国文,用国音读出来国字写出来的国文就是国语,最精彩的成为文学。”(31)值得注意的是魏建功先生接连用了三个“民族共同”,足见国语对于整合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地位。
共同的语言是巩固民族认同的首要质素,正如安德森所言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那么,晚清以降国语运动正是巩固这一想象的有效途径。
注释:
①[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53页。
②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2页。
③白涤洲:《介绍国语运动的急先锋——卢戆章》,《国语周刊》12期,1931年11月21日。
④《万国公报》月刊第114卷,1898年6月。
⑤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06页。
⑥劳乃宣:《〈简字全谱〉自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77页。
⑦朱文熊:《〈江苏新字母〉自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第60页。
⑧钱玄同:《发刊词》,《国语周刊》(京报附设之第七种周刊)第1期,1925年6月14日。
⑨《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见倪海曙编著《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始末和编年纪事》,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02-103页。
⑩张一麐:《抗战建国之第一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第259页。
(11)陈独秀:《说国家》,《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12)张东荪:《思想与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
(13)梁启超:《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899页。
(14)林同济:《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一个关于忠孝问题的讨论》,《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69页。
(15)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09页。
(16)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066页。
(17)梁启超:《爱国论》,《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72页。
(18)《国语之关系》,《申报》1922年10月18日。
(19)焉云鹏:《励行国语以收统一之效案》,《新教育》第11卷第2卷,1925年9月。
(20)《申报》1926年1月3日。
(21)陈启天:《国家主义与国语运动》,《申报》1926年1月3日。
(22)《统一国语之利》,《申报》1926年2月22日。
(23)吕一鸣:《国语的效用》,《学灯》6卷第8册第26号。
(24)《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80页。
(25)这一论述出自吴叡人,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26)许嘉璐:《序》,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等编:《国家、民族与语言——语言政策国别研究》,语文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27)彭惠今:《新文学运动与国语运动——五四前两大潮流的汇合》,《国语周刊》(南郑版)第21期,1942年6月1日。
(28)樊仲云:《关于大众语的建设》,《申报·自由谈》1934年6月30日。
(29)黎锦熙:《本会的编审工作》,《国语旬刊》第1卷第1期,1929年8月1日。
(30)黎锦熙:《〈国语〉周刊(南郑版)发刊词》,《国语周刊》(南郑版)第1期,1941年3月8日。
(31)魏建功:《国语通讯书端》,《国语通讯》第1期。(该期为创刊号未注年月,但翻阅第4期,出版时间为1947年2月。估计第1期应该在1947年1-2月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