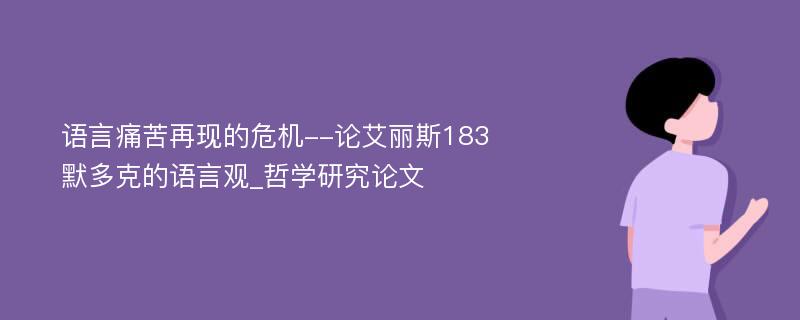
语言之病痛 再现之危机——论艾丽丝#183;默多克的语言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病痛论文,危机论文,艾丽丝论文,默多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西方作家普遍深感困惑,不知如何再现纷繁复杂的当代经验,他们为自己想象力的贫乏感到尴尬(Roth 34)。再现成为知识界关注的首要问题,语言和它所表达的东西之间的鸿沟问题处于当代文学和哲学的中心。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成为被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为“其显赫地位当代英国小说家无人可比”(Bloom 7)的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终生关注的问题。在这位“自乔治·爱略特之后英国最具智慧的”女作家的作品里(Fletcher 547),语言对所有的人物都有着深远影响。讲述真理是不可能的,这一概念反复出现,表明语言的功能发生了障碍。人物一次次地发现不能说话,因为不存在表达意图的词语。他们失去对词语指涉功能的信心,不论是书写还是口头语言,设法通过语言来交流的努力无不导致谎言(Bove 11)。
默多克关于语言的思想异常丰富,态度也极为复杂。本文作者认为,她的语言观与她独特的“崇高”小说理论密切相关。她指出当把观照的对象从自然景象换成人类生活的景象时,康德的崇高理论可以转化成艺术理论。小说家面对杂乱无章的外部世界,就如同观照者面对令人惊叹的无穷自然中的崇高对象。她锲而不舍地探索这种真实如何通过语言在小说中得以再现。对20世纪现实“崇高”特性的认识影响了她对语言的信任。语言是抽象和含混的,无力表达外部世界的偶合无序和人的独特性。语言又是有限制的,当我们努力扩大语言的边界时,得准备接受它的限制。在思想和语言的边界,当“看见”不能说的事情时,默多克不是沉默,而是采用特别的叙述策略。语言虽然出现指涉能力的危机,却仍然是有意义的。语言能通过忠于真实来完成根本任务,赋予无法清晰表述的现实以意义。这位自称“维特根斯坦式的新柏拉图主义者”(Chevalier 90),在对柏拉图的解读和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中阐明了自己的语言思想,在对德理达思想的批判中展现了他们殊途同归的语言观。本文将结合默多克的小说理论和实践尝试对此进行论述。
一
默多克在早期发表的著作《萨特:浪漫的理性主义者》(Sartre:The Romantic Rationalist,1953)和两篇论文“再谈崇高和美”(“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 Revisited”,1959)及“反对干枯”(“Against Dryness”,1961)中,提出了小说发展的两种对立传统模式。此后虽未再对此进行系统论述,但是原则上她明显持相同观点。一种是自由主义传统,以莎士比亚和19世纪简·奥斯丁、乔治·爱略特、托尔斯泰等经典现实主义作家为主;另一种是浪漫主义传统,起始于浪漫主义时期,经由艾米丽·布朗特、霍桑到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及其后继者,如萨特、加缪等。第一篇论文的标题提供了另一种表述。她运用康德对崇高和美的著名区分,指出浪漫主义传统尊崇创造“美的”神话模式胜于再现世界“崇高的”不同性。她称属于这一传统的典型作品为“水晶体”式小说,其中每一个引喻和意象都与作者构建的神话结构切合。它们是“关于世界简化了的文本,略胜于某种理论的化身,是一种通过给生活中不可思议的因素套上理论结构来约束它们的方法”(Nicol 5)。她对这类小说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解读现代主义小说,对“自由主义的”、“崇高”的小说的讨论则特别具有原创价值,并与她的语言思想密切相关。
默多克把康德的崇高理论转化成小说艺术理论。康德在区别崇高和美时指出,自然中的美是对象的形式问题,形式都有限制,而崇高是在没有形式的对象中被发现的。美可以说美在形式,这种形式仿佛经过设计安排,适合想象力和理解力自由活动及和谐合作,因而产生快感。崇高的对象则“适合表现心灵固有的崇高;因为对于什么是崇高,就这个词的恰当意义而言,不是感性形式所能容纳的,而是仅仅涉及理性思想。这种思想虽然不能充分展示,但是正是这种能用感性形式表现的不充分,才把心里的崇高激发起来”(Kant 49)。哲学家通常把崇高定义为一种情感经验,理性尝试了解无边无际、没有形式的自然,虽遭受失败却依然洋溢着生命力。默多克认为崇高孕育着一种悲剧概念,一种把文学和道德连接起来的理论(Murdoch,“Sublime”264)。最能够与道德和精神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小说,能够让我们认识自身之外广阔而多样的真实,这种认识最初给人带来恐惧感,随即因恰当理解而转化为振奋感和精神力量。不过,这种经验以最重要的形式带给我们的不是自然世界的景象,而是包含其他人的周围世界的景象(Murdoch,“Sublime”282)。当“再谈崇高和美”于1961年发表时,它不啻为一篇强有力的宣言:默多克将远离关于美的对象的现代主义美学,追求关于崇高对象的美学,即追求具有自由宽容精神的现实主义美学。
默多克对崇高对象美学形式的使用,似乎表明在她的小说理论和实践之间总是存在着鸿沟。这并不是作者为自己设定了一个过高的目标,作为小说家她无法企及。这一问题可以从战后作家面临的共同危机来解读。战后小说的主要形式是现实主义,它不同于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Gasiorek 77)。语言和真实之间的鸿沟问题是回归现实主义带来的特殊问题。对真实的语言学构造和用以限定、修正和容纳它的概念体系,20世纪始终有一种坚定的意识(Sussman 130)。到了后现代,再现进入真正的危机阶段,并处于后结构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批评的中心位置。默多克很看中古典现实主义作家为了忠实再现永恒真实而坚守的那些做法。他们坚信某些道德价值,这首先表现在小说结构上,其次在人物概念上。小说中有不同等级的声音和位置,作家处于顶点,占有统治地位。人物虽各有特殊性,但大体上是不变的,基本为读者熟知。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以这种方式让人相信,社会与此类似,依赖于一个紧凑自然的秩序。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却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很成问题,它所依赖的一套语言理论是虚假的。“语言不再现外部世界,而是构成那个世界;去试图描写外部世界,就是已经去解释它了”(Nicol 19)。
何以会产生这种变化呢?可以回到默多克早期关于语言的观点中去寻找答案。对于语言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她首先认为不可能有清晰的回答,因为人对语言的意识在最近的过去发生了变化。她曾写道:“我们不再能想当然地把语言当成交流媒介,它的透明性已经一去不返。我们就像长久以来站在窗前往外看但并没有注意到玻璃存在的人,有一天开始注意了”(Murdoch,Sartre:Romantic Rationalist 26)。虽然在英国这种意识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洛克,但只是在最近的一个世纪里,它才有了那种令人眼花缭乱和着迷的形式。人们几乎在每一个领域差不多同时都有了一种发现,原来“物质的(thingy)”世界观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被改变甚至瓦解。这种碎片化过程有时可能以一种新形式出现,比如在绘画领域,印象派画家发现一种更准确的观察,它给画家们带来一种纯粹的快乐。当莫奈宣称绘画中的主要角色是光线时,他并不感到失落。在快乐的印象派画家的眼中,自足的世界被转化成了表面闪光的迷雾,那是一种感觉的舞蹈。作家没有画家那么幸运,他使用的是词语,但却没有准备好接受新的技巧,作家由此经受令人痛苦的剧变,在语言运用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危机。首先是诗人对此作出极端反应,因为诗人总是比小说家对语言更为敏感。象征主义者尝试在诗歌中故意违反常情地运用语言,或者有意使之晦涩难懂(Murdoch,Sartre:Romantic Rationalist 26)。
诗歌语言尽管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交际语言”,但是诗人认为词语和句子理当拥有正常的指涉能力。语言指涉精确度对诗人一直是重要的,而现在整个语言的指涉特征似乎突然变成了一种障碍。就好像由于某种可怕的特殊原因,诗人开始把世界看成一团无法表达的东西,却仍然感受到言说的必要。这样诗人在两种极端方式中可以体验到语言的破碎过程。一方面,诗人可以接受甚至强化对真实的混乱感,对于这个过分丰富的世界,设法使语言变成完美表达。这将使语言超载,削弱其指涉特征,兰波就是一例。他似乎在寻求达到一种梦幻般的完满,通过大量堆积准确而又高度感觉性意象,在读者思想中制造一种无所不包容的高度混乱。另一方面,诗人可以设法把语言干脆从无法表达的变化当中完全排除,为语言本身构建一个纯粹非指涉性结构,如马拉美。他寻求使语言行使某种不可能的功能,让语言除了指向本身之外而无任何指涉功能,读者被一种纯粹的符咒镇住,语言的寻常意义被从大脑中有系统地清除。对于这两种诗人,语言都成了某种形而上的东西,他们需要与之进行斗争(Murdoch.Sartre:Romantic Rationalist 27)。
那么,是世界先变化,再把语言拖在后面,还是一种对语言的新意识突然使人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默多克认为,哲学家语言意识发生革命的原因是科学而不是诗歌。19世纪的科学方法和数学符号,使哲学家看到象征(包括词语)与真实之间的全新关系。科学定义模式被突然用来解释语言,一句话只有一种解释,而且是对感觉得到的观察作出的解释,观察决定解释的真实性。语言的功能成为界定、解释和预测感官经验。形而上的东西被排除在外,物质的东西被瓦解成表面或者感觉,这样陈述才具有合理性(Murdoch,Sartre:Romantic Rationalist 28)。令默多克扼腕叹息的是,这样的科学运动使人们丧失对语言交际能力的信心。由于交流取决于说话者对一个共同世界的经历,习俗常规把词语的使用跟这个世界联系起来。想必默多克会赞成尼采。尼采强调语言在塑造概念和信仰上的关键作用,人本来是完全可能发展一种相当不同的语言,因为在语言分类中存在任意性和偶然性。虽然所有的陈述都可能是“谎言”,但是尼采允许在真理和谬误、知识和错误之间有一种可行的区别。人如果要有一种社会生存,满足各种需要,彼此得就许多事物达成一致,包括为交流和合作的目的对事物的指涉。当一个人给予一个事物那种约定俗成的指涉时,他就在说真话(Nietzsche 79-91)。
在默多克看来,共同背景的丧失使语言对于交流日益表现出不足,在表现真实方面的能力令人怀疑。在她本人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实践之间,存在鸿沟,出现语言之病痛,再现之危机,便不足为怪了。
二
默多克的“崇高”小说理论决定了她对清晰的语言在再现真实方面的能力深表怀疑。她的哲学以对道德主体的人的理解作为开始。这个起点和萨特的一样,借用海德格尔的话,就是人被抛入这个荒谬的世界,被不同的他人和物包围,人试图赋予它们意义的努力遭到抵御。不过,她很快和萨特分道扬镳。作为第一位把萨特介绍到英国的哲学家,她不能理解萨特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什么对外部偶合无序的世界不是感到光荣而是恶心?”(Murdoch,Sartre:Romantic Rationalist 49)在她看来,孤独的现代人不应成为唯我主义者,对外部世界感到恶心,而是应当通过一个消除自我的过程,转向超验的真和善。如同另一位关注当代社会人之孤立无助的神秘主义哲学家西蒙娜·未伊一样,她的选择是转向柏拉图。在她关于哲学和语言本质的讨论中,柏拉图始终处于中心位置。
默多克反复玩味柏拉图关于语言和真实之间关系的思想。他的形式理论表明真理和善是真实、单一和简朴的。这些超验概念存在于理想的形式王国,超越表达,在被创造的世界里不能被完全实现。真理和善不可能以语言和逻辑的方式来传达,而只能通过回忆或者超语言的形式直接传达,就像语言出现之前一样。真正回忆起来的知识是理念,它以非语言的形式断断续续地向我们闪现。这里出现一个主要问题。根据形式理论,存在之物就必定得存在,因为它是“绝对”存在的形式或理念投下的影子。真实本身就是以同和异、静和动的形式展开,正是在语言的散漫使用之中,人才能公平地评判这些形式。可是随着语言被使用,谬误可能出现。语言会根据自己的设计或者人本身的需要和幻想,来给真实加上自己的形式。人会臆想、撒谎、揣测、讲故事,在这样做的时候让自己离开真理。语言既能表现真实,也会曲解真实。为此,默多克总是在作品中着力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对真实忠实和不忠实的两种语言之间进行协商。
柏拉图在关于语言和真实之间关系的思想中,明确区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像柏拉图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大哲学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一旦写下来了,就立刻不赞同自己的书面语言。他强调真理最多是在谈话中隐约闪现,哲学的本质就是谈话。真理在经过持续的讨论之后出其不意地降临在受过训练的思想者身上。“只有刻在听者心灵上的词语才能使他学到真理和善;口头上传递的真理才是人的合法之子。书写破坏了在场与真理的直接关系。由于真理只在当下意识、现场辩论当中为实体化的人而存在,书写正是一种使自己远离真理和真实的方法”(Murdoch,The Fire and the Sun 22)。人一旦获得真理之后,忘记它的危险性很小,因为真理存在于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
苏格拉底用一则神话来探讨书写的正当性和非正当性。索厄斯是住在古埃及的神,发明了数字、代数、几何、天文、跳棋等。他来到国王萨摩斯面前说他发明了一个有独创性的东西,叫做书写,它将提高埃及人的智慧和记忆。萨摩斯总是在做几何,但不会书写,他说书写是记忆和原始理解的低等替代物。人将会被引导认为智慧存在于书写当中,而智慧必须存在于思想当中。一本书不能回答,不能区分明智的或愚蠢的读者。它需要它的父母来为它说话。明智的人将在适当的灵魂中播下种子,被恰当理解的思想在正在进行的讨论中得以传递(Murdoch,The Fire and the Sun 21)。被书写的词语是人的不良意志的无助受害者,是一种第二手的低等表达。书写能够很容易变成谎言,哲学中真正重要的东西不能或很少被纳入被书写的词语中。语言本身也许就是一种障碍。柏拉图认为对于被创造出来的凡人,他们只能以被创造的方式去接近真理,即在瞬间的、有限的意识范围之中。人在书写中让自己与此远离,因此书写变成撒谎,或者带来与真理毫无干系的快乐(Todd 58)。
与此相应的是,默多克在她的哲学中指出,由于语言是不准确、抽象和含混的,所有的语言使用者都有不知不觉地撒谎的倾向。她承认语言超越它的使用者(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93-194)。使用者试图把主观内在思想转化成新形式,通常不期然地发现大量机会歪曲真理。这被归纳为一个三步式的过程①:为公众书写的词语双倍远离经验本身。首先,使用者有了经验之后想象抽象的形象,用抽象的词语向自己述说。然后,为了向他人传递这些概念,他把它们变成词语,词语的意思公众早已达成一致,只是任何听到的人都有不同的历史,因此对它们都有不同的看法或前后关系。由于词语不是它们所代表的物体的实际名称,误解时常发生(Heusel 69)。
对于如何用语言来再现真实的问题,默多克在第一部小说《网下》(Under the Net,1954年)中就开始探讨。主人公杰克·唐纳格是一位艺术家,在试图看清现实方面连连受挫。他把与哲学家雨果之间的谈话写进他的书《沉默者》里,谈话成了“词藻华丽的哲学对话”(Murdoch,Under the Net 38)。可是,对于真实发生的事,他的书能够传达给读者的只是一些浮浅表面的东西。小说中真实的人物在书写方面总是困难重重,如杰克的爱尔兰表兄芬恩。他“从不撒谎,甚至从不夸张”(Murdoch,Under the Net 42),杰克怀疑他不会写作。雨果则像默多克其他善的角色一样,对于通过文字来交流深感艰难。作者在此玩味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柏拉图式的区别,即口头语言更接近真实。默多克还揭示出这给创作小说情节带来的困难,因为善人总是趋向于一致,乏味无趣。善人像苏格拉底、基督和佛陀,从不写下什么,也不擅长在纸上表达(Conradi 42)。雨果注意到当他真的述说真理或叙述真实发生的事时,他口里流出的词语完全是死的。他说了一句很具维特根斯坦色彩且令人回味的话:“语言只是无法让你把经验如实地表现出来。整个语言是一台制造虚假的机器”(Murdoch,Under the Net 37)。
三
默多克的“崇高”小说理论强调外部世界的偶合无序和人的“独特性”,要表达这种特性语言力所不能及。她对此的回应是“语言是有限制的”,当我们努力扩展语言的边界时,得准备接受它的限制(Griffin 13)。“语言是有限制的”传递出了她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她的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他的哲学作出的反应(Heusel 24)。她对普通语言的观点与维特根斯坦的有着相同的来源。她赞同他对语言的理解,和他一样把语言看成人的大脑行为,句法和语法是一个框架,决定一个人能思考什么。她70年代和80年代的小说反映了他关于语言的革命性观点,探索了他关于人的交际习惯方面的几个论点。
维特根斯坦和巴赫金两兄弟一样,对语言的具体使用而不是本质感兴趣。相对于数学逻辑家和自然科学家使用的“特别语言”,他更关注普通人日常使用的普通语言。他早期存在幻想,以为用基本命题来勾画真实,可以获得真理。基本命题与所表现的事实之间存在着同晶型体关系:词语和它所指的对象相配。通过看命题所指的对象,有可能确定命题的意义。他把语言比成一幅画,逻辑命题提供的是关于事实的逻辑结构的画面。“一切真的命题的记述完完全全地描画出了世界。世界为一切基本命题的记述加上关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的记述所完完全全地描画了出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51)。他认为是公开的上下文的特点决定如何使用关于思想的词语,导致意义产生的那种刚性存在于社会框架之中,而不是与内向性表达的关系之中。人是通过观察思想语言在他人行为中如何被使用来获得它们的意义,而不是参考内在经验。“我们不再需要这样一个存在来确保语言的意义,也不需要一个所指来使外在行动明白易懂:两者都取决于公共语言的习俗和规则”(Antonaccio 78)。
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思想在二十多年之后出版的《哲学研究》中发生了变化,他说:“我写的第一本著作中有严重错误”(2)。他提出“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2),语言交流等同于人为了满足愿望和实现目标所做游戏中的动作。人由于害怕真实倾向于制造语言游戏,目的不仅是要生存下来,而且试图解释不能解释的,逃入给人慰藉的幻想。人醉心于自己的语法系统,制造的语言游戏通常是无稽之谈。如果能避开臆想,就有可能不醉心于语法图像。抵御这些倾向的选择并非不存在。通过逻辑以外的视角来看真实,比较对象,往往能看得最清楚(Heusel 36)。这与他自己原来把语言看作画面的观点矛盾。他把语言比作游戏,是为了打破西方哲学以及他本人原有的概念,即语言可以是某种超越自己的形而上的东西的画面。语言是工具,每个词语都是人可以用来做某些而不是另一些工作的工具。西方文化的一个主要幻觉,以为个人能够通过采用哲学的科学方式来理解或解释真理,维特根斯坦对此进行了革命性的颠覆,默多克的兴趣也正源于此(Heusel 38)。
维特根斯坦抛弃幻想,不相信传统西方哲学模式能够为人提供理解真实和决定行动所需的全部资源。科学哲学家只通过逻辑镜头来看,遗失诸多真实,醉心于科学推理和科学语言语法系统的状况需要得到医治(Heusel 38)。他从语言游戏概念加上生活形式中得到一种不同的准逻辑语言画面。与此相关,默多克质疑科学能否以真实有效的方式表现思维活动。绝大多数意识状态以各种感性或“情感”状态出现,对此没有一种系统化语言能够有效表达(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96)。当哲学试图分析的对象如此不同,而这种不同又是如此重要时,它应当保持多样化,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必须接受的东西、给予我们的东西、乃是——人们可以说——生活形式”(《哲学研究》345)。
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使得他不能肯定用任何语言来谈论宗教感受和伦理观。在1929年的伦理学演讲中,他开始分析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认为词语只能表达事实,善的本质与事实无关,因此不能用任何命题来解释。他谦卑地承认有一个与普通人一样的特点,那就是需要挑战自己的事实的、科学的语言以便对决定或判断进行,试图超越世界,也就是超越有意义的语言:“我的倾向,我认为也是所有试图写作或谈论伦理或宗教的人的倾向,就是与语言的边界相撞。这种在笼中与笼壁的碰撞,是绝对无望的。伦理学来源于人对生活的终极意义、绝对的善和绝对价值说些什么的渴望,就此而言,它不可能是科学。它说些什么不在任何意义上增长我们的知识”(Wittgeinstein,“Wittgeinstein's Lecture on Ethics”11-12)。由于不能谈论超验真实,在《逻辑哲学论》中他没有让它出现。他只说能够被说的,如自然科学命题或者与哲学无关的东西。他赞同神秘事物的存在,尊重不同性,正是这一点使默多克让自己的想象“向偶合无序的混乱”敞开(Heusel 13)。她一方面赞同把许多事物当成神秘事物来接受,另一方面不同意谈论道德绝对概念本身值得怀疑,不论该概念是理性的、哲学的还是普通的(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315)。作为道德哲学家,她别无选择,必须提出价值问题谈论内在思想,哲学研究有必要探讨内在思想发生的过程。她感叹现代哲学家忽略这一必要性,认为比准科学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像里尔克这样的艺术家能够用词语来揭示“丰富而含义深远”的细节。她强调有必要超越逻辑来接触为云雾笼罩瞬息万变的概念领域,人们依据它们而生活(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22)。
默多克的《作为道德指南的形而上学》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形成了一种辩证关系,这使得她能自由超越哲学的“科学”和“分析”模式。她推测他会赞同在思想和语言的边界,人常能“看见”不能说的。她猜测他可能只会说:“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思想事件,即思想画面、对自己说的话,或许还有需要暗喻式描述的更为晦涩的表达”(Murdoch,“Vision and Choice in Morality”97)。一个人感觉在思想中他想说的,比他用词语表达的要清晰得多。她指出在受到视觉和身体感觉刺激时,不为人注意的内在经验能更好地被传递,经验中充满着可觉察的东西。就语言在思想“里面”出现的状况而言,语言本身几乎无法跟各类想象区分,对于隐匿的身体知觉,语言有时也几乎无法跟感觉区分。面对不能说的,维特根斯坦的经典名言是:“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当沉默”(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20)。默多克碰到不能说的,没有采取避而不谈的策略,她自有一套解决方法,如采用并列、反论或插入意外事件等。例如在《修女与士兵》中,她展现而不是讲述生活的神秘。人物以一种嬉笑的、后现代的、不确定的方式玩一种令人迷惑的语言游戏。作者邀请读者把那些语言游戏的几种不同解读方式并列,同时体验写作、阅读和解释过程。读者可以随时参与作者和评论家的探讨,证明一个人的语言游戏总是他人批评的机会。这个过程解说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代表一系列视角的一系列标志,将帮助有洞察力的人看到语言游戏如何发挥作用(Heusel 57)。
值得一提的是,维特根斯坦用网这个意象来指语言和理论无法完全再现偶合无序的真实,就像网无法兜住放置其中的所有东西,默多克在《网下》提到他“细密的四方形的网”,象征理论化不能罩住网下的真实。在小说主人公杰克写的书中,他的主人公认识到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真实:哲学家要找到答案,必须进入理论化的网的底下,才能理解独特的细节。默多克本人用网来指语言:“语言是超验的,是一个终极的网,我们不能在网下爬过”(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234)。含义显然有所不同。
四
默多克尽管对清晰的语言表示怀疑,但仍然认为语言是有意义的,也是有用的。如果说“语言是有限制的”传递出她与维特根斯坦的对话,那么“语言是有意义的”则是她与德理达的交锋。她指出语言通过忠于真实来完成其根本任务,个人为了身外偶合无序的世界而设法创造性地调整语言。语言不应与人的意识分开,被当成方便的非人化网络,或者对少数人来说当成冒险的乐园。这里的“少数人”当然包括德理达在内。
在默多克看来,德理达因首先提出书写先于言语的思想而著名,实际曲解了柏拉图的“形式理论”。他对形式作出解释时玩了一些花招,使柏拉图对诡辩家的描述符合自己的需要。她称他为“天才的魔术师”,说他的方法“具有破坏性”,是“一种威胁”。她赞同索绪尔的语言描述理论,语言画面“就像一个由联系和可能性组成的巨大海洋,我们眼光扫过海面看不了多远”(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274)。这是为了理解语言而为它勾勒画像。可是,德理达走得更远,他使画面“凝固”成某种假定的真实。默多克坚决反对把语言这样的“活体”凝固起来。索绪尔把作为一个体系的语言与个人具体使用的语言区别开来,但是他赞同柏拉图,语言和意义的基础是言语(口头语言)而不是书写。面对听者,言语能够被正确理解,而书面语言则会被误解,与原意有距离。这一点遭到德理达的反对。他认为书写是根本的,从形而上的意义来看,书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或符号结构,意义由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超越说话者的当场具体谈话”(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88)。我们使用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不可见的其他含义的蛛丝马迹,因此,是语言在说我们。这一点让人想起巴特。巴特坚持认为,语言内在本质上是独裁的,因为在语言产生意义的各种方式上,统治和奴性盘根错节相互缠绕在一起。当我说什么时,我便宣称什么:不论用多少修饰词来包裹我说的话,我所使用的语言系统赋予我的话以独立的权力。可是,这种至尊被同样的语言符号染上奴性:我说的话已经被说过,我由于重复而陷入陈规老套和已被采纳的意见的控制。
默多克认为德理达的这个概念包含着一些严重的含义:我们似乎要失去个人的概念,文学作品中隐含的价值和道德将在结构主义者的画面中消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在德理达“对所有价值重新进行评价”的背后,是一个强大超人控制领域的概念。这就是海德格尔后期的人的概念和德理达的语言理论,代表着决定论的新形式。她觉察到在各个知识领域里都出现了去神话化的思潮,攻击传统观念,结构主义是其中之一②。她视之为精英意识,认为“后结构主义貌似合理,是因为它建立在一系列本身可被理解却被以误导人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之上。我们面对一幅相当令人寒心的画面。德理达和一、两位诗人能够玩语言游戏,就像海豚在水面上玩球,而其他的人都在下面黑暗处。这种方法具有破坏性”(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274)。
德理达称海德格尔为最后一位形而上学者,默多克认为他本人就是一位形而上学者,他的解构主义“看上去就像另一个形而上学”(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97)。他无法选择不创设体系,也就无法终结形而上学。她能够理解德理达和接受决定论形式的人,因为“它满足人的一种深层渴望:放弃、摆脱自由、责任、悔恨以及所有个人的不舒适,屈从于命运和‘不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的解脱”(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90)。后结构主义哲学的意义形而上学就像任何总体系统,为了对意义系统和行动进行分析而丧失个人和内心生活的复杂性,意义于是成为一种与自我相关的内在运动或语言游戏(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93)。文本以外任何东西都不复存在,因为是“文本”而不是“无”产生意义(Schweiker 217),每个说话者都被纳入语言系统,是语言游戏中的游戏人。
默多克最深切的忧虑就是这种去除语言的指涉特征,因为个人生活复杂性的形而上学背景将因此失落(Schweiker 216),人的道德信念和辨别真理的能力将被削弱(Rowe 13-14)。德理达的解构主义“通过消除具有道德价值的真理和真理追求的‘古老’概念”,终止对概念变化的哲学研究:“如果所有意义都延异了,所有普通区别都被消除了,例如真的、暧昧的和假的之间的区别,我们就开始对看上去简单、古老、普通的真理概念失去信心”(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194)。他去除语言的指涉特征,就文本指涉文本而言,就是扫除关于真理的任何理论。后结构主义者坚持认为真理只不过是语言效果,即便语言就“在那儿”,它也在躲避语言指涉的控制。默多克小说文本中提到的多数绘画都真实存在,这本身就部分否定德理达的论点。小说和绘画不仅构成意义的互文性和相互指涉系统,而且有效性来自直接指向独立存在的可靠经验现实,这证明语言的指向可以是外向的,而不仅仅是向内指向语言本身。
默多克对德理达的批评是激烈的,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某种一致性。她把传统形而上学定义为一种对隐蔽、先验形式的追求,一种构建终极真实的追求,也就是一个超验体系,它试图抵达事物的根本,展示在那儿的东西(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 259)。她与结构主义者对结构的渴望具有一致性(Heusel 3)。她本人所尊重的品质,也都为后结构主义者所尊重,如人类生活的纯粹偶然性、生活悲喜剧式的混乱和不完整。伊戈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指出:“默多克如此激烈地反对后结构主义,是因为它代表了自己看待事物的观点被令人尴尬地推向理性极至”(Eagleton,“‘The Good,the True and the Beautiful’”8)。他赞同德理达对所有书写的描述:重复自己,而不是讲述真理。“一个文本可能向我们‘展现’意义和含义的本质,文本无法把这个本质形成一个陈述”(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 134)。这同样是默多克探索的主题。她的哲学尽管表面上没有后索绪尔式的言辞,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相似的认识。结果就是在作品中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是现实主义作家对所指的信心,另一方面是相反的信念,即本质上无法通过语言获得真实(Nicol 20)。于是,她的作品永无止境地致力于表现真实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语言的这种使用也正是文学的解放力量,“在这里文字符号被赋予自由,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与真实游戏和作战”(Sheringham 7)。
语言和真实之间的关系问题经常出现在默多克的作品里,上述分析可以消除关于她语言思想的一些误解。有评论家指出她是反现代主义,反乔伊斯、反伍尔夫的,她的小说是维多利亚式的(Heusel 90)。的确,她不赞成现代主义者的语言观。她的最后一部小说《发往行星的消息》中的一个人物说:“大屠杀提醒人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战争的事实使她认识到二战之前的现代主义作家是浪漫的、不现实的。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语言游戏,以牺牲外部世界为代价,而唯有在那里才能遇见真实的人和事。她绝非维多利亚式的,她明确指出随着维多利亚时代一去不复返,人类对语言和真实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语言不能同人类的奋斗分离,人的表达都可能在竞争解释。她创造种种叙述策略,不仅仅探索词语内容,而且探索偶合无序的非词语表达的含义,如姿势等。她不同于乔伊斯,拒绝成为上帝式的作者,相反化身为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述者,与作品中的人物共同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以爱的目光关注着他们,让他们不受约束地发出不同的声音。虽然她必定会反对概括性结论,但是对于语言如何再现真实,我仍想概括性地说,她回到她的道德哲学的中心:除非个体都成为“相互关注的对象”,他们就不会使用一种共同的语言。
注释:
① 这个过程与锡德尼爵士在《诗辩》中指出的诗歌创作过程相似,只是他没有对语言产生怀疑。
② 当默多克用“结构主义”一词时,她包括了德理达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区别于其他后索绪尔理论,如符号学。
标签: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语言表达论文; 艾丽丝论文; 文学论文; 逻辑哲学论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