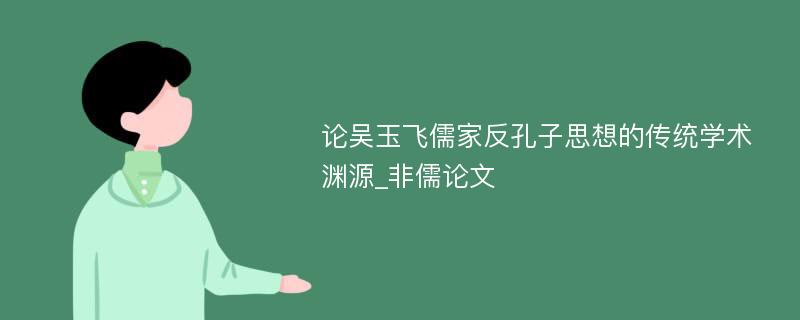
论吴虞非儒反孔思想的传统学术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学术论文,传统论文,思想论文,论吴虞非儒反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虞是新文化运动中非儒反孔的健将,他因激烈反对旧礼教和封建文化而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对于吴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许多人只着眼于其反传统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与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试图置吴虞反传统思想于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潮的流变这一宏阔背景中加以考察,评析先秦墨、道、法诸家及晚明异端思想家李贽对吴氏思想的深刻影响,以理清吴虞非儒反孔思想的传统学术渊源。
一、先秦墨、道、法诸家学说是吴虞非儒反孔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吴虞在致陈独秀的信中曾叙述自己非儒反孔思想的起因:“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大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思、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远藤隆吉、保天随诸家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刑法比较对勘。十年以来,粗有所见……”(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由此可见,吴虞的非儒反孔,既受到西学的影响,又自有其深厚的传统学术渊源。事实上,对他影响巨大的先秦诸子学说,绝非仅限老、庄一家。在传统学术中居于非正统地位的道、墨、法诸家,均是吴氏非儒反孔的思想渊源。
余英时教授曾指出:在新文化运动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在五四时代,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反正统的作品(从哲学思想到小说、戏曲、歌谣)都成为最时髦、最受欢迎的东西了。”(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4页。)分析吴虞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 可知余先生所论十分精当。吴氏对传统学术有相当的造诣,留学日本后,虽受西学的冲击,却未曾与旧学绝缘。故此,吴氏从传统学术中居于非正统地位的学说中寻求非儒反孔的思想武器,当不足为怪。
在先秦诸子中,吴虞对墨学最为推崇。早在辛亥革命前一年,他在《辨孟子辟杨墨之非》一文中对墨子的“兼爱”、“非攻”、“节用主义”、“经济主义”、“节葬”、“墨守”等主张以及“算学、重学、光学、机器学、工程学”等领域的发明创造予以褒扬,称“九流之中,惟墨足以与儒相抗”,认为墨氏“非徒谨守一节之人,乃通权达识之人也;非止修词坐论之人,乃实践笃行之人也。”并指出:“墨子兼爱主平等,则不利于专制”(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新文化运动当中,吴氏又专门写了《墨子的劳农主义》一文来分析、介绍墨子的学说。他高度评价墨氏“毁古之礼乐”,盛赞其废阶级、实行“君臣并耕”的思想:“墨子的学说,不但主张亲操橐耜,以自苦为事而止。甚至主张废弃儒家所主张的阶级制度,把尊卑贵贱、崇上抑下的礼教,一扫而空,以求上下同等,君臣并耕,不劳动者不得食。还说:‘君臣氓通约也。’他的通约,就是卢梭的《民约论》,他的主张,就是列宁的劳农主义了。所以墨子的学说,和儒家根本上绝对不能相容”(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 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 、79、 83—89、457、463、13、17、15。)。
对于道家的非儒思想,吴氏亦十分赞赏。他曾引用老子所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斥责儒家所主张的旧道德“不过是反对疾病的医药,简直是不祥之物。”对于庄子,吴氏更是推崇:“他把那些讲道德说仁义的诸侯大夫和一般人都认为是窃盗,一钱不值。……那一种不屈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何其伟大!”(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在《消极革命之老庄》一文中,他对老、庄在历史上所起作用进行了评析,赞扬其“能深知家天下者遗弃公天下之道德,而专以家天下之仁义礼智愚弄人民”、视封建统治者为“民贼”、“盗魁”(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 、457、463、13、17、15。)。
吴虞还从法家学说中吸取了许多非儒反孔的思想养料。他对管仲、商鞅、韩非等法家人物的许多言论不乏激赏之辞。早在1905年所作家训中,既赞扬法家:“夫仁义诗书,孔孟所常称道,而商君、韩非且斥之为贼为蠹,则世俗之见解,又何足定我之可否哉?(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 463、13、17、15。)1910年,在为《蜀报》所作祝辞中颂扬管仲之治其国,“其要尤在使智愚皆知之,智愚皆能之”,说明预备立宪就要使上下同德同力。而在《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中,则赞扬商鞅不务虚文,反对旧道德、专以富国强兵为务的精神,并称颂韩非反对空言仁义道德而主变革的精神,认为“其思想之博大,义理之明晰,论锋之锐利,实非儒家所及。”(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吴氏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大力推崇实非偶然,确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悠长的学术渊源。概言之,这是明末清初以来近三百年“复古解放”学术思潮发展的历史结果。梁启超在纵览近三百年学术思潮发展脉络时,一言以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于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可见,在“复古解放”的潮流中,复兴诸子学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明末清初,伴随着经济领域内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复古”思潮。即以“复兴诸子学”而论,这时即已渐露端倪。如,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提倡儒经与诸子百家并读,开“复兴诸子学”先声。至乾嘉时期,著名学者汪中力贬宋明理学,力图还孔子学于孔子,努力从先秦诸子中去考察儒家经典的本意。他推崇墨学,创“孔墨并称”说,否认孔学至圣的地位;他又以孔荀之道代孔孟之道,从而否定了宋儒的道统。19世纪后,俞樾、孙诒让等继汪中而宣传诸子学。至二十世纪初,以章太炎为首的“国粹派”更公开打出“复兴古学”的旗号。一时间,“复兴诸子”,发扬诸子精神的宣传蔚然成风。在这股“复兴诸子学”的声浪中,国学大师章太炎作《诸子学略说》,对先秦诸子一律以平等的眼光加以介绍,对孔学进行了严厉批评,将孔子指斥为趋时竞进,湛心利禄的“巧伪人”,从而使“复古解放”之风演变为非儒反孔的热潮。总之,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潮,从反对理学一直发展到对孔学的冲击,始终沿着“复古解放”的道路,以长江大河不达于海而不止之势渐次演进,从而为新文化运动时期声势浩荡的反孔潮流作好了铺垫。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难发现吴氏借先秦诸子学说以非儒反孔的学术关系。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学术浸润的新文化人,吴氏确乎受到了近三百年“复古解放”思潮的熏染。而汪中、章太炎等在“复古”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则给他的学术思想以深刻启迪。例如,在《读〈荀子〉书后》一文中,他发挥汪中《荀子通论》一书以荀子为孔学真正传人的观点,阐述了“孔学之流传于后世,荀卿之力居多”的看法(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 、457、463、13、17、15。);而他“九流之中,惟墨足与儒相抗”一说,更与汪氏如出一辙。又如,吴氏在著述中一再提到章太炎和他的《诸子学略说》:“知政治儒教当革政者,章太炎诸人也”(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 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 、457、463、13、17、15。);“太炎国学既深,又富于世界知识。 在日本时,读其《高等师范讲义》,悉能理解。……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近”(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 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明李卓吾以卑侮孔孟,专崇释氏,为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则儒教徒之心理与犷悍,可以想见,谬种流传至今日。某氏收取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烬于一炬,而野蛮荒谬之能事极矣!”(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 17、15。);“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攻孔子最有力,其《訄书》并引日本远藤隆吉‘支那有孔子,为支那祸本’之言。”(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 159 、122、7、 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 、457、463、 13、17、15。)可见,吴氏之非儒反孔,确实与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潮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二、李贽的异端的思想是吴虞非儒反孔思想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
除先秦诸子学说以外,晚明学者李贽的思想也对吴氏的非儒反孔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的出现,在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儒学异端,李贽(号卓吾)即是晚明异端思想家中的杰出代表。而李氏的异端思想,给吴虞以重要的影响。
吴虞十分崇尚李贽,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即写下《明李卓吾别传》一文,对其生平、著述、思想系统评析。
李贽异端思想对吴虞非儒反孔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数端:
其一,李氏对儒教和道学的批判,对吴虞的非儒反孔起了思想先驱作用。
在为李贽所作传记中,吴氏称赞卓吾对儒教和道学的抨击“抉摘世儒情伪,发明本心,剥肤见骨。”(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 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他赞同卓吾反对神化孔子的观点,引李氏《答耿天台书》之言以否定孔子“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地位:“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又引李贽《藏书·纪传总目前论》之语,公开声称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准则,而必须推倒盲从的教条,按照时代需要建立评价善恶真假的标准:“前三代,吾无论也。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耳。……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盛称李贽对道学家的批判“可谓洞厥情状,极嬉笑怒骂之致”,引《焚书》中李氏批驳耿定向的信,对封建卫道士作了辛辣嘲讽,斥责他们言行不一,讲学时高谈“利他”,行动上却“事事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名心太重也,回护太多也。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 、15。)。
其二,李卓吾借崇佛以非儒的思想,对吴氏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贽痛恨定儒学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然而,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之下,“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看不到社会的未来。为了摆脱封建主义束缚,他只好逃禅”(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 、15。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下)第3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走上了信仰佛教的路途,晚年还出家当了和尚。
但李贽之崇佛,实际是对儒学专制统治的消极反抗。这一借崇佛以非儒之举,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吴虞,成为其反孔非儒的重要手法。
在为李卓吾所作传记中,吴氏既称颂李贽之非儒,又为卓吾之崇佛大加辩护,表达了自己对佛学的向往:“夫非官吏及秀才,不能入孔庙观礼,贤关圣域,万仞宫墙,小人与女子无望焉,惟儒教为然。……夫惟无宗教之民,乃近于禽兽,彷徨怅惘,而无以安慰其心灵。故夫儒教之国,民之流入于他教邪教者滋益多……张问达、王雅量能焚毁卓吾之书于一时,诬陷卓吾之身于一日,而不能从根本解决,为移风易俗之图,此正卓吾所讥‘托名为儒,求治而乱者’矣”;“自宋至明,帝王卿相,圣贤哲豪,平民男女,兼宗二教,其徒实繁。何彼皆许其逃禅,此独禁其佞佛,摭拾一偏之谈,为卓吾罪哉?”;“吾国历代学者,多归心释氏。张怀泗诗曰:‘英雄到老都归佛。’钱谢庵词曰:‘人为伤心才学佛’。岂非生死两端,不可思议,沤珠电影,转瞬俱空,忠孝劳生(文天祥诗‘忠孝太劳生’)别求解脱,冀得身心归著之究竟?卓吾之于生死,泊然天累,由其得力于佛学者深也。何得坚持门户之见,以律非常奇伟之士乎?”(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吴虞力颂李贽之崇佛,其根本意图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推崇一样,在于打掉儒学的神圣光环、推倒儒学的至尊地位。在儒学定于一尊的中国封建社会,佛学虽时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但它与先秦诸子学说一样,毕竟是属于非正统的思想学说,其教义与儒学教条颇多相抵牾和冲撞之处。因此,在儒学至尊地位大受冲击、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和反正统思想均被大加利用的“五四”时代,其为吴虞这样的激进反孔人物所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李贽的妇女观,对吴氏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有启蒙作用。
李贽十分同情妇女们的悲惨境遇,猛烈抨击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对妇女的毒害与摧残大力倡导男女平等,乃是其反礼教、反道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肯定妇女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将夫妻关系提到五伦之首,并反对“夫为妻纲”,主张夫妻互敬互爱。他极力驳斥“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论调:“谓人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中册)他还力斥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教,热情讴歌卓文君、司马相如的私奔行为,为妇女择婚自由大唱赞歌。
李贽在妇女问题上的惊世骇俗之论,对吴氏批判儒家妇女观、鼓吹妇女解放的思想的形成起了较大的启蒙作用。早在1912年,吴虞的妇女解放思想即已初步形成。在他支持、鼓励下,其妻曾兰为《女权报》撰写了大批鼓吹男女平权的文章。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吴虞以凌厉的攻势向封建妇女观宣战,先后发表了《书女权评议》,《女权平议复唐氏》这两篇名噪一时的文章。从历史、社会进化、传统道德、刑律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及根源,集中讨伐了孔教愚弄、侮辱妇女的种种罪孽。他指出,所谓以乾坤为根据推演出来的三纲,是封建社会订立尊卑贵贱的虚妄之谈,“天尊、地卑、扶阳、抑阴、贵贱上下之阶级,三从、七出之谬谈,其于人道主义,皆为大不敬,当一扫而空之。”他号召女子“当琢磨其不道德,勉强其学问,增进其能力,以冀终得享有其权之一日。”(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尽管吴氏在文中未直接引用李贽的言论。但他倡导男女平等的手法如同李贽一样,主要着眼于运用历史事实、历史典籍以抨击陈腐的儒家妇女观(而非如同胡适、周作人等人一样主要着眼于宣传、介绍欧美妇女解放思潮),字里行间均可窃见李贽妇女观在吴氏妇女解放思想中的折射。而吴氏在《女权平议复唐氏》中为李卓吾等思想家在“君主、儒教专制之世”“皆不免于……焚书毁版、雷厉风行,言论出版,无复自由”(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的不幸遭遇而发出的强烈的不平之鸣,更是他在妇女问题上深受李氏思想启迪的明证。
三、结语
吴虞之所以热衷于墨、道、法等先秦诸子学说及晚明李贽的异端学说,其根源在于它们在儒学独尊的封建社会中均处于非正统、反正统的地位。他盛推上述各家学说,意在推倒儒学的至尊地位,恢复先秦“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为此他愤激地指出:“汉武以前,诸子之学与儒家平等。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罢黜百家之策行,而后孔学独尊,诸子之学,日就消沉”(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他认为:“天下有二大患矣: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在他看来,“盖辩论愈多,学派愈杂,则竞争不己,而折衷之说出,于是真理益明,智识愈进,遂成为灿烂庄严之世界焉。”他热情洋溢地表示“愿抠衣执鞭”,以“鼓言论思想之风潮也”(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 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这三百年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动,意识形态领域内儒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愈来愈强烈的冲击和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吴虞继承了近三百年以来“复古解放”、儒学异端等进步思潮,采用以传统反传统的手法,盛推墨子、老庄、韩非子、李贽等非正统、反正统思想家的学说,揭露和批判儒学专制、儒术独尊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大力倡导思想、学术自由,号召人们从孔学教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实质上是对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文化传统的空前大否定、大扫荡,在当时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然而,从弥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缺陷立言,我们探讨吴虞非儒反孔以传统反传统的战略手法时,更多的不应只看到其成就,还要看到其局限。
首先,吴氏对传统文化中非正统思想学说的继承缺乏升华,致使传统文化内部反正统、非正统学说中的某些非理性因素在其思想内恶性膨胀。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构成看,其以儒学为主体的正统文化并非全是糟粕,其非正统、反正统的部分亦非全是精华。对此吴虞缺乏理性的把握。他对传统正统文化的批判不构成扬弃,忽视了儒学内部包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因素;而在传统非正统、反正统文化领域内又对某些非理性因素不加分析地错误继承,因而他对传统文化中非正统、反正统思想的继承亦欠缺升华。例如,墨子的“兼爱”虽具有反剥削压迫的进步思想意义,但他宣扬一种超阶级的爱,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其“非攻”虽有积极意义,但亦有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的社会根源、严格区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性质的缺陷。对于墨子思想的上述局限性,吴虞显然缺乏科学的、理性的认识与分析。又如,老子将智慧、道德等人类文明成果视为祸患之源,主张废除一切文化,这实质上是一种代表没落阶级利益的虚无主义思想,而吴氏却对此不加分析地一味加以颂扬。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吴虞对李贽学说中的佛学思想成分不但未予理性批判,而且以激赏的态度全盘吸收,这就为其晚年由积极反传统走向消极遁世,成为佛教信徒埋下了伏笔。
其次,吴虞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的理解比较地浅薄,未摆脱以西学附会中学的传统思维模式。如:将卢梭的《民约论》附会于墨子的“通约”;将列宁的“劳农主义”附会于墨子的思想与主张;将“亚历斯菩之谓快乐”、“伊壁鸠鲁之所谓幸福”附会于杨朱之“快乐主义”,将“霍布士之所谓利己”、“欺宾塞之所谓自爱”附会于杨朱之“利己主义”(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 、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这些牵强的类比,恰暴露出吴氏西学修养的浅陋。
总之,吴虞非儒反孔的思想渊源,主要是传统文化内部的非正统、反正统思想因素。对于吴氏思想的总体评价,台湾著名学者殷海光的结论可谓精当:“和许多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一样,吴又陵的思想是在一种新旧杂糅的状态之中。不过,无论他在思想上的成就是大还是小,他充满了为时代而思想的热心和真诚”(注:转引自《台湾及海外五四研究诸著撷要》,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