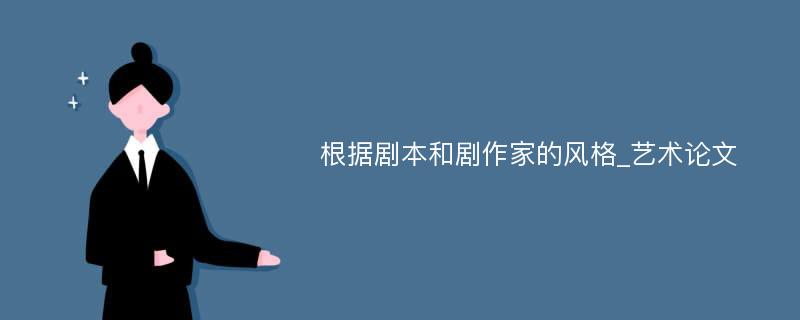
以剧本和剧作家的风格为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家论文,剧本论文,风格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风格,从演出实践的层面上来说,是以剧本和剧作家的风格为基础,又经过从导演到全体演职人员的再创造,而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风格。它是先后参加到风格创造的整个过程中来的多个创造主体通力合作的结果。这个过程包括了由剧作家先期完成的剧本风格的创造阶段和剧本完成以后由导演、演员、舞美等进行的舞台风格的创造阶段。
先期的剧本创作,基本上属于文学创作的范围,这时作家是风格创造的唯一主体。尽管有些有经验的作家,如老舍,在创作时常常会把诸如剧院的条件、导演和演员的特点等考虑在内,但剧本风格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却只能是作家自己的。对于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来说,真正属于他们的戏剧舞台风格的创造,只是在作家的创造基本完成以后才开始的,作家止步的地方正是他们起步的地方。这时,在多数情况下作家已经退出了创作过程,而他们则成了主要的创造主体。他们一方面在最终呈现于舞台的艺术风格中充分体现剧本原作的基本风格,另一方面也在这一体现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把自己的灵魂和血肉铸造进去,从而使风格成为他们自己的。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郭沫若、老舍、曹禺、田汉等著名作家的个人风格归入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流派风格中去,更不能说他们都属于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但是,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剧作的风格,对于北京人艺风格的创造与形成,无疑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个人风格,经过导演和演员的再度创造,经过一系列审美的中介环节的转化,或作为触媒,或作为载体,或作为材料与要素,一般都会同他们的剧目一起,程度不同地融汇到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总的风格中去。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无法否定的。
在具体剧目的演出中,焦菊隐非常强调对于作家风格的尊重,强调作家风格的决定作用。他说:“某一出戏的演出形式和风格,根据剧本的不同条件和要求,可以和另外一出戏的演出形式和风格不同。必须这样做。甚至同一个剧本,在不同导演的处理下,也会出现很不相同的形式和风格。但是,这一切,首先要由剧作者的风格来决定。”(《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风格是一个总体性、综合性的概念,它由众多的因素和层面组合而成,因此,同一个剧本,到了不同的导演手里,由于个人审美趣味的不同,素养的不同,着眼点的不同,在排演时往往会有不同的强调,再加上他们自己的独特艺术个性的融入,就完全有可能表现出不同色调的风格效果来。越是伟大的作家,他的剧本的风格内涵就越丰富,就越有可能为不同导演的再创造留下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这不仅没有否定,反而更加证实了作家风格的决定作用。
作家风格对于舞台演出风格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为剧本的风格是导演和演员进行舞台风格创造的基础、根据和出发点,剧本的风格决定着后来的所有舞台创造的基本性质、方向,以及大致的框架。这就是说,导演和演员的风格创造,只有在作家风格创造的延长线上进行,才会成功,否则他们的创造将无所凭附。所以,焦菊隐强调说:“从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导演,拿到文学剧本之后,首先要注意它的风格特色,找适当的演出形式,发挥其中精华,揭示剧本的主题思想。”只有首先掌握了剧本的基本风格特色,然后才能谈到导演自己的创造和发挥。而这创造和发挥,又决不是导演一厢情愿的随心所欲,“导演的构思和计划,无论多么活跃新颖,一定要符合剧本的内容和风格。”(《与兄弟团体探讨导演艺术问题》)
正因为戏剧的舞台风格首先是作家和剧本风格的呈现与传达,而舞台风格的创造和发挥,又以不能违背原作的基本风格特色为原则,所以焦菊隐一向非常重视对于不同作家的风格特色的细致分辨,务求准确地加以把握。他在理论上是这样认识作家风格的不同的:“总的来说,与其说作品是作家思维活动的果实,不如说更是作家感情活跃的果实。不过,在下笔的时候,每位作家对自己的感情的控制程度各有不同;对生活的着眼点和着重点各有不同;表现生活和人物的方法方式也各有不同。有的作家不拘泥于生活细节和人物细节,而只表现最重大的事物,人物的最激动的思想感情和人物对客观事物最鲜明的态度;有的作家,就运用某些日常生活现象,来突出生活的本质和面貌;又有一些作家,则着重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和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有的作家,力求工整;有的作家的笔势,一气呵成。这就形成了每位作家自己所独具的文学风格。”(《略论话剧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还在早年,当他对现代戏剧艺术大师易卜生进行系统研究的时候,就非常注意对其独特的整体风格特点的把握,他指出:“易卜生的艺术……他的作品,在技术方面讲很难找出错儿来。无论是对话,无论是结构,都极严谨如其人……我们读易卜生的作品,不像读旁的作家的,用不着斤斤于他的修辞和用字,仅读他的通盘风格就够了。”(《论易卜生》)40年代以后,他对契诃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研究并翻译了这位大师的主要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