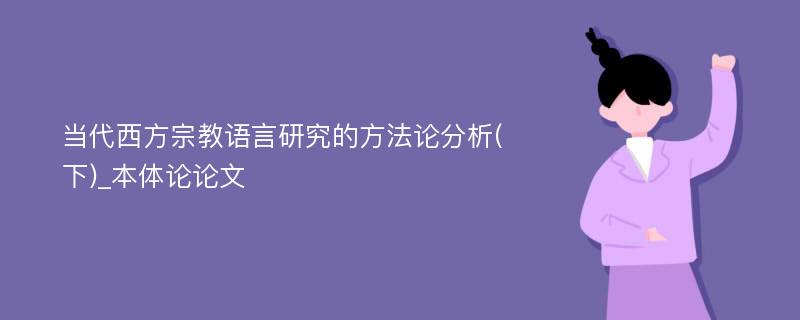
当代西方宗教语言研究方法论分析(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当代论文,宗教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生存论分析
当代西方宗教语言热中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怎样通过人类日常语言来谈论一个神圣的主题,即怎样谈论上帝的问题。由于宗教语言的独特性,借助于日常语言去谈论上帝必然引起一系列理论难题。在当代寻求克服这类理论难题的方法论努力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贡献就是由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提出继而被奥托(Rudolf Otto)、埃伯林(Gerh-ard Ebeling)、富克斯(Emst Frchs)等人发扬光大的生存论分析。
生存论分析的基本主张是要求从个人的生存处境出发来解释和理解新约圣经中传达的福音,从而把握基督信仰的本质。这种主张旨在解决当代基督教的信仰危机。当代基督教信仰受到了来自内、外两个方面的直接威胁:外在方面是科学世界观和历史相对主义的泛滥,导致现代人丧失了彼岸的价值尺度;内在方面则是新约圣经的神话语言已越来越难以被习惯于科学和历史语言的现代人接受和理解。布尔特曼的生存论分析,首先针对的是相对主义的历史批判。历史批判把基督信仰仅仅视为一个历史事件的信仰行业,否认它有超历史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而否认基督信仰的绝对意义,这是把历史现象当作自然现象一样进行“客观”研究的结果。布尔特曼认为,人与历史的关系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不可能像观察自然现象那样把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审视,人回视历史时必然会使自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只能带着自身的问题去询问历史,历史才能对带有自身问题的询问者敞开自身。因此,历史与个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生存论关联,个人只有从自己的生存境况出发去询问历史,历史本身才会提供与个人本身的生存境况相关的意义。
生存论分析虽然始于对相对主义历史批判的深刻反省,但布尔特曼主要还是把它作为一种解释方法用于破解新约圣经的神话语言,以便揭示出这种语言中隐藏着的真实意义。神语语言表达出来的对整个世界的理解是以天堂、人间、地狱为前提,并注重超自然力量的干预,这些观念显然与科学世界观相冲突。布尔特曼的回答是:神话的意义在于它间接表达了对人之生存的关注。圣经是用神话来谈论上帝进入人之生存时的言说,这种言说与人的生存问题和自然理解相关。“当我们与历史中的耶稣的话相遇,我们确无需要用一套关涉理性的有效性的哲学去辨析;耶稣的话不过是与带着需要解释自己的生存问题的我们相遇。”(注:布尔特曼:《耶稣基督和神话学》,纽约,斯克赖伯出版公司,1958年版,第4页。)由于上帝的话直涉人之生存问题的核心,谈论上帝就必须同时谈论自己,“上帝的问题和我自身的问题同一”。(注:布尔特曼:《耶稣基督和神话学》,纽约,斯克赖伯出版公司,1958年版,第53页。)这样,生存论分析又把对上帝的谈论转换为对人之生存的谈论。布尔特曼提出了生存论分析,即“解神话”(Demythologizing)。
解神话并非简单地将神话语言翻译为生存语言,它既是一种从生存处境出发,对生存本身给予生存理解的方法论上的建构,也是一种对圣经进行生存论解释的方法论。布尔特曼认为,对人的生存之追问与圣经中的提问是一致的。要解释圣经本文,必须以某种前理解为前提来进行设问,才能构成一种交流——问与答的逻辑。解释者向圣经本文设问的前提来自对自身生存问题的自我理解,即对自身生存有限性的意识,这是解释圣经的前理解。只有解释者把自己及其连带的问题置人解释活动之中,而自我理解把设问掷向与圣经本文主题的相遇,解释者与圣经本文才能建立起活生生的关联。同样,解释者对生存有限性的自我理解也必须以某种前理解为前提,这种前理解只能来自圣经主题谈论的上帝及其对人的恩典,只有依据这种前理解,人对生存有限性的自我理解才能达到超越有限性的神性维度。这里显示出了解释学的理解循环:一方面,圣经本文作为一种前理解为理解人的生存有限性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人之生存有限性的本文作为另一种前理解又为理解圣经本文提供了可能。于是,作为前理解的生存关联域便使解释——聆听上帝的话成为可能。上帝在其道(Word)中与人相遇,只有当个人在上帝之道中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上帝才在个人此时此地的生存中在场。上帝的在场就是信仰之发生,正如艾伯林所说:“信仰是作为此岸中的我在的生存之定在,但它并非外在于我的行为、苦难、希望和经验的一切,而是具体地在这一切之中。”(注:艾伯林:《基督信仰的本质》,苏黎世,1961年版,第125页,转引自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129页。)
布尔特曼用生存论解释方法成功地拯救了神话的真谛,并用一种丝毫未脱离人类经验范围内的语言重述了神话,使现代人可以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存在主义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此在分析所奠定的方法论基础。胡塞尔曾提出现象学的方法和原则是“回到事实本身”,海德格尔在继承胡塞尔现象学方法时拒斥了其先验主体和先验世界,转而将其与自己的存在论结合起来,要求按存在本身的显现来揭示存在的意义,从而消除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认识论痕迹。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追问存在本身的意义,这种追问必须有一个出发点,海德格尔通过现象学直观选择了以此在作为出发点来破解存在的意义,他由此发展了一套独特的基础生存论的分析——此在分析方法。此在分析是海德格尔展开存在的意义的必要的方法上的步骤。虽然海德格尔在对此在的理解中排除了人与上帝的关联,但是布尔特曼毕竟认识到此在分析对神学的间接支持,积极采用了此在分析方法,并力图向神学领域加以推进。他不仅把人与上帝的关联、人对圣经语言的感悟以及此在的带有决断性的本真生存同此在分析连结起来,而且采用这一分析扩展了传统基督教的相关概念,例如生存的历史性、可能性、事实性、时间性、未来性、有限性、决断性、焦虑、本真的存在与非本真的存在等等。当然,布尔特曼对海德格尔的利用并不彻底,此在分析仅仅是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存在论)研究的一个开端,尤其是晚期海德格尔转向与诗人和哲人的对话,把语言看作“存在”的家,这同样是为了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方法上的步骤——究竟以何种方式在本己的存在中言说那不可言说的存在本身。布尔特曼并未对此加以利用,以至于利科指责他为了利用海德格尔的“生存现象”而走了捷径。布尔特曼的生存论分析走了一条从人到神的路向,他试图扩展人类语言的日常用法,以便用它来谈论上帝。尽管他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除了神话的“语言描述”之形式,并使圣经本文的“福音宣示”之意义展露出来了,但当他把人类语言的一般用法扩展到上帝这一关节点时,则只能把上帝简化为一种生存之理想或价值观之核心,导致把上帝作为人类生存范围内的一个因素而被同化,从而否认上帝的神圣性和超越性,这是布尔特曼式生存论分析方法的内在缺陷所决定的必然结果。
四、生存论—本体论分析
在当代宗教语言研究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向就是试图把生存论与本体论融合起来,以期在谈论人的语言与谈论上帝的语言之间建立一座坚固的“逻辑桥梁”,这便是生存论—本体论分析所做的努力。这种努力由蒂利希(Paul Tillich)开始,继而麦奎利(John Macquarrie)作了进一步推进。
蒂利希认为,宗教神学始于人之生存所提出的问题,它应该采用“相互关联法”从生存上揭示存在的意义,而宗教神学对存在问题的关注只有通过哲学所使用的本体论范畴才能表现自己,因而从生存上揭示存在的意义就必须在启示中寻找答案。由此,他把宗教神学看作人的终极关怀,并在寻求表达终极关怀的语言问题上提出了象征论。“人的终极关怀一定要用象征才能表达出来,因为只有象征性语言才能表达这个终极。”(注:Dynamics of Faith,New York,Haper and Row,1957,P.41。)象征是一种语言表达形式。蒂利希从分析象征性语言的一般特点入手,着重分析了宗教象征。他认为,宗教象征与其他所有象征一样能展示一种实在层次;然而与其他象征又不同,它展示的是“实在本身之深层”,“此一深层是实在的所有其他维度与深度的基础,因此它不是和其他层次无关的,而是根本的层次,是位于所有其他层次之下的那个层次,是存在本身的层次,或者说是存在之终极力量。”(注:蒂利希:“宗教语言的本质”(The Nature of Rrligious Language),转引自张志刚:《走向神圣》,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宗教象征的独特性在于它揭示的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它既能“介入”此在之生存直接指向有限,为神性开放人性的追求,又能“介入”终极实在的维度直接指向无限,为此在敞开神性的大门。当然,蒂利希特别强调“介入”不是等同,即使最合适的象征,也无法达到其所象征的那种实在,它只有“分有”(Participation)那种实在。象征论是蒂利希在宗教语言问题上的一种方法论建构,他试图通过它来打开此在与上帝之间的一条通路。为此,他进一步强调指出,除“上帝是存在本身”这一陈述是一个非象征性陈述外,其他关于上帝的断言都是象征性的,都只能在此基础上以神学的方式给出。换句话说,一旦把“上帝”理解为“存在本身”之后,“存在”概念就构成了所有关于上帝的象征性陈述的基础,任何具体存在物(beings)都能作为存在(Being)的一个象征用来揭示存在的意义,因为它分有了存在本身(上帝),所以都具有作为上帝的象征的可能性。这样“存在”一词就成了蒂利希用来弥合关于人的谈论与上帝的谈论之间的鸿沟的词。
麦奎利认为,蒂利希的“存在语言”在关于人的谈论与上帝的谈论之间搭起了一座本体论之桥,尽管这座桥显得窄小而摇晃。麦奎利当然想把这座本体论之桥建造得更加牢固,他对神学语言进行了系统地考察,提出了神学语言的“基本逻辑”是生存论—本体论语言。他认为,神学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表达形式,这种话语之所以有意义,原因就在于它隐含着一种形式化的生存论—本体论结构。他在对神话、象征、类比、悖论等具体的神学话语类型进行考察之后指出:“这种具体的神学话语既有生存论的方面(它对使用它的人之生存发生影响,并唤起他们的信奉),又有本体论的方面(它要求为理解上帝或神圣存在的神秘提供洞察)。”(注:麦奎利:《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安庆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页。)因此,他主张在方法论上把生存和存在、生存论的东西和本体论的东西结合起来,从而为谈论上帝提供逻辑基础。生存论—本体论语言作为神学语言的“基本逻辑”,是生存语言向存在语言的过渡、转化。生存语言是描述人自身在世界中的生存结构以及属于这种生存的可能性之存在方式的语言,由于它扎根于人之生存的经验范围内,因而是一种较容易理解其意义的语言。然而,神学需要在超越人类意识的实在中为深信上帝是一个与人相对而独立的真实的相异者提供根基。为此,生存语言就必须向存在语言过渡。存在语言可以达到一种本体论的维度,人们可以用它来谈论超越人的实在。生存语言之所以能转化为存在语言,主要是因为这种语言中隐含着存在之类比。麦奎利在蒂利希的基础上所做的推进,就在于他对存在之类比的逻辑作出了理性的说明。他强调了作为生存者的人是“世界之中的存在”,他的生存有一种基本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既可显示为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之开放,也可显示为对同一世界中的具体存在者之开放。一方面,时间构成了存在与具体存在者之间任何类比的基础,也为存在之类比提供了可能性;(注:具体论证请参见麦奎利:《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安庆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另一方面,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者,他不仅存在,而且还具有使其他事物存在的能力,这种独特性存在使得他在上帝的创造性中占有了一份。麦奎利不仅赞同蒂利希把上帝理解为存在本身,而且进一步把存在理解为创造、维持并完善具体存在物的“使在”(Letting-be)。这样,人的独特性就使得阐明上帝特征的类比成为可能。经过存在之类比,生存语言与存在语言之间就可过渡、转化,这便是生存论—本体论语言的逻辑基础。他说:“海德格尔还告诉我们,没有脱离具体存在物的存在,存在只有在具体存在物之中并通过具体存在物才能被认识。所以,假若这包含着存在完全超越于任何特殊存在物的意义,那么,这也包含着它内在于具体存在物中,并在其中得到理解的意义。”(注:麦奎利:《谈论上帝—神学的语言与逻辑之考察》,安庆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3页。)
从蒂利希的象征语言(存在语言)到麦奎利的生存论—本体论语言,标志着生存论—本体论分析方法基本定型,这在当代宗教语言研究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这种分析方法试图站在存在问题的高度上,从存在的意义出发,来重新审视宗教语言的语义生成基础,它把宗教语言既作为一种生存论现象又作为一种本体论现象看待,以使人类语言超越日常话语所谈论的对象之有限性而与信仰和神学所要谈论的上帝之无限性发生关联,从而为神学语言确立一种“基本逻辑”。从方法论根源看,生存论—本体论分析是存在主义语言哲学的现象学方法与宗教语言的嫁接,尤其与晚期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学的本体论转向有关,这在麦奎利那里表现得十分突出,可以说是海德格尔显示存在者之存在的本体论的方法论直接启发了麦奎利的生存论—本体论分析。笔者认为,这种分析就其强调从本体论高度而又不离弃人类生存境况和现代文化背景来理解宗教语言的特殊性,并力图使之能为现代人所理解而言,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无论是蒂利希还是麦奎利,由于他们都受制于信仰主义立场,因而决定了他们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缺陷。我们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真反省其方法论,才能为揭示宗教语言的本质、功能和意义寻找到合适的分析工具。
标签:本体论论文; 宗教论文; 上帝悖论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基督教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现象学论文; 圣经论文; 特曼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