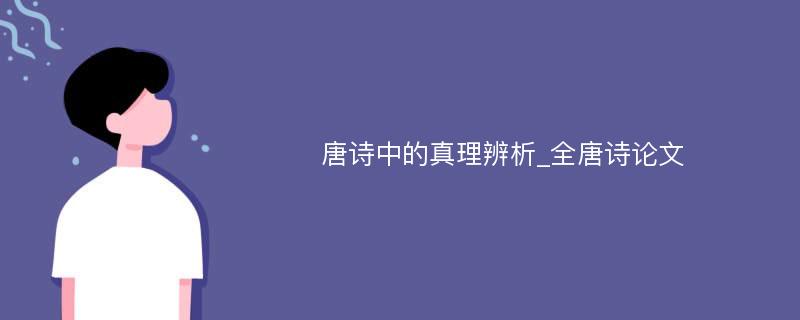
唐诗中的鉴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鉴真论文,唐诗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G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7)04-0043-06
一、郑谷《赠日东鉴禅师》
唐玄宗天宝十二载(753)正月元日,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臣云集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出席规模盛大的拜朝贺正仪式。上年抵达长安的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一行已经谒见过玄宗皇帝,获得“有义礼仪君子之国”称号;① 此次元日朝会,日本位居西班第二,新罗名列东班之首,遂引发“席位”之争,结果由吴怀实将军出面调停,日本与新罗对调了事。这一事件如果属实,说明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②
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元日朝会之后,玄宗皇帝又于三月及六月接见日本使臣。三月接见之际,藤原清河提出招聘鉴真赴日传教,由于玄宗命令道士同行,结果不了了之;六月的谒见大概是辞行,玄宗任命晁衡(阿倍仲麻吕)为送使,遣鸿胪大卿蒋挑捥护送至扬州,着淮南道处置使魏方进沿路照应。
藤原清河一行大致八月离开长安,沿运河一路南下,十月十五日至扬州延光寺拜见鉴真。自天宝元年(742)接受人唐僧荣睿等邀请决意东渡以来,12年间先后经历5次失败,因为遣唐使的来访,再次燃起鉴真东渡的希望。
鉴真一行搭乘的遣唐使船,当年十一月十六日离开苏州黄泗浦,十二月二十日终于抵达日本。本文聚焦于鉴真决意第六次东渡(十月十五日)至遣唐使船出航(十一月十六日)约一个月期间发生的事件,稽考唐人曾赋诗为鉴真送行的史实。
早在60余年前,日本学者春日礼智就推断司空图及郑谷的《赠日东鉴禅师》为赠别鉴真之作。他在《日华佛教交涉史年表》“天平胜宝六年(754)”条中论述道:
正月十二日,唐僧鉴真并弟子法进、祥彦、道兴、昙静、思託、义静、法载、法成、智首、潘仙童、胡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刀、膽波人善聪等二十四人,乘坐遣唐使大伴古麻吕的第三舶抵达筑紫太宰府。司空图及郑谷有《赠日东鉴禅师》诗,见《文苑英华》、《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③
大致同一时期,王婆楞在所著《历代征倭文献考》中,也认为《赠日东鉴禅师》所咏“鉴禅师”即为鉴真,但他把此诗的作者拟作“徐凝”,不知何据。
《赠日东鉴禅师》七言绝句,除了春日礼智提到的《文苑英华》、《全唐诗》、《古今图书集成》之外,郑谷《云台编》、周弼《万首唐人绝句》、曹学栓《石仓历代诗选》等亦有收录。《全唐诗》(卷六三三)列入司空图诗集,《全唐诗》(卷六七五)则当作郑谷作品,《文苑英华》仅作“前人”,但郑谷自编的《云台编》(卷中)收入此诗,作品当出自郑谷。其诗如下:
故国无心渡海潮,老禅方丈倚中条。
夜深雨绝松堂静,一点山萤照寂寥。④
如果此诗确系唐人为饯别鉴真所作,创作年代应该在天宝十二载(753)十一月十六日之前。可是拟为作者的三人,司空图(837-908)、郑谷(842-910)属晚唐诗人,徐凝在元和年间(806-830)任侍郎,他们纵横诗坛的时期比鉴真东渡晚一个世纪以上,所以把“鉴禅师”比定为鉴真缺乏根据。
二、皇甫曾《赠鉴上人》
日本学者藏中进致力于鉴真周边新史料的发掘,对唐代的诗文作品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在反复梳理检验了各种文本错误之后,最终注目于盛唐与中唐之际代表性诗人皇甫曾(721-758)的《赠鉴上人》,认定诗题中的“鉴上人”就是鉴真。
此五言律诗的标题及文中均没有出现“倭”、“日本”、“扶桑”、“日东”、“海东”等语句,故松下见林撰《异称日本传》等名著,均没有把此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资料对待。从这层意义来说,《赠鉴上人》虽然是广为人知的作品,但藏中进提出的观点可以说是一个“新发现”。
此作品除《全唐诗》外,还收录于唐宋时代的《中兴间气集》、《二皇甫集》、《文苑英华》以及明代的《唐诗品汇》、《古今诗删》等,流播甚广,影响颇大。《全唐诗》(卷二百十)题为“赠鉴上人”,别题“一作赠别筌公”,兹引录如下:
律仪传教诱,僧腊老烟霄。
树色依禅诵,泉声入寂寥。
宝[,龙][一作]龛经末劫[,远国][一作来],画壁见南朝。
深竹[一作户]风开合,寒潭[,泉][一作]月动摇。
息心归静理,爱道坐[,定至][一作]中宵。
更欲寻真去,乘船过海潮。⑤ [1](P2184)
诗题中的“鉴上人”到底指谁呢?藏中进仔细分析全诗的字句,认为满足“鉴上人”的人物,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僧侣,而且是具有多年“僧腊”的年老僧人;
(2)精通戒律,且与禅有密切关系的僧人;
(3)当时虽在静寂的僧堂中坐禅,但正在等待时机,准备“过海潮”的僧人;
(4)与作者皇甫曾为同时代的僧人。
藏中进通过反复论证得出结论:“满足上述条件的人物,我认为只有过海大师鉴真大和尚。”[2](P376)在此,笔者首先对条件(1)、(2)进行论述。
对应条件(1)的诗句为“僧腊老烟霄”。据真人元开(淡海三船)撰写的《唐大和上东征传》等可知,鉴真于垂拱四年(688)生于扬州江阳县,长安元年(701)于扬州大云寺出家,天宝元年(742)受入唐僧荣睿与普照招请,决意赴日传法,之后十二年间六次东渡。如果此诗为赠给天宝十二载(753)尝试第六次东渡的鉴真和上,那么当时鉴真已66岁,“僧腊”达53年,符合“僧腊老烟霄”的描述。
对应条件(2)的诗句为“律仪传教诱”与“树色依禅诵”。前句如《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淮南、江左净持戒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受戒大师”的那样,鉴真作为律宗名僧备受尊崇。至于后句的“禅诵”,藏中进征引《唐大和上东征传》如下的一节,指出鉴真师曾从智满学习禅门:[2](P385)
其父先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门。大和上年十四,随父入寺,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便就智满禅师,出家为沙弥。② [3](P16)
还有一些资料可佐证鉴真与禅的关系,如鉴真赴日后不久,淡海三船撰的《初谒大和上二首并序》中就有“禅林戒网密”;鉴真没后,石上宅嗣与藤原刷雄以及唐人高鹤林的追悼诗中,也有“禅草”、“禅光”、“禅院”。总之,作为描写“鉴上人”素行的“禅诵”,用在鉴真身上丝毫没有不适之感。
三、作诗的场所与时间
从上述《赠鉴上人》诗中描绘的年龄、经历以及宗派、素行等来推断,“鉴上人”比定为鉴真的两个条件极为一致。如果余下的场所和人际关系等问题也能解决的话,那么藏中进的学说将得到补强。
条件(3)出现了“静寂的僧堂”,藏中进推定其场所为扬州的延光寺或龙兴寺。天宝十二载(753)仲秋,以藤原清河为大使的遣唐使一行自长安南下,在赴出港地苏州的途中,于扬州的延光寺会见鉴真,商谈第六次东渡事宜。当时的情景,《唐大和上东征传》有如下生动的叙述:
天宝十二载岁次癸巳十月十五日壬午,日本国使大使特进藤原朝臣清河、副使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大伴宿弥胡万、副使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吉备朝臣真备、卫尉卿晁衡等至延光寺,白和上云:“弟子等早知和上五回渡海,向日本国,将欲传教。今亲奉颜色,顶礼欢喜。弟子等先录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和上名亦奏退。愿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在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时和上许诺已竟。[3](P40-41)
遣唐使劝诱之语“自作方便”、“去亦无难”似模棱两可,鉴真的回答看来斩钉截铁。于是,十月二十九日鉴真逃离官府严密监视的龙兴寺,赶赴遣唐使船停泊的苏州黄泗浦,十一月十日乘坐副使大伴古麻吕(大伴古万)的第三舶,十六日船队出港启程。
对于鉴真等待时机的寺院,藏中进指出:“诗中描绘老僧居住的僧房以及庭前的光景,当为鉴真大和上在扬州龙兴寺或延光寺之时。”[2](P382)其没有明确哪一个寺院,避开了延光寺或龙兴寺的特定。
关于作诗的时间,藏中进推定为鉴真自龙兴寺出走的“十月十九日”,并指出:“如上所述,十五日日本遣唐使一行至延光寺拜访鉴真之后,皇甫曾听到鉴真接受招请将要渡海的风闻需要二三天时间,如果将此要素考虑进去,确切的时间段为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这三天。”[2](P382)接着,藏中进又指出:“从《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十九日戌时从龙兴寺出,至江头乘船下’的状况来看,如果以《赠鉴上人》诗中‘深竹风开合,寒潭月动摇’描绘的景观为线索,可进一步推定为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深夜。”[2](P383)
需要说明的是,现存《唐大和上东征传》诸本均把鉴真等自龙兴寺出走的时间记载为“廿九日”,但与下文“(十月)廿三日庚寅,大使处分,大和上已下分乘副使已下舟毕”的记述相悖,故“廿九日”被认为是“十九日”的误写。
最后的条件(4)是关系到皇甫曾与鉴真是否为同时代人的问题。关于皇甫曾,《全唐诗》(卷二一零)载其略传云:
皇甫曾,字孝常,冉母弟也。天宝十二载登进士第,历侍御史,坐事徙舒州司马、阳翟令。诗名与兄相上下,当时比张氏景阳、孟阳云。《集》一卷,今编诗一卷。[1](P2179)
此外,《中兴间气集》(卷下)、《新唐书》(卷二零二)、《唐诗纪事》(卷二七)、《唐才子传》(卷三)等也有与上文大同小异的记载。
皇甫曾进士及第,《全唐诗》作“天宝十二载”。而此年,藤原清河率领第十二次遣唐使完成了使命,自长安出发,于十月十五日至扬州延光寺,招请鉴真渡日。可以发现,皇甫曾荣登进士、藤原清河等途经扬州、鉴真决意第六次东渡等这些事情较为巧合,那么皇甫曾赠呈鉴真饯别诗也纯属巧合吗?对此,藏中进指出:“此年,三十三岁进士登第的皇甫曾,于初冬十月的这个时候至江都扬州。听说鉴真大和上决意赴日之事,极为感动,遂至鉴真居住的僧房拜见,赠诗表达惜别之情。”[2](P383)
如上,我们对藏中进的观点作了一番概述。其功绩可谓至大,但其并没有解决所有的疑问。比如,别题中出现的“筌公”究竟何人?鉴真与皇甫曾赠诗往来的接点何在?如下,笔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考察,进一步推进藏中进提倡的新说。
四、鉴上人与筌公
皇甫曾的《赠鉴上人》诗,收录于多种文献,对于这些文献中的文字异同,藏中进有绵密的校勘。在此,我们省去烦琐的绍介,但诗题中的“鉴上人”与“筌公”的关系,至今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故我们首先以此问题为切入口进行探讨。
如上所述,《全唐诗》载为“赠鉴上人(一作赠别筌公)”,也就是说,虽然以“赠鉴上人”为诗题,但又有“赠别筌公”的别题。查看其他文献,可发现《二皇甫集》、《文苑英华》、《皇甫御使诗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所收)等均题为“赠鉴上人”,而只有《中兴间气集》题作“赠别筌公(一作赠鉴上人)”——“赠别筌公”为正题,“赠鉴上人”为别题。
《中兴间气集》为贞元元年(785)唐人高仲武收集肃宗、代宗二朝的名作而成,属于同时代的“唐人选唐诗”。因此,其史料价值自然比后世编撰的诗集要高,作为与原作品时代较近的善本,备受历代珍重。
那么,《中兴间气集》诗题中记录的“筌公”到底是何人呢?对此,藏中进指出:“‘筌公’是唐人呢,还是来自周边诸国在唐的留学者呢,今日难以究明。……管见所及,‘筌○’或‘○筌’之人未见于唐代的主要文献,《释氏疑年录》、《唐人行第录》等也未收载。视‘别筌公’为人名吧,其他唐代的文献没有记载,更没有见于日本文献。但不论如何,用‘筌公’呼称诗文内容受到某些限制的佛教僧侣,是极为不恰当的。……因此,作为此诗的标题,‘赠鉴上人’比较合适。”[2](P381-382)
上述藏中进观点的主旨有两点:其一,未见以“筌”为名号的唐人;其二,“筌公”的称呼不适合于僧侣。基于上述判断,藏中进主张舍去“赠别筌公”,而取“赠鉴上人”为诗题。但是,仅基于上述的理由,舍去与诗人皇甫曾同时代人编撰的《中兴间气集》的诗题,难以令人信服。考虑到这是一首赠送给欲渡海赴日的鉴真的送别诗,倒不如说“赠别”比单纯的“赠”要贴切。藏中进的判断是否有误呢?让我们进一步探讨。
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僧侣可否称呼为“公”。有唐一代,僧侣的尊称,在其名后加上“公”的现象是极为普通的。只要检索一下《宋高僧传》,就可以发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在称呼玄奘三藏的弟子唐僧窥基和新罗僧园测时,多使用“基公”、“测公”。另讳名为二字时,“公”放在后面的字后是一种惯例。因此,“筌公”大概是名为“○筌”之人的敬称。名字具有这样特点的人物在唐代并不是没有。例如,《佛祖统纪》(卷十五)就出现名为“李筌”的唐人。
如果以上的分析无误,那么可以推测鉴真拥有“筌”这一俗名或法号。支持此推测的史料有《延历僧录》(从高僧沙门释思託传)所载的如下一段文字:
思託述《和上行记》,兼请淡海真人元开述《和上东行传荃》。[4](P145)
研究学者们为如何解释“荃”字伤透了脑筋,迄今为止仍未有合理的答案。藏中进把此字视为书名一部分的同时,也指出:“《和上东行传荃》这一称谓是否为书名?还是《唐大和上东征传》的别称或略称呢?仍存有疑虑。”[2](P10)
也许这一制造麻烦的汉字“荃”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吧。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荃”与“筌”属于异形同字。“得鱼忘筌”的故事,原典为《庄子》(外物篇)所载的“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文中作“荃”,但意思与“筌”完全相同。《文选》中收录有郭璞的《江赋》,唐人李善在解释“罗筌”时指出:“筌,捕鱼之器,以竹为之,盖鱼笱属。”也就是说,筌为用竹制作的捕鱼渔具,故本字应该书写为“筌”。此外,用作“香草”之义时,二字可并用,但正字则为“荃”。
综上所述,《延历僧录》中出现的“荃”字,至今虽然难以究明,但与《中兴间气集》记载的诗题“赠别筌公”应该存在某种关联,可以视为指代鉴真之意。但是,“荃”字在《延历僧录》文中的位置却极为不自然,也许其前后有脱字,或者是原写本错漏产生的。⑦
如果这些问题姑且不谈,我们大致可以判断,在收录皇甫曾作品的唐人选唐诗集中,诗题作“赠别筌公”是不能舍去的,“筌公”应为鉴真的名号。
五、灵一与灵祐
藏中进的新说存在某些脆弱的部分,就是没有抓住连接鉴真与皇甫曾交往的接点问题。下面试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些考索。
鉴真多次渡航是触犯严禁私自出国的唐代法律的行为。天宝十二载(753)十月十五日,遣唐使至延光寺拜访鉴真之后,鉴真欲向日本国的消息传遍扬州城内,官府遂派兵加强警备龙兴寺。在此形势下,进士及第、刚登龙门的33岁青年诗人,为何去拜访欲打破国禁且已66岁的盲目老僧,并赠以惜别之诗呢?如果对此疑问不进行合理的说明,那么把“筌公”或“鉴上人”比定为鉴真的决定性证据是不太充足的。
在稽考鉴真与皇甫曾的人际关系时,名为“灵一”的僧侣徐徐浮出水面。灵一的传记见于《文苑英华》(卷八四六所收的孤独及《唐故扬州庆云寺律师一公塔铭》)、《唐才子传》、《宋高僧传》和《全唐诗》等。
基于上述传记资料,我们可以对灵一的生涯作一概述:开元十五年(727)出生,俗姓吴氏,广陵(今扬州)人。九岁出家,师事扬州龙兴寺法慎。之后,辗转于扬州庆云寺、延光寺、会稽南悬溜寺、余杭宜丰寺等。宝应元年(762)十月十六日,圆寂于杭州龙兴寺。除佛学著作《法性论》之外,《全唐诗》收录其诗一卷。其于春秋35岁夭折,是一位被誉为“诗僧”的希有俊才。
灵一在律学和诗文两方面,均具有较高的造诣。在律学方面,他与鉴真有种种关联;在诗文方面,则与皇甫曾保持密切交流。如果鉴真与皇甫曾之间存在接点的话,笔者认为灵一的可能性最大。
首先,我们来看灵一与鉴真的交往。扬州龙兴寺经律院居住着鉴真的先辈法慎(666-748),其门下名僧辈出,有被誉为“慎门三一”的昙一、怀一、灵一等人。鉴真与法慎同宗同寺,门下的弟子们自然有所交流。如《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鉴真“超群拔萃,为世师范”的弟子灵祐即师从法慎,与“慎门三一”有密切的交流。《宋高僧传》(卷十四)收录的《唐扬州龙兴寺法慎传》所载法慎的“上首”弟子中,灵一与灵祐并举。《宋高僧传》(卷十五)收录《唐余杭宜丰寺灵一传》所载灵一的“友善者”中,列举了慧凝、明幽、灵佑、昙一、义宣等人的名字。此外,据《全唐文》(卷九一八)收录的《唐苏州开元寺律和尚坟铭并序》记载,僧辩秀于天宝四载(745)师从东海大师鉴真受戒,随会稽大师昙一传讲。
如同上述,通过法慎、灵佑以及昙一等人,鉴真与灵一之间应该存在多渠道的交流。他们之间交往的接点,还不仅仅是他们周边的人际关系,他们生活的故乡扬州、他们活动的场所延光寺及龙兴寺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灵一与皇甫曾的关系。灵一仅活35岁,人生旅程较为短暂,但是其生命价值的丰富和深邃,通过其诗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其短暂的生涯中,佛教与文学的才能几乎同样卓越。诗文造诣较高的僧侣,世人尊称为“诗僧”。这样的人物在唐代约有60人左右,而灵一、灵澈、皎然、无可、法振、贯休、齐己等名列前茅。
灵一的作品在唐人高仲武撰的《中兴间气集》和姚合撰的《极玄集》中均录有4首。《全唐诗》(卷八零九)也收录其诗一卷,并有如下的略传:
灵一,姓吴氏,广陵人。居余杭宜丰寺。禅诵之暇,辄赋诗歌。与朱放、张继、皇甫曾诸人为尘外友。[1](P9123)
此外,《宋高僧传》(卷十五)收录的《唐余杭宜丰寺灵一传》载其“尘外之友”中,列举了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阳朱放、南阳张继、安定皇甫曾、范阳张南史、吴郡陆迅、东海徐嶷、景陵陆鸿渐等人。
另检索《全唐诗》,可以发现灵一与皇甫兄弟(皇甫曾与皇甫冉)之间,多次相互唱和送别诗文,具有亲密的交往关系。在此,笔者仅把相关作品的诗题列举如下:
(1)刘长卿《寄灵一上人初还云门(一作皇甫曾诗)》(《全唐诗》卷一四八)
(2)刘长卿《寄灵一上人(一作皇甫冉诗、一作郎士元诗)》(《全唐诗》卷一四八)
(3)李嘉祐《同皇甫冉赴官留别灵一上人》(《全唐诗》卷二零六)
(4)郎士元《赴无锡别灵一上人(一作刘长卿诗、一作皇甫冉诗)》(《全唐诗》卷二四八)
(5)皇甫冉《西陵寄灵一上人(一本题下有“朱放”二字)》(《全唐诗》卷二四九)
(6)皇甫冉《赴无锡寄别灵一、净虚二上人(一本有“还”字)云门所居(一作刘长卿诗、一作郎士元诗)》(《全唐诗》卷二四九)
(7)皇甫冉《小江懷灵一上人》(《全唐诗》卷二五零)
(8)灵一《酬皇甫冉西陵见寄(一作西陵渡)》(《全唐诗》卷八零九)
(9)灵一《酬皇甫冉将赴无锡于云门寺赠别》(《全唐诗》卷八零九)
(10)灵一《赠别皇甫曾》(《全唐诗》卷八零九)
(11)灵一《同使君宿大梁驿(与清江喜皇甫大夫同宿大梁驿诗小异)》(《全唐诗》卷八零九)
根据上述诗题,我们可以确认,灵一与皇甫曾作为“尘外之友”频繁应酬唱和诗文,而且同时与灵祐作为“友善者”也有亲密的交流。如上所述,灵祐为鉴真的门徒,是连接灵一与鉴真的重要媒介。
此外,皇甫曾与诗僧灵一亲切交流之事实本身,也表明了皇甫曾对佛教特别是律宗有深刻的理解。当他从灵一以及灵一周边的其他人员得知鉴真渡航的矢志不渝以及渡航九死一生的冒险行为,一定会被深深打动。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皇甫曾深知会被官府处罚也悄悄地赴龙兴寺拜访鉴真赠呈惜别诗的动机所在。
(附记:本文的部分内容,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宣讲,承葛继勇博士翻译成中文,谨表谢忱!)
注释:
①唐人思託《延历僧录》(卷二)记载:“使至长安,拜朝不拂尘。唐主开元天地大宝圣武应道皇帝云:‘彼国有贤王君,观其使臣趍揖有异。’即加号日本为有义礼仪君子之国。”
②关于此次事件,论者多引《续日本纪》(卷十九)天平胜宝六年(754)正月三十日条云:“副使大伴宿祢古麻吕自唐国至。古麻吕曰:‘大唐天宝十二载,岁在癸巳正月朔癸卯。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实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信其真者有之,疑其伪者有之。根据思託《延历僧录》(卷二)“复元日拜朝贺正,敕命日本使可于新罗使之上”记载,笔者以为不会是空穴来风。
③(日)春日礼智《日华佛教交涉史年表》附载于《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第四号(东京:日华佛教研究会,1940年10月),虽然比较陈旧,但不乏独到见解。
④诸本文字略有出入,如《全唐诗》(卷六三三)收录司空图《赠日东鉴禅师》,“渡”作“度”,“山”作“飞”。
⑤此诗诸本文字异同较多,除《全唐诗》考异之外,如《中兴间气集》“动摇”作“对摇”,“归”作“居”,“过”作“泛”。
⑥《唐大和上东征传》通行本(如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群书类从本、佛教全书本等)讹误甚多,故引文均据经笔者校勘的高山寺藏古写本,参见王勇《〈唐大和上东征传〉高山寺本题解并校录》,收录于《中日文史交流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⑦“筌”字尚有“序次”、“诠释”义项,而且草书字体与“鉴”相近,因此“和上东行传荃”也有可能是“荃和上东行传”的颠倒。暂且存疑,以待后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