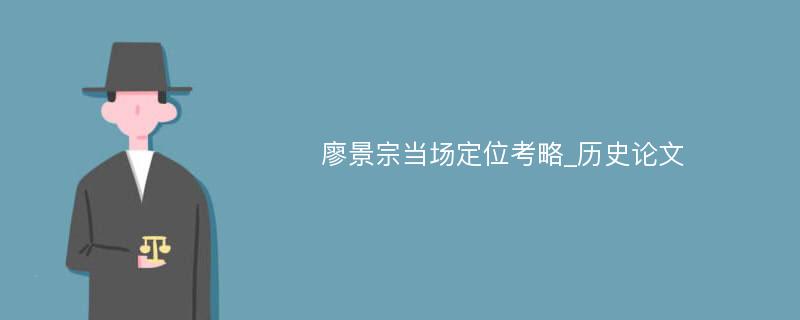
辽景宗即位考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景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6)06—0158—08
辽穆宗嗜酒好杀,不恤国政,无所进取,为国人所厌,故其在位十九年中,“谋反”、“谋叛”、“谋逆”事件屡屡发生。仅《辽史·穆宗纪》所载,计有应历二年(952年)正月,太尉忽古质谋逆,伏诛;二年六月,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澣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二年七月,政事令娄国、林牙敌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谋乱就执;三年十月,李胡子宛、郎君嵇干、敌烈谋反,事觉,辞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华割、郎君新罗等,皆执之;九年十二月,王子敌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萧达干等谋反,事觉,鞫之;十年七月,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谋反,伏诛;十年十月,李胡子喜隐谋反,辞连李胡,下狱死。九年之中,谋反者前后竟有七次之多。自十年十月李胡子喜隐谋反后,这类活动一度沉寂,直至十九年(969年)有近侍小哥、花哥等行刺穆宗,最后结束了他的统治, 而由世宗子耶律贤做了皇帝,是为辽景宗。
对于景宗之立,是否像《辽史·景宗纪》记载的那样简单,我一直心存疑惑,并将此疑惑写入论文《契丹贵族大会钩沉》:“景宗即位也是在穆宗被杀之后。穆宗无子,且‘酗酒怠政’,幼养于永兴宫中的耶律贤对其作为早有不满。穆宗被杀,他马上‘率飞龙使女里、侍中萧思温、南院枢密使高勋率甲骑千人驰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恸。群臣劝进,遂即皇帝位于柩前。’景宗即位是否也是仓促中的决定,我颇为怀疑。疑点有二:其一,景宗即位后,马上以‘宿卫不严’罪杀死殿前都点检耶律夷刺(耶律夷刺葛)和右皮室详稳乌古只。世宗遇害时,并未见宿卫被杀。而且,夷刺葛与穆宗为布衣交,一直是他的忠实臣仆。其二,杀死穆宗的近侍,即所谓‘应历逆党’小哥、花哥、辛古等,直至保宁五年(973年)才被抓获,不知是隐藏太深,还是有意包庇?因此,所谓‘群臣劝进’也可能是早有安排的必要程序。《辽史·景宗纪》还有一段穆宗有意传位于景宗的记载称:‘吾儿已成人,可付以政。’它究竟是出自穆宗之口,还是景宗拥立者们伪造的,也值得继续考察。”[1]
首先,我们对应历十九年前的七次“谋反”、“谋乱”、“谋逆”进行一番梳理,以找出其共同点与前后的差异。
第一次谋逆的太尉忽古质和第六次的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目前还难以确定其族属。
第二次的萧眉古得,只有《辽史·穆宗纪》一处记载,称“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宣政殿学士李澣等谋南奔,事觉,诏暴其罪。”[2] 这显然是对萧眉古得夺权活动败露后逃罪行为的记载。萧眉古得,《资治通鉴》、《契丹国志》载其汉名为萧海真,《旧五代史》称:“前翰林学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陈奏机事,且言伪幽州节度使萧海贞欲谋向化,帝甚嘉之。”[3] 《宋史·李澣传》载:“海贞与澣善,澣乘间讽海贞以南归之计,海贞纳之。”[4] 所谓“乘间”,或即萧眉古得(海贞)夺权失败,李澣乘机劝其南下投奔后周,事机不密,为人发现。
综合上述各种记载,萧眉古得系出国舅帐,辽世宗妻弟。官幽州节度使,虚职政事令。密谋夺权被察觉,走投无路,李澣乘机劝其投靠后周。萧眉古得采纳了他的意见,但南奔事再次暴露,穆宗下诏“暴其罪”。李澣是否参与了海贞的夺权活动,尚无足够的资料作出判断,但他不相信辽穆宗的治国能力,对辽朝政治形势的估计相当悲观,在海贞处境困难的情况下,为其设法,也为自己创造回归中原的条件,乃是顺理成章的。他甚至建议后周组织力量,北上灭辽。①
从萧眉古得南奔事发一个多月后,再次发生娄国等“谋乱”的事件看,这可能是一次活动的两个阶段。萧眉古得事机不密,败露后,不得已南奔避祸。娄国等或是与萧眉古得同谋而未被发现者,娄国甚至又加官为政事令。一个月后娄国与林牙敌烈、侍中神都和郎君海里“谋乱”。②
娄国,字勉辛,为东丹王耶律倍之子,辽世宗弟。火神淀之乱时,“手刃察哥”,穆宗即位,官南京留守。但“穆宗沉湎,不恤政事,娄国有觊觎之心,诱敌猎与群不逞谋逆”[5]。其实,娄国的叛逆,同前此历次谋叛一样, 都是由于穆宗的无能招致的宗室诸王对帝位的觊觎。
这次“谋逆”的又一个重要人物是耶律敌猎。敌猎,《辽史·穆宗纪》作敌烈,字乌辇,六院部人,世宗时官群牧都林牙。火神淀之乱时,察哥囚系不从乱的官员,敌猎也在囚系中。耶律屋质与寿安王耶律璟率兵平乱,察哥以事不成将杀被囚系的官员相威胁,敌猎以推荐寿安王之计说服察哥,被后者委以为使,见耶律璟。“寿安王用敌猎计,诱杀察哥,凡被胁之人无一被害者。乱即平,帝嘉赏,然未显用。敌猎失望,居常怏怏,结群不逞,阴怀不轨。”[6] 这就是第三次谋乱活动。这次活动又被发现,萧眉古得与娄国同时被杀。萧眉古得属国舅族,他可以参与夺权活动,却无由取得帝位,所以萧眉古得可能是娄国夺权的同党,只是因为过早暴露,为掩护同党才决定南奔的。如此,则第二次、第三次应为同一活动的两个阶段。
第四次,涉及李胡子宛、郎君嵇干、敌烈,更为严重的是“辞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华哥、郎君新罗”[2]。这次事件比前三次严重, 连穆宗的胞弟太平王罨撒葛也受到了牵连。李胡自辽太宗死,就觊觎着皇位,世宗在军中即位,粉碎了他的美梦。世宗被杀,又由耶律屋质仓促中迎立了穆宗,他又一次失去了即位的机会。他与诸子不甘心就此失去对皇位的继承,穆宗的残暴和无所作为又为其提供了机会,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之火。同时,同为太宗之子的罨撒葛,也纠集了自己的同党,图谋一试,他甚至向术者卜问吉凶。③ 他们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在处分上还是网开一面,随从者皆被处死,而主谋却得以逍遥法外。宛与罨撒葛皆被释,罨撒葛的最重处分也不过是被遣往西北戍边。如此处置,与契丹社会的传统习惯有关,早年的世选制为宗室诸王攫取最高权力提供了依据,只要得到贵族大会的认可就能使夺到的权力合法化。于是,一旦有机可乘,宗室诸王都会各施手段,纠集党羽,以求一逞。设使此次夺权得逞,则在李胡及其子宛和太平王罨撒葛之间还将有一场对决。皇位将在李胡系和太宗系间抉择。
罨撒葛之事后,诸王的夺权活动停止了五年,到应历九年,穆宗的行为没有任何改变,以穆宗的四弟王子敌烈为首,会同宣徽使耶律海思,再一次向穆宗的权力发起挑战,这是发生在穆宗朝的第五次“谋反”事件。
敌烈为辽太宗第四子,“多力善射”[7],曾参与援汉击宋战争,前已有东丹系和李胡系诸王谋取最高统治权,太宗次子罨撒葛夺权失败,如不乘机再起,太宗系的权力可能会转移到东丹系或李胡系。敌烈的“谋反”,是太宗系诸王保卫皇权的再一次尝试,也是辽朝宗室对穆宗的统治失去信心的表现。
参与这次活动的另一重要人物是耶律海思。海思,字铎衮,释鲁庶子。“机警口辩”,太宗时,诏求直言,他对与之交谈的明王安端和耶律颇德都有恰如其分的评价,为太宗所赏识,“擢宣徽使,屡任以事。帝知其贫,以金器赐之,海思即散于亲友,后从帝伐晋有功。”[8] 可见,这是一个有胆识、有才能的人。他参与谋反,应该说是对辽朝统治负责的表现。而选择了太宗子敌烈,则是对太宗系最高权力的保卫。不幸的是,敌烈未受到严惩,保守中还重新被封为翼王,而海思却被穆宗囚禁而死于狱中。
次年十月,李胡的另一个儿子喜隐也参与了对最高权力的争夺,且辞连李胡。这次惩治相对严厉,因为李胡二子两次谋反,可能都有李胡的指使,故他被逮入狱,且死于狱中。而对喜隐,曾经网开一面,“上临问有状,以亲释之。未几,复反,下狱。”[9] 如此看来,喜隐也曾两度参与谋反,那么,第一次可能就是以李胡子宛为首的谋反活动。这也应该是李胡夺权的两个阶段。而出头谋反者为其二子,幕后主谋则是李胡。
综观上述“谋反”、“谋叛”、“谋逆”、“谋乱”事件,第一次的主谋忽古质官居太尉,不知其为萧姓还是耶律;第二次的萧眉古得系出国舅;第六次的耶律寿远与楚阿不族属不详,这三次“谋乱”活动未见宗室诸王参与的记载。其余四次,无一例外都与宗室贵族相涉,这无疑都是宗室诸王的夺权活动。涉及的诸王有辽太祖幼子李胡及其子宛、喜隐,东丹王子娄国,太宗子罨撒葛、敌烈。其余协从者,皆是其拥戴者,而在处置上,协从者重,而诸王多数可免于惩处。李胡和娄国之所以从重,是因为他们都已参加了不止一次的夺权活动。④ 即便是未见诸王踪迹的第一、二、六这三次“谋乱”活动,也未必一定没有诸王的参与,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诸王的行动没有暴露而已。所以,无论哪一次“谋反”、“谋逆”、“谋乱”、“谋叛”,几乎都与诸王相涉,这是契丹社会的传统习惯在辽朝社会的反映。换言之,契丹世选制的残余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存在,它对辽朝皇位继承问题产生着重要影响。这是辽朝前期不断发生宗室诸王“谋乱”事件的社会根源。而穆宗在位时,此类事件尤多,则与穆宗本人缺乏政治理想、缺少治国才干和政治成就有直接关系,他不是一个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人选,这就不能不使其家族中自认有所作为者心生觊觎,试图凭借传统赋予的权利,以求一逞。在辽朝,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必要条件就是铲除这一传统习惯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看到,汉官在契丹贵族的争权活动中也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萧眉古得的南奔,有李澣帮助策划。结果是眉古得“伏诛”,李澣则“杖而释之”。喜隐的“谋反”,则有汉官韩匡嗣的参与。《辽史》中仅载“宋王喜隐谋叛,辞引匡嗣,上置不问。”[10] 似乎此事已不了了之,实则不然。 《韩匡嗣墓志铭》对此有一段十分隐晦的说明:匡嗣在太宗时,“以勋旧之胤,有干济之才,乃议褒升,罔循资级,特授右骁卫将军。在公既彰于勤瘁,进秩宜处于深严,改授二仪殿将军。……虽道无适莫,而运有穷通。三年不鸣,久居于散地。”⑤ 二仪殿将军为实职,即太祖庙详稳。这是喜隐谋叛前韩匡嗣的职位。所谓“道无适莫,运有穷通”则是说君主用人,并无薄厚之分,但个人的运气却有穷通之别。由于匡嗣在一段时间里,运气不佳,“居于散地”,被免了官。何以免官家居呢?匡嗣墓志一语带过,使人难知就里。而其妻的墓志则透露了相关信息。《韩匡嗣妻萧氏墓志铭》的相关内容,使这段历史得以恢复其原貌。墓志作者为了说明萧氏的“柔顺”与“仁厚”,将韩匡嗣参与贵族夺权活动失败后的处境作了如下描述:“应历中,秦王守兹直道,遘彼流言,因屈壮图,久居散地。夫人潜施辅导,益务唱随。罔以荣辱易其心,唯以穷通俟乎命。运当不字,既符云雷之屯;时偶大来,果应地天之泰。”⑥ 萧氏墓志中的“应历中”,据《辽史·穆宗纪》,当为“应历十年”⑦;“久居于散地”,即《匡嗣传》中“宋王喜隐谋叛,辞引匡嗣,上置不问”的结果。所谓“上置不问”,不过是没有治韩匡嗣助逆之罪。但也因此令韩匡嗣去官家居。所谓“直道”,即指废穆宗另立新君之举;所谓“流言”,正是喜隐事败露后,供词牵涉到了匡嗣,即“辞引匡嗣”;所谓“屈壮图”,则是废立事不成,匡嗣被迫家居的事实;所谓“三年不鸣”,则是引用典故,并非实指,匡嗣免官何止三年,自应历十年至十九年穆宗被杀、景宗即位,匡嗣免官家居达八年之久。⑧
墓志作者邢抱朴不愧史家,确有史家风范。这段文字,既表彰了墓主的美德,又展现了一段历史实情;既于墓主及其家人无伤,又堪称直笔。如不是他为我们留下这一珍贵资料,这段历史就可能留下空白。
这样看来,韩匡嗣参与了喜隐的夺权活动,已可坐实。但在对谋逆者的处理上,却有些值得深思之处。在对参与谋叛的契丹人,是主谋从宽而随从从严;而在有汉人参与的情况下,则是主谋从严而汉官从宽。李澣是“杖而释之”,匡嗣是“上置不问”,实则“置诸散地”。何以出现这样的反差呢?窃以为,或许汉官势力相对弱小,在辽朝统治集团或辽穆宗本人看来,还不足以影响大局,而宗室诸王才是皇权的真正威胁。但是,殊不知汉官参与的夺权活动,在某一时期不但足以威胁到辽穆宗的皇位,甚至直接关系到他个人的安危。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辽景宗即位的情况。
首先,将世宗与穆宗被杀的情况作一比较。《辽史·耶律屋质传》对世宗被杀前后的情况记载颇详。先是,有国舅萧翰,太宗子天德,安端子、世宗从叔刘哥、盆都等谋乱,时任惕隐的耶律屋质曾多次提醒世宗,世宗不听。直至刘哥怀刃行刺为世宗所亲见,才在屋质的坚持之下审问了他们。结果是诛天德,杖萧翰,迁刘哥,令盆都出使辖戛斯。此后,屋质对察哥的不法行为也有所觉察,并“表列泰宁王察哥阴谋事”,虽未引起世宗足够的重视,却任命屋质为右皮室详稳,负责世宗的保卫工作,谋逆者理所当然地将屋质视为夺权活动的最大障碍。故事件发生时,叛逆者扬言“衣紫者不可失”,屋质“乃易衣而出,亟遣人召诸王,及喻禁卫长皮室等同力讨贼。”[11] 可见,耶律屋质是这次讨逆的主要领导者。而后, 又在他主持下拥立了辽穆宗耶律璟。而时为寿安王的耶律璟对叛逆、讨逆与世宗被杀等事则漠不关心,对继任为帝也毫无思想准备。事发前,察哥曾向他透露消息,邀他一同起事,他不为所动。⑨ 事发时,他已回到自己的帐屋。“屋质遣弟冲迎之。王至,尚犹豫。屋质曰:‘大王嗣圣子,贼若得之,必不容。群臣将谁事,社稷将谁赖?万一落贼手,悔将何及?’王始悟。”[11] 接受拥立,也是在屋质陈说利害之后才决定的。《耶律屋质传》虽所用笔墨不多,但对事件的发展脉络交代得还是清楚的。虽事出仓促,因屋质早有戒备,故能及时平叛,使察哥的阴谋未能得逞。并在紧急情况下,派出自己的弟弟去迎请寿安王,以便拥立。而穆宗却毫无思想准备,在皇位虚悬、近臣拥立的情况下仍犹豫不决。将穆宗与此事无关的实情突显了出来。
穆宗被杀、景宗即位的情况与此大不相同。穆宗被杀,没有平乱者,仅有“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2] 的简单记载。景宗即位,则称“穆宗遇弑,帝率飞龙使女里、侍中萧思温、南院枢密使高勋率甲骑千人驰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恸。群臣劝进,遂即皇帝位于柩前。”[12] 穆宗被杀时,何人在身边,他们有什么行动?当时,耶律贤身在何处?何人向他报告的消息?驰赴行在意欲何为?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理由劝进?有无不同意见?景宗对此态度如何?一切付诸阙如,难道不应该问几个为什么吗?
其次,如何对待前朝侍卫。世宗被杀时,耶律屋质为右皮室详稳,因对夺权者早有警觉,故为他们所嫉恨,必欲置之死地。耶律屋质逃脱后,一面召集诸王,一面组织力量平乱。首先受命平叛的是禁卫长和皮室军,而且是招之即来。有关耶律屋质与辽穆宗平叛的过程,反叛与平叛者的态度,谈判的过程等,这在《辽史·逆臣上·察哥》中都有详尽的记录。
穆宗被杀时,景宗并未参加平乱,对行刺穆宗的小哥、花哥和辛古的去向也未追查,禁卫人员和百官的态度、行为也全不见于记载,这与世宗被杀和穆宗即位时的情况大相径庭。有的学者认为穆宗是死于奴隶起义,这并非全无可能,因为穆宗为人残暴,常以细故杀人,身边的近侍人员被杀者甚多,致使近侍人员不自安而起意行刺不无可能。假使如此,景宗即位后首先应惩治行刺者,并追究其同党,以便扫清余党,保卫自身的安全。何以对近侍人员竟未作任何盘查,却在事件起因、经过、参加者都没有弄清之前,便在即位当天迫不及待地处死了穆宗时的殿前都点检耶律夷刺葛和右皮室详稳乌古里?理由当然可以找到:宿卫不严。但这不能服人,须知夷刺葛和乌古里不仅是宿卫不严的责任人,还是重要的证人,甚至是嫌犯。那么,在未经调查、审理,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把重要的责任人、证人、嫌犯处死,原因何在?理由只有一个:灭口。
何人能实施杀人灭口呢?事件之后的掌权者。何人需要灭口呢?当然是事件的制造者和受益者,即辽景宗耶律贤。耶律贤即位绝不像《辽史》记载的那么简单,这是一次有准备、有预谋的夺权活动,事件的制造者们吸取了此前多次夺权失败的教训,组织得更周详,部署得更巧妙,事后掩盖得也更为严密。但是,掩盖得再严密,也终有暴露的一天。对《韩匡嗣墓志铭》进行认真的研究,便可使景宗阴谋夺权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喜隐夺权的失败,使韩匡嗣离开了权力中心,但他并未就此罢休,他吸取了失败的教训,改变了夺权的方式,计划更加周密了,行动更谨慎了。九年之后,终于一举成功。
《辽史》中无论是《韩匡嗣传》还是《景宗纪》,对景宗策划夺权和韩匡嗣参与其事都掩盖得十分严密,绝无一字提及。如果不是韩匡嗣及其妻萧氏墓志铭的出土,这段历史可能比“烛影斧声”更难于破解。而匡嗣及其妻墓志的出土,却给了我们一把破解历史谜团的钥匙。
景宗的即位是由两部分活动构成的。首先是穆宗之死。按《辽史》的记载,应历十九年二月己巳,穆宗“如怀州,猎获熊,欢饮方醉,驰还行宫。是夜,近侍小哥、盥人滑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2] 然后是景宗之立。“应历十九年春二月戊辰,入见,穆宗曰:‘吾儿已成人,可付以政。’己巳,穆宗遇弑,帝率飞龙使女里、侍中萧思温、南院枢密使高勋率甲骑千人驰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恸。群臣劝进,遂即皇帝位于柩前。”给人的印象是穆宗被近侍人员杀死,景宗在群臣拥戴下即位。而群臣之所以拥戴景宗,是因为穆宗有言在先。但事实究竟如何呢?我们将《辽史》中的相关记载结合《韩匡嗣墓志铭》和《韩匡嗣妻萧氏墓志铭》作一深入分析,或可恢复历史的原貌。
《韩匡嗣墓志铭》在“三年不鸣,久居于散地之后”,一转而为“七日来复,果验于连山”。“复”为《周易·上经·卦二十四》,“七日来复”指天道运行;“连山”为三易之一,其卦以纯良为首。这里是说,天道运行,周回反复;韩匡嗣背运已去,否极泰来。“属孝成皇帝缵绍宗祧,振拔淹滞。一见奇表,便锡徽章,授始平军节度使、特进、太尉,封昌黎郡开国公。寻加推诚宣力功臣。”景宗即位,匡嗣便交了好运,授始平军节度使之实职,官特进、太尉,爵封开国公,又加以功臣名号。匡嗣以何理由职、官、爵都得以超授?有何功德在景宗即位之初就授以功臣之号呢?《墓志铭》说是以“奇表”和“振拔淹滞”,似乎前此耶律贤并不认识韩匡嗣,做了皇帝后才得见其面,为其“奇表”所动,又知其“淹滞”已久。且不说只因“奇表”便授以高官、显爵、重职、功臣号,与理难通,就是实际上,耶律贤与韩匡嗣也并非晚至其为帝时始见。《辽史》虽刻意掩盖了耶律贤夺权的有关事实,却未能彻底掩盖他与韩匡嗣的关系。《辽史》中不只一处记录了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辽景宗即位前,与耶律贤适、韩匡嗣、女里等关系非常密切,不时一起发泄对时局的不满:“初,景宗在潜邸,善匡嗣。”[10] 是他们关系密切的证明。耶律贤“既长,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与韩匡嗣语及时事,耶律贤适止之。”[12] “景宗在潜邸,常与韩匡嗣、女里等游,言或刺讥,贤适劝宜早疏绝,由是穆宗终不见疑,贤适之力也。”[13] 是他们时常一起议论时政、发泄不满、组织队伍、阴谋夺权的行动写照。只是耶律贤适比较谨慎,不时提醒他们,故而他们的活动没被穆宗发觉。
邢抱朴在《韩匡嗣妻萧氏墓志铭》中则直接道出了匡嗣升官的真相:“俄属景宗成皇帝中兴宝祚,图用旧人。”显然,对于耶律贤来说,韩匡嗣并非因“奇表”和“振拔淹滞”才得以在景宗即位时荣升,而是因为他乃景宗在潜邸时的“旧人”。这是个什么样的“旧人”呢?这是一个在闲居期间帮助耶律贤策划夺权活动的“旧人”。
参与耶律贤夺权活动者,我推断,至少有韩匡嗣、女里、萧思温和高勋。
韩匡嗣因参与喜隐夺权活动是选错了对象,史载:“喜隐轻傈无恒,小得志即骄”[9],不足以成大事。匡嗣因此被撤职,心有不甘,一定会物色新人,以求再举。他与耶律贤关系密切,当然会将其列为新的人选。他们既能在一起议论时政,表达对穆宗的不满,就有可能策划取而代之。景宗初即位就大力提拔韩匡嗣,并授以功臣名号,显然是对他参与策划夺权活动的酬赏。由此推断韩匡嗣参与了景宗的夺权活动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女里出身卑微,为积庆官官分人。穆宗时,为习马小底。“景宗在潜邸,以女里出自本宫,待遇殊厚,女里亦倾心结纳。及穆宗遇弑,女里奔赴景宗。是夜,集禁兵五百以卫。既即位,以翼戴功,加政事令、契丹行宫都部署,赏赉甚渥,寻加授太尉。”[14] 这样,我们对景宗即位时的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是女里将穆宗被杀的消息报告了耶律贤,并组织了禁兵五百人保卫耶律贤,或者说这五百人是景宗夺权一旦遭到抵制即可实行反击的武装力量。显然,女里是耶律贤的同党,他的具体任务就是观察近侍人员行刺的成败,通风报信。《辽史·女里传》中交代了耶律贤网罗女里的原因和方式。此人性贪,所谓“待遇殊厚”,恐怕是以金钱拉拢他入伙的。以一个驯马的使令人,一举而官政事令,领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实职,不久又加官太尉,与韩匡嗣的待遇何其相似。而“赏赉甚渥”,则是迎合了他“素贪”的本性。我甚至大胆推测,利用近侍人员谋杀辽穆宗的计策,是韩匡嗣参与谋划的,指令是女里传达的。因为他是使令人,与近侍、盥人、庖人的地位接近,与他们联系不易引起注意。与前几次不同,这次夺权活动乃是借他人之手行刺,而策划者始终隐于幕后。景宗在位期间,对女里、高勋等百般庇护,也是对其以往功劳的报偿。⑩
高勋是随同杜重威降辽的,他好结权贵。辽世宗时,为枢密使,总汉军事。辽穆宗时,封赵王,为上京、南京留守。穆宗被杀时,他是率甲骑驰赴迎驾者之一。因此,“景宗即位,以定策功,进王秦。”[15]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耶律贤适,他与耶律贤和韩匡嗣关系不错,他是否参与了夺权活动,目前还难以找到证据。但他保护了耶律贤与韩匡嗣,是毋庸置疑的。景宗即位时,贤适“以功加检校太保,寻遥授宁江军节度使,赐推忠协力功臣。时帝初践祚,多疑诸王或萌非望,阴以贤适为腹心,加特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3] 次年,萧思温被害后,接任北院枢密使,兼侍中,赐保节功臣号。从景宗即位后,贤适官位的迁升和功臣号的赐予看,贤适应该也是这次夺权活动的参加者,至少是知情者。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耶律贤与萧思温、韩匡嗣、高勋、女里等,利用群臣对辽穆宗的失望情绪和近侍人员对辽穆宗的恐惧,借近侍之手杀死了穆宗,由萧思温等拥立为帝。
萧思温是景宗这次夺权活动的最大受益者,是谋杀穆宗的主将,景宗亲信集团的核心。他系出国舅,为敌鲁族弟忽没里之子,尚太宗女吕不古,为穆宗姊夫或妹夫。(11) 有女三人,长适太宗次子罨撒葛,次适李胡子喜隐,幼为萧绰,适东丹王耶律倍之孙、世宗子耶律贤。(12) 是思温三女,分嫁于太祖长子耶律倍、次子德光和幼子李胡三系。值得注意的是,萧思温的长婿罨撒葛、次婿喜隐前此都曾做过夺权的尝试,可惜皆未成功。长、次二婿夺权失败后,思温不得不将夺权的希望寄托在幼婿耶律贤的身上。史载:“思温尝观诸女扫地,惟后(萧绰——笔者注)洁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16] 为了萧氏家族,为了爱女, 为了耶律贤夺得最高权力,是他参与夺权的动机和动力。穆宗时,思温官南京留守,负有保卫南京,抵御后周的重任。但他在军中,“握齱修边幅”,不以军务为意,周世宗北伐时,他“不知计之所出,但云车驾旦夕至;麾下士奋跃请战,不从”。究竟是无能,还是不想为穆宗效力,我认为是后者。《辽史·萧思温传》批评说:“时穆宗酗酒怠政,思温以密戚预政,无所匡辅,士论不与。”那么,在穆宗被杀的事件中,他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应历)十九年,春蓃。上射熊而中,思温与夷离堇牙里斯等进酒上寿,帝醉还宫。”[17] 穆宗这次醉酒,极有可能是萧思温等人的有意安排。对穆宗行刺成功,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飞龙使女里等拥立景宗。这就回答了景宗为何人所立的问题。景宗即位,官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预其选。加官尚书令,封魏王。以其女萧绰为皇后。这样看来,罨撒葛和喜隐的谋逆,背后都有萧思温的影子,而耶律贤的夺权则是萧思温的最后一搏。可以说,萧思温是这次夺权活动的真正主谋。
联系穆宗被杀和景宗即位前后几天的情况来看,穆宗被杀的前一天,耶律贤得到了“吾儿已成人,可付以政”的许诺;接着是“思温与夷离堇牙里斯等进酒上寿,帝醉还宫”;然后是“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弑”,这一连串的事件绝非巧合,而是筹划周密的夺权活动的行动部署。
宋人对辽朝这次权力更迭的记载是“是岁(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契丹主明为帐下所弑。明性严忌,会醉,索食不得,欲斩庖者,庖者奉食挟刃杀明于黑山下。明立凡十九年,谥穆宗,号天顺皇帝。无子,诸部首领迎立天授皇帝兀欲之子明记,号天赞皇帝,更名贤,改元保宁。”(13) 这里,宋人对政变内情全然不知,他们的记载完全是得自辽朝官方的消息,故而与辽穆宗和辽景宗本纪的口径完全一致。
辽景宗的夺权成功,也付出了不小的政治代价。在诸王的目光集中在穆宗的宝座上时,人人都想成功,成功者如愿以偿,失势者当然将仇恨之火发泄在景宗的同党身上。萧思温目标最大,受惠最多,也就成了政敌的首选目标。景宗即位的翌年五月,萧思温被谋杀。(14) 九月,获谋杀萧思温的凶手国舅萧海只、海里、神覩。显然,萧思温是死于政敌之手,而非盗杀、贼杀。由此可以看出,宗室夺权活动背后,都有国舅的参与甚至主使。
参与耶律贤夺权活动的五人中,除韩匡嗣、耶律贤适外,均不得令终。与萧思温一样,高勋和女里也都未得善终。
高勋与女里死于保宁十年,(15) 前者为“赐死”,后者为“诏狱诛之”。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居功放纵,有碍于辽景宗的统治。《辽史·耶律贤适传》载:“大丞相高勋、契丹行宫都部署女里席宠放恣,及帝姨母、保姆势薰灼,一时纳赂请谒,门若贾区。贤适患之,言于帝,不报。”但是,高勋等人的作为激起了普遍不满,也遭到百官的弹劾:“保宁中,(高勋)以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帝欲从之。林牙耶律昆宣言于朝曰:‘高勋此奏,必有异志。果令种稻,引水为畦,设以京叛,官军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纳。寻迁南院枢密使。”[15] 耶律昆的弹劾实属捕风捉影,并无实据,它反映的是高勋的不得人心。
同时,高勋又卷入了另一起谋杀案,景宗弟只没妻安只制造鸩毒,高勋与之合谋,将毒药送给驸马都尉萧啜里。萧啜里之妻是景宗的姐妹和古典(胡古典、胡骨典)。这又是一起皇族与后族联合的谋杀行动,其对象为何人,未见明确记载。但高勋因此被除名。据《景宗纪》,此事发生在保宁八年。(16) 《高勋传》又载“事觉,流铜州。”兼采《景宗纪》与《高勋传》所载,则高勋于保宁八年因送人毒药事除名后,被流放到铜州。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寻又谋害尚书令萧思温,诏狱诛之,没其产,皆赐思温家。”[15]
令人意外的是女里居然也被牵入此案,“保宁末,坐私藏甲五百属,有司方按诘,女里袖中又得杀萧思温贼书,赐死。”[14] 高勋与女里,是否与萧思温被杀案相涉,很难定论,或许是因为他们过分骄纵,激起了广泛不满,为人栽赃陷害,也未可知。还是《耶律贤适传》所载可信度更高,他弹劾女里、高勋,甚至涉及景宗的姨母和保姆,却无一言提及女里、高勋谋害萧思温。所以,他们谋害萧思温事难以定论。贤适死于乾亨初,对高勋、女里的弹劾也很坚决,但始终没能将其扳倒,于是,所谓高勋以南京叛、馈萧啜里毒药和谋杀萧思温等,或许纯属子虚。试想,早在萧思温遇害的第四个月,就已经查出了凶手,而《高勋传》则将谋害萧思温事系于保宁八年之后,显然无法令人信服。而萧思温被害八年后的保宁十年,才从女里袖中搜出“杀枢密使萧思温贼书”,则更加令人难以置信。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明,女里和高勋因参与景宗夺权有功,受到景宗的恩宠与庇护,骄纵不法,贪赃受贿,为时论所不容,以一般的过失已无法治其罪,才不得不罗织种种耸人听闻的罪名将其置于死地。当然也不排除他们的骄纵影响到辽景宗的统治,为了皇位的安全,不得不除掉他们。
韩匡嗣和耶律贤适二人均得令终。韩匡嗣所赐功臣号为“推诚宣力”,耶律贤适所得功臣号为“推忠协力”、“保节”。“宣力”与“协力”虽一字之差,匡嗣与贤适的角色定位即可明朗,韩匡嗣所起的作用当仅次于思温。而“保节”一词也如实地反映了贤适“忠介肤敏,推诚待人”[13],不居功自傲的品行。
汉官韩匡嗣至少参与了萧思温策划的两次夺权活动。他何以不屈不挠、屡次追随萧思温呢?这要从韩氏与萧氏家族的亲密关系中查找原因。据宋人记载,萧绰曾许嫁韩德让,后因耶律贤求婚于萧,思温才将萧绰嫁与耶律贤。(17) 此事有三个直接后果:
萧家悔婚,就欠了韩家一份人情,韩家不予计较,两家关系可更进一步,于是韩匡嗣才可能成为萧思温的同党。又,匡嗣妻萧氏属国舅大父房,为敌鲁曾孙,萧思温为敌鲁族弟忽没里之子。思温与萧氏为同族,这种婚姻关系和同族关系也可能是萧思温与韩匡嗣结成同党的又一因素。
萧思温之所以悔婚,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在长女、次女已嫁入太宗系和李胡系后,思温又谋划在太祖长子耶律倍系安插上一个女儿,故夺已许嫁韩氏之女改许耶律贤。可以说,萧绰是思温的政治赌注。萧思温确非等闲之辈,他以三女分别嫁给辽太祖和述律皇后的长子耶律倍的孙子耶律贤、次子耶律德光和幼子李胡的儿子耶律罨撒葛和耶律喜隐[18],无论皇位转入辽太祖三子中的哪一系,他的女儿中都可能有一位当上皇后。
追溯应历十年喜隐的谋反,《辽史》仅记“辞连李胡”、“辞连匡嗣”。其实,还应有一位最大的漏网者,他就是萧思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推测:早在应历三年,萧思温可能就已参与了罨撒葛的夺权活动,那一次暴露的是李胡子宛,“辞连罨撒葛”,萧思温则是一个躲在幕后的隐藏最深的阴谋家。此事败露后,萧思温不死心,他还有二女婿赵王喜隐。或许他联络了韩匡嗣,也可能匡嗣主动投靠了萧思温,于是,在思温为喜隐谋取皇位时,匡嗣就出场了,这才有喜隐谋反“辞连匡嗣”的情况发生。当然,萧思温有自己的算盘,能否实现还要看客观情势,穆宗的无所作为则给他提供了机会。两次夺权皆未成功,他就不能不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小女和耶律贤的身上了。看来,萧思温是一个城府极深又善掩饰的人,他在穆宗朝表现得如此消极被动,一则是不愿为其效力,一则是以无能掩饰其阴谋,即所谓韬晦之计。景宗夺权后,他本可大展宏图,可惜却很快就被谋杀。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活动太频繁、太隐秘了,契丹贵族们或早有觉察,或直至他取得成功后才恍然大悟,于是,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政敌们的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他自己,则因多次努力终获成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忽视了对手,不想乐极生悲,最终死于政敌手下。
幽州韩氏的韩延徽与玉田韩氏的韩匡嗣之父韩知古是较早入辽的汉官,在官场上,延徽起步早于也高于知古,但在辽朝中后期,知古家族的影响和势力要远远大于韩延徽家族。自辽景宗始,辽朝的皇位继承权由德光一系转入耶律倍一系,这是辽朝皇室权力交接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韩氏家族在辽朝地位的重大转折,韩匡嗣在景宗继统的活动中立了不世之功,韩知古的事业,自他得以发扬光大。自此,玉田韩氏与辽宗室的关系日益密切,直至韩德让赐国姓,出宫籍,隶季父房。玉田韩氏的势力也就高居于幽州韩氏之上了。
需要说明的是,揭示景宗即位的内幕,并非是指责其夺权的非法性。相反,如果穆宗的统治继续下去,将会把辽政权引向衰败,而景宗的即位,稳定了辽朝的统治基础,为中兴和全盛奠定了基础,这次的权力交接对辽政权来说是幸运的、值得肯定的。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景宗即位是向穆宗夺权的结果,意在说明辽政权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契丹社会世选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其残余在继续向辽朝政治施加影响。辽朝前四帝时,像中原地区那样的嫡长子制尚未确立。穆宗朝的多次谋反、谋逆、谋叛,正是两种制度转型期辽朝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无奈与尴尬。
景宗夺权的成功对辽朝政权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它结束了穆宗的残暴统治,扭转了辽朝统治衰败的趋势,为中兴奠定了基础。由于萧绰执掌了辽朝的最高统治权,使她的治国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辽政权的统治得已巩固和发展,直接促成了辽圣宗时期全盛局面的形成,也将萧绰造就为辽朝的契丹女政治家。
韩匡嗣以汉官身份参与了契丹上层的权力之争,景宗、圣宗统治时期,以韩氏家族为代表的汉官地位明显提高,使辽朝统治范围内汉文化的影响进一步增强。甚至辽宋澶渊之盟的签订,汉官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如王继忠在双方间的沟通促成了澶渊之盟的签订,而汉官的地位提高及其在辽朝重大问题至少是辽宋关系决策方面施加的影响,也明显重于辽朝前四帝时期。从宋人对韩德让的评价上即可看出辽朝汉宫对辽宋关系的态度:“自为相以来,结欢宋朝,岁时修穆,无少间隙,贴服中外,无有邪谋。”[19]
景宗即位后,辽朝政治发展的进程明显加快,景宗与皇后萧绰和他的继承人圣宗继续推行自太祖、太宗以来就已逐渐开始的胡汉分治制度,进一步完善南北面官制,整顿吏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调整赋役制度,加强对属国和属部的管理,使科举制度化等等。
更为突出的是景宗的统治催生了辽朝的嫡长子继承制。穆宗时诸王“谋乱”的频繁发生,是契丹旧俗在特定条件下的发挥作用的反映。辽景宗是在多次“谋乱”失败后的侥幸成功者,虽然旧俗给了他们机会,但时代毕竟是前进了,社会毕竟是发展了,旧俗不能再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新制度也处于呼之欲出的时刻了。景宗在汉官的影响和自身的领悟中,认识到了旧俗对皇权的威胁,改变旧俗的意识增强了。萧绰在景宗朝的执政经历使之受到了锻炼,其政绩也提高了她本人的威望,虽然景宗体弱多病,但在蕃汉臣僚的辅佐下,扭转了穆宗时的混乱,安抚了宗室诸王,稳定了社会秩序,调整了与宋朝的关系。圣宗虽年幼即位,萧绰的继续执掌国政使辽朝最高权力得以平稳交接。积累景宗、圣宗两朝的经验教训,嫡长子继承制的出现已是势所必然。辽朝文献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嫡长子继承制制定和形成时间的记载,但圣宗以景宗嫡长子身份即位;兴宗虽非嫡子,而在圣宗无嫡的情况下,以长子身份即位也是正常的;兴宗在世时,虽曾有过千秋万代后转位于弟重元的许诺,但嫡长子洪基还是得以较顺利地继承了皇位;辽道宗本已立了太子濬,只是由于耶律乙辛的擅权,使太子被害致死,皇位继承上又出现了变数,但最终耶律延禧还是以嫡长孙的身份继承了皇位。所以,自辽景宗始,辽朝事实上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应该说是辽朝贵族政治走向衰落的标志。
收稿日期:2006—05—28
注释:
① 《册府元龟》卷七六二《总·忠义三》:“今皇骄騃,唯好击鞠,耽于内宠,固无四方之志。观其形势,不同以前。亲密跺臣,尚怀异志,即微弱可知。……乘其乱弱之时,计亦昴和,若办得来讨,惟速;若且和,亦惟速,将来必不能力助河东。”
② 《辽史·穆宗纪上》:应历二年七月,“政事令娄国、林牙敌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谋乱就执。八月,眉古得、娄国等伏诛,杖李澣而释之。”
③ 《辽史·方伎·魏璘传》:“璘尝为太平王罨撒葛卜僭立事”;《辽史·皇子表》:“罨撒葛,太宗第二子,谋乱,令司天魏璘卜日。觉,贬西北边戍。”
④ 李胡二子两次谋反,第二次更“辞连李胡”,故被囚。娄国在世宗时,曾阴谋篡取其兄的权力,穆宗对其早有戒备,故被杀。《辽史·逆臣上·娄国》:娄国阴谋向穆宗夺权,“事觉,按问不服。帝曰:‘朕为寿安王时卿即以此事说我,今日岂有虚乎?’安国不能对。”
⑤ [辽]马得臣《韩匡嗣墓志铭》,见刘凤翥、金永田《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考释》附录一,《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新9期。
⑥ [辽]邢抱朴《韩匡嗣妻萧氏墓志铭》,见刘凤翥、金永田《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考释》附录二,《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新9期。
⑦ 《辽史·穆宗纪上》:应历十年“冬十月丙子,李胡子喜隐谋反,辞连李胡,下狱死。”
⑧ 参见刘凤翥、金永田《辽代韩匡嗣与其家人三墓志铭考释》及其附录一《韩匡嗣墓志铭》、附录二《韩匡嗣妻萧氏墓志铭》,《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0年新9期。
⑨ 《辽史·逆臣上·察割传》:“帝伐周,至详(祥)古山,太后与帝祭让国皇帝于行宫,群臣皆醉。察哥归见寿安王,邀与语,王弗从。”
⑩ 《辽史·耶律贤适传》:“大丞相高勋、契丹行宫都部署女里席宠放恣,及帝姨母、保姆势薰灼。一时纳赂请谒,门若贾区。贤适患之,言于帝,不报。”
(11) 《辽史·公主表》:太宗长女吕不古,应历间封燕国长公主,保宁中封燕国大长公主。《辽史·萧思温传》:思温“太宗时为奚秃里太尉,尚燕国公主。”知思温妻为太宗女吕不古,太宗时封燕国公主,保宁间封燕国大长公主。故《萧思温传》称:“思温以密戚执政。”
(12)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五咸平六年:“萧氏有姊二人,长适齐王……次适赵王。”齐王即辽太宗次子罨撒葛,赵王即李胡子喜隐。
(1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其主明”,即辽穆宗。
(14) 《辽史·景宗纪上》记载:保宁二年五月,“盗杀萧思温”。
(15) 《辽史·景宗纪上》:保宁八年,“秋七月丙寅朔,宁王只没妻安只伏诛,只没、高勋等除名。”《景宗纪下》:保宁十年,“五月癸卯,赐女里死,遣人诛高勋等。”而《女里传》载,女里死于“保宁末”;《高勋传》载,高勋死于“保宁中”。当以《景宗纪》为准,是女里、高勋死于同一天,一赐死,一伏诛。《女里传》的“保宁末”较《高勋传》的“保宁中”更为准确。
(16) 《辽史·景宗纪上》:保宁八年七月,“宁王只没妻安只伏诛,只没、高勋除名。”
(17) 《路振乘轺录疏证稿》:“萧后幼时,常(尝)许嫁韩氏,即韩德让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妇于萧氏,萧氏夺韩氏妇以纳之。”见贾敬颜《五代宋金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中华书局,2004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