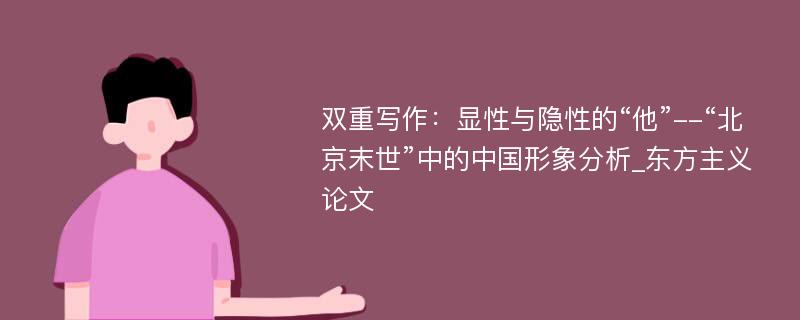
双重书写:显性与隐性的“他者”——《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的中国形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显性论文,隐性论文,北京论文,中国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 (2007)01—0238—06
中国,作为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在不同的世界历史时期有着迥然有别的形象。中国在法国文学中的形象更可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自16世纪传教士把中国介绍到西方起,中国形象便与“理想国”、“桃花源”结下不解之缘。此后几个世纪,中国都成为一代代法国作家神往、探寻的对象。[1] 然而,随着西方帝国海外殖民的疯狂扩张,尤其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的两次鸦片战争及八国联军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国形象发生彻底扭转。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2] 正是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这位擅写异国情调的作家常常把他在异国《东方》的旅行见闻以一种“虚构加写实”的混合方式进行加工创作,因而他的作品多是具有“印象派艺术”风格的半自传体小说。[3] 他的《冰岛渔夫》和《菊子夫人》对于中国读者并不陌生。① 然而,《在北京最后的日子》这部真正与中国相关的作品,人们却知之甚少。② 这是一部纪实性很强的文学作品,是20世纪初身为海军文官的绿蒂两次到中国北京进行战地考察的日记汇编。
身为军人,绿蒂虽然屡次重申自己的“文官”身份,似欲极力撇清与侵略行动的干系(北京在他到之前已沦陷),但落笔仍脱不去自恃优越的文化心态。他与中国在空间上的近距离接触使得《在北京最后的日子》这部作品成为对灾难中国的“唯丑”记录:“蒙昧的”、“破败的”、“死亡无处不在的”中国是一个“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以解体为明显标志的帝国”[4]。而这也正是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所针对的东方主义——一种西方排斥、贬抑、宰制东方的意识形态化的东方主义,一种具有明显否定色彩的东方主义的文学印证。[5] 这一重书写从空间的维度上建构起殖民主义的合理性。
作为文人,绿蒂“对异域的态度又是暧昧的”,在其“自身所属的高度文明”之外,他深受“异域魅力”之惑,并试图通过比较来反驳欧洲人对东方的“造假与错解”[6]。在他的“异国情调”视域中,眼前的中国固然蒙昧、丑陋,但远古的中国却仍如同一个美好神话,有着曾令其先辈诸如伏尔泰等人痴迷的魅力。在这部作品中,绿蒂凭借臆想与记忆唤出了一个“理想化”、“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一个隐性的“他者”形象。这一重书写体现着另一种“东方主义”——一种被“遮蔽了的‘东方主义’,一种仰慕东方、憧憬东方,渴望从东方获得启示甚至将东方想像成幸福与智慧的乐园的‘东方主义’”[7]。这种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无疑是文人绿蒂对其自身文明感到困惑、无奈的一种内心隐忧与精神危机的流露。因而,这重书写又从时间的维度上解构了殖民主义的合理性。这一重书写深藏于前一重书写之下,不能一目了然,所以不易为读者觉察。本文欲尝试从这双重的维度来完整读解这部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一、显性的“他者”
言“他者”必以“自我”为参照。“自我”必本能地自动地优先于“他者”,并会根据“自我”的需要来定位“他者”。无论“他者”殊异于“自我”,还是同一于“自我”,即“另一个自我”或“自我的异体”,“自我”始终操纵着话语权。“自我”的这种“话语霸权”根据不同需求,必然有不同的服务指向,或政治,或军事,或经济,不一而足。从历史上看,19世纪是欧洲工业革命以后,社会逐步进入现代化的时期,同时也是欧洲向外扩张的时期,史称西方殖民时期。[8] 根据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这一时期正是西方以“主体”的“自我”对“客体”的“他者”进行殖民拷问的时期,是西方文化有意构筑低劣、被动、堕落、邪恶的东方形象,使东方成为西方观念与权力的“他者”的时期,是生产文化与物质霸权、培养文化冷漠与文化敌视的具有否定色彩和意识形态性质的东方主义的时期,是建构其殖民思想霸权的时期。[9]
军人绿蒂脱离不了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视域。他首先是殖民军代表,有着殖民者的视角,一个“居高临下”的视角。作品中多次出现“高高在上”的描写,或立于长城之上,或登临“玉岛”之巅,或凭眺“圆顶”亭台。那种“(中国)大地在我脚下”的征服欲浮动于字里行间。中国在这鸟瞰的图景中不可避免地被矮小化、“扁平”化、丑化、妖魔化和“意识形态”化。[10] 这是一个“以死亡标志的国家”,充满着“死亡、尸首和腐烂的困扰”,然后就是“破旧”、“衰败”。这是他对亲眼目睹的中国——一个显性“他者”的书写。这重书写集中展现在对中国景观与中国人的描述上。
最先跃入绿蒂眼帘的是中国的自然景观。“在这[……]荒漠般的平原上,[……]城市在黑暗中延伸着,狼藉遍地,到处闻得到瘟疫和死亡的气息。[……]都穿行于这黯淡的平原上。起先,也是[……]灰土地;接下去,变成了给冰霜打蔫的芦苇丛和牧场。[……]又过不多时,就看到平原上布满了无数的坟,[……]在我们眼前绵延不绝着的完全是一个死人的国度[……]”(第15页)。纵使其间有生物,也抹不去四处弥漫的死亡气息;更有芦苇和高粱这两样恐怖的植物:“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会撞上那高粱丛中横伸出一条腿在路面上恭候着我们的死尸”③(第21页),或在那“芦苇丛中,到处藏着一些微微泛白的球状物,那是死人的脑袋”(第31页)。此类描写俯拾即是。
中国的人文景观更占据作品的大量篇幅。中国的建筑物着墨最多:从大沽炮台、北京长城、城市民居、皇宫宝殿一直到墓地园林,色调多以灰、黑两色为主。“北京的长城[……],有着巴比伦的外貌,这黑黢黢的巨物,[……]城墙上纤草不生”(第51页);进入城门,“是一座瓦砾和灰烬的都市;[……]经过一场战火硝烟,所有略微陈旧的建筑都给粉碎了,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第52页);进入皇宫,“大殿洞开,风声呼啸,燕雀满栖。[……]到处是一样的荒凉,一样丛生的杂草,一样如坟场般哀丧,一样有划破沉寂的噪聒声”(第143页);离开北京,前往皇陵,“除了我们和树上的几只乌鸦,在这无边的陵园里,一切都是凝滞的、死气沉沉”(第207页)。整个中国的“城市、乡间,死亡无处不在”;“蒙昧的古老帝国”正在趋于解体。中国的形象是“衰败”的,“腐朽”的,“残破”的,“不再有丝毫恢复的可能”(第69页)。
绿蒂关注的另一焦点是中国人:中国百姓、中国官员及中国匪民。“黄皮肤”、“细眼睛”、“留长辫”,长着“奇丑无比的脸”,身穿“蓝布裤或长袍”、“猥琐龌龊”的中国男人以及“吊眼睛”、“小脚”、“穿着一模一样蓝布衣”的中国女人构成了人数最多的民众阶层。
至于中国官员,通常都是些“头戴羽翎红扣官帽”、“垂着灰色山羊胡子”、“留着长指甲”、“干瘪瘦削”的老头,爱“行大礼,说客套话”(第191页);也有像李鸿章这样的高官,显得“谜”一般“难以捉摸”、“狡黠阴鸷”:“(李)又询问我们在‘北宫’都干了些什么,很小心地打探,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在那儿搞破坏。我们在做什么,他比我们更清楚[……]。然而,当我们向他证实我们并没有毁坏什么时,他那张谜样的脸上装出了满意的神色。[……]尽管由于我‘文官’的头衔获得了他的款待,但这位中国的《一千零一夜》里的衣着破旧、处境寒酸的老臣却总是让我感到不安。他看上去深藏不露,不可捉摸,或者可能隐隐有些许轻蔑和讥讽之意。”(第132页)
中国匪民则指义和团团民,这是被间接描写的另一大群体。因为作者抵达中国时,真正的战争已告结束。他对中国匪民的了解更多借助一位法国传教士之口。他则不吝笔墨夸大这些匪民“野蛮”、“残忍”、“暴虐”等特征:“(义和军)大肆杀戮中国民众及外国人,尤其是北京地区的基督教徒”,一旦落入他们手中,“等待(那些被俘者的)将是伴着乐声和狂笑的可怕的折磨,大卸八块,先拔指甲,抽脚筋,挖脏腑,然后割掉脑袋,挑在棒端游街”(第57页)。
无疑,这些出自殖民者视角的描述正印证了当时的文化语境一亚洲“黄祸”论的流传。他们觉得那“四、五亿颗与(他们)转向相反的脑袋”是“不可阐透”的,是随时可能会“拿起武器进行一场(他们)无法估料的复仇”的(第208页)。我们看到作品中关于中国形象的这一重书写是完全顺应当时文化语境的需要的:那个国民污秽龌龊、建筑物随时倾圮、万物覆盖死灰、死亡到处肆虐、行将枯朽的古老帝国正是20世纪初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面对年轻的西方文明,这个帝国的“古老”意味的不再是历史悠久、文明渊长,而是“腐朽”、“解体”、“衰亡”。这个显性的“他者”形象被一塑再塑,目的是为西方的殖民行为进行辩护。不外是想说明,这些东方人太“野蛮”了,西方人之所以要进行殖民活动,完全是为了“文明与博爱的事业”服务。[11]
二、隐性的“他者”
针对赛义德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所关注的东方主义,中国学者周宁进一步提出“另一种东方主义”的理论。他指出:“西方文化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而后一种“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比后殖民主义理论所批判的东方主义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前者是“意识形态化”的东方主义,而后者是“乌托邦化”的东方主义。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知识或社会想像,意识形态的功能是整合、巩固权力,维护现实秩序;而乌托邦则具有颠覆性,超越并否定现实秩序”[12]。那么,作为文化产物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是否存在这另一重观照呢?
我们注意到作品中,中国之于绿蒂,仍是一个神秘、魔幻、美好、令人神往的国度。只是作品被“意识形态”化过于浓厚的东方主义的读解方式所“遮蔽”,读者难以领会到“另一种东方主义”的存在。其实,绿蒂为这一重书写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根据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关于形象学所提出的“两条轴”理论:客体方面,有在场和缺席轴;主体方面,有迷恋意识和批判意识轴[13],对应绿蒂的双重身份。如果说对于中国“他者”这一客体,作为主体的军人绿蒂有机会去那里“执行任务”和“实地考察”,有在被注视者文化中“位移”的实际经历,因此作品中出现最多的是“到场”的经验,对显性“他者”中国的直观复制,从而受主体的殖民视角所限将主体意识延伸到“批判轴”上,那么,当作为主体的文人绿蒂有意使得客体中国“缺席”或使之虚化时,其主体意识必然延伸向“迷恋轴”。也因此,当读者深度细读作品时,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隐性“他者”的形象。
在居留中国期间,绿蒂时不时提醒自己要“置身境外”,还特意申请了一间书斋:“我被获准可以把这座位于一片沉寂之中目前尚无人能住的宫殿当书斋用几天,今天上午就开始归我使用了。”(第80页)书斋使得主体绿蒂与客体中国间的交互“缺席”成为可能。中国从而不再是空间上的“他者”,而成为时间上的“他者”。“他者”不在眼前,而在历史的“别处”:在遥远的过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在绿蒂热衷异国情调的个体梦想中。绿蒂在对“他者”中国的这一重书写上运用了托多罗夫所说的“荷马法则”④[14]。他用心理上的距离为这个“他者”创造存在的可能,并坠入深深的“迷恋”。
如果说显性的“他者”形象过于灰暗,那么,这个“缺席”的、隐性的“他者”形象则要鲜活得多。在某个章节中,他写道:“‘莲花湖’和‘汉白玉桥’!这两个名字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了。这是仙境的名字,指的是那些不可能被看到的事物,而其名声早已穿越那不可逾越的高墙不胫而走了。对于我,这名字让人联想到光影与色彩的图像;[……]‘莲花湖!’……我所想像的,正如中国诗人所咏唱的那样,是一汪清澈透亮的湖泊,湖面上浮着满满的敞口圣杯般的莲花,是一个开满粉色花朵的水的原野,一个完全粉红的空间。[……]‘汉白玉桥!’……是的,这由一系列白色石柱支撑的长长的拱桥,这极为优雅的弧形,这一排排雕着怪兽头的柱栏,正符合了我对中国既有的想法:太华丽,太中国化了。”(第72页)而关于“天子之城”的建筑及其饰物的勾画更是浓墨重彩:“(帝王的老巢)在傍晚的这个时分,为我一人展示着它那琉璃瓦顶的异乎寻常的美态。[……]弧形的黄色琉璃瓦在红彤彤的阳光照射下熠熠放光,呈现出我们从未领略过的华美;在屋顶的四角,有如翼的装饰,在下部近边缘处,排列着吻兽,几百年来保持着相同的姿势,一动不动。当太阳西下的时候,那黄色琉璃瓦的金字塔顶闪闪发亮,[……]简直像一座金子的城市,然后又成了红铜的城市……”(第136页)由此,一个亦真亦幻的中国形象随着淋漓的色彩变得鲜活起来。
无论如何,这一重书写应该说是“理想建构多于真实描写的”[15]。作品中,“魔术幻灯(fantasmagorique)”是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词语,它被四次提及。“这个词从古老意义上展示了使灵魂再现的艺术,或是一种超自然的神怪的场景。”同时,也更加表达出他看待“他者”中国的另一个视角、另一种态度。“他从一种对一个正在解体的国家抱着看透了态度,过渡为对它的过去、艺术及文化的欣赏。”[16] 而这个过渡实现于他对隐性“他者”的渴望与召唤之中。这重“他者”形象因而被赋予美好的乌托邦色彩。
由此,这后一重书写是不能不提的。因为它正折射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精神世界的困惑和动摇。他们开始怀疑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核心,并试图重新在西方文明之外,在古老的东方找到启示与救赎。再度掀起的“东方热”不仅承继了浪漫主义时代有关东方的异国情调式的想像,更复兴了启蒙运动时期西方运用东方文明针砭西方社会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精神。[17] 在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学中出现了“一群东游的诗人”,他们“是怀疑的一代,探索的一代,尽管因着不同的机缘,不同的身份离家远游,但多半出于对自身文化的怀疑和颠覆,出于对‘他者’相异性的诱惑和吸引而走进中国,将之视为投放自己梦想的合适场所”[18]。而中国无疑是这群“诗人”精神或文化远游的“重镇”。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在艺术创作的“借尸还魂术”下“死而复生”,作为隔世的“他者”,穿越几个世纪重现于许多虚构或写实的文本中。中国之于文人绿蒂,从空间上代表着美好的东方,从时间上代表着美好的过去,是他那种怀乡恋故情结的寄托与精神和谐的向往。因此,中国于他仍不失为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绿蒂这一向内的视角,不是猎奇,而是深度的内窥、精神的投诚和感情的皈依。这一重“他者”形象反映着他以及同时代其他西方作家心中所向往的一种人生在世的方式。面对西方现代文明,他毫不掩饰厌恶之情:“我们欧洲城市的鸟瞰图呈现的却是一个多么荒蛮的丑态:一堵堵丑陋的山墙,粗糙的瓦片,烟囱林立的肮脏的屋顶,此外还有纵横交错的黑压压的恐怖的电线网!”(第135页)面对他构筑的精神家园,他感到无地自容:“文明在别处,真正的野蛮人是我们。我们出现在这里,举止粗俗,满身灰尘,疲惫沮丧,肮脏不堪,貌如未开化的野蛮人,无异于置身仙境的僭越者。”(第76页)
相反,他重拾先祖们对孔教乌托邦的崇尚,推崇以儒家精神为主体的道德秩序(如对逃亡途中晚辈尊爱长辈以及两位义和团“白女神”宁死不屈的气节等的描述)。他用“扬名”、“永生”、“古老”、“令人心灵安宁”对孔庙大加赞誉:“这是一座超凡脱俗的庙宇,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的庙宇。[……]更像一所学校,是哲人云集,冷静交谈之所。”(第113页)他用孔庙的一句碑铭为西方“那些忙着整理和调查的年轻学者们”解“文学是什么”之惑:“未来的文学将是同情的文学。”(第113页)而他对文学关注的意义远远超乎文学本身,是关乎全人类的。这个遥远的隐性“他者”激励着他的想像,对它,他是“景仰、崇敬、惊叹”的!
我们看到这部作品中“显性”与“隐性”他者的双重书写实为文献式中国形象与想像式中国形象的双重书写。这双重书写既体现了赛义德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所针对的东方主义,也反映了“另一种东方主义”。这双重书写是20世纪初期的文学对西方殖民主义合理性的建构与解构。它体现在大量二元对立关系的表述中:军人/文人,欧洲/中国,殖民意识/救世良知,丑化/美化,空间/时间,现实/梦幻,切近/遥远,灰白/彩色等。正如托多罗夫所说,绿蒂的作品中“可能更有喻世意义的是,异国情调可以与殖民主义如此容易地并存,而二者的意图却如此对立:一个赞颂异域,一个贬抑异域”[19]。这种悖论式的双重关系体现着作者难以排解的内在矛盾。他既是文人又是军人,他游移的视角决定了他与中国这个“他者”之间特殊的关系:认同或疏离。“这也就涉及到通过价值判断的两种相对主义(是我们优越于他者;还是他者优越于我们)。”[20] 当他对自己的文明感到充分自信时,那么“他者”的形象就变得低劣、丑陋、邪恶;当他对自己的文明产生怀疑时,那么“他者”的形象就得以美化,成为西方文明自我批判与超越的标尺。显性“他者”与隐性“他者”形象是作品中自我抵牾的一个悖论。一个生发于社会历史现实层面,反映出20世纪初期西方看待“他者”东方的一种殖民心理;一个孕育于人类文化精神层面,反衬出西方对东方“他者”可望不可即的一种民族心理积淀。易言之,这种双重书写是西方主体内在矛盾的一种外现,也是西方企图借助东方人文进行自我救赎的一种反映,它昭示着西方已对现代文明精神实质进行反思的开始。因此,随着20世纪初期“东方热”的再度高涨,抑“显性”他者、扬“隐性”他者的书写是必然的趋势。而克罗岱尔、谢阁兰、圣·琼—佩斯、佩雷菲特、雷米等人无不是在以各自的方式拓展或继续着绿蒂对“隐性”他者形象的表述。这种双重书写可以说是20世纪初中国形象书写起承转合的一个契合点。
[收稿日期]2006—11—16
注释:
① 这两部小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由徐霞村和黎烈文介绍到中国,后有戈沙于1980年重译《冰岛渔夫》,更使之在我国广为流传。
② 这部作品曾由我国现代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翻译,译文连载于1930年至1931年间的《前锋月刊》上,后更名为《在帝都——八国联军罪行记录》,1989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③ 本文所引《在北京最后的日子》版本,见文后参考文献[2]。以下均只注出页码。
④ 托多罗夫在《我们与他者》一书中曾就“我们”与“他者”之间的相异关系提出两个法则:其一为“荷马(Homère)法则”,这一法则基于公元1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本(Strabon)的一个说法,他认为对于荷马,最遥远的国度是最美好的,因此这个法则指“他者”距离“我们”越遥远就越易被美化;其二为“希罗多德(Hèrodote)法则”,根据这一法则,“我们”始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他者”距离“我们”越遥远就越易被丑化。
标签:东方主义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他者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殖民扩张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