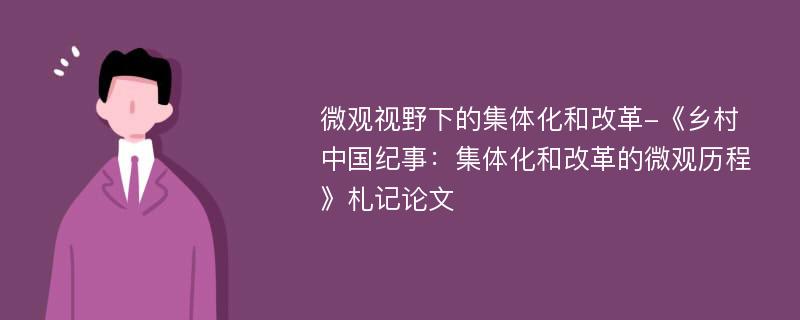
微观视野下的集体化和改革
——《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札记
罗 静
(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太原030006)
摘 要: 《乡村中国纪事》一书从微观的角度探究中国农民在集体化时期的行为模式,以原始的资料为依托考察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将农民的“异动”模式归纳为“正义的抵抗”与“正当的抵抗”,国家也在这之中逐渐重视农民的态度;外加的政治参与制度与内嵌的社会纽带、惯性共同形塑着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对农民经济行为、政治行为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李怀印将集体化时期的中国农村以一种微观的、发展的、连续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揭示了国家与乡村的互动和农民行为动机的复杂性。
关键词: 乡村;集体化;改革
《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从微观史的视角探究集体化各改革时期中共乡村的社会经济变化,重点考察位于长江中下游江苏中部下河地区“秦村”的历史变迁,尤其是从所折射的中国农民在不同制度机制下的动机和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李怀远先生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乡村中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国家和乡村的关系、基层干部与村民的关系、集体化时期的经济激励与农业效率的问题这几个方面。
一、国家与乡村的关系
书中论述群众在20 世纪50年代农民对于集体化的抵抗,以秦村为例来揭示出了两种基本农业抗争模式,即所谓的“正义的抵抗”与“正当的抵抗”。以往对于集体化时期的研究大多认为农民对于国家的农业政策是顺从的,对于国家强硬的集体化要求被动地接受。但事实是,由于集体化的速率太快,农民的收入下降、干部腐败和合作社经济管理紊乱引起诸多不满,农民开始对集体化进行抵抗。“正义的抵抗”是指农民以其固有的价值观和共同认知为基础,并根植于他们的是非观、集体记忆、民间宗教信仰、传说或者是社会习俗之中,他们认为自己的抵抗行为是符合道德和正义的。在对50年代早期粮食“统购通宵”运动中,村民们通过使用这一“正义”行为的模式进行反抗,有的少报收入、隐藏粮食、贿赂干部来降低粮食征购指标、更有甚者痛打和咒骂干部,村民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符合道德和正义的。在50年代对于集体化的抵制中,农民抗争的新手段与诉求是“正当的抵抗”,即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确立起对农村的控制,农民们开始使用政府本身推行的意识形态和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利用官方媒体中学到的语言以及政府允许的途径,将行动合理化、合法化。而这大多是村庄中的精英阶层,他们不公开挑战国家制定的各项政策和制度,而是集中攻击滥用权力的地方干部。
周海珠等研究者针对国内首家三星级绿色建筑运行标识酒店营运阶段碳足迹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论显示绿色酒店较普通酒店碳排放降低了35.63%,客,酒店客人人均碳排放强度为48.76 kgCO2/(p·a),空调碳排放和照明碳排放是降低酒店能耗与碳排放的关键,为酒店的低能耗与低碳运营提供了量化的参考依据[4]。
中国农民对国家从“正义的抵抗”至“正当的抵抗”,这种持久和普遍的的抵制压力,使国家不得不最终放弃或者大幅度调整不切实际的措施,政府越来越注重农民的需求。社会主义国家从敌对走向调和,在面对50年代合作化的骚乱中,国家强调使用说服教育而非暴力镇压的方式对待不满的农民,国家自身做了大幅的调整,为了安抚村民,公开责备、批判或者撤换不称职的基层干部,并出台一系列的农村政策,以改进合作社财务管理、集体收入分配、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以及基层干部与普通村民关系等问题。国家对农民抵抗行为变现出的新反应揭示出村民在形塑国家队农村政策的最终形态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促使国家在集体化时期不断调整农业政策的实用主义取向的延续。
二、基层干部与村民的关系
基层干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在李怀印的笔下也远比传统意义上的“统治—屈从”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更加丰富和复杂。中共在基层政权的建设中,通过正式的政府体制向乡村急剧扩张,新的价值观念在农村蔓延,对乡村的权力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外加的制度和观念,与农民自身内部固有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相互作用,不仅对于精英阶层的行为有强化作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制约作用。所以,农民群体中内生的惯例和观念,加上外设的正式制度和话语体系,决定了农民表达意愿以及与干部互动的方式。
现状柴米河两侧堤防顶宽及顶高程不足,局部顶宽仅1 m,顶高程低于设计防洪水位,难以抵御柴米河上游20年一遇来水。
翻转课堂主要以知识的传授与知识内化的颠倒为主要的价值理念和核心要求,有效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桎梏。其中传统的教学过程只关注教学课堂知识的讲授,知识内化则侧重于学生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学生需要通过课后练习和反思的形式来完成老师所布置的任务。在翻转课堂之中老师知识的传授与学生知识的内化实现了有效的颠覆,学生可以直接结合个人的学习情况,在课后通过信息技术的有效应用来完成老师所布置的任务,知识传授直接可以在课后完成。
1)液化石油气的特性:液态密度:580kg/m3;气态密度:2.35kg/m3;气态相对密度:1.686;引燃温度:426~537℃;爆炸上限:[V(能发生爆炸的气体体积)/V(含有能爆炸气体的气体混合物总体积)]:9.5%;爆炸下限:V/V:1.5%;燃烧值:45.22~50.23MJ/kg。
三、经济激励与农业效率的关系
本书揭示生产队成员对集体生产所采用的实际策略,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的性别、个人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特定阶段、派活机会的多少、在群体中的角色,尤其是生产队长的管理能力。传统的学者将集体化时期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的原因归结于国家的过度抽取和过密化,但集体化时代的团体劳动并不像传统学者认为的缺乏效率,在工分制下个人劳动与收入相联系,生产队长的管理策略等集体农业的逻辑,共同解释了为何中国农村集体生产的效率并没有普遍认为的那么低。整个集体化时代的农业,总体上能够维持必要的生产效率,从而不仅能够快速扩张人口,增加预期寿命,还能满足国家获取农村剩余的需要。
本文对家庭周期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每个农户在家庭周期的不同阶段其劳动者与被赡养者之间的比率发生变化,而造成不同农户间的收入差距。质言之,中国集体化组织内的农户贫富差别主要是“人口分化”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分化导致的。起始家庭由于家庭规模较小,夫妻身体强壮,生产者与赡养者的比率基本平衡,或稍稍有利;成长家庭中父母是主要劳力,子女多未成年,所挣得工分不足以抵消实物分配,一般赊欠集体的债务最多,往往是集体中最穷的;成熟家庭的优势在于劳力众多,这类农户的生产者与被赡养者比率最高;老化家庭仍具有劳动者和消费者的比率优势,可从已婚分家的儿子那里得到工分补贴,人均劳动日和现金收入仅次于成熟家庭。后来,由于政府生育政策和劳动报酬政策的改变,家庭周期的规律在20 世纪70年代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并进而影响了处于不同周期阶段的农户的经济状况。
在集体化完成时,基层干部数目庞大,如何将基层干部纳入有效控制之下,成为党与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依靠少数的国家干部对巨大的基层干部进行自上而下的监督显得不切实际,国家采纳的是所谓“群众路线”,即依靠农村集体组织的普遍成员自下而上地加以监督。从20 世纪60年代初到集体化时期结束,中央控制基层干部的方式共有三种:其一,经常性的反贪污、反渎职的政治运动;其二,“人民来信”,村民向上级揭露基层干部的恶行;其三,让群众参与生产队日常的“民主理财”。整个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不断承受来自上下级的压力,外加的政治参与制度与内嵌的社会纽带、惯性共同形塑者基层干部和普通村民之间的关系。
例如,20 世纪70年代计时制与计件制在秦村实施,两种不同的劳动报酬制度会在不同的情况下对社员劳动效率产生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在计件制下,村民们无疑想增加自己的收入,多劳多得。但如果干部疏忽了自己在监督、验收、记功的责任,就会导致社员只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另一方面,计时制如果应用到适当的农活上,干部在劳动管理上方法得当,也不一定会导致效率低下。这里李怀印提到的是,即使国家政策和劳动报酬制度对农民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但是这种生产队内部无形的规则、观念对农民个人行为的选择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他强调了集体组织内部非正式的行为准则、惯例和认知,而非外在的政策、制度在规范农民的日常劳动行为中起到的作用。
四、发展的连续性与微观视角
中国集体化时代农业产出的稳步增加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相应提高,但是,劳动生产率低不意味着经济或者社会没有发展,实际上,集体化时代农业生产的生态、技术条件以及农村居民的生活标准皆有引入注目的改善。中国乡村各地的集体组织利用大量的劳力建设防洪和灌溉工程,从根本上改造了农业的自然环境,同时绿色革命将一些新品种、新的农业技术引入乡村社会。
集体化时代的发生的改变为1980年之后乡村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改革时期农户收入增长的原因,不单单是农民更高的农业生产积极性,也不仅仅是由于家庭产出的增加,而主要在于国家放松并最终取消了控制农村资源的各项措施。集体化时期与改革时期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动力的背后,是农村经济在集体化与改革两个时期之间的连续性,改革时代乡村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由于此前集体经济为农民家庭提供了稳固的技术、生态基础,而且还因为国家放松并最终废除了集体化时代约束经济增长的抽取方式。与以往研究中将集体化与改革时代两种不同的农业制度对立的观点相反,李怀印强调与突出的是这两个时期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连续性。
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皆有其特有的时代性,但是如果过分强调时代的断裂性,历史研究就失去了鉴知古今的意义,模糊了整个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历史的延续与贯通也被人为地断裂了,虽然可以将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特征加以总结归纳,但是历史延续性背后的变迁才是能真正全面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
《乡村中国纪事》对乡村共同体中作为个人和团体的村民做微观层次的分析,本书将研究的重点转向村民个体,即在正式制度与当地固有的非正式制度共存与互动的历史背景下,观察村民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以江苏省东台市秦村为研究对象,借助秦村的原始资料来研究集体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与农民行为。以往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出发,多关注在正式制度之下的农民行为,容易陷入官方设定好的框架,而李怀印以微观的视角和丰富的档案资料分析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下农民的行为动机,让我们在微观层面更直观地看到集体化时期农民行为及其动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参考文献:
[1]陈耀煌.李怀印两本中国农村史研究的商榷[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0,(70):223-229.
[2]李金铮.问题意识: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解释[J].晋阳学刊,2011,(1):13-21.
[3]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4]辛逸.历史学家集体化的诉说——《乡村中国纪事》札记[J].中共党史研究,2014,(11):12.
[5]陈靖.集体化时期研究的微观视角及方法——读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97-200.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1X(2019)31-0038-02
收稿日期: 2019-06-28
作者简介: 罗静(1994-),女,山西交城人,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 吴高君]
标签:乡村论文; 集体化论文; 改革论文;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