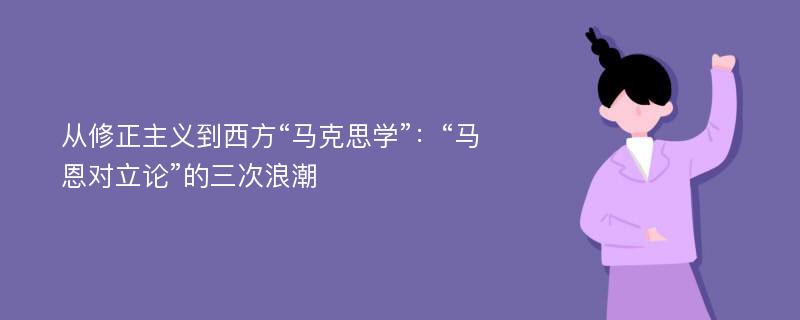
[摘 要]“马恩对立论”是西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研究中的一种代表性观点。这一观点虽由西方“马克思学”于20世纪60年代正式提出,但其思想源头却可追溯到修正主义诞生之时。自伯恩施坦以降,“马恩对立论”在其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形成了三次浪潮,第一次肇始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挑战,中经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攻击,最终鼎盛于西方“马克思学”炮制的“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断。这三次浪潮虽然都打着理论纠偏的旗号,但无一例外都隐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内核。系统梳理三次浪潮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其遭受或政治、或学理的批判与辩护,有助于认清“马恩对立论”的思想实质,更好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关键词]马恩对立论;三次浪潮;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
历史地看,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存在差异或不一致的观点由来已久,攻击他们相互对立的“小品文”也在历史上“交替出现”。1883年,恩格斯在致伯恩施坦的信中提到,“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它们与“马克思把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1](p13-14)。马克思逝世后,这种说法更是甚嚣尘上,甚至越来越呈现出把二者对立起来的倾向。尽管恩格斯多次声称自己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一致”[2](p232),但这并没有堵住“悠悠众口”,反而引发了大量质疑“自然辩证法”甚至反对他的声音。按照西方“马克思学”代表人物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集中出现过两次反对恩格斯、制造“马恩对立”的理论浪潮,第一次出现在恩格斯逝世后到1914年,第二次出现在 1923 到1939年[3](p34-35)。事实上除了以上两次,还有第三次浪潮,这就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以莱文自己和法国学者吕贝尔为代表的更为全面彻底的“西方马克思学的挑战”[4]。这三次浪潮都打着反对恩格斯的旗号,蓄意炮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对立甚至互相反对的言论,以达到分裂甚至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
实验组中护理满意度为不满意、满意、很满意的患者分别为1例、3例、38例,护理满意度为97.62%,对照组中护理满意度为不满意、满意、很满意的患者分别为8例、10例、24例,护理满意度为80.95%,实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护理满意度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一、第一次浪潮: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挑战
1883年马克思逝世以后,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恩格斯肩负起了整理出版马克思文献遗产和阐释马克思哲学的重任,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的未竟事业当中,并接连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至死都没完成)等著作。这些理论工作,无疑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发展和系统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却也引发了不少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异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不一致”甚至“对立”的声音开始在欧洲各社会民主党内部出现。恩格斯在世时,这些异议尚且能够得到有效的遏制和针锋相对的批判;恩格斯逝世之后,这些异议很快便发展为反对恩格斯,进而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理论浪潮。
第一次浪潮主要由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代表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和施米特(Conrad Schmidt)掀起,但最早对恩格斯直接发难的“小品文”却并非来自他们。最早的质疑来自恩格斯逝世两年后的1897年,由J.斯特恩完成的《经济的和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一文首先提出了两种唯物主义的区分——经济的唯物主义和哲学的唯物主义,指出前者是立足于社会的和经济的生活形态的一种“历史的学说”,后者是从物质概念出发的“一元论”的一种形式,并且直指“马克思是一位经济上的唯物主义者,而不是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者”[3](p37)。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创造者不是别人,正是恩格斯。
显然,伯恩施坦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这种看法。在他看来,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行不通的,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也都是不可能的。他反对把唯物主义和物理学搅在一起,反对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等同起来,认为那样会削弱意识、观念等精神要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至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研究的批判分析方法,与康德的认识论原理是一致的。因此,他站在新康德主义的立场上抬高理想、道德、信念等精神要素的作用,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主张用新康德主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他公开声称“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5](p335)。这里说的“传统教义”,指的就是被他称作“神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一种对早期宗教形而上学的修正,而恩格斯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没有上帝的加尔文派教徒”[3](p39)。在他那本被称为“修正主义圣经”的《前提和任务》的序言中,伯恩施坦更是公开承认了自己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意图:之所以写作本书就是为了向人们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5](p106-107)。
胡四一:水资源“三条红线”指标体系的确定充分考虑了区域的水资源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用水需求,同时还要考虑到它的区域差异性,既要体现对落后地区加大节约和保护力度的压力,又要对先进的地区提出激励措施。具体考核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二次浪潮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在俄国取得了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的革命却相继以失败告终。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下子同时发生”[12](p539),相反却导致了纳粹法西斯主义的上台。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的俄国而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没有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崩溃反而在继续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出现历史曲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怎样探索适合自身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些问题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正确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做出科学解答。这一时期一批重要著作如《自然辩证法》(1925)、《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927)、《德意志意识形态》(1932)、《巴黎手稿》(1932)以及其他大量手稿、书信的问世给重新检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探索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此,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反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机械决定论的立场上,强调阶级意识和文化领导权等上层建筑的历史作用,同时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对立起来,主张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本真精神。
这一时期,除了有来自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攻击,还有来自俄国民粹派、黑格尔派和马赫主义者的轮番挑战。1907年,俄国民粹派分子维克多·切尔诺夫在《马克思主义和先验哲学》一文里,“一开始就企图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起来,谴责恩格斯的学说是‘朴素的独断的唯物主义’,是最粗陋的唯物的独断主义”[8](p19)。1910年,波兰学者斯·布尔楚维斯基完成了堪称“系统反对恩格斯的第一本专著”[9]——《反恩格斯论》,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指责恩格斯并非是马克思理论的继承者而是背叛者,提出《反杜林论》中贯穿的“实证主义”倾向与马克思坚持的“人本主义”立场存在着根本对立。在《唯物主义史话》一书中,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Bendetto Croce)坚持认为马恩之间的关系“仅仅限于私交,在理论上是根本对立的”[10]。鲁道夫·蒙多尔福(Rudolfo Mondolfo)于1912年完成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更是在哲学观点上详细论述了马恩之间的重大分歧。此外,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波格丹诺夫也抛弃了他早年坚持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接受了马赫主义的经验要素论和不可知论,鼓吹恩格斯的辩证法学说早已过时,企图模糊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感觉论的界限,从而事实上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马赫主义者。
想到他们自己也在卖假货,老道就趁着没什么客人,教了教王祥分辨假货的打发时间。刚好现成的假货有的是,老道随手就从摊铺上拿起一个玉佩:
可以看出,第二次浪潮不再像第一次浪潮那样主要借助于新康德主义、达尔文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社会思潮从外部攻击马克思主义,突出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而是试图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异中寻找反对自然辩证法的依据,从内部破坏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而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由于其哲学层面的探讨相对较深,影响也比第一次更加深远。不过,与第一次浪潮的结局一样,第二次浪潮也随着斯大林主义的胜利而被打得粉碎。1924年,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说,高度肯定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理论意义,这也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地位得到了巩固。正像政治上的莫斯科路线被第三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坚决贯彻一样,哲学上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也为西欧各国共产党所效仿。但政治上的胜利毕竟不能带来哲学上的胜利,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广泛影响并没有被很好地清理,这也为后来西方“马克思学”再次掀起“马恩对立论”浪潮留下了学理空间。
1900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随着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控制了第二国际,政治上的胜利也保证了哲学上的胜利,辩证唯物主义在第二国际内的统治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虽然后来第二国际的内部矛盾日趋激化,修正主义集团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篡夺了领导权,马恩对立的声音也日益高涨。但直到第二国际破产之前,修正主义者攻击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意图始终受到比较及时和坚决的批判。并且,随着第二国际被列宁开创第三国际所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路线得到了彻底贯彻,恩格斯不同于马克思的声音也暂时归于沉寂。
二、第二次浪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辩证法的责难
作为他的亲密战友,康拉德∙施米特紧随着伯恩施坦对科学形而上学展开攻击,甚至竭力为伯恩施坦遭受的来自社会民主党内部正统派的批判而辩护。1899年继伯恩施坦发表“异端邪说”[6](p16)之后,施米特同样抛出惊人言论,提出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要以“进化”一词代替“辩证法”一词。因为对工人而言,“‘进化’概念是更明白易懂的”[7](p33)。在伯恩施坦和施米特那里,社会进化代替了物理过程,社会群体和物种改善代替了物质和运动。由此可知,19世纪末的进化论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冲击可见一斑。但伯恩施坦显然比施米特更直接、更彻底,他由此把矛头对准了恩格斯,认为恩格斯并非总是“马克思的准确解释者”,指出“有时恩格斯没有准确地解释马克思的理论”“恩格斯在这里的阐述与我们所知的马克思的说法不相符”[3](p38)。可以说,正是这些“不相符”“错误”“自相矛盾”为伯恩施坦、施米特等修正主义者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举起修正主义大旗、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找到了依据。
由上可见,在轻罪与重罪划分标准方面的主要争议就在于,到底是以犯罪本身的严重程度来划分,还是以犯罪所适用刑罚的轻重来划分,抑或二者兼顾?只有先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对轻罪范围的划定才能顺利展开。
在第一次浪潮中,伯恩施坦、施米特等人的攻击受到了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等强有力的回击。考茨基反对伯恩施坦把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关的内容渗入马克思主义之中,批判了伯恩施坦在《前提和任务》中对辩证法的责难,强调了自然界中对立面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斗争应用于阶级斗争之中的必要性。普列汉诺夫紧跟考茨基的批判脚步,他以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为阵地,分两条战线同新康德主义和生机论派论战。《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康拉德·施米特》和《唯物主义与康德主义》是为反对新康德主义而作,《战斗唯物主义》是为反对生机论派而写,它们“促使了对恩格斯的唯物主义的相信成为第二国际的一条信仰原则”[3](p51)。列宁同样遵循着普列汉诺夫的路线,在1898年写下了《施米特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文,批判了施米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又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著作中,坚决捍卫了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揭露了伯恩施坦等机会主义者试图“用‘简单的’(和平静的)‘演进’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11](p13)的企图。
在其成名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Ceorg Lukacs)首先对“自然辩证法”概念进行了攻击和责难。他批评《反杜林论》没有正确理解“辩证法”的概念,甚至都没提到“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法关系”[13](p50)。在他看来,这显然是与马克思在《提纲》中反复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思想相违背的。卢卡奇甚至觉得,恩格斯《反杜林论》中的论断影响了整个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而欧洲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忽视革命主体的作用,导致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丧失。对于恩格斯的“错误”,卢卡奇最终归结为,恩格斯盲目遵循了黑格尔的指引,把辩证法应用于自然领域,创造出与历史辩证法相对立的自然辩证法,从而使马克思的整个哲学有了“缺陷”。因此,必须认识到历史辩证法是辩证法的核心,而“恩格斯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扩大到自然界”[13](p51),毫无疑问是一种非法挪用。尽管在1967年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放弃了把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对立起来的观点并且对此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以及在后来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已经把辩证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根据”[14](p181),但后人却无视这段“重新定位”,仍然抱着“卢卡奇已经抛弃的错误观点”[15]不放。
西方“马克思学”公开宣称,他们要以中立、客观、科学的立场,超越意识形态的纷争,还原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来面目,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位。尽管这种纯学术性和超越意识形态性的口号为他们赢得了许多赞誉,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大量引进、翻译、出版了西方“马克思学”的著作,但是他们公开散布“两种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意图却是不证自明的。
如果说科尔施反对自然辩证法,是因为它无法满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需要;那么葛兰西(Gramsci Antonio)反对自然辩证法,则是因为它与“实践哲学”的核心原则相违背。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的核心在于实现了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历史观与经济物质观的完美结合,而不像辩证唯物主义那样把一切变化都归结为外部的、物质的、客观的因素。因此,葛兰西同样对辩证唯物主义持拒斥态度,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但他并没有像科尔施一样直接批判列宁,而是把矛头对准了在哲学立场上与列宁极为相似的布哈林,指责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宣扬哲学唯物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描绘为一种进化论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他强调,仅仅就“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复合词汇而言,关注的重点应该是“历史”,而并非“具有形而上学根源的第二个词”[17](p538)。正因为存在这种思想,也就不难理解葛兰西会在其著作中一再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在政治行动中的重要性。
虽然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并没有公开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但他们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定位以及用历史辩证法反对自然辩证法的立场,事实上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断言马克思恩格斯对立开了一个思想源头。遵循着他们这一思想路线,列裴伏尔(Henri Lefebvre)反问道:“如果辩证法来源于自然界,那么它怎么能是革命的呢?”[18](p184)施密特(Alfred Schmidt)提出:“离开人的自然界本身就是虚无,辩证法不是自然界的永恒规律,它只属于人的现实,人的活动和认识。”[18](p179)布洛赫(Ernst Bloch)认为,辩证法只存在于由人所创造的世界,表现于人的主客体关系之中[19](p469)。
两组盐岩试验所得到的单轴压缩全应力—应变曲线(图5),分别通过横纵两个方向对图5进行分析对比,可分别得到饱和卤水处理和是否含有夹层两个方面对试验曲线的影响。
三、第三次浪潮: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主义合法性的攻击
在这次浪潮中,创造“马克思学”这一术语的法国学者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充当了助推“马恩对立论”的旗手,他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基于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文献学考察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批判性反思,吕贝尔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思想方法的原初产物,而是由恩格斯构想出来的”[21](p17)。为此,马克思不需要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的问题负责,真正需要负责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恩格斯。就如同1957年联邦德国学者伊林·费切尔(Iring Fetscher)在《从无产阶级哲学到无产阶级世界观》一文中指出的,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事实上破坏了马克思一直以来强调的阶级自觉和阶级行动的统一,并最终使之蜕变为僵化的官方意识形态[22](p148-181)。由此,吕贝尔提出承袭恩格斯路线的苏联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不可靠的,必须在中立客观的基础上重新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1970年,著名的《反恩格斯提纲》被吕贝尔提出后,国际上立即吹响了喧嚣一时的批判恩格斯、制造“马恩对立”、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集结号”。随着此次浪潮的发酵,“马克思学”的中心也从德法转移到了原先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发达的英美。
几乎与卢卡奇同时,科尔施(Karl Korsc)发表了同样激起强烈反对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虽然科尔施并没有过分强调马恩之间的对立,但还是指出了二者思想存在不可忽视的重大差别。他提出,“后期的恩格斯完全堕入了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之中,而不同于马克思——他的更富于哲学家气质的文友”[16](p50)。在他看来,这显然与马克思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适合于无产阶级政治需要的社会革命的理论路线是大相径庭的。正因为如此,科尔施坚决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路线的继承者——列宁。他对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持高度批判的态度,认为它“来源于一种绝对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学存在观”[16](p82)。在这一点上,潘涅库克与科尔施持有相同的立场。在《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一书中,潘涅库克同样大肆讽刺了列宁,并把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看成是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典型,深入探讨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科学的分离。
第三次浪潮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由吕贝尔、李希特海姆、莱文等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掀起。这一时期,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余波还未消散,并且愈益展现出跟恩格斯联系起来的倾向;横贯东西方冷战帷幕下的意识形态交锋愈演愈烈,促使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成为双方的焦点。掩盖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下的社会问题屡屡涌现,不断激起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呼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马克思学”从书斋式的学院派一跃成为引人注目的国际显学,甚至连一向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的苏联学界都不得不出来回应,以争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20]。
2016年,为了有针对性地了解宁夏图书馆持卡读者的基本特征及阅读习惯,更好地开展读者服务,宁夏图书馆特面向广大持卡读者开展问卷调查。调查时间为2016年11月15日~11月25日,采取随机发放纸质调查问卷200份。经过10天的随机调查,回收182份,去除无效问卷9份,实际有效问卷173份,问卷有效率为86.5%。
在英国,1961年历史学家李希特海姆(George Lichtheim)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一书中以恩格斯草拟的《共产党宣言》草稿同马克思定稿的《共产党宣言》进行对比分析,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在所有领域上都存在差异的结论。相较而言,恩格斯对“工业革命”的青睐使得他具有比马克思更浓厚的技术决定论色彩,而《宣言》更强调工业革命的灾难性后果,更多地关注人性的实现和提升[23](p58-60)。由此,他提出,“恩格斯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决定论者和实证论者”[24]。受此影响,流亡到英国的波兰学者科拉克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在197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主流》三卷本中同样大肆书写马恩之间的对立,并且受到西方学界的追捧。与他们相比,恩格斯研究学者、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似乎是一位温和的隐蔽的马恩对立论者。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卡弗一共出版了三本有关恩格斯的研究著作:《恩格斯》《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与思想》。不过他既没有明确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致性,也没有绝对“宣扬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峙”[25],而是在解释学视域中理解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错误阐释和对马克思思想的背离,特别是多次提及马克思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表示出的冷淡态度,指出恩格斯“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内部关联、矛盾及反映诸范畴强加于马克思的著作,将其重新解释为马克思主义的而非马克思的著作”[26](p109),无疑限定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在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就质疑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对把辩证法从社会历史领域扩展到自然领域[27](p330-331),显然这也为后来的美国“马克思学”学者所继承。到了诺曼·莱文时期,“马恩对立论”发展到顶峰,他本人更堪称是将“马恩对立论”全面化、体系化的第一人。莱文抛出两种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的对峙,坚持认为“恩格斯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矮化”[28],竭尽所能想要证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对立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全面的。从《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1975)、《辩证法内部对话》(1984)到《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2006)、《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对话》(2012),莱文详细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多方面对立,归结下来有以下四点:一是哲学素养不同——理性激进主义和道德激进主义;二是哲学基础不同——以人为中心的左翼黑格尔主义和以物质为中心的右翼黑格尔主义;三是哲学理论不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四是社会发展理论不同——社会发展多线论和单线论。正因为存在上述对立面,恩格斯也被莱文称作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3](p2),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被认为是“可悲的欺骗”。
有意思的是,虽然西方“马克思学”掀起的第三次“马恩对立论”浪潮由于其哲学层面精深的学理讨论,一度成为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问题,影响十分深远,但最终却“走向了一个自我否定的过程——从‘马恩对立论’走向‘马恩同质论’”[29],遭到了包括美国学者阿尔温·古德纳尔(《两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矛盾和异例》)、J.D.亨利(《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活及思想》)以及英国学者S.H.利各比(《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在内的西方马克思学内部的学理反击,重新确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上的一致性,这显然不同于第一次、第二次浪潮中“一致论”的拥护者们立足于政治批判基础上的情感愤怒和道德谴责。西方“马克思学”本想以中立、客观、科学的立场去评判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却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恩格斯、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老路。如果说前两次浪潮只是“马恩对立论”的酝酿和发酵,那么到了第三次浪潮时,“马恩对立论”事实上已经系统化、成型化,并且也正是在第三次浪潮遭到的学理批判中开始走向消亡。
四、结语
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挑战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再到西方“马克思学”的攻击,“马恩对立论”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演变历程。无论是第一次浪潮中首次发出马恩“不一致”的声音,还是第二次浪潮中着力探寻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差异,抑或是第三次浪潮中公开制造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面对立,它们的意图都是一致的:通过攻击恩格斯晚年特别是自然辩证法,制造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意图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以达到分裂甚至消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虽然每一次浪潮都毫无例外会遭到或政治、或学理的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其一再抬头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关系?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像已经饱受批判的“马恩对立论”那样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之间重大差别或者根本对立,否则不仅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亲密战友的否定,也是对他们彼此合作长达40年之久、被列宁誉为“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30](p85)的友谊的否定。同样,也不能由此滑向另一个极端,抱持“马恩同质论”,否认他们之间的差异或不一致。应该说,这种差异或者不一致的存在,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科学的。因为就算是一个人,其思想也会随着社会状况的改变、个人思考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变化,所谓马克思之青年、成熟、晚年的区分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因而,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正确的看法是既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本质上的一致性,同时又不否认他们存在某些具体观点上的差异;既肯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继承,同时又不否认恩格斯晚年基于发展的基础上做了某些具体观点的修正;既肯定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第一小提琴手”的伟大作用,同时又不否认恩格斯对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巨大贡献。这看似是一种折中,但又何尝不是我们今天所应秉持的正确态度?恰如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一书中提出的,“除了全盘接受和全盘否定之外,我们至少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持另一种态度”[31](p11)。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美]诺曼·莱文.辩证法的内部对话[M].张翼星,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4]黄楠森.《辩证法内部对话》序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5]殷叙彝.伯恩施坦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舒贻上,等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65.
[7][英]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8]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余品华.国外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J].求索,1986(1).
[10]王凤才,袁芃.MEGA2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J].探索与争鸣,2016(2).
[11]列宁全集(第1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14][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M].白锡堃,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5]马拥军.“马恩对立论”之根源何在[J].学术月刊,2013,45(03).
[16][德]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17][意]葛兰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8][苏]I.B.H.别索诺夫.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M].德礼,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19][德]布洛赫.主体—客体:对黑格尔的解释[M].柏林:韦尔莱出版公司,1951.
[20]张亮.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传统分期模式的形成及其评价[J].理论探讨,2005(2).
[21]Maximilien Rubel.Rubel On Karl Marx:Five Essay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22]Iring Fetscher.Marx and Marxism[C].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1.
[23]George Lichtheim.Marxism:an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24][美]J.D.亨勒,黄文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一致性[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3).
[25]吴家华.“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基本观点与研究新进路[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4).
[26][英]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M].姜海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7][美]悉尼·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M].徐崇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28][美]诺曼·莱文,张亮.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学”——诺曼·莱文教授访谈录[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6(6).
[29]文浩.历史辩证法视域中的恩格斯——“马恩对立论”百年回望与当代思索[J].南京大学学报,2005,42(1).
[30]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美]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M].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8.003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8-0019-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视域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研究”(16ZZD048)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袁文华(1992—),男,湖北阳新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谢倩(1993—),女,湖北恩施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
